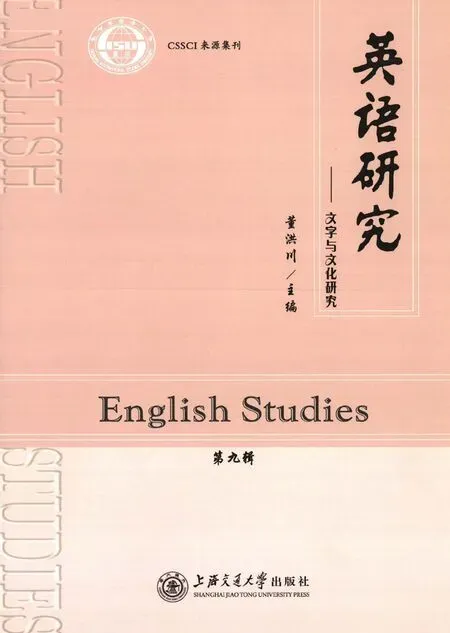女性跨文化书写的叙事学研究
——以中国叙事为例
龙 丹
(四川外国语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重庆 400031)
0.引言
女性跨文化书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女性叙事,女性通过游记、传记、小说、报道等书写异国体验或想象,向本国读者讲述他者的故事,借他山之石攻玉,建构女性主体。莫妮卡·弗卢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2007:262)在《认同/他性》一文中强调跨文化书写对身份认同的建构作用:讲述他人的生活与讲述自我一样是建构自我的方式。通过再现他者,作者“在认同与差异交替发生中对我和他者关系的重新认识与重新建构”(Fludernik,2007:261)。女作家如何在跨文化体验和跨文化书写中建构自我?现实的越界如何在叙事中表现出来?本文运用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奠基人苏珊·S.兰瑟(Susan S. Lanser)等学者所提出的女性叙事学阐释方法,以20世纪上半叶书写中国的白人女作家为研究对象,分析女性跨文化书写的叙事学特征,并阐释这些叙事策略对建构女性主体所起到的作用。
兰瑟在1986年发表的《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TowardaFeministNarratology)中以《埃特金森的匣子》(Atkinson’sCasket, 1832)为例,提出从叙事学角度研究女性文本的结构特征,弥补以意识形态批评为主的女性主义批评的缺陷;同时通过研究女性文本以丰富叙事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从女性主义角度重新定义叙事学,弥补结构主义叙事学以白人男性文本为主的单一性。兰瑟重新定义叙事学术语,以便更好地阐释女性主义文本,包括叙事声音(narrative voice)、叙事模式(narrative level)和情节(plot)等。
1.半私下型叙述模式
兰瑟提出公开性叙述(public narration)和私下型叙述(private narration)两种叙述模式,“公开型叙述是指叙述者对处于故事外的受述者(读者)讲故事,私下型叙述指的是对故事内的某个受述者(人物)进行叙述”(申丹,2004a:4)。兰瑟还提出“半私下的叙述行为”:“叙述是私下的,但除了其标示的受述者,还意在同时被另一个人阅读。”(Lanser, 1986:353)申丹教授认为“兰瑟将叙述模式与社会身份相结合,关注性别化的作者权威,着力探讨女作家如何套用、批判、抵制、颠覆男性权威,如何建构自我权威”(申丹,2004a:6)。历史上女性通常以信件、日记等私下型叙述的形式书写,其表面的书写意图似乎并不是为了发表,因此不会挑战男性的话语权威,更加不会颠覆社会不允许女性公开发表言论的性别规约。这种表面私下型的叙述一经出版却得到更多人阅读,在表面遵循男性权威的掩饰下暗中颠覆,反映了女性与男性权力和话语之间的协商。
女性跨文化书写在两个方面“越界”进而挑战男性权威:第一、女性书写主体跨越种族和国家的疆界,颠覆了“女性合适的位置在家里”这一传统性别规约,她们不仅拒绝做“闺中的天使”,而且闯入他者世界,冒着“玷污”白人血统的危险。当白人单身女子项美丽独自穿行在非洲大陆时,陌生的白人男性愤怒地问道:“夫人,你的丈夫呢?”(Kuthbertson,1998:114)第二、女性公开出版她们的异国见闻,僭越了男性掌控的话语空间。赛珍珠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引起美国男作家的极度愤恨,如福克纳宣称自己不要跟“中国通伯克夫人”(Mrs. Chinahand Buck)相提并论(Lipscomb,1994:104)。福克纳的言语反映了男性对女性书写的否定和鄙视。
在男性虎视眈眈的凝视之下,女作家采取“半私下型叙述”与之协商,表面自觉地占据边缘位置,承认男性权威并向其示弱,暗中建构女性权威。这在女性跨文化书写的书名上可见一斑,如《亨利艾塔·沙克回忆录》(AMemoirofMrs.HerriettaShuck, 1846)、伊娃·简·普莱斯的《中国日记》(ChinaJournal, 1889—1990)、《在远东:玛丽·杰拉尔丁·吉尼斯的中国来信》(IntheFarEast:LettersfromGeraldineGuinessinChina,1901)、《外交官夫人在国外》(ADiplomat’sWifeinManyLands, 1910)、A.S.罗的《我眼中的中国:一个女人的天朝来信》(ChinaasIsawit:AWoman’sLettersfromtheCelestialEmpire, 1910)、美国公使夫人萨拉·派克·康格所著的《中国来信》(LettersfromChina,1909)等。与正统的文学样式如小说、诗歌等不同,女性跨文化书写往往采取日记、回忆录、信件等形式纪录她们的跨文化体验,就连英国19世纪著名的旅行家伊萨贝拉·伯德(Isabella Bird)的中国书写起初也是以书信体的形式出现,在她的《长江流域及其他》(YangtzeRiverandBeyond,1899)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她在公开场合表示自己并不打算出版这些作品,即并非蓄意与男性争夺话语权。女作家们甚至在书名里标注出“第二性”,如“一个女人的来信”“外交官夫人”或者干脆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标题中,表面是在遵循男性话语权威,提醒读者注意这是来自女性的叙事,是女性与家人之间、女性与朋友之间、至多女性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私下型叙述,不企图引起广泛的关注,也不会与男性作家争夺话语权威。但是一经出版,这些作品势必引起其标示的受述者以外的读者关注,因此这些作品“事与愿违”地成为女性对男性话语权威的挑战。
女性作家集中书写他国的女性体验以及内闱生活,将作品呈现为异国姐妹私下向自己吐露的闺房密谈,这是男作家无法进入的女性空间,这样的书写在满足本国读者窥探异域的欲望的同时,建构了一个男性无法匹敌的女性话语权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Pearl S. Buck)的第一部小说《东风·西风》(EastWind:WestWind, 1930)的叙述者是中国妇女桂兰,其标示的受述者是作者本人,桂兰称她为“我的姐妹”。整部小说是桂兰向她的美国好朋友的私下叙述,讲述的自己与新式丈夫的婚姻以及哥哥与他的美国妻子的婚姻。小说开篇指出受述者“我的姐妹”虽然出生在美国,但在中国生活多年,因此能够理解“我”将要讲述的故事:“我所讲都是真的。我称你为我的姐妹。我会告诉你一切”(Buck, 1930:3)。通过强调受述者/作者精通东西方文化的事实以及她因此获得中国妇女的信任,小说开篇就确立了作者赛珍珠的话语权威,这是其他作家所无可比拟的。
《纽约客》专栏作家项美丽(Emily Hahn)作为民国文人邵洵美的美国妾,不仅与中国文人交流,并通过他认识宋美龄,得到独家采访宋氏姐妹的机会,成为唯一获得宋美龄认同的传记作家。她与邵洵美的关系赋予她独特的机会,帮西方读者试图揭开中国家庭的神秘面纱:“我跟着他们(邵洵美)绕到了幕后,通过奇异的脚灯窥视那个旧世界。那样新鲜又奇妙。”(Hahn, 1944:10)项美丽的上海冒险包括鸦片、舞厅、战争等,为西方读者再现奇异的中国,迎合他们的奇异想象,让她成为所谓的中国专家。《纽约时报》这样评论她,项美丽与其他坐在黄包车里面逛上海花园桥的作家不同,她书写自己的亲身体验,善意地观察人与事 (王璞,2005:171)。
美国左翼女性主义作家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的中国书写也有半私下叙述的特征。值得一提的是她与缫丝女工的交流。她们虽然语言不通,但拒绝男翻译在场,通过手势和绘画交流,分享她们拒绝婚姻、罢工等叛逆经历,这是缫丝女工对史沫特莱的私下型叙述。中国革命妇女的故事也是由她们讲述给史沫特莱,然后再由她转述给美国读者,如“妇女起来了”中的中国妇女蔡妈妈要求史沫特莱写信给美国妇女自救会,告诉她们中国妇女的胜利,告诉她们没有牺牲就没有胜利(史沫特莱,1985b:250)。“沈阳五妇”中的中国妇女是叙述者,向史沫特莱讲述她们的故事:“一个小个子中国妇女正在诉说”,或是“一个年轻女教师……坐着讲述”(史沫特莱,1985a:456-457)。史沫特莱把自己比作录音机,在记录中国妇女的故事时尽量客观。当她的作品在美国发表时,她特别要求编辑不要改动文字风格,因为朴素的文字真实再现了中国妇女的生存状态,“请你们别把它改得文绉绉的”(史沫特莱,1985a:3)。史沫特莱强调自己作为旁观者的局限性,她坦承自己只是一个旁观者:“我所写的并非中国革命的精髓。”(Smedley,1976:158),这样并没有让读者质疑她作为叙述者的可靠性,反而增强了她的叙述权威。
兰瑟(2002:5)在《虚构的权威》中指出,文本的实际行为反映了意识形态的张力,而女性声音实际上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采用半私下型叙述的女性跨文化书写彰显了女性书写主体与西方性别规约、男性写作传统以及男性权威之间的对话协商,通过特殊的叙述模式和写作类别,表面遵循男性规范却暗中进行颠覆,从而建构独特的女性叙述权威,让女性发声。
2.多重叙述声音
兰瑟借用巴赫金的复调(polyphony)指女性文本中的多重叙述声音。如《埃特金森的匣子》中包含表层叙述声音(赞扬丈夫和婚姻)、隐含的叙述声音(隔行阅读所展现的对丈夫和婚姻的批判),以及表面文本中通过否定结构对社会普遍存在的婚姻关系进行的揭露和批判①。申丹(2004b:140)指出,女性主义叙事学家结合探讨叙述声音与女性主义政治,研究其社会性质和政治涵义,并探究作者使用某种叙述声音的历史原因。在女性跨文化书写的文本中往往有多种叙述声音,表达书写主体与书写对象之间的跨文化协商与对话,也展现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与交流。
赛珍珠在《大地》(1998a)中采取全知全能的作者型叙述声音,考虑作者的国籍和性别,这部小说是一个美国女性向本国读者讲述中国他者的故事;然而小说常常从中国人的视角再现美国,东、西方声音形成张力。小说主人公王龙见到外国人时不知其是男是女(87);他眼中的外国人蓝眼睛像冰一样……大鼻子像从船舷伸出的船头一样从他的脸颊上凸出来(99)。他看到的基督像更是让他感觉奇怪:一个皮肤白白的人像吊在一个木制的十字架上,这人几乎裸体,只是在生殖器周围盖着一片布,看起来他已经死了(99)。最后这些画着圣像的纸都被王龙的丑妻子阿兰用来纳了鞋底。在赛珍珠之前,美国人脑海里的中国人是男人扎着辫子、女人裹着小脚、嗜杀女婴、吸食鸦片的野蛮无知的东方人②。赛珍珠不仅将他们再现为如邻居一般的正常人,而且通过展现中国人眼中的奇怪的美国人形象向美国读者揭露刻板印象的荒诞滑稽以及促进跨文化交流与理解的重要性。
史沫特莱的复调叙述表现为叙事易妆③的特征。她在数篇文章中采用中国女性自述的方式呈现故事,但作者的声音若隐若现。《中国人的命运》讲述了数位中国女性的故事,其中革命女性张晓红被塑造为理想女性。“献身者”中张晓红是故事的叙述者,讲述了她的出身以及在革命中成长的过程。其中关于下层社会“妹仔”被买卖、包办婚姻等很明显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妇女悲惨的女性体验,是中国女性的声音。但另一个声音来自作者史沫特莱,如文中对资产阶级的批评:在英法、东南亚的殖民地干活的都是穷苦的农民、工人、华南的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们在高工资的诱惑下,或者只不过为了填饱肚子,就接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史沫特莱,1985a:339)。史沫特莱(1985a:332)称这种现象让她看清了资产阶级的本来面目,也唤醒了她的责任。。
在作品的某些部分,他者张晓红的声音甚至被作者的声音取代,她通过笔下的人物表达坚定的革命信念:为革命献身的男男女女坚定了她的信仰,激发她无穷的力量(史沫特莱,1985a:338)。史沫特莱在《大地的女儿》中也表达了相似的思想:“我不是那种为美而死的人。我是那种因贫困而死的人,或是权贵的牺牲品,又或是为了某项伟大事业牺牲的战士。”(Smedley,1973:8)因此,史沫特莱作品中既有中国革命女性的声音,也有作为左翼知识分子自我的声音。通过让中国妇女说话,史沫特莱把她的左翼思想投射在他者身上并与之认同,通过他者言说自我。
女性主义叙述声音的复调在跨文化书写中的另一个表现为双声对话。美国作家项美丽在自传小说《太阳的脚步》中以她和邵洵美夫妇的跨国三角恋为原型,塑造了美国现代女性多萝西和中国传统女子美凤两个女性形象。叙述声音虽然是作者型叙述或第三人称全知全能叙述,但叙述者的聚焦在多萝西和美凤两人之间转换,分别展现各自眼中的对方,犹如两种叙述声音在对话。多萝西眼中的美凤 “她就像一个发光的小瓷人”(Hahn,1940:88)。而美凤眼中的多萝西是“一个丑陋的、大脚、笨拙的外国人”(Hahn,1940:105)。这两种叙述声音分别代表传统和现代的女性身份认同,叙述双声的对话反映了作者项美丽在两种女性角色之间的协商。作者把自己再现为争取妇女权力的现代美国女子,而中国妇女被锁在她的房子里,就像被置于一个珠宝盒中,是她同情的对象(Hahn, 1942:42)。
美凤和多萝西这两种角色被赋予象征意义,她们之间的差异代表了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女性身份危机:她们受自由主义思想的鼓舞,试图出走家庭,在公共空间实现自我,但传统的性别观念仍然认为女性合适的位置是家庭,高呼女性“回家去”(Chafe,1991:175)。女性个体在这两种角色中难以抉择。小说《太阳的脚步》将传统的女性角色投射在中国女性角色身上,把多萝西塑造为追求自由平等的现代女性,通过叙事双声的对话再现了美国社会当时面临的性别问题。
巴赫金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为例阐释复调小说的叙述模式,陀氏小说中众多的声音和意识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不同声音具有充分价值,共同组成真正的复调,他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也是直抒己见的主体”(巴赫金,1988:29)。在女性跨文化书写中,作者的声音、白人女性的声音以及他者的声音互相对话,虽然在某些作品中仍然是作者的声音起主导,未能如巴赫金所言避免作者的对象化投射,但多种叙述声音展现了作者身份认同中与各种权力话语的协商以及自我身份认同中的他性。
3.文本间性
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Gerard Genette)在《隐迹稿本》(Palimpsests:LiteratureintheSecondDegree, 1982)中研究 “文本间性”(trans-texuality),即通过研究不同文本之间的关系来揭示其他相关文本对某一个文本阐释的影响。他认为与某个主文本存在跨文本关系的有五种依附文本:“互文”(intertexuality)、“类文本”(paratexuality)、“元文本”(metatexuality)、“超文本”(hypertexuality)和“统文本”(architectuality)。“互文”本之间在母题、形式等方面互相借鉴;“类文本”通过标题、副标题、前言、后记等文内标识形成文本; “元文本”评价或引用其他文本;“超文本”直接引用其他文本使得文本中出现被‘嫁接’文本;“统文本”以文类特征明示让读者觉察到其跨文类特征(Genette, 1982:2-5)。女性跨文化书写不同于小说、诗歌等正统文学样式,往往兼具虚构和纪实的特点。女作家以各种形式反复书写她们的跨文化经历,其在文本样式上体现的跨界也象征了女性跨文化书写的“跨文化”“跨界”等特征,因此热奈特关于文本间性的定义对于研究女性跨文化书写的叙述样式具有启发意义,尤其是研究某一作家的几部作品之间的文本间性。
赛珍珠多部作品之间有明显的互文特征。以她论文集《论男女》(OfMenandWomen, 1941)和小说《大地》(TheGoodEarth, 1931)以及《群芳亭》(PavilionofWomen, 1946)为例,三部作品有一致的母题——探讨女性个体自由与家庭义务之间的关系。小说《大地》和《群芳亭》虚构性较强,赞赏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同时鼓励女性追求自我救赎;论文集《论男女》针对美国妇女的性别认同危机,提出女性要走出家庭,实现自我。这三部作品都聚焦女性与家庭的关系这一问题,形成互文,既有小说与非小说之间的对照,也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形成对话,呈现了作者女性思想成熟的轨迹。《大地》想象了一个朴实、沉默、勤劳、温顺的东方女性,《论男女》呈现了现实中的美国女性。《论男女》与《大地》不仅文类不同,阐述的思想也各异。赛珍珠在《大地》中歌颂无私奉献家庭的阿兰,在《论男女》中却鼓励美国妇女离家出走。但第三部作品《群芳亭》协商、调和这种小说与非小说、他者与自我的差异,其中的主人公吴太太兼具美国妇女的自由主义诉求和阿兰代表的传统美德,是自我与他者的理想融合。
《群芳亭》从思想上改写《大地》,从文类上改写《论男女》;而《群芳亭》和《大地》分别从正反两面注解《论男女》中的论点。赛珍珠在东西文化之间、小说与非小说之间、中美两国女性之间形成对话。在《群芳亭》中通过吴太太这个理想的女性形象化解两种文化和两种文类之间的矛盾,建构了跨文化身份书写中的身份认同。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多部中国作品之间呈现类文本和超文本的特征。美国女性主义者佛罗伦斯·豪(Florence Howe)在《革命中的中国妇女》后记中论及史沫特莱作品的文类特征:《中国战歌》融合了自传、报道、人物特写、历史、旅行文学以及托尔斯泰式的战争中的乡村场景描写(Howe, 1976:189)。她认为史沫特莱的作品挑战英语文学现有的规范:虽然美国对中国的兴趣日益高涨,但《中国战歌》却停止印刷了,这说明了我们文学标准的局限。《中国战歌》与《革命中的中国妇女》一样,无法被归为任何一种文类(Howe,1976:190)。
史沫特莱的《中国战歌》共分为十章,由56篇短文组成。第一章“早年的回顾”讲述了史沫特莱来华前的主要经历,几乎是她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的缩影,重述了她在小说中讲述的故事,呈现类文本特征。此外,这部作品中的某些文章曾发表在《新共和》《新群众》等美国左翼文化期刊上,后来进行修改以独立的章节出现,因此具有超文本特征。以“妇女起来了”一文为例,该文主人公是参加革命的农妇“蔡妈妈”。经麦金农夫妇考证,史沫特莱以1938年在南方游击队中的见闻为基础构思的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时尚》(Vogue)杂志上,标题是“没有牺牲,没有胜利”(“No Sacrifice … No Victory”),后来以“妇女起来了”(“The Women Take a Hand”)为题收入《中国战歌》中(Mackinnon,1976:120)。
项美丽对同一个人物或事件反复书写,呈现超文本和元文本特征。各个不同版本的故事之间形成张力,后面的作品既重复前面的作品又进行改写,就像羊皮纸书写一样,这种重复书写解构了虚构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在项美丽所有的中国作品中,书写最多的是她的中国情人邵洵美,他在《中国与我》(ChinatoMe, 1944)中以真名洵美出现,在《太阳的脚步》(StepsoftheSun, 1940)中化名孙云龙,在《潘先生》(Mr.Pan,1942)中是潘海文。项美丽不厌其烦地描写邵洵美俊美的外貌,小说《太阳的脚步》写道:“塑造云龙面孔的那位雕塑家,一定施展出了他的绝技,他从高挺的鼻梁处起刀,然后在眼窝处轻轻一扫,就出来一副古埃及雕塑似的造型。”(Hahn, 1940:12-13)杂文集《潘先生》中的海文“苍白、幽灵一般,留着一缕中国式胡子,穿着深色长袍,细长的眼睛里是空洞而悠远的眼神”(Hahn, 1942:5)。自传《中国与我》这样描述洵美:我已经多次写过他,以多种形式——洵美是无法穷尽的写作源泉,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提到他(Hahn, 1944:8)。项美丽的中国经历包括她与邵洵美的恋情,她与中国文人如温源宁、吴德生等的聚会,她的上海冒险包括体验舞女生活、抽鸦片等反复出现在她各种文类的作品中,包括小说《太阳的脚步》,发表在《纽约客》上的文章以及传记《中国与我》。
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克里斯蒂娃从精神分析的视角重新阐释互文性的概念,认为互文性是重构主体意识、抵抗权力规范的革命性力量:互文的陈述相互交错,在交流协商中相互否定,唤醒或摧毁先前的话语结构(秦海鹰,2003:2)。就文类而言,上述三位美国女作家都僭越了西方传统文学的边界,她们的作品混杂了小说、民族志、自传、新闻报道、杂文等多种文类特征。就叙事程度而言,三位作家的跨文化书写模糊了虚构与现实的界限,既有虚构叙事,也有零度书写,这是她们的跨文化镜像认同在文学形式上的表现,对他者的再现既有真实的写照,也有主观的想象。女性跨文化书写模糊文类界限,呈现给读者的有虚构的跨文化想象,也有真实的跨文化体验,将自我与他者融合,借他山之石表达女性书写主体的女性思想。
4.叙述与性别
兰瑟认为,按照传统叙事学的定义,《埃特金森的匣子》这一信件可谓毫无情节可言(plotless)。信件的叙述者所呈现的是等待、停滞、被动的状态,是一个没有情节的故事。但兰瑟认为,情节的另一个层次存在于写作行为本身,“书写的行为变成欲望的满足,讲述成为预言的行为(predicated act),好像讲述本身就是解决方案,是解脱”(Lanser, 1986:357)。在这个层次,叙述者、受述者和读者共同成为故事的情节。另一位美国学者罗宾·沃霍尔-唐文(Robyn Warhol-Down)(2008:30)将叙事与性别认同之间的关系表述得更为清楚:当读者阅读叙事文本,他/她就可能修正自己性别表述。因此,阅读叙事文本也会影响读者的性别。换言之,女性叙述、女性书写、女性阅读在建构女性性别认同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跨文化书写不仅纪录而且延续了他者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东西方女性共同成为故事的情节,关于他者的叙事也影响了受述者、作者和读者的性别认同。
在女性跨文化叙事中,作者的性别以及意识形态影响叙事,如左翼作家史沫特莱书写革命中的中国妇女,“福莱勃尔”④项美丽则书写她的上海冒险,赛珍珠书写中国农民和农妇等。另一方面,叙事也影响作者的性别认同,自我成为他者故事的延续。史沫特莱前往中国之前因政治、婚姻等原因几乎精神崩溃,她在中国人民的革命以及对他们的书写中重构自我,正如劳特(Paul Lauter)(1973:412)所认识到的一样,“中国改变了一切”,“对中国人民深深的同情和理解立刻吸引了史沫特莱,好像他们的斗争延续了她儿时所书写的一切” 。史沫特莱的中国叙事建构了一个左翼思想的乌托邦,在这里被压迫阶级被赋予坚定的信仰和勇敢的斗争精神,人与人之间维持着纯洁的同志友谊,虽然生活艰辛,但革命的宏伟目标激励着大家前行。正如刘小莉(2012:45)所言:“与其说中国的红色革命吸引了史沫特莱,不如说她从一开始就将这场革命理想化,在其中寄托了消灭剥削与压迫,消除种族、国家界限,消解父权制婚姻,实现妇女解放,实现大同社会的主观愿望。”在这个理想叙事中,史沫特莱自我建构为一个理想的女革命者,不受性别、阶级的困扰。事实上,史沫特莱通过她的中国叙事在国际左翼联盟的影响日益增大,成为美国左翼文学代表作家之一。正如兰瑟所言,作者、读者与叙述者共同组成故事的情节,史沫特莱的生平延续了她笔下人物的故事,而叙事也成为她性别认同的重要元素。
罗宾·沃霍尔-唐文认为阅读叙事也影响读者的性别,赛珍珠及其作品对美国女性的影响正是如此。赛珍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一举成为美国最受瞩目的女性,她在《哈泼》(Harper’s)等杂志上发表了数篇文章对美国二战前夕的性别问题深入讨论,还于1941年发表了论文集《论男女》,批判把女性束缚在家的男性传统,同时批评女性缺乏打破传统的勇气,呼吁女性走出家庭,实现自我。洛伊斯·班纳在《现代美国妇女》中谈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兴起了一场“回家去”运动,“甚至受过大学教育的妇女也继续把结婚看成她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目的”(班纳,1987:226)。在这一背景下,赛珍珠在《论男女》中的主张非常具有革命意义,批评家认为她预示了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在《女性的奥秘》中的自由主义主张。三年之后赛珍珠出版小说《群芳亭》,借中国女性的故事向美国读者阐释家庭义务和女性自由之间的平衡对女性的重要性,这对面临性别角色认同危机的美国女性而言,可谓是一本行为指南。她在《群芳亭》对美国女子玛格丽特说:“和我们一样,你们结婚是为了种族繁衍,但你们违心地说这是爱情。”(赛珍珠,1998b:312)这里玛格丽特代表美国现代女性,赛珍珠把她当成言谈的对象,实际上是直接在向美国妇女讲话,希望她们与中国妇女一样,在追求自由的时候,不可忽视对家庭的义务。
克里斯蒂娃(Kristeva)认为文本并非由确定的主体决定,而是建构主体,通过文本的越界行为实现。文本一方面接受既有的法律和规约,生成意义和主体,另一方面又质疑、改变、超越意义和主体:“只有通过它们的表演(艺术再现和诗性语言),本能爆发、穿透、变形、变革、改变主体和社会为自己所设置的边界。”(Kristeva, 1984:103)文本实践把社会关系中被规范、固定的主体改变成过程中的主体(subject in process)。女性跨文化书写通过文本的越界建构女性主体,它们与正统的文学作品不同,呈现独特的叙事特征:作者采取多重叙述声音呈现自我与他者的对话,将自我投射在他者身上,通过与他者的协商更清楚地认识自我;以多种文类反复书写跨文化体验,在文本间将想象与现实融合,塑造理想的女性形象;采用半私下型叙述与男性叙事规约协商,建构女性权威,重构现代女性主体。
注释
①对这首诗歌和兰瑟批评的详细分析请参见申丹,“‘话语’结构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话语’研究评介”[J].《国外文学》, 2004(2):3-11。
②伊罗生(Harold Issacs)在《心影录——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和印度的形象》(RefectionsinOurMind:TheImageofChinaandIndiainAmericanMind)中对截至20世纪50年代美国民众心目中的中国进行调查,将中国形象分为六个阶段:①崇敬时期(18世纪);②蔑视时期(1840—1905);③仁慈时期(1905—1937);④钦佩时期(1937—1944);⑤幻灭时期(1944—1949);⑥敌视时期(1949—)。
③西方学者在研究18世纪英国小说时发现叙事易装这一特征,即“男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女性叙事者的声音”讲述故事,把“男性自我投射到想象的女性角色身上”进行叙事。参见:MadeleineKahn.NarrativeTransvestism:RhetoricandGenderintheEighteenth-CenturyEnglishNovel[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2-6.
④Flapper一词源自一战前的英国,最初指十几岁的女孩。在一战后的美国杂志、荧幕、文学中广泛使用,指十几、20多岁的女孩。中文翻译有摩登女郎、飞女郎、福莱勃尔等。本文采用“福莱勃尔”一词,这是对“flapper”一词的音译,避免“摩登女郎”“飞女郎”等词所隐含的刻板印象和道德上的负面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