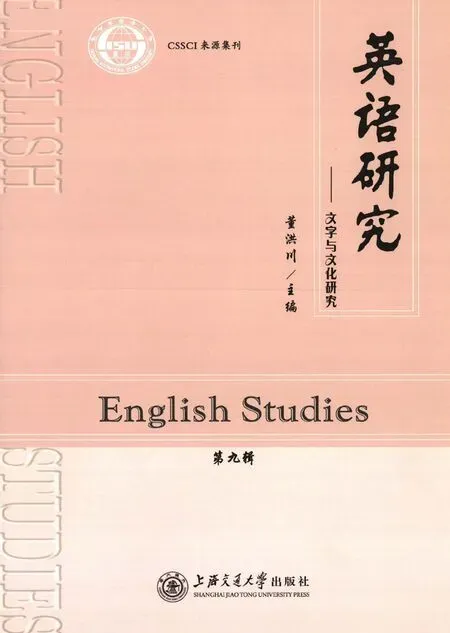从老舍作品的域外传播看中国文学如何成为世界文学
生安锋
(清华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系, 北京 100084 )
1.老舍作品的域外传播概况
2016年11月21日,人民网刊登出一篇文章,《老舍在美遗失原稿重大发现海外遗珍〈收获〉即将刊出》(覃博雅、常红,2016)。原来是上海译文出版社赵武平先生在哈佛大学施莱辛格图书馆编号为“MC465”的浦爱德(Ida Pruitt)档案里,找到了《四世同堂》一些失落的章节的英文译稿。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国内看到的《四世同堂》并非全本。老舍的《四世同堂》分为《惶惑》《偷生》和《饥荒》三部分,创作于1944—1949年间并陆续连载、出版。最后一部《饥荒》(68至87段)最初于1950年在周而复主编的《文学》杂志第四卷上连载,到第87段时突然宣布全书刊载完毕,而原稿也被毁于国内历次运动。1981年,人们在由浦爱德翻译并于1951年出版的美国版本《黄色风暴》(TheYellowStorm)中,发现了被缩减的《四世同堂》的最后13段,于是由马小弥翻译并发表于1982年第2期《十月》杂志上。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版本是《惶惑》《偷生》和《饥荒》(前20段加上马小弥后来从英文版转译的13段组成的)。人们过去一直以为老舍写满一百段后全书就结束了,但从2016年在哈佛大学所发现的译稿底稿来看,老舍其实共写了103段。①
这则趣事让笔者开始重新关注老舍作品在国外的翻译和传播问题。其实,在中国所有的现代作家中,老舍作品被译介的数量、被译入的国家或者外语数目都是非常多的,其数量估计仅次于鲁迅。②老舍的小说、戏剧、散文等,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开始被翻译成英语,如《人同此心》《且说屋里》等短篇小说;而从这一时期开始,老舍的作品也逐渐被翻译成日语,包括小说《小坡的生日》《赵子曰》和《骆驼祥子》等。(李越,2013:63)到现在,老舍作品已经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这其中包括英语、法语、日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丹麦语、韩语等。甚至最早出版的研究老舍的专著并不是以汉语在中国出版的,即使是汉语的也不是在大陆,③而是斯乌普斯基(捷)的《一位现代中国作家的历程——老舍小说分析》(英文版,1966年)、安季波夫斯基(苏)的《老舍早期创作》(俄文版,1967年)和兰伯·沃哈(印)的《老舍与中国革命》(英文版,1974年)。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的全国性老舍研究机构并不是在中国,而是1984年在日本成立的“全日本老舍研究会”,而“中国老舍研究会”成立于1985年。日本也率先出版了百科全书式的《老舍事典》。据统计,日本是对老舍作品翻译最早、数量最大的国家,也是除了中国之外世界上老舍研究成果最丰富的国家。在日本,仅《骆驼祥子》就有十几个日文版本,日文版的《老舍小说全集》十卷本(1981—1983)甚至比中国同类的文集还早,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日关系恢复后甚至一度出现了研读老舍著作的“老舍热”。老舍也是中国现代作家中作品被译成法文最多的作家之一,其代表性小说《骆驼祥子》和《四世同堂》等早在1947年和1955年也分别被译成法文出版。另外,老舍及其作品在苏联及现在的俄罗斯(费德林、彼得罗夫、安季波夫斯基、博洛京娜等)、新加坡(王润华等)、美国、捷克、法国、加拿大等国都有广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续静,2012: 8-10)。另据统计,老舍的作品被翻译成英语的主要包括:长篇小说《骆驼祥子》(1945,1964,1979,1981,2010)、《离婚》(1948,1948两个版本)、《四世同堂》(1951)、《牛天赐传》(1951,1986)、《鼓书艺人》(1952)、《猫城记》(1964,1970)、《二马》(1980,1984,1987,1991)、《正红旗下》(1981);30多篇中短篇小说和《龙须沟》(1956)、《茶馆》(1980,1980)等五部戏剧也被译成英文出版。总之,美国出版的老舍英译作品约60多种(包括重译本),英国也有一些译本如《牛天赐传》和一些短篇小说等。这样,老舍的16部长篇小说中就有九部被译成英文,而且很多著作有多个译本,如《二马》有四个译本,《骆驼祥子》有五个译本。
2.从戴姆罗什的世界文学观看老舍作品的世界文学性
老舍的著作,无论从翻译与传播的时间、数量、广度及其在国外的接受度看,都可被看作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世界文学概念的提出以及世界文学的发展,其实早在数百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早在近200年前(1827年),德国著名文学家歌德就对其门徒艾克曼说过:“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歌德,1978:113)时隔20年后的1847年,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再一次申述和回应,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论述当时正在兴起的全球性资本主义市场及经济发展时顺带提及或者推及人类文化的,他们指出:“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2009:276)世界的文学或者世界性的文学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经济贸易的繁荣是分不开的。而在资本扩张时期,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全球殖民事业以及伴随而来的军事行动、宗教传播、商贸活动等,客观上造成了全球性的文化流动与交往。在此之前,小规模的贸易和个体性的旅行活动、留学活动等也都对促进地域间的文化交流发挥着作用,但是18世纪以来帝国主义殖民活动所带来的规模化的、深层次的、强制性的、遍及亚非拉澳各州的文化交流却是之前那种零星的、散漫的、断续式的文化交往所不能比拟的。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进程始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而从那时起,现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也就开始了。
歌德对于世界文学的定义和提出,其实也是其作为一代文豪的自身文化涵养的体现,甚至可以被看作是实践世界文学的身体力行者和典型代表。歌德既是德国古典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擅长各种文学体裁的文学家,又是著名的思想家、画家和科学家。歌德一向认为,如果一个人不懂得任何外语的话,那他等于对自己的语言也一无所知。歌德自己除了母语德语外,还精通拉丁语、希腊语、法语、意大利语、英语和希伯来语,经常阅读世界各地的文学作品。歌德正是在这种懂别人、懂世界进而懂自己的良性循环中,才认识到世界上不同文学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不同民族文化之间极强的互补性,进而提出世界文学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概念的。世界文学的概念经过近二百年的酝酿和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和世界文化交流互动的加深和日益频繁,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再次引起了众多东西方学者的关注和讨论,并重新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当代美国文学理论家、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弗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于2000年发表了《关于世界文学的猜想》一文,针对新批评的封闭式文本细读,他提出“远距离阅读”的观念;尤其是他受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之影响,提出世界上的文学发展是一个权力不平等的中心—边缘形式的结构,早期的世界文学是一个马赛克式的拼贴。各民族文学之间交流甚少,而现代阶段的世界文学才发生了实质性的交流,并构成了一种所谓的“世界文学体系”。(Moretti,2000:54-68; 2013: 46)而在哈佛大学教授、《诺顿世界文学选集》主编马丁·普契纳(Martin Puchner)看来,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描述存在着世界文学时代是否已经到来的矛盾,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世界文学在时间上的开放性:世界文学存在于当下,却是面向未来的;世界文学不是指人类文学的全体,而是指一种“世界性的”文学,这个“文学的子集”与世界整体都保持着一种至关重要的关系。(普契纳,2015: 55-57)但是,相对于以上诸种理论,戴维·戴姆罗什的世界文学理论更具明晰性、创造性和系统性,又因其专门谈到翻译在世界文学形成过程中的重大作用而较其他理论更为全面也更具操作性,因而对于我们在此思考老舍著作的世界性更为贴切。
在戴姆罗什看来,对世界文学的定义自歌德以来就存在三种基本范式:作为文学经典、作为代表性作品和作为观察世界的窗口,但世界文学并不就是世界上所有民族文学的总和,而是在产生文学作品的源文化之外广泛流通的文学。世界文学可以从世界、文本和读者这三个维度来加以定义:“①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间的椭圆形折射。②世界文学是从翻译中获益的文学。③世界文学不是指一套经典文本,而是指一种阅读模式——一种以超然的态度进入与我们自身时空不同的世界的形式。”(Damrosch, 2003:281)④下面,笔者想借此视角来探析老舍著作在国外的翻译、传播与接受。
在戴氏看来,将世界文学理解为民族文学之间的椭圆形的折射,有助于解释或者澄清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当一部文学作品进入世界文学系统之中时,他们当然仍会带有原民族文学的痕迹或印记,这些痕迹随着扩散领域的不断扩大而传播益远并不断发生折射现象。戴氏指出:“因此,世界文学总是既与宿主文化(host culture)的价值取向和需求相关,又与作品的源文化(source culture)相关;因而是一个双重折射的过程,可通过椭圆这一形状来描述:源文化和宿主文化提供了两个焦点,生成了这个椭圆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作为世界文学而存在的文学作品,既与两种文化同时密切相关,又不由任何一种文化单方限定。”(2003:283)老舍的著作,从作为源头的中国文化空间走进英语或者其他的宿主文化空间,仍然带有中华民族的强烈的民族性和地域特点。翻译到英语世界后,虽然会丢失一些东西,但是却也引起了很多读者的共鸣和欣赏,获得了数量可观的读者,在新的文化中形成了一个新的“焦点”,与其在中国文化中原来的焦点交相辉映,既相互平衡又相互激发。戴氏在谈及这一点的时候,尤其强调比较文学学者和世界文学研究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和作为主体的研究者的自主选择性。中国的读者在老舍作品中看到的可能是对战乱年代百姓的民不聊生,是对腐败僵化的官僚体制的讥刺和失望,是对积弊已久的国民性的讽刺和批判。而美国读者在老舍作品中所读到的与中国读者所读出的可能会有重叠的地方如战争创伤、悲剧性社会现实等,但其“焦点”所在之处可能更偏重于对普遍人性的挖掘和对异域风貌、陌生的中国社会与历史文化的展现,甚至十分关注老舍的语言风格与叙事模式。(李越,2013:30-38)美国的读者必然会带着已有的“三观”和意识形态去阅读和理解作为一个外国作家的老舍的作品。这种双焦点因能相互阐发而相映成趣,共同构筑起一个互动型的世界文学文化空间。
上文提到文学在翻译中的损失问题,其实是老生常谈了。所谓无法翻译成外语的东西就是诗,但这其实是一种过于绝对的说法。事实是,国内外无数诗人的作品都被翻译成了外语,无论是我们所熟悉的中国典籍《诗经》和李白、杜甫、白居易、寒山的诗句,还是西方的《荷马史诗》和但丁、弥尔顿、莎士比亚、拜伦、庞德、艾略特的诗句,都被翻译成多种外语并被世界各地数以亿计的读者所赏析。其他文体的文学更毋庸赘言。对于在语言上一味地追求完美的人来说,翻译中的损失或多或少总是有的。但在戴氏看来,世界文学却是从翻译中获得好处并大大增值的文学。他认为:“在翻译中常常受损的文学,通常局限于本民族或者本地区的传统之内;而从翻译中获益的文学则变成了世界文学,在其范围扩大后,其风格上的损失会被深度上的增加所抵消,正如《吉尔伽美什》和《哈扎尔辞典》这两部迥异的作品”。因此“世界文学的研究应当以比截至现在更为积极的态度去接纳翻译”(Damrosch, 2003:289)。在笔者于2008年对戴氏的一次采访中,他曾指出自己通晓12种语言并能用这些语言进行学术研究,但他仍旧认为翻译对于比较文学研究者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因为世界上没人任何人能通晓世界上所有的语言。(生安锋,2010:221)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先生可谓百年不遇的语言奇才,他不但会讲33种中国方言,而且通晓多种外语包括英语、德语、法语、日语、俄语、希腊语、拉丁语等。赵先生不但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和现代音乐学的先驱,还曾于1945年当选为美国语言学学会主席。但即使是像歌德、赵元任、戴姆罗什这样有极高的语言天赋的人,也从未否认翻译的必要性。因为据统计,全世界有5000多种语言,所以即使一个人再有天赋,他也不可能学会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那么在不同民族之间的沟通方面,借助翻译就成为一种必然。尽管翻译有着诸多不如意之处,但老舍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后在美国反应相当不错。《骆驼祥子》英文版出来以后就成了畅销书,而《四世同堂》的译本《黄色风暴》出版后也获得了一致的好评。老舍作品在海外尤其是英语世界的广泛流传和读者对他的认可度,无疑是因为他的很多作品,甚至可以说是他的所有的重要作品,都被很好地翻译成了英语的缘故。
戴氏对于世界文学的第三个维度的定义是,世界文学不是一套固定的经典文本,而是一种阅读的方式,一种以超然的态度进入与我们自身时空不同的世界的形式(英文原文:...not a set of canon of texts but a mode of reading: a form of detached engagement with worlds beyond our own place and time)。(Darmrosch, 2003:281)这里的“engagement”为了语义通顺而翻译为“进入”,其实是认识、交流甚至还有“交战”的意思。此处的意思就是以一种保持距离的、超脱的态度,去与世界文学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陌生世界或者他者文化进行一种沟通、交流、协商甚至是“交战”。在戴氏看来:“世界文学不是必须要掌握的(这也是不可能的)一大堆材料;而是一种阅读模式,可以通过少量作品来加以精深的(intensively)体验,这与通过广泛(extensively)研读大量作品是同样有效的。”(Darmrosch, 2003:299)与沉浸在单一文化或单一语言中进行学习不同,“阅读和研究世界文学本质上是更为超然的研读模式,它与文本进入一种不同的对话,不涉及身份,不牵涉对其加以认同或者掌握的问题,而是坚持距离和差异的原则(the discipline of distance and of difference)。我们与作品的遭遇之地不是在源语的文化中心,而是位于由来自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的作品所形成的“力场”之中。这种椭圆关系已经刻画出了一种外国民族传统的特征,但由于椭圆的急剧扩大及折射角度的增加,会在程度上有所差异。世界文学作品恰似在一个电场(charged field)中相互作用,这一电场是由一系列流动的、变化多样的并列与组合而构成的”。(Darmrosch, 2003:300)根据上下文句意,这里所谓的“超然”并不是说要读者超然物外或者完全超脱于原文文本或者语境之外,而是强调阅读翻译作品时所需要秉持的距离感和张力。老舍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和传播,对于英语世界的读者而言,就构成了这样一个远离中文语境的、“超然的”阅读空间。中国的读者首先关注的是老舍作品中所反映的战乱频发以及由此所导致的百姓的穷困潦倒,是对社会不公、官场腐败的批判和愤慨以及对国民性堕落的哀叹与讥刺,而美国的很多读者和评论家却注意到了作者老舍贫穷的经济状况和政治上的无党派属性,从而肯定了其艺术创作上的相对独立性。(李越,2013:32)这既是国外读者由于其自身的历史文化背景所形成的解读模式,更是对来自异域的世界文学采取一种“超然的”视角所成就的独特理解模式。老舍的作品作为一种来自异域的经典之作,被英语世界的读者所欣赏、接纳或者批评,被放置于英文读者的异域文化之中去理解和阐释,这也就是戴氏所说的作为一种阅读模式的世界文学。近年来,虽然中国文学作品的外译数量和质量都有了很大的飞跃,但总体而言,我国的现当代作家中能翻译成外语并在国外出版的毕竟还是少数。但是,一旦翻译并在国外发表,这就是向世界文学走出了第一步,或者说,翻译是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必要条件,虽然并不是一个充分条件。
3.反思与展望: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
但是,我们用歌德、戴姆罗什等西方学者的理论来分析老舍著作在异域的传播与接受,并不是要以此来证明西方理论的有效性或者验证某个理论的普适性,我们只是尝试以老舍著作为例,以世界文学理论为参照去检视和发掘我们文学的世界性价值或者世界性,以期在同一个维度上构建起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借助对世界文学这一概念重新阐发和更加深入的认识,促进中国文学更快地融入世界。老舍出身满族却自幼饱读汉族诗书,早年即可撰写中国传统古诗文,1920年代初赴英教学,又熟读狄更斯、但丁、莎士比亚等西方名著并开启小说创作生涯。老舍先后在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瑞士、德国、意大利、新加坡、美国等国教学、著书或游历多年;既有极深的中国传统文化造诣,自身又精通英文,甚至参与了自己多部作品的翻译;老舍对于各种宗教如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都有深刻的认识。因此老舍可谓满汉交融、中西汇通,其自身的经历就是一个跨文化交流的典范,而其作品在异域的传播和接受也堪称中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之一部分的典型范例。老舍多次在小说如《赵子曰》《二马》中借着人物的口指出中外文化交流的必要性,认为中国必须要虚心学习先进的外国技术与文化,通过兴教育、办实业救亡图存、复兴中华,消除外国人对中国的偏见和歧视,这样中国才能与外国平等相待,共同“建设一个和平不战的人类”(老舍,2013:590)。应该说,这种对不同文化间和平交往、共生共存的期盼是文学与文化界有识之士的一种共识。英国著名现代派诗人艾略特就曾经说过:“如果希望使某一文化成为不朽的,那就必须促使这一文化去同其他国家的文化进行交流。”(1984:193)我国学者、《萌芽》杂志的编辑曾小逸在20世纪80年代初也曾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交流意味着一切的时代”,“不在交流中发展,就被交流所淘汰”。(曾小逸,1985:23-25)倡导世界文学,积极推动世界文学观念的普及与深化,就是要借用他人的眼光来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学和世界文学之关系,借用一个“超然”的视角去重新审视我们的民族文学,并积极推动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更加深度有效的理解和更加友好的相处做出贡献。
其实,在莫瑞提、戴姆罗什等西方学者建构起自己的世界文学理论之前,我们就有为数不少的学者对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文学与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等问题做出过深刻的思考,并提出了极具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我们甚至可以将我国学者对世界文学的兴趣和推崇追溯到20世纪初。那时很多政治家、文学家或学者如康有为、孙中山、梁启超、老舍、郭沫若、茅盾等人就对世界主义思想以及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作出过深刻的思考。郑振铎在1922年就强调将全人类的文学看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并认为文学是“人类全体的精神与情绪的反映”,是“人类的最崇高的情思”;因为尽管有时代与民族的差别,但“在文学作品上,是没有‘人种’与‘时代’的隔膜的”。(郑振铎,1998:142,138)
而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曾小逸就曾开风气之先,主编了《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一书,他在该书的长篇导言中深刻论述了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世界文学的理解和期望。他认为:“各民族文学向一体化世界文学发展的过程,也是文学的民族性在交流中融合为更高意义上的文学的人类性的过程。”(曾小逸,1985:33)他因而提出一种“全球文学意识”或者“世界文学意识”,以对抗狭隘的民族主义所带来的消极意识:“惟有以世界文学意识,而不是以文学上的狭隘民族主义或任何其他似是而非的观念,才可能认识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交流时代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曾小逸,1985:33)从这些深刻而极具前瞻性的论述可以看出,在历经多场政治和文化浩劫之后中国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关系的辩证思考、对文化开放心态的期望和肯定以及对世界各地各族文化交流的信心与乐观精神。
进入21世纪,我国众多学者都从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和主体性出发试图对世界文学做出自己的定义和阐释。方汉文(2011:51)教授认为:“世界文学归根结底就是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差异性与同一性并存,是全球化的多元文学呈现。”刘洪涛(2014:252)教授也指出世界文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承担着文学世界大同的理想;另一方面,当世界文学观念进入具体实践时,又会与特定民族的文学利益联系在一起。”这里的关键是:随着我们对世界文学概念认识的加深和参与度的提高,我们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自外于世界文学之外,而是应该采取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故而应该“把中国文学看成世界文学的参与者,世界文学大家庭中的一员”,中国文学应该被“放到与其他国家文学平等的地位上,成为世界文学的共同构建者”。(刘洪涛 2014:8)客观而辩证地处理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微妙关系,用一种宏阔的眼光去审视包括自己的文学在内的各民族文学,用一种世界的胸怀去拥抱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珍视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尊重差异性与异质性,推崇包容和礼让,这无疑是我们作为学者和知识分子最为明智、也最有担当的做法。
我国比较文学学者王宁教授指出,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助力中国文化的世界化,“直接推进了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2016:37)。但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情况却是不容乐观的,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张隆溪先生看来,中国传统经典文学中很多最重要的作家如苏东坡、陶渊明等在国外都不为人所知,而世界文学观念的日益普及正是矫正这种“严重的不平衡”(2016:18)的大好机会。但是,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其间必然要经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而且我们也期望,未来的世界文学并不只是通过英语或者任何单一的语言来认可、翻译、分类、传播的文学。笔者曾经指出,老舍作品如小说《二马》《小坡的生日》和戏剧《大地龙蛇》等中包含着丰富的世界性或者世界主义因素,(Sheng, 2017)这也是老舍文学率先成为世界文学之一部分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处不赘述。
4.结语
综上所述,老舍著作在国外传播与接受的案例,使得这些作品不仅超越了老舍所出身的满族的民族性局限,而且也超越了中国汉语语境及狭隘民族性的限制,在国际文坛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甚至时至今日,老舍的文学成就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与鲁迅、茅盾等一样举足轻重的地位,老舍进而也成为较早走出国门藩篱、成为世界文学之一部分的典范。从老舍的这一案例中,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以下几点:翻译在文化传播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故而我们要注重翻译,尤其是高质量的对外翻译;积极学习外国的语言与文化,突破自己原有的文化限制,拓展文化视域,养成一种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并借用他者的眼光重新审视自己,加深对自我文化的认识;正确对待民族性和世界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树立人类整体意识和世界文学意识,拒绝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在注重文化自主性的同时加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心;注重文化交流,发扬我国传统中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追求世界多元文化的共存共荣;借力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促进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尽快打破中外文化交流中的“贸易逆差”现象。总之,探讨和思考老舍作品走出去的得失成败,对于反思我们目前还相对闭塞的文化现状和自足自满的文化心态,对于呼应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文化战略,对于思考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如何打破国界的限制和狭隘民族性的羁绊,真正融入世界文学和世界文化,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注释
① 新发现的部分已由赵武平先生翻译并刊登在《收获》杂志2017年第1期上。
② 关于鲁迅著作在英语世界的翻译情况,可参阅杨一铎、禹秀玲的论文《英语世界鲁迅传播的历史分期及特点》,载《北方文学旬刊》,2014(1):215-216。
③ 1977年香港学者胡金铨出版了《老舍和他的作品》,1985年台北天一出版社出版了朱传誉主编的《老舍传记资料》系列丛书。在大陆,1982年山东大学主办了全国第一次老舍学术讨论会,1984年在青岛举行了全国第二次老舍学术讨论会,北京1985年成立了中国老舍研究会,出版了曾光灿主编的《老舍研究资料》和王惠云、苏庆昌撰写的《老舍评传》。1986年举行了第三次中国老舍学术讨论会。
④ 本文在引用戴姆罗什的《什么是世界文学?》时,参考了查明建、宋明炜等2014年的译本并在必要时根据英文原著做了少许改动。
⑤感谢华北电力大学外国语学院王苗苗副教授提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