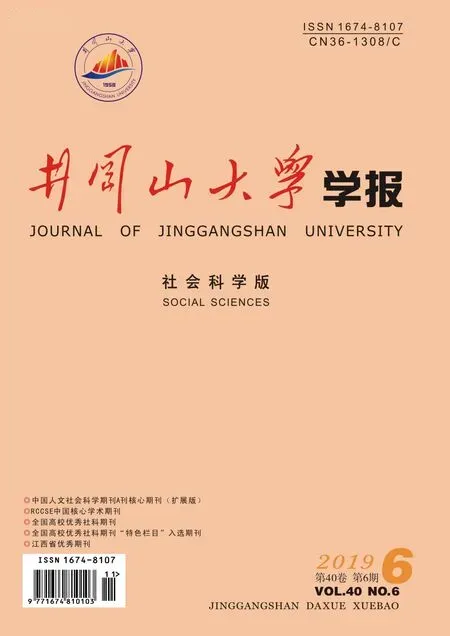“十七年”合作化小说的政治伦理叙事
曹金合
(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 洛阳471934)
对“十七年”的合作化运动而言,自上而下地发动民众参与到浩大的生产关系变革的过程中去,当然离不来小说的教化作用,而统帅舆论宣传和教育民众的思想基础则是占据核心地位的一大二公的政治伦理。因此,在特定的历史时空和政治文化语境下的作家都把政治伦理放到了小说叙述话语和叙事策略的最突出位置: 设置话语主体的尊贵身份以加强政治伦理的可靠性和权威性,强化政治叙事话语的神圣性和感召力。 政治伦理的表现形态和审美意识是由小说中的政治叙事话语来突显的, 话语的规约性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叙事话语与政治伦理的建构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 作用与反作用的矛盾张力也丰富了“十七年”合作化小说的审美形态:“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伦理不仅建造了现代政治生活方式、文化氛围,而且成就了一整套关于社会认知的文学话语程式。 ”[1]从理论上说,政治伦理规约所表现的国家、 人民和个体之间的利益具有同构性和一致性,但在具体实践中,先后顺序、 缓急程度和轻重差别之分却也导致彼此之间存在着异质因素和不和谐的音符。 尤其是个体农民习以为常的自私观念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得到改变的情况下, 政治权威话语倡导的一大二公的伦理价值观念就成为对症下药的制胜法宝。
一、 话语主体的尊贵身份强化政治伦理的权威性
这种大公无私以社为家的政治伦理观念必须靠富有神圣感召力的“卡里斯马型”的伟人的特别作用才能实现,“卡里斯马是一切富于原创性和感召力的个人领导的根源,它表现在使领袖与群体、统治与服膺之间维持一种个人性和情感性关系。 ”[2](P6)毛泽东凭借着在战争与和平建设年代积淀的领袖魅力、 高尚的人格和高瞻远瞩的韬略成为亿万人心目中最红的太阳, 他的言语、行动、指示、著作都具有无形的力量,使民众心甘情愿地服膺,因此,毛泽东作为“卡里斯马型”的人物与民众形成的“号召——跟从”的密切关系,自然是一元独尊的政治叙事话语所选择的最佳精神符码。在“十七年”的合作化小说中,合作化带头人和积极分子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 总是在“毛泽东”、“毛主席”、“毛主席著作” 的红光烛照下获得巨大的精神动力。 《野姑娘》(李准)中小公鸡嘴村的冬妞在上级领导田牛群的百般阻挠下, 仍然以“明组暗社” 的方式阳奉阴违地应付上面的检查,底气来自于最高领袖毛主席的指示, 所以区领导提出的农业合作社“只准办好,不准办坏!”的苛刻条件、必须经过“中央批准”的大帽子都失去了威信。 《李双双小传》(李准)中思想落后富有大男子主义的孙喜旺听毛主席的话才打破乡村伦理中的面子观念, 在熟人形成的乡村社群中不再纠结于个人的利益,听从媳妇的建议洗心革面,要以大字报的形式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严重的时刻》(王汶石) 中的县委书记陆蛟之所以在面对罗村管区东片十二个村庄遭遇的一场强大的冰雹, 以及严重的天灾让不知所措的民众陷入悲痛深渊的危急时刻,能够镇定自若,是因为有毛主席,“如今毛主席指引咱们又走上了公社化的道路”,遇到灾难之后,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团结互助精神真正让社会主义的政治伦理落到实处。 团结协作、 昂扬奋斗、共渡难关、人定胜天的政治话语所充满的正能量确实离不开毛主席的神圣感召力。 萧长春(《艳阳天》)也是“按照毛主席自力更生的教导”,从毛主席身上获得了克服困难的巨大勇气和战斗的精神力量,才把东山坞农业社即将垮台、人们纷纷外出逃荒的慌乱局面稳定下来, 党和毛主席作为农业社的强大后盾, 增强了他战胜困难的硬骨头精神。
毛主席作为“缺席”的在场者,对“十七年”合作化小说政治伦理观念的传播所产生的影响力,具有任何媒介所无法代替的特殊地位。 毛主席语录、像章、塑像、画像、选集等衍生物带来的政治理念, 使偏僻的乡村也充满了泛政治化的日常生活景观。对小说所描绘的合作化运动的领导人来说,斗争经验的丰富性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是一般积极分子所无可比拟的, 但原创力和神圣性的匮乏机制注定只能从富有神圣品质的形象和物品身上寻求动力源。因此,合作化小说中备受爱戴的领导者除了及时从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中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还可以凭借知识的优势,直接从《毛泽东选集》中取得攻克难关的途径和渠道。所以文本中出现大段的引述《毛泽东选集》的话以增强政治话语的启示性,也是常见的叙事策略。《创业史》中的县委副书记杨国华对区委书记王佐民的政治话语表述不仅显得更为深刻, 而且在分析小家小户几千年的小农经济生活的落后性和他们受压迫、 剥削的处境造成的革命性的辩证关系上,直接引述《毛泽东选集》以加强政治伦理的独尊地位,自然为改变和教育农民摆脱自私、落后、消极、散漫、狭隘、愚昧等异质因素提供了无可辩驳的依据,与“教育农民是严重的任务”的伦理观念相得益彰。《风雷》(陈登科)中的祝永康遇到挫折力不胜任时,从老首长应维业送给自己的摘记毛主席语录的日记本中得到了精神焕发的动力源。 他由默念到大声朗诵毛主席语录与他目前的困境完全吻合, 在念的过程中产生的热血沸腾、浑身是劲、兴奋跳跃、拍打额角、自言自语等生理反应,也包蕴着精神的审美因子,这样,“任凭风吹浪打,我自闲庭信步”的坚定跟从毛主席的指示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使祝永康带领黄泥乡的民众走在合作化的道路上再也感觉不到巨大的心理压力。 但毕竟政治伦理的直接宣教缺少了艺术的软化作用, 产生了某些审美缺陷,在这方面做到政治话语与审美形式、风景描绘与政治教化、 诗情画意与方针政策的有机契合的还是《创业史》借助毛主席诗词所做的景色描摹:合作化运动后,男女老少都冒着严寒扫雪归田的热烈场面,用毛主席的《沁园春.雪》中的两句诗词“江山如此多娇”“红装素裹,分外妖娆”进行修饰,水到渠成地得出“总路线的力量真伟大”的结论,避免了乏味的政治说教。
二、 政策条文的普泛化凸显政治伦理的思想意蕴
政策条文在“十七年”合作化小说中的普泛化与政治伦理的内涵和外延密切相关。 由于“政治伦理是根源于一定政治生活习性、从该种政治生活中生成一种政治生活的规定。 所谓基本价值,即人们为什么和应当如何过一种政治生活的规定”。[3](P693)因此,民众的日常生活在凸显政治挂帅的时代语境中就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伦理色彩, 其中所表现的伦理价值观念成为民众必须遵从的行为准则, 其权威性来自于政策条文的制定者、发出者、宣传者和阐释者的身份和地位,其合理性在于适应了建国后避免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的乡村民众的伦理诉求,所以,合作化小说的作者采用不同的叙事策略来阐释分析政策条文的价值意义, 从而形成了带有迥异政治理性色彩的艺术风貌。
首先是某些政策条文的重大性和权威性不允许叙事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做出带有主观色彩的阐释, 而合作化小说的情节和细节又需要这些政策条文对民众进行舆论宣传以便达到教化的目的,叙事者在意识形态和审美的两难中往往会牺牲艺术性的本体要求, 迎合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标准。有时候作家是在理性思维的烛照下,有意识地借助具体的方针政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加强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如柳青在《回答〈文艺学习〉编辑部的问题》中提出“我不能想象一个人经常不看报,不细读社论,不看与自己面对的生活有关的报道、论文和通讯,闷头深入生活的结果能写出作品。 ”[4](P35)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五年计划和建设目标、统购统销和互助合作、自愿互利原则与脱离贫困的道路等有关国家大政方针的政策条文, 熟读报纸和社论的柳青是深谙其中政治分量的, 它没有给作者留下发挥和阐释的叙事空间, 因此柳青就直接把它作为政治文本镶嵌于小说的整体结构中。
当然, 直接引述政策条文的目的是为解决积极分子在合作化运动中遇到棘手的问题服务的,遇到现实工作中必须解决又不容易解决的难题时,就成为方针政策充当救兵的情节突破口。胡正的长篇《汾水长流》中,杏园堡村的互助组长郭春海将互助组的潜力充分挖掘之后, 发现无论怎样小心谨慎费气败力地发展生产力, 也只能维持止步不前的局面。 怎样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调动民众的干劲和创造力积极发展生产? 怎样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凝聚人心进一步为办好农业社做准备?怎样在老牛破车的薄弱家底上克服重重困难取得更大的成绩? 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县委李书记带领工作组到杏园堡来之后迎刃而解。 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是“大张旗鼓地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这样—来,郭春海可真是有雪中送炭的感觉, 在农业生产合作的灯塔照耀下信心百倍地动员贫下中农入社。 这样事半功倍的实践效果, 并不是在所有合作化小说描绘的情境中都是如此的,对于务实的农民来说,单凭抽象的政策条文的劝服有时候并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山乡巨变》中常青农业社的社长刘雨生对盛佳秀动员入社进行解释、 计算和劝说的道理,无非是“小农经济受不起风吹雨打”、“个体经济没得出路”、“合作化的道路是大家富裕、共同上升的大路”等等,这些枯燥干瘪的政治话语没有乡间鲜活生动的物质话语的支撑, 是很难说服深受民间伦理价值观念熏染的落后群众加入农业社的,所以,在“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方针政策也不能消除盛佳秀的顾虑之后, 刘雨生的感情牌还是起到了关键作用, 最终她按照政策条文的要求入社走集体化的道路, 这还是显示了政治伦理的权威。 不管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遇到多少坎坷曲折和磨难考验, 最后的结局一定是按照政策条文所指明的方向奔向合作化的康庄大道。
如果让直接引述的大段的方针政策打断了小说前后情节发展的文意和文脉, 不仅在艺术的情节设置上违背了小说一般遵循的规律和技巧,更不能充分发挥教化的功能而失去小说应有的作用。 因此,在合作化小说中,叙事者更多地采取设置情景语境的方式, 间接地将党的方针政策融入具体的情景中, 潜移默化地改变民众的伦理价值观念。周立波的《禾场上》采取喜剧的方式,让卖弄学问的詹七“高级社,就是高级社”的同义反复,引发大家哈哈大笑酝酿的轻松愉快的氛围, 引出真才实学的邓部长对高级社的解释“高级社是:取消土地报酬, 实行按劳取酬, 多劳多得, 少劳少得……”。 然后采用苏格拉式问答,环环紧扣地设置不劳动与真正失去劳动力的鳏寡孤独之间的区别,对于后者,政府和农业社采取老有所养的方针政策保障他们的生活, 得到全屋场乡民的热烈欢迎。这种步步紧逼逻辑严密的问答方式,对方针政策的舆论宣传可以起到愈辩愈明的作用, 对民众理解方针政策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所以李准的《冰化雪消》中对红旗社副社长刘麦闹只顾自己不顾落后的红光社的本位主义批评, 仍然采取了郑德明社长设问的方式, 让一心为社却感到满腹委屈的刘麦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什么叫大公无私?”“为啥要掏出良心干?”等小儿科的问题到“可是咱们既然是领导大伙走社会主义, 难道就能抱住咱们一个社,对别的农民就不管吗?对别的社就笑话他们、打击他们吗?”[5](P32)提出的问题直指麦闹心病的要害,对于理论修养比较肤浅、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比较偏狭的积极分子来说, 在跳出一家一户狭隘的小圈子融入到社会主义的大集体的飞跃过程中容易出现的思想问题, 确实起到了对症下药的作用。
在合作化小说中, 也有作家设置落后人物思想观念的转变或者是设置一个问题情景来宣传方针政策, 正是政策中包蕴的大公无私的伦理观念使得只顾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民众深受教育。 马烽的代表作《三年早知道》中的乡村能人赵满囤,入社后由一个令人头疼的自私自利的社员转变为任劳任怨一心为社的水利专家, 正是为了说明地委书记讲话的正确性:“个体生产转为集体生产,经济基础变了, 人们的思想意识也要逐渐起变化的。 ”小说按照扁平化人物的塑造模式,设置人物前期在集体生产的环境中令人喷饭的不合时宜的言行举止和后期真正全身心入社后焕发出忘我的劳动精神的鲜明对比, 使得经济基础的转变带来人的思想意识的变化的抽象哲理也为目不识丁的老农欣然接受。如果说,马烽在实现教化民众的伦理目的的时候是采用和风细雨的水磨工夫, 那么李满天在短篇《正副会计》中对具体的方针政策的阐释就采取了急功近利的方式。 小说设置的双记和凤英的对话, 对主题思想和叙事意图的表现太简单直接, 仅仅用双记的话——“那菜卖给国家,自然是支援了社会主义建没;同时,卖得的钱,又发展了咱们的集体经济;分给社员的,又满足了社员的利盆。这三方面……”来回应凤英的菜种好了获得大丰收“对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都有利”的结论, 由于没有情节的支撑, 自然显得比较枯燥无味。
三、 教育民众入社以实现政治伦理的目的诉求
教育和发动农民心甘情愿地加入合作社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是政治伦理所追求的最终效果。作为后发国家, 资本原始积累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只有采取集体经济的方式, 才能在有限的资源之内利用价格的剪刀差加强工业资源的配置。 站在国家的战略层面就必须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 改变土地所有制的形式, 扬弃几千年来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私有制,构建以集体为单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这方面,合作化运动对刚刚从弱肉强食的“丛林发则” 里拼杀出来的现代化民族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正如领袖毛泽东所认为的那样:“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 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 ”[6](P1432)在合作化小说中,对政治伦理观念作为指针, 引导民众改变自私自利思想加入合作社的复杂过程都有精致的描绘。 由于不同的作家感悟和理解方针政策方面的差异, 主体与客体之间相生相克的融合程度的深浅各别, 自然导致政治伦理在动员和教育民众的过程出现异彩纷呈的审美景观。
千百年来小亚细亚的耕作模式形成的农民既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又是只顾个人利益的私有者的双重身份, 作为代代相传的原型意识潜在地制约着农民伦理价值观念的转变。 农民生长的传统闭塞的文化环境不可能产生一大二公的伦理观念和公有化的集体耕作模式,所以,著名的评论家蔡翔认为中国当代的社会政治结构中存在一种“动员结构”,即“政党政治通过‘干部’完成对群众的动员和改造”。[7](P100)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中通过区委书记朱明的讲话将平静的乡村很快掀起合作化运动的高潮的外部动员因素暴露无遗, 在大会总结阶段提出的宣传、 个别串连、 三同一片等方法,发动时要对症下药、考虑做说服工作的人选资质、解决农民现实迫切的问题等,都显示出主流政治话语对民众的传统伦理观念而言的异质性,最后强调根据各乡汇报的形势再努力一下, 入社农户跟总农户的比例要达到区里要求的指标百分之七十。指标的制定和现实的汇报相结合,都可以看出动员结构在政治任务的完成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没有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大压力和舆论宣传对民众的心理产生的巨大冲击, 就不可能如此迅捷地掀起入社的高潮。由此可见,不是民众自下而上地自发产生合作化运动的热情推动社会主义向前发展, 而是干部作为政党政策的传达者积极动员的结果。 这就在文本反映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舆论宣传与实际的民众在务实精神的驱使下产生的疑虑情绪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比, 也在作者的情节铺排中留下了叙事的裂缝。
首先, 政治伦理采用今昔对比的方式显示出入社后的巨大优越性, 借鉴民间知恩图报的伦理观念强化入社的积极性和坚定性。 因为民众一旦决定加入合作社走集体化的道路之后,“集体主义成为国家占主导地位的道德原则,从此,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取代了封建宗法伦理道德, 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代替了封建宗法整体主义。 ”[8](P22)毕竟是异质的伦理观念对民众熟悉的宗法伦理观念和人性本能的自私意识强行改塑, 因此大量的合作化小说为了完成教化民众的任务, 才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新旧社会的生活对比来强化政治伦理观念的感召力。 西戎的《王仁厚和他的亲家》中的王仁厚在干部老高的教育下, 认识到从前是自私剥削的不公正之路导致少数人有钱多数人穷, 现在是连接国家和社员桥梁的农业社搞好了, 就不愁没好日子过。过去福荫后代长宜子孙的陈腐观念,在后辈儿孙集体劳动创造财富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已成为不合时宜的遗形物, 因此他才按照现代伦理观念对自己的儿女亲家富农罗成贵投机倒把贩卖粮食的行为进行揭露和批判, 自己身在社内心在外的尴尬矛盾状态终于在强大的政治伦理感召下回归到全身心入社的同一状态。马烽的《三年早知道》 中爱占小便宜的赵满囤由硬着头皮入社成为最难缠的社员到一心为社任劳任怨, 其心理嬗变的转捩点是社长甄明山以情感人的数落: 今年夏天下雹子遭受天灾仍然分得了比往年多的粮食,显示出投其脾性的物质话语所具有的激励机制;七月得急病, 是社员们连夜淋着雨给你请来医生后送入医院,没有现钱,是社里雪中送炭优先替你垫上吃药打针花下的一百多元钱。 这是借用知恩图报的传统伦理观念所打出的感情牌, 社里不计前嫌地关心和照顾他产生的感情的软化作用,使他决定洗心革面,做一名大公无私的新社员。 《灾后风波》(履冰) 以旧社会留下的破棉袄为道具说明遇到灾荒,有多少人家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今在党的英明领导和人民公社的集体力量的合力作用下战胜了困难和挫折, 两相对比对产生退坡思想的唐兴顺产生了巨大的心灵触动, 在王书记的谆谆教导下,他的恐惧、羞愧、后悔在忆苦思甜的语境中更加坚定了和农业社绝无二心的意志。 此外,张朴的《王国藩的故事》中的社长王国藩对不谙世事的小伙子的教导,《创业史》 中的梁生宝利用埋葬拴拴他爹的机会发表的讲话, 都是在新旧社会两重天的对比中宣传农业社的优越性。
其次,政治伦理以强大的话语优势对“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许诺造成了一定的压制。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多快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因此现代性的科层组织和讲究生产效率的现代理念, 都意味着组织起来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是历史和时代提出的必然要求。但自古以来一盘散沙自由散漫的状态养成了农民的个体自由伦理观念,根深蒂固的土地情结又使得他们不会轻易放弃到手的土地,千百年来的天灾人祸注定了民众的生存意识中特别注重物质的力量, 所以入不入社是一个与出身、财富、家庭没有必然关系的复杂问题。 伟大领袖毛主席看到了乡村生活观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要求对合作化运动不能采取简单地一刀切的方式强迫农民入社,认为“对于一切暂时还不想加入合作社的人, 即使他们是贫农和下中农也罢,要有一段向他们进行教育的时间,要耐心地等待他们的觉悟,不要违反自愿原则,勉强地把他们拉进来。 ”[9](P428)可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操之过急简单粗暴的现象时有发生,文本作为对现实生活的镜像式反映,在带有主观色彩的想象和描摹的过程中尽管受到主流价值观念的限制和规训,但还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留下了政治伦理在合作化小说中的鲜活面影。
当一个农民出于加入合作社可能会 “烂场合”、“饿肚子”、“干部多拿多占”等方面的顾虑,不愿入社的时候, 为了完成上级入社指标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会采取各种方式逼迫入社,这在《山乡巨变》 中对待中农王菊生不愿入社的问题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由于他的农具齐全、土地肥沃、肥料充足、技术一流、扎实肯干等有利条件,自然不愿入社被别人沾光, 但农业社的领导干部早就把他当作未来的社员,关键是采取怎样的方式,让铁石心肠的菊咬筋回心转意自愿加入农业社。 小说为此在所谓的自愿和实际的强迫的矛盾裂隙中铺排了大量的情节,无论是在猪栏原来贴着“血财兴旺”的地方,现在覆盖了“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参加农业社,大家同上升”的宣传标语,还是在他原来双幅门贴的两张花花绿绿的财神上, 也蒙上了“听毛主席的话 走合作化的路”的对联;无论是社长刘雨生对他讲述的在肥料、石灰、农药和新式农具方面,政府自然是先满足社里的制度,还是小学生扮演王菊生不愿入社的行为极尽嘲弄之能事,以至于“菊咬”成了小孩子彼此吵架的诨名;无论是农业社和王菊生一家劳动竞赛累倒他的娘子军和童子军以突显农业社的劳动积极性, 还是在他生产最困难的时候不计前嫌无私援助, 都是为了酝酿让他入社的条件打基础。可是,这样的入社自由还有“自由”的本原色彩吗?途径、方式和方法的无所不用其极与终极目的的绝对性之间的张力确实彰显出政治伦理的霸主地位。
四、结语
政治伦理独尊地位的形成也与话语的发出者的尊贵身份有密切的关系。 以不容置疑的口吻传达方针政策的人不是基层领导干部就是一心拥护党的路线的积极分子,这些“以各级劳模英雄和群众组织领袖为主体的乡村新式权威逐渐控制了乡村政权,并占据了乡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中心地位。 ”[10](P446)话语权的更迭意味着不同于传统的士绅阶层的伦理价值观念的变革, 大一统的政治伦理高扬一大二公、无私奉献、积极进取、勤劳苦干的时代精神的时候确实是理直气壮, 在没有任何其他力量对其进行制约的前提下, 它自身携带的物极必反的另类消极基因, 也会将其反面性的弱点暴露无遗。 《三里湾》中的退坡党员范登高在不入社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就是“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想坚持自愿原则就要摘除“党员的招牌”等政治话语的强大攻击下,也只能乖乖地缴械投降;《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在杨小四之类的干部压制下,“大字报”、“大辩论”、“乡政府”、“法院” 等政治名词携带的权威力量将她撒泼的心态给整治住了, 在落入杨小四设置的摘自由花实际上是偷社里的棉花的圈套之中, 只因按照乡村文化观念的本能骂了一句 “你是说话呀还是放屁哩?”就被三队长张太和剥夺了坦白的权利;《山乡巨变》 中的副社长谢庆元利用职权维护下村的小团体利益, 体现出地缘关系对他的伦理观念的影响,就被盛淑君、陈雪春等积极分子扣上“资本主义思想”的大帽子。
乡村绵延不绝流传千年,靠的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家庭、家族和宗族之间的和谐关系,社会契约和长老统治形成的教化力量要比成文的法律更有效果。 在新中国成立前,“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靠乡绅。 ”[11](P220)可以说这就是对乡村自治的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的最好概括。解放后乡村政权结构的发展变化,意味着蛛网式的国家机构深入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村长、村支书、会计、队长等乡村科层权力制度和机构的设置, 为合作化运动蓬蓬勃勃的开展和有效运转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但由于合作化运动的目的与民众从物质欲望出发改变现状的革命诉求发生了矛盾冲突, 农民实实在在的个体私利需求与优先满足国家建设需要的政治伦理之间的裂隙是难以调和的, 作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权力机构又不是压制民众的暴力机关, 因此民众在合作社富裕之后才能使得小家庭富裕的抽象意义上的继续革命的热情并不高,不愿入组、不愿入社的现实境况促使政策的制定者提出“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口号便是明证。“权威意识形态急切地希望在落后的文化环境中找出觉悟高、 思想先进的英雄人物作为道德楷模,来刺激和强化具有‘现代化特征’的社会主义建设。 ”[12](P75)因此,在合作化小说中塑造如此众多的合作化带头人和积极分子作为示范的榜样和楷模, 对民众的入社积极性的舆论宣传上升到国家政治的层面上来表现就没有什么可奇怪之处, 政治革命对民众物质欲望的许诺与经济革命脱物质化的伦理要求之间的矛盾背反是合作化小说难以弥合的裂隙, 留下的美学症候确实需要从政治伦理的角度抱着理解的态度进行分析。
——浅评《入社礼的仪式与象征:关于生与再生的秘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