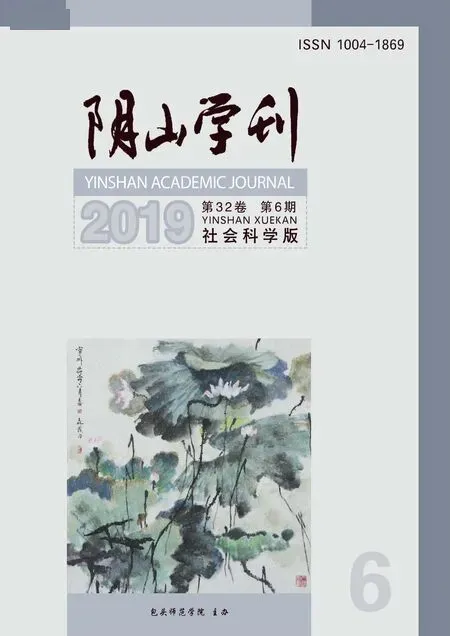丰 饶 之 海
——资源视域下的海疆史研究*
王 楠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研究所,北京 100732)
诚如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所言,历史学家对当代实际问题做出的最大贡献是推崇复杂,而不是简化思维。[1]每一个钻进历史万花筒里的人,都会耳濡目染形形色色的历史讲述方式——即所谓的“历史叙事”(Historical Narrative)。
海疆史研究者也不例外。然而,当我们动笔之际,可能会不自觉地坠入“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中。“宏大叙事”是以某种线索因素为绳结,把已经发生的事情编排成一个连贯的历史过程,同时为线索因素的合理性进行辩护,贯穿于对历史过程的整体叙述中。按照李怀印的观点,在线索因素的牵引下,不同的历史叙事——尽管其细节各异——都围绕着共同的历史主题而展开。如此类推,历史便理所当然地被建构成一条运动轨迹。[2]过去,它往往影响着人们对历史事件的讲述。换言之,如果海疆史研究者试图推陈出新,那么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另辟蹊径,寻求更贴近日常生活的新基调。
海洋承载的舟楫之便和渔盐之利,尽管代表了人类与海洋间最为本质的互动交流方式,却并未得到足够关注。杨国桢等学者已经指出,海洋既是生产活动的背景,也是生产活动本身。唯有尊重海洋自身的发展演变,才能在陆海互视中给予其准确的定位。[3]那么对学者而言,如何发掘和关注海疆的物质性,又如何在资源视域下描摹海疆的历史?
一、海疆的物质性
从鸭绿江口至南沙群岛的万里海疆上,活跃着形形色色的人群——渔民、船员、水警、海军、科学家和油矿工人,他们的命运看似各不相同,却都与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交织在一起。近年来,中国正被愈演愈烈的黄海渔业争端、中日钓鱼岛争端以及南海争端所困扰。放眼全球,海洋争端同样改变着波斯湾、地中海和鄂霍次克海等诸多区域的地缘政治格局。假如涉海问题仅仅发生于当代,那么平心而论,历史学家或许应该缄口不言。事实并非如此,今天的诸多海洋争端,往往都能从历史中追根溯源。
我们总是将历史和法理比喻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两只拳头,而两者的境遇却迥然相异:当国际法和海洋法研究蓬勃开展之际,海疆历史领域始终不温不火。我们挥出了一只拳头,却把另一只拳头藏进口袋里。很多学者坠入西方人设置的陷阱,被拖入喋喋不休的、与历史渐行渐远的论战,甚至以当代国际法和海洋法为基准,拷问中国对海域和岛礁的开发管辖等历史活动的合法性。撇开当前学术界重法律、轻历史的风气,在国家海洋权益博弈的舞台上,历史不应该成为被攻击的标靶。通过追溯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海疆史研究提供了一种知识储备,它们或能揭示治理海疆的经验,或能裨补国际法和海洋法的缺漏,或能在外交维权中派上用场。
在大多数语境里,海疆这一词汇本身带有遥远、偏僻乃至疏离的色彩,其英文词条(maritime frontier)也脱胎于“边疆(frontier)”——即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笔下的那道不断向西推移、罪恶与荣耀交相辉映的拓殖前线。[4]受到上述观念的影响,研究者们往往遵循一种纯粹的政治叙事,把海疆描绘成军事活动的前哨站、国家利益的博弈场和商业贸易的交通线。这种叙事框架固然包含了一些物质性因素,但仍然不够“唯物”,因为它缺乏对生态和资源的描述。
毋庸置疑,“海疆”之于生活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从哼唱渔歌、摇橹呐喊的传统渔民,到驾驶渔轮、操纵拖网的现代渔工,对他们而言,海疆不仅象征着国家边界与权益,更承载着一种必不可少的谋生之道。先辈们利用海洋和搏击风暴的历史何其久远:从铁人、木船、樯橹和风帆的时代开始,人类的军事、外交和经济手段,大都由获取鱼群、海盐和矿藏等资源的需求衍生而来。从资源与技术角度,我们可以甄别海陆生产方式的差异性:在陆地上,河流和山峦把土地切割成不同的单元,农民在田地四周种植藩篱、开通阡陌,彼此划出显著的人造界限。而海上生产则截然不同,根据鱼类的资源分布及数量波动,渔民不断调整技术形态和作业区域,甚至跨越黄海从事“赶鲱鱼”等迁徙性渔业,[5]并以新的方式延续至今。无论海疆观念形成于何时,先辈们早已探索、穿越和开发这些被当代人视为边界的海域。
我们应该承认,现实中的海疆并非如理论般灰暗,它是一座布满资源、等待人类攫取的资源库。过去学者们看待海疆的方式,可能有些狭隘。以资源为纽带,海疆历史与现实呈现出一种跨越生态、社会和文化等层面的交叉性,而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纯粹的政治层面。在涉海研究中,我们不应撇开渔盐之利和舟楫之便谈论海疆,也不要拒绝从政客、商贾和渔民的生活经历中捕捉灵感。
二、考察海疆史的资源维度
根据权威学者的界定,海疆史的研究范围包括我国拥有主权的海域、拥有主权或管辖权的岛屿以及沿我主权海域的陆地部分(海岸线);中国海疆史的学术范畴包括海洋疆域史、海洋政策与海洋思想史、海防史、海上丝绸之路和海上贸易史等。[6]
与此同时,追溯海疆历史之前,我们绕不开另一个学术概念——“海洋史”。翻阅《牛津大百科全书·海洋史卷》(OxfordEncyclopediaofMaritimeHistory),可以发现海洋史的研究主题相当丰富,包括渔业、捕鲸、国际海洋法和海军的历史,造船和航海的历史,海洋科学(如海洋学、制图学等)的历史,海洋勘探、海洋经济贸易、海洋航运、海洋旅游的历史,文学艺术中有关海洋主题的历史,水手、乘客以及以海洋为纽带联结的陆地社会的历史。[7]我们必须承认,海洋史是一个非常关注资源和交流的研究领域,它倡导的理念对海疆史研究大有裨益。
如果把前文的海疆史概念搬过来,与海洋史相互比照,我想任何人都很难拒绝一种解释:即海疆史立足国家权益,关注享有主权的海域、岛礁和海岸线,而海洋史更偏重于以资源开发和海上交流为纽带的叙事模式。这并不妨碍海疆史与海洋史之间的联系——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在海疆史研究中,关注的对象当然是海洋,而海洋是浓缩人类文明发展史诸多因素的重要载体,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人类与海洋之间的历史关系、探索海洋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8]事实上,无论海疆史学家也好,海洋史学家也罢,都不太介意两者的差别:一方面,没有人否认韩振华、吴凤斌等学者对越南某些地名的考证是海疆研究,即使那些地方现在并不属于中国;另一方面,也没有人以资源开发和海上交流为准绳,将区域性的海洋历史地理研究完全排斥在海洋史的门槛之外。
谈到学科归属,早在20世纪90年代,韩振华先生就指出,南海史地是边疆史地的组成部分。[9]其他从事海疆问题研究的专家,也多半视海疆历史为边疆学(Borderland Studies)的一个分支。但是在探讨历史上中国海疆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要素时,我们很难将自身的研究同海洋史学者区分开来。如果为了凸显差别,刻意制造“海疆政治”“海疆经济”“海疆文化”“海疆社会”之类的新概念,恐怕也只是命名上的标新立异,而研究对象和方法如出一辙。不过换个角度,我们会发现海洋史学家也经常使用海疆的概念。2014年,有学者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海洋环境史的评论——《被遗忘的海疆》,[10]标题很文艺而又不失严谨——我们当然想知道此前遗忘了什么,但不会纠结于那些东西到底属于“海洋”还是“海疆”。所以,不要刻意用学科归属来切割内容相似的研究,应该允许“亦此亦彼”的案例存在。我们将很多案例纳入海疆史的范畴,同时也承认它是海洋史的一部分。反之亦然。
为了将海疆史从僵化之中摆脱出来,我们借鉴了沃斯特提及的研究层面:一是地球的各种系统——包括气候、地理和生态系统——伴随时间的变化,二是人类自这些系统中谋求生计的生产模式的变化,三是文化态度的变化及其在艺术、意识形态、科学和政治中的表现。[11]无论谈及海洋环境、海洋经济还是海洋权益,资源在其历史发展中的角色都颇为相似,当代海洋争端本身往往裹挟着资源争端。
基于中国海疆史的研究范围和学术范畴,如何嵌入资源维度呢?将沃斯特提及的三个层面移植过来,我们便发现了考察海疆历史的新线索:一是海洋资源及其社会需求,二是以海洋资源为纽带的生产技术、政策法制和冲突争端,三是由海洋资源衍生的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
三、叙述海疆史的资源线索
1.海洋资源及其社会需求
从历史进程看,人类对海洋资源本身的需求处于不断增长之中。早期人在捕鱼拾贝的同时,也自海洋中采集了少量奢侈品。例如,南海所产的玳瑁,自古便受到风雅之士的推崇。汉朝人将鳞片加工成宝石,镶嵌于饰品上。到了明中期,玳瑁被皇室官宦作为身份的象征。[12]再比如,公元3世纪,南方海滨出产一种外形奇特的蠕形动物,吴国人把它唤作“土肉”,炙烤后食用。[13][14]总体看来,传统时代的人们除了果腹之需,对海洋资源的需求量并不大。
到17至18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根据美国学者罗威廉(William T. Rowe)和濮德培(Peter Purdue)等人的描述,清帝国开始了所谓的“内亚转向”,“中国西进”等一系列事件均发生于此际。而日本学者松浦章认为,中国在海洋贸易中的某种“海洋转向”也不容忽视。因为在清朝军队西进的同时,满载着丝绸和瓷器的中国商船也频频扬帆出海。当然,“内亚转向”抑或“海洋转向”,无非是历史学家集中地看某一类史料的结果。[15]
驱动所谓“海洋转向”的因素,除了松浦章提及的海上贸易外,还有近海资源的枯竭和社会需求的变化。正如包茂红所言,如果将近代环亚洲海域视为一个整体,那么在这一时期,海洋渔业和矿业资源得到广泛开发利用,不同国家之间经常为争夺资源发生战争。[16]这些没有硝烟的战争,酿成了前所未有的资源危机。
19世纪20年代,江苏官员王文泰有感于近海鱼类和贝类的数量及个体饱满度下降,他忧心忡忡地写道:东海县和灌云县曾盛产蚶子、干贝、蛏子和海螺。由于需求过大、采集频繁,目前近海贝类濒临灭绝。如果不发展远海渔业,那么近海渔获物终将被捕捞殆尽。[17]今天的海洋资源危机和跨国性渔业争端,也印证了王氏的警告。
总之,从物质和社会需求的线索出发,海疆史研究可以关注生物种群丰歉对海洋资源争端的作用,探讨资源本身对海疆民众生计的重要性及其对海疆社会经济发展的持续影响力。
2.以海洋资源为纽带的生产技术、政策制度和冲突争端
在海洋资源开发史上,古代中国人曾经占据优势。比如,借助先进的航海技术,汉唐的使节和商人经常穿越南海,去东南亚和阿拉伯地区进行贸易。长期以来,中国渔民以岛礁为基地,捕捉鱼类、采集珊瑚和拾取马蹄螺。一些考古证据表明,他们的足迹从东沙群岛不断向南延伸。相比之下,南海周边国家在早期资源开发中并不活跃。19世纪前叶,一些名为“黄沙队”“长沙队”的越南民间组织曾多次到近海岛屿,捞取沉船上的珠宝。[18]有人推测打捞队是在西、南沙群岛作业,而很多中国学者指出,这件事未必可信。[19]退一步说,即使打捞队登上了岛礁,仍然不能作为争夺领土主权的依据,因为它缺乏中国那样系统的开发历史资料。在国际法学家看来,这也远非一种持续性的经济剥削和行政管辖。
随着时间推移,西方人通过海上征服攫取的经济利润,远超过中国人耕海牧渔的收益。经济史学家一般认为,由于生产技术和劳动力的制约,西方人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模式(包括生产规模、机械化程度以及劳动者技能等要素)更易催生内在动力。
以民国前期南海诸岛的资源开发为例,可以看到制度、技术等要素扮演着何种角色。1910年,广东地方官员开始组织南海诸岛的磷矿开发,同时邀请商人投资经营渔业。一批技术人员登岛考察矿区,并监督挖掘工作。从东沙岛采挖的鸟粪须由香港转运至广州,收益不敷成本,政府运营的磷矿开采很快就变得难以为继。1912年,新成立的民国广州军政府招揽商人继续开发磷矿。商人们获悉这一消息后,纷纷致函军政府开发东沙岛的鸟粪、水产和盐业。他们手持采矿执照,甚至得到政府配备的驻岛警察。然而在国内,磷矿加工业并不成熟,中国商人所采的磷矿大部分要廉价贩卖至日本加工,再由日本商人将磷肥倒卖给中国农民。由于利润不高,中国商人何瑞年打着“合作开发”的幌子,把采矿权出卖给日本磷矿商以坐收租金。岛礁磷矿开采中出现的非法套利活动,原因之一便是中日工业生产设施的差距。1928年初,沈鹏飞率领一支由部委代表、国民党员、军事将领和科学家组成的调查队登上西沙群岛,查封了何瑞年的工厂。根据工厂档案披露,1919年,一家日本公司的分公司便在岛上开采磷酸盐。此后七八年里,每月都有船只由此处向分公司提供原材料来源。为了抵制日本进一步入侵,沈鹏飞敦促中国及早成立公司,招募工人登岛开矿。但他附带了一个避免触怒日本人的条件:尽管何瑞年的傀儡公司被吊销了许可证,但新的登岛者必须与日本人达成协议,才能接管和使用先前的设备。事实上,这项条件没能避免财产纠纷,当中国工人登岛接管设备时,遭到日方的抵制,以致广州当局不得不召回这些无事可做的工人。如我们所知,中国调查队几乎不受挑战地宣示了主权,而登岛开发和居住等计划却不了了之,可见国内的磷矿加工业并不能与之匹配。广州当局意识到,鸟粪开采必须结合磷肥加工业的发展。后来批准开设的几家磷肥工厂,都具备从开采到加工的完整生产链条。[20]1932年,当广州当局决定收购私营肥料工厂时,国家也随之包揽了磷矿的开采权和经营权。
当然,海洋资源开发的效率和利润,并非完全取决于工业力量。在很多场合,它仅仅是劳动者的技能差异而已。举个例子,东沙群岛近海盛产一种海藻——“海人草”,可以医治肠道蛔虫症。1917年以后,商人们获得政府批准,纷纷登上东沙岛捞取海人草。他们起初雇用了很多中国渔民,却缺乏劳动效率,连最强健的渔民都无法忍受连续几天潜水作业。即使潜入水中,从珊瑚礁中剪下海人草也殊为不易,后来,渔民就逐渐消极怠工。就在商人们感到棘手的当口,有人听说琉球渔民自幼便被强迫泡在海水里,可以潜水十多分钟,擅长从事艰苦的水下劳动,于是商人们尝试雇用琉球渔民采集海人草。[21]中日渔民之间,原本只存在潜水和采集技能的差异,可是在近代南海的紧张局势下,这种差异致使日本商人有隙可乘,石丸庄助、仲间武男和松下嘉一郎等人先后多次潜入东沙岛,盗取磷矿和海人草。[22]
总之,偱着这一线索,海疆史可以讲述政策制度和技术模式。从内容上说,它涵盖了国家与地方具体的资源开发政策制度,以及以海洋资源为纽带产生的技术和生产模式的历史变化。
3.海洋资源衍生的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
学者们通常认为,中国海疆文化以中华文化为主体,同时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一方面,由于大陆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大陆文化不断移入海岛,使海岛文化具有与大陆相似的传承性,从而在海岛上形成与大陆同源同根、代代相传的中华文化。[23]另一方面,由于海疆自身的开放性,必然发生频繁的文化互动、碰撞和交融,在中华文化基础上糅合外来的异质成分。上述观点主要基于文化的主体性和兼容性。那么抛开属性,从具体内容来说,与资源相关的海疆历史文化大致有两类:
第一类是人们对资源本身文化认知的历史变化。众所周知,由于海洋意识、海权观念、海洋战略等因素在近代国家建构中的地位日渐重要,人们在审视海疆的资源开发活动时,往往赋予其事关国家民族立场和权益的某种象征性——我们承认,有关海疆资源开发活动与海洋权益之间联系的思考,在古代中国并非完全找不到萌芽,但它与民族国家概念的结合却发生于近代以后。
渔业资源开发就被赋予过这样的意义。清末民初,改革派官员张謇曾力陈捕鱼权与海权的联系:海权属于国家,而捕鱼权属于人民,两者不可分割。不厘清捕鱼权,则不能巩固海洋权益;不增强海上力量,则不能捍卫捕鱼权。世界各地联系日益紧密,海上贸易禁令已经解除,所有国家都在努力建设海上力量,倘若中国不及时制定计划,捕鱼权将遭受侵犯,海上力量也会逐渐衰微。到了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商人重新搬出张謇的“海权即渔权”思想,试图说服民国政府对外国侵渔活动做出回应。1925年以后,山东沿海的水警、海军以及渔航局实施护渔方案,扣押日本渔船并处以罚金,暂时遏止了日本侵渔活动。[24]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渔船大量驶入舟山渔场从事生产,几乎将大黄鱼和真鲷捕捞殆尽。中国外交部多次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认为此举侵犯中国的领海主权和渔业权益。
类似的情形还存在于岛礁矿产资源开发中。清朝末年的东沙岛事件引起中国政府的警觉,并通过军事巡海宣示对西沙群岛的主权。但是,贸然派出驻岛守军可能会遭到日法等国的干涉,所以李准呼吁晚清政府:“招徕华商承办岛务,官为保护维持,以重领土,而保权利”,言下之意,采取招揽华商登岛的方式,造成经年累月开发的既成事实,可以逐渐平息岛礁归属权的争议。后来二十多年里,晚清政府及其继承者民国政府大致延续了这一策略。在中国官方委派下,科学家数次勘测西沙群岛磷矿石的资源储量和化学成分。民国政府发布公告招商后,商人们纷纷响应,要求将渔业、盐业和矿业一并承办,认为没有比这更好的护卫领海主权的方式了。20世纪30年代,面对法国考察勘测和日本资本渗透的挑战,中国又逐渐将磷矿的开发经营权收归国营。这些资源开发活动看似柔和,却被证明是一种捍卫南海岛礁的主权和相关权益的可行之策:20世纪最初30年里,没有其他国家公开声索过南海岛礁的主权。直到1933年,法国制造“九小岛事件”后,南海局势才由暗流涌动走向剑拔弩张。
第二类是现代人看待先辈们围绕资源产生的一系列开发、经营活动的方式的历史变化。拿南海诸岛来说,中国考古学家在一些岛礁上发现了大量中国文物,时间从汉唐跨越至明清时代。比如,甘泉岛有几座珊瑚小庙,还有大量灶具、陶瓷和钱币,可以推测有唐宋渔民暂居于此。[25]而越南方面的考古学家则声称,他们发现了“越南风格”的古代文物。
那么,如何理解当代学者之间的这种分歧?换句话说,南海岛礁上的出土文物,如果可以追溯到汉唐时期,那么它们属于中国风格还是越南风格呢?众所周知,自公元1世纪马援率领汉朝军队征服九真开始,到10世纪中叶,越南北部始终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因此,国际法学者可能会认为,这种争论的政治意义大于学术意义。[26]
总之,在这一层面上,海疆史学者可以探寻海洋资源所附带的文化意义:包括管理开发权与国家主权之间的联系,开发活动与国家、民族和边疆观念建构之间的联系,以及现代人在怎样的语境和立场下,对那些涉及资源开发的历史事实进行何种文化解读等具体问题。
结 语
先民对海洋资源的依赖主要为渔盐之利,仅仅掺杂着少量的奢侈品需求。明清之际,随着经济、技术和社会需求的变化,民间出现了以获得更多资源为目标的扩张运动——人们在拓展陆地资源边疆的同时,也朝向资源丰饶的远海进军。这类所谓的“海洋转向”,不仅丰富了传统的资源库,而且酝酿了一种朴素的疆域观念。
17世纪以后,伴随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传统意义上的边疆观和海疆观逐渐消解,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开始萌生和发展。当不同国家的资源开发范围发生冲突时,需要一种更确切的、凌驾于“资源边疆(海疆)”之上的主权概念。例如,无论是黄海的传统渔场,还是南海的历史性权利区域,由于它们位于不同国家政权之间,所以并不排除资源开发权共享的可能性。为了在海洋资源争端中占据优势,出现了一系列现代意义上的涉海主权行为。围绕资源的开发、管控与争端,中国官方和民众广泛地参与涉海活动,共同推动了我国海疆固化和底定的进程。
在海疆的缔造进程中,海洋资源所衍生的历史文化,与现代海洋主权的概念发生了交叠。传统时代,当渔民把渔场摆在遥远的岛屿和海域时,这些地方往往被视为我国的海上疆域;围绕海洋资源的采集利用行为,被视为对海疆本身的开发和管控。古人对海疆主权等概念的阐释,与当代人存在显著差异。为了服务于眼前的涉海外交,历史学家往往需要寻求传统海疆观与现代海洋主权观念之间的契合点,以便适应激烈的法理论战需求。海洋资源的开发管控行为,便被赋予现代意义上的文化阐释。这两种阐释方式,构成了叙述海疆历史的文化线索。
倘若海疆历史与生活毫无牵连,那么按照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说法,它仅仅是一部死去的历史,一部编年史。一旦我们忽略人的存在,就抛却了海疆历史中真实、柔和而富有感染力的一面。如同博尔斯特(W. Jeffrey Bolster)呼吁的那样,历史学家应该公正地审视人类及其文化,揭示个人的意愿、行为、价值观以及社会机构所扮演的角色。[27]无论海疆史被寄予多么强烈的政治功用,它本质上仍属于人类历史范畴,离不开官员、渔夫、水手和商贾等历史角色的缔造。当我们超越纯粹的考据和檄文式的语言,与活生生的现实发生关照时,海疆史研究便找到了它的物质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