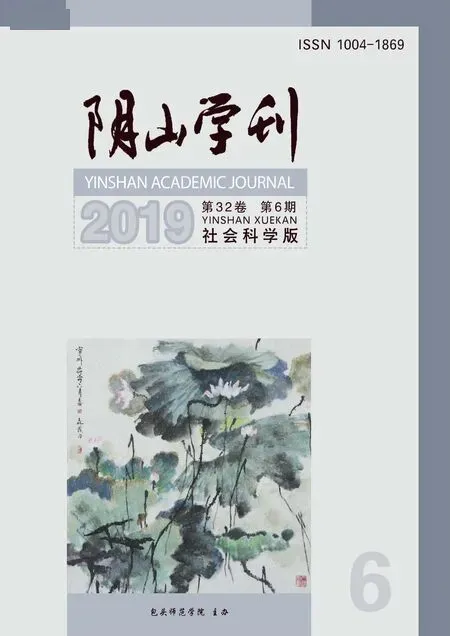《史记》中门客的叙事功能*
赵 建 军
(包头师范学院 文学院,内蒙古 包头 014030)
引 言
作为史传文学的开山之作、巅峰之作,《史记》的主体自然是那些位高权重的王侯将相。他们参与历史事件,影响历史进程,是当之无愧的历史的主角。但在春秋、战国乃至秦汉之时,有一个边缘性的群体——门客也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成为此一时期活跃于历史舞台的一支有生力量。在《史记》中,他们人数众多,时隐时现,构成《史记》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即试图考察这一群体在《史记》叙事中的作用。
门客,又有食客、客、宾客、门人等别称,是寄食于权门且效力于权门的才智之士。平王东迁以后,史称“春秋”,礼崩乐坏,王权衰落,诸侯争霸,大夫崛起。这一剧烈的历史变动导致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即由传统的贵族—平民二元结构逐渐转向新型的皇帝—官僚—庶民的三元结构。大致说来,庶民包括士、农、工、商四种身份。士号称“四民”之首,或来自于失势的贵族,或来自于有才学的庶民,士阶层之勃兴是春秋、战国之际的一个重要历史现象。他们或者成为学士,或者成为隐士,或者成为侠士,而其中寄食于权门且效力于权门的一批人,即成为门客。
门客的身份并非一成不变。有些才智杰出、功勋卓著的门客会脱离原来的恩主,跻身于权贵的行列,从而成为《史记》某些篇章的传主。如蔺相如,本来“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1]2439,出使秦国,不辱使命,完璧归赵,“赵王以为贤大夫,使不辱于诸侯,拜相如为上大夫”[1]2441,事见《廉颇蔺相如列传》。又如李斯,西游秦国,先“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1]2540,后累官至丞相,是《李斯列传》的传主。像这样的人物,虽曾身为门客,但后来发迹显达,已成为传主,本文不视之为门客,当然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本文所讨论的对象,只是始终作为配角的门客。
一、推动情节发展
《史记》的主体部分是“本纪”“世家”及“列传”,这三部分中的历史人物都是历史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创造了恢弘诡谲的历史。司马迁以这些历史人物为单元,一篇一人,或一篇数人,在纪传体的框架内拼合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图卷。写人必然叙事,通过一系列经由选择与安排的事件,才能建构人物生平,刻画人物个性,揭示人物命运。每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即传主,经过司马迁的生花妙笔的刻画,跃然纸上,血肉丰满。在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传主无疑是事件的当事人、主人公。但在有些人物传记中,传主会遇到困扰,甚至身处险境,当此危难之际,便会有门客现身,或者出谋划策,为恩主指点迷津;或者挺身而出,为传主排难解纷。可以说,在某些关键时刻,门客展示了独特的才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推进了情节的发展。
《史记》的《张耳陈馀列传》自然是以张耳、陈馀二人为传主,叙述了两位乱世英雄由合到分的人生经历。但在这篇传记中,门客频频现身,在二人的历史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至司马迁在文末的“太史公曰”中特别提到:“其宾客厮役,莫非天下贤俊,所居国无不取卿相者。”[1]2586今即以《张耳陈馀列传》为例,说明门客在情节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张耳尝亡命游外黄。外黄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张耳,乃谓女曰:“必欲求贤夫,从张耳。”女听,乃卒为请决,嫁之张耳。[1]2571
张耳本为亡命之徒,客游外黄。外黄富人的门客慧眼识珠,认为张耳可为“贤夫”,外黄富人父女听从了门客的建议,把张耳收为赘婿。此后在外家的资助下,张耳得以客游天下,并结识刘邦,为他此后追随刘邦建功立业奠定了人脉基础。
其后张耳、陈馀加入陈涉义军,从武臣征讨河北之地,并拥立武臣为赵王。赵王武臣使部将韩广北略燕地,韩广却自立为燕王。武臣率军攻打燕地,反被燕人擒获。如何解救赵王武臣,成为张耳、陈馀的当务之急。此时,门客中有专司烧火做饭的“厮养卒”主动请缨,出使燕国,游说燕将。
赵养卒乃笑曰:“君未知此两人所欲也。夫武臣、张耳、陈馀杖马箠下赵数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岂欲为卿相终己邪?夫臣与主岂可同日而道哉,顾其势初定,未敢参分而王,且以少长先立武臣为王,以持赵心。今赵地已服,此两人亦欲分赵而王,时未可耳。今君乃囚赵王。此两人名为求赵王,实欲燕杀之,此两人分赵自立。夫以一赵尚易燕,况以两贤王左提右挈,而责杀王之罪,灭燕易矣。”燕将以为然,乃归赵王,养卒为御而归。[1]2577
燕国以赵王武臣为人质,要求赵国割让土地;赵国既想迎回武臣,又不想割让土地,两国相持不下,“张耳、陈馀患之”[1]2576。这名门客以一介之使游说燕将,摇唇鼓舌,陈说利害,未失寸土,使赵王武臣得以安全返回。由这名“厮养卒”之口,读者也可以知晓,张耳、陈馀才高志大,终究不肯屈居人下,这预示了二人最终“据国争权,卒相灭亡”[1]2586的悲剧结局。
其后另一部将李良反叛,杀死赵王武臣。张耳、陈馀侥幸得以脱身,面临事业如何继续的问题。当时局面,可谓危如累卵,一着不慎,可能满盘皆输。好在关键时刻,又有洞察时势而见识高明的门客现身。
客有说张耳曰:“两君羁旅,而欲附赵,难;独立赵后,扶以义,可就功。”乃求得赵歇,立为赵王,居信都。李良进兵击陈馀,陈馀败李良,李良走归章邯。[1]2578
这名门客为张耳、陈馀分析形势,提出扶立赵国后人以收揽人心的正确建议,二人从善如流,勠力同心,不但稳住了局面,而且打败了李良。扶立赵歇,复兴赵国的事业,是张耳、陈馀一生中最后一次成功的合作。
其后赵王赵歇、张耳被秦将章邯围困于巨鹿,陈馀作壁上观,赖项羽之力始化险为夷。战后张耳指责陈馀见死不救,陈馀一气之下,脱解印绶,假意做出交出兵权的姿态。是否收回陈馀的兵权,张耳犹豫未决。
客有说张耳曰:“臣闻‘天与不取,反受其咎’。今陈将军与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张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1]2580
张耳听从门客的建议,顺势收回了陈馀的兵权。张耳、陈馀本为患难与共的刎颈之交,经巨鹿之战,彼此产生嫌隙,但尚有转圜的余地。而张耳门客的一番话,用冷冰冰的权力斗争哲学否定了温情脉脉的至交情谊,激化了矛盾,导致二人关系急转直下,由心生嫌隙迅速变为彻底绝裂。
其后项羽分封天下,陈馀未得封赏。
陈馀客多说项羽曰:“陈馀、张耳一体有功于赵。”项羽以陈馀不从入关,闻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县以封之,而徙赵王歇王代。[1]2581
陈馀的门客说服项羽,陈馀才得以封侯。陈馀被封为侯,为其嗣后进一步崛起奠定了基础,也为其嗣后与张耳刀兵相见埋下了伏笔。
其后陈馀因怨恨项羽封赏不公,联合齐王田荣叛楚,并首先发兵偷袭常山王张耳,二人关系遂由和平相处转变为敌我斗争。“张耳败走”,打算投靠项羽。
甘公曰:“汉王之入关,五星聚东井。东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虽强,后必属汉。”故耳走汉。汉王亦还定三秦,方围章邯废丘。张耳谒汉王,汉王厚遇之。[1]2581
门客甘公通晓天文,以天象为由,建言张耳归附刘邦。这无疑是张耳一生中最为关键的一次选择。
其后韩信与张耳一起攻灭赵国,“斩陈馀于泜水上”[1]2582。二人的关系最终以兵戎相见、陈馀被杀画上句号,不能不使人感慨欷歔。张耳与陈馀本为至交,终成仇敌,二人关系的变化与势力的消长既是个性、形势使然,也是门客活动促成的结果。
其后“汉立张耳为赵王”[1]2582。张耳去世后,其子张敖继位。张耳的门客贯高等因刘邦傲慢无礼,自作主张,想要刺杀刘邦,被人告发,赵王张敖被捕。在其他同案犯都畏罪自杀的情况下,“贯高与客孟舒等十馀人,皆自髡钳,为王家奴,从来”[1]2584,极力为赵王鸣冤脱罪,终竟取得刘邦的信任。最终,赵王张敖不仅被无罪释放,还被封为宣平侯。
张耳与陈馀身丁乱世,一生跌宕起伏,感情由合到分,其经历颇富戏剧性与传奇性。在这两人的传记中,尤其是一些关键时刻,门客一再出现,为他们剖析利害,建言献策,甚至亲力亲为,以身报主,其言行或者消弭冲突,或者造成矛盾,从而推动情节向前发展,影响了他们的人生和命运。在《史记》中,这样的情况不乏其例,如为后世所熟知的毛遂自荐、鸡鸣狗盗等事,亦属此类。
二、衬托人物个性
《史记》是历史与文学的完美结合,司马迁写《史记》,不是流水账式地记载人物生平履历,而是能“在实录的基础上进行了形象化的塑造,不单写人物事迹,而且写出了人物的性格和灵魂”[2],这是《史记》作为史传文学的主要成就。《史记》中有些人物形象的塑造,即与门客相映衬,也是司马迁采用的一种刻画人物的方法。
以门客映衬恩主的人物个性,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正面衬托,一种是反面衬托。所谓正面衬托,就是在塑造恩主的人物个性时,门客与之良性互动,相互成全,取得相得益彰的效果。如《管晏列传》写春秋时齐国的名相晏婴,指出他为政“以节俭力行重于齐”[1]2134的特点,但重点却在于表现晏婴的善于知人的特点。以下事件即服务于这一宗旨:
越石父贤,在缧绁中。晏子出,遭之涂,解左骖赎之,载归。久之,越石父请绝。晏子戄然,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免子于厄,何子求绝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方吾在缧绁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1]2135
晏婴知道越石父虽在缧绁之中,却是贤德之人,所以才肯“解左骖赎之”,知人爱贤之心昭然可见。但虽有其心,而未尽其礼,虽然赎免了越石父,却表现出主人、恩人的傲慢,“弗谢,入闺”。越石父主动请求绝交,指出晏婴“知己而无礼”的错误。在这件事情中,晏婴与越石父以恩主与门客的关系,更像一对诤友,越石父及时指出晏婴的错误,晏婴及时改正了自己的错误。有了越石父的衬托,晏婴显得不仅知人爱才,而且诚恳谦恭,形象更为动人。
战国时代养士之风最胜。“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1]2510四人合称“战国四公子”,就中信陵君最能得士。“公子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1]2377如何表现他的“仁而下士”呢?司马迁不惜笔墨,穷形尽相地叙述了他邀请夷门侯生赴宴的过程。“置酒大会宾客”之时,信陵君“自迎夷门侯生”。“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何等傲慢,但“公子执辔愈恭”。侯生又提出绕道去看他的朋友朱亥,并且“故久立与其客语”,而“公子颜色愈和”。最后,“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1]2378。太史公叙事,笔法疏荡变化,讲究虚实详略,其实而详者,要么是历史大事,要么有助于人物刻画。迎请侯生一节,非关政治军事,算不上历史大事,但对于信陵君形象的塑造,却是至关重要。在这一过程中,主客之间的关系既见张力,更有和谐,如同双簧一样步步推进,最终成功地塑造了信陵君“仁而下士”的形象。
秦汉之际的田横,继乃兄田儋、田荣之后为齐王。在刘邦统一天下后,田横先是“与其徒属五百馀人入海,居岛中”,后“与其客二人乘传诣雒阳”。但中途止步,并且自杀。理由主要是:“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刘邦“以王者礼葬田横”后,“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刭,下从之”。后刘邦又征召其馀尚在海中的五百人,这些人“至则闻田横死,亦皆自杀”。田横认为臣事刘邦是耻辱之事,可谓不甘人下;不甘人下而自杀身亡,可谓刚烈。他的门客也义不独生,自杀殉主。主客能同生共死,同样具有刚烈的性格。以至太史公感慨道:“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1]2648-2649
在《史记》中,还有主客之间形成反衬关系的情况。如《魏公子列传》中:
秦闻公子在赵,日夜出兵东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请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诫门下:“有敢为魏王使通者,死。”宾客皆背魏之赵,莫敢劝公子归。毛公、薛公两人往见公子曰:“公子所以重于赵,名闻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庙,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语未及卒,公子立变色,告车趣驾归救魏。[1]2383
信陵君窃符救赵之后,滞留赵国。经毛公、薛公两人提示劝说之后,幡然醒悟,才返回魏国。在这件事情上,信陵君显得怯懦而昏聩,而毛公、薛公两人却能审时度势,剖析事理,颇有洞见、远见。
太史公作《酷吏列传》,“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为声”[1]3154。其中张汤不仅以酷烈著称,而且“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1]3138,办案则“舞文巧诋以辅法”[1]3140,是酷吏的典型。
汤之客田甲,虽贾人,有贤操。始汤为小吏时,与钱通,及汤为大吏,甲所以责汤行义过失,亦有烈士风。
田甲作为张汤的门客,不是阿附顺从,而是能指责张汤“行义过失”,故而太史公称其“有烈士风”。田甲之“有贤操”与张汤的刻薄寡恩、希颜承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酷吏又有杜周,“其治大放张汤而善候伺。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1]3153如此行事,招来一位门客的责问。
客有让周曰:“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这位门客的责问正中要害,而杜周不思悔改,狡黠自辩,门客义正辞严的揭露,反衬出杜周弄法媚上、怙恶不悛的丑陋嘴脸。
三、抒发人生感慨
众所周知,鲁迅先生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所谓“无韵之《离骚》”,就是指《史记》在写人记事之际,能把个人的的情感寄托其中,使《史记》具有了浓郁的抒情性。对此,清人刘熙载予以高度评价,《艺概·文概》中称:“太史公寓主意于客位,允称微妙。”[3]
司马迁因替战败投敌的李陵辩护,被下狱治罪,遭受宫刑,史称“李陵之祸”。这一场变故,不仅使司马迁的身体横遭摧残,也使他的心灵遭受重创。除悲剧性的生命体验和对知遇的渴求之外,还有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感慨,都源自于此次变故。在《报任少卿书》中,司马迁历数周文、孔子以来的创作,认为这些创作都是“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4]1865这些生命的痛感就是司马迁内心的“郁结”,被司马迁有意而自然地融入到了历史人物的叙事中。司马迁又声泪俱下地言道:“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4]1859危难之际见真情,司马迁受难时,“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这正是自私的、势利的人性的暴露,司马迁感慨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良有以也。在抒发他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之感时,写门客的聚散成为一个常见的手法。恩主与门客虽然恩义相许,但二者之间确实是一种后天形成的、比较松散的主客关系,恩主发达时,宾客如云;恩主失势时,树倒猢狲散。一聚一散之间,恰恰是以势利为转移;门客的聚散,准确、及时地反映了恩主的身世浮沉。
请看下面三个例证:
廉颇之免长平归也,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及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1]2448(《廉颇蔺相如列传》)
太史公曰: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1]3113(《汲郑列传》)
可以说,阳光之下无鲜事,历史惊人地相似!当孟尝君、廉颇、汲黯、郑当时等人权势煊赫时,门客如蚁聚膻,如蝇竞血,都来相附;一旦丧失权势,则门客作鸟兽散,改换门庭。冯认为:“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这就如同市集朝暮之聚散一样。廉颇的门客亦振振有词,说出一番“天下以市道交”的道理为自己辩护。所谓“市道”,即商贾逐利之道。一言以蔽之,就是权势的有无、利益的有无,决定了门客或留或去的态度。恩主与门客之间关系看似温情脉脉,实则是现实冷酷的利益交换关系。翟公于此深有感触,把这种现象提炼为韵语格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想必这也是司马迁的心声。
并非所有的门客都忘恩负义,追逐势利,也有一些有始有终,不离不弃的门客。比如上文提到的冯,在齐王废黜孟尝君后,“诸客见孟尝君废,皆去”,唯有冯通过游说秦王,最终恢复了孟尝君的地位。对于这些不顾利害、秉持节操的门客,司马迁心存敬意,所以《孟尝君列传》中,冯所占篇幅极大,成为门客中少有的血肉丰满的人物。其他地方对于此类门客的义行,也往往交代一笔,甚至要提及他们的福报。如上文所引《张耳陈馀列传》中,贯高等门客极力为赵王张敖鸣冤脱罪,其后不仅张敖得以昭雪,而且这些随从的门客也得以升迁:
于是上贤张王诸客,以钳奴从张王入关,无不为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时,张王客子孙皆得为二千石。[1]2585
随从张敖入关的门客,善有善报,不仅本人骤跻高位,而且泽及子孙。又如:
主父方贵幸时,宾客以千数,及其族死,无一人收者,唯独洨孔车收葬之。天子后闻之,以为孔车长者也。[1]2962(《平津侯主父列传》)
主父偃是汉武帝时的名臣,因贪黩被告发,身死族灭。门客孔车为他收尸下葬,这一义举受到皇帝的首肯,誉之为“长者”。司马迁不避行文枝蔓,特地表出这些门客的义行,其用意所在,应是借此显示作者鄙薄势利之交的态度,表达呼唤人间真情的心声。
结 语
门客这一群体,应运而生,不甘寂寞,但因其身份的依附性,决定了他们在王侯将相主导的历史舞台上,只能是历史的配角。在司马迁笔下,给予这一附属群体一定的舞台空间,让他们发挥才智,与主人共同完成了一幕幕生动的历史剧。门客的活动在他们恩主的历史上,有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完整历史叙事的必要环节。甚至恩主形象的成功塑造,有时也要借助于门客的陪衬。司马迁还即事寓情,借门客的聚散,批判了唯利是图的世道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