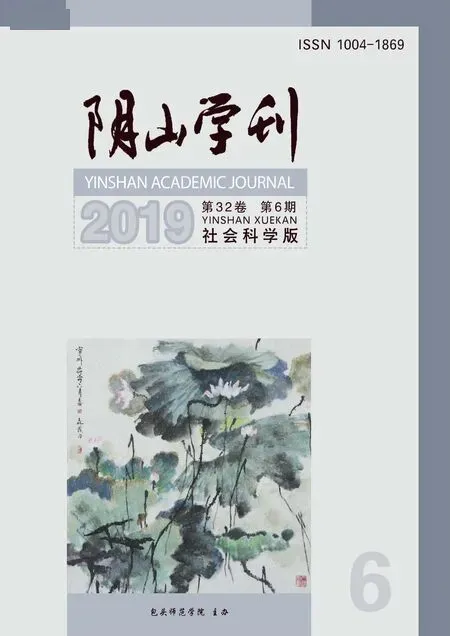评析Bickerton的语言进化突变论及其语言观的哲学特征*
周 文 美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9)
作为现代语言进化论的领军人物,Bickerton对传统进化论大胆提出挑战,在其1995年的著作《语言与人类行为》中阐述了他的语言哲学观,从进化论的角度探讨了语言起源、本质、语言与意识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1]Bickerton认为,“语言不是人类大脑高度进化后的产物。人类只是偶然进入了语言的领地”[2]56,而语言的出现与发展的直接结果就是人类的意识、思维与智力也得到了发展。该论述的出现立即引发了众多学者们的关注。他的语言进化论究其本质是一种语言中心论。本文将分析其语言进化论的核心内容,试图从理性主义和存在主义的西方哲学认识论视角分析其语言观的哲学特征,并指出其语言观存在的合理性及一些相关问题,来探讨其对加深语言进化问题和人本质问题认识的意义。
一、Bickerton的语言进化突变论
Bickerton的语言中心论认为,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语言。语言的出现赋予人类行为最独特的认知能力和意识活动。语言的核心特征在于句法。Bickerton认为,人类语言的发展不是缓慢平稳进化的,而是经历了两个阶段,其两段论(two-stage account)揭示了语言之于人类产生和存在的关键意义。
(一)原始语言阶段
原始语言(proto-language)阶段呈现出的语言特征是词汇很少,词与词之间没有结构关系,就像一颗颗由语义连接的珠子组成的珠串,没有“合并”(merge)和语言“递归性”(recursiveness)的存在[3],表达手段极为有限,不流畅、有停顿和犹豫,几乎所有的语言单位都能在自然界中找到所指。这与两岁以下的孩子、早期的夏威夷洋泾浜语,以及经过训练后的类人猿所呈现的语言很相似。Chomsky的语言进化突现观对Bickerton语言进化观点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其理论立论过程中使用很多乔氏术语。Chomsky认为原始语言应该会有符号的“合并”,并不赞同原始语言的存在。Bickerton不认可Chomsky的思想,认为“合并”存在于句子层面,原始语言中没有句法。[3]
(二)句法语言阶段
Bickerton认为句法产生于他所假设的“神奇的一刻”(magic moment)。在那一次灾难性的事件中,大脑的内部结构产生了质的变化,人类语言完成了从原始语言到自然语言(human natural language)的飞跃[1]69-70。句法是大脑自然而然的产物,是人类头脑中一种抽象的内在逻辑机制,能把凌乱、独立的词汇连接起来,组成具有无限生成能力、极其流畅和具有可解释性的语言。Bickerton认为原始语言与现代人类语言不仅有句法之分,更存在二者在词汇方面的本质差异。人类语言的词汇与自然事物分离,以意义关系和结构分层次储存在意识场里,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突显了人类语言的“位移性”(displacement),这种结构特征使得人类语言明显区别于动物交际系统,也正是这种特性才使抽象的句法成为可能。[2]58
二、Bickerton语言观的哲学特征
理性主义(rationalism)是西方哲学的一种认识论理论,该理论认为理性是知识的主要来源,是运用抽象推理就可以认识事物及其结构,不需要通过经验验证而获得关于事物真理的一种天赋知识。近代西方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Descartes强调理性思维的作用,否认真理性认识的感性来源和感性认识的可靠性。作为西方现代哲学流派之一的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从揭示人的本真存在出发来揭示一切存在物的存在结构和意义,以及人与自然界、社会的关系。其主要代表人物Heidegger认为,语言的本质是存在的本真居所,而非表达功能和工具性质。语言经验反映存在的本质和内在结构,哲学家只有通过语言才能把握存在的本质和内在结构。Bickerton语言观中关于语言起源、语言本质、语言和意识关系的三个方面具有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或存在主义特征。[4]14-15
(一)语言起源突变论的理性主义特征
从古希腊Plato对语言起源的研究开始至今,该问题仍然悬而未决。20世纪Aitchison的语言嵌合式进化说单纯用延续性(continuity)与非延续性(discontinuity)来解释语言的进化,主张语言是“靠某些已有的东西应急生成”[5]259,语言和人类行为一样属于嵌合式进化(mosaic evolution),即语言的某些方面具有很强的延续性,其它方面有一定或者没有什么延续性[6]。Pinker则认为语言是生物本能(language instinct)。他认为语言不是文化的产物,不是学会表达时间或政府管理方式之类的知识,而是一种使用起来丝毫不知其内在逻辑的本能。语言的复杂属性不是父母或教师能教会的内容,而是生物禀赋[7]。新达尔文主义的渐变论(neo-Darwinian gradualism)认为,“现代人类语言是由原始语言过渡发展而来的。先有原始语言的词汇,继而产生了现代人类语言的句法”[2]57-58。21世纪Chomsky的天赋思想认为,基因变化诱发了语言,语言是人类物种的先天禀赋,不是逐渐学得的后天产物,介于中间的语言存在是难以想象的。这与Bickerton语言突变论关于突变天赋能力的观点如出一辙。
Bickerton继承发扬了Heidegger的存在主义,通过对原始语言研究分析进一步论证了原始语言与人类自然语言之间没有过渡阶段存在的可能性。他认为完全意义上语言的出现是突变的结果,以句法为核心。Bickerton找到了支撑突变论最充分的理由。首先,现有证据证明人类认知是突变而成的。两百多万年前,在人科动物进化过程中没有留下行为和技术方面逐渐发展的痕迹。十二万年前南部非洲出现的认知飞跃和语言突现论表现出理论上的一致性。其次,尚未找到原始语言和人类语言之间有同期出现的各种中介语言和某些稳定阶段,至少从大量失语症、言语困难症、一语和二语习得的发展阶段以及语言官能的反常现象中没有找到相应证据。句法的自毁无法恢复性证明没有语言发展中间阶段出现的可能性。[5]259Bickerton语言起源突变论合理的方面在于从多学科视角为深入研究语言起源问题提供了新的范式和思路。其哲学基础属于理性主义,具有典型的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特征。
(二)语言生物性本质观的存在主义特征
什么是语言?Bickerton在分析人们对语言概念两个误解的基础上阐明语言生物性的本质观。第一个是语言工具性的误解。第二个误解是语言交际功能的唯一性。传统的语言哲学把语言的交际功能提升到非常重要的位置,认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语言的交际功能。Bickerton认为这种观点是大错特错的,因为动物也会使用符号来交际。很显然,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语言的表征功能,人类用语言储存信息、进行思维活动、表达思维和意识,语言是不受时空限制的开放系统。相比之下,动物的“语言”仅仅局限于表达情绪与需要,其单一孤立的交流单位不能组合传达新的意义,最终导致其交流方式的封闭性。从这个意义上讲,Bickerton认为人类行为的基础是语言,研究人类的行为就必须研究人类的语言。只有语言才使能使人类感知、体验和再现所处的世界。
Bickerton主张语言本质上是人类这一物种经进化而来的生物性特征,并非可创造的文化性特征,来源于人的本真存在,是随着人本真存在的发展进化来的,是不能被创造的。Bickerton关于语言本质观的合理性在于从人本真存在出发来解释语言的存在结构和意义,通过研究语言的生物性本质来研究语言结构的生物特性即大脑神经网络结构这一人本真存在的重要内容之一。它从人类自身的生物特性解释语言的本质特征,强调语言结构的生物特性和人本真存在对语言生物特性决定作用同时,也强调语言对人本真存在的影响,其哲学基础属于存在主义,具有典型的西方哲学的存在主义特征。[4]16
(三)语言与意识关系的存在主义特征
句法的出现是人类基因突变的结果,这种突变促使大脑结构复杂化,更重要的是促使人类思维和意识产生。Bickerton把意识界定为人类大脑达到高度发达程度后而出现的创造性特征,他区分了三种意识形式。第一意识(consciousness l, Cl)是所有生物(动物和人类)具有的一种线上意识,既包括对外部环境的客观感应,也包括内部主观产生的体验。人类不但具有Cl,还可意识到自己的意识,这种意识的意识就是第二意识(consciousness 2,C2)。第三意识(consciousness 3,C3)是指用语言表达思想感情的能力。例如,我感到痒(C1),知道自己痒(C2),能说出“我痒”(C3)。Bickerton强调,C2和C3只为人类所有,因为只有人脑才可回顾和反思意识内容。他认为人类只有一个意识C2,语言使得C2产生的三个结果整体出现。[2]59-60作为拥有语言物种的人类必然会意识到自身的意识,并对其进行表达和分析。人类的自主能力和主动性引出了语言在其意识形成过程中的决定作用。
Bickerton三种意识形式的区分让我们从存在主义视角更清晰地看到了语言的生理基础。意识为语言的出现和运作提供了生理基础和必要条件;神经系统的本真存在为语言提供初级的生理基础;语言突变促使人类大脑质变,为意识的产生提供了本真存在的生物基础。Bickerton关于语言和意识关系的观点的合理性在于从人的本真存在出发来揭示意识发展的必要条件(语言的存在结构),从二者共同的生理基础——人的本真存在(人脑神经网络)出发,揭示意识的内在结构是语言的生理基础,语言的存在结构是意识发展的必要条件,二者联系密切不可分割,是人类思维认知过程中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哲学基础是存在主义,具有西方哲学典型的存在主义特征。[4]17Bickerton思想激进偏颇,观点大胆创新,但他过分强调语言生物性的本质以及语言和意识关系的生物性特征,忽视了语言社会性的交际功能和社会文化属性特征,很难彻底全面揭示语言的本质以及语言和意识关系的本质。
三、对Bickerton的语言进化突变论的简评
Bickerton的语言哲学观认为,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语言,突出了句法的核心作用。Bickerton的语言中心论是一种语言决定论。该理论在语言认知观和研究方法这两个方面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和局限性。
(一)强硬的模块说、偏颇的突变论和温和的认知观
长期以来,以Chomsky为代表的许多认知学家推崇大脑本质的“模块说”,即大脑是由一系列各司其职、高度专门化且相对独立的模块所组成。语言是大脑的一个独立模块之一。Pinker更是坚持一种强硬的语言交际观,认为思维可以独立于语言之外,不依赖语言存在,语言的功能只是传达思维。Bickerton的突变论旗帜鲜明,不做任何温和的修饰,突出语言的中心作用,把语言几乎等同于整个中央认知系统。在他看来,句法是人类语言的核心,句法和命题推理构成了人类认知的基础。抽象的语言的出现带来抽象的思维。Bickerton过于偏颇的突变论缺乏有力的经验证据的支撑,欠缺进化心理学的证据——大脑的中央认知系统完成复杂的认知功能是由语言模块和各感觉模块巧妙结合的结果,因此难免会导致其语言认知观的前后矛盾。
Carruthers接受乔氏的模块说,其温和的语言认知观(a weak form of cognitive conception of language)认为,虽然语言是大脑的一个独立边缘模块,但它的基本功能是思维的载体,与思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认知活动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Carruthers指出Bickerton观点中的不足,认为Bickerton既否认了大脑的模块本质,又割裂了原始语言与句法语言之间的联系,语言进化的两段论过于简单,不符合进化事实。Carruthers认为,虽然原始语言抽象程度低,但创造性思维的开始是思维既能以直观想象的方式利用视觉模块,又能利用内部言语(inner speech)来使用语言模块以支持其自身功能。语言就像一个国际通用语言,作用于不同的模块之间,它是命题思维和概念思维的载体,在人类的创造性思维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8]
(二)研究方法的逻辑推理
Bickerton反驳新达尔文主义的渐变论,对传统进化论提出了颠覆性的挑战。他认为,语言进化过程中,具有意义的“神奇一刻”是句法的出现。该观点主要是基于抽象推理而形成,具有典型的理性主义特征。但缺乏直接的考古记录和经验证据进行推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许多学者质疑Bickerton研究中的因果推理太模糊[9],观察对象有限,观察时间过短,是否属实还有待证明[5]259,只能作为一个有待验证的假设。由此可见,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要遵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人类语言发展是人类进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始语言是人类语言进化若干阶段中的第一阶段,语言进化要从原始语言逐渐地发生量变,最后实现质变过渡到人类自然语言阶段,这样的语言进化观才是较为合理和全面的。
四、结 语
虽然Bickerton的语言中心论存在一些缺陷,但他试图从众多领域研究人类语言起源,阐述语言起源的认知,为深入研究语言起源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他对语言起源研究的重大贡献是对克里奥尔语的发展研究成果,为他的推理立论提供了比较强硬的推理依据。他将语言学与人类起源和进化研究紧密结合,将语言视为人类起源和进化的唯一先决因素,剖析语言本质的同时,看到了语言对于人类存在的关键意义,更是对人之为人、语言与思维、语言与意识关系等这些有关人本质问题的执着追求。因此,“任何解释人类行为的企图都必须建立在语言理论基础之上”,因为“只有明白了语言,我们才有可能明白自己”[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