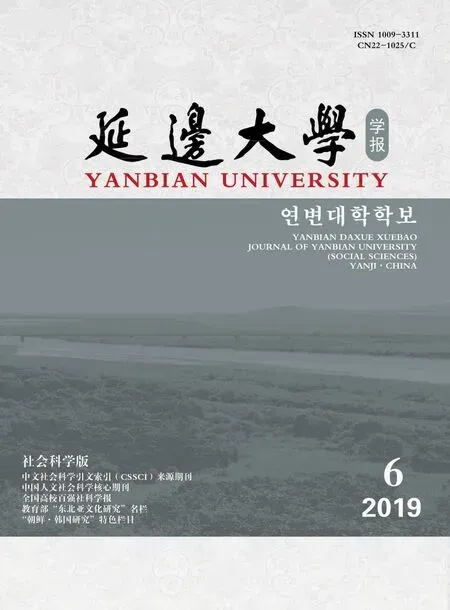中国制度性权力提升的现状与困境
杨 慧 刘昌明
国家实力提升与国家权力增长是一个动态匹配的过程。国家权力的大小以国家实力为基础,但一国的资源禀赋、经济水平、军事能力、科技水平等并不会自觉转化为影响力本身。在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高度制度化的国际秩序中,国际制度早已深深嵌入国家保持权力、增加权力、显示权力的过程,国家间的不对称性相互依赖也在国际制度框架下表现得最为显著。实力与权力非同步性增长的理论逻辑使增强自身的国际制度影响力成为新崛起国家的基本诉求。
从现实来看,综合国力的增长与积极的制度参与为中国国际制度影响力提升奠定了基础,但中国的制度性权力与自身实力仍长期处于不对称的状态。在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体系加速转型的背景下,如何将日益增长的实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已成为关系到中国能否继续顺利崛起的关键课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强调,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1)《授权发布: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29/c_1116983078.htm。那么,如何客观认识中国在现行国际制度体系中发挥的作用?中国在国际制度中影响力的提升面临着哪些阻碍因素?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是提升中国制度性权力的前提。本文在对国际制度性权力的概念内涵、评估维度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评估当前中国的国际制度性权力现状,并进一步探讨中国制度性权力提升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一、国际制度性权力:概念特征与评估维度
在无政府体系下国际行为体的互动和交往中,国际制度在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合作效率的同时,也会导致利益分配的“非中性”。(2)张宇燕:《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改革》1994年第2期,第97-105页。在制度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主导国,常常借助国际制度或国际机制对其他行为体的选择进行限制或施加影响,以谋求自身利益。由此,国际制度性权力(Institutional Power)可被定义为“国家行为体在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进程中对其他行为体产生的影响,是一国在某一国际制度框架中拥有决定权的配额”。(3)Barnett M.N.,Duvall R.,“Power in global govern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Susan Strange,“States and Markets”(2nd edition),London:Pinter,1994,pp.24-25.
(一)国际制度性权力的特征
首先,国际制度性权力是一种不对称的权力。本质上,国际制度的建立就是制度性事实的构建过程,即以国际组织的成员身份为载体把一种“地位—功能”赋予某个行为体。(4)王丽:《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一种文化视阈的阐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70页。但是,一个国际制度的建立也意味着某些国家可能被排除在制度之外,甚至直接成为制度的针对对象。因此,获得国际组织的成员身份并适应这一制度框架的规则和规范是一国制度性权力的来源基础。
其次,国际制度性权力是一种约束性权力。国际制度的约束力源于内嵌于其中的制度规则和议程设置。任何制度的建立和运行都以规则为基础,规则的调整不仅影响制度运行的结果,而且会从根本上改变制度的性质。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往往是规则的最大受益者,行为体通过对他者理性行为和选择能力的制约,谋求自身在权力关系中的优势位置,使自己的行动目标与他者的目标相调适。(5)Barnett M.N.,Duvall R.,“Power in global govern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16.各国针对国际制度主导权的竞争,实质上是关于国际规则制定的竞争。
此外,国际制度性权力是一种同化性权力。制度构建的过程就是行为体共同利益汇聚的过程,也是制度主导国塑造其他国家利益诉求的过程。以国际制度为中介,主导国甚至可以在他者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对各国谋求利益的行为进行约束,使他国的国家利益与自身利益相协调,使他国的行动计划与自身的行动目标相一致,即获得相应的国际制度性权力。
(二)国际制度性权力的评估维度
国际制度性权力的上述三个特征表明其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性权力。一国制度性权力的消长寓于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交往互动过程中,与国家在制度中的参与度和影响力有关。其中,参与度是指一国参与国际制度的领域是否多元和广泛,影响力是指一国对其他行为体行为的限制能力和对整个制度体系的改变能力。对应国家在参与国际制度进程中的行为表现,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对一国的制度性权力进行评估:
一是国际制度适应能力,即国家通过调整和改变自身以适应制度环境的能力。一方面,国家只有加入某一国际组织并取得该组织的成员国身份,才能成为这一组织机构的“利益相关者”,进而获得影响这一组织和制度相关事务的权力,而这一过程需要国家调整自身,以达到制度规范的标准和要求。另一方面,一国加入某一国际制度后,组织成员的增减也会影响该国在这一制度框架下对其他成员国的影响力,因而需要不断保持对这一制度的适应性融入。具体而言,国家的国际制度适应能力可以从三个指标进行具体评估:1.国家参与全球性和地区性国际组织的数量。成员身份数量越多表明国家对现行制度体系的融入和参与越深入。2.国家加入或签订的多边条约数量。由于多边条约的内容多涉及国家间在具体问题领域的行动协调,因此国家加入或签订的多边条约数量越多,表示该国在组织行为中的协作能力越强。3.组织经费分摊比例。这一指标主要衡量国家对国际组织的贡献度。组织经费分摊越多代表国家对国际组织的贡献越多,参与能力和参与意愿越强。
二是国际制度塑造能力,即国家对国际规则、议程设置以及组织职员构成的影响力。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过程就是一国不断“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部分国家能够借助自身的领导力影响制度构建的内容和方向。这种影响力具体表现为:1.对国际制度规则的塑造能力。规则是国际制度运行的基础,在相对实力有限的情况下,行为者通过改变国际制度运行的规则和设置新的议程可以获得对自己更有利的结果。2.对国际议程设置的塑造能力。即将自身重视的议题列入国际制度议程,获得优先关注的能力。3.本国公民在国际机制中的任职情况。一般而言,国际组织对于其国际职员的来源都有具体的原则规定,如地域公平原则、能力原则、会费比额原则等。(6)《国际组织中国高官日益增多 世界需要“中国声音”》,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106/c70731-23451371.html。本国公民在国际组织中任职数量越多,任职职位越高,则该国在组织中能获得更高的代表性和话语权。
三是国际制度创设能力。创设新的国际制度可以实现对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相关问题领域的规则、规范和实践进行全面改造,并提供可供替代的选择,从而增加自身在现行国际制度体系中的影响力和权威性,提高自身的制度理念在国际社会的接受度和认可度。通常,新国际制度的创设有两大动力:一是国家间力量对比变化为其提供基础条件,二是全球性或地区性危机的出现为其提供新机遇。国际制度最终能否创设成功取决于国际社会成员相互较量和博弈的合力。一国的国际制度创设能力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更细致的评估:1.创设的国际制度领域。一般而言,高政治领域(如军事、安全等)利益共享的空间更小,其制度创设难度高于低政治领域(如经济、社会等),因而能够在高制度领域创设新制度的国家拥有更大的制度性权力。2.创设的国际制度数量。国家能够创设国际制度的数量越多,制度性权力越大。3.创设的国际制度规模。新国际制度的成功创设离不开成员国的参与和支持,因此成员国参与数量越多,主导国的制度性权力越大。
二、中国国际制度性权力现状评估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逐渐从国际制度体系的边缘走向中心,经历了“无参与—基础参与—深度参与—建设性参与—领导性参与”的过程,(7)Nina Hachigian,Winny Chen,and Christopher Beddor,“China’s New Engage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security/reports/2009/11/06/6974/chinas-new-engagement-in-the-international-system/.由体系的旁观者转变成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和改造者,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自身制度性权力的持续提升。依据以上指标体系,对当前中国制度性权力的现状进行评估如下:
(一)成熟完备的国际制度适应能力
中国具备的广泛的国际制度适应能力体现在对各类国际组织和多边条约的适应性加入。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加入国际组织的数量迅速增长。特别是1977年到1996年间,中国参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数量从21个增加到51个,在非政府组织中的席位从71个猛增到1 079个。(8)[美]伊莉莎白·埃克诺米、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中国参与世界》,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50页。此后,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目前已经加入了几乎所有政府间国际组织。另一方面,中国始终积极倡导联合国以及多边主义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地位,累计缔结了23 000多项双边条约与协议,加入400多项多边条约。(9)《王毅在第四届世界和平论坛午餐会上的演讲(全文)》,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628/c1002-27218748.html。以近十年为例,从2009到2018年,中国共加入85项多边条约,内容涵盖政治、经济、科教文卫、通讯、人权、劳工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10)此数据根据外交部网站“条约情况”相关数据整理而得,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tyfg_674913/。
此外,在与国际组织开展务实合作的同时,中国对国际组织的贡献也逐步提升。中国分摊联合国会费的比例已经连续六次增长,从1980年的1.62%增长到2016年的7.92%,在成员国中位列第三。(11)Rakesh Dubbudu,“How much do various countries contribute to the UN Budget?”,https://factly.in/united-nations-budget-contributions-by-member-countries/.2016-2018年,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费用贡献率达10.2%,在成员国中位列第二。(12)“How we are funded”,https://peacekeeping.un.org/en/how-we-are-funded.中国积极参与多边国际制度,不仅使中国快速融入了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并且成为其中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力量,为中国国际制度性权力的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由此可见,中国在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中的制度适应能力已经较为成熟和完备。
(二)稳步提升的国际制度塑造能力
随着对国际事务的全方位参与,中国逐渐改变了对国际制度被动适应的局面,不断培育自身对制度的塑造能力,对国际机制内部的组织结构、决策机制、价值理念等与制度设计相关的要素更加关注,尝试对国际制度中不合理的规则和规范进行改革。(13)Stephen Olson,and Clyde Prestowitz,“The evolving role of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https://www.uscc.gov/Research/evolving-role-china-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
一是对国际规则的塑造。如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国积极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改革,致力于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使其能够更加充分地反映各国在世界经济中不断变化的权重。二是对国际制度议程的塑造。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更加积极主动,2014年主办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和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CICA),2016年主办二十国集团(G20)峰会,2017年主办金砖国家峰会。一系列主场外交的成功举办,为中国将不断增强的实力转化为影响力提供了机会和平台。三是对国际组织职员构成的塑造。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参与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的高层职位竞选,在非联合国系统的国际组织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进入领导层。根据联合国人力资源数据年度报告的统计,2000年供职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中国籍专业人员为457人,这一人数到2016年已增长到1 035人。(14)“Personnel statistics”,https://www.unsystem.org/content/un-system-human-resources-statistics-reports.
由此可见,中国正努力成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和制度议程的设置者。尽管当前中国的规则设置能力仅在自身具有优势的国际金融和贸易领域较为突出,其他关乎国家主权的分裂势力问题、领土领海问题、涉及全球性的环保问题等,由于现行国际制度规则的固化和自身实力的相对有限性,中国还未能找到把国内治理经验转化为国际规则并在其中发挥积极性、建设性作用的有效方式。但总体来看,中国的国际制度塑造能力正在稳步提升。
(三)国际制度创设能力初步显现
随着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不断深入,中国对国际制度的理解和认知愈加深刻,主动创设国际制度,更好地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成为必然的战略选择。(15)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74页。近年来,借助自身在国际金融和地区经济一体化领域的潜在领导力,中国开始尝试进行制度创设的实践。(16)Tang,S.,“China and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Order(s)”,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32,No.1(2018),pp.31-43.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的成立是中国主动创设国际多边合作制度的典范,也是中国在全球经济秩序中角色转型的标志性事件。从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提出筹建亚投行的倡议,到2015年12月正式宣告成立仅用了两年时间。截至2019年9月,亚投行的正式成员国已达100个,表明中国的制度性权力和领导力获得了较广泛的国际认同。(17)“Members and Prospective Members of the Bank”,https://www.aiib.org/en/about-aiib/governance/members-of-bank/index.html.在经济多边合作机制方面,2010年建成的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中国倡议并商谈的第一个自贸区,也是当前世界人口最多、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在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方面,2001年中国发起并参与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目前已成为维护中亚和中国西部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多边安全机制。此外,2016年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发起的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是中国在能源领域发起成立的首个国际组织,标志着全球能源互联网由理念迈向了共同行动。(18)《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成立 刘振亚当选主席》,http://www.chinanews.com/business/2016/03-31/7818126.shtml。
综上,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国际制度适应能力、塑造能力、创设能力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低到高的发展。总的来看,20世纪70年代前,中国的国际制度性权力仅表现为有限的制度适应能力。国际制度体系的后来者身份使中国与国际组织的互动经历了艰难的磨合期。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后,中国积极加入各类国际组织与多边合作机制,制度适应能力迅速提升。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议程塑造方面表现出更高的灵活度,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国际制度塑造能力有了显著提高,不仅提出一系列新的外交理念,还在其指导下积极进行制度创设的尝试。以亚投行为代表的国际制度创设初获成功,是中国制度创设能力增强的表现,也标志着中国国际制度性权力的全面提升。
三、当前中国制度性权力提升的困境与挑战
如上所述,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及参与国际制度广度与深度的扩展,中国制度性权力的提升既是国际权力结构发展的逻辑结果,也是中国实现与其他国家互利共赢的现实选择。但是,作为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力量,中国制度性权力的提升意味着原有制度性权力结构的平衡被打破,其引发的体系规范重塑必然会面临现行国际制度体系结构的压力和挑战。
(一)中国制度性权力提升面临全球权力结构扁平化的制约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制度性权力结构日益呈现出碎片化和扁平化的发展趋势。随着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国际事务的控制力下降,国际权力分布从集中趋向分散,呈现出多中心、多力量的格局,全球治理和决策也由少数国家垄断的局面逐步向更多力量参与的趋势发展。(19)尉洪池:《国际关系中的权力流散》,《求索》2013年第3期,第240-242页。权力基础的不断分散不仅造就了新的大国,而且使任何国家都越来越难以获得超级大国地位所需的相对实力和在某一领域里的绝对制度优势。(20)[英]巴里·布赞著,刘伟华译:《权力、文化、反霸权与国际社会:走向更为地区化的世界秩序?》,《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1期,第16-33页。
这一趋势对单一国家制度性权力的提升产生了明显的制约效应。二战后,美国凭借其实力优势,实现了美国治下的霸权,以美国为主导建立的国际制度塑造了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然而,当今中国制度性权力提升面临的国际环境与当年美国制度霸权建立所处的国际环境已经迥然不同。国家间实力对比的变化,使得权力在经济、安全、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分布碎片化,特别是对于环境与能源安全问题、恐怖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权力广泛而不规则的分配在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使得各国的利益分布也更加分散。(21)杨文静:《重塑信息时代美国的软权力——〈软权力在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介评》,《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8期,第61-62页。虽然各国际行为体更加需要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协调彼此的行动,但共同利益的汇集变得更加困难,合作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这成为影响中国制度性权力提升和获得的重要制约因素。
(二)中国的制度性权力提升受到制度变迁路径依赖效应的限制
“路径依赖”本是制度经济学的概念,即认为技术演进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效应是指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强化。国际制度同样具有自我存续的惯性,从国际制度中获益的行为体会主动适应并强化这一制度安排,从而期望获取更大的收益。(22)唐世平:《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沈文松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1-82页。因此,现有制度框架内可供崛起国选择的空间和范围非常有限,其谋求改变现有国际制度是十分困难的。
中国制度性权力提升所面临的路径依赖效应具体体现为“身份异质与规则同质”现象。(23)王栋、曹德军:《再全球化:理解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新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7-8页。与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崛起的背景不同的是,中国是在一个高度制度化的环境中实现自身实力增长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和以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为核心的国际贸易体系,构成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全球性的国际制度网络。由于制度本身所具有的稳定性特征及制度背后的内在利益结构维系,使得西方在提及中国与国际秩序时常常带有一种排他的语境,先入为主的西方中心视角使得中国被认为是一个需要教化和改变的“他者”。因此,在现行制度体系下,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制度性权力的进一步提升将面临来自原权力分配机制的压力和阻力。随着新兴经济体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影响力和贡献率的提升,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优势地位日渐式微,二者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将更加激化,未来国际贸易、气候治理、金融监管等领域的制度变迁必将受到现行制度路径依赖效应的制约。
(三)中国制度性权力的提升面临现有制度体系主导国的战略挤压
在国家实力结构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国家间的制度性权力处于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中。一国制度性权力的增长不仅会引起国际制度权力结构本身的调整,而且也会引发国家间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的变化。大国制度性权力的全面提升在一定意义上将打破传统的利益结构,从而推动国际秩序的重塑。由此,崛起国获取制度性权力的行为将受到在原权力结构中占有主导地位国家的战略反制。
作为现行制度体系的主导国,美国是影响中国制度性权力提升进程的重要变量。近年来,随着中国制度性权力的不断提升,美国的心理不适也与日俱增。这一方面是由于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使美国对其自身权力的多寡变化极度敏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前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使美国日益感受到自身权力的有限性以及主导国际事务的乏力。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倾向愈发明显,中国被视为现行国际秩序的破坏者,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在经贸领域,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遭到美国政界和学界的恶意指责,自2018年持续至今的贸易摩擦更使中美关系日益呈现出零和博弈的特征;在安全领域,美国提出“印太战略”试图以拉拢印度和东盟国家的方式,重塑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以全面遏制中国崛起。此外,美国遏制中国制度性权力提升还表现在双方围绕伙伴争夺展开的竞争,这使亚太地区国家特别是一些传统上习惯奉行“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中小国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甚至面临“选边站”的挑战,不仅加剧了中国周边地区局势的不稳定,更导致近年来钓鱼岛问题、南中国海问题频频升温,成为制约中国制度性权力提升的阻碍因素。由此可见,中美之间围绕地区经济、安全领域呈现出的制度竞争将使中国制度性权力提升的外部环境更加恶化,并且这一局面在短时期内很难得到改善。
四、结语
制度性权力不仅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标志,也是维护和谋求自身利益的基本手段。综观历史发展,国际制度性权力结构最终受制于国际实力结构,但二者之间的调整和变化并非同步,国家制度性权力的变化常常滞后于其实力的调整。中国实力的增强与其国际制度性权力就正在经历着这样一个动态匹配的长期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使其在国际实力结构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国际制度参与的广泛性和适应性也在显著提升,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国际制度中的议程设置和制度塑造等核心能力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中国国际制度性权力的提升面临着当前全球权力结构扁平化、制度路径依赖效应及现行制度体系主导者战略遏制等因素的制约和挑战。对此,中国要从战略层次上进行规划设计,顺应全球权力结构的演变趋向,通过国际理念创新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消解国际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效应,力求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不断拓展自身发挥作用和影响的空间,以实现自身国际制度性权力的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