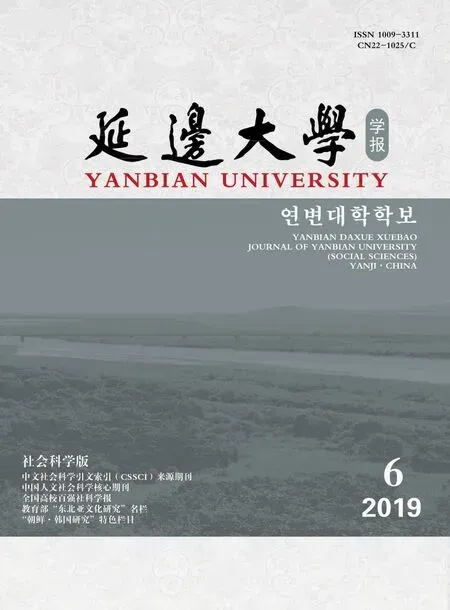论朝鲜朝文人张维对《庄子》的接受
孙惠欣 宫 官
张维(1587-1638年),字持国,号溪谷、默所,谥号文忠,是朝鲜朝中期“汉文四大家”之一。张维所处的朝鲜朝中期可以说是《庄子》在朝鲜传播和接受的低潮期。“百年之间,天下知有阳明,而不知有朱学,异端之害极矣。”(1)[韩]李植:《泽堂先生别集》卷15《追录》,《韩国文集丛刊》(088),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2年,第526页。一些坚守儒家正统文学观的文人视老庄为“异端”,认为老庄对朝鲜文坛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统治阶级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为了巩固儒学的正统地位,控制佛老“异端”思想的传播,甚至在《学令》中规定科考学子要长读“四书五经”及诸史等书,科场禁止挟庄老佛经杂流百家子集等书。在这样的背景下,张维仍以《庄子》为效法典范,积极学习《庄子》,并在作品中不断阐释《庄子》,对《庄子》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主要从张维对《庄子》的学习借鉴和发展两个方面来分析其对《庄子》的接受,揭示其与《庄子》之间的关联。
一、对《庄子》的学习借鉴
张维喜读老庄之书,“盖公未冠,已尽读四书二经骚选庄韩等书,是惟无读,读必穷极其究,挑抉其微,涵演咀嚼”。(2)[韩]朴弥:《溪谷集·溪谷先生集序》,《韩国文集丛刊》(092),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2年,第4页。只用一年就学完了《阴符经》全本书,并为其做了注解。“孔子既殁,而诸子之书出焉,唯老子庄周明道德之趣。”(3)[韩]张维:《溪谷集》卷7《阴符经解序》,《韩国文集丛刊》(092),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2年,第118页。张维以身作则,始终倡导学习《庄子》。朝鲜朝时期著名文人李植在《支离子赞后跋》中记载了张维晚年改号为“支离子”的缘由:“溪谷翁杜门谢病,改号支离子,自为之赞以示余”。(4)[韩]李植:《泽堂集》卷9《支离子赞后跋》,《韩国文集丛刊》(088),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2年,第160页。张维晚年沈痾缠身,闭门谢客,并将自己的号改为“支离子”。“支离子”取自《庄子·人间世》中的人物“支离疏”,由此可以看出庄子在张维心中的地位之高和其对自然无为境界的神往。同时,张维把对庄子的膺服转化为文学上对《庄子》的学习借鉴,他的许多作品都有着明显的对《庄子》的接受印记,许多文章的主题、故事框架、表现手法、动物形象等都取法《庄子》,甚至直接或间接地化用《庄子》语句。
(一)寄托鹓鶵之志
张维和庄子都生活在政治混乱的时代,相似的生活背景加深了张维对《庄子》的认识,并通过文章寄托心志。庄子生活的战国中期是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时期,诸侯征战,社会动荡。庄子心系天下,感之尤深。张维所处的朝鲜朝中期也是党争不断、统治者们争权夺利的时期。张维无比厌恨当时朝廷的黑暗腐败,便把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和反思诉诸笔端。张维的许多文章都运用了《庄子》的艺术手法,甚至一些动物形象也直接取法、仿效《庄子》,如《鸱得腐鼠吓鹓鶵赋》:
嗟来鹓鶵,吾将语汝。物之荣辱,系其所处。相彼沧浪,清浊自取。尔之生矣,于彼山区。氛浊不到,清净是都。汝若乘气而游,择地而趋,高飞兮远集,与仙灵兮为徒。彼鸱之吓,恶得加诸。今汝行乎烟火之墟,入乎垢污之宅,随燕雀而周旋,冒尘埃而出入。彼鸱视之,犹其匹敌。疑汝之分其所嗜,恐汝之夺其所欲。猜防之至,其势则然。汝实取之,彼何过焉。往者莫追,来今慎旃。(5)[韩]张维:《溪谷集》卷1《鸱得腐鼠吓鹓鶵赋》,《韩国文集丛刊》(092),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2年,第26页。
张维《鸱得腐鼠吓鹓鶵赋》的主旨和故事情节与《庄子·秋水》的《惠子相梁》十分相似,显然在构思上受到了《庄子》的影响。《惠子相梁》中设置了三个形象:“鸱”是猫头鹰,比喻势力小人;“腐鼠”喻指宰相之位;“鹓鶵”比喻高洁之士。庄子以鹓鶵喻指自己,鸱喻指惠子,并运用对比手法进行讽刺,表达对权贵的鄙弃,笔触犀利。张维《鸱得腐鼠吓鹓鶵赋》中“鸱”“腐鼠”“鹓鶵”的形象均取自《惠子相梁》,鹓鶵“生于昆仑之阿,长于丹山之穴,遨游乎寥廓之上,栖息乎清虚之城。青鸾朱凤兮为其俦侣,黄鹄白鹤兮是其奴仆。含元和以内充,沐沆瀣以外泽。朝食琅轩之实,夕饮醴泉之液”,(6)[韩]张维:《溪谷集》卷1《鸱得腐鼠吓鹓鶵赋》,《韩国文集丛刊》(092),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2年,第26页。腐鼠则是“虫蛆所蚀,蝇蚋所聚。烂皮带毛,臭肠满肚”。(7)[韩]张维:《溪谷集》卷1《鸱得腐鼠吓鹓鶵赋》,《韩国文集丛刊》(092),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2年,第26页。张维褒贬分明,立场明确,是与“腐鼠”为伍,还是同“鹓鶵”遨游天际,他坚定地选择了后者。面对污浊的政治环境,张维不愿阿谀奉承,不愿为统治者的牢笼所困缚,而愿做鹓鶵。张维通过品质高洁的“鹓鶵”,表达了自己对崇高精神世界的追求和对理想人格的向往,讥讽了“鸱”这种逢迎权贵、为追名逐利用尽心机的人。《庄子》旷达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张维对仕途纷争和人生处世的态度,使他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去审视自我,由此展现出一种豁达洒脱的风姿。
(二)抒发蜗角之愤
《庄子》中有些故事情节看似荒唐,实则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谐谑的同时充满哲理,透彻犀利,令人深思。《庄子》中的所有人物、动物都有其独特的个性和特征,人可以用虚化的形象来体现,物也可以用拟人化的形象来反映。宋代李涂评论《庄子》:“文字善用虚,以其虚而虚天下之实”,(8)李凃:《文章精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59页。虚实之间的奇思构想、辛辣讽刺,是《庄子》的一大特征。张维文章中的批判精神、讽刺意味、对社会现实清醒而深透的认识,都有着《庄子》的痕迹,如《蚁战十韵》:
蠢动均函气,玄驹亦摄生。慕羶求易足,戴粒命偏轻。略有君臣义,能无厉害争。分封夺国土,欺弱互兼并。牛斗军声振,鱼丽阵势横。吹尘腾急炮,垒芥作长城。欻尔分成败,居然见脆勍。相持同广武,鏖战等长平。蛮触传非妄,槐安事可惊。古今风雨地,何处可休兵。(9)[韩]张维:《溪谷集》卷29《蚁战十韵》,《韩国文集丛刊》(092),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2年,第480页。
张维的《蚁战十韵》借鉴了《庄子·则阳》中“蛮触之争”的故事。“蛮触之争”是戴晋人给惠子讲的寓言故事:蜗牛左边触角的国家叫触氏国,右边的国家叫蛮氏国。两个国家经常争夺地盘,最终引发了战争,战况惨烈,伏尸百万。庄子把触氏、蛮氏两个国家大胆夸张为蜗牛触角上的国家,而国土不及蜗牛触角大的两个国家却是因为争地而开战,想象奇特,构思玄妙。庄子用强烈的夸张形成讽刺,以简洁的语句对战争进行批判,辛辣有力。张维《蚁战十韵》的故事结构与《庄子·则阳》相似,讲述了蚂蚁们为了争夺国土而相互残杀的故事,“大虫食小虫,疆者饱弱肉。吞啖世界内,物物相残贼”。(10)[韩]张维:《溪谷集》卷25《索居放言十首》,《韩国文集丛刊》(092),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2年,第420页。蚂蚁本来就渺小,然而蚁战却能有“牛斗军声振,鱼丽阵势横”的阵势,文中引用了汉代刘邦的广武、晋阳之战的典故来形容蚁战的战势,接着引用了《庄子》中“蛮触之争”的典故。最后一句“古今风雨地,何处可休兵”是点睛之笔,深刻地披露了当时社会党派之间为蜗角之利而争斗的丑恶社会现象。张维把对现实社会的反思通过夸张的故事表达出来,讽谕了封建统治者的凶猛残暴,表达了对战争的愤恨。张维的讽谕寓言充满了《庄子》的批判精神,通过夸张的动物形象、荒诞的情节来反映现实,化解悲愤。
(三)开展孟庄之辩
《庄子》中有许多文章是人物之间的问答对话形式,问答相间的叙述形式是《庄子》的一大特点。在问答过程中,双方对于主题的观点并不一致,继而对主题进行争论和辩驳,因此与一般叙述结构相比,问答形式更具“辩”的色彩。如《庄子·秋水》中的“濠梁之辩”就是庄子与惠施同游濠梁之上,俯看倏鱼出游从而引发联想,然后开展了一场“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辩论。张维对《庄子》问答论辩艺术借鉴颇多,如《设孟庄论辩》就是一篇孟子与庄子围绕“齐物论”进行论辩的虚构作品。不同于普通的论辩体散文,《设孟庄论辩》全文都是问答形式,这种行文结构、论辩性的问答和论证观点的思维方式都体现了他对《庄子》的深度学习。《设孟庄论辩》大量引用《庄子》中的词语和典故,全文共九段:第一段交代了孟子和庄子相遇的因由;第二段由庄子问询孟子远来何故开启对话形式;第三段孟子以请教庄子“齐物论”为由,提出对齐万物的质疑;第四段庄子把孟子的请教看作是受教,认为孟子的请教之说是悖论,再顺势设问为何“物之不可齐”;第五段孟子陈述万物不齐的观点;第六段庄子就自己“万物可齐”的立场对孟子进行推理性辩驳;第七段孟子提出了“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观点对庄子进行反驳;第八段以庄子“道不同不相为谋”结束论辩;第九段道明了作文缘由。《设孟庄论辩》以“齐物论”为论辩主题,通过文中孟子和庄子逻辑严密的论辩,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设孟庄论辩》中孟子和庄子论辩的内容,有许多是张维直接化用《庄子》文意。
是故太山虽大,未尝有余,秋毫虽小,不见不足,未尝有余。何矜其大,不见不足,何訾其小,知此则知小大之齐矣。彭祖之寿而有所终,殇子之夭,亦尽天年,有所终则未足为修,尽天年则不可谓短,知此则知修短之齐矣。鲵桓之渊,不测其深,鱼鳖居之,以为乐国,而人蹈之者死;粪秽不洁,过者掩鼻,而狗彘甘之;损于尺者益于寸,弃于寒者须于热。是故以大拟小,以可方不可,则愈争而愈乱矣。各适其宜,各任其分。则无大无小,无可无不可……大道无名,荡荡冥冥,真性无体,混混默默,万化之所由起,而众妙之所由出也。(11)[韩]张维:《溪谷集》卷3《设孟庄辩论》,《韩国文集丛刊》(092),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2年,第59-60页。
这是《设孟庄论辩》第六段庄子的论辩,文中的庄子主张万物可齐,肯定万物“物性”的不同,然后通过万物在根源上的一致性论证万物本一,万物可齐。认同万物可齐是以承认万物差异性为前提的,如果万物不存在差异,也就没有齐同的必要了。物各有其“物性”,所以物与物是有区别的。文中用太山与秋毫的大小之别、彭殇寿命长短的差异、鲵桓鱼鳖和人居所的不同、人和狗彘对粪便的排斥态度的不同等例证说明世间万物具有不同特征,千差万别。其中,太山秋毫“小大之齐”和彭殇寿夭“修短之齐”是化用《庄子·齐物论》的“夫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乎殇,而彭祖为夭”。虽然世间万物“物性”不同,但万物“各适其宜,各任其分”,即任其不齐,各安其分,顺应自然性情,内心便再无大小之分。最后从根源来看,万物同源,故万物一齐。“大道无名,荡荡冥冥,真性无体,混混默默,万化之所由起,而众妙之所由出也”中,张维从实际的生命过程、生化现象出发,在对万物起源的追溯过程中揭示万物产生的根源和方式,即万物都源于“道”“气”,都是在“道”的支配下“气”化生万物。张维通过孟子和庄子的论辩阐释“齐物论”,层层推进,逻辑清晰,灵活巧妙。《设孟庄论辩》从问答论辩形式、思辨逻辑到思想内容,都深受《庄子》的影响。
二、对《庄子》的发展
《庄子》以“道”为本,以“自然”为旨归,主张“万物与我为一”,倡导“自然无为”。张维受《庄子》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庄子》物我观的认同,对自由自适人生境界的追求。在文学创作理论上,张维接受《庄子》“自然”“真”等理论,并结合时代背景,融入自己对文学创作的见解,主张文学创作是自然真性情的表现,反对抄袭模拟,倡导学术自由。
(一)崇尚天机之妙
“庄子哲学思想对韩国古典美学、古代文论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中朝鲜朝后期诗论‘天机论’文学思想与文学风格的形成,与庄子哲学思想的影响有着深刻的联系。”(12)任晓丽、邱峰:《朝鲜朝后期诗论“天机论”与庄子哲学》,《外语教学》2014年第2期,第81页。“与许筠同时代的张维,从自然认识的视角,认识庄子的‘天机论’,开创了独特的诗歌意识‘天机论’。”(13)蔡美花、郭美善:《朝鲜古代“天机论”的形成与发展》,《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60页。“天机”的概念起源于中国,在朝鲜朝前期传入朝鲜,之后逐步发展成为具有朝鲜特色的诗歌理论。张维接受《庄子》“自然”“真”等理论,将“天机论”发挥到可以作为文学评论的价值尺度,进一步完善了诗论“天机论”。
诗,天机也。鸣于声,华于色泽。清浊雅俗,出乎自然。声与色,可为也;天机之妙,不可为也。如以声色而已矣,颠冥之徒,可以假彭泽之韵;龌蹉之夫,可以效青莲之语。肖之则优,拟之则僣。天何故,无其真故也。真者何?非天机之谓乎!……而凡形于口吻,动于眉睫,无非诗也者。及其成章也,情境妥适,律吕谐协,盖无往而非天机之流动也。(14)[韩]张维:《溪谷集》卷6《石洲集续》,《韩国文集丛刊》(092),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2年,第113页。
张维论诗,最注重的就是“天机”。“天机”最早出现于《庄子·大宗师》:“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陈鼓应先生注曰:“天机:自然之生机。”(15)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71页。张维认为“天机”是一种不可为的妙境,是最直观的体悟。张维强调诗歌创作的自然性,无论是感物吟志,还是表情达意,都要出于自然,并以此作为创作宗旨和艺术追求。张维这种“出乎自然”“不可为”的“天机”诗论主张与《庄子》的自然观十分契合。文中的“声”即音韵,“色”即文辞藻饰,这些外在形式方面是“可为”的,而天机之妙则“不可为”。张维称那些一味模仿、刻意押韵和堆砌辞藻的诗人为“颠冥之徒”“龌蹉之夫”。张维不仅在诗歌创作上反对矫揉造作,在古文创作上也反对刻意雕琢藻饰,甚至将“不事雕饰”视为评论文章的标准:“先生于文章,不事雕饰,而气力宏厚,波澜老成,蔚然成一家言”。(16)[韩]张维:《溪谷集》卷6《高峰先生集序》,《韩国文集丛刊》(092),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2年,第106页。“时有兴会,辄信笔成章,不事雕饰。而一时宗匠诸公,多称赏其美。”(17)[韩]张维:《溪谷集》卷6《梧阴集序》,《韩国文集丛刊》(092),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2年,第116页。“不事雕饰”并不是完全摒弃文辞修饰,而是要运用得当,过于刻意的雕饰便失去了真意,不能称之为绝世佳作。“我朝之文,大不如前丽。称名家者三,乖崖、占毕及近代崔简易。三家短长,余于简易集序略论之。占毕似最优,以其词理备耳。”(18)[韩]张维:《溪谷先生漫笔》卷1《我朝文章大家有三》,《韩国文集丛刊》(092),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2年,第578页。相比朝鲜朝前期“文以载道”的儒家文学观,张维不拘泥陈腐旧规,主张“华实兼备”的文道观,认为文道并非对立,而是要同时“兼备”。“修辞”与“理趣”应是相辅相成的,两者并行,平衡发展,任何一方有偏颇,都会过犹不及。所以张维在评论当朝诗文大家时,也首推出于自然、辞理通畅之作。张维反对刻意雕琢、崇尚自然与《庄子》的自然观一脉相承。

张维认为诗歌创作是“天机之流动”,创作主体的艺术构思应是自然自由的。作诗不能勉强,勉强而作的诗歌,即便情境妥适,音律和谐,也不能称之为“天机之流动”。张维提倡学术自由,对当时独尊儒术的学术垄断进行了强烈批判:“中国学术多岐,有正学焉,有禅学焉,有丹学焉,有学程朱者,学陆氏者,门径不一。而我国则无论有识无识,挟策读书者,皆称诵程朱,未闻有他学焉。……我国则不然,龌龊拘束,都无志气。但闻程朱之学世所贵重,口道而貌尊之而已。不唯无所谓杂学者,亦何尝有得于正学也”。(23)[韩]张维:《溪谷先生漫笔》卷1《我国学风硬直》,《韩国文集丛刊》(092),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2年,第573页。朝鲜朝前期,性理学成为当时新的伦理秩序和政治体制的依据,具有国教一样的地位。儒学的兴盛,对当时社会政治和各种社会意识层面均有很大影响,对文学影响尤为深刻,甚至形成了独尊儒术的学术垄断。张维认为应广泛学习前人经典典籍,但不应被既有模式所束缚。张维这种学术上追求自由、勇于创新的观念都深受《庄子》影响。
(二)追求无极子之境
张维认同《庄子》“万物与我为一”的物我观,崇尚“自然无为”,追求“物我一致”的人生境界。张维能够站在“道”的高度,以相对的眼光看待世事万物,以自然坦然的心态面对万物变迁,可见他对《庄子》的接受是高境界、高层次的接受。
夫无极子之巧,视不以目,运不以手,思虑不以心知,镌琢不以锥鏧,无缋彩而文,无毛羽而饰。本乎自然,体乎无为,运乎无气。以阴阳为器,以五行为材,行以四时,化以风雨,传翼而飞,著足而走,根荄华实,羽毛鳞介,情性之通塞,窍穴之开阖,方圆长短之形,白黑玄黃之色,物物具备,充满乎天地者,皆无极子之为也,而无极子未尝自以为巧。……无为而无不为,以合乎天则。然后无极子乃始为公子役矣。夫得无极子为役,造化为我技,万象为我物,陶铸天地,砻磨日月,卷舒风云,琢抉山河,物物皆我之为,而我未尝有所为。(24)[韩]张维:《溪谷集》卷3《无极子之巧》,《韩国文集丛刊》(092),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2年,第47页。
张维笔下的无极子是一位“天下无出其右”技艺高超的雕刻工匠,他以道为本,以巧技为末,视物不以目,取物不以手,思考不以心,雕刻不以锥具。《无极子之巧》中的人物无极子与《庄子》开篇“吾丧我”的故事异曲同工,无极子“视不以目,运不以手,思虑不以心知”便是南郭子綦“吾丧我”的状态。“以阴阳为器,以五行为材,行以四时,化以风雨”则是《庄子》中的“天人合一”。“而无极子未尝自以为巧”与《庄子·大宗师》中的“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本质一致,相比于“形”,张维更注重“神”的传达,只有“本乎自然,体乎无为,运乎无气”,才能做到传神,其中的“自然”便是道,即本于道,而“道”作用于万物的方式是“无为”,由此将自然无为的意旨揭示了出来。《无极子之巧》故事中有位楚公子,他最喜雕刻之巧,所以寻遍天下的能工巧匠,如闻哪位雕刻工匠手艺超群,必以厚礼相邀。东郭先生告诉楚公子有一位叫无极子的雕刻工匠,雕刻的作品举世无双。于是楚公子便想见识下无极子的技艺,但无极子不应问答,不受邀求。东郭先生便告诉楚公子要摒除一切欲望杂念,静心凝神,三月后无极子之居便可隐然而现,“无为而无不为,以合乎天则”,无极子便可为楚公子所役。这里的“无为而无不为”即自然无为,“张维通过对‘无极子之巧’的描述,表达了对‘丧我’‘无我’之境的追求”。(25)郝君峰:《朝鲜时期士大夫对庄子的受容及其寓言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仁荷大学,2011年,第79页。
张维认同《庄子》“万物与我为一”的物我观,主张人与世间万物平等,这个“平等”是在尊重世间万物都有各自性情特质差异的基础上,追求跨越物我差别的境界。“自在而鸣,群和互答,无求于人,不忤于物。纵喧闹之可厌,亦何异夫吾人之叫呼而欢谑。盖物我之一致,各自安其所而乐其适。在昔达者,知鱼之乐,亦有先正若张、朱氏,喜驴鸣而惬心,闻蝉声而醒耳。乐吾之乐,而与物同,盖默通乎至理。”(26)[韩]张维:《溪谷集》卷1《蛙鸣赋》,《韩国文集丛刊》(092),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2年,第23页。《蛙鸣赋》主要讲述了在仲夏之月,群蛙繁衍的鸣叫声十分鼓噪,张维被蛙鸣侵扰得坐卧难眠,于是便找人用各种方法驱散蛙群。待一切恢复宁静,终才心愉体畅。之后有客笑论张维此举过甚,张维听后有所启悟,便借由《蛙鸣赋》中客之口阐释了《庄子》“万物与我为一”的物我关系。虽然蛙鸣扰人,但蛙鸣是“自在而鸣,群和互答,无求于人,不忤于物”,其本质与人们的笑声或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声音没有区别。“盖物我之一致”,从人和万物与青蛙和万物在宇宙中的地位来看,人和青蛙是同等的。“各自安其所而乐其适”,天地中所有人、事、物都有不同的特征,且正是由于万物的差异性,世界才更加和谐,万物都要顺应自然,这样才能自安自乐。之后,张维引用了庄子的知鱼之乐、张载和朱熹喜闻驴鸣的典故来加以阐释,认为庄子可以感受到鱼之乐,张载和朱熹能够在听驴鸣中体会到自然的和谐之处,是因为他们物我不分,认为万物与我一致。由此可见张维对“物我一致”人生境界的追求。
三、结语
张维对《庄子》的接受不是表层浅显的接受,而是高境界、多方面的接受。张维从《庄子》中汲取养料,创作的寓言通俗易懂又充满哲思,以鹓鶵自况,寄托心志,批判讽刺,反映现实。张维对《庄子》“齐物”思想也有着深刻的领悟,认同《庄子》“万物与我为一”的物我观,崇尚“自然无为”,追求“物我一致”的人生境界,并吸收《庄子》中的哲学思想,将其内化为文学创作理念。在文学创作上,张维接受《庄子》“真”“自然”等理论,认为诗歌创作是“天机之流动”,创作主体的艺术构思应是自然自由的,强调文学创作的内在真实性、天然性,进一步完善了诗论“天机论”。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可以看出《庄子》对张维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