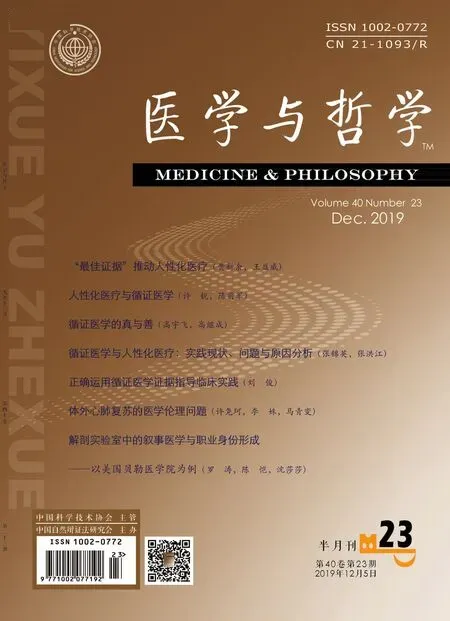耆婆及其医学思想探析
梁玲君 李良松
佛教自古印度传入我国后,对我国传统医学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其中,耆婆对佛医学的传播影响深远,是研究我国传统医学乃至古印度医学不容忽视的一位代表性人物。陈寅恪认为“吾国旧时医学,所受佛教之影响甚深,如耆域(或译耆婆)者,天竺之神医,其名字及医方与其他神异物语散见于佛教经典,如《柰女耆婆温室经》及我国医书如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王焘《外台秘要》之类,是一例证”[1]。耿刘同在《中医学与佛医》中指出“印度医学人物中对我国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耆婆”[2],耆婆在医学发展历程中的贡献可见一斑。耆婆在医学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但在现代医药学领域中耆婆鲜为人知,笔者认为探析耆婆及其医学思想,对于理解传统医学体系中的相关内容和临床实践有参考价值,本文试就耆婆及其医学思想进行论述。
1 耆婆生平概述
耆婆,又称耆婆伽、耆域、时婆、时缚迦,他不仅精通佛学,而且医术精湛,是佛陀时代极具神话色彩的著名医生。相传耆婆自幼聪慧,立有“愿我未来世作大医师供养佛”的志愿,跟从当时名医宾迦罗勤习医学,医技超常精进。耆婆学业期满后,其师为锻炼其意志,“与耆婆弊故之衣,不与粮食,耆婆辞师还去”,于是耆婆攻克重重苦难,开始了行医之路。耆婆治愈的首例病案是以用酥煎之药物进行灌鼻清洗的方式治愈婆伽陀城大长者之妇患12年之久的头痛。后耆婆因治愈瓶沙王痔疮出血而被聘为御医,成为御前第一名医,专门负责为国王、佛陀、佛门弟子及宫内之人治疗疾病。现存的文献资料中记载,耆婆屡次为佛陀和佛门弟子治愈疾病,佛门将其尊为“医王”,并且享有“神医”、“良医”等佳誉。后汉安世高译的《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评价耆婆为“大医王,疗治众病”,东晋竺难提译的《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咒经》以“良医”来称谓耆婆,如“此国人民遇大恶病,良医耆婆其道术所不能救”[3]。在我国传统医学中,有文献记载耆婆的名望可以与我国黄帝、名医扁鹊相媲美,如《张仲景五脏论》载“黄帝而造《针灸经》,历有一千余卷。耆婆童子,妙娴药性,况公厶等凡夫,何能备矣”[4]19,文中将耆婆与黄帝分庭抗礼;《张明德邈真赞并序》载“寻师进饵,扁鹊疗而难旋;累月针医,耆婆到而不免”,将耆婆与扁鹊相提并论,可见耆婆在当时社会中的影响力之大。范行准在《胡方考》中写道:“自六朝以来,传入胡方之主角,为婆罗门教徒、佛教徒,在晋宋时代多奉耆婆为大医。”[2]耆婆治疗疾病涉及面广,涵盖内、外、妇、儿、五官各个科别,尤其在儿科上,有“小儿医”之称,如西晋竺法护译的《修行地道经》载“复有小儿医,其名曰尊迦叶、耆域、奉慢、速疾,是等皆治小儿之病”。印度民俗“杜鹃鸟斋戒”等,即是纪念医王耆婆的风俗,至今在印度依然盛行[5]。
2 耆婆医学思想
耆婆以精通医术闻名于世,有妙手回春之术,曾屡次治愈各种疑难沉疴。从现存文献资料可知,在医学思想方面,耆婆对药物学的认识、疾病的基础理论、诊断和治疗等各个方面均有其独到见地,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2.1 万物皆药的用药思想
耆婆在药物学的研究上见解深刻,洞晓药理,对药物的认知有独到的见解。《张仲景五脏论》开首写到“耆婆童子,妙娴药性”,“妙娴”两字道出耆婆在药物学上有真知灼见。耆婆提出了“万病皆药”的用药思想,这一观点体现了其对药物认识上的开放性,大大扩充了药物的来源和应用范围,丰富了药物学的品种,在药物学发展史上烙下了深刻的印记,耆婆提倡“天下所有,无非是药”的理论。《佛说柰女耆域因缘经》中记载耆婆在求学中因认识到“天下草木皆有所用,皆可入药治病”的理论,其师认为其医道已成。《杂譬喻经》中以神话故事的形式记载耆婆去世后,天下草木为之哭泣,因只有耆婆对药物的功效了然于心,后世医家或使用错误、或药物剂量不能很好地把握而致使疾病不能治愈,“天下草木皆可为药,直不善别者故不知耳。昔有圣医王名曰耆域,能和合药草作童子形,见者欢喜众病皆愈。或以一草治众病,或以众草治一病,天下之草无有不任用者,天下之病无有不能治者。耆域命终,天下药草一时涕哭,俱发声言:‘我皆可用治病,唯有耆域能明我耳。耆域死后无复有人能明我者,后世人或能错用,或增或减令病不差,令举世人皆谓我不神,思惟此以故涕哭耳’。”北凉昙无谶翻译的《方等大集经》中明确指出耆婆“万物皆药”的用药观点,“耆婆医王常作是言:天下所有,无非是药”。
佛法在传播的过程中,常常借用耆婆“天下所有,无非是药”的药物观比喻佛法,通俗易懂地阐明佛法义理,客观上宣传和弘扬了耆婆万物皆药的思想,也极大地丰富了耆婆药物使用观的认知群体。《大般涅槃经疏》卷二十四云:“譬如耆婆执草成药,佛亦如是,遍一切法无非中道,中道即是佛性。”《佛说海印菩萨所问净印法门经》卷七云:“譬如耆婆医王,普观大地一切草木无非是药。修行般若波若蜜多经菩萨亦复如是,观一切法无非菩提。”
唐代医家孙思邈在药物观上吸收了耆婆“万物皆药”的思想,在《千金翼方》卷一“药录篡要”中云:“有天竺大医耆婆云: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斯乃大医也。”[6]正是基于耆婆的这一用药观,孙思邈指出“神农本草,举其大纲,未尽其理,亦犹咎繇创律”,故述录药名品,“欲令学徒,知无一物之非药耳”[7]。自此以后,中医本草药味数量不断增加,诸多外来传入的药物被我国传统医学使用并记载。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云“敝维敝盖,圣人不遗;木屑竹头,贤者注意,无不弃物也”[8],这与耆婆“万物皆药”的思想观是一致的。
2.2 医学基础及诊断内容
佛经中关于耆婆佛法的观点和行医的故事可以反映出耆婆基础理论和诊断的方式。如《大般涅槃经》卷第十八云:“耆婆答言:‘大王,譬如渴人速赴清泉,饥者求食,怖者求救,病求良医,热求荫凉,寒者求火,王今求佛亦应如是’。”这一说法说明耆婆认识事物的思维模式,但也可由此推知耆婆在医学上治病原则上的思路,即针对疾病的病因选择与此相对应的药物,依据疾病病因而投以相对应的治疗法则。这种观点某种程度上与我国传统医学中“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等的原则是一致的。又如透过《四分律》等记载耆婆治愈的案例中,可知耆婆问诊上遵循三步骤,即“何所患苦?”“病从何起?”“病来久近?”反映出耆婆问诊上的特点,重视疾病的现病史和既往史。耆婆对疾病预后的判断精准,对病情的发展过程和治愈过程了然于心,如《佛说柰女耆域因缘经》中耆婆判断迦罗越之女在手术之后十天疾病便可痊愈,并嘱咐“好令安静,慎莫使惊,十日当愈平复如故,到其日我当复来”。
2.3 治病法门丰富
耆婆精通药物、医方、针刺诸术,治病法门丰富。从现存文献可知,耆婆在头痛、疮疡、下利、便血、水肿、痈肿等疾病方面有丰富的诊疗经验,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可知,耆婆在疾病的治疗方法上,诸法并用,众法并举,涉及药物疗法、刀针疗法、针刺疗法、沐浴疗法、饮食疗法等治疗手段。
2.3.1 药物疗法
耆婆在使用药物进行治疗时,既可“一草治众病”,又可 “众草治一病”,说明在治疗疾病中,耆婆对单味药物或复合药物的选取非常灵活,如《四分律》卷四十记载耆婆以煎酥为药治愈尉禅国王波罗殊提陈旧性的头痛。姚秦沙门竺佛念译《菩萨从兜术天降神母胎说广普经》卷七记载有耆婆为佛陀治理“左肋患风”所开的复合性药方,“当须牛乳、象尼奥、舍利沙、毕钵、尸利沙、胡椒,煮以为汤中,服之则差”。在给药途径上,耆婆使用方法丰富,涉及内服法、灌鼻法、涂酥法、药膏涂抹法、嗅闻法等。如《经律异相》卷三十二记载的灌鼻法治疗头痛:“时,耆婆诣长者妇,即取好药以苏煎之,灌长者妇鼻及口中。苏唾俱出,使人以器承之,苏还收取,唾别弃之……后病得差。”[9]《四分律》卷四十记载令病人饮用药酒进行麻醉:“尔时耆婆,即与咸食令渴,饮酒令醉,系其身在床。集其亲里,取利刀破头开顶骨示其亲里:‘虫满头中,此是病也。’”耆婆重视药物剂量的使用,对药量的把握精准,如《十诵律》卷二十七记载耆婆为佛陀治疗冷湿病中提到,耆婆要求佛陀嗅药草熏的青莲华遵循“一嗅十下,二嗅二十下,三嗅三十下”,而佛陀“一嗅其药十下,二嗅二十下,三嗅二十九下”,耆婆得知后,知佛陀身病未尽,嘱佛陀“须饮少暖水,饮已更一下,如是随顺满三十下”,后佛陀康复。
2.3.2 刀针疗法
耆婆善用刀针治疗疾病,刀针疗法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手术疗法的雏形,《佛说柰女耆域因缘经》《佛说柰女耆婆经》《四分律》等均涉及耆婆运用刀针治疗疾病的案例,可见当时耆婆运用刀针技术之娴熟程度。耆婆刀针疗法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重视刀针治疗导致的疮口的愈合。耆婆刀针治疗的病案中均提到要使用神膏涂抹疮口,以帮助刀疮的快速愈合。虽未提到修复疮口的神膏所用的具体药物,但却为我们提供一个外涂药物的治疗思路,用以加速刀针疮伤的愈合。(2)应用刀针治疗的严谨性。从问诊到刀针手术,再到手术后遗症的处理,环环相扣,可谓面面俱到。如《四分律》中记载耆婆刀针治疗瓶沙王患痔疮出血案例中,先进行问诊,了解疾病的病情,再全身麻醉,使用温开水将患处泡洗后,用刀针割破患处,清洗疮口,涂上药物,整个手术过程可知耆婆应用刀针之严谨、程序之完备、手法之娴熟。(3)刀针与药物并用,增强疗效。刀针手术治疗后,要配合使用具有不同治疗作用的外用神膏,两者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如耆婆运用刀针行破腹术纠正肝脏位置的案例中提到,其术后用三种神膏,其功效分别为“补手所持之处”、“通利气息”、“生合刀疮”。有关耆婆使用刀针的治疗案例记载与《后汉书》中关于中国外科鼻祖名医华佗诊疗疾病的记载相似。为此,国学大师陈寅恪在《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中写道:“考后汉安世高译《柰女耆婆因缘经》所载神医耆域诸奇术,如治拘啖弥长者字病,取利刀破肠,披肠结处,封着罂中,以三种神膏涂疮……其断肠破腹固与元化(华佗之字)事不异,而元化壁县病者所吐之蛇以十数,及治陈登疾,令吐出赤头虫三升许,亦与耆域之治迦罗越家女病不无类似之处……”[10]这一考证反映出耆婆刀针技术水平的高超。
2.3.3 针刺疗法
文献资料中屡次记载耆婆“生而把持针药”、“初生时手持针药囊”、“生时一手把药囊,一手把针筒”等, 由此可窥探出在佛陀时代针刺之术就已盛行,耆婆乃是针刺疗法的大家。敦煌医书《张明德邈真赞并序》云:“寻师进饵,扁鹊疗而难旋;累月针医,耆婆到而不免。”[4]178点明了耆婆擅长针刺之术。《十诵律》卷四十中关于耆婆治疗痈肿案例中记载耆婆认为应当将痈肿捅破,挤出脓血,并配合药物拔出脓物的治疗方式,文中虽未对操作的具体工具进行描写,但通过分析可知,与我国传统医学中的三棱针点刺的治疗方式是相似的,是针刺的一种治疗形式。耆婆的针刺之术是有传承的,据《高僧传》记载,东晋僧医于法开,妙通医学,“师事于法兰,祖述耆婆”。《绍兴府志》中记载了于法开针刺配合羊肉羹治疗难产,“开命产妇食羊肉十余块而后针之,须臾儿即产下”。
2.3.4 其他疗法
耆婆善用沐浴却疾之法,《佛说温室洗浴经》中记载耆婆请佛及佛弟子入温室澡浴,“愿令众生长夜清净,秽垢消除,不遭众患”,强调了沐浴的防病治病作用。《毘尼母经》卷第六云:“耆婆医王观病处药,若得浴室此病可差。复欲令祇桓精舍中浴室得立。”耆婆提倡饮食疗法,如《萨婆多毗尼毗婆沙》卷一载耆婆认为以断食的方法治疗佛门弟子之病,“目连问耆婆曰:‘弟子有病,当云何治?’耆婆答曰:‘唯以断食为本。’”《四分律》卷三十四载耆婆药物配合羹等类的饮食将养形式疗疾,“时耆婆童子,疗治佛及比丘僧,给与吐下药,或可与羹者作与,不可与者不与作,或与野鸟肉作羹,随病者所食,蒙此转得除差”。耆婆还强调充足的睡眠有助于疾病的治疗,如《维摩义记》卷第二记载阿那律“多日不眠遂便失眼”,拜访耆婆为其治疗,“耆婆对曰睡是眼食,久时不眠眼便饿死”。
3 与耆婆相关的医方
《医方类聚》云:“药名之部,所出医王,黄帝造《针经》,历有千卷。药性名晶,若匪神仙,何能备著? ……耆婆童子,妙述千端,喻义医王,神方万品。”说明耆婆医方功效之神奇。从现存文献资料考证,不乏以耆婆之名命名的医书,如《隋书·经籍志》记载的《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二卷,《宋史·艺文志》录有三卷《耆婆脉经》、一卷《耆婆六十四问》和一卷《耆婆五脏论》,《医心方》收录的《耆婆方》,此外,还有《耆婆针灸图》等。但这些著作只能定论为冠以“耆婆”之名,是否是耆婆本人所作还有待考证。范行准在《胡方考》一书中记载:“印度人奉耆婆为大医,一如中国人之崇奉扁鹊,此亦可耐人寻味之事也。更可耐人寻味者,中国医家往往好托名扁鹊;彼西来僧侣,亦恒托名耆婆医炫其术;更有不少中国人托名耆婆而传者。”耆婆本人医药学知识丰富,医学水平高超,诊疗经验丰富,以致诸多传入中国的印度药方,被冠以“耆婆”之名[11]。由于汉魏六朝时期诸多与耆婆相关的医学著作现已亡佚,无从考证后世所传的医学著作是耆婆本人所作还是托名所作。但冠以“耆婆”之名,即足以窥见耆婆对当时医学发展的影响意义。
孙思邈的《千金翼方》卷二十一中收录了“耆婆治恶病”,涉及11首方,7论,乃是僧医治麻风病的经验总结。卷十二载有“耆婆汤”,《千金翼方》记载“耆婆大士治人五脏六腑内万病及补益长生不老方”。《千金要方》中记载有“耆婆万病丸”,孙思邈指出:“以耆婆为良医,故名耆婆丸。”客观上反映耆婆医学思想对孙思邈选方用药有影响意义,孙思邈的医学观受益于耆婆的医药学思想。《耆婆书》出土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第17窟,现存写卷属印度医学体系,有医方精选集的特点,其中不乏佛门医学的影响[12]。《耆婆五脏论》冠以“耆婆”之名,但该书目不见于佛门典籍,颇多医学思想结合中国传统医学反映五脏、五行的学术特点,认为其是医家托名之作[13]。《医心方》中收录的《耆婆方》经考证似为隋朝以前的著作,有学者认为其治疗所用的方药与中国传统医学体系如出一辙,只是引用了一些佛门医学术语,疑似佛教信众借耆婆之名所作。诸多以“耆婆”名冠名的医书,虽可能是托名之作,但却说明耆婆在医药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影响力量。
4 结语
综上所述,透过耆婆的生平、医学思想以及后世医家托其名所作的诸多著作,可知耆婆医学水平高超,具有丰富的诊疗经验,其思想在医药发展的长河中有重要的影响价值,也可看出耆婆在中印医学交流史上所做出的贡献。佛经中记载的耆婆的案例难免会神话或夸大耆婆的影响力,但不能因此而淡化耆婆在医学发展中所作出的贡献。我国现存文献中记载有诸多耆婆名义上的著作,恰恰说明耆婆在隋唐及其之前对我国医学的影响力,正确认识耆婆的医学思想,有助于理解我国传统医学中吸收借鉴外来医学的学术内容,进而更好地服务于临床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