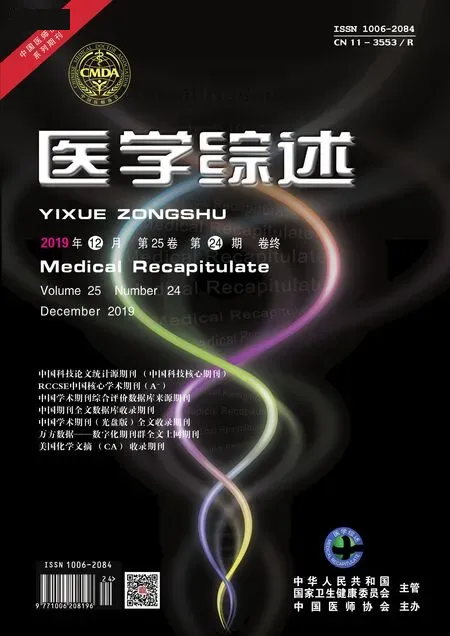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伊马替尼耐药治疗新进展
于冬旭,高玉娟,杨立莹,杨东光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a.血液内科,b.中心血液实验室,哈尔滨 150001)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hronic myeloid leukemia,CML)是一种常见的造血系统恶性肿瘤,主要表现为骨髓中髓样细胞的增多和不受控制的生长及其在血液中的积聚。CML的标志是费城染色体,其由染色体9和22长臂之间的相互易位产生,该染色体易位导致Bcr-Abl表达,Bcr-Abl是具有组成型活化的Abl酪氨酸激酶的原癌融合蛋白。其通过激活下游信号蛋白促进白血病的发生,从而增加细胞的存活和增殖[1]。这些信号蛋白包括RAS/促分裂原活化的蛋白激酶激酶、磷脂酰肌醇-3-激酶(phosphatidylinositide 3-kinase,PI3K)/蛋白激酶B(protein kinase B,PKB/Akt)和Janus激酶/信号转导及转录激活因子[2]等。以伊马替尼(imatinib mesylate,IM)为代表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TKIs)是治疗CML的一线药物,该药能特异性阻断ATP在Abl激酶上的结合位置,使酪氨酸残基不能磷酸化,从而抑制Bcr-Abl阳性细胞的增殖,相对于干扰素、白消安、羟基脲等传统治疗药物,IM可显著提高CML治疗效率及早期患者的生存率,但该药物并不能治愈CML,且可能出现IM的耐药,对晚期CML患者IM疗效欠佳,不能阻止疾病的复发和进展[3]。IM的耐药机制复杂,按是否与Bcr-Abl相关可分为Bcr-Abl依赖性或Bcr-Abl非依赖性[4]。现就CML IM耐药机制及新治疗进展予以综述。
1 IM耐药机制
1.1Bcr-Abl依赖性耐药机制 Bcr-Abl依赖性耐药机制主要包括Bcr-Abl基因点突变、Bcr-Abl融合基因的扩增、Bcr-Abl蛋白的过表达等,其中Bcr-Abl激酶结构域发生点突变是最常见的耐药原因[5],而T315I突变是最顽固的点突变,占Bcr-Abl激酶结构域点突变的15%[6]。IM主要作用于Bcr-Abl融合基因区域,若其作用位点发生突变,则药物将不能与其结合从而导致下游异常信号转导,临床表现为肿瘤细胞的继续增生克隆,因而产生耐药[7]。同时,Bcr-Abl基因中的突变能干扰Bcr-Abl的激酶结构域与抑制剂分子之间形成的关键氢键,削弱Bcr-Abl蛋白结合抑制剂分子ATP结合位点的能力。最常见的Bcr-Abl激酶区突变主要为以下4个簇区发生突变:P-环簇、T315近侧簇、酶促反应簇和A-环簇,其中P-环和T315I的突变作用最强且最常见,可完全阻断IM与ATP的结合[8]。除Bcr-Abl激酶突变外,Bcr-Abl融合基因的扩增和蛋白的过度表达也是导致IM耐药的常见原因,其可使原有剂量的IM不足以控制病情,从而导致耐药的发生。
1.2Bcr-Abl非依赖性IM耐药机制
1.2.1白血病干细胞(leukemia stem cells,LSCs)的存在 CML-LSCs或称白血病起始细胞是所有CML细胞的共同祖先。LSCs的一些生长特性决定了其对TKIs的治疗具有抵抗作用。①虽然Bcr-Abl蛋白赋予了CML-LSCs白血病的特征,但Bcr-Abl并非CML-LSCs赖以生存的唯一蛋白。在IM的作用下,CML-LSCs还可以通过其他信号维持存活。研究证实,尽管IM对CML患者静止期和循环中干、祖细胞的Bcr-Abl蛋白活性具有抑制作用,却无法清除CML-LSCs[9]。②CML-LSCs具有遗传不稳定性,随着对CML治疗的深入研究发现,CML-LSCs逐渐产生基因突变,形成CML的克隆演变,对现有治疗方法产生抵抗[10]。虽然TKIs持续作用,但CML-LSCs仍可以维持存活状态,并随着克隆演变最终失控生长,这是CML发生非Bcr-Abl依赖式耐药的根本原因[11]。因此,清除对治疗不敏感的CML-LSCs,是治疗 IM耐药的关键[12]。
截至目前,研究者已发现多种CML-LSCs赖以生存的信号通路及其相应的靶向性药物。这些信号通路主要包括Bcr-Abl/PI3K/Akt/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通路、Hh(Hedgehog)通路、Wnt通路、Bcl-6/p53通路等。研究发现,PI3K/Akt/mTOR通路经常在许多人类癌症中被激活,PIK3CA突变和人第10号染色体缺失的磷酸酶及张力蛋白同源基因功能丧失可导致对靶向PI3K/Akt/mTOR信号转导途径治疗的敏感性增加;同时该研究还发现,PI3K/Akt/mTOR通路与IM耐药相关[13]。因此,鉴定靶向抑制剂可以为CML治疗提供新策略。
Hh信号转导途径是进化上的保守途径,其在调节涉及正常干细胞分化和增殖以及无脊椎动物和脊椎动物中适当分离的各种发育和生理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然而,学者发现在胚胎发育期间Hh通路的错误调节会引起各种先天缺陷及几种肿瘤转化和恶性肿瘤[14]。此外,Hh通路在维持体细胞干细胞和多能细胞中起重要作用,它参与了肺、牙齿、肝脏、前列腺和膀胱中上皮干细胞的再生增殖,且这种信号转导通路可能与癌症干细胞的维持相关。因此,通过抑制Hh信号转导通路靶向癌症干细胞是一种可以有效改善癌症患者临床结果的潜在治疗方法[14]。Hh通路是一条干细胞通路,但作为CML-LSCs的重要通路,Hh信号分子并不位于Bcr-Abl的下游,也不能被TKIs所抑制,提示对IM耐药的患者,需联合Hh靶向性抑制剂进行治疗。
自从Wnt信号通路被发现以后,许多针对Wnt信号通路及其抑制剂在恶性肿瘤治疗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Wnt信号通路分为经典的依赖β联蛋白途径和非经典的不依赖β联蛋白途径,β联蛋白是正常造血干细胞自我更新和生存所必需,Wnt/β联蛋白通路在CML-LSCs的持续存在中具有重要作用[15]。
Bcl-6/p53通路对肿瘤细胞对抗肿瘤药物的敏感性有调节作用。体外和体内研究表明,费城染色体阳性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细胞和IM耐药的CML细胞均有Bcl-6蛋白的高表达;Bcl-6介导p53的上调,Bcl-6通过靶向p53诱导IM耐药细胞的生长抑制和凋亡[16]。
此外研究发现,CML-LSCs表达的某些蛋白可作为其潜在的治疗靶标,如γ联蛋白[17]、血红素加氧酶-1[5]、蛋白质精氨酸甲基转移酶5[18]等与IM耐药密切相关。
1.2.2LSC的骨髓微环境 对于白血病、淋巴瘤等恶性血液病,癌细胞与骨髓基质细胞动态相互作用,且更有可能在骨髓微环境中产生耐药性。研究发现,骨髓微环境中的可溶性因子,如基质细胞衍生因子-1、CXC趋化因子配体12和白细胞介素-6可介导肿瘤细胞的归巢、存活和增殖,并引起可溶性因子介导的抗药性[16]。CXC趋化因子配体12的激活是导致白血病细胞耐药的关键因素之一,其在造血干细胞归巢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介导人和小鼠祖细胞的存活和增殖。骨髓微环境通过激活CXC趋化因子配体12/CXC趋化因子受体7通路和胞外信号调节激酶磷酸化诱导CML细胞对IM治疗的抗性[19]。
1.2.3多药转运体和药物靶酶的过度表达 IM的耐药机制非常复杂,研究表明,多药转运体和药物靶酶的过度表达可能与CML的IM耐药有关[20]。其中,研究最深入的机制为由P-糖蛋白(P-glycoprotein,PGP)和多药耐药相关蛋白-1介导的多药耐药。PGP由多药耐药基因(ATP结合盒B亚家族成员1转运蛋白基因)编码,并参与药物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多药转运体,如PGP、多药耐药相关蛋白家族、乳腺癌耐药蛋白等,均能促进转运,缓解细胞内药物外流或囊泡分离,导致细胞内药物浓度降低或药物分布改变。而以PGP和多药耐药相关蛋白-1介导的多药耐药为最佳研究对象[20]。
2 CML与IM耐药治疗
2.1Bcr-Abl依赖性耐药的治疗 针对不同的耐药点突变,已靶向研发出二代、三代TKIs,它们不仅对IM耐药的点突变分别起效,且激酶活性更高,抑制能力更强。其中,二代TKIs(尼洛替尼、达沙替尼和布素替尼)对除T315I外的一系列Bcr-Abl突变均有效。三代TKIs(扎那替尼)则可靶向性抑制含有T315I突变的Bcr-Abl阳性CML细胞。虽然Bcr-Abl单突变的CML患者对扎那替尼具有初始反应,但晚期患者对该药的反应有限,因为连续使用TKIs会导致Bcr-Abl激酶结构域复合突变,这种突变对扎那替尼耐药[21]。虽然新一代的TKIs可分别对各自耐药突变起效,但也能造成患者出现TKIs多药耐药现象[22]。因此,耐药患者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案,死亡率极高。
2.2Bcr-Abl非依赖性耐药的治疗 研究发现,丙泊酚[23]及靶向表皮生长因子受体激酶底物8(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kinase substrate 8,EPS8)[24]可以作用于Bcr-Abl/PI3K/Akt/mTOR通路。Tan等[23]通过体内体外联合实验,系统研究了丙泊酚及其联合应用对细胞系、患者细胞和小鼠模型的影响。结果发现,丙泊酚与TKIs联合应用对CML细胞的作用具有特异性,且不影响正常细胞,故其可能成为IM治疗的新选择。EPS8被鉴定为一种致癌基因且在广谱实体瘤中起重要作用,其与急性白血病患者的不良预后或化学抗性相关。Huang等[24]通过体外研究发现,EPS8通过Bcr-Abl/PI3K/Akt/mTOR途径调节Bcr-Abl阳性细胞的增殖、凋亡和化学敏感性,EPS8的敲低减少了BALB/c裸鼠中的K562细胞增殖。因此,单独靶向EPS8或与TKI组合可能是一种新治疗策略。
目前,研究的Hh通路抑制剂均以Smo为靶点,包括GDC-0449、LDE225、PF-04449913及BMS-833923等,Hh通路抑制剂的药理活性较Smo的天然抑制剂环巴胺提高。且研究发现,Hh通路抑制剂与TKIs联合应用,在治疗CML的临床前研究中获得了满意疗效[25]。此外在急性髓系白血病中,环巴胺能恢复LSCs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提示这类药物也可能作为逆转耐药药物[26]。研究证实,三氧化二砷对Hh通路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主要是通过抑制转录因子Gli1和Gli2的信使RNA表达,并同时上调Hh通路抑制因子ptch的信使RNA表达发挥作用[27]。可见,三氧化二砷应用于IM耐药的CML患者将会显示更大的药用价值和更广阔的应用前景。
目前针对Wnt信号通路,没有直接拮抗β联蛋白的药物,只有一些小分子Wnt通路抑制剂,如AV65、FH535、吲哚美辛等,它们可以减少β联蛋白表达并诱导CML细胞凋亡。因此,新的Wnt信号通路抑制剂有望为CML的治疗提供更多选择。
研究发现,高三尖杉酯碱可以作用于Bcl-6/p53通路,不同细胞经高三尖杉酯碱处理后,Bcl-6的表达均有中度下调;而CML患者的Bcl-6表达水平明显高于正常人,且Bcl-6在CML急变期患者中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CML慢性期患者[16]。高三尖杉酯碱的抗白血病机制不同于IM,其是用于IM耐药患者的最有效药物之一。同时,高三尖杉酯碱是蛋白质翻译的抑制剂,它通过影响核糖体的A位点来阻止蛋白质的合成,且可以通过阻断Bcl-6/p53通路抑制IM抗性细胞的生长并诱导细胞凋亡,这为IM耐药及不耐药患者的治疗提供了新选择[16]。
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是一类抗肿瘤药物,它通过增强组蛋白赖氨酸残基的乙酰化作用放松组蛋白核心表面被抑制基因的转录,其可以选择性杀伤恶性肿瘤,同时保留正常细胞。此外,用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与TKIs联合应用,可消除CML和急性骨髓增生性疾病中静止的LSCs。虽然口服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可以消除CML中的静息LSCs,但对其杀死LSCs的潜在机制尚不清楚。Jin等[17]通过用生物素标记的探针捕获,证实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对γ联蛋白的抑制作用导致CML-LSCs的消除,故γ联蛋白可能是LSCs的新型治疗靶点。Wei等[5]发现,血红素加氧酶-1通过调节组蛋白去乙酰化酶的表达参与CML细胞中耐药性的发展,这可能是CML治疗的新靶点。Jin等[18]通过体外实验发现,在CML细胞中Bcr-Abl和蛋白质精氨酸甲基转移酶5之间存在正反馈环,且在人CML-LSCs中观察到蛋白质精氨酸甲基转移酶5的过表达。另有研究表明,组蛋白精氨酸残基的表观遗传甲基化修饰是控制LSCs自我更新的调节机制,且蛋白质精氨酸甲基转移酶5可能为LSCs的潜在治疗靶标[26]。
针对基质细胞衍生因子-1、CXC趋化因子配体12和白细胞介素-6等骨髓微环境中的可溶性因子,Li等[19]研究发现,千层纸素A通过干扰CXC趋化因子配体12/CXC趋化因子受体7激活和胞外信号调节激酶磷酸化来增强IM的效应。因此,千层纸素A可能是增强IM效应和逆转耐药性的潜在药物,其为IM耐药的治疗带来新选择。
靶向PGP逆转癌细胞耐药性是目前研究最广泛的策略之一。虽然已对PGP抑制剂进行了四代研究,但由于其抑制能力不强,故没有一种药物应用于临床。而NFV(Nelfinavir)可以避免这一缺点,它是一种蛋白酶抑制剂,被用于治疗艾滋病,可能是一种潜在的PGP抑制剂。体外实验数据表明,NFV通过降低细胞内ATP含量与ATP和PGP结合位点竞争以抑制K562/ADR细胞PGP的功能,其与ADR结合导致活性氧类增加,阻断胞外信号调节激酶/Akt信号转导途径以增加细胞凋亡,从而逆转多药耐药[28]。Germacrone是一种萜类化合物,其已被报道可逆转乳腺癌细胞的多药耐药。Pan等[29]研究发现,Germacrone可通过抑制多药耐药1基因/PGP表达,逆转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K562/ADM细胞对阿霉素的耐药性,提示其可能是一种新的CML化疗多药耐药逆转剂。
3 小 结
CML是一种起源于造血干细胞水平的恶性克隆性疾病,随着IM的问世,大部分CML患者得到治愈,但仍有一些患者出现耐药,且达到完全分子生物学缓解的患者,停用IM也存在复发风险。目前针对不同突变位点设计的二代和三代TKIs,虽然可以分别对各自耐药突变起效,但也能造成患者出现TKIs多药耐药现象。研究发现,TKI不能清除CML-LSCs,大部分应用TKI治疗的CML患者Bcr-Abl信使RNA持续存在,但其具体耐药机制尚不明确[30]。未来,需进一步探究靶向CML-LSCs的耐药机制,根据不同的耐药机制研发更多新药物,从而为治愈CML提供更多的治疗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