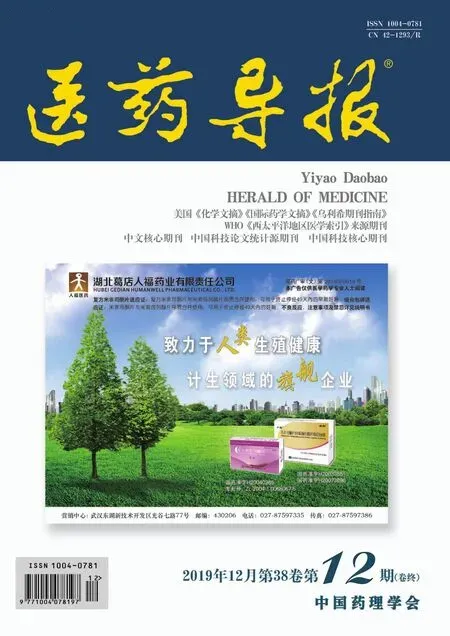表柔比星膀胱灌注致慢性心包积液1例
叶静,张宇祯,谢诚
(1.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药学部,苏州 215006;2.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药学部,乌鲁木齐 830011;3.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苏州 215006)
1 病例资料
患者,男,57岁,身高155 cm,体质量53.3 kg,体表面积1.548 m2。主诉“体检发现心包积液4 d”于2017年8月28日入院。患者自诉平日无明显不适,8月24日体检时胸部X线片示全心扩大,后查心脏超声示心包大量积液,左室收缩功能正常,舒张功能减低,左室射血分数0.68。既往有“乙型肝炎后肝硬化”病史1年余,平素口服恩替卡韦片(0.5 mg、每天1次);1年前因“膀胱占位性病变”行“经尿道膀胱肿瘤电气化术”,术前胸部X线片示心影外形及大小正常,术后分别于2017年9月6日、9月12日、9月23日、11月18日、2018年1月6日、3月13日、4月24日、6月5日、7月3日和7月31日予表柔比星50 mg加入0.9%氯化钠注射液50 mL行膀胱灌注治疗,至本次入院共计10次,累积剂量323 mg·(m2)-1,期间行膀胱镜检未见明显异常。否认药物、食物过敏史。入院诊断:心包积液,乙型肝炎后肝硬化,膀胱肿瘤切除术后。
入院体检:体温36.4 ℃,血压136/88 mmHg(1 mmHg=0.133 kPa),脉搏66次·min-1,呼吸16次·min-1。两肺呼吸音清,未及明显干湿啰音。心率66次·min-1,律齐。双下肢无水肿。实验室检查:白细胞计数4.66×109·L-1,中性粒细胞百分比0.604,总胆红素13.8 mmo·L-1,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20.1 U·L-1,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25 U·L-1,白蛋白48.6 g·L-1,球蛋白28.3 g·L-1,血肌酐72.0 μmol·L-1,三酰甘油0.96 mmol·L-1,总胆固醇4.12 mmol·L-1,凝血酶原时间11.2 s,三碘甲状腺原氨酸1.08 ng·mL-1,甲状腺素85 μg·L-1,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4.42 pmol·L-1,游离甲状腺素15.06 pmol·L-1,促甲状腺激素1.59 mU·L-1,N末端脑利钠肽前体39 pg·mL-1,抗核抗体、免疫组套和肿瘤全套等各项检验指标均无明显异常。心脏超声左室长轴切面观示舒张期左室后壁后方可探及2.4 cm液性暗区,心尖四腔切面观示舒张期心尖顶部、左室侧壁外方、右室侧壁外方分别可见0.4,1.9,1.2 cm液性暗区,右房顶部上方可见1.0 cm液性暗区,左室射血分数0.67。肝胆胰脾超声未见明显异常。胸部CT示心包腔内大量水样密度影。腹部+盆腔CT未见明显异常。Child-Pugh评分为5分,肝功能分级A级。2017年8月30日行心包穿刺术,抽出黄色微浑心包积液约300 mL送检,实验室检查:李凡他阳性,有核细胞计数1191×106·L-1,中心粒细胞百分比0.18,淋巴细胞百分比0.80,组织细胞百分比0.02,总蛋白56.76 g·L-1,白蛋白4.84 g·L-1,球蛋白51.9 g·L-1,乳酸脱氢酶170 U·L-1,腺苷脱氢酶5.6 U·L-1,淀粉酶37.0 U·L-1,糖5.89 mmol·L-1,可见淋巴细胞和间皮细胞,未见明显异型细胞。2017年9月6日复查心脏超未见明显心包积液,左室射血分数0.60,当天予以出院。术后患者未再行膀胱灌注,继续口服恩替卡韦片(0.5 mg、每天1次)。2017年10月25日门诊复查心脏超声左室长轴切面观示舒张期左室后壁后方可探及1.5 cm液性暗区,右室前壁前方可探及0.8 cm液性暗区;心尖四腔切面观示舒张期心尖顶部、左室侧壁外方、右室侧壁外方分别可见0.3 cm、1.5 cm、0.9 cm液性暗区;右房顶部上方可见1.0 cm液性暗区;左室射血分数0.74。2018年5月23日再次复查心脏超声左室长轴切面观示舒张期左室后壁后方可探及0.9 cm液性暗区,右室前壁前方可探及0.2 cm液性暗区,心尖四腔切面观示舒张期左室侧壁外方、右室侧壁外方分别可见0.4 cm、0.3 cm液性暗区,左室射血分数0.53。
2 讨论
心包积液的主要病因包括感染、创伤、恶性肿瘤、代谢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和药物等[1-5],其中单发心包积液多继发于急性感染、创伤和药物[6]。虽然严重肝硬化者也可出现心包积液,但多继发于胸腹腔积液后。本例患者“经尿道膀胱肿瘤电气化术”后次日即予以表柔比星膀胱灌注,至此次体检发现心包积液入院1年期间共灌注10次,累积剂量323 mg·(m2)-1。根据入院后的相关检查检验结果可排除药物以外导致心包积液的常见原因,而蒽环类药物引起心包积液确有相关报道[7-9],结合该患者的病情进展情况考虑可能是表柔比星膀胱灌注引起慢性心脏毒性。
蒽环类药物导致的心脏毒性按照出现的时间可分成急性、慢性和迟发性心脏毒性,其对心脏的器质性损害从第1次应用时就有可能出现[10],呈进行性加重,且不可逆[11],而慢性和迟发性心脏毒性与其积剂量呈正相关[12-13]。以多柔比星为例,即使累积剂量仅为50 mg·(m2)-1时也能观察到左心室收缩和舒张功能障碍[14]。此外,有研究显示在给予蒽环类药物的数年后仍可导致左心室组织和功能亚临床心脏超声变化。LOTRIONTE等[15]对18项涉及22815例使用蒽环类药物的临床研究进行Meta分析后发现,经过中位数长达9年的随访其亚临床心脏毒性发生率为18%,临床心脏毒性发生率为6%。
根据美国纽约心脏协会(NYHA)关于心脏不良事件评定标准(CTC AE4.0)[16]可将心包积液分为5级:1无症状,ECG或体检(摩擦音)时发现心包炎;2有症状性心包炎(如胸痛);3心包炎伴生理改变(如心包缩窄);4危及生命的后果,需要介入紧急治疗;5死亡。张雁等[7]报道了1例乳腺癌患者予以表柔比星75 mg·(m2)-1联合环磷酰胺600 mg·(m2)-1,21 d为1个周期的化疗方案,2个周期后患者出现胸闷、不能平卧,心脏超声提示心包积液,左室射血分数0.50,诊断为表柔比星引起的急性心脏毒性。BRICE等[8]对40例接受3个疗程ABVD化疗(多柔比星累积剂量150 mg·(m2)-1,博来霉素累积剂量60 mg·(m2)-1,长春地辛累积剂量12 mg·(m2)-1,达卡巴嗪累积剂量1500 mg·(m2)-1和纵隔放疗40 Gy后的霍奇金病患者进行为期6个月至3年的随访后发现,所有患者的左心室射血分数为50%~77%,但有8例出现了轻微心包积液。FASANO等[9]则入组了12例乳腺癌患者,每月予以多柔比星脂质体[30 mg·(m2)-1]和多西他赛[30 mg·(m2)-1]进行循环化疗直至病情进展或产生毒性,结果有1例患者出现了3级心包积液。经查阅MEDLINE数据库虽未见蒽环类药物膀胱灌注致心包积液的相关报道,但有研究显示膀胱灌注后化疗药物进入血液循环的量与膀胱基底膜的厚度和完整性呈反比[17]。TSUSHIMA等[18]以5例行经尿道膀胱肿瘤切除术的患者为研究对象,术后予表柔比星50 mg/100 mL膀胱灌注1h,分别在给药后30,60,120和240 min检测血药浓度,结果显示血药浓度最高的1例患者在给药后30和60 min时均为9 ng·mL-1。TAKAO等[19]则以21例行经尿道膀胱肿瘤切除术的患者为研究对象,术后予吡柔比星20 mg/40 mL膀胱灌注2 h,分别在30 min和2 h检测血药浓度,结果显示血药浓度最高的1例患者为23 ng·mL-1。说明经尿道膀胱肿瘤切除术后予蒽环类药物膀胱灌注可以进入血液循环,且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此外,蒽环类药物代谢相关基因的差异性也可能导致其易感性不同[20]。因此,正如《蒽环类药物心脏毒性防治指南(2013年版)》[21]所述,蒽环类药物没有绝对的“安全剂量”。
本例患者提示,虽然蒽环类药物膀胱灌注常见的不良反应多为短期内膀胱局部毒性反应,如血尿、排尿困难和膀胱痉挛等局部刺激症状,而其心脏毒性较为罕见,但在临床应用过程中仍应加强对患者的长期观察和随访,避免进展为严重不良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