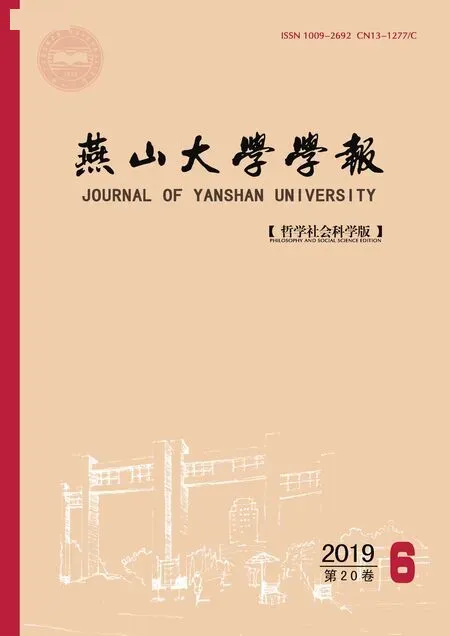跨学科之镜鉴:美国汉学视阈中国古典小说宗教议题的主要维度
何 敏,王玉莹
(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610054)
一、引言
在北美汉学界对中国古典小说研究领域,文学与宗教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现代汉语中的“宗教”来自日语转译英文的“Religion”。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之前,汉语中没有词语可以对应西方话语里的“Religion”。最早的传教士受基督教影响,认为中国本土的宗教实践是“迷信”。[1]一直到20世纪,仍有汉学家认为中国“缺乏宗教启发性”[2]。西方人士在面对中国宗教时,往往面临如下困惑: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都具有其明确的特征、范畴、内容、指向。而中国的宗教与传统文化密不可分,其宗教实践与源自西方的“religion”一词所涵盖的意义指向甚为相异,有其独树一帜的独立性,这也是早期传教士和汉学家无法正确认识中国宗教的原因。
可喜的是,今天的汉学家逐渐认识到这种基于中国文化的宗教独特性。劳格文(John Lagerwey)指出:“中国宗教是一个象征系统,它跳出阶级社会的共同象征体系,包括儒教、佛教、道教、连同各种巫教的神职人员及看风水、看相、算命等占卜活动……中国的宗教研究必须首先考虑中国人的宗教经验,要用中国人自己对宗教的理解和实践来理解中国宗教。”[3]劳格文的论述里有对中国宗教独特存在的理解与尊重,这是与西方“Religion”概念有所相异的表达。
中国古典小说与宗教渊源很深,从小说的源起开始,小说便与宗教结下了渊源。作为通俗性很强的样式,小说中总是会出现各种宗教现象。余国藩写道:“现代多数文史学家眼中的‘小说’一词,可溯至汉末与六朝其时在上与在下,汲汲关怀广义上可称之‘超自然’的问题,举凡‘不朽’、‘来生’、赏罚与因果关系,以及道术、巫法、炼丹等都是他们关注的事物。”[4]359从“因果报应”,到“炼丹术”“巫法”,古典小说中的宗教描写呈现混杂化、通俗化,这种通俗性让它对大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谨从劳格文对中国宗教的界定出发,从古典小说的起源、素材及小说中体现的宗教内容三方面,来探讨美国汉学界对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宗教叙事研究。
二、宗教与小说起源
美国汉学界对中国小说起源有诸多理论假设,其中主要的一种,即杜志豪(Kenneth DeWoskin)的“六朝志怪起源说”和梅维恒(Victor Mair)的“变文起源说”。
1976年,密西根大学汉学家杜志豪发表的《六朝志怪与小说的诞生》,成为汉学界探索小说溯源的重要作品。杜志豪认为:三国、西晋的志怪作品中,已经能看到佛教影响。到了东晋,志怪作品中记述佛法、僧徒的故事明显增多。六朝末端,史传与志怪开始分流,叙事文本呈现出新的特征。六朝志怪有强烈的宗教特征,这缘于志怪与宗教的诸多联系。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基本完备。很多志怪小说都打上了很深的道教烙印。《神仙传》《抱朴子》《搜神记》中,为了宣传神道,写作者常用故事做载体,讲究故事的完整,人物的丰满,他们刻意渲染气氛,突出人物,使读者受到强烈的文学感染。面对虚幻的神仙鬼道,写作者在时空上进行了富有想象力的虚构创造,他们常采用第三人称限制视角叙事,力图要使读者相信虚幻的故事为真实。因此他们列举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籍贯,着力描写当事人所见所感的主观感受,进入观察主体的内心世界,为读者再现故事情景。这是一种包含虚构的文学想象。虽然志怪中的鬼神神仙常常来自上古神话中的原型,其中也多有神仙鬼怪、巫术方士,成为“古今语怪之祖”。魏晋南北朝的“志怪”之作,成为中国小说史的开端。因此,杜志豪的结论是:“很难想象,没有在《搜神记》中呈现出来的虚构想象,会有唐传奇的产生。同样,没有《诗经》,或者《汉书》的描写,会有《搜神记》。”[5]
杜志豪的“六朝志怪”起源说里探讨了道教对小说起源的影响。“变文起源说”则探讨了佛教与小说起源的关联。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梅维恒教授认为:源于印度佛教影响的变文,对中国白话小说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变文产生前后,中国的叙事文学有着本质差异。正因为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影响到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方方面面,也最终导致中国叙事文学里有真正的“虚构性创造”[6]因素的产生。
小说的本义是“虚构”。在变文出现之前,中国没有实际意义的虚构文本。中国在唐代之前的文本里呈现出来的是对真实的模仿,在佛教进入中国之前,文本中的幻想因素对中国读者而言是完全陌生的。唐代的佛教让务实的中国人有了“虚”的概念,也因此才有了“虚构”的理念与创作激情[7]5。敦煌变文出现之后的中国叙事文本与早期叙事的明显差异正在于变文的想象呈现出来的虚构性。一种文学类型不会无缘无故发生如此明显巨大的变化,从印度到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南亚国家传来的变文成为解释这种突然变化的谜底。而中国早期叙事传统为何与印度和西方的传统如此不同呢?梅维恒认为:“闪语与印度的宇宙观里,世界由独立于存在之外的事物构成,闪族文化认为创造者拥有从无到有的创造能力(无—创造者—全部事物)……中国的本体观则截然不同,中国认为世界切实存在,决定事物顺序(无—程序—一切)。”[7]6
唐代的佛教传入中国后,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中国人对虚构世界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印度的“空”的观念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虚构过程,中国的叙事观念因此产生巨大转向,变文开创了新的叙事潮流,从佛教真正切实融入中国社会的唐代开始,叙事开始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最终汇聚成后世小说发展的洪流。中国具有虚构意义的小说正是受了印度韵散结合以表达佛教或历史故事的形式的启发而形成。佛教的演绎先间接讲经,而后演绎佛教故事,这与后来白话小说的形式非常相似。变文抄录者在抄写的过程中按照自己的想象对原作进行增补,在“一说一抄”的过程中,叙事内容不断扩展,情节愈加丰富,这种模仿与想象对白话小说创作也形成影响。到了明清之后,文人开始有意无意地模仿口头文学,创作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本,最终形成明清时期的繁荣景象。
梅维恒的论述为中国小说起源添加了一种新的注解。虽然对梅氏的看法可能会有不同意见,但“不管我们是否同意梅氏之论小说起源,相信没有人会反对佛教曾为虚构文学提供素材,引进过新的文学与语言形式”[7]6。佛教传入中国,不仅意味着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宗教,也意味着一种文化的引进,其影响力之强,遍及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每一个侧面。
三、宗教内容:小说创作的素材
中国小说有记实的传统,古典小说因此或多或少和宗教产生了关联。如作品中出现的大量题材都来自宗教。一些宗教观念如“业报”“人生如梦”等,结合佛祖、高僧、奇人的事迹,为中国小说提供了很多素材来源。宗教成为社会环境描写的组成部分,或成为安排情节的一种手段。
1.宗教成为小说题材
美国汉学家注意到宗教题材在文学作品中的普遍性。冉云华(Jan Yun-hua)在《佛教文学》中指出:“中国古典小说与佛教渊源甚深,小说史几乎从开篇起,便与佛教相关。佛教对中国古典小说而言,其首要影响便是为小说创作提供了素材,激发了小说作者的想象力,并影响了作者的人生态度和宇宙观,再折射到作品之中。”[8]
佛教作为小说的素材,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西游记》。《西游记》的来源是《大唐三藏取经史话》,是一出说经话本,共三卷十七段。《大唐三藏取经史话》来源于一桩历史史实:唐僧取经。唐太宗年间,年仅25岁的青年和尚玄奘和一名弟子只身前往天竺游学,这在佛教史上是一桩奇迹。根据玄奘的事迹改编的文本,成就了中国古典小说史上最伟大的神魔小说《西游记》。汉学家浦安迪(Andrew Plaks)对此评论:“小说《西游记》是一组不断扩充的一套故事之最终阶段……小说与它原始素材的关系,只有当这些素材被铸入新的文体模型后使故事发生了根本性的结构变化,并被赋予新的意义。”[9]175
在中国小说的演进过程中,从变文而来的韵散结合的文体,衍生出了诸宫调、宝卷、弹词等说唱文学,并表现于话本中,成为章回小说来源的重要素材。以宝卷为例,宝卷是宋末起出现的一种俗文学艺术,和变文关系密切,作者大都是僧侣尼姑,内容有佛经故事、劝事文、神道故事和民间故事,内容大多宣扬佛教教义,即因果报应、修道度世的生活,宗教色彩非常浓厚。韩南指出:“《金瓶梅》中有几处引用宝卷来源,分别来自《五祖黄梅宝卷》《黄氏女宝卷》《金刚科仪》《五戒禅师宝卷》等,内容以因果报应、得道修行为主[10]106。”
2.小说中的佛教思想
西方汉学界关注佛教思想在古典小说中的反映,小说作为中国社会儒家传统中的非主流文学模式,对佛教思想有着精确的表达。佛教往往关系着小说的主题及整个故事的结构和框架。古典小说中,如果深入地辨析,会发现不同程度地存在佛教思想成份。如因果报应、地狱轮回等。汉学家在解读古典小说时,往往对此做出敏感回应。
明清时期,佛教净土宗倡导业报轮回,因果报应、无常苦空等宗教思想成为小说中的美学特征。韩南(Patrick Hanan)指出:“到了《金瓶梅》成文时期,运用佛教说教已经成为小说文体美学轮廓中常见的格局,甚至在根本套不上这种教义内容的作品里也用来作为一种固定的结构格式。”[10]114夏志清(C.T.Hsia)也认为:因果观借助报应、转世的描写,给作品以故事框架。部分小说里,这已成为一种模式,如《红楼梦》中绛珠仙草的还泪即是一例。何谷理(Robert Hegel)注意到明朝人对小说认识常常攀附经史子集,强调其“扶持纲常”“天道轮回”“因果报应”的社会效果。《隋唐演义》《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西游补》这样的小说是“作家们用以表达他们严肃的艺术实验追求和精神表达的文学形式,很多作家得用小说来提出或解答他们对涉及到人类生存意义的疑问。”[11]317世纪时,中国佛教已充分世俗化,渗透于生活与观念的方方面面,白话作品中显示出明显的佛道影响的痕迹。在世情类巨著《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中,全书都多少依据佛理为基本框架,小说中有僧尼出现,佛教成为社会环境描写的一部分。即使是李渔的性喜剧《肉蒲团》中,也是作者在依据佛理“传达一个道德信息”[11]171。
明清时期的“文人小说”处处皆体现出“空”和“因果报应”的宗教教义。小说中,谈佛说空常常体现为具体情节中体现出的“空”,将“空”设定为小说中的人物、情节、主旨。浦安迪认为,将“佛学说教”或明或暗地表现,已成为小说的固定格式。佛教中,“五蕴”由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五种因素构成,本质为空,世间万物都是假象。“色”与“空”是理解《金瓶梅》的核心关键,“财色皆空”体现了《金瓶梅》全书的立意。小说中,西门庆的贪财好色促使他不择手段地积累,大肆挥霍,最终因为性欲和物欲的极度膨胀而毁灭。这正是作者对世事无常和万事皆空的表达。同时,因果报应的概念贯穿着《金瓶梅》的全部情节。“佛学上的因果报应概念在各回中是这样表述的:第10回‘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第29回‘冤有头债有主’;第59回也有类似的句子。”[9]162小说中的“物归各主”“看官听说”都突出地指明那些正在进行的事情会得到什么样的后果,这在小说中第19、30、31、62、82、87 回都有明确的体现。 因此,浦安迪明确得出结论:《金瓶梅》全书就是一个在复杂的人际关系框架下的佛学因果报应框架。小说中所有相关人物的言行举止都是僧侣们眼中的“空”。“色”即是“空”,“在这部可说是整个中国文学中描写世情最精辟入微的杰作里,它那反复告诫人们要从声色的虚幻中觉悟过来去领悟一切皆空的说教,听起来让人心灰意冷。”[9]113《西游记》中,作者也在谈“色”与“空”。小说中,人物历经磨难,最终到达圣地。从出发到回归,唐僧师徒不过回到了原点。《西游记》是一部对“空”的超越文本,“悟空”的名字中,作者在探讨“空”存在的意义。“色”和“空”都是虚无,成道之路是指返归自我,而不是成佛之后消灭自身[9]235。
佛教的结构模式多衍生于佛教的报应理论,这在多部古典小说中得到体现。如余国藩认为,在《红楼梦》中,作者将人生如梦的观念放在一个强大而复杂的小说体系中,构成了一个复杂多变的复调叙事世界[12]。故事中发生的一切都是前世注定,故事中的人物是身在宿缘而转世投胎,人物之间关系前世注定,结局也早就注定。这样的叙述,可以加强故事的完整感,适合明清时期民众的审美心理。
3.小说中的道教表现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以“道”为最高信仰。道教与小说有天然的亲缘关系。志怪体、传奇体、话本体、章回体,都与道教有密切联系。道教强调自然无为、以柔克刚,强调“有生于无”,强调对虚的重视,这对文人的品格塑造产生重大影响。
汉学家对道教在小说中的表现有很多论述。牟复礼(Frederic W.Mote)在《中国思想之渊源》(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a)中认为,《易经》是中国思想的最早原型之一。浦安迪也在其著作中大量引用《易经》和道家美学论证其观点。如在《红楼梦的原型与寓意》中,浦安迪论证《红楼梦》中的“大观”意义是“封闭空间中的广阔视野”[13],这符合《易经》《庄子》中出现的“大观”的含义。《红楼梦》中包含了中国博大精深的哲学和宗教思想,如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大乘佛教等思想。
阴阳五行学说缘自《周易》,对后来古代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汉学界里对社会性别研究的焦点之一正是女性与男性的阴阳互补的性别关系结构。南加州历史学教授费侠莉(Charlotte Furth)认为,中国传统中黄帝的身体从根本上就是雌雄同体的,“阴阳调和”正是雌雄同体的一种表述。夏志清认为,古典小说中女性书写与中国传统中的阴阳有关。柏蒂娜·耐普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无论儒家、佛家,对女性的轻视都显而易见。只有道家的阴阳平衡论对女性有所尊重。因此,她力图探讨中国的绝对父权体系对女性书写的影响。艾梅兰指出,中国人的道德秩序是以阴阳为基础的。在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矩阵中,阳属于统治者,家长、长者、男性;阴属于被统治对象,包括孩子、幼者、女性。阳凌驾于次等的阴之上,只有将阳高于阴的秩序固定下来,社会才能稳定,否则过剩的阴会有力地颠覆阳的秩序,引发天灾人祸。
《镜花缘》是一部与道教颇有渊源的明清小说。林语堂的二女儿林太乙是《镜花缘》的英译者,她在译本中专门添加“世俗道教注”(A Note on Popular Taoism),详细给西方读者介绍《镜花缘》中的道家思想,因为“李汝珍借用世俗道教的特征表明他自己对人生的看法”[14],林译本受到广泛欢迎,这与译者对道教的详尽注释,以帮助欧美读者理解中国宗教有关。高张信生(Hsin-Sheng C.Kao)在其作家专论《李汝珍》(Li Ju-Chen)中,讨论了小说中呈现出来的道家谪仙回归模式。虽然《镜花缘》的故事情节纷繁复杂,但纵观全书,至少可以理清一主一次两大故事线索,从小说主要线索看,百花仙子及群花被贬谪入世开端,而副线则是唐敖等勤王党与武则天的斗争,这条副线依然运用了同样的模式,所有人物都非肉体凡胎,而是天上星宿下凡,来体验人世的。所以,故事结构无论是主副线都遵循了思凡——人间——天上的故事过程,完成降凡——历劫红尘——悟道回归的叙事任务。
道教中有一类人物叫方士,黄宗智(Timothy Wong)认为:如果从中国方士传统出发,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刘鹗的生活与小说。刘鹗像传统方士一样多才多艺,他治理黄河、经商、懂占卜、中医,老残也治理黄河、行医、占卜、懂音乐地理以及国外科技。作为一名旅行者,老残不属于他走过的地方,亦不属于他参与活动的任何集体。老残与官方有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这正好符合杜志豪对方士的定义,方士“取悦于宫廷,亦闻名于普通人。他们从官方得到保护,官方也需要他们,因为有权势的人从有很好声名的方士那里得到有益建议,这也是他们了解民意的一个好办法”[15]。《老残游记》里老残因为他的非官方身份了解了人间疾苦,然后把这些反映到他信任的官员处解决问题。老残的角色正是刘鹗的角色,一个20世纪的道士。
“混沌”是道教中一个常见意象。它与西方神话源头的卡俄斯(Chaos)在界定上有相似之处,汉学家对此概念很感兴趣。中国的“混沌”一词来自《庄子》,代表着一种天然的“没有秩序”,这是一种阴阳交融的和谐状态,“混沌”与大观园里少女天真浪漫的气质相契合,是大观园的一个特点[16]。周祖彦认为,《红楼梦》中反复出现的“混沌”,反映了作者的道教思想,曹雪芹在经历了生活上的诸多失意之后,转向道教寻求安慰。很自然地,他会将“混沌”的概念和形象反映在他的作品之中[17]。
四、宗教混杂及其文本呈现
作为通俗性很强的文学样式,古典小说中总是会出现各种宗教人物,无论是佛、菩萨、道士,还是和尚、女仙,都充满了市井气息。汉学家和国内学者一样,注意到中国文学中宗教与儒家倡导的道德理念相结合,表现出佛道合一或三教合一的色彩。“合一”,指儒、释、道的宗教活动存在于同一个故事空间,教理、教义同时出现,互相影响。这是一个宗教世俗化的进程,这种模式在明清的白话长篇里尤其普遍。
1.古典小说中的宗教混杂
中国历史中的佛、释、道教本属于不同的宗教派别,古典小说中却常常出现僧侣、书生与道士同时出现的场景。其中出现得最多的是:佛道混杂或三教合一。汉学家基于国内相关研究的基础,对各种宗教混杂现象亦做出相应诠释。
古典小说宗教混杂书写中,最常出现的是佛道相杂。小说中常出现一僧一道结伴而行的现象。《红楼梦》中的空空道人出现在小说第一回:“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忽从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而在后面又写道:“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转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18]对“空空道人”究竟从何而来,在小说中有何意图,寄寓作者何种愿望,汉学家对此做出多种解读。“空空道人”,意指“空”,首先关于“空空道人”是道士还是和尚,汉学家有不同的看法。从“访道求仙”,可见“空空道人”是道家人物,而后“悟空为情僧”,则“空空道人”是佛家的人物。对“空空道人”的身份,汉学家也各持已见。李前程(Li Qiancheng)认为“空空道人”是僧人,而浦安迪在《离开花园:关于中国文学名著的思考》(Leaving the Garden:Reflections on China’s Literary Masterwork)中则认为,空空道人是一个道士。马克·费拉拉(Mark Ferrara)也认为空空道人是和尚,是“从佛教禅宗角度解读曹雪芹人‘隐意’的最佳方法”[19]。对“空空道人”到底属于佛,还是道,汉学家和国内学者一样,各执一辞,尚无定论。对“空空道人”的不同看法,正是小说书写中将佛道混杂的例子。
虽然同为佛道混杂,但小说作者对佛道的态度仍然有所区别。何谷理认为:《西游记》《西游补》明显是扬佛抑道的,而《封神演义》《绿野仙踪》则扬道抑佛。《隋唐演义》中的“王敖老祖”“梨山老母”都是道教的神仙。在《西游记》中,镇压孙悟空时,如来与玉皇大帝同时出马,镇压造反的猴子。西天取经途中,在镇压妖魔鬼怪时,菩萨和道士也常常出现在同一画面之中,体现出佛道的融和,这与中国历史上佛道二教在根本教义上有部分相似性有关。佛教与道教都要求修行者摒弃个人欲望,远离与尘世的关联,清心寡欲,达到超脱之境[11]210。马倩(Qian Ma)在分析《镜花缘》时认为,《镜花缘》中是抑佛扬道。小说展开的逻辑是:在道教的谪凡框架中夹杂着因果报应模式,这一模式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屡屡出现。
三教合一的论述中,首推浦安迪在《明代四大奇书》中对《西游记》的论述。浦安迪认为,《西游记》书中出现了很多宗教术语和宗教意象,不属于佛、释、道中任何单独派别,“与其说是一种人为的折衷主义运动,不如说更像是整体的结合”[9]210,这首先体现在“心”的存在。“心猿”是全书一个重要意象,无论是佛教、道教、亦或儒教,都从不同角度关注“心”,《西游记》正是一部关于“心”的旅行。从外部看,它是一部朝圣之旅,同时,它亦是一出内心求道的寓言。朝圣之路上的妖魔鬼怪正是心中的挂碍。如“三打白骨精”故事中,白骨精三次化为人形,唐僧即为其所迷惑,这正是一种“昧心”。可以发现,朝圣之旅的终级目的并非遥远的佛门圣地,而是一场内心的修行,《西游记》就是一场以“心”统三教,三教共同对内心的自我关照。
而“心”与“道”的关系究竟如何呢?作者吴承恩与译者余国藩皆认为“心”与“道”可互证。前者将《西游记》第一回回目标题取名为“灵根育孕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即作者认为“道”之所生在于“心”之所养;后者认为《西游记》是一部将虚构的情节与宗教意义结合紧密的作品。“这种宗教意义,乃由小说中直指儒释道三教的经典所形成的各种典故与象征组成。三教并陈,又大量取其所需教义。这正是《西游记》能够屹立中国小说史的原因。”[4]367
2.僧道度脱悟道框架
佛道二教因其对外物和功名的淡泊,形成超脱的处世态度,形成各自的悟道传统,因此有了很多度脱的小说文本。多尔·利维(Dore J.Levy)认为,佛家思想是小说的哲学框架,但小说的主旨是对智慧的思考。李惠仪(Li Wai-yee)质疑贾宝玉是否真的悟道,“以情悟道”是警幻仙姑的使命,“迷幻”是指被相入一个迷狂的充满幻念的世界,“警幻”意味着主体对虚幻的意识。[20]玛丽·司各特(Mary Scott)认为,《红楼梦》和《金瓶梅》两部作品以复杂的对称结构,展现了两个家庭在不当的行为之后走向毁灭,或悟道。小说中,无论是花园、主要人物形象,都带有佛教意义的“财”“色”特点,对贾宝玉和西门庆而言,故事中的主线都是修炼的过程。可以说,大乘佛教行善济世的入世精神,正是作者选择度脱的根本原因。不同的是,贾宝玉悟道出家,而西门庆“色即是空”,最终归向虚无。小说从哲学角度而言,都是“道”的诠释,是对整个中国文化历史的概括,而贾宝玉和西门庆都不能从历史的宏观角度,理解生活的本质。
李前程的《启悟小说:〈西游记〉、〈西游补〉和〈红楼梦〉》是一部从宗教角度解读古典小说的论著,该书可以看作是汉学界第一部专门论述佛教思想对中国章回小说影响的专著,自出版伊始,在汉学界既有较大影响。李前程认为:中国章回小说将佛教启悟观念融入了小说的叙事框架,在《红楼梦》中,宝玉的性格是“痴”,“痴”为佛教所说的“三毒”之一,佛教式的解脱必然要求宝玉戒绝“痴”心,进入度脱框架。“佛教大乘派宣扬的寻求解脱的思想传统和赎罪方式对《红楼梦》的情节、结构、表达方式、内部矛盾与冲突的化解以及小说结局宝玉出家的情节安排都有重要影响。”[21]153《红楼梦》在第一回就明确指出:要神瑛侍者与绛珠仙子下凡度脱凡人,这显示了它对度脱文学的熟悉与继承。《红楼梦》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宗教性质文本。
“宝玉唯一的解脱是摆脱情欲的吸引。他的痴情是牵绊,他一直希望与之相伴的女人是他的魔障。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些女性于宝玉而言,正是《西游记》与《西游补》中的妖魔。”[21]130
贾宝玉的悟道与《西游记》中的悟道不同,《西游记》的度脱框架是:舍离—启悟—回归,小说人物要历经一番启悟历程,回归佛界。《红楼梦》则关注世俗中的种种欲望,否定世事人情。李前程多次引用脂砚斋的评语来指出《红楼梦》中的佛教思想,“以情悟道”体现了这部小说的特色。贾宝玉深情、用情,到了情之极致,但最终抛下凡情,转情为悟,去寻找“道”的天地。而“悟”的途径是通过度脱者。在《红楼梦》中,警幻仙姑和空空道人都是度脱者的形象,得道的僧道为了启悟被度脱者,往往要引导他们认清世界的本来面目,度脱的方式常常是入梦。《红楼梦》中的柳湘莲在尤三姐自刎后,梦见她来告别,而后出家。贾宝玉神游真如福地,领悟自己与林黛玉的前世关系,得到度脱。在《西游补》中,董说发挥其想象力,整部小说建构于孙行者的梦境,在“青青世界”“古人世界”“未来世界”中经历种种魔难,最终被虚空主人唤醒,走出梦境。“梦境”承载着董说多层次、多维度的创作目的。
《西游补》在佛教方面的度脱观也引起不少汉学家的关注。何谷理认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非肉体凡胎,不识情欲为何物。而《西游补》的作者为孙悟空补上“出情”的一课,让他遇到鲭鱼精,以“先走入情内”,再“破情而出”,最终悟道。“鲭鱼”是“情欲”的谐音,被当做“妄心”的代表。《西游补》中,处处可以看到“情”的暗示。《西游补》正是通过佛家人生如梦的思想,以完成孙行者的度脱之旅。白保罗关注《西游补》里悟空“悟道”的过程。英雄要认清“来路”或“本来面目”,启悟的方法是进入梦境。小说中,孙行者穿梭于古今,各种富贵如浮云。小说最终的指向是出世修道的传统,核心在于对人生真谛的终极意义追问。葛锐(Ronald Gray)指出,西方红学对小说中佛教思想的关注使大家忽视了道教的体现:“宝玉的思想发展和他回归石头本原的结局,可以视为是道家启悟历程的寓言。”[22]这对于绝大多数倾向于从佛教解脱角度解读贾宝玉的结局,显得与众不同。
五、结语
美国汉学界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宗教叙事研究成果多样,从报刊上的只言片语,到期刊、博士论文,乃至专门著述,大大丰富了汉学界的古典小说研究。研究呈现出斑驳陆离的纷繁色彩,赋予了古典文本更广阔的意义空间。总地说来,汉学界的宗教叙事有如下特点:
其一,善于借用中国学者成果。汉学家一贯重视来自中国的研究资料。如浦安迪的研究体现出以中国传统小说评点为依据,再深入探讨古典小说的叙事方式,发现它与西方叙事文学的异同。
其二,中西比较宗教的角度。汉学家的古典小说宗教叙事研究或多或少使用了中西比较宗教的方法论,丰富了比较宗教学的内容,并进一步拓展了古典小说研究的范畴与影响,使之在世界上开始更为广泛的跨文化对话与交流。
其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美国汉学界对古典小说宗教叙事的研究体现出明显的跨学科特征。研究者站在跨文化的视野中,通过对来自不同背景知识范式的清理,运用来自文学与宗教学之间的概念、范畴、话语、规则来互相阐释,建立起跨学科的话语诠释模式。这成为汉学界古典文学研究的一大特征。
古典小说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我们赞赏汉学家们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与理解,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但让世界认识中国,也从另一个认知角度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身。在全球化浪潮已经席卷全球每一个角落的今天,立足于中国文学和文化本位,美国汉学家的中国古典小说宗教叙事研究对于拓展中国文学的海外意义空间,对于中学西传和“输出东方”,对于推动中西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