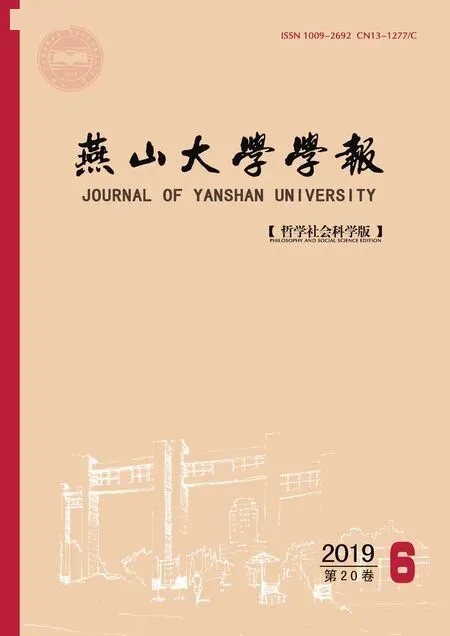刘若愚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观
李 洁
(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110819)
一、引言
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是美国汉学界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这些华裔学者,具有良好的中西文化背景和学术素养,视野开阔,视角多元。他们在西方语境下,对中西文学和诗学展开比较与研究,探索中西文学和诗学的相互阐发和交汇途径,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这个学术族群中,最为显赫且最早具有国际影响的首席学者就是刘若愚”。[1]67刘若愚(James J.Y.Liu,1926—1986)是美国华裔学者,在中国文学研究和中西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成果卓著。他的八部英文专著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学和诗学,并进行现代意义的阐释,寻找中西诗学的契合点,致力于探索和建构具有普适性的世界诗学体系。
作为中西文学和诗学的研究者和批评家,刘若愚在中国的文学和诗学研究领域,广受关注。国内对刘若愚的研究,多集中在比较文学领域,集中在对其文学研究和诗论体系的探讨上。与此相比,对刘若愚的翻译成果和翻译思想的关注与研究,是不足的:一是因为他的身份主要是文学和诗学的研究者,而不是翻译家,他翻译中国古典诗歌,是为讲授、介绍和阐释中国文学和诗学服务的;二是因为刘若愚本人对自己的翻译思想很少做系统的理论阐释;三是因为他主要翻译了一些唐诗宋词,译文的数量和影响比较有限。
本文以刘若愚的The Poetry of Li Shang-yin:Ninth-Century Baroque Chinese Poet(《李商隐的诗》)[2]一书为例,探讨刘若愚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观。目的在于,丰富国内相关翻译研究,思考以刘若愚为代表的西方华裔译者与中国本土译者、西方(欧美裔)译者的不同翻译理路,及其背后折射出的文化情怀、思维方式和诗学传统,探索中国诗歌走向世界的多元途径。
二、译者身份观
译者身份观是译者对自己的职业身份和文化身份的认识和定位。
第一,刘若愚指出,在西方,从事中国诗歌英译的主要有两类人:“诗人—译者”(the poet as translator)和“批评者—译者”(the critic as translator)。这两类译者的翻译目的不同,目标读者不同,翻译方法不同。“诗人—译者”首先是诗人,比如庞德(Ezra Pound,1885—1972)、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1874—1925)等,翻译的目的是用英语再创作出一首好诗,让译文读者在阅读中获得精神愉悦和审美感动,体会诗歌的魅力。“批评者—译者”首先是批评家,比如刘若愚自己,翻译服务于自己的文学研究和批评,目的是让译文读者了解中国诗歌的特点或其它相关知识。[3]以李商隐的《乐游原》为例,比较刘若愚和许渊冲译文如下:
【例1】原文(李商隐《乐游原》):
向晚意不适,
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刘若愚译文[2]160:(Lo-yu Heights)
Toward evening I feel disconsolate;
So I drive my carriage up the ancient height.
The setting sun has infinite beauty—
Only,the time is approaching nightfall!
许渊冲译文[4]:(On the Plain of Royal Tombs)
At dusk my heart is filled with gloom;
I drive my cab to ancient tomb.
The setting sun appears sublime,
But O, ’tis near its dying time.
由例1不难看出,许渊冲的译文“用‘双声’、‘押韵’、‘抑扬’的方法来传达原诗的‘音美’;用英诗格律来传达原诗的‘形美’”[5],更具艺术性和文学创造性。而刘若愚的译文紧贴原文,亦步亦趋,尽量保留了原文的用词和句序,不做创造性的发挥。这是因为,刘若愚对自己的身份定位是“批评者—译者”,他的译文是供研究者或批评者“参阅的文献”[6],关注的是知识,是信息,是为中国诗歌的介绍、阐释和批评提供素材和例证,而不是诗歌的审美愉悦问题。
第二,刘若愚是具有双重文化背景的“离散译者”。“对于华裔汉学家而言,中国文化是其灵魂之根,而西方文化则是安身立命之本”。[7]他们“既是西方文化的认同者,也是中国文化的捍卫者”[7]263。这种“双重性”文化身份,体现在刘若愚的古典诗歌英译上:一方面他要“求同”,翻译时要照顾英语读者的接受能力,使中国诗歌顺利进入西方读者的视野;另一方面更要“存异”,不希望译文过度“归化”,不希望中国诗歌在英文书写中变形走样,希望保留原诗中的文化和审美信息。比如,在《李商隐的诗》一书中的“翻译问题”一章,刘若愚对诗歌中文化意象的处理,提出了具体的想法:首先,他建议保留原诗中的文化意象,比如,“柳”译为willow,“杜鹃”译为cuckoo;当英语中相应的词汇缺省时,可以用音译的方法,“梧桐”译为wut’ung,“嫦娥”,译为 Ch’ang-o,而不是 goddess of the moon。[2]34-47他认为,每一个文化意象的背后,都有它的文化渊源和内涵(“柳”谐音“留”,有挽留、思念之意;“杜鹃”象征凄凉、哀伤;“梧桐”象征相思之苦、闺怨之愁),是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资源。
【例2】原文(李商隐《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
偷桃窃药事难兼,
十二城中锁彩蟾。
应共三英同夜赏,
玉楼仍是水精帘。
刘若愚译文[2]105:(Again to the Sung Sisters of Hua-yang Temple,on a Moonlit Night)
Stealing the peaches and pilfering the elixir cannot both be done.
Inside the twelve city walls the bright-colored toad is locked up.
One should enjoy it together with the Three Blooms,
But the jade tower is still behind the crystal curtain.
译诗语言符合英语语法和表达习惯,这是一种妥协和让步,是译文顺利进入英语读者视野的前提。东方朔三次在王母处“偷桃”、后羿“窃药”、仙人的华美居处“十二城”、月中“彩蟾”、“三英”(宋华阳三姐妹)、“水精帘”等典故或意象,承载着丰富的中国文化内涵和联想意义,刘若愚采用了直译加文外注释的方法。在西方文化语境中,他遥思家乡,希望把这些承载着中国文化信息的词语或典故传递给英语读者,不希望它们失落、变形,或者被误解、误释。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1946—)在编译中国文学选集时,则有不同的考量。以动植物名称的英译为例,宇文所安认为,用英语词汇对应翻译,读者可能难以理解这些动植物名称在中国文化中的关联意义,因此,他选择了美国人熟悉的动植物词汇来翻译,比如,将“梧桐”译为beech(山毛榉),“杜若”译成mint(薄荷),“杜衡”译成 asarum(细辛)。[6]75
综上,“批评者—译者”和“离散译者”的身份,决定了刘若愚的译诗基本思路:语言基本符合英文表达习惯,目的是便于读者理解;形式与原诗亦步亦趋,尽可能地体现原诗的句法特点,目的是引导读者体会到一点原诗的样貌,便于学习、研究和批评;对原诗中的文化元素,采取“异化”的立场,直译保留富含文化内涵的典故、意象等,目的是为中国文学文论批评和研究者提供所需的知识和信息,也为保留母语文化特质做出努力。
三、原文解读观
对原文的解读,是译者翻译活动的起点和基础。探讨刘若愚的原文解读观,目的在于观察和分析华裔汉学家在原文解读方面的特点,理解他们与中国本土译者和欧美裔汉学家的不同。这里探讨刘若愚对原诗形式的解读观、对原诗意义的解读观、对中国诗学的认识和解读观。
在对原诗形式的解读上,毋庸置疑,与中国本土译者一样,刘若愚有足够的能力敏锐察觉和正确认识中国诗歌形式的种种特征,这是中国译者和西方华裔译者的优势。刘若愚从小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语言文字的深厚修养。他曾执教于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多所学校,讲授和研究中国文学、中西比较文学和诗学。他在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中国诗学》)[8]一书中,对汉字的起源,对汉语的语法特征、汉字的声调音节等汉语本质属性,对中国诗歌的结构特征、修辞手法、典故隐喻等,都有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特征在英译中的难点和可译性限度,也有清醒而现实的认识。
在对原文意义的解读上,刘若愚既不像多数中国译者那样,采纳“知人论世”的作者中心解读观,从时代背景和作者生平入手,把作品看作是作者自传或影射之作,固守已有观点;也不像有些西方汉学家那样不拘一格,强调读者的自由解读。作为在中西文化间游走的华裔汉学家,他既受到中国传统解读方式的影响,也受到读者批评理论、阐释学、接受美学、新批评等西方思潮和研究方法的影响。一方面,他不否认时代背景、作者背景、历代注释等信息的辅助作用;另一方面,他拒绝从作家的经历和历史语境入手去解释诗歌。他主张文本细读,重视对文学文本的语言结构和修辞张力的考察和研究,重视以作家的系列作品为依据,来考察和解读意义。例如,对李商隐《锦瑟》一诗的意义的解读,“他否定了前人的悼亡、自伤、寄托诸说,而提出了古今中外都有的‘人生如梦’的新说”[3]序5。也就是说,对意义的解读,刘若愚更加深入、全面。
在对中国传统诗学的认识和解读上,刘若愚更具优势,这是他的学术专长。对句式松散、一词多义、缺少语法逻辑连接成分等汉语意合特征,对言不尽意、意在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诗歌言意关系,对意象并置、创造意境、写意传神等诗歌创作特征,对以物观物、物象自现等道家美学影响下的诗歌鉴赏特征,刘若愚都有具体的研究。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和鉴赏特点的深层次理解,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风貌和精神气质的深刻把握,对中国传统诗学的深彻认识,使他在翻译中更加审慎,对中国诗学和文化在翻译中的保留和传播问题,有更深层次的考量。
【例3】原文:(李商隐《无题》)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刘若愚译文[2]66:(Without Title)
It is hard for us to meet and also hard to part;
The east wind is powerless as all the flowers wither.
The spring silkworm’s thread will only end when death comes;
The candle will not dry its tears until it turns to ashes.
Before the morning mirror,she only grieves that her dark hair may change;
Reciting poems by night,would she not feel the moonlight’s chill?
The P’eng Mountain lies not far away;
O Blue Bird,visit her for me with diligence.
由例3可见,有了对原诗形式的深入理解,刘若愚同叶维廉(Wai-Lim Yip,1937—)等华裔汉学家一样,更希望尽可能地在译文中保留中国诗歌的形式,保留深层次的中国诗学“模子”(叶维廉),这是中国诗歌的独特风貌,是他们想让西方读者了解的东西。他没有像叶维廉那样,改变和打破英诗句法的规范,而是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方式:为了符合英语表达习惯,他会添加一些语法成分,但不做过多发挥,尽可能地保留原诗在句法上的独具匠心之处。他的译诗语言显得亦步亦趋,文采不足,其实这正反映了他对中国诗学深层次的认识:在翻译中国古典诗歌时,如果译者添加过多语法成分,或是进行各种创作发挥、逻辑推断和经验性介入,会框囿读者的视觉和感觉指向,削弱原诗的意象效果,减小读者的多元理解空间,缩小读者自由进入原文和自由联想的空间,“会歪曲原诗的美感印象的层次和姿态”(叶维廉)[9]。
对原诗意义的解读,首先,刘若愚不同意一些学者的传统观点:李商隐想进翰林院,求助令狐绹,令狐绹升官后,为避嫌拒绝见客,致使李商隐处境艰难,相见难,离开又不甘心。刘若愚认为,这就是一首爱情诗,表达诗人对所爱慕女子的思念。他在译诗后,给出了自己的阐释,比如:“难”有两层含义:一是情人爱而不得,相见也难,分别也难;二是分别以后,难以有机会再见面或道别。“东风”和“百花”,既指诗人和诗人爱慕的女子,也是对景物和季节的交代;“丝”有双关意义:既是思想、想起的意思,也是思念、渴望的意思,既是情思,也是愁思;“灰”有两层含义:既指蜡烛燃尽后的粉末,也用灰色烘托阴郁的氛围。“晓镜”“云鬓”“夜吟”“月光”是诗人在描摹女子对青春易逝的慨叹,让人想起“嫦娥应悔偷灵药”(李商隐《嫦娥》),想起“心酸子夜歌”(李商隐《离思》)。[2]66-67这些详尽具体的阐释,反映了刘若愚的文本细读精神,也反映出他在原诗意义的解读方面,基于传统,但不囿于传统,在传统中不断发展和深入。这与宇文所安等一些汉学家是不同的。宇文所安对意义的解读,往往独辟蹊径,敢于提出新的见解。例如,李清照的形象,在宇文所安的理解中,是一个 “面对沉湎于金石书籍中的丈夫,内心出现裂缝、不无闺怨的有血有肉的女性”[10]。我们从宇文所安与林语堂的《金石录》译文的比较中,就可以看出这种意义解读的差异。
四、译本建构观
刘若愚翻译的李商隐的诗、北宋主要词家的词,或者其它一些诗歌译作,总是伴有大量阐释和批评的,也就是说,《李商隐的诗》等,既有译著的性质,也是学术研究专著,从中我们可以分析出刘若愚的理想的译本建构模式。
第一,翻译与研究相辅相成,阐释和批评是译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跨时空、跨语言和跨文化的翻译活动中,刘若愚认识到,译文读者不可能通过译诗,完全了解中国诗歌各个层面的特质。如果说,诗是翻译中丢失的东西,译者对原诗的创作背景、语言特点、典故暗示、意象意境、意义意蕴等的介绍、批评和阐释,正是在译文外做补偿的有效手段。在《李商隐的诗》一书中,第一部分对历史背景、传记信息、李商隐诗歌的研究成果、以及翻译问题,都做了具体介绍;第二部分是100首李商隐诗歌及其译文,在每首诗后,刘若愚对重要典故、诗歌的意义和内涵,做了解释和评论;第三部分是批评性研究,对中国诗歌理论、李商隐诗歌的境界以及语言特点进行了介绍和分析。这些译文外的阐释、批评等是对译文的完善,有助于读者对原诗的认识和理解。
第二,既然没有“尽善尽美”的译文,如何把“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学作品传递出去呢?刘若愚殚精竭虑,提出了理想的多元建构模式:译本由原文、拼音标注、逐字标注、韵律节奏标注、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2]46)、批评阐释等多个部分组成,目的是尽可能地从多个层面贴近原文(如见例4)。
【例4】:原文(李商隐《锦瑟》节选):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刘若愚译文[2]44-47:(The Ornamented Zither节选)
拼音标注:
Chin se wu tuan wu-shih hsuan
Yi hsuan yi chu ssu hua nien
Chuang sheng Hsiao meng mi hu-tieh
Wang Ti ch’un hsin t’o tu-chuan
逐字标注:
Ornamented zither no reason fifty strings
One string one bridge think flower year
Chuang master morning dream confuse butterfly
Wang Emperor spring heart entrust cuckoo
直译:
The ornamented zither,for no reason,has fifty strings,
Each string,each bridge,recalls a youthful year.
Master Chuang was confused by his morning dream of the butterfly;
Emperor Wang’s amorous heart in spring is entrusted to the cuckoo.
刘若愚希望从不同的层面,向读者展示中国诗歌的样貌。拼音标注,可供读者模仿性阅读,了解中国诗歌在语音层面的特点,体会到“hsuan”和“tu-chuan”等词汇的韵律之美;逐字标注,可帮助读者了解原诗的建行特点以及用词和意象,例如:“Ornamented Zither” (锦瑟)、“fifty strings” (五十根弦)、“Chuang master” (庄子)、“butterfly”(蝴蝶)、“Wang Emperor”(望帝)、“cuckoo”(杜鹃)等。对于读者来说,这仅仅是一些词汇的堆砌,但是,附着在词汇上的新鲜有趣的意象,或许可以满足西方读者的阅读创新期待,提供给他们一个自由连接和想象的空间;直译,尽可能贴近原诗的句法特征,同时按照英文的表达习惯做了处理,虽文采不足,却有助读者了解原诗的意义和诗句的大致表达程序。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翻译李商隐的100首诗,还是翻译北宋六位词作家的词,刘若愚都是倾向于这种“直译”。他认为,意译(free translation)后的诗歌虽然有利于读者欣赏,但是不能作为批评和研究原诗的基础,因为意译的诗已经与原诗有了相当大的距离。因此,虽然清楚直译的诗歌“诗性”不足,他依然坚持直译的方法。[2]46
刘若愚提出了这种多元模式,但他在《李商隐的诗》一书中,并没有贯彻做到,或许是因为篇幅有限的原因。在1974年出版的Major Lyricists of the Northern Sung960—1126A.D.(《北宋主要词人》)[11]一书中,他践行了多元模式,在每首词后面,都给出了原文、拼音标注、逐字标注、直译、注释、音调韵律标注,以及批评阐释。不难看出,这种译本模式是他的理想。
五、结语:价值和意义
本文从三个层面探讨了刘若愚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观。作为华裔汉学家,他的翻译理路,不同于许渊冲、汪榕培等中国译者,也有别于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庞德、宇文所安等西方译者,具有自己的特点和价值。
从译者身份上讲,许渊冲、汪榕培等中国译者,多是国内英语语言文学的讲授者、研究者,他们热爱中国诗歌和翻译,是文学翻译家。他们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己任,通过自己的“逆向翻译”,向西方传递中国诗歌之美。西方译者中,有诗人,有外交官,有传教士,有汉学家,有的兼有多重身份。他们立足西方文化语境,从以译介中国诗歌来传播基督教,到通过译介中国诗歌来改变西方社会和文化,到介绍、研究和学习中国诗歌,西方译者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目的和文化考量。刘若愚是诗歌和诗学的研究者,是当代华裔汉学家,具有离散译者的文化身份,他平等对待中西文化,一生都在探索中国诗歌在西方语境中的传播和阐释方式,寻找中西文学和诗学的融通道路。他翻译中国诗歌的文化考量,既具有民族性,也具有国际性。
从原文解读上看,许渊冲、汪榕培等中国译者,受生活环境、教育和学术传统影响,对原文文本的形式和意义的解读,有着相对统一、固定、且不易改变的认识;理雅各、翟里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等早期西方译者,在翻译中国古典诗歌时,重视原文的文献价值,注疏据典,对原诗的解读比较传统;宇文所安等当代西方译者,受西方哲学思潮和研究方法的影响,“不依赖成型固有的观点,对原文的意义和形式做出了自己富有创见的解读,在他的解读中,中国文学经典形象被重新建构”[12]4,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也在译文中焕然一新。也就是说,中国译者深谙中国古典诗歌的诗学传统,对形式和意义的解读,比西方译者有优势,但是不容易有新的观点和突破,而西方译者会给我们的解读带来新鲜视角和观点,但也难免有误读、误释的可能。相比之下,刘若愚这样的西方华裔译者,既有中国传统,又受西方治学方法影响,既尊重传统观点,也努力创新。因此,他对原文的解读,显得更加谨慎、深入,也更加包容、开放。
从译本建构上看,中国译者多数是文学翻译家,他们关注美,关注形式,关注诗性和诗境的传达,他们的译本注重文学价值、审美价值。理雅各、翟理斯等早期西方译者的译本,注重考据,注重意义的完整和准确,他们的译本注重的是经学价值和文献研究价值。庞德、洛威尔等西方译者,摆脱原诗形式桎梏,用英语重新书写,创作出的是适合英语读者欣赏的诗歌新篇,他们的译本丰富了英语诗歌的内容和形式,具有文学创新价值。当代汉学家宇文所安的译本,构建形式差异系统,提出新的意义解读观点,关注人情人性,关注诗歌中传达出的“人”的生命状况和精神世界,体现的是当代西方学者的思维方式和学术传统。不同于这些译者,刘若愚的译诗,是用来辅助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他的译本中,翻译和阐释批评并行,从不同层面展示和介绍原诗,更加关注的是译本的工具性,具有工具价值。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研究注意力转向了译文的生产者—译者。译者的成长和生活环境、文化和历史根基、心理认知和情感个性,都是译者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国古典诗歌翻译为不同时代、不同趣味和秉性、不同理念和追求的中西译者提供了广阔的驰骋空间。他们各有优势和不足,也难以相互替代。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中国译者的逆向翻译,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分享和传播,是文化自信的体现;西方译者的译本服务于不同的时代和目的,有着不同的诉求和风貌;以刘若愚、叶维廉、余宝琳(Pauline Yu,1949—)等为代表的西方华裔译者,在中西文化之间,上下求索,有着自己的诗歌英译思想和路径。“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周易·系辞下》),这些不同的路径最终汇聚在一起,共同为中国诗歌走向世界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