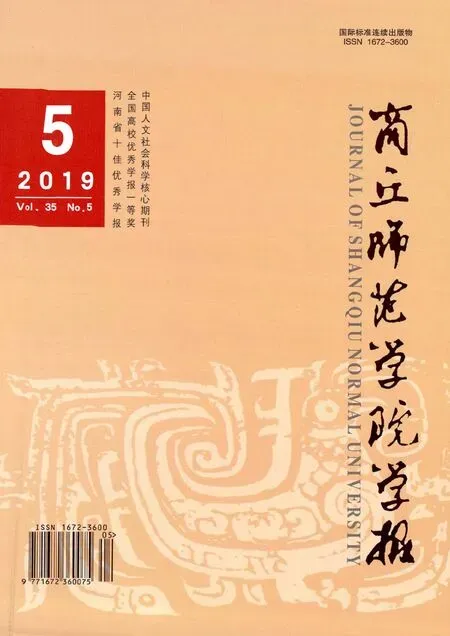清代中叶士人“明道”的困境与出路
高 思 达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根据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内在进路,宋明理学的“天理”观是对先代儒学“天人相应”说的继承和改进,但是由于程朱理学本身潜在自然与规范之间的对立,因此伴随着明清气一元论的推广,人欲逐渐成为自然本身,“天”(天理)的权威性受到挑战并迅速衰落,社会活动本身不再与神魅式的天道观相联系,表现出客观化和理性化的倾向。这一倾向延续至清代中叶,就是重视名物训诂和经典考证的乾嘉学派的兴起。
乾嘉诸子的治学目的,在于以求真的态度,探求“六经”之道,恢复周孔礼教,为当下变动不安的社会状况寻求对治之策,此即戴震所谓“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的“十分之见”[1]185。但是,伴随着乾嘉诸子大规模的考订经书活动,经学的至尊性和真实性发生了冲突。作为社会秩序和政权合法性的依据,经书本身并非简单的事实承载者,其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弥合历史与现实的缝隙并进而指导现实规范的操作。尽管考据学家们信奉尊经明道的宗旨,但是在“实事求是”理念指导下的经学考据活动,已经使得经书至上的地位受到动摇。有见于此,以常州庄存与为代表的学者,出于护卫“道统”的需要,一方面极力回护被判为出自伪《尚书·大禹谟》的“虞廷十六字心法”,另一方面试图调和汉宋矛盾,重新确立儒家的价值系统。至此,清代中叶的“明道”运动出现两种类型,一类是以戴震为代表的“辨伪求道”式的考据进路,另一类是以庄存与为代表的“护伪存道”式的“道统”进路。由是,乾嘉学术出现经与道一分为二的学术困境:在追求“圣人之道”的过程中,应如何处理历史事实与现实价值之间的矛盾?
本文的论述,尝试梳理清代中叶“求真”与“护伪”两派的思想进路,揭露隐藏在思想背后的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紧张与乾嘉的学术困境,进而以龚自珍之“尊心”观为代表,辅之以浙东史学理念,探究弥合经道分裂的可能方式,以期彰显本文的写作目的。
一、“由辞以明道”是否可能?
明清之际,社会鼎革,一批学人反思心学空谈之祸,高扬经学大旗,其中有昆山顾炎武,力倡“经学即理学”,主张回归经学要旨。顾炎武认为,明清之际的理学,实为禅学,“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括帖之文而尤易也”[2]231。黄宗羲亦持相似观点,认为“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游谈”[3]。在顾黄二人看来,明季学子奉语录而弃经书的态度,实乃歪曲儒家性理思想与经世主旨的本意,欺世盗名,“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尚论者以为立功建业,别是法门,而非儒者之所兴也”[4]。因此,清初诸位学人大都重视回归经典,以文意诠释的方式,重组儒家思想资源,以期在异族的统治之下,保留汉文化的话语权并安顿社会秩序,此谓“圣人之经,即圣人之道也”,即文本再诠释的目的在于利用先代经典,探究圣人治世的内在原理和外在方式。这种“以经明道”的学术态度,一方面使得经世之学备受重视,另一方面则掀起了“汉学热”,即推崇汉儒著作,原因在于汉儒距离先秦时代较近,其作品被后世篡改的可能性降低,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此乃臧琳所谓“考究诸经,深有取于汉人之说,以为去故未远也”[5]。这种崇尚汉学的观点,被乾嘉考据诸子所接受,并在学术路径上出现了“汉宋对立”的态势。
乾嘉考据学家们的治学特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对内,旨在通过研究一字一句之原义而通晓经文大道,戴震有一段文字最能说明此种意图:
今人读书,尚未识字,辙薄训诂之学。夫文字之未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未能通,妄谓通其心志,此惑之大者也。论者又谓:有汉儒之经学,有宋儒之经学,一主训诂,一主义理,夫使义理可以舍经而求,将人人凿空得之,奚取于经乎?惟空任胸臆之无当于义理,然后求之古经,而古今悬隔,遗文垂绝,然后求之训诂,训诂明则古经明,古经明而我心同然之义理,乃因之以明。古圣贤之义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昧者乃岐训诂、义理而二之,是训诂非以明义理,而训诂何为?义理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于异端曲说,而不自知矣。[6]86
在戴震看来,古圣先贤讲解的经文义理,都存在于典章制度之中。然而古今悬隔,今人已不知古人之名物度数究竟为何,这就需要今世学者从训诂处入手,理解字句之义,而后才可以通读经典,通读经典之后才能使人性廓然明朗。由此可见,以戴震为核心的乾嘉考据学家们,志在知晓典章义理,恢复圣王之道。段玉裁即认为,“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既通乎性与天道矣,而考核益精,文章益盛,用则施政利民,舍则垂世立教而无弊”[6]122。在乾嘉诸子的认知中,“精考核”与“通天道”实乃一体两面,最终均将作用于现实政教。
乾嘉考据的另一特色,即在于推崇礼教。事实上,随着宋元明三朝平民社会的扩大,礼教下移,其内在超越的一面——“理”之“礼”的影响慢慢消失,而其外在之形式——“事”之“礼”的影响却以简单化的形式渗透民间。按照沟口雄三的观点,从朱子学到阳明学的思想史转化,即儒教的大众化路线,在硬体的层面毋宁是伴随着“礼教”化的形式促进这一事态的发展[7]194-246。由于王学末流思想出现狂妄失态的趋势,因此清初的部分学人,兴起了“儒家礼教思潮”,主要表现为以礼为教的道德论、以礼为治的经世论和以礼为学的三礼经学的研究[8]。质言之,即向具象性和客观性的存在靠拢。这一思想潜流,对清代中叶以乾嘉学派为主的考证学带来深刻影响。
在考据学家戴震的主张中,“理”乃“情之不爽失”,人之欲望的恰当满足即为“理”的价值所在。戴震之论,一方面进一步削弱了“理”的超越性,另一方面则打开了现实性和客观性的大门。然而,戴氏的思想,亦有其不足之处,对于欲望的不可遏制,即“私”的泛滥缺乏外在的规范性。此一不足,稍后为私淑弟子凌廷堪弥补纠正。
有关凌廷堪的学术思想,最著名者莫过于“以礼代理”的主张。凌廷堪认为:
圣人之道本乎礼而言者也,实有所见也;异端之道外乎礼而言者也,空无所依也……圣人不求诸理而求诸礼,盖求诸理必至于师心,求诸理始可以复性也。[9]32
针对戴震论“理”中出现的因平面化和现实性而带来的问题,凌廷堪的主张发挥了牵制作用。凌氏认为,孔子之所以重视“礼”的功能,目的在于证明“礼”才是通往“复性”的正确而具体的操作。“礼”的出现,正是为了应付社会上出现的师心自用的混乱状态,为社会有序化提供了一套可以操作的标准。与凌廷堪同时代的学术官僚阮元对礼教亦格外重视。他在给广东学者陈建的著作《学蔀通辨》作序时强调,“朱子中年讲理,固已精实,晚年讲礼,尤耐繁难,诚有见乎理必出于礼也。古今所以治天下者礼也,五伦皆礼,故宜忠宜孝即理也”[10]1062。阮元对朱熹早年讲理而晚年重视“礼”意的态度表示赞扬。阮氏指出,“理”之论述来源于对“礼”的分析,“五伦”是“礼”的内在精神的体现。由此可见,伴随礼教的泛化,原先由“理”而转型出来的“礼”论,在此已发展成为高于“理”的判断基准。
出于追求社会秩序的需要,乾嘉诸学人均对先秦礼乐制度作出过考订,试图从中寻找三代圣王制礼作乐的具体章程。如戴震曾凭《考工记图》名动京师,一时官方学人如纪昀、钱大昕等纷纷折节与交;凌廷堪作《礼经释例》,江藩美其成就“上绍康成,下接公彦”。不仅民间学者汲汲于礼教建设,在上位者同样重视“礼”的外在规范作用。如乾隆帝在《钦定大清通礼》篇首有谕:“朕闻三代圣王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所以总一海内,整齐万民,而防其淫侈,救其凋敝也。”[11]后世贵族争于奢侈,服饰无度,礼教衰败。同时,由于礼制过于复杂,难以向平民阶层推广,因此乾隆帝要求总理大臣会议“萃集历代礼书,并本朝回典,将冠昏丧祭一切仪制,斟酌损益,汇成一书,务期明白简易,俾士民易守”[11]。在此,乾隆帝认为,礼教有助于安政治民,维护统治秩序。总之,无论是在野士人还是居庙堂者,均认同礼制的重新考订,能够方便沟通古今,借古制而兴新世。
然而,讽刺的是,无论是“由辞以明道”的字词考据,还是“明礼以安世”的礼制考订,伴随乾嘉学风的大盛之后,却走向了学派诸人本希望达到的“修齐治平”理想的反面。由字而通辞,由辞而明道,明道而知圣人之治,这是考据学家燃烧精力的政治寄托。然而考据之学,虽穷尽毕生气力,欲弄清三代车马、明堂、官制为何,却终究无法在实际政治中执行。尽管考据学的原意是为了通过对三代器物的研究而达到圣人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但事实上这一理想只不过是学人的一厢情愿罢了。同时,由于乾隆后期社会治理失衡,贫富差距加大,各地小股农民起义不断爆发,社会已然百病丛生,然而考据学家们却依然高举汉学大旗,闭门造车,咬文嚼字,这就引起了支持宋学的士人以及部分有识之士的不满,如方东树批评段玉裁“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6]39;邵懿辰亦认为,“士大夫鹜为考证训诂之学,内不本身心,外不可推行于时,虚声慕古,古籍愈出而经愈裂,文华日盛而质行衰”[12]。由此可见,在考据学盛行的学界内部,因汉宋之争以及出于对时势关心的需要,发生了严重分裂,学者们对待学术的态度无法做到精诚一致。再者,由于考据学通过对经典字句的再解读,得到了与正统程朱义理派大相径庭的文本含义,这就影响了当时以程朱理学为官方标准答案的科举考试的进行。各路士人学子在考场中纷纷以字义为据,“创新”经典解读,儒家政治圈赖以生存的科举制度发生取士危机,以至于皮锡瑞发出“科举取士之文而用经义,则必务求新异,以歆动试官;用科举经义之法而成说经之书,则必创为新奇,以煽惑后学”[13]200的感叹。
从根本上看,乾嘉考据学的危机,来源于历史事实与现实社会价值之间的分裂。一方面,考据学家过于迷信汉代儒学,斤斤于一字一句,试图从断篇残章中寻找汉代经师们遗留的解经奥秘,结果反而使得追求客观的“圣人之道”陷入了“泥古”的圈子。同代学人许宗彦曾讥汉学家之举为“考之仓雅,攻其训诂,其有不通,又必博稽载籍,辗转引申以说之。一字之谊,纷纭数千言,冗不可理而相推以为古学”[14]。另一方面,考据学家们对经典本身的义理解读不到位,由于考据作为一种治学手段,本身极其烦琐机械,而学者自身又“泥古不通”,故而对于经书本身的意义,大都漠不关心。这一问题,即使是在汉学家内部,部分学人亦对此颇感不满,如阮元说过,“近之言汉学者,知宋人虚妄之病,而于圣贤修身立行大节略而不谈,乃害于其心其事”[15]。从时间跨度来看,考据学家们重视汉儒之琐碎章句而忽略宋儒之“天道性命”,本就极容易使学问失去丰富内蕴,对考据学初衷而言是走入了一误区。
总之,随着乾嘉考据学的深入推进,其学派面临巨大困境,不仅未能理解三代“圣人之道”的主旨思想,反而因为缺乏理论上的超越旨归而陷入僵化的状态。这一状态,引起了同时代部分学者的忧虑,汉学自身需要突破传统解经的陈旧模式,丰富义理内涵。这项工作,在以常州庄存与为代表的《尚书既见》中得到初步反映。
二、“道统”之辩:从“求真”走向“护伪”
理学道统论主要围绕“虞廷十六字心法”。“虞廷十六字心法”出自《尚书·大禹谟》记载的尧禅位于禹时的一段话:
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16]93
其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是宋明理学道统论的依据,也是政权执有者推行统治、维持世道人心的理论源泉。可以说,《尚书·大禹谟》一文的重要价值,即在于以此“心法”沟通内在价值与外在准则,使得规则的制定得以获得超越现实的引导意义。
然而,在清初,随着阎若璩著作《尚书古文疏证》一书的出版,以“虞廷十六字心法”为核心的理学道统论出现危机。阎若璩指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一语乃袭用《荀子·解蔽篇》之《道经》语,复掺杂《论语》“允执厥中”而成十六字,因此宋儒所谓“虞廷十六字”纯属拼凑伪造。黄宗羲为阎氏此书作序,盛赞其功,认为“此十六字者,其为理学之蠹甚矣”,“后之儒者……穷天地万物之理以合于我心之知觉,而后谓之道,皆为‘人心’、‘道心’之说所误也”[17]3。
尽管阎若璩通过经典考据的方式,证实东晋梅赜所献《尚书》25篇为伪作,但同时代人,如万斯同、方苞、李光地、陆陇其、李塨等人,均对阎氏著作提出反对。如李塨在给毛奇龄之《古文尚书冤词》一书作序时称:
初,先生作《尚书释疑》数十条,盖虑世之疑古文者而释之,然未尝示人也。及塨南游时,客有攻辨《中庸》《大学》《易》系以及三《礼》三《传》者,塨见之大怖,以为苟如是,则经尽亡矣!急求其故,则自攻《古文尚书》为伪书始。[17]739
李塨之所以“大怖”,乃在于意识到辨伪会给传统经学带来颠覆性后果。李光地对此亦有警惕,他指出:“古今文之辨多矣。虽朱子亦疑之。近年学者则毁诟尤甚焉,其语殆不足述……然则,古文云者,疑其有增减润色,而不尽四代之完文,理或有之矣。谓其纯伪书者,末学之肤浅,小人而无忌惮者也。”[18]1086在李光地看来,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的出现,恰好给小人提供了攻击儒学的借口。阎氏之书,是儒学经典发生内部转折的关节点。日本学者吉田纯指出,《尚书古文疏证》的流行,是造成经学两大思潮——维持经典还是制造经典——纠葛的中心[19]45。
不幸的是,多年后,李光地对“小人而无忌惮者”的担忧在乾隆朝上演。和珅专权,朝纲败坏,价值系统委坠于地,当时的常州学派代表人物庄存与对此忧心不已。庄存与的治学特色,在于“践履笃实于六经,皆能阐抉奥旨,不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20]。是故庄氏治经,不同于同时代学人之汲汲于文字真伪,而是“惟以知人论世为准”来发挥经世用意,从而达到兼采汉宋、通达圣道的为学境界。尽管常州学派以善治《公羊》而闻名于世,然而庄存与却尤长于《尚书》。龚自珍曾指出:“(庄存与)幼诵六经,尤长于《书》,奉封公教,传山右阎氏之绪学,求二帝三王之微言大旨。”[21]141龚自珍师事庄氏外孙刘逢禄,为常州学派继承人,自对师学渊源了解无误。但是,龚氏并未分明庄存与与阎若璩之治《尚书》的区别。阎氏之书,重在考辨真伪;而庄氏之学,则重在匡扶圣教,延续道统。故庄绶甲为其父之《尚书既见》作跋时提到:
先大父(庄存与)……后见阎征士若据《古文尚书疏证》攻讦过甚,叹曰:“此启后人变乱古经之渐,五经将由此糜烂矣。汉唐以来,圣教衰微,独赖有五经在,犹得依弱扶微,匡翊人主,默持世道,安可更有兴废哉!”[22]
龚自珍亦言:
(庄存与)自语曰:辨古籍真伪,为术浅且近者也;且天下学僮尽明之矣,魁硕当弗复言。古籍坠湮十之八,颇藉伪书存者十之二,帝胄天孙,不能旁览杂氏,惟赖幼习五经之简,长以通于治天下。昔者《大禹谟》废,“人心道心”之旨、“杀不辜宁失不经”之诫亡矣;《太甲》废,“俭德永图”之训坠矣;《仲虺之诰》废,“谓人莫己若”之诫亡矣;《说命》废,“股肱良臣启沃”之谊丧矣;《旅獒》废,“不宝异物贱用物”之诫亡矣;《冏命》废,“左右前后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数言幸而存,皆圣人之真言,言尤疴痒关后世,宜贬须臾之道,以授肄业者。[21]142
庄存与深知《尚书》乃皇子读书学道的重要教材,出于存道统、安天下的实用角度,庄氏对所谓“辨古籍之真伪”嗤之以鼻。他认为,《尚书》存在的意义即在于让读书人(尤其是帝王)通经致用以治理国家。身为南书房的大臣、乾隆的贴身秘书,庄存与能做的就是借助经书的力量和儒家的道统论,与和珅一派斡旋,以挽救世道人心。故此,庄存与“居上书房,深念伪《书》中如《禹谟》之‘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太甲》之‘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道罔不亡’、《吕獒》之‘玩物丧志,玩人丧德’等语皆帝王格言,恐伪《书》遂废,后世人主无由知此,因作《尚书既见》三卷”[23]1167。可见,庄存与作《尚书既见》的目的,在于“存帝王格言”,延续道统的合法性,龚自珍称其著作为“欲以借援古今之事势……数数称《禹谟》《虺诰》《伊训》,而晋代剟拾百一之罪,功罪且互见”。庄氏明知东晋梅赜所献为伪,却依然选择回护伪经,引导天下士人重归孔孟正道,此乃庄氏以“道统”至尊的方式来救治人心。尽管此书出版后深受汉学家们的批评,但庄氏毕竟象征着调和汉宋的先驱;同时,由其领导的常州学派,开启以微言经世的学风,对后学特别是今文经学家的影响巨大。艾尔曼由此指出,庄存与的观点体现了他和清朝官方意识形态在思想上的一致性,是经学、国家权力的合法性以及政治阐述三者合一的产物。很明显,庄存与的思想动机,是出于对以儒家“道统”思想为核心的统治秩序的维护和对思想统一的支持[24]72。
然而,尽管以庄存与为代表的“护伪”举措是为了维持儒家思想统治的合法性地位,但针对乾嘉学派陷入事实与价值割裂愈来愈大的困境,庄存与试图放弃客观真实而以伪经来维护价值体系,这会导致社会活动重新回到君主个人权威统治之下,从而出现与清初理性化与客观化思潮相违背的态势。换言之,虽然“道统论”的提倡有助于获得超越的内在,却无法摆脱以统治者为核心的“圣人之道”的集权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庄存与的思想,扼杀了清初政治理性主义的萌芽,实乃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
综之,清代中叶的“明道”运动发展至后期,分为以汉学家为核心的“求真”派和以维护“道统”为核心的“护伪”派,两派主张虽异,但均无法解决“明道”运动带来的困境。由此,清代中叶的学界出现一种怪圈:学人既想要依据实事求是的态度,考究三代真相,弄清圣人“制作”的真相;但在接近真相的同时,又不得不维护承载儒家“道统”的伪经本身。此种困境,非一学问性格豪迈者则不可破。这一任务,交由清代中叶思想的继承者——龚自珍来完成。
三、何以“明道”?——龚自珍“尊心”论的思想史意义
龚自珍思想深受家学与师学的影响,兼文字训诂与《公羊》微言于一体;同时,龚氏近承浙东史学精神,尤与会稽章学诚之史学观点相近。章学诚生于考据学派势头最为炽烈的乾嘉时期,彼时,戴震已是名震一方的考据大家,而章学诚在学坛的地位则远逊于戴氏。然而,实斋对世风转向颇有留意,著《文史通义》,提出“六经皆史”的观点。章氏指出,古者官师合一,官之职守即为管理礼乐教化之事,后来官师治教相分,私门著书盛行,于是出现了“立教者离法而言道体”的现象。但是实际上,“学者崇奉六经,以为圣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时,各守专官之掌故,而非圣人有意作文章也”。因此,实斋强调:
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之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微,其无当于实用也。[25]216
为学的出发点当是为当代人伦日用服务,通晓掌故则需与经术合而言之,否则即是精而无用。由此可以看出,实斋之学,乃一重事理相摄之学,重社会教化之学。他提出的其他诸如“性情怡得”“史意与史德并重”等观点,无一不是重视人文化成过程中道德、知识与现实的统一。实斋的知识论,是经“时”与守“义”的相互作用,是“常”与“变”的辩证统一;而他的道德观,则无一不重视人文化成过程中的内外相合。
实斋此种学问与人事并举的治学态度,给龚自珍带来极大启发。大抵史家之忧,总关乎国计民生。《春秋》《史记》《通鉴》等,作文者无一不以儒家情怀关怀人世,因此史学往往容易与治世之道相互关联。自珍深研史著,主张“出乎史,入乎道”。如何才能“出史入道”?龚氏认为,关键在于“尊心”:
史之尊,非其职语言、司谤誉之谓,尊其心也。心如何而尊?曰能入。何谓入?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系,国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其于言礼、言兵、言狱、言政、言掌故、言文章、言人贤否,如其言家事,可谓久矣。又如何而尊?曰能出。何谓出?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系,国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与有守而皆非所专官。其于言礼、言兵、言狱、言政、言掌故、言文章,言人贤否,辟优人在堂下,号啕舞歌,哀乐万千,堂上观者,肃然踞坐,眄睐而指点焉,可能出矣。[21]80
“尊心”的关键在于“能入能出”,而这一入一出,皆关系现实风俗制度。龚自珍身处的时代,朝堂百官“朝见长跪,夕见长跪”,民间则风俗败坏,以私田抢占水道,“细民盘踞而不肯见夺”。有见于此,龚自珍以“尊心”之法探究史籍内涵,从而沟通古今,试图从“救人心”处入手,挽救世风,推动社会变革。
龚自珍将“心”的作用与现实制度相关联,其背后的思想理路来自于他对“心力”的推崇。在龚自珍看来,“心无力者,谓之庸人。雪大耻,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21]15-16。凡规划国是、改革弊政,皆源于“心”具有内在的力量。自珍如此推崇“心”的作用,与其佛学背景有关。据同县吴昌绶所编《定庵先生年谱》记载:
先生学佛,铁君为第一导师,与仁和钱东父居士、慈风和尚四人,皆奉彻悟禅师之书,笃信赞叹。慈公深于相宗,东父则具教、律、禅、净四问。在京师认睿亲王子镇国公容斋居士,好读内典,遍识额纳特珂文、西藏、西洋、蒙古、回部及满汉字,校定全藏,凡经有新旧数译者,皆访得之,或校归一是,或两存之,三存之,自释典入震旦以来,未之有也。[21]606
龚自珍早年颇精唯实,42岁时始遇天台宗,对其中“一心三观”“一念三千”之旨深有感触。自珍在天台宗的思想辨析中,看到了“心”的巨大能量,尝作《发大心文》,其中有言:
是故欲修布施,发心为先;欲修安忍,发心为先;欲修止得,发心为先;欲修精进,发心为先;欲修静意,发心为先;欲修智慧,发心为先。[21]392-393
按照晚清佛学思想的发展轨迹,佛学经历了对人——释迦牟尼的信仰,到对超人——佛祖的信仰,最后又转向对“本心”的信仰的过程[26]245。这一由外而内的宗教情感的转换过程,其实质是彰显人的自我价值,提高自我认识。在这一思潮之下,自珍将作为信仰之佛学的出世精神转化为入世动力,援佛入儒,提炼“心”的优先地位,以实现心灵安顿与社会责任的统一。
事实上,对“心力”的推崇,即是对“自我”能动作用的肯认。道光三年(1823),龚自珍作《壬癸之际胎观》九篇,内有论述“自我”概念的短文一章:
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圣人也者,与众人对立,与众人为无尽。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毛羽肖翘,我理造文字言语,我气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别造伦纪。众人也者,骈化而群生,无独始者。[21]12-13
这段话的内涵十分丰富:首先,“我”在这里是主体精神觉醒的重要标志,然而,此处之“我”,并非个体意义上的存在,而是“众人”之意的化身,象征“类的主体性”。此“类的主体性”与道德主体无关,而是认知主体和实践主体的展开。这一展开的过程,就是对“圣人之道”的践履。其次,“圣人”在此有两类含义,一类是制礼作乐的“圣王”,另一类则是基于“自我”的“大道”的化身。在龚自珍的思想中,“圣人”并非简单地归类为某一天才卓著的特殊人群,而是以“众人”为内涵的“自我”可能性的成长。“圣人”与“众人”的对立,并非空间概念上的正反两面,而是“我”如何去成为“我”的过程中的一种无限可能;成长过程中的“我”即是“圣人”本身的形成。因此,“圣人”是一无穷象征,通往“圣人”之“道”即是“众人”的“自我”实现。此即“圣人”既与“众人对立”又“与众人为无尽”之意。
龚自珍“自我”概念的提出,为乾嘉学术困境觅得一条出路。大抵经道分离的危机根源,在于如何对待“人”这一拥有自主意识的存在。按照乾嘉考据诸人的观点,规范现实之“人”的行为依据来源于先代圣王遗留的礼乐制度,倘若能在当下恢复三代之制,则“近于圣道不远矣”。在此,一切以依于经典之客观“制作”为标准,“人”的设定处于被动地位,依附于历史而无所作为,最终导致了考据学出现脱离现实的趋势;而按照常州庄存与的“道统”观,尽管在义理上有了来自“天道自然”的支持,但却同样未能正视大部分“人”的价值作用,仅将社会发展希望寄托于少数权贵。在此,“人”(普通人)的生命缺乏活力,受压于威权之下,这使得庄氏思想发展成为替集权制呐喊助威的力量,背离客观主义兴起之世风,故《尚书既见》甫一发行即遭学界斥责。在乾嘉学术的困境中,龚自珍力倡“自我”,无论是历史标准还是“道统”承继,皆以“众人”之“我”作为核心,“我”是有史以来至高无上的价值判断标准;而“我”之所以能够衡量价值大小,在于有无畏之心力,一切但凭本心做主,符合本心者当下施行,不合本心者弃之草野。至此,“我”掌控了古今上下事物的运行标准,化屈服为主动,“我”即存在即超越。龚自珍以当下之“心”为念,以“自我”为中心,横跨经典与现实,在融合儒佛的基础上弥合事实与价值分裂的缝隙。
四、结语
清代中叶的“明道”运动,在乾嘉考据“求真”和常州庄氏“护伪”中走向困局,追根溯源,在于轻视“人”的主体创造性,或泥于古制,或崇尚权威,最终双方皆与时代发展要求相背而行,造成了经道分离,理论脱离实际。龚自珍的出现,一方面继承了浙东史学经世致用的精神,另一方面延续了晚明以来儒佛合流的体系,发挥“心力”,高扬“自我”主体,使得价值规范的制定标准从历史语境和统治权威下解放出来,走上以“众人”之集体作用为核心的独立道路。通过龚自珍对“心”的重新定义,儒学政治论逐渐摆脱道德至上论和圣王制作观,嘉道儒学出现转型,走向了大众化和平实化。应该说,将龚自珍视为乾嘉学术的转折人物,有一定合理性[注]吴根友认为,龚自珍上承乾嘉语言学,下开今文先河,“是乾嘉学术、思想向近代转化的关键人物之一”。本文则从另一角度论证此一观点。 详见吴根友、孙金邦:《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