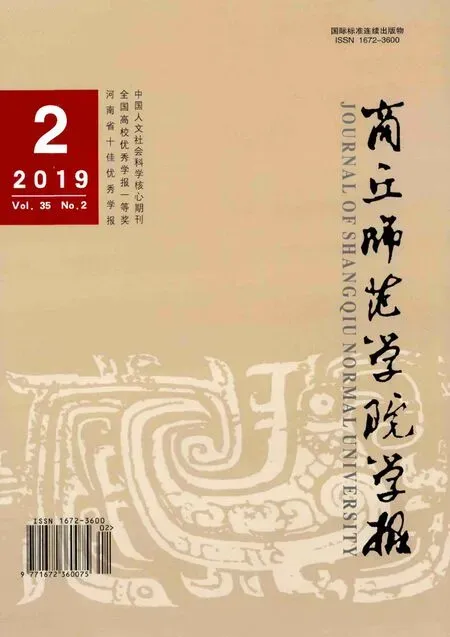文学与历史的联动
——格非“江南三部曲”探究
吴 世 奇
(兰州大学 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20)
文运关乎国运、文脉联通国脉。中国文学从古至今就有着反映社会、表现历史、描写现实的传统,无论是开创了现实主义精神的《诗经》,还是开启了浪漫主义传统的《离骚》,直至新文学以来的《子夜》等,无不与民族、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这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体现得尤为突出,百年中国新文学参与、见证了百年中国的社会历史变革发展,使得中国新文学与中国百年发展史之间有一种联动机制。无论是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鲁迅等新文学先锋倡导“科学”与“民族”,还是当下莫言、贾平凹、余华等作家表现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百态,都表明了中国新文学有“‘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1]526的人文情怀与担当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尽管有些文学形态表现得与社会有一定的距离,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能够完全脱离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文学可以视为对社会现实的“浓缩”。 “《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在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2]683-684。中国当代著名学者型作家格非的《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三部长篇小说,因故事发生地点设置在江南而被合称为“江南三部曲”。在“江南三部曲”中,格非通过陆秀米、谭功达、谭端午等主要人物,勾连起自晚清直至当下百年左右的中国社会历史。如果说陈忠实在《白鹿原》中所叙述的是一个民族的一段“秘史”,那么,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民族的世纪“寓言”。
一、人生追求的乌托邦色彩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从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到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期间跨越了数千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一部中国诗歌史即是半部中国文学史。中国新文学也有着鲜明的诗化传统,仅就小说这一文体而言,也与诗歌有着密切关联,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形成了以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作家为代表的“诗化小说”或者“抒情小说”流派。这种小说“呈现出了一些独特的形式特征,如分解叙事,经验的零碎化,借助于意象和象征以及小说中注重引入散文、诗歌及其他艺术形式等”[3]。格非的小说创作向来具有诗意,这与其出生在南江水乡不无关系,《傻瓜的诗篇》《人面桃花》《望春风》等都或隐或显地表现出诗的意蕴。在一定程度上,“江南三部曲”可以称得上是一部诗,它具有诗的质地、格调、意蕴,尤其是在审美层面上,“江南三部曲”是“文化诗学”视野下的一个范本。对于中国读者而言,仅从“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这几部题名,即可感悟到一种惆怅的诗意,而这也正是作者所要表达的主题之一,是对人生目的、人生理想、人生命运的一种难以捉摸的追寻,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与幻灭,它也以寓言的形式折射出一个民族的百年风雨历程。这种对“乌托邦”式理想的追寻,或隐或显地贯穿于“江南三部曲”之中,并且作为一种隐喻,对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建构以及时代的变迁作了注脚。从历时性层面来看,陆侃、张季元、陆秀米、谭功达、谭端午以接力的形式完成了这一“历史的接力”,都走上了一条虚无缥缈的追寻道路,似乎都在重演当代的“西西弗斯神话”。
中国自古就有关乎乌托邦的设想,例如庄子在《逍遥游》以及陶渊明在《桃花源记》里面所建构的理想空间,就与西方社会关于乌托邦的阐释有共通之处。西方社会在16世纪初就产生了关于乌托邦的重要著作,其概念主要以英国托马斯·莫尔所建构的为主,“乌托邦(Utopia)意指一个虚构之所,其词义是‘没有这个地方’(nowhere),从字源上看是一个空间化的概念”[4]。这一带有荒诞色彩的追寻以陆侃的“风雨长廊”设想拉开序幕。《人面桃花》中的陆侃是晚清时期的一位知识分子,曾经中过进士、做过州官,罢官后在家读书赏花,过着隐士般的生活,因一天偶得《桃源图》而产生了一个执念,认为普济就是晋代陶渊明所言的桃花源,而村子前的那条河就是武陵源。于是,陆侃痴心于心中的那个世外桃源,要在全村种上桃树,并且要建一条能够连接村里每一户人家的风雨长廊,让普济人永远免除日晒雨淋之苦。显而易见,没有人能够理解陆侃的这一行为,他自己也被认为是“疯子”,最终成了“阁楼上的疯子”,直到有一天突然下楼离家出走,人们才逐渐忘记了他。福柯曾经以探讨“癫痫”与“死亡”来指代“癫痫”与“文明”,“癫痫主题取得死亡主题并不标志着一种断裂,而是标志着忧虑的内在转向,受到质疑的依然是生存的虚无,但是这种虚无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外在的终点”[5]13。“癫痫”与“文明”的关系也是中国新文学一直探讨的,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清醒者即是以“狂人”的形象出现的,而后知识分子无论是选择“独唱”或者“合唱”,其实内心深处都是有着一种孤寂、虚无、甚至疯癫之感的。陆侃及之后的张季元、陆秀米等都被认为是“疯子”,而他们也都住进了陆侃曾经居住的“阁楼”,作者的这一精心安排应该是对福柯有关论述的一个互文性策略,从而丰富了这种“乌托邦”建构的内涵。陆侃最后选择离开,这似乎是一个暗示、一个象征,表明以普济为符号的当下社会并不存在建设“大同社会”的空间,只有去一个不知道终点的“远方”寻找。
陆侃离家出走之后,身份颇为神秘的张季元来到了陆家,他的出现影响了陆秀米的一生,既促使她由一个天真烂漫、懵懂无知的少女成长为一位对爱情具有独特追求的女性,也在无形之中对她后来走上革命道路起到了引导作用。在20 世纪初,曾经横渡日本的张季元与几位志同道合的人成立了反清组织——“蜩蛄会”,并且拟定了建设新社会的《十杀令》,其中带有浓厚的“大同社会”的思想色彩。但是,蜩蛄会成员之间似乎也同床异梦,就连张季元本人也常常因对秀米的痴恋而怠慢了革命,最终张季元等许多蜩蛄会成员在很短几年间就被清廷铲除,无论是他的“咫尺桃花”还是革命理想,也都如一场春梦般去无痕迹。“当张季元被秘密杀害之后,他的那本日记便成了陆秀米的启蒙之物——可以说,她的‘性启蒙’和‘革命启蒙’是同时完成的,这使得她的革命倾向一开始就与来自生命与血液之中的原始记忆与‘本能冲动’挂上了钩”[6],他所留给陆秀米的,是一本日记,一个启蒙,一个执念。
陆秀米从花家舍回到家里时,与离家之前已经有了脱胎换骨般的差别,受在花家舍所看到的人们生活情景以及张季元的影响,她似乎要重走陆侃和张季元的道路。她到家之后即一头扎进父亲以及张季元曾经居住过的阁楼,疯狂阅读了张季元的日记后,有了让人觉得疯狂的举动。她先是聚拢一干人马搞了一个放足会,让村里妇女不再缠脚,而后又成立普济地方自治会,设立育婴堂、书籍室、疗病所、养老院,还计划修水渠从而使得村民的农田都可以用江水,开办公共食堂让大家在一起吃饭,甚至还要成立殡仪馆和监狱。她的这些举措刚开始便有许多人反对,尤其是富家大室,后来连自己内部人马也有人倒戈,这无疑使她产生了强烈的幻灭感,以至放弃了一切,只保留了普济学堂。但是,她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初衷与宏愿,仍然与谭四等几个不愿离去的人一直坚守革命信念,甚至幻想能够靠龙庆堂的力量攻打梅城。最终,由于龙庆堂的叛变,包括自己的儿子在内的许多人被清廷官兵剿杀,自己的大同社会的构想以及革命的愿望完全破灭。
“江南三部曲”中类似的反映追求与理想破灭的情节还有许多,这种追求与理想带有很大的乌托邦色彩,“这种乌托邦精神,既是人物的生存理想,也是他们安顿自我灵魂的园地,它是一种自我审美的存在,是人物拒绝堕落、反抗异化的武器,而不是对社会秩序的空想”[7]。在“江南三部曲”中,许多人物的这种追求令人钦佩,虽然最终都未逃脱“镜花水月”的宿命,但它本身并没有任何差错,错的是它存在的社会与时代。所以,这种追求与理想是值得赞赏的,也是缺乏根基的。但是,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依靠的正是这种“桃花源”“大同社会”“乌托邦”般的设想,前代人的失败尝试或许能够为后人打下基础。通过对“江南三部曲”的阅读,我们似乎能够想起自鸦片战争以来,在追求民族独立解放、国家富强振兴的道路上,许多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他们的方案与实践有的失败了,但这并非毫无价值与意义,为后来的社会建设与发展带来了有益的启示,这或许也是格非在考察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观念。
二、人类命运的神秘莫测感
人的命运是难以预料的,格非更是一位非常善于表现人的命运的神秘性、偶然性的作家,似乎带有一定程度的宿命论色彩,这在其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许多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神秘’作为可以感受不可言说的主观体验为人类所共有,这种体验在理性主义兴起以前,与宗教、巫术等搅和在一起,影响着人们的生活。”[8]《迷舟》《大年》《青黄》《风琴》《敌人》等作品,在对人的命运、人的心理描写中,都流露出浓厚的神秘主义气息。这种对命运的神秘性以及历史偶然性的表现,在“江南三部曲”中俯拾皆是,比如为什么陆侃在离家出走前说要下雨了就真的下了雨,陆夫人在临终前说要下雪了就很快下了雪,为什么陆侃、张季元、陆秀米都住进了那间恐怖的阁楼,陆秀米早已提防翠莲却未行动,翠莲的命运竟然难以逃脱算命先生所言,偏偏在谭功达去外地时普济大坝出事了。
在《人面桃花》中,最具神秘色彩的恐怕就是陆秀米的梦境与遭遇了。孙姑娘惨遭杀害后,陆秀米梦见自己去参加她的葬礼,孟婆婆提着篮子给每人发一朵黄色的绢花,碰巧就差自己的一朵,梦的后面还有张季元在寺庙中对自己的非礼行为。梦醒后还是不知不觉跟着送葬的队伍走了好远,待她看见孟婆婆提着花篮每人一朵发白色绢花时,突然心头一沉想到了梦境,就在这时孟婆婆走过来对她说就差她一朵。陆秀米从这个梦与现实的对照中,参禅般地悟出人即便在清醒时也是在做一个更大、更遥远的梦。又如陆秀米在花家舍做的一个白日梦,看见一个浑身是血的人来到自己床前,把自己的被杀以及在花家舍的建设告诉了陆秀米,并且预言还会有人重蹈覆辙。等梦醒后,韩六进来告诉了她王观澄被杀的消息,竟然与梦境相同,而她也因此领悟到世间一切都是虚幻。另外,在陆秀米听“忘忧釜”的声音时,觉得自己身如羽毛飘在空中,最后竟然落在了一个荒坟上,再听又觉置身于人迹罕至、桃花流水、鸟语花香、与世无争的禅寺。当陆秀米在出嫁之日被土匪劫持到花家舍时,竟然发现困住自己的湖心岛上的景色以及对面花家舍的场景,竟然与之前莫名其妙的感受一样。陆秀米和老虎关于革命的谈话也极具神秘色彩,当老虎问陆秀米何为革命之时,陆秀米竟然说“革命,就是谁也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知道他在革命,但他还是不知道他在做什么”[9]227,而且用爬遍皂龙寺一砖一瓦的蜈蚣却不知道皂龙寺整体样子来形容自己在革命中的感觉,这一切似乎是受到命运的支配,宿命早已决定了一切,自己的一切挣扎都是徒劳的。
细心阅读《山河入梦》的话,不难发现姚佩佩的一生经历也是充满了命运的安排与捉弄,费尽心思还是无法逃脱上帝之手的控制。谭功达把姚佩佩从一个洗澡堂解救出来安排到自己办公室后,经常写几个神秘莫测的算术等式:44-19=25;44-23=21;21-19=2[10]4。这或许只是谭功达无意识下的行为,却一直吸引着姚佩佩去解码,终于有一天似乎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但这更进一步地把她的命运与谭功达交织在一起。她通过紫云英花朵占卜自己与谭功达的姻缘,尽管自己不愿相信那个预言式的结果,却终究没有摆脱与谭功达“云泥两端”、红消香断的劫数。在姚佩佩杀死金玉出逃的过程中,命运似乎又给她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她逃出梅城后的第一站是界碑,然后是莲塘、吕良、银集、临泽等,谭功达用笔在地图上把她停留的所有地点连起来之后,吃惊地发现姚佩佩根本没有逃脱,而是绕着高邮湖转了一个大圈,按照行走轨迹眼下似乎马上就要回到出发点。如果说姚佩佩在懵懂无知的情况下,像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尚且在情理之中,但她的足迹反映在地图上竟然是一个奇怪的圆圈,以至于使谭功达觉得即便是让他用圆规也画不出这么一个圆来。不过希望尚存,因为现在姚佩佩所在的三河与梅城县城还隔着一个普济,而去普济只有两个地点可以选择,其中一个就有姚佩佩非常熟悉的普济大坝,但姚佩佩却阴差阳错地选择了另一个。这不可思议的结局在给人带来神秘感之时也夹杂着恐怖感,它似乎能够起到悲剧引起的“怜悯”和“净化”效果,也留给读者一个思考自身存在的空间。
从这种命运的神秘性以及历史的偶然性叙述之中,读者能够发现格非在“江南三部曲”中继承了先锋文学创作时期的艺术手法,也能够透视出自清末民初一直到当下的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轨迹,这其中就不乏历史的偶然性,或许这也正是作者对待历史的一种姿态与认知。
三、复杂多变的人性与道德
在“江南三部曲”中,格非揭露出了人性的复杂之处以及人性的弱点与被困,比如告密、诬陷、嬗变、狡黠、欺骗、趋利等,淋漓尽致地描述出各个时代、各类人物的心理活动,具有心理小说的功底。“轻松地揶揄和包容一切,同时也厌倦着一切的格非,还是严肃地在作一个时代的精神描摹。”“‘江南三部曲’类似个人的精神成长史,是个作减法的过程,写个人如何从名利、欲求、梦想等——解脱剥离出来,剩下的是生命最朴素平淡的面貌和存在。”[11]在《人面桃花》中,陆秀米被困在花家舍时曾经听韩六论述过人心。韩六认为,每个人的心都是被围困的小岛,这一论断似乎契合“江南三部曲”中所有的人物心理。这个比喻形象生动地表现出人心难测、人与人难以有效沟通以及人心的孤寂感与挣脱欲等许多方面。
人都是难以安于现状的,即便是有着优厚的生活条件,仍然想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人心也是如此,它虽然被围困但却不是束手就擒的,它具有强烈的挣脱欲。陆秀米被困在花家舍之后,韩六告诉了她可能被“揉票”,她是作了拼死抗争的准备的,无论这种准备最后的效果如何。再者,在父亲走失以及张季元被杀之后,她的内心不仅没有感到恐惧,反而有了狂热的感情,结合父亲的设想、张季元的志愿以及在花家舍所看到的人们生活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宏大理想,走上了一条革命道路。即使在遇到挫折、自己的内心不能够被人理解之时,陆秀米依然没有屈服,她的内心还是在努力挣扎,力图摆脱目前的困境。
自古官场如战场,官场之中的明争暗斗是无处不在的,而谭功达的屡次受挫皆因为看不透人心。当谭功达有聂竹风作为坚强后盾时,白庭禹对他的一系列提法虽然有所意见但出于巴结上司还是与他站在同一战线,后来还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侄女白小娴介绍给他,想以此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利益。当谭功达与白小娴的婚事告吹之后,尤其是在白庭禹越来越想把谭功达拉下马之时,谭功达仍然缺少必要的防备与反制,最终自己一步步走进别人设下的圈套。如果说谭功达看不清白庭禹还情有可原,那么摸不透自己曾经的下属钱大钧就属于太过天真与单纯了。钱大钧表面上对谭功达这位曾经的首长现在的上司忠心耿耿,背后却瞒着谭功达搞了不少阴谋。而这一切似乎都是人心的欲望在作祟,金钱、权力等成了人竞相追逐的对象。另外,谭功达在花家舍考察时,也了解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花家舍如今的民风淳朴、与世无争、大公无私等美好、和谐的一面,竟然是建立在设立检举、揭发制度基础之上的,经过那样一个特殊时期的考验,人们的内心可能是被外力驯服的,而不是自发的、本性的。这与福柯所探讨的“规训与惩罚”似乎有相似之处,“监督不停地进行着”,“权力根据一种连续的等级体制统一地运作着,每个人都被不断地探找、检查和分类”,“一种广延性权力以一种确定无误的方式统治每个人的肉体,使该城镇变得静止不动,这就是一个治理完善的城市的乌托邦”[12]220-223。
在《春尽江南》中,人们似乎对道德底线不断突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也十分匮乏,即便是在夫妻之间有时也难以坦诚相待。谭端午和徐吉士等文人在大学期间还是意气风发的有志青年,但因为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个事件彻底失去了知识分子应有的精神风貌,在经历一番痛苦的挣扎与自我放逐之后,就沦为了追求庸俗、腐化生活的穷酸文人。谭端午在与庞家玉结婚生子后,仍然不时背着妻子和陈守仁、徐吉士等人混在一起去追逐女性。而后来庞家玉也为了家庭以及个人利益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也成为一个与人偷情、知法犯法之人,而这一切似乎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了。尽管在故事最后庞家玉选择了维护家庭、为了不给家人带来痛苦离家出走,但丈夫谭端午一开始却一直没有明白其良苦用心,甚至猜测庞家玉是外面有人了才与自己离婚,这是否能够从一个层面反映出夫妻之间默契、信任的缺失呢?
人性一直是古今中外文学艺术创作备受关注的一个对象,文学本质上是人学,它主要是关注人的情感、人的体验、人的发展、人的存在,而人性无疑是世上最为复杂的东西,无论是西方基督教中所谓的“原罪”,还是中国古代的“性本善”“性本恶”,抑或是现代以来西方以及中国作家对“国民性”的探讨,都难以十分有效地揭示人性。从文学伦理学上而言,人是一种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斯芬克斯因子来源于古希腊神话的狮身人面形象,它代表了人的理性与动物性的统一。“斯芬克斯因子对我们现实社会中人的基本特点作出了说明,即现实中的人在客观上无法割裂同其他动物的联系,也同样具有同其他动物类似的特点,正是人身上具有的这个特点,我们可以把人称为斯芬克斯因子或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用斯芬克斯因子来解释现实中的人,解释人身上共存的不可分割的道德性和动物性特征。”[13]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处处在书写人性,也在探究各个时代人性的差异以及背后的社会、历史、时代等影响因素。尽管我们不能像“红学”研究那样考据格非所书写的具体历史事件,但文本自身还是折射出了自清末以来的社会历史变化给人的心理、思想带来的影响与冲击。从这种意义上而言,格非在“江南三部曲”中对人性的探讨,也是对一个民族的心理个性、价值情感的探究,显示出了严肃性、厚重感、寓言性。
四、“江南三部曲”的局限
“江南三部曲”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它有审视历史的厚度,也有关照当下的温度;既坚持了审美的高雅,也探究了社会的变迁,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然而,通过文本细读,似乎感觉“江南三部曲”还有些可以进一步完善之处。例如,在《山河入梦》中,作者试图把谭功达塑造成当代贾宝玉的形象,但是文本中所呈现出来的这一人物形象,显然与贾宝玉有较大出入。如果说两者有相似之处的话,就是都是“花痴”,看见年轻貌美的女性都会着魔一般神魂颠倒。除此之外,谭功达与贾宝玉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且不说谭功达功名心极强而贾宝玉厌恶经济之学,即便是在“花痴”这一点上,两者也是具有明显差别的。贾宝玉喜欢女性的同时也非常了解女性,知道女性的价值,深得女人心,而谭功达似乎除了喜欢之外对女性一无所知,也不能够细致入微地体贴、呵护女性,无论是对姚佩佩,还是对白小娴,甚至后来的张金芳,都远不及贾宝玉。
另外,在《春尽江南》中,作者安排了一个凄美的结局,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显示出了作者高超的表现技巧以及独特的思想情感。但是,倘若按照“江南三部曲”的整体发展格局以及《春尽江南》所表现的主要社会内容与时代特征,以这样的一个结局收官,似乎在表现主题上与整个文本所呈现出来的走势略有偏离。如果把结局略加改动,改为庞家玉因为厌倦了徒有诗人虚名且感情泛滥的丈夫谭功达,厌倦了把自己当作一个男人一样日夜操劳,喜欢上了之前与人偷情时的刺激和愉悦生活,所以选择离家出走,似乎能够获得更为丰富的艺术效果。
一方面,它可以表现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之死”这样一个时代主题,也能够在“江南三部曲”内部形成一个知识分子谱系,反映出一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社会地位的变迁,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文本提升到知识分子“寓言”的高度。“当先锋作家们纷纷从形式主义高地撤退并转向现实时,格非十年磨一剑的‘江南三部曲’却将目光投向了百年中国的乌托邦历程。在广袤的历史空间中,三部曲建构了一个历史的阐释者与‘话语讲述的年代’和‘讲述话语的年代’之间无限对话的过程,既再现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沧桑巨变,也揭示了乌托邦理想在时代变迁中发生的变异以及它对当代人精神生活的影响。”[14]
另一方面,它也能够把当下的一些社会乱象、存在的荒诞性等主题表达出来,因为《春尽江南》所反映的时代背景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这是一个思想开放、多元的时代,在社会氛围、经济利益以及消费主义的驱动下,人们似乎失去了价值规范。作者选择以一个温情的爱情故事作为结局,或许是出于一种恻隐之心,让读者相信人间尚有温情、温暖和挚爱,而这是至死不渝的,能够超越时代的慌乱与荒凉,穿越时空与生死界限,正所谓“烟霞褪尽的岁月,亮出时间的底牌,白蚁蛀空了莲心,喧嚣和厌倦,一浪高过一浪,我注视着镜中的自己,就像败局已定的将军检阅他溃散的部队,幸好,除了空旷的荒原,你也总是在场”[15]376。
总而言之,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是一个开放的、丰富的、多层的文本。“‘江南三部曲’分别写了民国初年、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现实。这样的宏阔构思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风云变幻与世事沧桑。”[16]透过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我们能够考察百年中国所走过的艰辛历程,能够以独特的视角走进历史、认识历史、阐释历史,也能够从个人存在的层面领悟人命运的难料、人性的复杂,它的寓言性也正在于此。尽管这一经典之作还有进一步完善的余地,但毋庸置疑的是,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会成为“茅盾文学奖”桂冠上的一颗耀眼的明珠,甚至代表了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质量与水准,值得人们进一步地解读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