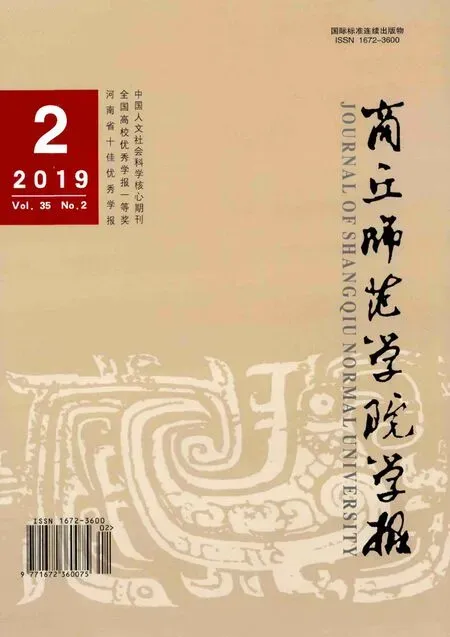方以智对《庄子·逍遥游》“小大之辨”的新诠
蒋 丽 梅
(北京师范大学 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学院,北京100875)
《庄子·逍遥游》由斥晏鸟之笑鲲鹏引出“小大之辨”的讨论,开启了庄子独具魅力的逍遥之境,其所开创的精神境界和审美意境为无数知识分子所向往。但是后世的注解在庄子关于小大问题的讨论上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庄子到底求大还是齐大直接影响到人们对逍遥境界的理解。而《庄子》文本中又存在着可供多种诠释的可能。一种看法是从庄子的用心之处提出小大问题的讨论的归旨是其远大之论,比如林希逸以为庄子“只是形容胸中广大之乐”[1]4,褚伯秀也从庄子时代的问题意识指出:“南华老仙盖病列国战争,习趋隘陋,一时学者局于见闻,以纵横捭阖为能,掠取声利为急,而昧夫自己之天。遂慷慨著书,设为远大之论,以发明至理,开豁人心。”[1]4而王夫之、释德清则主张“小大之辨”意在扬大抑小,《庄子》书中蜩与学鸠以小笑大中的嘲讽之意以及庄子追求高远浩渺的道境,都显示出庄子本人对大而化之的推崇。但《齐物论》中齐小大的主张,又为郭象阐释“小大之殊,各有定分”[2]13的观点提供了支持,郭象的各适其性的说法也成为解释“逍遥游”的重要主张。晚明遗民方以智在其《药地炮庄》中对“小大之辨”给出了创新的阐释,提供了一种反观大小问题的新态度,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角度来重新考察庄子的论述。
一、鲲鹏之喻
鲲化为鹏的故事在《逍遥游》中反复出现了三次,庄子通过相似的语句反复讲述这个故事,以虚构之真实勾画出逍遥的意境。《逍遥游》开篇鲲化而为鹏,两次所说的“不知其几千里也”,足可见其形容之大,更不用说能容摄此极大之鲲鹏的南冥与北冥。庄子对宏大的描述,引导读者想象从北往南的浩渺空间,从而摆脱自身形体的拘束,寻求精神的提升和超越,因此林云铭《庄子因》评论说:“‘大’字是一篇之纲。”但是对鲲的隐喻的解释又存在着小大两种争议。陆德明《经典释义》云:“鲲,音昆,大鱼名也。”《玉篇·鱼部》也说:“鲧,大鱼。”崔譔云:鲲当为鲸[2]3。船山也以为“其为鱼也大,其为鸟也大,虽化而不改其大,大之量定也”。将鲲视作大鱼,那么鲲鹏展翅就是事物之间因为形的变化而造成了生存空间的不同。但另一些著述又提出不同的看法,比如《尔雅·释鱼》:“鲲,鱼子。凡鱼之子名鲲,《鲁语》鱼禁鲲鲕,韦昭注:鲲,鱼子也。……段玉裁曰:鱼子未生者曰鲲,鲲即卵字。”[2]3这些看法将鲲比喻为鱼子或者未生之鱼子,这样一来,鲲化而鹏则成为一个由小变大的隐喻。
方以智对小大之辨的讨论首先体现为对“鲲”之字义的疏解,他说:“鲲本小鱼之名,庄用大鱼之名。鹏即凤也……《约机》曰:怒飞形容其鲲化,海运描写其冥徙。此表一收一放,两端用中,体用双冥,何分大小。”[3]103方以智承认“鲲”字本义是小鱼,但他又指出庄子用一种对比的手法,将鲲视作生活在几千里之大的北冥中的大鱼之称。鲲怒飞化而为鹏,鹏海运徙于南冥,虽然空间变化,但并不妨碍二者终为一体,因此不必就执着于何鸟何鱼。他说:
客曰:北冥有鱼,何故化鸟?愚曰:谓是鱼耶?客疑议,愚曰:谓是鸟耶?客曰:不是鱼不是鸟毕竟是何?愚踏狗子作声。[3]102
恕中举鲲鹏云:“若道有分别,本出一体。若道无分别,又是两形。毕竟如何评论?”击拂子云:“竿头丝线从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3]103
观我氏颂曰:“鲲鹏变化一身中,大块焚来恰负风。怜目怜心都罢却,满溪流水落花红。”[3]105
“踏狗子作声”是要让人们放弃追问鱼化为鸟的原因,因为这种设问本身就是将二者分为二物,“从君弄”“意自殊”就是要人摆脱“怜目怜心”的主观臆想,转而用事物之自然来观想鱼鸟一体而两形的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方以智的思考立足于《庄子》的文本,通过字义训诂的方法,却又能以“可参而不可诂”的态度跳脱于字句之外,以一种全新的角度来理解庄子之“大”。尽管方以智在破执方法上采用了禅宗的思考方式,但他最终用于破除小大二分的精神内核却仍然是儒家式的。通过对《周易》和《中庸》思想的援取,方以智将小大问题表述为以下两个不同的层次。
第一,小大本是一物。他说“一在二中,用二即一。南北也,鲲鹏也,有无也,犹之坎离也,体用也,生死也”[3]100。此处借用“坎离”来对南北和鲲鹏,北冥为阴寒之地,南冥则为阳热之地,正与后天八卦图中坎离卦的方位相合。坎为水,有隐伏之意,而离为火,象征着光明,成玄英所谓“北盖幽冥之地”“南即启明之方”,也有同样的意思。而从十二消息卦上来看,从坎到离正是从冬至到夏至阳气逐渐蒸腾的过程,正是“六月息”中的半年之意。方以智提出:“《道藏》以九万里配周天。三千,乃三十分之一。六月,乃十二之半。南北配坎离,此一合皆然,但不可执说耳。”[3]104这里方氏以《齐谐》所言“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来说鹏之所飞乃一周天之远,从北至南,正是周行而回到原点的过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说坎即是离,南即是北,而小大也是如此,即小即大而无分大小。
第二,不执小大,以中为尚。方以智以《中庸》“两端用中”之说来破小大之二分。他将《逍遥游》中的鲲鹏之事称呼为“鲲鹏之梦”,认为庄子后来在《齐物论》中以“大泽焚”“河汉冱”“疾雷破山”“飘风振海”等说法,用心良苦地破除人们单纯以大为美、以鲲鹏为庄子自况的理解。后来清代陆树芝也以为“旧解误认庄子以大鹏自寓,失之远矣”[4]1。而《齐物论》中关于至人不寒、不热、不惊之神通在于至人能无心不住,表现于外就是能做到“喜怒哀乐之未发”,符合中道之行。他还曾引虚舟子之言曰:“圣人游于未始有无之中,故随万物之相待,各无相待,而即以击之怒之培之徙之笑之悲之,即以游之息之而化之矣。是随大小长短得失之代错而本无累也。”要言之,不偏不倚地随顺万物之自然状态,才能使圣人在相待与无相待之间实现逍遥之游。
二、怒飞积厚
庄子的“小大之辨”还隐含着有待与无待的分歧。《逍遥游》中庄子以“绝云气、负青天”的恢宏气势,在视下中体察到“生物之以息相吹”,获得一种超越于具体事物之上的更为广大的视野。在这种论述中,似乎鲲鹏图南成了一个无需工夫、仅需领悟即能实现的境界,逍遥也因此成为无待的理想状态。这一结论直接影响到下文关于“小大之辨”中关于何为“适”的讨论。
方以智在注释中从《庄子》原文“怒而飞”与“积厚”二词着手,阐述了大小之辨的工夫路径。林云铭和褚伯秀都主张将“怒飞”与《齐物论》篇之万窍怒号、《外物》篇之草木怒生之“怒”联系起来,林氏以为“怒”乃用力之意,而褚氏则提出当把怒字与息字对看,体察其中万物并作且复归的深意。方以智征引了褚伯秀的观点,他指出:“怒字是炉鞲,不肯安在生死海中。有过人的愤懅,方能破此生死牢关,从自己立个太极,生生化化去也。”显然,方以智将个人情绪之愤怒与用力之努两个含义统一到个人气质的变化中,认为鲲化的动力根源于要挣脱生死的牢笼,实现生命的突破。他又说:“不变化,徒溺法身死水,乃化鸟而怒飞。”“死水”一词也屡见于《药地炮庄》,表达了方氏对他所处的社会时代的一种无奈与绝望,更展现出他因入禅而在生死大难上的勘破。他将这一情感贯注于对《庄子》的理解中:
愚曰:死水浸透,喷出南华,天亦是池,依然齑瓮。因视下而太息曰:是甚东西,指南为北?不知其几千里,犹是焦冥睫上,怒作什么?[3]104
这里,方以智将自己置于庄子的立场,将“视下”理解为一种更具超越性的领悟,将“几千里”之大比喻为“焦冥”之小,将南北视作一处,将天视作池。可以看出,在这种大小观上,方以智与惠施的主张达成了某种共识。他在“怒”的意义上肯定个人以“怒”为动力,不断追求,以实现精神境界的提高,但又在道的境界层面上否定“怒”的必要性,从而与《中庸》的中和之道保持一致。更进一步说,方以智在“体”的层面否定了“怒”的必要,却并不反对在“用”的层面上做“怒”的工夫。同样,他否定在“体”的意义上作小大之二分,但并不反对在“用”或“显”的层面上存在小大之差别,并主张通过“怒”的工夫来实现以小化大的可能。
方以智还对世人执小与穷大的看法提出了批评:“执小固为井鲋,穷大亦是丰蔀。望此第一篇,徒侈其大,非胶杯耶?”[3]106“井鲋”出自《周易·井卦》九二爻辞“井谷射鲋”,“丰蔀”出自《周易·丰卦》六二爻辞“丰其蔀”,王弼注曰“蔀,覆暧,鄣光明之物也”。方以智认为,执小与穷大都会造成认识上的障碍。与郭象不同,他直接以“以小笑大”来理解《逍遥游》中蜩与学鸠、斥晏鸟之笑。他反对将“二虫”理解为“鹏与蜩”,认为庄子本文还是通过大与小的对立来揭示二者不同的志趣。大鹏图南并非一味穷大,其中的“积厚”正是其工夫笃切之处,这种下学而上达的工夫,才是真正实现大鹏培风负天的翅膀。而鹪鹩之属则囿于见闻,没有向往的觉悟,更不用说工夫了。
方以智还将庄子所谓“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理解为“大知依然不离小知,大年依然不离小年”[3]107,将处于对待关系中的大小问题通过绝待加以创造性的解释。庄子通过对比彭祖、朝菌、蟪蛄等生命的长度来揭示时间的相对性,从而说明小大都是相对而言的,对事物大小的界定取决于用以对比的参照系。但另一方面,庄子又通过大之更大的描述向读者描述出一种超越于现实存在的更为广阔的时间与空间,激发人们向着更为高远的道境追寻。方以智则引用其外祖吴应宾的一句“灵椿只在骷髅边”[3]108,将庄子想象的“大年”拉入到他所描绘的骷髅世界中来。方以智还借取了佛教的“大千世界”的观念:一日月照四天下,覆六欲天、初禅天,为一“小世界”,而一各大千世界则包含有小、中、大三种“千世界”,故称三千大千世界。在这种时间观念对照下,冥灵与大椿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方以智指出“久亦是暂”“小与大同”[3]108,从而破除人们在对待关系中对事物加以区分的做法。方以智云:“大观之破小知,虚游之遣实累,虽状极于鲲鹏,妙至于御风,终对待中事耳,非逍遥之本致也。”[3]110在庄子那里,能够绝云气的鲲鹏只是实现了视下和南冥之游,仍未能实现与万物为一的境界。而从方以智的角度来讲,即便鲲鹏已实现了“无待”的逍遥,从“绝待”的层次来看,也还是未能真正领悟逍遥之乐。
三、逍遥真意
通过将“无待”转化为“绝待”,方以智从新的角度来阐释逍遥真意。在《药地炮庄》中,他引用了郭象之“自足”与支道林之“至足”这两个最具代表性的逍遥义,但又有自己创造性的理解。郭象认为:“大小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照此,鹏晏鸟各尽其分、各适其适,从它们自身的角度来说就是实现了同样的逍遥,而且彼此的逍遥是一致的,并无大小高低的区别。而支遁则以为,鹏失适于体外而晏鸟有矜伐于心内,未能当其所足、足于所足,所以都未能到达逍遥的境界。方以智并不同意支遁的看法,他试图去协调郭象的“自足”与庄子的高远境界之间的隔阂:
愚曰:“大小各适之中,不碍椿夭菌寿,亦不碍椿久于菌也。不碍鹏晏鸟一视,亦不碍鹏高于晏鸟也。故曰:本无大小,大大小小。单见本无大小者,是至人。全见本无大小,而雅言大小时宜者,是大人。”[3]109
方以智在继承郭象“各适”之说的基础上,肯定鹏晏鸟二者在境界上确实存在差异。他因此提出两种人格境界的区分,一种是至人,一种是大人。在他看来,能够领悟到本体之“本无大小”而又不妨碍发用上之“大大小小”,才算达到了逍遥的境界。
《庄子》的“大人”之说,主要见于《秋水》《知北游》《徐无鬼》《则阳》等篇,用以形容得道之人,有时也可与“至人”通用[注]《秋水》云“大人无己”,可与《逍遥游》“至人无己”说参看。。 “至人”一说在全书中多见,而“大人”则未见于内篇之中。方以智将“大人”与“至人”区分开来,并将前者凌驾于后者的境界之上。他在《浮山闻语》中也提出“大人因,君子复,众人循”,将“大人”视作君子人格之上的状态,这种看法根源于儒家典籍中“大人”的人格特质。《周易·文言》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将大人描述成为与天地、日月、四时、鬼神共在的最高存在;而《论语》中三畏之一的“大人”、《孟子》中大丈夫的人格等,也都将“大人”视为理想君子人格的重要形象。方以智将儒道二家的“大人”联系起来,以为大人是见得独体者,而独体“弥下纶上,旁费中隐”[6]218[注]方以智著、张永义注释:《药地炮庄笺释·总论篇》,华夏出版社,2013年,第218页。方以智以为:“曾知费隐一章,大小俱尽。”见《药地炮庄》,华夏出版社,2016年,第318页。,费、隐二字出自《中庸》“君子之道费而隐”,费指用之广而隐指体之微,是极广大而尽精微的意思,即人们既需在洒扫日用中发明本体,也需对遍在之体加以揭显。方以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指出单见、全见的分别,认为至人虽能见到大小之一如,却未能洞见世间大小变化中道的贯通,因此成为一偏之见。
方以智还运用了觉浪道盛的观点,将对大小问题的讨论拉回到未始有之初处:
杖人曰:“游于未始有之初,则己亦无有,又安有人?又安有万物之相待?又何有小大、动静、长短、得失之为累?始于鲲鹏之化,终于大树之块然极不能化者,亦能自得于无何有之乡,如神人之自神,视此又何物不可化,以共游于未始有无之天哉?”
道盛以为,逍遥之游应贯彻于未始有与有之中,而从万物未及有分的状态来看,事物并不存在大小、动静等对待,因此大小的观念是后生的。他还提出从具有生命自觉意识的鲲鹏到不具意识的大树,都有实现逍遥的可能,因此我们不应对“游”的主体进行区分。在《逍遥游》文末,方以智引用吴应宾的话说:“俗人执着,且激向那边去,因此执着那边,更是执着。”[3]118其目的正是要破除人们对大小的执着,以及对以大抑小、以小化大的执着,进而解除人们对逍遥之游的执着。
四、余论
方以智以体用和禅宗的喝问来止息历来学者对小大问题的纷争,他的“本无大小,大大小小”的结论,在继承郭象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缓解了《逍遥游》与《齐物论》之间的冲突。在不失庄子旨趣的基础上,他又能借助《周易》《中庸》的思想资源,将儒家“中”的观念引入对大小问题的讨论中,引导人们在洞悉独体、追求高远的方向上实现“中和”之大人理想。在对鲲鹏之喻的分析中,他既能充分意识到鲲鹏自身的局限性,又能借鉴鲲鹏图南之工夫,鼓励人们以生命之怒跳脱现实的束缚,激发其超越生死的斗志,从而不断变化气质,最终实现生命的超越与再造。清代刘凤苞在其《南华雪心编》说:“欲借鲲鹏变化,破空而来,为‘逍遥游’三字立竿见影,摆脱一切理障语,烟波万状,几莫测其端倪,所谓洸洋自恣已适己也。”[5]1方以智以绝待破除相待与无待,以超越偏见之“至人”,实现全见体用、不离体用的“大人”人格,他的看法对于我们重新审视《庄子》的理想人格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