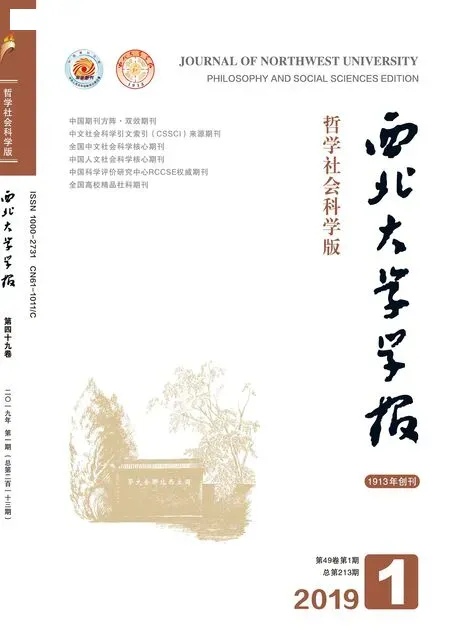竞“道德”、逐“智谋”与争“气力”
——先秦兵学文化的嬗变轨迹考察
黄朴民,赵立民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 北京 100872)
先秦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尝云:“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1](P487)他的本意是指人类社会处于不断发展过程之中,概括而言,可以分为“上古”“中世”和“当今”几个阶段。不同社会形态有各自活动的中心命题,而统治者则应根据变化了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世异则事异”[1](P486)“事异则备变”[1](P487)。由此可见,这段言辞是韩非子乃至整个法家历史发展观冼练而扼要的表述。当然,韩非子将“上古”的时间范围,界定在虚无缥缈的有巢氏、燧人氏阶段,乃是有问题的。且不说有巢氏等在历史上是否为真实的存在,即便有,与“道德”恐怕也扯不上关系,因为在当时,只会有残忍、暴虐的“血亲复仇”式的杀戮与灭绝。正如传说中的圣王尧、舜、禹攻灭三苗之战一样,战争的结果是“黎苗之王……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不夷于民”[2](P101)。所谓的“道德”,仅仅是后人理想主义化的虚幻想象而已!
但是,如果将韩非子所说的“上古”以及“中世”,在时间的坐标上稍作下移,“上古”对应殷商、西周及春秋前期;“中世”对应春秋晚期与战国前期;将所谓的“当今”,理解为韩非子自身所处的战国中后期,那么,我们可以发现,“上古竞于道德”,恰好吻合了商周“礼乐文明”体制下的社会政治基本特征,“中世逐于智谋”,正好为“礼崩乐坏”政治局面的形象写照,“当今争于气力”,在某种意义上,反映着由“争霸”走向“兼并”与“统一”的历史演变之大趋势。
这种时代趋势,投射到先秦时期的兵学文化,也能够从一个侧面体现其发展上的三个基本阶段:① 以《军志》《军政》《令典》“古司马法”等典籍为主要载体的创始阶段,即以“军法”为主体的初始阶段。此阶段的根本特征,就是“竞于道德”,即所谓的“以礼为固,以仁为胜”[3](P57)。② 以《孙子》的出现为标志的转折发展时期,《孙膑兵法》以及诸子论兵之作也属于这一阶段的延续。换言之,即以“兵法”形成并占主导地位为标志的高度成熟阶段。此阶段的特色为“逐于智谋”,也即《孙子兵法》中强调的,乃“兵者诡道”“兵以诈立”。③ 以《六韬》《管子》成书为显著特征的综合融汇、全面总结阶段。此阶段的中心主题,就是“争于气力”,在“大争之世”,在走向天下统一的前夜,要确保国家在战争中取胜,就必须注重加强国家的实力,只有具备强大的实力,方能统一天下,这叫做“多力者王”, 所谓“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4](P82)。
一、“以礼为固,以仁为胜”视域下的“竞于道德”
班固曾指出:“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5](P1762)这段话,其实高度概括了三代战争的基本特征,亦可视为是对韩非子“上古竞于道德”历史观念在军事领域得以印证的具体描述。
所谓“竞于道德”,反映在战争活动中,就是强调要具有规则意识、底线意识,“争义不争利”。至少在诸夏内部,如果彼此间矛盾到了激化的程度,非得动用战争这个最后手段来解决问题,也必须遵循一定的道德伦理原则,光明正大、公平合理进行交锋。商代的情况,受史料所限,已很难具体追溯和复原,西周以及春秋前期的状况,则可以通过《尚书》《周礼》《司马法》《左传》《国语》《逸周书》等传世典籍的记载,有限度地加以考察和认识。总体的精神,就是战争中的双方要贯彻与落实有关“礼乐文明”所规范的基本要求,遵循和执行“军礼”的相应规则,所谓“以礼为固,以仁为胜”,就是很形象的概括。
这些“竞于道德”的战争活动,大致体现为以下几个具体方面:第一,战争宗旨的明确性与崇高性,强调“吊民伐罪”“师出有名”。如,在《周礼·夏官·大司马》中就明确提出了“九伐之法”:“大司马之职,掌建邦国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国。制畿封国以正邦国,设仪辨位以等邦国,进贤兴功以作邦国,建牧立监以维邦国,制军诘禁以纠邦国,施贡分职以任邦国,简稽乡民以用邦国,均守平则以安邦国,比小事大以和邦国。以九伐之法正邦国,冯弱犯寡则眚之,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陵外则坛之,野荒民散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弑其君则残之,犯令陵政则杜之,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6](P1802-1803)“及师,大合军,以行禁令,以救无辜,伐有罪。”[6](P1811)
这“九伐之法”,在“古代王者司马法”中同样得以提倡,并得以在今本《司马法·仁本》中保留了下来,其强调战争的宗旨为“讨不义”:“贤王制礼乐法度,乃作五刑,兴甲兵以讨不义,巡狩者方,会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乱常、背德逆天之时,而危有功之君,遍告于诸侯,彰明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祷于后土四海神祗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后冢宰征师于诸侯曰:‘某国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师至于某国,会天子正刑。’”[3](P26)并且将这一原则提升到“仁义”的高度来予以最充分的肯定:“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3](P2)
因为“竞于道德”,那么在战争中,无异会多了许多道德禁忌,这包括不能够趁人之危,不允许违农时,让民众遭受苦难,不能够在严冬或酷暑这样的季节兴师打仗,等等。这在《司马法·仁本》中同样有明确的要求:“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3](P10)另,《太平御览》所载的《司马法》佚文对此道德禁忌亦有述及,所谓“春不东征,秋不西伐,月食班师,所以省战”[7](P97)。
由于“竞于道德”,在具体的战场交锋过程中,就必须尊重对手,奉行光明磊落、堂堂正正的原则,进退有节制,厮杀讲礼仪,杜绝诡诈狡谲的行为,摈弃唯利是图的做法。这就是《司马法·仁本》中所倡导的基本作战准则:“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义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终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时合教,以为民纪之道也,自古之政也。”[3](P17)《司马法·天子之义》中也有相似的主张:“古者,逐奔不远,纵绥不及。不远则难诱,不及则难陷。以礼为固,以仁为胜。”[3](P57)而《谷梁传·隐公五年》则简洁概括为:“伐不逾时,战不逐奔,诛不填服。”[8](P5142)同时,禁止在战场交锋时实施偷袭,如《司马法》逸文就指出:“无干车,无自后射。”[6](P1811)即不准冒犯敌国国君乘的车,禁止从背后攻击敌人。《左传·文公十二年》亦云:“死伤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险,无勇也。”[9](P4020)
如果说《司马法》《谷梁传》等的言辞还是属于战场“竞于道德”戒律在理论上的表述, 那么, 楚宋泓水之战后宋襄公的“高论”, 则是从具体史实的角度, 说明了这种主张,还是为当时一些人所信奉的, 拥有非常大的受众市场: “君子不重伤, 不禽二毛, 古之为军也, 不以阻隘也。 寡人虽亡国之余, 不鼓不成列!”[9](P3937)
正是因为“竞于道德”,战场纪律的相关规定,也不能不体现出一定的人文关怀。优待俘虏,救死扶伤,禁止残暴的报复行为也就成了执行战场纪律中的必有之义了。《尚书·费誓》曰:“无敢伤牿,牿之伤,汝则有常刑;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追逐,只复之,我商赍汝。乃越逐,不复,汝则有常刑!无敢寇攘,逾垣墙,窃牛马,诱臣妾,汝则有常刑!”[10](P542-543)《司马法》也指出:“冢宰与百官布令于军曰:‘入罪人之地,无暴神祗,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1](P26-27)
也是由于讲求“竞于道德”,在战争善后问题上,胜利一方对敌手也并非赶尽杀绝,除恶务尽,而是能够在确保胜利的前提下,保留对手的生存机会,让其维系自己的血胤。这就是所谓的“兴灭国,继绝世”[11](P5508)“既诛有罪,王及诸侯修正其国,举贤立明,正复厥职”[3](P27)。武王灭商,乃册立纣王之子武庚,继续奉殷商之血祀,就是例子。尽管,周武王并不信任武庚,派遣管叔、蔡叔、霍叔在旁监视与控御,是为“三监”,但是,在形式上毕竟是做到了“正复厥职”。即使武王逝世后,“三监”与武庚勾结,发动叛乱,逼得周公只好率师东征平叛,但等到平息叛乱之后,还是寻找到纣王庶兄微子,封建诸侯,国号为宋,以继续保持殷商的血胤相传,在整个西周与春秋,宋国于周室为宾客,爵为上公,地位有其特殊性。这也是日后诱发宋襄公蠢蠢欲动,萌生充当春秋霸主的原因之一。宋国的情况不是个案,郑庄公复许,楚国恢复陈、蔡两国,皆相类似。参之以《左传》,信而有征。鲁昭公十三年(前529),楚“平王即位,既封陈、蔡,而皆复之,礼也。隐大子之子庐归于蔡,礼也,悼大子吴归于陈,礼也”[9](P4502)。又,鲁昭公十六年(前526),“楚子闻蛮氏之乱也与蛮子之无质也,使然丹诱戎蛮子嘉杀之,遂取蛮氏。既而复立其子焉,礼也”[9](P4513)。又,鲁哀公二十四年(前471),“邾子又无道,越人执之以归,而立公子何”[9](P4738)。
孟子曾有知人论世说,只有从“竞于道德”的立场考察,我们才能对人们有关宋襄公战争礼仪的评价抱有“同情之理解”,明白为什么宋襄公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迂腐做法会被一些人推崇备至,甚至夸张到“文王之战”的地步,《公羊传》言:“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12](P4905)在《公羊传》看来,宋襄公成了“有王德而无王佐”的明君,甚至周文王所从事的征战也没有超过宋襄公这种举动。司马迁也在《史记·宋微子世家》中同出一辙的赞赏宋襄公:“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宋襄之有礼让也。”[13](P1971)
因为无论是《公羊传》的作者还是司马迁,他们都能回归历史现场,了解和认识“竞于道德”,乃是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这个时期的战争有其特色,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所以,不能以当下的逻辑去简单地否定历史上特定阶段的逻辑。更何况,这种“竞于道德”的历史事实,其内涵还具有抽象的价值意蕴,会有时空上的超越性,换言之在绝对的功利标准之上,还有绝对的道德标准!
二、“兵以诈立”时代主题下的“逐于智谋”
《孙子兵法·谋攻篇》云: “将者, 国之辅也。 辅周, 则国必强; 辅隙, 则国必弱。”[14](P52-53)因此, 先秦兵书普遍关注将帅队伍的建设, 其中, 尤其重视身为将帅者的个人素质修养与培育。 不过, 从其所论将帅基本素质的内容要求与排列次序来考察, 我们可以发现, 它其实透露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与价值取向。 如, 《孙子兵法·计篇》言将有五德: “将者, 智、 信、 仁、 勇、 严也。”[14](P8)梅尧臣注曰: “智能发谋, 信能赏罚, 仁能附众, 勇能果断, 严能立威。”而《六韬·龙韬·论将》则把将帅应具备的素质归纳为“五材”。 “所谓五材者, 勇、 智、 仁、 信、 忠也。 勇则不可犯, 智则不可乱, 仁则爱人, 信则不欺, 忠则无二心。”[15]
至于《孙子兵法》,情况则有明显的不同。在孙子看来,一位优秀将帅的最重要素质,乃是“智”。“智能发谋”,身为将帅者,不管如何仁爱,无论怎样厚道,如果没有一个聪慧的脑袋,都毫无意义,毫无价值。因为只有睿智,方能高明地搜集与甄别各种信息;只有睿智,方能辩证地分析事情的利弊得失;只有睿智,方能深刻地洞察事物的发展趋势;只有睿智,方能全面地评估敌我实力的优劣短长;只有睿智,方能正确地选择战略进攻的突破方向。所以,在“将有五德”中,“智”毫无疑问处于首要的位置,对其余“四德”,有着统率与引领的关键性作用。而这种以“上兵伐谋”为纲领的“五德”观,恰好从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体现了孙子所处的春秋战国之际,也就是所谓的“中世”的最显著、最突出历史文化特征,正如韩非子所概括的那样,“中世逐于智谋”!
众所周知,自春秋晚期始,战争的残酷性也达到了新的程度。《墨子·非攻下》云:“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堙其沟池,攘夺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刭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16](P218)即是形象的描述。
但春秋后期战争最大的新特色,还在于当时战争指导观念的重大变化。这就是在“尚智重谋”历史大趋势引领之下,“道德至上”“宗仁本义”的君子之战渐渐淡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诡诈”战法原则在战争领域内的普遍运用,用班固的话说,便是“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5](P1762)。
声东击西,示形动敌,兵贵神速,出奇制胜,后发先至,兵不厌诈,设伏诱敌,突然袭击,避实击虚,奇正相生,攻其不备,诡诈奇谲的战争指导,风靡一时,独领风骚。在这里我们已经很难看到过去中原战争中经常遵循的“成列而鼓”的做法,也不曾见到像鄢陵之战中郤至遇到敌方君主必下战车,向敌君致敬,“免胄而趋风”[16](P4165)的现象。而所谓“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亦由此而得到历史的验证。
这种战争指导观念的变革,其最深厚的文化土壤,就是时代主题业已由“竞于道德”转变为“逐于智谋”了。所谓的“兵者诡道”“兵不厌诈”“兵以诈立”,等等,本质上都是“崇智尚谋”在战争这一特殊领域的集中体现!这不仅反映在当时的战争实践上,也体现在这一时期的军事理念建树方面。
既然不再是“竞于道德”,已经是“逐于智谋”,那么,这就意味着进入了新的时代。而新的时代,则势必会有新的战法,在这个过程中,武器装备的进步,其意义也许特别值得关注。换言之,武器装备的发展和作战方式的改变,这应该是“逐于智谋”时代特征得以形成的重要推手。以前的作战方式是车战,车战必须先摆阵势,不摆好阵就不能打,这是密集大方阵传统战法,机动性很差,适合于大家客客气气交手过招。现在步兵重新崛起,又成为军队的主力兵种,它比较灵活,机动性要强得多,可以不必像车兵那样先排阵后开打。后来出现的骑兵更是雷厉风行,更讲究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兵种变了,作战方式也要随之变化,作战方式变了,则作战观念也得跟着变,这是多米诺骨牌效应。另外,地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主要在是黄河中下游平原打,大平原地势平坦,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车战最合适不过,可现在到了丘陵地带、江河湖泽地带,就根本不能再用以前那种排兵布阵的方式了,《司马法》所说的“车不驰,徒不趋”[3](P74)全成了过气的战法,“竞于道德”的历史主题既然改变了,那么,伴随它而生的“军礼”自然也会随之退出历史舞台。最最要命的是,车战在这时遇到了一个最大的克星,就是强弩的出现,“积弩齐发”成为当时一种威力巨大的战法,驾车的马匹、车上的甲士全成了飞蝗般箭镞的活靶子,贵族再有涵养,也经不得这么大的杀伤,只好不情愿地与“道德”说“拜拜”了[17]。
另外,战争地域的扩大,对“逐于智谋”风尚的形成也有显著的影响。春秋前期,打来打去,就是这么有限的一块战场,就是齐国、晋国、秦国、楚国,还有郑国、宋国、鲁国,等等。可是到了后来,吴国、越国、中山国都先后冒出来了,战场开始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淮河流域伸展。这些战场上的新角色没有背上“道德”那么沉重的包袱,这样战争中就不再有那么多的君子之风,诡诈之道越来越风行,而主张保持贵族的尊严,提倡打堂堂正正之仗的宋襄公成了不合时宜的丑角,只配给自诩高明的人嘲笑、讥讽了。
紧密对接仪器仪表行业需求,培养学生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现代科学创新意识,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培养从事多领域的智能仪表设计、开发的智能仪表研发型人才,培养在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行业进行过程控制仪表选型、安装、调试与维护的仪表高水平应用型人才[3]。
孙武、伍子胥、范蠡等人的相关论述,是主要代表。孙子战争观的诡道原则,应该说是对战争本质属性的深刻反映。战争的艺术魅力在于,战争双方斗智斗勇,隐形藏真,欺敌误敌,变化莫测,先立于不败之地,而不放过任何可以击败对手的机会。所有这些,都表明了战争是一种多变、灵活,无固定模式,不讲究繁礼缛节的特殊社会活动,诡诈奇谲是战争的本质特征。而孙子“兵以诈立”的思想,其核心乃是强调以灵活的战术,快速的机动,巧妙的伪装来造就优势主动的地位,成为胜利的主宰,“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14](P128-129)。显而易见,《孙子兵法》注重于探讨作战指导,并指出,“兵者,诡道也”[14](P12),这是对讲求“道德”,申明“军礼”做法的革命性变革。它无疑是对“军礼”传统的彻底否定,是战争观念上的重大突破,一次创新,一次革命。换句话说,孙子的诡道论,深刻揭示了战争活动的本质属性,是中国古典兵学思想发展上的一次质的飞跃,也是《孙子兵法》区别于“宗仁本礼”古司马法,而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兵学经典的重要标志。
具体而言,在战争目的方面,《孙子兵法》明确提出“伐大国”;在战争善后上,《孙子兵法》主张拔“其城”,隳“其国”;在作战方式上《孙子兵法》一再强调“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14](P218);在后勤保障及执行战场纪律方面,《孙子》则宣扬“因粮于敌”,主张“掠于饶野”[14](P220)“掠乡分众”[14](P130)。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均反映了春秋后期的战争指导思想,较之于“竞于道德”的西周与春秋前期,已经有了许多显著的变革、发展和差异。南宋兵学理论家郑友贤曾强调指出:“《司马法》以仁为本,孙武以诈立;《司马法》以义治之,孙武以利动;《司马法》以正不获意则权,孙武以分合为变。”[14](P289)这显然就是对“竞于道德”与“逐于智谋”所导致的时代差异性的高度概括。
伍子胥、范蠡等人的战争指导观念也和孙子基本一致,也不再是局囿于“竞于道德”,而完全立足于“逐于智谋”了。如,伍子胥提出高明卓越的“疲楚误楚”方针,主张“亟肄以罢之,多方误之”[9](P4617),这显然就是“变诈之兵”勃兴条件下的产物,是“逐于智谋”的一个形象诠释。又如,范蠡的兵学思想,同样充满了“逐于智谋”的时代精神,他一再主张“随时而行,是谓守时”[2](P575),强调要通过各种积极的手段,转化双方的优劣态势,剥夺敌人有利的条件,暗中增强己方的实力,从而摆脱被动,占据主动的地位,即所谓“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2](P585)。他提倡“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2](P578)“得时无怠,时不再来”[2](P584)。他后发制人,把握战机,及时出击的思想,同样属于进步的战争指导观念,是“逐于智谋”的生动写照。这些思想来源于春秋战国之际变化了的战争实践活动,同时进而更好地指导着新形势新条件下的战争,从而使春秋战国之际的军事活动呈现出充满生机的新面貌。
三、“争于气力”与战国中后期的兵学观念变革
刘向称战国形势的特点是:“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18](P2)从吴越战争到晋阳之战,这种局面,到战国中后期尤其明朗化。其最大的特色,就是春秋时期争霸战争的终结,战国时代以兼并为本质的战争的到来。
兼并战争的激烈和残酷程度要远远超过以往的争霸战争,这一点早在晋阳之战中就表现得十分明显。对此,《孟子·离娄下》有非常准确而扼要的概括:“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19](P5920)这种局面,到战国中后期尤其明朗化。当时的战争,已从兼并的角逐进一步发展为统一的追求了。“天下恶乎定?定于一。”[19](P5920)而“定于一”的根本途径唯有一个选择,那就是通过残酷的杀戮与殊死的较量。
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兵学文化的主题,不仅“竞于道德”早已成为了明日黄花,而且连“逐于智谋”也是时过境迁了。因为,“上兵伐谋”固然美妙,但现实的状况是,实力才是确保在战争中夺取胜利的根本条件,没有强大的实力,那谋略就无所施展其能,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子所说的“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14](P64),说到底,就是实力优先原则。这一点,在兼并与统一战争中表现得尤为显著。于是乎,战国中后期各诸侯国尽管还注重于“伐谋”“伐交”,但其战略运用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了“伐兵”与“攻城”上来了,“争于气力”遂成为了当时兵学文化的最大主题,先秦兵学的发展,合乎逻辑地进入了第三阶段。
在“争于气力”的特殊时代,当时兵学家的主流观点,就是要顺应这个历史潮流,充分肯定战争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所谓“大明发而万物皆照,大义发而万物皆利,大兵发而万物皆服”[15]。
“争于气力”,要求人们对兵学的功能与作用,有清醒的认识与准确的定位。这方面,当时的兵家曾作过深刻的阐述,如《商君书》认为,当时的社会正处于武力征伐的时代,天下大乱,群雄兼并,一日无已,“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4](P54)。在这样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战争乃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务,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安危存亡:“名尊地广以至王者,何故:[战胜者也]。名卑地削以至于亡者,何故?战罢者也。”[4](P108)要立足天下,称王称霸,就必须通过战争,“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4](P20)。《商君书》认为这才是“适于时”的做法。为此,其积极主张战争,反对所谓“非兵”“羞战”之类的论调,强调“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4](P107)。
又如,韩非子也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决不能指望别国不来侵犯,而要增强自己的实力,使自己强大得足以令敌国不敢轻启战端:“不恃外之不乱也,恃其不可乱也。”[1](P520)指出这乃是“王术”,即“争于气力”、统一天下的策略和战略。
再如,《管子》同样强调战争的重要作用,肯定战争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管子》认为战争直接决定着君主地位的尊卑,国家处境的安危,是实现君主尊贵、国家安定的重要途径:“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诛暴国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则兵者外以诛暴,内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20](P534-535)《管子》指出,战争虽然谈不上高尚,但在当时天下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关头,它却是“辅王成霸”的基本手段,不可或缺:“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20](P317)所以,《管子》要求明智的君主务必“积务于兵”,注重和开展军事活动。指出假如“主不积务于兵”,等于是将自己的国家拱手交给敌人。基于这一认识,《管子》反对无条件的偃兵息武,指出兵不可废置。即便是在黄帝、尧、舜那样的盛世,都不曾废弃兵事,那么“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顺,而求废兵,不亦难乎”[20](P314)。所以宋钘 、尹文提倡的“寝兵之说”和墨家鼓吹的“兼爱之说”,在《管子》作者的眼中,纯属于亡国覆军之道,必须痛加驳斥:“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20](P79)
不仅三晋法家与齐地法家清醒认识到所处的“争于气力”环境,因而高度“主战”与“重战”,其他学派在这方面也不乏类似的识见,像黄老学派也主张“争于气力”“以战止战”;《经法》就明确肯定战争的意义与价值:“所谓为义者,伐乱禁暴,起贤废不肖,所谓义也。[义]者,众之所死也。”[21](P78)其必定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造就“地广而民众兵强,天下无敌”[21](P18)的局面。
当然,“争于气力”,并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必须有切实可行的措施与手段,通过相应的途径,达到自己预定的战略目标。在当时的兵家看来,只有进行农战,致力于富国强兵,才能够真正拥有从事战争的物质基础与制胜条件。《商君书》《韩非子》《管子》对此均有充分的阐述,其明确表示:“凡战法必本于政。”[4](P68)“内政不修,外举事不济。”[20](P351)他们均认为,要确保国家在战争中取胜,就必须注重加强国家的实力,只有具备强大的实力,方能统一天下,这叫做“多力者王”。他们也明确指出,国家的强盛与否是由国家的实力所决定,并认为恩德也产生于实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4](P82)这就是“政胜”:“政久持胜术者,必强至王。”[4](P70)
而所谓“政胜”的具体表现,乃是实行“农战”。为此,当时的兵家一再强调了从事农战的重要性,“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22],从而造成“不暴甲而胜”[22]的优势地位。“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4](P46)“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4](P22)甚至认为,农战是富国强兵,实现霸、王之业的关键:“能行二者于境内,则霸、王之道毕矣。”[4](P139)相反,如果不进行农战,则必危及国家,丧失兼并事业的主动权:“彼民不归其力于耕,即食屈于内,不归其节于战,则兵弱于外。入而食屈于内,出而兵弱于外,虽有地万里,带甲百万,与独立平原一贯也。”[4](P138)在他们看来,农耕是攻战之本,两者不可分割,重战和重农必须结合。因为农业生产不仅为战争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人民致力于农耕,才会安土重居,既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也可以驱使民众为保卫国土而殊力死战。“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4](P25)
因为在他们看来,实行“农战”的直接效果,就是富国强兵,“能越力于地者富,能起力于敌者强,强不塞者王”[1](P520)。“国富”是“强兵”的基础,而“强兵”则是保证国家安全的根本条件。一旦做到了富国强兵,那么克敌制胜便有了基本保障:“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20](P924)反之,如果经济落后、军力不强,那就会直接导致国家危亡,不可不加以警惕:“战士怠于行阵者,则兵弱也;农夫惰于田者,则国贫也。兵弱于敌,国贫于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1](P302)
要“争于气力”,那么,思想的统一,政令的贯彻,就至为关键了。所谓“兵战其心者胜”[1](P519),即必须让民众树立起战争的观念,“服战于民心”[1](P519),重视和积极参与战争活动。《韩非子·心度》中所说的“先战者胜”正是此含义。这里的“先战”,就是“战其心”,使民众的思想专一于战争。所以必须“壹赏”“壹刑”“壹教”。所谓“壹赏”,就是“利禄,官爵,专出于兵,无有异施也”[4](P96);所谓“壹刑”,即统一刑罚,“刑无等级”;所谓“壹教”,就是“当壮者务于战,老弱者务于守,死者不悔,生者务劝”[4](P105),即把教育统一到“乐战”上来。使得“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4](P105),造成“怯于邑斗,而勇于寇战”[4](P68)的社会风气。韩非指出,一旦做到这三点,便可令行禁止,上下一致,无敌于天下了:“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必行,壹教则下听上。”[4](P96)是谓“兵战其心者,胜”。换言之,这在物质上则是要奖励耕战,“富国以农,距敌恃卒”[1](P492),其明确主张“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赏”“显耕战之士”,以此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同时,修明政治,信其赏罚,发展经济,鼓舞士气,“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1](P497)。一旦真正做到了这一点,那就能够“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1](P494),拥有了统一天下的“王资”。
总之,到了战国后期,随着兼并战争的日益激化,先秦兵学的主题又悄然有了新的转移。“竞于道德”基本失语,“逐于智谋”也逐渐弱化,代之而起的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争于气力”,传统兵家实际影响力有所削弱,而法家人物的兵学观点则把持了话语权。这是历史的必然,但同时也是历史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