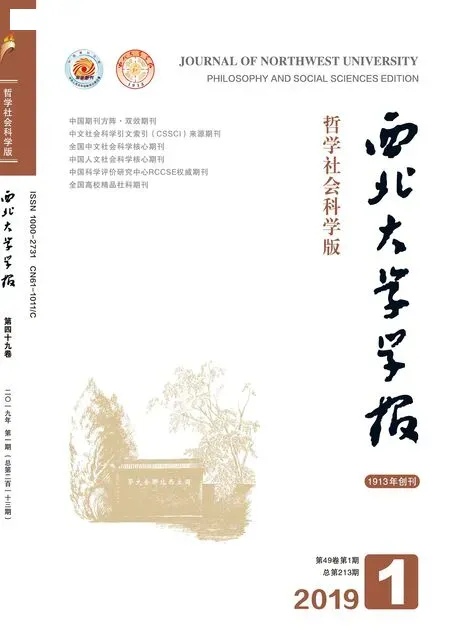北宋中后期兵学发展特征论略
王军营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两宋王朝长期武事不振,频受外来民族军事威胁,最后皆亡于外患。然而,兵学发展却取得辉煌成就,形成了一次中国兵学史上的高潮。目前,学界有关北宋中后期兵学发展问题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大多偏重宏观粗线索条勾勒[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刘庆《“文人论兵”与宋代兵学的发展》,《社会科学家》1994年第5期;陈峰《宋代主流军事思想及兵学批判》,《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王联斌《宋代兵书及其军事伦理思想》,《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戴伟华《北宋文士与兵学关系述略》,沈松勤主编《第四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这些研究因研究主旨区别,对北宋中后期的兵学发展只不同程度地有所涉及。,或对具体军事著作或特殊军事人物进行专题考究[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专著编写组《中国历代军事思想》,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赵国华《中国兵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姜国柱《中国军事思想通史·宋元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此外,尚有众多考究典型人物军事思想的专篇论文。,尚缺乏置于历史环境中,进行必要的整体与系统解剖,从而形成深入认识[注]魏鸿的《宋代孙子兵学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就宋代孙子兵学的时代背景、发展轨迹、文献学考察、理论发展与军事实践等进行系统考究,是笔者目前所见社会历史环境与兵学理论研究结合较好的一部专著。。
一、北宋中后期的兵学发展
(一)政治社会环境
北宋立国后,逐渐结束了晚唐五代以来长期分裂割据局面,采取多种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宋朝统治。太祖、太宗及其后继者“惩创五季而矫唐末之失策”[1](P789),大力整肃军队,将军权紧握手中。王夫之说,宋太祖因“怀黄袍加身之疑,以痛抑猛士”[2](P120),在宋初便采取了“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3](P255)。由于“崇文抑武”国策长期推行,北宋社会长久弥漫着重文轻武的风气。“时时以五代动乱为戒的宋廷,更难以放松对禁军的警惕。以文制武的制度格局、种种限制、多方猜忌,事实上并非由于‘轻武’;而在这样的国家政策导向下,社会上则有重文轻武的观念流行。”[4]“澶渊之盟”后,宋廷进一步将内部稳定和文治建设作为朝政主要目标,一度明令禁止研习兵书。景德三年(1006),真宗颁布诏书:“天文兵法,私习有刑,著在律文,用防奸伪。”[5](P734)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张方平说:“国家用文德怀远,以交好息民,于今三纪,天下安于太平,民不知战,公卿士人耻言兵事。”[6](P378)士大夫讳言兵事,甚至写诗作文也很少涉及军事领域。
北宋中叶以后,辽和西夏两大强敌同时威胁北方。宋仁宗朝,宋军数次与西夏开战,屡屡惨败,西北边患严重。苏轼云:“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无意于兵。将士惰偷,兵革朽钝,元昊乘间窃发,西鄙延安、泾原、麟府之间,败者三四,所丧动以万计。”[7](P1050)宋廷不得不开始重视军事问题,倡导兵学研究。如此以来,社会上出现了谈兵论战的热潮。苏舜钦云:“臣窃见自西寇逆节,天下言兵者不可胜计。”[8](P134)晁公武说:“仁庙时,天下承平久,人不习兵,元昊既叛,边将数败,朝廷颇访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9](P634)文人儒士群体从之前的冷漠看待武力、军事因素,逐渐转变为热衷关注军事问题,纷纷谈兵论兵,从而形成一种社会风尚。与此同时,兵学发展也走出低谷,逐渐发展繁荣。
北宋中后期,神宗当政后,锐意改革,决心富国强兵。所谓“神宗一改真宗、仁宗、英宗诸朝以防御西夏为主的战略,转而为积极进取”[10](P56-57),“神宗是北宋中后期最想有所作为的皇帝,一心想消灭西夏和辽朝,恢复汉唐疆域”[11](P44)。司马光说:“及神宗继统,材雄气英,以幽、蓟、云、朔沦于契丹,灵武、河西专于拓跋,交趾、日南制于李氏,不得悉张置官吏,收籍赋役,比于汉、唐之境,犹有未全,深用为耻,遂慨然有征伐、开拓之志。”[12](P8689)较之前期,宋廷政治趋于外向,更加重视军备武力建设,对外也陆续采取了一些军事行动。在宋廷的重视和大力倡导下,兵学发展更趋于高潮。
(二)兵学发展概况
北宋中后期,“是宋代军事思想的重要发展时期”[13],兵学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
唐宋时期,“武举制度的创立,武庙、武学的设置,《武经七书》的刊行等使得兵学超越私家著述,跨入正规教育行列,更促进了兵学的发展”[14](P360)。武举作为常举制度大致于唐代前期创设,武则天“长安二年(702)正月十七日敕:天下诸州宜教武艺,每年准明经、进士贡举例送”[15](P1030)。但经唐末五代战乱,至北宋前期,数十年间武举制度中断不存。“唐设武举,以选将帅。五代以来,皆以军卒为将,此制久废。天圣七年(1026),以西边用兵,将帅乏人,复置武举。”[16](P44)据《宋会要》载:“仁宗天圣七年(1029)闰二月二十三日,诏置武举。”[17](P5586)至宋神宗朝,重新恢复后的武举已步入正轨。武庙设置源自唐初,“贞观中,以太公兵家者流,始令磻溪立庙”[18](P379)。宋承唐制,武庙祭祀也沿袭下来。北宋中期,为加强武备与国防建设,宋廷也积极探索军事人才的选拔和教育。在仁宗庆历三年(1043)五月,“诏置武学于武成王庙,以阮逸为教授”。八月,因一些臣僚反对而废止。神宗“熙宁五年(1072),枢密院言:‘古者出师受成于学,文武弛张,其道一也,乞复置武学。’诏于武成王庙置学”[19](P3915)。于是,武学制度在宋代渐趋完善。此外,宋廷组织各方人力,陆续修纂、校刊,完成了系列大型兵书,并积极从民间访求知兵士人。所谓“宝元、康定之间,元昊叛。诏书求才谋之士,于是言事自荐者甚众。辄下近臣问状,高者除郡从事,其次补掾史,且数百人”[20](P737)。总之,在宋廷各种重视军事的政策、措施推动下,兵学发展于北宋中后期渐趋高潮。
北宋中期, 西夏元昊屡次统兵侵宋, 朝野各方士人聚焦于西北边患, 一时间谈兵论兵蔚然成风。 许多文人士大夫大谈战术策略与用兵之道, 关注边防和军事问题。 其中颇为知名者如范仲淹、 欧阳修、 宋庠、 宋祁、 张方平、 富弼、 文彦博、 尹洙、 包拯、 苏颂、 梅尧臣、 王安石、 司马光、 沈括、 苏洵父子等,均有言辞策论涉及军事,或撰有兵学著作。此风延至北宋晚期,正如秦观所谓:“今世之学兵法者,肩相摩,袂相属。”[21](P633)
如此以来,兵学发展取得了众多显著成果。除当时诸多臣僚颇有影响的涉兵策略篇章与琐碎言辞外,官方和私人编写、校订、注释和撰述了数量惊人的兵书专著。
仁宗庆历七年(1047)六月,曾公亮、丁度等奉诏组织了一批学者,编成《武经总要》四十卷,由皇帝作序,成为中国军事史上一部以“武经”命名的最早官修兵书。此时还出现了多家《孙子》注释之作,如时人所谓:“仁庙时,天下承平久,人不习兵,元昊既叛,边将数败,朝廷颇访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故本朝注解孙武书者,大抵皆当时人也。”[9](P634)其中,梅尧臣、王皙、何氏、张预等人注释作品,后来被采入《十一家孙子注》而刻版广布,直至流传当今。作为帝王的宋仁宗,另撰有兵书《攻守图术》三卷[19](P5283)。当同知枢密院事韩亿“又言武臣宜知兵,而书禁不传,请纂其要授之……于是帝亲集《神武秘略》,以赐边臣”[19](P10298-10299)。此外,丁度“上《庆历兵录》五卷、《赡边录》一卷”[12](P3770)。王洙撰《武经圣略》十五卷[注]笔者按:《武经圣略》很可能是《经武圣略》之误书,亦即《三朝经武圣略》,参见(宋)晁公武撰、孙猛校正《郡斋读书志》卷一四“《武经圣略》十五卷”条下笺注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43页)。,张预撰《百将传》十卷[9](P644),另有《兵法精义》《庆历军录》[22](P20)等多种见诸名称的兵书。
神宗也多有亲论军事文辞,“皆赐中书密院及边臣手札,言攻守秘计”,哲宗元祐时被综编为四十卷[17](P3206)。元丰三年(1080)四月,神宗特诏命国子监司业朱服等人专门负责校订“武经七书”,“诏校订《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版行之”[12](P7375)。以此作为官方武学教材。此时,私家军事著作也为数不少。参与校刊“武经七书”的武学博士何去非撰有《何博士备论》《司马法讲义》,施子美《施氏七书讲义》,张商英托名黄石公,撰《素书》一卷。熙丰变法的主将之一吕惠卿,撰有《三略素书解》一卷。吴章撰《司马穰苴兵法注》、张载撰《尉缭子注》等。这些也都在引用古代战例和兵学前贤言论基础上,阐发自己的理论见解。结合西北战争实践,王韶撰《熙宁收复熙河阵法》三卷,沈括、吕和卿等于熙宁八年(1075)上《修城法式条约》二卷等[13]。
二、北宋中后期兵学理论基本特征
北宋中后期,兵学迎来兴盛局面。在宋廷大力倡行下,朝野众多士大夫积极研究军事理论,推动了兵学长足发展。前代就兵学一些重要内容,如将帅、谋略、敌情及战阵等,虽有涉及或论述,但在体系上并未明确孰重孰轻。然而,北宋中后期的兵学理论内容却较明显地体现出一些基本特征。
(一)普遍重视选任将帅
仁宗庆历时官方编修的大型兵书《武经总要》,卷一首篇即《选将》,可见时人对将帅问题的重视程度。其书云:“传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又曰:君不择将,以其国与敌也。由是言之,可不谨诸?古者国家虽安,必常择将。”[23](P19)作为官方颁布的兵学典籍,该书集中反映了当时主流社会所偏重的军事理论。
众多私家自撰或注解、发挥的作品,无疑也普遍继承、发展了传统兵学重视将帅的内容。在《强兵策》中李觏多番论述将帅问题,引述孙子“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之观点,反对君主对将帅权力过多干预和控制,说:“今兹兵兴矣,将用矣,惟上心旷然,与忠贤为一体,无置节目于其间,则将才入神,军锋如雷,功业亦可成也。”[24](P167)苏洵《权书》首篇即阐述“为将之道”[25](P29),且云:“将战必审知其将之贤愚。”[25](P34)晁公武记王洙编《武经圣略》云:“宝元中,西边用兵,朝廷讲武备。是时洙奉诏编祖宗任将、用兵、边防事迹,分二十门。”[9](P643)即“任将”属其重心内容。何去非说:“盖军之所恃者将,将之所恃者气。以屡胜之将,持必胜之气以临三军,则三军之士气定而情安,虽有大敌,故尝吞而胜之。”[26](P488)“战必胜攻必取者,将之良能也。良将之所挟,亦曰智、勇而已。”[26](P537)而张预编《百将传》,“观历代将兵者所以成败,莫不与孙武书相符契,因择良将得百人,集其传成一书”[9](P644)。“宋人托名诸葛亮所著的《将苑》凡50章”[27],更是专门讨论为将之道的兵学著作。
另外,北宋中期以后,众多士大夫围绕边疆军事问题纷纷谈论应对之策,主要内容即有将帅问题。苏舜钦说:“汉之乱,由后族典北军;唐之乱,由中人领神策。禁旅之官,不可不慎也。近年不择其才,以宠近臣,何以魁壮皇武,备御非常乎?”[8](P120)张方平认为:“用军决胜,在乎统帅,统帅不一则威令不行,不相为用,非成功之势也。”[6](P265)尹洙认为:“夫善御戎狄者,在乎任将帅,训士卒,积金谷,利器械。无事则守,有警则战。故守则有威,战则必克。无他道也,重威严备而已。”[28](卷二三《备北狄》)庆历元年(1041)三月,宋夏好水川之战失败后,范仲淹即上《论不可乘胜怒进兵奏》,谏止报复性用兵,贸然对夏开战,曰:“自古败而复胜者,盖将帅一时之谋,我既退衂,彼必懈慢,乘机进战,或可图之。”并引述《孙子》“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故明主谨之,良将警之,安国之道也”[29](P767)。英宗治平二年(1065)正月,时任参知政事的欧阳修举荐孙沔为帅臣,上言:“谅祚猖狂,渐违誓约。朝廷御备之际,先在择人。”[12](P4935)在《择帅》中,张载针砭时弊,认为:“择帅之重,非议者得言。本朝以武臣典强藩,轻战忘患,故选用文臣节制,为计得矣。然冦雠入境,则举数万之甲付一武人,驱之于必战之地,前后取败,非一二而已。然则副总管之任,系安危胜负之速,甚于元帅,而大率以资任官秩次迁而得,窃为朝廷危之。”[30](P358)苏轼说:“窃以为天子之兵,莫大于御将。”[7](P93)
因此可说,传统兵学内容中大量关于将帅选拔任用、识人辨才、素质培养等理论精髓,被传承下来,并进而得到发展。在当时的兵学著作与谈兵文辞中,这些内容即大量呈现出来。
(二)重视兵机谋略方面
兵机谋略属传统兵学理论基本内容之一,宏观地看,历代传承大体限于特殊的社会上层人群。然而,北宋中后期发生了较大变化。朱东润说:“庆历而后,有识者多言陇右,不可谓不知缓急矣。”[21](P1)北宋以来科举制逐渐完善,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数量急剧增加。随着边疆危机出现,士大夫谈兵论兵成为一种风尚。朝野士人关注兵法谋略,相比之前范围层次更广、更深,上升至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宋仁宗在御制《武经总要叙》结尾曰:“出提金鼓付之阃事,取鉴成败可以立功,贵伐谋而无幸胜,善统众而无专勇。”[23](P7)明确指出谋略是将帅统兵作战的重要条件,而其御撰《神武秘略》即“纂古今兵书战策及旧史成败之迹,类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凡四门三十篇”[9](P642)。从宋人对孙子“将者,智、信、仁、勇、严也”的理解和注释,亦可看出对谋略的重视程度。梅尧臣曰“智能发谋”,王皙曰“智者,先见而不惑,能谋虑、通权变也”,何氏曰“非智不可以料敌应变”,张预曰“智不可乱”[32](P7-8)。在《贵谋》篇中,石介说:“天下有大忧危,国家有大菑患,圣贤发至诚,运至智,定至谋,以扶安之。圣贤之诚,诚矣;圣贤之智,明矣;圣贤之谋,果矣。如机之发,如蓍之占,如节之合,作于此而应于彼,言于近而验于远,不差毫厘。”对圣贤运用智谋治国救困大力称赞,他认为:“圣贤之谋必行,则自古无丧身,无败家,无亡国,无倾天下。丧身、败家、亡国、倾天下,由圣贤之谋不用也。”[31](P83)李觏指出:“夫兵者,诡道。有形或不可视,有声或不可听,合散如雷电,隐见如鬼神。而欲以昔人之余论,叹往之陈迹,拟议于其间,不亦难乎?”所以将帅要懂得适时应变,灵活用兵,“是谓反兵法而用兵法也”[24](P172-173)。
神宗朝何去非说:“昔者东汉之微,豪杰并起而争天下,人各操其所争之资。盖二袁以势,吕布以勇,而曹公以智,刘备、孙权各挟乎智勇之微而不全者也。夫兵以势举者,势倾则溃;战以勇合者,勇竭则擒。唯能应之以智,则常以全强而制其二者之弊。是以袁、吕皆失,而曹公收之,刘备、孙权仅获自全于区区之一隅也。”[26](P483)北宋末期秦观说:“臣闻兵家之所以取胜者,非特将良而士卒劲也,必有精深敏悟之士,料敌合变、出奇无穷者为之谋主焉。”[21](P625)其时兵学著作不再烦论。
(三)重视熟悉敌我实情
重视掌握敌我实情也是此时兵学主要关注的内容之一。 《武经总要》曰: “然则善制战者, 必先审于己, 一得地利, 二卒习服, 三器用利, 然后察彼之形势。 不明敌人之政者, 不加兵; 不明敌人之情者, 不誓约; 不明敌人之将者, 不先军; 不明敌人之士者, 不先阵。 知彼知此,则始定计于内, 出兵于境。”[23](P109-110)可见宋代官方主政群体充分重视熟悉掌握敌我实情,这也从部分宋人注解孙子“知己知彼者,百战不殆”可证。梅尧臣认为:“彼己五者,尽知之,故无败。”王皙说:“校尽彼我之情,知胜而后战,则百战不危。”张预曰:“知彼知己者,攻守之谓也。知彼则可以攻,知己则可以守。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苟能知之,虽百战不危也。或曰:士会察楚师之不可敌,陈平料刘项之长短,是知彼知己也。”[32](P62)
北宋朝野士大夫论兵也普遍认识到战时熟悉敌我双方实力非常重要。宋夏战事爆发后,尹洙即认为宋方集结重兵在边境陷于被动,是对敌方内情,尤其地理形势很不熟悉:“近者王文忠、潘湜失利,皆以不知山川险易,为其邀击,此不按地舆之失,非战士材武之劣也。”[28](卷二三《按地图》)苏洵说:“凡兵之动,知敌之主,知敌之将,而后可以动于险。”[25](P29)军事行动前需充分了解敌方领导层,“将战,必审知其将之贤愚: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持之则容有所伺而为之谋,乘之则一举而夺其气”[25](P34)。只有对敌我情况非常熟悉,正确估量双方实力,最终才能达到“攻敌所不守,守敌所不攻”[25](P43)。其子苏轼亦云:“料敌势强弱,而知师之胜负,此将帅之能也。”[7](P89)苏辙则曰:“《兵法》有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彼而不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夫惟知彼知己,而后知所去就哉!”[33](P974)由此可见,北宋士大夫谈论军事时对熟悉敌我实力非常重视。
(四)重视阵法阵图
阵法属古代兵学重要内容之一。吴晗说:“所谓阵法就是野战的战斗队形和宿营的防御部署;把队形、部署用符号标识,制成作战方案,叫作阵图。”[34](P87)将军队作战阵法绘图描述记录下来即阵图。
在军事上,北宋中后期延续了宋初以来重视阵法阵图的传统,也成为当时兵学发展鲜明特点之一。《武经总要》专门载有当时流传的一些阵法阵图,编者云:“今取古今阵法,绘出其图,以存梗概,俾将帅度宜而行之。若能沿古以便今,闻一而悟十,触类以长此,又寄之明哲,要之与孙吴暗合为极致耳。历代阵法,沿袭各殊,盖施予古者,或泥于今……雍熙中,契丹数盗边境,太宗皇帝乃自制平戎万全阵图,以授大将,俾从事焉。今存其详,用冠篇首,以示圣制云。”[23](P274)除太宗“平戎万全阵图”外,仁宗也曾对近臣赐、阅所藏阵图,“大宋庆历中,上出《临机指胜图》,赐近臣”[23](P323)。庆历五年(1045),“庚戌,御迩英阁, 读《三朝经武圣略》,出阵图数本并陕西僧所献兵器铁浑拨,以示讲读官”[12](P3748)。至和元年(1054)三月壬申“赐边臣御制攻守图”[12](P4255)。南宋王应麟《玉海》卷一四二、一四三《兵制·阵法》,同《兵制·兵法》内容相并列,辟出专设门类,记载历代阵法阵图。其中,明显可见北宋新成的阵法阵图几乎占多半。这些皆从侧面说明了当时兵学的趋向。
另外,北宋中期以后,众多士大夫论武谈兵也涉及阵法或阵图,如韩琦、范仲淹等人皆有相关传世奏议。“元昊叛河西,契丹举众违约,三边皆警,天下弊于兵。公(杨偕)于此时,耗精疲神,日夜思虑,创作《兵车阵图》刀盾之属,皆有法。”[35](P440)皇祐三年(1051)二月,“丙午,泾原经略使夏安期上弓箭手阵图”[12](P4081)。嘉祐四年(1059)六月,“翰林学士胡宿,看详驾部员外郎尹瞻所进裴子新令及八阵图,颇精,降诏奖谕”[36](P2650)。
北宋中期,军队操练即比较重视阵法阵图。如八阵法,“法曰:八阵者,盖本裴绪新令方、圆、牝、牡、冲方、罘罝、车轮、雁行之名也”[23](P283),说明该阵法继承前代而又有所发展。庆历五年(1045) 五月“己卯,遣内侍押班任守信往河北路教习阵法”[12](P3773)。次年六月“壬申,召河北教阅诸军, 并用祖宗旧定阵法, 其后来所易阵图, 亦令主将闲习之”[12](P3832)。
三、北宋中后期兵学发展成因:兵学传统与时局共同激荡
北宋中后期,兵学发展迎来繁荣局面,产生了数量惊人的著述。相比前代在理论内容上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这是长期以来兵学的传统内容与当时现实社会环境共同作用之结果。
首先,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兵学的传统基本内容,包括军事将帅、兵机谋略、掌握敌我实情等方面成果丰硕。
譬如重视军队统帅。宋神宗时校刊的前朝“武经七书”,对军队选帅命将进行过不同程度探讨。《孙子·计篇》中预测战争胜负七要素,首谈“主孰有道”,其次即论“将孰有能”[32](P9)。《作战篇》云:“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32](P39)孙子认为优秀将帅对国家社会作用重要。《吴子·论将》提出:“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37](P51)“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37](P53)并专门探讨将领应具备的各种条件及分析敌情要领。这种认识在以后兵书中被多次阐述,如《六韬·论将》云:“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可不察也。”[38](P449)《奇兵》云:“将者,人之司命,三军与之俱治,与之俱乱。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38](P461)《三略·上略》指出:“夫将者,国之命也。将能制胜,则国家安定。”[39](P6-7)又如,重视兵机谋略。《孙子》处处即有体现,《计篇》云“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推崇兵不厌诈的诱敌思想。《汉书·艺文志》曰:“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至于孝成,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即汉成帝时任宏受命整理兵书,将传世兵书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所谓“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而“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可见推重权谋机变乃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再如传统兵学重视熟悉敌我实情。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熟悉敌方情况,了解自己实力,精确估量敌我双方优劣,每场战斗都不会失败。“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吴子·料敌》即判断敌情,并提出因敌致胜方法。所谓“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37](P45),必须查明敌人虚实,而攻其弱点。传统兵学的理论精华被很好传承下来。唐初李靖说:“孙武所谓‘先为不可胜’者,知己者也;‘以待敌之可胜’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臣斯须不敢失此诫。”[40](P274-275)再者,阵法、阵图也属古代兵学重要内容之一。《尚书·牧誓》即载周武王伐商之牧野战前誓师辞,其中“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等,明令士兵服从阵法要求,统一作战。先秦《吴子》《孙膑兵法》《六韬》等重要兵书,即有明确论述阵法的专篇或内容。
其次,北宋中后期社会环境特殊,表现在军队将帅素质、士大夫谈兵风尚与复杂的政治局势等方面。
北宋开国后延至中期,军队将帅水平趋于下滑,整体素质逐渐降低。北宋中叶以后,西北边患严重,宋夏开战,宋方多次惨败。“崇文抑武”国策长期推行,造成武将群体素质普遍降低。“长期倍受压抑和歧视,在宋仁宗朝造就了武将队伍素质更进一步下降的后果,遂产生了一批怯懦无能、品行低劣的将帅。”[41](P109)如田况所说:“今将帅士卒,素已懦怯,未甚更练。”[19](P9778)韩琦在前线反映:“庆州久缺部署,高继隆、张崇俊虽有心力,不经行阵,未可全然依任。驻泊都监之内,亦无得力之人。”而武将魏昭昞、王克基“未尝出离京阙,便使领众御戎,昨来暂至延州,皆已破胆”[42](P164-165)。刘敞云:“即今武吏多不愿临边,有不得已就职者,皆畏避……边臣有才者寡,可用者少。”[20](P593-594)正如清初王夫之所论,当李元昊反叛时,“于是而宋所以应之者,固宜其茫然也。种氏以外,无一人之可将,中枢之地无一策之可筹。仅一王德用之拥虚名,而以‘貌类艺祖,宅枕乾冈’之邪说摇动之,而不安于位。狄青初起,抑弗能乘其朝气、任以专征,不得已而委之文臣”。形势危急时,宋廷缺乏军事将帅人才,迫不得已而命文臣统兵。“吟希文(范仲淹字希文)‘将军白发’之歌,知其有弗获己之情,四顾无人,而不能不以身任。”[2](P93)许多担任军事统帅的文臣或不谙军旅,或畏懦胆怯,治军无方,往往借助酷刑来维护威严。一些庸夫懦将更是如此。如,真宗时益州王均变乱,起因即“神卫卒赵延顺以众怨钤辖符昭寿,多用亲随仆言,榜箠军人”[43](P777),从而伺机叛乱;而宜州兵变,因“知宜州刘永规驭下残酷,军校乘众怨,杀永规叛”[19](P9706)。仁宗庆历时,光化军兵变与长官韩纲“性苛急,不能抚循士卒”关系重大[19](P10299)。“今沿边主兵之臣,既不遴择其人,及军士作过,不问乱所由起,一概被罪,遂使骄兵增气。”[12](P3800)神宗熙宁三年(1070),负责对夏军事指挥的韩绛,虽进士出身,而“素不习兵事,注措乘方”,军中士卒“众皆怨望”“调发骚然”“庆卒遂作乱”[19](P10303)。北宋末期,知京兆府盛章为树威立信,“一日杀戮无辜者数十人。军兵汹汹,几至变乱”[44](P667)。针对军中弊政,欧阳修沉痛指出:“癃钟跛躃、庸懦暗劣之人,皆委之要地,授以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为朝廷危之。”[12](P3256)鱼周询说:“朝廷用空疏阘茸者为偏裨,募游惰怯懦者备行伍,故大举即大败,小战辄小奔。”[12](P3930)总之,至北宋中期,将帅素质降低也引起朝野上下充分关注,为适应内政与边事需要,提高将帅水平也成为宋廷治国的当务急需。
北宋中期以后,士大夫中形成谈兵风尚。北宋中期的国家政治生活中,文臣士大夫居于主导地位。面对内外交困的现实危机,许多人心怀国事,渴望建功立业。这从部分士大夫的言谈、诗文中即可看出。如苏洵向韩琦自荐:“洵著书无他长,及言兵事,论古今形势,至自比贾谊。所献《权书》,虽古人已往成败之迹,苟深晓其义,施之于今,无所不可。”[25](P301)可见,他对自己的兵学谋略颇为自信。庞籍词云:“儒将不须躬甲胄。指挥玉尘风云走。战罢挥毫飞捷奏。倾贺酒。三杯遥献南山寿。”[45](P2)梅尧臣踊跃奋发,以诗言志:“介胄奉儒服,诗书参将谋。”[46](P117)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亦云:“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对儒将指挥若定的风度可谓非常向往。郑仅“少年锦带佩吴钩。铁马追风塞草秋。凭仗匣中三尺剑,扫平骄虏取封侯”[47](P445)。何去非更声称“使儒而知将,则世将有所不能窥也”[26](P514)。
北宋士大夫普遍认识到战时熟悉、掌握敌我双方实情的重要性。如《宋史·尹洙传》称颂:“自元昊不庭,洙未尝不在兵间,故于西事犹练习。其为兵制之说,述战守胜败,尽当时利害。”[19](P9838)即可见时人对出自实践的兵学理论重视程度。王韶更在“试制科不中”后,“客游陕西,访采边事”[19](P10582)。一番实地考察,为其后征战熙河奠定了坚实基础。
另外,阵法阵图在北宋受到重视,与当时复杂的政局关系密切。文人士大夫谈兵,能较容易地接受阵法阵图的表现形式,即足不出户,身不戎服便可俯观军阵。此外,如前所论,阵法阵图也得到宋廷皇帝充分重视。一些学者认为,北宋皇帝干预军事、御赐阵图,现象比较常见,“在中国古代战争中,为了更有效地发挥军队多兵种与群体作战的效果,产生了阵法以及阵图。至北宋时期,统治者长期对阵法予以高度重视,不断加以建设,更通过授阵图指挥作战”[48]。
四、结 语
综而述之,北宋中后期,兵学发展出现繁荣局面,产生了数量众多的兵学著作。从理论内容上看,这些兵学成果具有一些基本特征,其形成原因非常复杂,是当时各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北宋中后期兵学理论的蓬勃发展,对当时政治、军事与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部分士大夫臣僚担任地方统兵帅臣或军中僚佐,如范仲淹、韩琦、尹洙、蔡挺、王韶、章楶等,直接将自己的兵学理论付诸现实军事实践,推动了现实的军事技术与理论水平发展。研究北宋中后期某位军事人物或某个区域的军事思想,必须结合当时的客观兵学发展理论特征,进行全面思考。如此所成论断才会更加接近历史真相。
——刘家文
——徐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