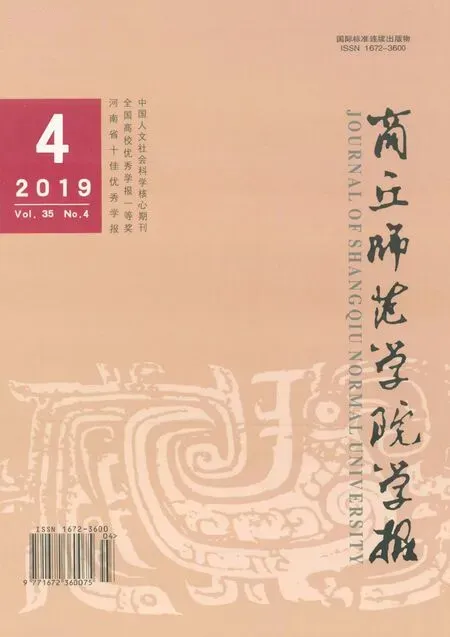时间意识与《西厢记》抒情效果达成
李晓敏 吴艳玲
(1.山西师范大学 现代文理学院,山西 临汾041000;2.山西师范大学 社科处,山西 临汾041000)
王实甫《西厢记》是中国戏剧史上广为传颂的经典,其思想性和艺术性在元杂剧中都堪称翘楚。贾仲明在对《录鬼簿》的补撰中有《凌波仙》一词称赞道:“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1]171明代王世贞在《曲藻》中说:“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2]31王骥德在评点《西厢记》时,也说:“古戏必以《西厢》《琵琶》称首。”[3]223诚然,《西厢记》以其强烈的抒情性和卓绝的艺术感染力,获得了千百年来人们的喜爱和推崇。是什么成就了《西厢记》如此高超的艺术魅力呢?对此,前人从多方面进行过探讨。但时间意识与该剧抒情效果达成之间的关系,尚未被学界充分注意。
时间,是人类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自我意识。时间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自身的存在得到了主体的确认。正如谢林所说:“时间原本是内在智能的直观形式”,“它只是存在于我们之内”[4]173。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发生在特定的时空中。时间作为一种隐性的自我意识,时时刻刻对主体的行为和情感产生影响。在古代戏剧中,时间意识的存在对戏剧效果的实现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西厢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对时间意识的强调,是理解该剧整个情节推进、意境构建和人物塑造的重要角度。本文将从这几个方面对此问题逐一探讨,敬请方家指正。
一
王实甫《西厢记》对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很多情节都进行了完善和增补。同时,王实甫创造性地打破了元杂剧一本四折的体制,将其扩充为五本二十折,这不仅扩充了剧本的容量,也增强了故事的曲折性和生动性。这一点,历来为研究者所称颂。但我们认为,该剧曲折的情节设置和矛盾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时间意识的强调。
首先,从本剧故事的开始来看,就体现了时间意识与故事情节的密切联系。如第一本《张君瑞闹道场杂剧》的《楔子》老夫人自述曰:
(外扮老夫人上开)老身姓郑,夫主姓崔,官拜前朝相国,不幸因病告殂。只生得个小姐,小字莺莺,年一十九岁,针黹女工,诗词书算,无不能者。老相公在日,曾许下老身之侄——乃郑尚书之长子郑恒——为妻。因俺孩儿父丧未满,未得成合。[3]1
这里的“三年之丧”即是一个明确的时间概念。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细节在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中是没有交代的[5],很明显是王实甫有意地改编和提示。据《礼记·杂记》:“少连,大连善居丧,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忧。”[6]1142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儒家讲究直系亲属去世之后,要为其居丧,而三年就是其基本期限。长期以来,这种制度已经变成一种司空见惯的礼制。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很可能就对这个“三年之丧”的时间概念熟视无睹。其实不然,这一时间概念,应该是整个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条件。正是因为有了“三年之丧”,莺莺才没有与郑恒完婚;正是因为有了“三年之丧”,才为老夫人悔婚埋下伏笔;也正是因为有了“三年之丧”,其后郑恒才要回来。如果不是这一时间概念的存在,故事的这些重要关目和矛盾就无从谈起。可以说,这个看似寻常的“三年之丧”,实际上是贯穿整个故事前后的时间意识。由于其某种程度上的“隐秘”性,使得整个故事的构建不露针黹,前后连贯。
其次,在整个故事的构建中,也时时体现出时间意识的重要性。如第二本写到孙飞虎兵围普救寺,情急之下张生挺身而出,以三日为期,剧中借此渲染了一种紧张的戏剧矛盾:
(飞虎领兵上,围寺科)(卒子内高叫云)……三日内将莺莺献出来与俺将军成亲,万事干休。三日之后不送出,伽蓝尽皆焚烧,僧俗寸斩,不留一个。(夫人、洁同上,敲门了)(红娘看云)姐姐,夫人和长老都在房门前。(旦见了科)(夫人云)孩儿,你知道么?如今孙飞虎将半万贼兵围住寺门,道你“眉黛青颦,莲脸生春,似倾国倾城的太真”,要掳你做压寨夫人。孩儿,你怎生是了也?[3]50
孙飞虎准备强抢莺莺,兵围普救寺,提出“三日”之限。这“三日”的时间概念,也是对剧中主要人物内心及其行为的重要限制。无论是当事人莺莺、崔夫人,还是法本、红娘,都被这一限期搞得神情紧张,尤其是崔夫人,显然已经是手足无措。这就为接下来故事情节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若不是这时的手足无措,也不会有对张生出谋划策的倚重。这也就说明,老夫人提出解普救寺之围者即以莺莺相许本是在这种时间压力下的权宜之计,这与后文老夫人“此计较可。虽然不是门当户对,也强如陷于贼中”的表述正好呼应。这也就暗示了解围之后的老夫人可能会出尔反尔。可见,“三日”之限,既对故事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凸显了张生的挺身而出,同时又对情节的发展有重大铺垫,使得故事的结构出人意料之外,又尽在情理之中。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同时,在实际的舞台演出中,使得观众会为这短暂的期限而产生一种情绪上的紧张,从而更好地吸引观众体会戏剧本身的喜怒哀乐,达成很好的表演效果。
再有,莺莺是在春天少女怀春,而其后崔张的私会偷情也安排在春天,这也不是偶然的。春天这样的时间概念,象征着万物复苏,欣欣向荣,是生命的希望,也是爱情滋长的季节。将崔张的恋爱和偷情安排在这样的季节,既是中国传统季节性思维的结果,也与中国文人的伤春情结有关。正如党月异所说:“崔张二人在这样一个缤纷的季节相逢,抑制不住内心的渴望,终于走上一条偷情之路。”[7]同时,春光易逝的感慨和伤春惆怅的情怀,更加能衬托出男女主人公情爱的缠绵悱恻,也给全剧蒙上了一层朦胧、感伤的意境。
总之,时间在《西厢记》中,并不是简单的概念,而经常是构建戏剧重要关目的有机组成因素。正是因为有了时间意识的加强和凸显,使得该剧很多的情节和矛盾达成了更好的舞台表现,其抒情效果的达成,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关联。
二
《西厢记》的意境营造非常具有艺术感染力,这一点已被学者广泛认识[8]。可以说,对中国传统诗歌艺术的借鉴和熔铸,是其抒情效果实现的关键。而在这方面,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作家对时间意识的关注。以广为读者所知的《长亭送别》为例来看:
首先,崔张离别的时间被限定在“暮秋天气”,这本身来自中国抒情文学传统。西晋的陆机曾言:“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9]12诚然,中国文人有着浓郁的“悲秋”情结。将崔张的离别放在这样一个“暮秋”的时间点,就必然更增加了离别的惆怅。正因为如此,莺莺才会情不自禁地发出“好烦恼人也呵”的哀叹。同时,这种特殊的时间意识,引出下文的景物描写: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3]158
在后世读者的眼中,此段写景堪称经典,然若非中国文学中长期形成了“悲秋”传统及王实甫对这一时间意识的刻意凸显,长亭送别的抒情效果达成,恐怕要大打折扣。“黄花”和“西风”这对寒秋的典型意象,自然引发了 “悲秋”的时间意识,使得读者或观众主观上参与了对剧本意境的构建,从而加深了对人物情感的深层体验,最终被其离愁别绪所深深感染。
“离别”本来就是中国传统诗词中最常见的题材,在文学史上出现过很多优秀的作品。柳永的《雨霖铃》可谓是其中的经典名篇。细读文本不难发现,无论是《董西厢》还是《王西厢》,都在送别意境的整体营造上借鉴过《雨霖铃》的艺术经验。其尤为突出的特征,正是对时间意识的掌控和安排,深得柳永三昧。这突出表现为王实甫在这场长亭送别过程中对时间意识的一次次刻意强调。如其曰:
恨相见得迟,怨归去得疾。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晖。马儿迍迍的行,车儿快快的随,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3]159
作家在这里所涉及的,其实是离人对时间的复杂感受。可以说,时间在整个送别的过程中所充当的,正是离人的对立面。它的存在,会造成抒情男女主人公内心的紧张感。时间意识是离别者最大的敌人。所以,此处送别张生的莺莺,对时间表现出极度的敏感。而王实甫正是抓住了这一心理细节,在字里行间对其进行精细的描摹。“折柳送别”本是古人传统,以寄托对远行者的挽留和思念,因此文中讲“柳丝长玉骢难系”。但为了功名,更是为了崔张的爱情,张生的离去是不可改变的现实。莺莺对此无奈,但在无奈中又希望作出一点无谓而深情的“对抗”。所以她仍希望“疏林挂住斜晖”!然而,时间是客观存在的,不会因为任何人的主观不舍而稍作停留!所以这句“疏林挂住斜晖”,只能是一种绝望中的希望。莺莺的这种感觉实际上是属于她自己的“心理时间”而非客观时间。至此,我们真正体会到时间意识在莺莺内心所引发的细微而真挚的情感变化。也只有明乎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长亭送别中莺莺对张生的深情。而这,在具体展开崔张离别的场面描写之前,已经为其后感情的迸发作了充足的蓄势。
其次,在描写长亭送别的整个过程中,作家也是有意让时间意识一次次凸显。这在文本中往往是以“催促”的形势体现的。上文已论,时间是离别者最大的精神压力来源,时间不断流逝本身就是对离别者的催促。所以,才会有上文所言莺莺式的“心理时间”或即对时间的有意回避。然而,主人公越是回避,王实甫就越是要让时间凸显。如其曰:
(夫人云)小姐把盏者!(红递酒,旦把盏长吁科云)请吃酒![3]159
这段语言描写非常简短,也非常传神。在这里,作家通过老夫人之口,安排的不过是离别饯行时最正常不过的行为——“把盏”,而这却是对时间的有意提示和凸显。因为“把盏”即是饯别的开始,同时也是离别的倒计时。上文已经写到崔张在离别时“执手临歧”,完全沉浸在两人构建的情感“小世界”中,似乎要忘记整个世界,当然也忘记了时间。这显然已经将崔张之情写到了深处。但王实甫的高明之处不仅于此,在这时安排老夫人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第三者出现要求“把盏”,就刻意去提示了时间的存在。崔张构建的情感“小世界”,在现实“大世界”的时间意识面前濒临毁灭。崔张内心本身就存在的对时间的敏感,因老夫人的提醒而加剧。自然,接下来必然是莺莺对离别惆怅之情的抒发:
合欢未已,离愁相继。想着俺前暮私情,昨夜成亲,今日别离。我谂知这几日相思滋味,却原来比离别情更增十倍。[3]159
显然,莺莺的这种惆怅情感正是时间使其内心紧张感加剧后的产物,或者说莺莺的情感正是被时间逼迫而出。正因如此,读者对崔张的同情和对老夫人的厌恶才会感同身受,被文本深深吸引。事实上,王实甫并不满足于老夫人对有情人离别的一次残酷打断。其后,老夫人又重复道:“红娘把盏者!”虽然换成了催促红娘,但仍是在催促莺莺。这里,又是王实甫有意对时间意识的凸显和提示。如果第一次老夫人催促已经使得崔张情感紧张度加剧的话,这第二次无疑是火上浇油。进而,将整个离别的愁绪推向新的高潮。类似的时间提示,在下文还有,如:
(夫人云)辆起车儿,俺先回去,小姐随后与红娘来。
(红云)夫人去好一会,姐姐,咱家去![3]160
这里的文本似乎是红娘来提示时间的存在,但隐含的仍是老夫人给崔张的压力。所以,纵观长亭送别的整个过程,老夫人的催促时刻不曾停歇,而时间作为悬在这对男女头上的利剑随时有掉下来的威胁。这就营造出了整个关目哀婉、凄美的意境。抒情主人公的情感实际上正是被时间意识逼迫而出,贯穿送别的整个过程。时间意识参与了这一关目抒情效果达成的全部。这在整部戏剧中并非特例,而是作者最常使用的一种构思技巧。
总之,纵观王实甫《西厢记》的整个剧本的意境营造,时间作为一个无形的恶魔时时威胁着抒情主人公的精神世界。而且它还常常由一种隐性的存在被刻意提示进而“出场”,使得整个戏剧的情感气氛骤然紧张,将戏剧的事情效果不断推向高潮。这不仅增强了全剧的抒情性,而且牢牢抓住了观众的心理期待,使人不禁为之深深吸引,随之或喜或悲。
三
郑振铎曾言:“中国的戏曲小说,写到两性的恋爱史,往往是二人一见面便相爱,便私订终身,从不细写他们的恋爱的经过与他们的在恋时的心理。《西厢》的大成功便在它的全部都是婉曲地细腻地在写张生与莺莺的恋爱心境的。”[10]69《西厢记》作为一部文学经典,其人物形象的塑造在中国戏剧史上也具有很强的典型性。追求爱情的莺莺,痴情风魔的张生,泼辣机智的红娘,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认为,时间意识的凸显,在该剧塑造人物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来看莺莺。剧中莺莺首次与张生有交流,是月下对诗。面对张生的借诗传情,莺莺的回答是:
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3]21
张生对莺莺一见钟情,所以才会在月夜苦等,莺莺与红娘烧香,正好给了他倾诉衷肠的机会。但莺莺又何尝不是对爱情久已抱有憧憬之情?“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一句,正好写出了青春少女对春季这一特殊时间概念的敏感。大好的春光怎能辜负?而自己的青春也正如这大好的春光一样,应该有一个真正能懂得欣赏的人出现。然而在张生出现以前,莺莺只能春光虚度,眼看青春流逝,内心的惆怅和期望溢于字里行间。正是这次与张生的“正面交锋”,建立了情感联系,也集中体现了莺莺少女怀春、自由大胆追求爱情的女性形象。在此,莺莺时间意识的体现,起到了很好地塑造人物性格的作用。
再有,上文所论孙飞虎兵围普救寺曾提出“三日”之限,在如此紧迫的时间下,将故事的矛盾冲突推向了高潮,同时也将莺莺及老夫人推向了绝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莺莺主动提出将自己献给孙飞虎,并说:
(旦云)不如将我与贼人,其便有五:
第一来免摧残老太君;第二来免堂殿作灰烬;第三来诸僧无事得安存;第四来先君灵柩稳;第五来欢郎虽是未成人,须是崔家后代孙。[3]51
通过时间的逼迫,在强烈的矛盾冲突下,莺莺深明大义,自我牺牲的形象就得以展现出来。这也就越发使得莺莺的形象完整而具有魅力。
再来看张生。张生最大的特点就是痴情,即“风魔”。如第二本第五折中,红娘为张生出计约定莺莺晚上烧香时让其以琴传情,在等待莺莺的过程中,张生就感到了时间的漫长。如其曰:
(末上,云)红娘之言,深有意趣。天色晚也,月儿,你早些出来么!(焚香了)呀,却早发擂也;呀,却早撞钟也。[3]91
字里行间表现的是张生的“风魔”。但这一特点倒可以从他对时间的感受作以解读。从“月儿,你早些出来么”一句来看,说明张生觉得时间太慢了,他急于向莺莺倾诉自己的衷肠,所以对“月亮”都有了埋怨和催促的心理。他显得有些迫不及待。对月亮的祈求,充分表现出张生的可爱和呆傻,也更体现出其陷入爱情的志诚。其后又说:“呀,却早发擂也;呀,却早撞钟也。”这句说明张生对约定时间的到来感觉太快,有些许的惊慌中又满含惊喜,多少有点措手不及。这时,他对时间的感觉是过得太快了。这和前面看似矛盾,其实不然。正是这种貌似矛盾的复杂心情描写,才足以表现张生向莺莺表白之前的兴奋、紧张和痴傻。如此细致的心理,通过作家对人物的时间意识的认真刻画,可以说活生生展现在观众和读者面前。
当然,《西厢记》中通过时间意识塑造张生形象的例证很多。如第三本第二折写张生拿到红娘传简,苦等与莺莺月夜相会之前的一段描写就很具有典型性。其曰:
(末云)万事自有分定,谁想小姐有此一场好处。小生是猜诗谜的社家,风流隋何,浪子陆贾,到那里扢扎帮便倒地。今日颓天百般的难得晚。天,你有万物于人,何故争此一日。疾下去波!“读书继晷怕黄昏,不觉西沉强掩门,欲赴海棠花下约,太阳何苦又生根?”(看天云)呀,才晌午也,再等一等。(又看科)今日万般的难得下去也呵。“碧天万里无云,空劳倦客身心,恨杀鲁阳贪战,不教红日西沉!”呀,却早倒西也,再等一等咱。“无端三尺乌,团团光烁烁;安得后羿弓,射此一轮落?”谢天地!却早日下去也!呀,却早发擂也!呀,却早撞钟也!拽上书房门,到得那里,手挽着垂杨滴流扑跳过墙去。[3]113-114
这段文字可以说又是《西厢记》中描写张生痴情风魔的经典文字。对于为爱苦闷消瘦已久的张生来说,红娘送来的简帖儿正如救命稻草般珍贵。而张生又从中读到了所谓的“月夜之约”,这就更加让他喜出望外,甚至得意忘形。所以他是无比期盼晚上的到来,“天,你有万物于人,何故争此一日。疾下去波”一句,多么的痴傻,多么的可爱!把张生内心对约会时间到来的渴盼描写得淋漓尽致,同时也将其“风魔”的性格刻画到极致。下文的一看再看,一等再等,又将其内心面对时间的煎熬细致如丝地表现出来。时间在此时对渴盼马上与莺莺成就好事的张生来说是最大的敌人,但正是这个敌人的凸显,将张生的性格刻画得生动迷人,使张生的人物形象给读者和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处,可说是王实甫《西厢记》在刻画人物时很好地利用时间意识的又一成功关目。
时间是一把悬在人头上的利剑,它对人心时时是一种威胁,随时有可能掉下斫伤人的灵魂。人与时间,经常会处于一种紧张对立之中。正因为如此,时间与人的关系,被很多文学经典关注。就此,笔者曾撰文认为:“由于时间具有线性的、流逝性、不可逆性的特征,往往在能清楚意识到时间存在的主体那里会造成一种情感上的紧张和恐慌情绪,而这种情绪的存在,实际上玉成了很多文学经典的艺术感染力。”[11]是的,我们认为,《西厢记》最感人至深之处,正是男女主人公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所体味到的悲欢离合。这些悲欢离合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关联。本文分情节推进、意境构建和人物塑造三个方面探讨了时间意识与全剧抒情效果达成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仅是为了对问题的探讨更加条理,三者在全剧的表现并不是割裂的,常常是融合为一的。同时,时间是人类共同的心理感受,当抒情主人公被时间逼迫时,观众或读者往往都能感同身受。正是这种作家、主人公与读者、观众的共同心理体验,让《西厢记》的抒情能穿越历史时空,将其感人的力量渗透到每一个人内心,从而成就了其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