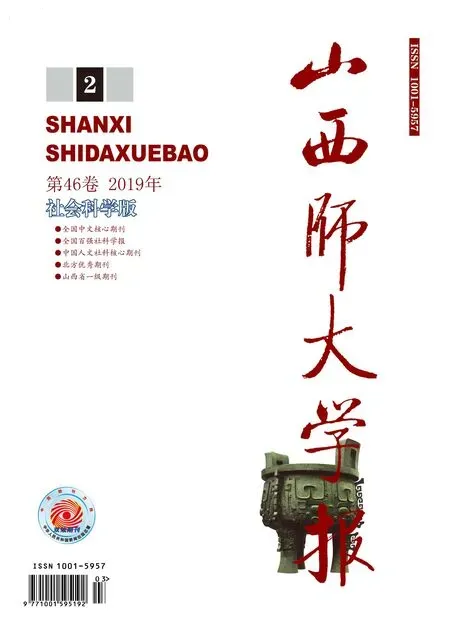两汉“以吏为师”皇权专制主义本质探析
刘 承
(许昌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0)
两汉时期的帝制中国,皇权犹如一张铺天盖地的巨大罗网,笼罩在整个社会之上。作为体现帝王意志的施政方式,“以吏为师”是连接帝王与民众沟通链条的一个特有一环。然而在其政治实践中,专制的幽灵无处不在,它的强大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还渗透到人的思想乃至精神层面,成为古代中国人一系列思维、概念、范式的由来。说“以吏为师”是思想专制的代名词,恐不为过,其中的缘由,值得我们深思。
“以吏为师”的研究历来为学界关注。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分别从“循吏的教化功用”“言轨于法”“‘天高皇帝近’的意识形态构建”等方面做了深入考察。近年来,李振宏先生提出“皇权专制社会”说,从“以吏为师的根据”“以吏为师制度设计中官员与老百姓的关系”“以吏为师的历史评说”三个方面予以论析,最后揭示出古代统治者“设置天子圣明的结局,打出以吏为师的旗帜,他们费尽心机所要的实际上也就是‘专制’二字”。[1]“以吏为师”是皇权时代的产物,本已无可置疑,但随着近十余年来国学热、新儒家言说的兴起,一些学者竟极力美化儒家德治,企望恢复“以吏为师”,恢复两汉时期定儒学为一尊的专制体制。有鉴于此,笔者拟从德治角度来探析“以吏为师”专制恶果,希冀思想界对这一制度的专制本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一、汉代“以吏为师”的德教内涵
思想统一——对思想的绝对控制,是每一个王朝统治者孜孜以求的目的。它与政治统一并驾齐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思想统一更为重要。汉代大一统帝国建立后,如何实现思想上的统一,便成了帝王们亟待解决的问题。于是,汉代统治者全面继承了秦代“以吏为师”的治民方式,其终极目的只有一个:维护皇权专制,贯彻皇帝意志。
《论语·为政》载孔子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3]61又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3]68孔子认为,征服人心的关键在于发挥统治者的道德表率作用,即以德服人。因此儒家的政治理念就是德治,亦即人治。汉王朝建立后,从帝王意志出发,在新的一统形式下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将人们的思想、情感乃至精神世界纳入自己可控的范围内,这就需要一个能够长期进行社会教育的思想工具。在这种背景下,儒家的德治理念便被汉统治者所重视和倡导。《汉书·文帝纪》载汉文帝十二年诏曰:
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4]124
汉统治者推广以德教民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以孝治天下。汉代帝王认为,孝悌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基层官吏除了管理百姓正常生产活动之外,还应该充分发挥孝悌的影响力。因此官吏应加强自身道德建设,作为“民之师”“民之表”,在民众中间传播孝悌精神。《后汉书·循吏传》记载了这样一个生动的例子:
览(仇览)初到亭,人有陈元者,独与母居,而母诣览告元不孝。览惊曰:“吾近日过舍,庐落整顿,耕耘以时。此非恶人,当是教化未及至耻。母守寡养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于一朝,欲致子以不义乎?”母闻感悔,涕泣而去。览乃亲到元家,与其母子饮,因为陈人伦孝行,譬以祸福之言。元卒成孝子。乡邑为之谚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鳲枭哺所生。”[5]2480
这是一个妇人状告自己儿子不孝的案子。仇览的处理方法是亲自到陈元家里,向陈元陈述人伦孝道之义,用感化的方式,终使陈元成为有名的孝子。仇览的做法践行了孔子所倡导的“道之以德”的施政理念,的确实现了老百姓的“有耻且格”。此事并非个例,我们在两汉的《循吏传》中经常会看到官吏“谨身帅先”“力行教化”“以礼训人”等字眼。这些记载表明,汉代官吏在履行以德教民之责时体现了很强的责任意识。他们事必躬亲,循循善诱,树立典型,对乡间教化进行有序疏导,将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灌输到百姓的思想深处,真正做到了将基层民众的思想统一到官方意识形态的要求上来。
除了地方官亲掌教化外,汉统治者还非常重视“三老”在基层管理事务中的作用。三老的组织规模相当可观,有学者据尹湾汉墓出土木牍《集簿》的记载,统计出仅东海郡所辖十八县,就有县“三老卅八人,乡三老百七十人”,[6]42足见当时乡间教化组织人数之众。三老教化的内容,《后汉书·百官志》记载说:“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5]3624说明除孝道外,表彰仁、义、礼、智、信等善行都属于三老的职责,这也表明汉政府在乡间教化上明显带有弘扬儒家伦理道德的色彩。
余英时曾说:“儒教在汉代的效用主要表现在人伦日用的方面,属于今天所谓文化、社会的范畴。这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所以无形重于有形,民间过于朝廷,风俗多于制度。在这方面,循吏所扮演的角色便比卿相和经师都要重要得多,因为他们都是亲民之官。”[7]141的确,让官员用道德熏陶的方式教化百姓,对于稳定社会秩序的确是积极有效的。相比秦法的苛暴,汉代以德教民则显得颇富人情味,更具温柔气息。然而,在德治的光环背景下,为何说道德教化这一看上去极具正能量的施政手段,我们却将它和思想专制相挂钩呢?为什么官员的道德感化,百姓对道德宣传的接受,这些看起来完全是自主自愿的行为,造成的却是思想上的专制呢?这些问题,看似矛盾,却值得深思。只有揭开其温情的面具,才能看到以德教民的专制本质。
首先,以德教民促进了忠孝观念对全体国民的控制,保障了皇权专制体制的巩固。徐复观在分析孝道在大一统专制下的演变过程时指出:“孝道的本身虽不会助长专制,但经过这一偷天换日的手段,把父子关系的孝道偷到君臣的关系上去,这便犯下了助长专制之嫌。”[8]150忠孝观念被汉代帝王奉为统治基石,天子是天下的中心,是父母,是独尊;老百姓是子女,是小民,这样的定位确立了帝制时代家天下的统治秩序。于是,父子亲情的“孝”便上升到君王与臣民关系的“忠”的高度,事君如事父母,对父母不孝即是对君王不忠。张分田曾将忠孝一体的观念总结为以下四点,即“君父一体,移孝作忠”“忠比附孝,孝制导忠”“忠孝相同,难分彼此”“忠君孝父,绝对义务”。[9]72—73这种将孝与忠视为一体的方式,使得人们无形中在心灵深处对皇权意志产生深深的敬畏。以道德来驯化人心,用孝治来巩固专制,孝道伦理之所以在帝制时代的中国有这么旺盛的生命力,原因就在于此。另一方面,以德教民从根本上奴化了人的心灵,造成了思想上的愚昧和落后。孔子在《论语·泰伯》中有一句颇为经典的名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3]531,可谓一语道出了“以吏为师”的专制本质。为什么说只能让老百姓照着去做而不让他们知道呢?因为他们愚鲁、无知,只能被动接受。在“以吏为师”的制度设计中,德治都是从官吏这一主体方面来提要求的,如“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等,而民众在德治行程中的定位,根本没有任何主动性和自觉性可言,充其量不过是我正视你们的存在罢了。说穿了,就是做统治者的顺民而已。且这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没有任何强制并暴力的意思。
费孝通曾说:“儒家很有意用思想形成一个建筑在教化权力上的王者,他们从没有热心于横暴权力所维持的秩序。”[10]98也就是说,德治从来不依靠横暴权力,它甚至比通过法令来对民众进行灌输要“温和”一些,“人道”一些。而恰恰是这种看似温情脉脉的教导,却真正宣布了对民众思想的禁锢。百姓无须思考,也没有思想的权利,一生一世,立言立行,都要听从父母官的教化,以父母官的教育作为人生的唯一准则。有研究者指出:“思想的创造力丧失了,完全变成了没有思想也不会思想并从不提思想要求的群氓。”[1]从皇权专制的角度来说,统治者胜利了;但从思想发展的角度来说,我们的民族却深受愚昧和无知之苦。这是德治结出的苦涩恶果,“以吏为师”难辞其咎。
二、“民之师”:一种温情脉脉的思想专制
“以吏为师”顾名思义就是以官吏为师。对于绝大部分普通百姓而言,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仅仅是道德教化,仅仅是被要求如何去做统治者的顺民而已。这些百姓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般不去思考政治问题,也不会直接与皇权意志相冲突。但是拥有文化知识的学人则不然,他们是社会中的精英分子,是学术和思想的承载者,对于政治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批判意识,因而不可避免地会与皇权意志产生矛盾。对于这批在社会成员中只占少数的知识群体,如何利用“师”的职能对其进行思想专制,较之广大普通百姓,更为统治者所重视。
与秦始皇“坑儒”的血腥手段不同,汉统治者控制学人的方式是定儒学为一尊,以博士为师,将学人纳入儒学的思想体系中。雷戈曾说:“如果说意识形态职能的普遍化表现为百官皆师,那么意识形态建制的专业化就体现为博士为师。”[11]318就知识和学术层面来看,“以吏为师”不妨说就是以博士为师。无论是在国家层面的太学、宫邸学、鸿都门学,还是在各郡国、府县、乡里的学、校、庠、序等,所有的老师都是由博士本人或博士官指派的专业官吏来担任的,所教内容无外乎儒家所传承的那几部经典。如《后汉书·儒林列传》载:
(张兴)习《梁丘易》以教授……稍迁博士……弟子自远至者,著录且万人,为梁丘家宗。
(牟长)长少习《欧阳尚书》……长自为博士,及在河内,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
(蔡玄)学通《五经》,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顺帝特诏征拜议郎,讲论《五经》异同,甚合帝意。[5]2588
这些材料显示,通过官方的强力推动,儒学完全独占了国家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成为一家独大的显学。博士官所教授的弟子,人数动辄千余人,甚至上万。这么多人同时学习儒家“五经”(有的甚至只修习一经),真是蔚为大观。这说明儒学已真正扩散到国家的每一个角落,这是统治者所期望的场景。
汉代以博士为师,真正实现了统治者定儒学为一尊的愿望。表面上看,儒学的传播都是自发的,如果从“民之师”角度来看,问题便一目了然。
“民之师”思想专制的第一个表现是“学什么”的问题。董仲舒在他的“贤良对策”曾提出:“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4]2523(《汉书·董仲舒传》)此语一举奠定了汉代独尊儒术的政策导向。它告诉人们:我只尊崇儒学,只表彰“六艺之科”;我虽不禁绝其他学说,但我不让它们跟儒学“并进”。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其他学说越来越边缘化。即使学习儒学,也只能学习经过汉人改造后的儒学,亦即经过政治干预后的儒学。事实上,原始儒学经过汉人的改造和诠释,在汉代一统思想的全面洗礼下,已经失去本真。熊铁基曾说:“汉人对先秦典籍的改造,必然打上汉人的时代烙印,也就是打上汉人的思想烙印。”[12]245这一思想烙印,就是只选取儒学内部有利于皇权一统的一些思想元素,即只强调王权至上、等级有差;只强调共性,而忽略个性;只重视伦理道德,而忽视人的本性和真情。儒学的提倡,包括儒学思想体系的改造,都是政治干预学术的结果。“皇权对儒学的强力介入,就是要把它改造为政治的组成部分,或者说使之成为政治的附庸——国家意识形态。”[13]所以学人学什么不是由自己选择的,而是皇权意志所规定的。归根结底,都是出于思想专制的需要。
“民之师”思想专制的第二个表现是“学了之后干什么”的问题。学习儒学最大的用途就是做官。武帝以后,在唯用儒士政策的影响下,大批学子将儒学视作获取功名利禄的唯一途径。西汉大儒夏侯胜就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4]3159“青紫”比喻高官显位,经术如果能通晓了,那么取得高官显位就像捡起地上小草一样容易。班固在《汉书·儒林传赞》中更是直言:“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4]3620一句“盖禄利之路然也”,确实揭示了汉代儒学与官禄相结合的实质。顾颉刚先生说:“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制裁;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诱引。结果,始皇失败了,武帝成功了。”[14]57顾先生所说的“成功”,就是用利禄将大批读书人纳于皇权体制之中,接受体制内的管控。读书——做官——忠君——为民之师,在统治者看来,这是一个统一思想的良性循环,但对于学人来说,作为思想者的个体,也就最终被彻底地征服。作为思想者,最需要的就是自由的意志、独立的人格、开放的头脑和舒展的心灵,而这些人的体制化,则意味着这个社会中最具思想力群体的被消灭,意味着思想的被消灭![1]
“民之师”思想专制的第三个表现是严守师道权威。师道观念早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权威崇拜意识。师道尊严不仅表现为师与君、亲并重,弟子必须敬之如君,亲之如父,“不失师法”是一种公认的美德。然而捍卫师说却造成了学人囿于门户之见、固执己说的现象。皮锡瑞说:“先儒口授其文,后学心知其意,制度有一定而不可私造,义理衷一是而非能臆说。世世递嬗,师师相承,谨守训辞,毋得改易。”[15]93与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盛况相比,汉代儒学的发展缺乏学术的交流和融通,已经失去鲜活的动力。师不仅是学术主宰,而且与君、父一样拥有无上的权威。在师道权威下,弟子往往敝于师说,埋头于皓首穷经的故纸堆中,缺乏思想的创造性。学术失去批判性、兼容性和创造力,学人的思想日益僵化,唯命是从。严守师道权威,归根结底,还是拜倒在皇权意志的权威下。
简言之,用儒学来控制学人,用官禄来诱引学人,用师道权威来压倒学人,是汉统治者针对知识群体进行思想专制的一种手段。在“以吏为师”的设计里,“民之师”观念下的教育早已超出传道、授业、解惑的范畴。它是以德教民的一部分,是一种更高级意义上的德治。
三、“以吏为师”的历史启示
“以吏为师”使得皇权通过官吏实现了对百姓言行的规范和疏导,保证了国家意识形态对基层社会的有效管控,彻底实现了皇权意志对于人心的控制。它给予我们的历史启示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以吏为师”其实是皇权圣化的产物,归根结底就是以天子为师。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崇拜圣王的国度。“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16]31天子的权威无边无际,圣王的光芒普照一切。圣王崇拜“决定了民只能是圣人的依附者和附属物,在圣人养民的前提下,庶民百姓从身体到灵魂都要受到圣人的宰制,人们是没有任何主动性的”[17]309。千百年来,我们的民族基本上都是在圣王和暴君的怪圈中打转转。在天子圣明、君师合一的观念下,帝王不仅是天然的政治权威,而且还是道德仪表和文化权威。人们都要不容置疑地聆听“圣言”“圣训”的教诲,都要无条件地接受“圣断”“圣裁”的结果。承接皇权意志的“以吏为师”,实则就是圣王观念的延伸。人们接受了天子的神圣,自然也就对天子委派的官吏深信不疑。因为官吏是代天子牧民的,是朝廷命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就等同于天子。《史记索隐·绛侯周勃世家》谓:“县官谓天子也,所以谓国家为县官者,《夏官》‘王畿内县即国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县官也。”[2]2079“县官”与“天子”互训,意味着基层官吏与民众的接触被观念性地构制成为一种“如君亲临”的意识形态效应。[18]“圣王”是专制主义社会精神的最高抽象,官吏的训导就是天子的训导。“以吏为师”从根源上说就是以天子为师,天子的话都是真理。
其二,“以吏为师”思想专制特征向人们揭示,思想的统一其实是对个性思想的吞噬,最理想的统治莫过于对人心的控制。“以吏为师”造就了深厚的“民之师”观念,它意味着尊师重教与权力至上的叠加,意味着官吏在民众面前就是权力和真理的化身,意味着全体民众永远成为官方说教的对象。在皇权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全体民众都要沿着官方所制定的思维方式、思维路径去思想,甚至连思维的结果都已经提前设定好了。更为奇特的是,思想专制已不仅仅是统治者的要求,广大民众也已欣然接受思想的被专制。他们习惯于听从一种思想的支配,习惯于接受一种解释,当出现不同的解释时,反而显得茫然、困惑、不知所措。汉代以来的思想专制使得我们的文化土壤上只强调思想的共性,而难以容忍个性和多元思想的迸发。简言之,“以吏为师”造就了一个顺民的社会,在这种观念主宰下,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只能是一个群体的世界,几乎没有个人的位置。
其三,“以吏为师”的专制本质说明,“民本”永远也跳不出“君本”的专制范畴。“以吏为师”所体现的为政以德、平政爱民等特点,无一不闪耀着“民本”思想的光辉。然而在“民本”背后,却悄然矗立着“君本”这个强大的、冷冰冰的身影。人们常常称道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和荀子的“君民舟水”说。可是孟子民之“贵”和社稷“次之”实质上却是为君之“尊”做铺垫,荀子的舟水比喻却是在论证“君者,民之原也”“君者,国之隆也”[19]263的主旨。皇权专制下的“以民为本”充其量只是一种治术,其终极目的则是捍卫皇权的稳固。“爱民”的君主居高临下,通过“以吏为师”向民众宣扬保民、养民、富民、教民。因为民众的一切都是君主恩赐的,就连民众的“命”也是握在君主手中。因此,“以吏为师”所体现的“民本”,实际上是以“君本”为前提条件的。“‘民本’就是‘君本’,是‘君本’的修饰性转义表达。”[20]291
总之,两汉统治者所奉行的“以吏为师”,是一个务在推行思想专制的制度。其所构造的思想统一,绵延两千多年,直到近代“五四”时期才有所松动。本文最后想要说明一点:本文并非想要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与深厚,也并非与当代的文化传承唱反调,而是旨在通过“以吏为师”来揭示中国古代皇权专制主义的本质,使人们能够清醒地看到它的弊端。我们应该反思,为什么权力崇拜、官本位意识、主宰意识等依然弥漫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为什么人们的精神生活依然受到一元性、盲从性和非批判性等惰性思维的影响?这些问题,不正是当今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需要汲取的深刻教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