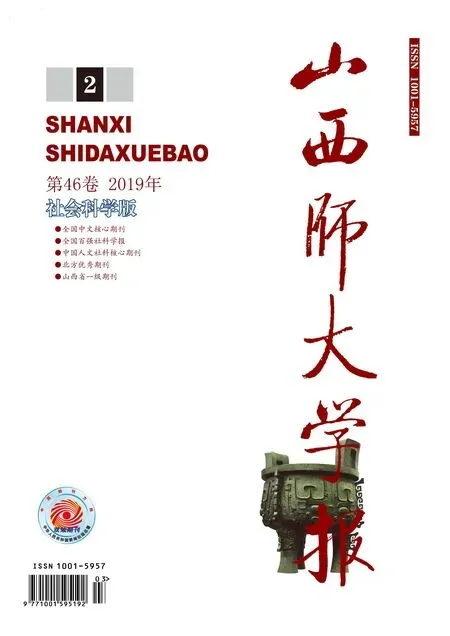论上海法租界第二特区法院的现代化司法
崔 雅 琼
(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学院,上海 200042)
上海法租界第二特区法院成立于1931年8月31日,是南京国民政府在收回中法会审权之后,于法租界内设立的第一个中国法院。南京国民政府在北京政府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司法改革。通过照搬西方法制,进行大规模的立法活动,使中国的司法配置和法律法规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向现代法制的转型。[1]204虽然第二特区法院是由国民政府依照西方法制设立,具有现代法制特征的法院,但因受地缘因素和历史因素的影响,法院现代化司法的开端,可追溯至法租界会审公廨时期。①法租界会审公廨:后文简称“法公廨”,它建于1869年4月,是法人在上海法租界内设立的,由中国政府承认并派官员会同法人共同审理华人为被告案件的审判机关。法公廨的司法权虽规定由中法双方共同实施,但是实际上掌控在上海法租界行政当局的手中。法公廨撤销后,由新设立的第二特区法院来承接它的司法工作。在这一时期,公廨的司法已经呈现出现代法制的特征,比如原告与被告的称谓、庭审程序、律师制度等。其现代司法的开端比华界地区早50年左右。[2]但是那时的司法是建立在不平等条约基础上的。例如:在遇到华人和外人的案件时,法官会偏向外人一方,或者在遇到中国审判人员与法国审判人员对案件判决意见不一致时,依照法人的意见判决。这样的司法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外国法制在法租界内的强行适用,加速了先进法治思想在租界内的传播,使租界司法现代化的发展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快于华界地区;二是国民因国家司法主权的丧失而遭受屈辱和不公,加速了中国人民收回国家司法主权意识的觉醒。
我国人民在经历了漫长、曲折的收回会审权斗争之后,法公廨被撤销。第二特区法院作为斗争的胜利成果,取代法公廨承担法租界司法工作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首先,法院设立于最早接触现代法制的上海法租界,其司法是否更接近或者达到现代法制的要求?其次,受政治因素的影响②依据收回会审权时中法双方于1931年7月28日签订的《关于上海法租界内设置中国法院协定》(后文简称《协定》)第3条规定,法院适用中国法律的同时,亦应顾及法租界的行政章程。可以得知,法人对第二特区法院的干预并未完全消失。例如,当时的法国人杜克担任第二特区法院的法律顾问。,法院在面对外国列强和政治权势之时如何司法,是否做到司法独立?
一、法院配置展现现代司法的面相
为了更好地承接法公廨的工作,避免外人对新设法院的指摘,国民政府在法院的司法配置方面,尤其是司法人员的选任上格外重视。
(一)注重司法人员的法律素养
第二特区法院的人员任用标准依照国民政府司法部法官任选标准执行。此时司法人员选用办法十分严格。比如法官资格的取得,首先需具有法律专科或者大学法律专业的文凭,才有资格去参加法官考试,考试合格后还要到地方法院进行两年的实习,之后需参加司法官再试,及格者才被分配到法院担任候补推事,如果要到正职法官还要再经过法院内部的层层考核。[3]87然而,从第二特区法院的司法人员情况来看,显然高于这一标准。
第二特区法院在设立初期共48位司法人员,其中毕业于国内法学院校的42人,毕业于日本法学院校的1人,毕业于欧美法学院校的5人,司法人员受过正规法学教育的比例达到百分之百。对比同时期的上海地方法院,其司法人员共95人,其中25人不具备法学院校的学习背景。[4]因此,从两个法院司法人员的专业教育比例上看,第二特区法院高于上海地方法院。
此外,法院的院长以及首席检察官由具备较高的专业素养、具有丰富司法经验的人担任。例如,法院的第一任院长应时(任职时间1931年8月—1934年4月)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后在瑞士洛桑大学获法学学士,在巴黎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留学英、法、德、瑞,前后共11年。曾经担任前北平法律馆副总裁、前北大法律系教授、前北平储才馆教授、前临时法院推事,并充任前北平司法部收回会审公廨委员会委员等职务。首席检察官陈备三,上任时51岁,有充备的司法工作经验,曾任浙江建德地方检察厅检察长、上海地方审判庭推事、江苏高等法院审判推事,高等检察厅检察官、江苏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5]担任本院院长时间最长的王思默先生是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的法学硕士。
由此可见,国民政府对法院任用司法人员的重视程度。法院对司法人员专业素养的硬性要求,与传统法制中行政兼任司法的情形形成巨大的反差。司法人员的专业化是司法独立于行政的基本条件,也是司法独立的基础,属于现代法制的内容。
(二)部门设置体现现代司法特征
中国传统法制没有民法和刑法的区分,法公廨时期虽然对传统法制有所突破,将案件分为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但是缺少民事审判和刑事审判应有的配置。案件只在类别上有了区分,并没有做更细致的规定。比如同一审判官既负责民事,也负责刑事案件的审理。第二特区法院完善了法公廨在这方面的不足,还设置了具有现代法制特征的检察机构。法院的审判机构和检察机构之间、审判机构内部的分工也更加细致、明确,与传统法制中民刑不分、以刑为主的“衙门司法”形成了鲜明对比。
1.民刑分离、分工细致的审判机构。首先,法院审判机构内部的分工十分细致,一改传统法制中民刑不分的审理模式。审判机构具体由各庭和负责行政工作的书记室构成。各庭包括民庭、刑庭、民事执行处、刑事执行处,以及民事调解处。其中民庭和刑庭内又分设地方庭和简易庭,对地方庭和简易庭的受案范围亦做了详尽的规定。[6]此外,各庭有固定的审判人员负责民、刑案件的审理。例如,在法院设立初期,民庭由庭长应时(由院长兼任),推事庞树蓉、罗人骥、邵梦同负责审判工作;刑庭由庭长葛之箪,推事熊彚苹、章朝佐、朱甘霖负责审判工作。[7]法院的法庭组成实行独任制,由一名推事组成,另配置一名书记员负责法庭记录。法院的组成与现代法院中简易庭的组成方式相同。
其次,对于审判之外的行政工作,比如庭审单的书写、法庭记录、判决书的送达等工作,由负责行政工作的书记室承担。第二特区法院的书记室内部组成十分庞杂,书记室下设有十二个科室,分别是文牍科、纪录科、民事执行处、刑事执行处、统计科、庶务处、赃物库、翻译室、报到处、录事室、执达员室、司法警察官。其中,文牍科是所有科室中事务最繁杂的一个科室,其下又设四个办公室来辅助工作,主要负责撰写文稿、收发文件。如此细致的分工是中国传统司法中没有的,书记室的设立为法院更好地行使审判职能提供了保障,在实现案件的审判工作和行政工作相分离的同时,也展现出法院部门设置现代化的一面。
2.法租界特有的检察制度。检察制度是西方法制进步的产物,为制止法院专权,保护受害人,确保受害人公平应诉而生。[8]国民政府将这一制度引进中国,承担对刑事案件的侦查、公诉以及对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职能。但因法院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原属于检察机构的职权被法租界警务处(巡捕房)代为行使。[注]中法双方签订的《协定》中,法方为了保留法捕房的权力,仅允许检察处对中华民国《刑法》中的第103条至第186条规定的案件享有起诉权,对检察权处处限制。导致在实践中绝大多数案件由法捕房提起公诉,检察部门只是行使参加庭审和发表意见的权力。应该认识到,虽然检察处大部分的权力被巡捕房代行,但是也是审检分离制度实现的另一种方式,具有现代法制的特色。然而,不可否认国民政府对检察权的放弃,不仅仅是其在收回会审权时的妥协,也为法人继续干预租界司法埋下了隐患。之后的历史也证实了这一点,比如上海青帮头目黄金荣就利用法人的势力和帮派的势力,操纵司法给当时的社会秩序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二、司法运行体现现代法制的特征
法院在人员任用和部门设置等外在的配置上均体现了现代法制的特征,对于法院内部司法运行的情况,通过对运行程序、审判统计、以及个案审判等方面的分析,亦得出符合现代法制要求的结论。
(一)司法运行整体呈现现代化
司法运行的过程具体可以拆分为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四个环节。这四个环节涉及巡捕房、法院和监狱三个部门。其中,案件的侦查和审判分别由巡捕房和法院负责,一改中国传统法制中由一个行政机关负责的惯例。
巡捕房对刑事案件侦查之后,对于决定起诉的案件,于受案后的第二天由捕房律师[注]捕房律师是法租界司法室的工作人员,其职能是代表法租界警务处向法院提起公诉的,相当于检察官的职务。向法院提起公诉。对于仍需侦查的案件,在将犯罪嫌疑人交由法院开庭审理后继续带回捕房收押,对已经侦查结束的案件则在法庭庭审结束后,将犯罪嫌疑人押于法院看守所。民事案件则由原告自己向法院提交诉讼状,之后进入法院审判环节。
首先,由各庭对案件进行分配。民事案件由庭长按照收受时间分配于民庭推事,刑事案件由当日值班推事直接受理分配,确定开庭日期,再由纪录科书记官负责通知答辩律师、捕房律师和检察官莅庭。根据法院年度审判统计工作显示,在法院稳定时期[注]1933年度至1935年度为法院的稳定时期。依照民国年度统计时间为当年的7月1日至次年的6月1日,这三年度时间即为1933年7月—1936年6月。民事庭年均受理案件7814件,刑事庭年均受理案件5696件。除去法院休息日,民事庭5位推事平均每天要审理5—6件案件,刑事庭的5位推事每天要审理3—4件案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值得一提的是,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年度审结率非常的高。以1934年度为例,民事案件结案率为94.2%,刑事案件的年度结案率为98.9%,接近百分之百。[7]这一数据可以说明,法院很少出现长期羁押的案件,证明法院审判运行状况良好。
其次,案件在审理的过程中有明确的诉讼程序。比如审判刑事案件,先由推事确认被告人的身份,再由捕房律师宣读起诉意见书,之后由被害人或者其代理人进行陈述,双方当事人及各自的律师开始法庭质证。[9]值得注意的是,刑事案件的审判增加检察官列席,对案件审判发表意见,此时的庭审已有标准的庭审程序,而且这种庭审程序与现代庭审十分近似。此外,案件的审理时间亦在8小时工作时间内进行,如:开庭时间一般为上午9时到10时,下午2时至3时。
最后,案件的执行环节,对民事案件的执行和刑事案件的执行有明显的区分,不再是中国传统中的对所有案件一律适用笞、杖、徒、流、死进行判罚。对于民事案件的执行,由民事执行处来负责,由执行推事带领被执行人到会计科缴纳现金及物品等,与现代法制中以金钱给付为主的方式相同。刑事案件则由刑事执行处接到科刑通知书后,将犯罪人交由监狱部门依照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执行,刑罚种类亦是现代刑罚中的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
(二)案件的审判体现现代司法理念
首先,绝大多数案件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审结。[注]《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羁押被告,侦查中不得逾二月,审判中不得逾三月。如需延长羁押期间,侦查中不得逾二月,以延长一次为限。参见吴瑞点校:《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章 被告之羁押)》,上海法政学社出版,1935年,第23页。以1935年度为例,本年度的民事案件共7568件。除去3352件属于民事调解的案件,剩下属于普通审判程序的4216件案件中,一个月内审结的有2170件,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审结的有1036件,剩余的10件在三个月以上完结。4605件刑事案件中,不满一个月审结的有4164件,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审结的有408件。[10]
其次,明确区分主犯、从犯、教唆犯的量刑。法院在审理共同犯罪的案件时,注重对每个被告人在案件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定性,最后在判决书中写明被告在案件中是主犯还是从犯,并体现在具体的量刑中。例如,1935年10月法院对有着“江北皇帝”之称的顾竹轩教唆杀人案的判决,在本案中共有四个被告,主犯王兴高、被雇凶手赵广福、帮助犯张亭桂,以及教唆犯顾竹轩,他们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20年,以及有期徒刑15年。[11]显然法院依据他们所起的作用,在量刑上进行了区分,在其各自的判决书上也有明确的量刑理由。
最后,对死刑的慎用。在法院的稳定时期,共审理了29件杀人案件。其中被判处死刑的有2人,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有2人,判处10年至20年有期徒刑的有15人,无期徒刑有10人。三个年度中因杀人被判处死刑的比率为6.9%。查看两名死刑犯的相关档案,其中一人王得玉因报复杀害13岁少年,因犯罪手段极其残忍,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公愤,被判处死刑。[12]另一个被判处死刑的是顾有亭,判决书上记载了其持枪抢劫,并在逃跑过程中打死一人,打伤一人的犯罪行为,属于犯罪后果严重的情况。[13]两件死刑案件的共同点都具有犯罪手段残忍,犯罪后果严重,且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的特点,与当代的死刑判决标准相似。此外,依据每件案件的庭审记录单可以看出,绝大多数杀人案件经历5—9次的开庭审理。例如,富德利克杀人案经历了9次开庭。[14]杀人案经过多次开庭的情况也证明了审判人员对杀人案件的谨慎。
综上得出,第二特区法院无论是在司法运行过程中,还是在案件审理上,都体现了现代司法的一面。
三、隐藏在第二特区法院现代化司法下的黑暗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处处体现现代法制特征的法院。但是仅凭这些就认定法院司法达到现代法制的要求未免有些草率。第二特区法院现代化司法是否只是表象?体现现代法制理念的司法独立是否落实在司法实践中?
(一)司法过程中的刑讯逼供现象
我们从29件杀人案一审(即第二特区法院)档案中看到的是审判的高效性、合法性,然而在查看29件杀人案的上诉情况时,却有6件案件记载了在第二特区法院审理的过程中,遭受刑讯逼供的情形。29件杀人案中,选择上诉的共有24人,在其上诉答辩状中有6人声称自己是因在一审中受到刑讯逼供,才被迫承认杀人行为的。例如,张殿臣在其上诉答辩书中这样表述到:“用严刑吊拷、摩电等,迫令承认单独杀害顾道生。经一星期之时间,实因畏刑,极残酷,无法乃含冤承认……”[15]其余5人的上诉答辩状中也可以看出,当时主要是用吊拷、电摩的方式进行刑讯。除了档案资料中记载的刑讯之外,在一些传记、著作中也可以看到法捕房刑讯被关押者的记载,比如《史良自述》中记录了她作为熊氏兄弟的辩护律师,到法捕房去会见他们时,他们正在被巡捕刑讯逼供的情形。[16]14以及1942年档案记载的法捕房对一个被怀疑盗窃的8岁男孩多次用刑的事例[17]252,可见刑讯在法捕房并不鲜见。
刑讯现象的普遍,与提倡民主、法律条文和司法配置上已达到现代化的法院显得格格不入。刑讯逼供反映了司法落后的一面,从根本上说是现代司法理念没有真正地在司法中践行,现代司法的外形下是法制的落后与黑暗。
(二)司法为权势左右
说到旧上海的权势,势必会联想到当时的帮派势力。其中与司法密切相关的就不得不提青帮头目黄金荣。黄金荣曾在法租界巡捕房任探长、督察长达34年之久。[注]黄金荣曾任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一职,是华人在法租界警务处担任的最高级别。参见朱晓明:《上海法租界华人巡捕研究》,载《史林》2012年第1期。这期间勾结社会的地痞流氓,行尽敲诈勒索、绑架之事,依仗法国殖民者的势力贩卖毒品,开设赌场,从中谋取暴利。[18]256他在自己所著的《黄金荣的自白书》承认:“成了巡捕之后,是我罪恶生活的开始……成为法帝国主义的工具,来统治和压迫人民。”[2]作为司法机关的巡捕房竟成了法租界中恶势力的保护伞,可以想见当时司法的黑暗。
此外,反映当时的权势左右司法的又一力证是对顾竹轩教唆杀人案的审判。顾竹轩有着“江北大亨”“江北皇帝”之称,在上海的势力不可小觑。当他被控以教唆杀人的罪名时,其他帮派便借势打压顾的势力。比如,黄金荣为了打击顾竹轩的势力,利用其与捕房的关系对顾落井下石。[19]最后,案件经过了三级审判,用了15年的时间才告终结。一个案件审判用了15年的时间是十分荒谬的,这背后反映的是司法被帮派势力和当权者操控的事实。
而顾竹轩本人也被其亲信王兴高指证说,曾在上海策划多起谋杀案件,其中至少杀过7位有名望的人物。[20]95可见,当时上海司法混乱和黑暗。难怪曾任公共租界临时法院院长的何世桢先生,回忆法院的工作时写道:“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什么‘司法独立’,全是胡扯!……还不是依靠外国人的力量,才幸免于蒋介石的行政干涉么。”[21]81
第二特区法院的司法状况只不过是当时社会法制的一个缩影,南京国民政府对西方先进司法制度的效仿,引进先进的司法理念,并不代表司法制度的有效性。[22]558—559在时局动荡的外在环境下,在外国列强和政权的束缚下,在有着几千年行政司法合一的法制传统中,要想真正实现司法独立公正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
四、法院现代司法的实践困境
第二特区法院地处的上海法租界,是我国最早接触西方先进司法制度的地区之一,在法院设立之前,具有现代法制特征的理念和制度就已经在此传播和实施,这里的法制环境相比其他地区来说更有利于现代司法制度的实施。然而,从法院的司法实践来看,所谓的现代化司法只不过是一个形式。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以及行政左右司法的传统思想,是导致司法形式化、司法独立不可行的根本原因。
(一)动荡的社会环境使司法独立丧失实现的土壤
司法独立指的是法官独立、审判独立,判决的执行不被任何利益干扰。具体来说司法独立,首先要有独立的司法组织,从形式上做到与行政组织的分离;其次,为确保司法公正,法官不应受任何外来的干扰,应结合自身的法律知识和案件事实作出判断;最后,司法只为实现法律的目的,维护法律的尊严,不能成为任何权力的工具。它源于法律,只服务于法律。[23]205
显然依照这一标准,第二特区法院的司法独立只是形式上的独立。晚清政府的昏聩无能,西方列强对我国司法主权的践踏,加速了国民改良国家落后法制,引进外来先进司法制度的思想意识的觉醒。为我国改变行政司法一体、司法听从于行政、法制意识薄弱、贪腐丛生的社会现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然而遗憾的是,法租界的民众并没有真正地了解先进的法制,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最初接触这些现代法制的方式是被迫的,它带着侵略色彩,在被认知的过程中伴随着痛苦和屈辱。另一方面是法国侵略者在上海通过不断的越界筑路,以及与中国当政者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等行为,将法租界不断地扩大,并逐步掌控租界行政和司法,使租界成为“国中之国”。在这个“国中之国”中,外来侵略者开始深谙我国行政干预司法之道,租界内领事官对案件有最终的决定权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对于租界内的民众来说,其压迫国人的本质与清政府等政权组织无异,法人的到来只不过是掌权者的更换,并且带来了些新鲜的做法而已。这样的认知,显然不利于现代法制的发展,司法独立也是妄谈。
虽然经过之后的斗争和努力,民国政府收回了法租界的会审权,设立了隶属于自己司法体系的法院。但是因为民国政府的妥协,法人仍可以对法院的司法进行干预。蒋介石为了稳定政局,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依附外人的势力,使租界内法人的权势依然不可小觑。此时的法院受到来自外来殖民势力和政权势力的双重束缚,租界内帮派势力的纷争,租界各路军阀的混战,加之恶劣的政治环境,使司法独立的主张只能化作泡影,沦为当权者操纵司法的工具。
(二)传统的司法理念使现代化司法流于形式
第二特区法院司法运行过程中呈现的现代化审判程序、法定审理期限内审结案件、区别主、从犯的量刑,以及慎用死刑等司法实景,符合现代法制的要求。但是司法过程中出现较多的滥用私刑、司法机构与社会恶势力相勾结,以及依仗权势操纵司法的现象,又将被认为已经达到现代法制要求的司法打回了原形。法院司法的现代化只是一个表象,只是在形式上完成了向现代法制的转型。
出现这种司法形式化的根本原因是由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造成的。当外人司法独立的法制理念猛然传入被君主专制制度统治几千年的中国时,民众的反应是震惊的、不接受的。我们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认知和接受,因为任何一个异化事务的引入,都需要一个吸收、同化、与本地的传统习惯充分“磨合”的过程。但是对于西方先进司法制度的引进方式,不是被殖民者强行适用,就是被当权者生硬照搬,以图用引入先进司法制度的办法挽救或者稳定他们的统治。以如此方式传入,虽然使民众知道有这样的法制理念,但是很难取代已根深蒂固的传统法制思想。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国人对于西人法制思想十分抵触,常见报纸上将聘请律师称为“怪的现象”;对袁世凯的复辟,许多民众认为是正统的巩固,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事情;就连在政法学校读书的学生也无法分清专制和共和的差别。[24]375足可见当时民众对现代法制理念的陌生和排斥。
南京国民政府为了解决出现的法律危机,提倡社会本位的司法理念,但是其适用效果却与预设相反。社会本位理念的提倡反而为伦理大于法制,司法服务于行政提供了合理的借口,是与中国传统法制理念的暗合。几千年来,中国民众思想中法律从来不代表权利,它是统治者威吓、束缚、惩治人们的工具。在义务本位的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律永远是听从于政权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特权意识,以及“以和为贵,息讼止争”的贱诉意识,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就被替代。
南京国民政府一面实行法制现代化的改革,一面宣扬“以党治国”的主张,就注定与现代法制背道而驰,出现现代司法流于形式的局面。即使法院中有一些到西方学习现代法制的司法人员,并且这些司法人员也曾想过成为司法独立、公正的捍卫者,但是在面对这样的治国理念和主流思想时,也只能随波逐流,任凭权势者左右。
综上所述,通过对第二特区法院相关档案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对当时的第二特区法院的司法有了更真实、公正认知。法院司法独立的难以实现,为权势操纵的实景,折现出民国司法的状况。盲目照搬西方法制,忽略了本国国情,导致先进司法制度难以与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的思想真正融合。再加上屡开战事、社会动荡,现代法制理念缺少稳定的传播环境,以致出现司法现代化仅是形式上的,而实质仍是传统法制为主导的局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民国司法改革开启了向现代化法制转变的大门,在转型期出现的重复与迷茫也正是其变革价值的体现。第二特区法院司法的经验和教训也为当下的法制建设提供了借鉴,裨益于未来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完善。也正是经过这种检验、再检验的历史过程,才能真正修正我们曾固守的错误理念,推动我们的司法朝着更完善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