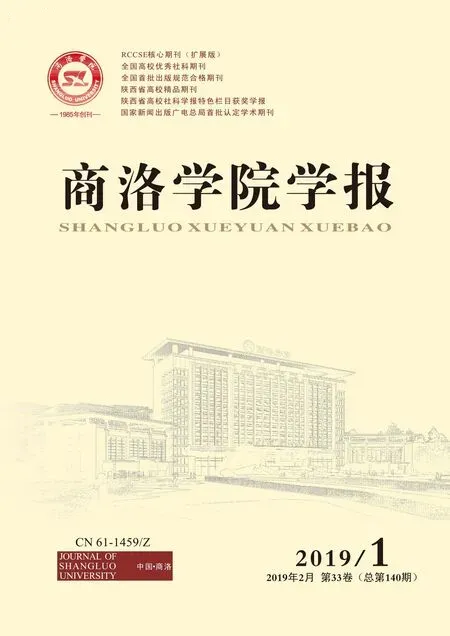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纠葛
——论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
张瑶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119)
王瑶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是为适应建国初期高校学科调整而应运产生的第一本新文学史教材,其上、下册分别由开明书店和新文艺出版社于1951年9月和1953年8月出版。《史稿》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的“书写范式”,它自觉地以正史的姿态融入集体的时代合唱,向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靠拢,努力“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1]3,为新文学的发展灌注了《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内容。这无疑体现了要求进步的王瑶在建国初期意欲将自己的学术生命与渴盼已久的新政权、新社会相结合的炙热心情,即如他后来所言:“此书撰写于民主革命获得完全胜利之际,作者沉浸于当时的欢乐气氛中,写作中自然也表现了一个普通的文艺学徒在那时的观点。”[2]但王瑶也深知学术研究在遵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的同时,绝不能将其作为“套语或标签”,“来代替对具体现象的历史分析”[3]6。这也便使得《史稿》呈现出了两种话语体系的碰撞与纠葛,交织与变奏[4]。在附和主流话语叙述规范的过程之中,王瑶一方面意欲借用新文学史的抒写为新政权的合法性“正名”,但另一方面,当论及具体文学现象时,他又尽量调解集体化的政治话语与个人化的学术话语之间的矛盾冲突,试图使两者达成某种微妙的契合和共鸣。
一、绪论的设置
事实上,王瑶在早年即以“左翼理论家”自诩,在清华时便有“小胡风”和“小周扬”的绰号。他于1935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在担任《清华周刊》和《新地》杂志编辑期间,发表过诸多分析中国时政局势的政论文,在30年代便极力推崇文艺的社会功用,强调“新的文艺是时代的号炮,是民众的传声筒”[5]16,并盛赞集体创作“使文艺达到一个更高级的发展”[5]20。恰如钱理群教授所言:王瑶“是首先成为一个‘政治活动家’的,到40年代师从朱自清先生以后才走上学术研究道路。”[6]并且,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一方面努力研究学问,希望成为一个学者;一方面也对民主运动多少做点事情”[5]266。所以,王瑶无疑是以主人翁的姿态来迎接新中国的成立的,建国后日趋强化的革命意识形态与他自身所持有的左翼知识分子的特质构成了相对和谐的共同体。他在未转向新文学研究之前便认为进行古典文学研究需要具备三方面的基础,即“古书的知识,包括历史和文学;历史唯物论;马列主义文艺理论”[5]265。而历史唯物论和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即是建国后集权化的教育体制要求学术研究所应遵循的“新观点”和“新方法”之一,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者要将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在特定时期所形成的文艺思想作为进行新文学史叙述的“元话语”。这也无怪乎王瑶在对新文学展开论述之前,专辟《绪论》一章,主要以《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理论思想为依托,借以阐释新文学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
《绪论》的设置展现着著者的文学史观,我们甚至可以将统摄全书的《绪论》看作是文学史著作的“微缩版”。在《史稿》中,《绪论》下分四小节,分别为“开始”“性质”“领导思想”和“分期”。王瑶在“开始”部分便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新文学所呈现出的斗争性与工具论的色彩,继而先验式地认定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是和政治斗争密切结合着的”[1]1,并借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关新文化的经典论断点明了文学服务于政治的附属地位。而在“性质”一节中,他更是径直地为“新文学”之“新”赋予了更为先进的时代内涵,文中说:新文学“是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服务的,又是新民主主义的一部分,因此它必然是由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文学。简单点说,‘新文学’一词的意义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学。”[1]8并且,为了进一步说明新文学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紧密关系以及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地位,王瑶还在指出新文学政治属性的同时,比附《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中国阶级地位变化的相关论述,向读者勾勒出了一条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不断消亡,无产阶级文艺思想不断增长的清晰线索。他在书中说道:新文学“也包含一部分具有民族独立思想和反封建内容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但其比重和地位却是随着时代而日益减低的”[1]6,而“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一个时期比一个时期更加突出,巩固,扩大,并逐渐走向健全和完备地步的”[1]10。他不无牵强地认为“新文学自始即是为共产主义思想所领导的”[1]10,并将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二卷一期上的《青春》一文看作是“已经表示出无产阶级先驱者为民主革命献身的勇敢精神”[1]11。而实际上,《青春》所要表达的仅仅是对于青年冲破樊笼,重拾朝气的美好希冀。由此可见,在《史稿》的《绪论》中,王瑶采用“我注六经”的方式,以革命政治话语为主要依托,以“革命史观”作为论述的基础,为《绪论》注入了强烈的政治功利性色彩。这也便使得主流的政治权力话语淹没了个人化的学术话语的自我表达,文学的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特征也因此得以加强,对于无产阶级的倾向性占有支配了严谨繁复的学术考证,鲜明的革命意识形态完成了对文学史叙述语言的收编与征用。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绪论》完全就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图解和演绎,而是对其有所取舍的。具体来说,王瑶在《绪论》中重点抓住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中所提出的“统一战线”的思想和新文学所持有的“反帝反封建”的特性,而并未着重突显无产阶级对其他各民主阶级的改造。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本身就具有过渡性质,其国体为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式,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7]676,而“现阶段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7]706。所以,王瑶便以此为理论依据,在论述完新文学的性质之后,又刻意提醒道:“就作品的思想内容和作者所代表的社会阶层来说,它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样是统一战线的,包括各民主阶级的成分”。“五四以后,随着中国革命的进展和社会的激剧变化,很多作家都经过了思想上的进步和转变”,“如果片面的,就作家的出身或某一部作品来指定他的阶级属性,是很危险的事情”[1]8-9。而且,他还将中国新文学的历史认定为“是在鲁迅、毛泽东所领导的方向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并指出“鲁迅就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那个时期之最正确完备的体现”[1]15。众所周知,鲁迅在前期还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此,王瑶对于鲁迅经典性地位的重申既符合毛泽东对于“鲁迅方向”的论断,又有利于吸纳更多的作家入史,这就为文学史的叙述提供了一个相对开阔的“弹性空间”[8]。
换言之,王瑶虽然在绪论中,突出了新文学所具备的阶级属性和无产阶级在新文学中的领导地位,但他在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按照政治态度对作家进行阶级定性时,却并未如之后的文学史叙述者那样,急切武断地为作家划分队伍,并对其予以“棒杀”,而是以科学实证的态度,结合历史语境,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他的论述基本上还是在比较合理的范围内进行的。他在后来也曾指出:“小资产阶级思想是有其社会基础的,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合法的,是不可能完全消灭的。”[5]271也就是说,王瑶充分意识到了新文学中阶级结构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并为后文中所涉及到的具体的文学批评设置了一个可适调节的“缓冲阀”。而这也正反映出了王瑶在编写《史稿》时的矛盾心态,他一方面小心翼翼地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纲领,唯恐其叙述与之相违背;而另一方面他又担心因结论过于绝对以致丧失文学史景观的丰富性。实际上,这一矛盾心态也体现在他对于《史稿》的框架与体例的编排上。
二、框架与体例的编排
韦勒克、沃伦在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中指出:“大多数文学史是依据政治变化进行分期的。这样,文学就被认为是完全由一个国家的政治或社会革命所决定。”[9]261而王瑶对于新文学的分期则显然受到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文化革命”分期的影响,并把每一个时期的分期状况与之相对照[10]。他以“五四运动”为起点,将1919年至1949年这三十年间的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并在《绪论》中略微叙述了每一个时期的文学发展状况及特点。这四个时期分别为:第一编《伟大的开始及发展》,包括的是1919年至1927年这十年间的文艺发展情况,与之相呼应的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论述的“文化革命”的第一和第二个时期;第二编《左联十年》,包括的是从1927年革命阵营分化之后至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的文艺成就,相对应的则是毛泽东所说的“文化革命”的第三个时期;第三编《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包括的是从1937年7月抗战爆发之后到1942年《讲话》发表这一时期的文艺发展;第四编《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刻画的则是1942年《讲话》发表之后至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召开这段时间的文艺发展及新变。由各编的标题可以看出,王瑶想要着力描摹的是新文学随着革命形势的持续推进而不断发展壮大的情形,并且,与此相应的是,在《史稿》中各编的篇幅比例也是随着这条历史线索而不断增大的,第一编共有114页,第二编共有176页,第三编共有203页,而到了第四编,则有241页[11]。由此可见,文学自身的价值体系被固定在政治的框架之内,文学发展所遵循的内在的规律并没有在《史稿》中得以充分体现,在各编篇幅比例不断增加的背后隐含着的则是作者对于取得胜利的新生政权的推崇与歌颂。
当然,这种依靠政治事件划分文学史的方式在当时特定的语境中无可厚非,更何况,王瑶在对文学史的分期中还多少照顾到了文学自身演变的特点。这一点便体现在他对“1921年”这个年份的处理上。1921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年,理应被当作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突出强调,例如刘绶松在1956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便将新文学的第一个阶段设置在了1917年至1921年间。但王瑶却在《史稿》中谈道:“‘五四’初期,还没有纯粹文艺性的社团和期刊,许多主张都发表在《新青年》上,然而从全体看来,《新青年》到底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批判的刊物”,“因此,不可能有更多的力量和篇幅来照顾到文学,尤其是创作。所以在1919年到1921年的两年中,就文学史说,就值不得分为一个独立的时期”[1]15。也就是说,王瑶对于文学史的分期并不是对政治史分期的盲目对应,而是秉承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从最基本的历史史实为入手,对其进行细致的考证辨析。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他对于“1942年”这个时间节点的阐释与说明。王瑶之所以将1937年至1949年期间的历史拦腰截断,是为了突显毛泽东《讲话》的重要性,如他在书中所言:“我们不以抗战八年为一期,而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分期的界线,就因为这讲话实在太重要了”,“而且,历史证明了这讲话全部的高度正确性”[1]18-19。但他对《讲话》思想的诠释与注解却又是有所保留的。他认为《讲话》的突出成就就是确定了“人民本位”的方针,就是把“文艺为什么人与如何为的问题”弄明确了,解决了左联所提出的“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即作家与人民群众关系的问题,但却并没有重申由《讲话》所确立的“政治批评第一,艺术批评第二”的批评标准,并且,他还在正文中说道:绝不能将“文学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狭义地“理解为不允许写别的人物或生活”[12]216。即使是到了新时期,王瑶也仍重申毛泽东在《讲话》中所解决的文艺与人民关系的问题,是“我们今天仍然必须坚持的科学原则”[3]252。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王瑶在注重政治与文学深层互动的同时,也以政策阐释者的身份采用有意淡化某些言论的方法表达了作为个体的自我对于领导者文艺思想的看法。实际上,王瑶对《史稿》体例的编排则更显示出了他作为一个学者所具有的敏锐的眼光。
一本书的体例体现着全书的整体框架与面貌,它是一定内容的外在表现形式。《史稿》体大思精,共收录300多位作家的创作成果,涉及作品近千部。它采用的是“文体型”叙述模式,在每一编之后又下设五章,第一章先以适当的篇幅总论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历程,涵盖文学运动与思潮、思想论争、创作趋向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而作为全书重点的其余四章则分别论述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这四种文体在各时期的创作实践。并且,王瑶在每一章后又以作品描写的主题为组织单位,下分若干小节,尽可能地从纷繁错杂的历史现象中概括出某类作家作品的共性,体现其典型特征。如《史稿》第一编的标题分别为《觉醒了的歌唱》《成长中的小说》《萌芽期的戏剧》《收获丰富的散文》,其中在《觉醒了的歌唱》中又下分“正视人生”“反抗与憧憬”“形式与追求”等三小节的内容。而读者也很容易从这言简意赅而又准确生动的标题中窥探出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基本面貌。并且,我们如果将每一编中各章的标题串联起来,也能大致勾勒出一条文体自身发展演变的脉络。以诗歌为例,他将这三十年来诗歌在各个时期的发展状况分别命名为:“觉醒了的歌唱”“前夜的歌”“为祖国而歌”以及“人民翻身的歌唱”。相较而言,这固然是一种较为政治化的表达方式,但也确实反映出了诗歌在每一时期所具有的鲜明的时代特色。
由此可见,《史稿》并没有“企图把文学史作为文艺思想的斗争史,甚至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插图’”[3]610,也没有“把文学史简单地变成作家作品论的汇编”[3]4,更没有只把目光放置在少数重要作家作品上,而是深入到原生态的历史现场,展现新文学的总体历史进程,注重文学自身的本体特征和发展演变以及文学与时代的紧密联系,它突出的是对现象群体的研究,而非对个别的文艺现象进行孤立地考察探究。实际上,这也正显露出了作为学者的王瑶所一以贯之的文学观念。他认为:“文学史不能以文学运动为主,尤其不能以政治运动为主”,而“应该以创作成果为主要研究对象”[3]14。“作为历史科学的文学史,就要讲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讲重要现象的上下联系,讲文学发展的规律性”[3]4。简言之,王瑶对《史稿》体例的编排充分表现出了他对于文学本体意识的重视,而这也正与主流政治权力话语形成了明显的张力。所以,在当时日渐左倾的文学生态中,就有评论家以此为依据,对《史稿》进行批判。如曾有论者指责王瑶在《史稿》中对于各编的命名是“随心所欲的生造出一些奇奇怪怪的题目”,“更严重的问题是在这种形式主义的体例下面,王瑶先生不问作家的流派、主次、进步与落后,更不问作家的思想是革命还是反革命,一律平等相待”,这就使文学史“根本看不出同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全貌,主流与逆流的斗争,文学主流的成长、发展;看不出文学发展与社会现实阶级斗争的关系”[13]。其实,这也正从侧面反映出了王瑶并没有对所选作家做抽象式的简单化的处理,而是坚持从作家作品的质量与数量出发,对其进行评述。那么,在这种评述方式中,他又是如何处理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之间错综复杂的纠葛的呢?
三、作家作品和社团流派的选取与论评
一般来说,文学史是作为经典化了的文学的历史,文学史写作的过程即是编纂者依据于某种价值判断和评价体系对历史现象不断进行剔除筛选以至改写重构的过程。甚至可以说,“在文学史中,简直完全没有属于‘中性’事实的材料”。“初步简单地从一般著作中选出文学作品,分配不同的篇幅去讨论这个或那个作家,都是一种取舍与判断”[9]28。那么,王瑶又是如何对新文学中浩如烟海的作家作品与社团流派进行选取和论评的呢?
我们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在《史稿》中的“失踪者”。通览《史稿》,我们会发现王瑶在第二编中并没有对作为三十年代文坛重要组成部分的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的相关情况进行系统地介绍与描述。他只是在谈及到三十年代文艺论争时,轻描淡写地说道:“关于杂文的价值,京派与海派,标点明人小品等,都曾引起过一些原则性的论争,我们从鲁迅杂文及《乱弹及其他》这些书中都可以找到那战斗过来的痕迹。”[1]168但论述也就仅限于此。王瑶在后文中除了对沈从文、芦焚、卞之琳等几位京派作家进行零星的评述之外,再也没有花费过多的笔墨铺陈这两大文艺阵营的创作情况,而是选择对其进行“遮蔽式”的处理。实际上,这样做正好论证了毛泽东所提出的“国民党实施文化‘围剿’失败”的观点,并凸显了左翼文学在三十年代文坛的主流地位,给读者留下了革命文学尽领一时风骚的印象。所以,王瑶也就直接将第二个十年命名为“左联十年”,并声称:“左联的组织形式虽然从成立到解散只有六年(1930—1936),但这十年期间整个可以说是由左联来领导的。”[1]17那么,以此类推,为了显示出四十年代解放区文艺所呈现出的盛状,为了展现由《讲话》而带来的“新的人民文艺”茁壮成长的广阔前景,作为与《讲话》所传达的精神相异甚至是相逆的作家与流派如张爱玲、钱钟书,九叶诗派等,则自然会被《史稿》排除在外。
但不可否认的是,王瑶还是比较有魄力地让一些在当时就存在争议的作家与流派享有了“入史”的资格,并对其给予了相对公允的评价。如王瑶在论及周作人时,并未以他后期的“变节”作为评判的标准,进而因人废言,抹杀他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全部贡献,而是实事求是地承认:《人的文学》“虽然说得很笼统模糊,但算是当时的正面意见”[1]30,“《平民文学》《新文学的要求》等文章,对当时的运动也发生过一些影响”。并且,他还指出:“在《自己的园地》和《雨天的书》里,还有一些现代人的感情和思想,不满意于现实和封建文化的文字,虽然也并不就怎么‘勇敢’。”[1]131又如,他虽然指责新月派所宣扬的“人性论”思想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论调,并将新月派与左翼文学的论争视为促成左联成立的原因之一,但他也同时意识到:“格律诗的提倡至少在当时有一种澄清的作用,使大家认为诗并不是那么容易作,对创作应抱有一种严肃的态度。”[1]75而且,当论及到新月派中的具体诗人诗作时,他主要还是从审美的角度出发肯定该流派对于诗歌形式的独特追求,当然,其中也不乏对个别诗作所流露出的“颓废”“病态”色彩进行一定的批判[14]。在文中,他引用茅盾的评价将徐志摩定位为“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并用极为精简的言语道出了徐志摩诗歌的艺术特色,即“章法的整饬,音节的铿锵,形式的富于变化”[1]74。而他对于闻一多诗歌的评述则更是不惜赞美之词。在王瑶看来,“闻氏正是一位忠于诗与艺术,引导新诗入了正当轨范的人”[1]75,“他的诗谨严精炼,是抱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严肃创作态度的”[1]76;并且,在他诗歌中还体现出了一种爱祖国和为人民的精神。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王瑶还在《史稿》中选取了在四十年代就被郭沫若斥为“御用文人”的沈从文的作品进行了点评。他虽然从题材入手对沈从文的小说颇不满意,认为他的小说是在“有意借着湘西、黔边等陌生地方的神秘性来鼓吹一种原始性的野性力量”,而作品的传奇性则使得小说“脱离了它的社会性质”,以致沦落为“一个奇异哀艳而并无社会意义的故事”。当谈到沈从文的艺术风格时,王瑶也不无中肯地认为:沈从文“运用文字的能力是很强的”,“他的文字自成一种风格,句子简练,‘的’字用得极少,有新鲜活泼之致”[1]236-237。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从上述内容看出王瑶在《史稿》中所秉持的评价标准与价值观念。在他看来,“题材本身的意义实在是最重要的”[1]110,“笼统地反对或赞成一种文体都是没有意义的,这主要需看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内容”[1]302。并且,在《史稿》中,与作品的思想内容相对应的创作手法也暗含了某种价值立场。王瑶曾在文中说道:“只要是尊重‘五四’文学革命的民主主义传统,愿为人民革命服务的作家,那就只能是现实主义和反抗的革命的浪漫主义。”[1]49因此,在论评作品时,王瑶往往首先衡量的是这部作品是否具有革命性与反抗性,是否运用了现实主义手法或所谓积极的浪漫主义手法反映了人民大众最真实的生活,是否在其中透露出了一种强烈的爱憎情感与昂扬向上的战斗精神。这也便使得《史稿》成为了“一部主要由‘不满’‘反抗’与‘革命’三种政治声部所合成的史学三重唱”[15]。而王瑶之所以会在评述作品时着重凸显其社会意义,既在于他要遵循当时主流的叙述规范,也离不开他在早年所受到的左翼文艺传统的影响,以至于到了八十年代,他仍坚持将沈从文定位为“名家”,而不是将其划分到“大家”的行列[3]24-25。
所以,王瑶在品评《阿Q正传》时,会特意强调文本的主题并不是对于辛亥革命不彻底性的批判,而是意在说明革命的动力是要向农民身上去追求的。依据此种逻辑,也无怪乎王瑶会对叶紫的小说赞不绝口。他认为叶紫的小说真正担负起了文学的战斗责任,在其作品中,没有概念化的描写,没有感伤情绪的表达,尽管写作技巧不甚圆熟,但在文本中却含有一种健旺的精神。也就是说,作品越是贴近于工农大众,越是贴近于革命,便越是能够得到编者的青睐与赞赏。而反之,如果作品没有体现出鲜明的社会意义,则会受到一定的批评与否定。如王瑶在评述曹禺的剧作时便认为“《雷雨》的题材本来是极富于现实意义的”,但作者在处理这些题材时却“特别强调了阴暗的宿命论的观点”,这就会使得“主题被他的‘憧憬’所歪曲”,“性爱与血缘的各种巧合的伦常纠葛”也“冲淡了这个悲剧的社会性质”[1]272。除此之外,他还指出由于曹禺在《原野》中“渗入了过多的神秘象征色彩”,并且纠结于良心谴责等抽象观念的表达,所以也就使得“《原野》的现实性反逊于《雷雨》”[1]275。又如他在论及老舍的创作时,以较为严苛的态度指责《骆驼祥子》“和社会背景的联系还嫌过于模糊”,并且认为老舍“作品中的思想性是比较薄弱的”[1]232-233。再如他在评点艾青诗作时,又专门补充道:“他的忧郁本来是植根于中国人民的苦难的,与一些作家的颓废性的忧郁不同,到他与人民革命的主流汇合以后,就变为爽朗的笑声了。”[1]51并且,他还对艾青情感态度的转变赞赏有加,王瑶认为艾青在《北方》与《旷野》中已经摆脱了知识分子的情感,诗作所表达的已经完全是人民大众的实际感受了。
但如同王瑶自己所言:他在灵魂深处实际上“是把文艺和政治分开的,是二元的,而且实际上是艺术性第一的”[5]270,所以,他在反复申说作品应具有革命性与人民性的同时,也并没有因此而忽略对于作品艺术性的强调,也下意识地对一些作品所流露出的个人色彩表示了认同。如他认为冯至的诗歌“富有热情与忧郁,而长篇叙事诗尤称独步”[1]80;而李金发则善于“利用文言文状事拟物的辞汇,补足诗的想象,努力作幻想美丽的诗”,李金发的象征诗“虽难解,音调却和谐”,并且,“喜欢用替喻,讲感觉,富于异国情调”[1]79;戴望舒的《望舒草》在写作技巧上则更是有着很高的成就,毕竟,诗人“懂得怎样表达自己的情绪,‘为自己制最合自己的脚的鞋子’”[1]201;汉园三诗人的风格尽管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注意于文字的瑰丽,注重想象,重视感觉,借暗示来表现情调”[1]198。再如他还在《史稿》中独具慧眼地指出:俞平伯的散文“不重视细致的素描,喜欢‘夹叙夹议’地抒写感触,很象旧日笔记的风格。文言文的词藻很多,因为他要那点涩味,絮絮道来,有的是知识分子的洒脱与趣味”[1]127。何其芳的《画梦录》是“由象诗一样的美妙的文笔组织成的富于诗意的散文”,作者“对于每一字句都不放松,爱用赋予新意的譬喻或典故,来暗示他的美丽而飘渺的想象”。作品“文字浓丽精致,表现的是一些叹息青春易逝,多情而带颓废气息的幽思”[1]305。废名的小说“地方性很强,有鲜明的地方口语”,“在冲淡的外衣下,浸满了作者的哀愁”[1]103。萧红的《呼兰河传》则“象叙事诗或风土画一样,有着一种低徊的凄婉的情调”[12]138。由此可见,在《史稿》中,王瑶巧妙地将顿悟式的富于创见的阅读感受,成功地融入到了宏大的叙事之中。这也便使得《史稿》在张扬与压抑之间,在政治式分析与审美式批评相互缠绕过程之中,形成了独特的言说方式与叙述模式。但也正因为如此,《史稿》也便在以后频繁的上纲上线的政治运动之中,成为了被重点批判的对象。
四、结语
王瑶虽然在撰写《史稿》时无法以高蹈的姿态突破历史的局限,超越时代的束缚,但他也力图在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之间找寻可供依托的中介,在遵从意识形态指令的前提之下,保持对于学术个性的追求。实际上,无论是王瑶对于《史稿》绪论的设置,还是对于框架与体例的编排,亦或是对于作家作品和社团流派的选取与论评,都真实地反映出了他在特定年代中所历经的矛盾与困惑,以及所抱有的真诚与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