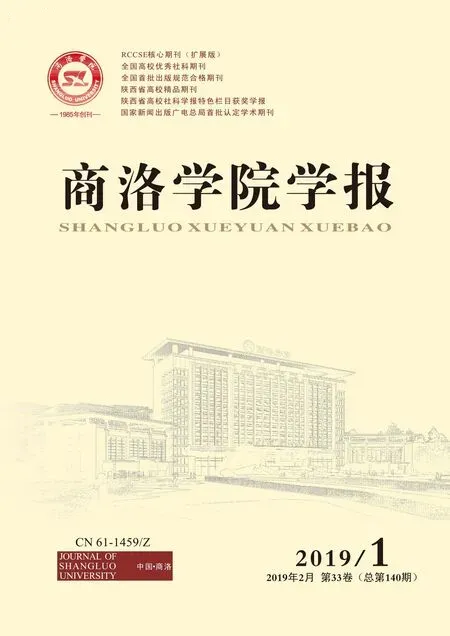秦岭的传奇性书写
——论贾平凹新作《山本》
董雯婷
(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069)
《山本》是贾平凹的第16部长篇小说,他在后记中表示,他最早的构想是整理出一本秦岭的草木记、动物记,“没料在这期间收集到秦岭二三十年代的许许多多传奇。去种麦子,麦子没结穗,割回来了一大堆麦草,这使我改变了初衷,从此倒兴趣了那个年代的传说。”[1]523在后来的一些访谈中他也数次提到了“传奇”这个词,传奇性显然已深深刻印在这部小说中了,其空间模式、人物塑造特征和当代历史小说的笔法都具有鲜明的传奇色彩,注意到这一点对解读小说至关重要。
实际上,在小说创作中对传奇性的重视和利用并不是中国当代作家的专利,蔡斯在1957年出版的《美国小说及其传统》中就写道:“我的主要的、似乎也是不可回避的主题是罗曼司或罗曼司小说与小说自身之间的关系……大多数优秀的美国小说都是罗曼司。”[2]这里的“罗曼司(romance)”在中文语境中常常被意译为“传奇”[3],虽然它在历史源头上与中国语境中的传奇不尽相同,但作为一种文学创作中的“传奇倾向”却是相通的。正如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所说:传奇(romance)的倾向“与‘现实主义’相对立,按理想的方向规定内容的固定程式。”[4]23它的范围可以扩展到从神话、传说到民间故事、童话等文学形式。尽管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它都被排除出严肃和经典文学的范畴,但在最近一个世纪中西作家们的创作中,传奇性已经不再意味着曾受到贬斥的“等而下之的文学”[5],而是指向一种具有时代特征和独特魅力的叙事笔法,在后现代时期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学原型,它在无数欧美当代作家的作品中一再出现,已经引起了许多西方理论家和批评家的注意。反观中国,以贾平凹、莫言等人为代表的当代作家同样表现出这一创作趋势。
一、一座最伟大的山——叙事时空体的传奇性
《山本》这部小说中最具存在感的莫过于秦岭了,正如作者所言:“《山本》的故事,正是我的一本秦岭之志”。小说聚焦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秦岭,并称之为“一道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着黄河长江,统领了北方南方,它是中国最伟大的一座山。”[1]1这样的表述使秦岭脱离了日常现实、进入一个传奇化的、极具象征意义的层面。苏珊·弗里德曼曾提出“空间化”的概念以对小说情节观念进行更加复杂的处理和探讨,她认为叙事不仅具有穿越时间的横向运动,而且还具有一种将叙事的横向面与文学、历史及心理性互文本联系起来的垂直维度——正是它使得情节的空间观念得以复现[6]。由于显而易见的与历史、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的关系,具有传奇倾向的小说的研究必须极其重视它们那独特的空间类型。
小说里的秦岭作为一个叙事空间,表现出强烈的、超现实的传奇性质[7]。这首先表现在其中的动植物是奇特的,具有现实中没有的属性或行为。比如小说里涡镇上的皂角树全身都长了硬刺,德行好的人经过时它就会掉下一两颗皂角。而狗会突然说了人话:老的太老,小的太小。麻县长有次坐在石桌前看书,连续三天有一只青蛙每次都爬上旁边的石桌,他说如有事你跳到我脚面上。蛙果然跳到他脚面上,他跟着青蛙来到一个石堤前的深潭,就发现了一具死尸。还有一次井宗丞在高门镇想起自己被杀的战友,在一棵青冈树下许愿:若他们死后有灵,树上的叶子就往下落。“话刚说完,树上果然往下落叶子,冬天的树叶子都是枯了,颜色仓黑,而青冈树的叶子却血红血红,竟然一树的叶子全然落下,树落得光秃秃的,落叶几乎把他的脚面都埋没了。”[1]246-247陆菊人的公公杨掌柜死去后,家里的猫来到跟前,尸体就突然坐了起来。这些奇异的、别具通灵意味的动植物和现象在小说里随处可见,贯穿始终。
贾平凹曾表示他写《山本》时,“在秦岭深处的一座高山顶上,我见到了一个老人,他讲的是他父亲传给他的话,说是,那时候,山中军行不得鼓角,鼓角则疾风雨至。这或许就是《山本》要弥漫的气息。”[1]525这也表明,秦岭的奇特故事并非只是街头“怪谈”,而是一种系统性的气质,它在形式上是世界传奇文学通行的传奇式空间。巴赫金曾以“传奇时空体”理论来概述传奇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时空模式,指出这种空间“已并非充斥着奇闻笑谈,而是充满了奇异的怪事。那里的每一件东西,如武器、衣服、泉眼、桥等,都有某种奇异特征或者干脆带有魔力。”[8]351而在《山本》中,这些奇异的特征又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万物有灵的思想,表现出中国式传奇的特色,小说里井宗丞在被杀之前抵达崇村的时候,作者详细写了他看到的一种叫水晶兰的花,这花在他眼前迅速变成了一棵枯杆,并借一个小兵之口说:我们叫它是冥花。花预示了井宗丞即将到来的死亡。文中所有关于植物、动物的异象与主人公一起,都被统摄在秦岭这个巨大且统一的传奇空间里。
其次,人物在传奇时空体中常面临着现实里难得一见的或奇特、或神秘的机遇。比如小说主人公井宗秀与陆菊人的故事就开始于那三分胭脂地,这块被风水先生预言“能出官人”的风水宝地因为机缘巧合成为井宗秀父亲的墓地,继而给他带来了时运,冥冥之中造就了这位乱世英雄。而传奇主人公的一大特点,就是在传奇空间中追逐这种奇特的机遇,并享受它带来的福利,“主人公经历完全不是只有读者感兴趣的‘灾祸’,而是他本人也感兴趣(对他也有吸引力)的‘奇遇’,传奇受它所在的这一奇特世界的影响,自己也获得了新的情调。”[8]348后来井宗秀又因一个意外机遇——岳掌柜的横死而拥有了岳家的资财,并准备给父亲迁坟,这时陆菊人告诉了他那块地的秘密,为了获得这风水宝地的福运,井宗秀立即放弃了迁坟,并从此信誓旦旦“我一定要当个官人的”。在主人公崛起过程中出现的数次奇特机遇和对这种机遇的主动追求和利用,使小说的叙事时空充满了传奇色彩。在那些传奇性最浓郁的冒险小说里,正是这种“机遇”起到了激励读者冒险的作用。
有评论家认为,井宗秀的父亲恰巧葬在了能出官人的风水宝地一节“是一个典型的‘谶纬叙事’,给全书上了冥冥无常,兜兜转转的‘暗扣’”[9]。然而纵观整部小说,井宗秀的起势与龙穴宝地间的关系虽有“谶言纬语”的特点,但却更贴近于传奇性书写。因为前者“将不同时间所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叙述,使过去发生的事件与正在发生的事件和将要发生的事件之间形成一种神秘的逻辑联系……并从叙事空间上铺陈展开,使得预测性言辞系统化、结构化”[10],在中国文学史上与史传文学有密切的关系,其所托是一种实录精神,表现的是“在某个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只不过前一件事和后一件事有“神秘的逻辑关系”罢了,而这种关系又往往与“经天纬地”“五行历运”的宏大叙事相联系。但井宗秀的发迹和灭亡同时却有着极为突出的偶然性:不仅井宗秀的父亲之死是偶然、得葬风水宝地也是偶然,就连这块地的秘密本身也源自于陆菊人偶然间窥得赶龙脉的风水先生,这使发生在他身上的谶语应验事件与巴赫金所言的传奇叙事时空体密切相关:“某件事正好发生在某段时间、甚至某个瞬间……整个世界都归结到‘突然间’这一范畴上,归结到奇特而出乎意料的偶然性这一范畴上。”[8]348井宗秀最终的死亡也是突然间就发生了,超出所有人的预料,纵观全书,包括井宗秀、五雷、阮天保在内的诸多人物的命运和儒家的五行历运并没有关系,只是某一个体的极具偶然性的崛起、抑或灭亡。与谶纬叙事相比,此处叙事显然更强调“某事正好发生在此时”,这都标志着小说中的秦岭这一独特的叙事时空体浓郁的传奇特色。
二、英雄、红颜与智慧老人——人物塑造的传奇性
在《山本》这部小说中,传奇性的又一典型体现在于人物塑造上。正如弗莱所言,传奇经常散发出一种强烈的主观意识,“它的作者不去努力塑造‘真实的人’,而是将其人物程式化使之扩展为心理原型。”[4]210尽管《山本》在塑造人物时并没有忽略真实的一面,但它对传奇性的倾向仍然是明显的,这在小说里主要表现为以井宗秀为代表的英雄、以陆菊人为代表的红颜,和以陈先生为代表的智慧老人三种形象。
小说里的乱世英雄井宗秀是一个典型的传奇式男主人公,这个人物勇猛果敢、有情有义且知恩图报,是涡镇的守护者,但同时也显露出精于算计、残酷凶狠的一面。评论家陈思和曾对照《水浒传》中的宋江来评价《山本》里的“极其残忍”“虚伪”的井宗秀:“《水浒传》里称宋江是呼保义及时雨,那是作者对宋江的性格、行为都有所认同;而《山本》的作者则用非常高明的反讽手法来写一个嗜血成性的英雄人物。”[11]但如果我们深入小说中对井宗秀的描写,会发现作者虽然不回避井宗秀坏的一面,可同时也常常表露出对他的欣赏,比如说井宗秀“从来不说一句硬话,可从来没做过一件软事”。作者对他显然不只是“冷峻无情的批评,不动声色的反讽”(陈思和语)。
如果我们能够从传奇范式来看待小说中的人物的话,这种颇具争议性的英雄实际是弗莱与詹明信所认为的传奇主人公“基本边缘性”的典型体现。这首先表现为他们虽然超出常人的智勇,并常常经历着神话一般的事件,但却不是神话式的主宰自我命运的英雄。井宗秀作为一个小小的画匠徒弟,聪敏过人,巧舌如簧,本来是师傅决定做的事情最后却都是照他的意思来;父亲葬进龙穴宝地后他立即飞黄腾达,什么都能做成,如有神助。但很快他也在乱世之中迷失了,变得残酷、暴虐,小说结尾时他不顾众人反对、在镇上大兴土木建钟楼和戏台,又为报兄长的仇残酷地虐杀了邢瞎子,终于天怒人怨,在自己家中被人暗杀。詹明信曾总结道:“传奇中的传统的英雄……表现为一种无知和糊涂,标明他们是某个平凡的观察者,对超自然的冲突感到震惊,他们被不知不觉地纳入到这种冲突,获得巨大胜利的奖赏,丝毫不曾意识到一开始就处于危险中的东西。”[12]105作为一个传奇式主人公,井宗秀尽管有超出常人的智勇和神秘力量的护佑,但仍是一个被蒙蔽双眼的凡夫俗子,这使他的错误和迷失都情有可原,作者和读者不会因此而轻视或批判他。
其次,传奇式人物的“边缘性”还表现在他们的亦正亦邪上,正如詹明信所言,“不论他们是奴隶还是妇女,由于必须求助于欺骗和诡计而不单是身体的力量,他们都更密切的与恶作剧的精灵而不是光明磊落的英雄相联系。”[12]100井宗秀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城府、算计和在战争中打磨出的残忍,都是他传奇式人物性格的一部分。贾平凹还特别给井宗秀的边缘性又加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就是使他因大腿受伤而变成性无能。“阉割”是贾氏作品常见的一景,他偏爱塑造站在性别边缘处的人物,并认为中国文学史上的贾宝玉、诸葛亮、宋江、唐僧都是这样的雌雄同体者[13]。这也使人物与那些正统的英雄主人公相区别。既然有缺陷或不光彩的一面在传奇式人物中是惯例,也就不应以此作为作者意图“讽刺”的证据。更何况传奇与讽刺彼此对立互不相容,“因二者分别捍卫理想和现实”[4]78,传奇式人物身上注定很少见到浓郁的讽刺色彩,而是作者主观意识的一种承载。贾平凹在谈到《山本》的创作时也说过:“写人更有意义,更能表达我所要写的对于现实的恐惧和对于生命的无奈。”[14]可见在他的眼中,井宗秀的凶狠残酷其实是他想表现的时代和命运悲剧的一部分。
小说里另一种典型的传奇式人物是陆菊人所代表的红颜,弗莱曾指出“传奇的模式展现的是一个理想化的世界:英雄都勇敢,女人都美貌,歹徒都凶残。”[4]192传奇式女主人公总是世间一切美好的化身,表现出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小说里的陆菊人容貌姣好,她和花生“一到街上,惹得所有人眼睛都发亮,迎面碰着点头招呼,走过去了,又都扭头回看。”[1]384陆菊人还是包括井宗秀在内的涡镇人的“镜子”和守护者,曾急中生智使土匪五雷的表弟被马蜂蜇死,且对茶行的生意也游刃有余,多次得体地处理过急事、大事,表现出超人的智慧和谋略。她在王团长强抢民女给唐建时出面反对:不能纳不来粮了就抢人家女儿,这不是和土匪一样吗?井宗秀强迫别家女子来给自己服务时,陆菊人还送给他那面古铜镜让他“自照”,可见她内心的善良和正直,正如井宗秀对她的评价:你就是我的菩萨。陆菊人的外在形象和内在品质都是几乎无暇的,这使她成为传奇中的红颜而不是日常现实中的女人。
陆菊人的传奇性还表现在,她的形象和性格中核心的部分从小说一开始就不曾改变过——不到十二岁时她就懂得偷窥赶龙脉的人看穴地,又故意抹掉了竹筒上的气泡,使那块地的秘密只有她一人知晓,这与小说最后她秘密去打探井宗丞死讯时的谨慎与智识一脉相承。正如弗莱所言,传奇的“中心人物从不发育也从不衰老”[4]246。巴赫金也指出,传奇的人物传记时间“不改变主人公生活里的任何东西”,是一种“超时间空白”[8]349。陆菊人从小说开头做富足的涡镇的童养媳,到小说结尾成为涡镇仅剩的几位幸存者之一,目睹涡镇的灭亡,是整个故事中国传统式“轮回”世界观的中心,她的始终不变的性格和品行使她独具传奇人物的特色。
另外,贾平凹的小说常有能洞悉天地奥秘、人间事理的人物,小说里的陈先生和宽展师傅就是代表,他们与传奇故事中的“智慧老人”形象极为相近。这种人物与喜剧中的“自贬者”相通,貌不惊人甚至形容卑下,作家对他们也每每轻描淡写,“使其性格没有棱角,没有充分展现出来”[4]246。小说里陈先生是个瞎子,给人看病,嘴总是不停地说;宽展师傅是个哑巴,整日里要么读经要么吹尺八。作者对他们外形和行为的摹写都很简单,只突出一项核心特质,那就是洞悉世事的智慧和淡然。比如陈先生要求杨掌柜一定要按时点灯,杨掌柜质疑他是个瞎子还要点灯,陈先生说,天暗了就得点灯,与看得见看不见无关。而对镇子的英雄守护者井宗秀,陈先生也冷眼看得清楚:啥时没英雄,世道就好了。小说结尾陈先生问陆菊人今日初几,并感叹这一天到底还是来了。荣格曾在《原型与集体无意识》中称“智慧老人”为“意义的原型”,他们代表着集体潜意识中的“智慧和知识”或“非凡的洞察力”,“智慧老人象征着隐藏在生活混乱之中的先验的意义,是灵魂的父亲……是一个精神仪式。”[15]他们实际上是人类祖先适应环境经验积淀的人格化表现形式,具有高度的凝缩性和理想性,在传奇故事中被固定为一个类型化的形象不断出现,正如英雄、红颜这样的传奇型人物一样,对其所属类型的认识是我们理解小说和作者意图的重要依据。
三、残酷的崛起与毁灭——历史小说笔法的传奇性
作为一部当代历史小说,《山本》中的许多人物和事件都能在历史上找到原型,比如井宗秀就是以历史上的军阀“榆林王”井岳秀为原型的,他为兄报仇的酷刑取材于井岳秀对仇人剖心剥皮的事例,而陆菊人开茶行则取材于安吴寡妇周莹的事迹。正如弗莱所言:“当一部小说所写的内容已成为往事,它就更具有传奇的性质。”[16]历史小说与传奇紧密的关系在古今中外都有无数例证。
纵观世界文坛,从上世纪中期至今,层出不穷的历史小说俨然已成为一种新的创作现象和潮流,许多评论家都注意到了当代作家们对历史编写的兴趣,哈琴的“编史元小说”和埃利阿斯的“元历史罗曼司”理论都是对后现代历史小说的有力阐释。其中埃利阿斯的“元历史罗曼司”不仅注意到了哈琴所言的这些作品中的历史编写和非理性主义、反经验真理等特点,还指出当代欧美历史小说是一种“历史罗曼司”,与现代时期的那些小说不同,它以一种罗曼司——传奇的范式来建构文本,“从这个世界的压抑中释出想象——那种文化的、性欲的、或是神话的无意识的压抑。”[17]147而在《山本》的阅读中则可发现,这部小说与埃利阿斯所分析的以想象、神话和无意识为典型特征的欧美当代历史小说有许多相通之处。
首先,当代历史小说作家们成长于战后世界,在直接或间接地目睹了20世纪“历史的丑陋的奇观”后,“作家们明显地迷恋历史的血腥倾向……暴力被视为一种特殊的历史意识,而不是历史本身的自动或中立的产物。”[17]53《山本》这部小说问世后令许多评论者和读者们印象深刻的便是小说中血腥恐怖的场景内容,比如被剥了人皮作鼓的三猫,被开膛剜心抠眼珠的邢瞎子,逃进粪池又被抓出来割头的王魁,还有无数死状惨烈的小人物:被炮弹炸烂双腿,脑袋陷进胸腔,只剩半边脸等。这些内容乍一看令人咂舌,有哗众取宠的“刻奇”嫌疑。但这正反映出包括贾平凹在内的当代历史小说作者们对历史之残酷、暴力的认知,正如詹明信在《政治无意识》中的名言:“历史即是创伤”(history is what hurts)[18], 它的存在超越了我们的现实经验,令我们震惊和惶惑。贾平凹在谈到《山本》中随处可见的残酷死亡时也这样解释道:“在那个年代,死亡随处可见,并不是要死的壮烈,我对死亡的认识,更是我对那个年代的诅咒。”[14]
其次,在后现代时期将“庞杂混乱”的历史素材转换为有机的小说作品时,作家们放弃了表现和记录“历史真实”的努力,历史注定是非理性的,混乱的和反阐释的,无法以科学经验主义去认识和概括。因此像许多当代历史小说一样,《山本》也不得不走向时间和空间上的模糊化、孤立化,它不仅将所有的故事都局限在秦岭这个空间中,对外部的世界——省城乃至整个中国发生的事要么完全不提、要么点到即止。正如贾平凹所说:“不好处理的地方就模糊处理。比如说模糊了时间和各种番号。故事的时间也和历史时间有错位,就是要达到模糊处理的目的。”[19]这也是小说传奇性的又一表征:传奇书写的环境总是相对脱离于具体的社会历史现实,“在相对独立的真空环境中将人物理想化,释放出作者自身性格的因素”[4]453,这也意味着在《山本》这样的小说中苛求权威性和客观性是不妥当的,它不是一部具有“实录精神”的历史小说。
再次,当代历史小说采取了一种两结合型的叙事笔法,也是两种不同的看待历史的方式,即埃利阿斯所言的基于神话和魔法的罗曼司——传奇型、基于经验主义的真理的历史型。其中,后者追求与过去的具体现实对话,试图“将历史恢复为合理的调查和科学方法的产物,同时又很小心地将自己区别于幼稚的或庸俗的经验主义预言”[20]161,它本质上是一种对历史崇高的渴望和不懈追求,也可被视为后现代历史小说对元小说激进的“反叙事性”和“过于陌生化”的矫正。这需要的是一种旁观者的客观视角,它的代表是小说中的麻县长,他从外地调任来涡镇,记录了秦岭的山水与造物,对这里发生的一切苦难亲眼目睹却无能为力。他曾表示自己不能为秦岭添一土一石,就所到一地记录些草木,或许将来可以写一本书。而在小说结尾,对世事绝望了的麻县长跳涡潭自杀之前,留给蚯蚓的就是两部珍贵的手稿,《秦岭志草木部》和《秦岭志禽兽部》。这也是作者在小说创作之初打算作的“草木记、动物记”在小说里的化身。
而传奇型叙事则意味着那些“神奇的故事”,以一种“虚构症”(fabulatory)去解构历史叙事,正如作者所言:“《山本》里虽然到处是枪声和死人,但它并不是写战争的书。”[1]524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暗含着后现代对认识论的质疑:战争、历史,这些客观存在的往昔并非可以被理性、中立地记述的,取而代之的是那些主观建构的神奇故事,在小说里表现为以井宗秀为代表的英雄人物的戏剧性崛起和灭亡这条情节主线。在这样的故事里,作者并不奢求与真实的、具体的过去对话,而是经由传奇型叙事以想象与有意识虚构传达一种“永恒的、关于人性和世界的真理”[20]162。井宗秀与中国古往今来的历史传说中所有传奇式的英雄站在一起,而陆菊人则属于那些陪伴和影响他们的理想型女性,井宗秀从一个画匠之徒跃升为旅长,陆菊人从一个童养媳到茶行统领,最后两人又一前一后失去了这一切。这样的人物组合和情节走向在中国古往今来的无数传奇故事中都曾出现过,实际上是弗莱所言的那种所有文学中都存在的原型故事的又一个变体,其中承载的“真理”正如作者的那句诗所概括的:世界荒唐过,飘零只有爱。与麻县长和他所代表的“秦岭草木、动物记”叙事模式不同,这种承载着原型的传奇叙事超越了地域、时间的界限,以想象和虚构抵达了文学永恒性的那一面。
四、结语
《山本》这部小说采用了传奇性时空体和人物塑造模式,始终维持“传奇型”与“历史型”两种叙事方式之间的张力,“同时在两种看待历史的方式中看到真理,而不觉得需要使一个完全从属于另一个”[19]162,这与当今世界范围内流行的历史小说的创作潮流相似,也是后现代文化与思维模式的一种体现。而对于中国作家而言,这种模式甚至可以上溯到《红楼梦》《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它在当代文坛上重焕生机并获得新的发展,不仅意味着华语小说在全球化时代并不是落寞的,更因其传奇性书写中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而彰显着中国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