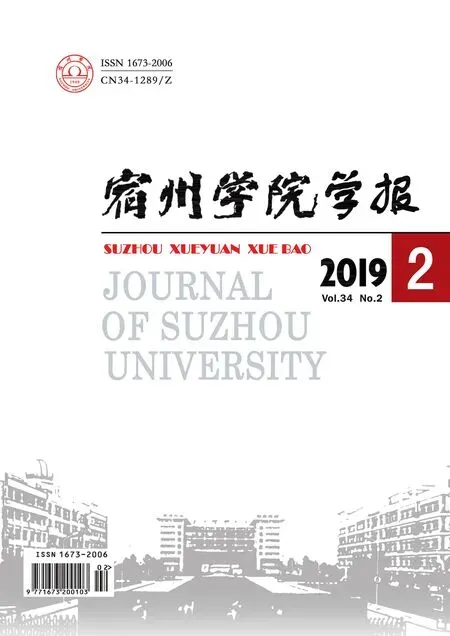《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人物形象的模糊与盖茨比的梦想
石 平,周海云
蚌埠学院外国语学院,安徽蚌埠,233030
1 问题的提出
在阅读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Fitzgerald)的《了不起的盖茨比》(TheGreatGatsby)时,人们会发现其中存在着某些模糊不清的地方:故事表面上看似简单,情节看似虚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隐晦的语言,而非明晰的描述;盖茨比(Gatsby)作为小说的主要角色,在整个故事中始终保持着一种看似模糊的轮廓,并且始终伴随着他那莫名其妙的庸俗的梦想;盖茨比对黛西(Daisy)的追求笼罩在理想化的朦胧之中,与其说这是现代小说的特征,倒不如说更像是浪漫主义诗歌的典型特征;而故事的叙述者尼克一方面敏锐地观察和准确地记录周围人的故事,另一方面却刻意地与故事中的各种事件保持距离。或者说,菲茨杰拉德本人应当首当其冲:这本书的语言丰富而复杂,取材于各种各样的来源,如圣经和基督教话语以及艾略特(T.S.Eliot)和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现代主义散文。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书中创新了20世纪的浪漫主义,并秉承了现代主义对高冲击力语言的要求,将每句话都赋予了一定的意义[1]。但所有这些“模糊不清”并没有引起不可知论者的担忧,也没有给读者带来可怕的模棱两可的感觉。它更倾向于激发读者的兴趣,把读者吸引到书中来,并对读者的理解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让读者去解开盖茨比那难以名状或者模糊不清的渴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盖茨比的批判主义者们往往似乎更想要揭示这些模糊的表象,去透视并解构它们的本来面目。
2 主人公盖茨比的模糊轮廓
当故事从尼克(Nick)自己的道德谴责和他对盖茨比的矛盾评论开始时,人们就产生了一种对盖茨比的模糊感。书的开头对盖茨比作了相当抽象、隐晦的描述,介绍他“仿佛与那些记录一万英里以外地震的一台精密仪器有关”[2]6,甚至没有使用形容词来描述他的个性。把盖茨比比作地震仪并不能帮助读者把盖茨比形象化。尼克使用了一种对话的语气,即用了没有逻辑联系的“if…then…”结构中的条件句。“一连串表示成功的姿态”与“他身上的某种魅力”[2]6有什么关系?读者无法看到对盖茨比外貌特征方面的完整的描写,他们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尼克在某种程度上有所保留,他并没有完全致力于这种具体的外貌描写。《了不起的盖茨比》开头的这种描写令人感到了一种无法迅速传递和理解的模糊感。此外,尼克与盖茨比在彼此被介绍之前的开场对话也显得简短而模糊。
“您看起来很面熟,”他彬彬有礼地说。“战争期间您是在第一师吗?”
“嗯,是的。我在第二十八步兵连。”
“我在第十六连,一直干到一九一八年六月。刚才一看到您我就知道我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您的。”
我们谈了一会儿关于法国一些阴雨、灰暗的小村庄的事。[2]48
读者通过他们的对话了解到的是关于盖茨比参与战争的事实陈述,但是接下来的谈话却被简化为尼克的间接话语,并且可能会透露出更多关于盖茨比的信息,在不经意间让读者对盖茨比的某些方面有所了解。通过描述两位退伍军人讨论他们的战争故事,可以很好地塑造盖茨比的形象。然而,作者再次“克制”自己,没有提及他们谈论的具体城镇或他们看到的事件。盖茨比在小说的大部分章节里都是言语不多,说话含糊其词,或者通过尼克对他的话进行改写。在情节发展方面,从沃尔夫山姆(Wolfshiem)开始接受盖茨比,到他成为一名热情好客、慷慨大方的派对主人。读者只能从流传着的关于盖茨比的“他杀了一个人”或者“战争期间的一个德国间谍”的疯狂谣言中了解到盖茨比,甚至直到最后也没有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澄清。
读过《了不起的盖茨比》初稿之后,麦克斯韦·帕金斯(Maxwell Perkins)在给菲茨杰拉德的信中写道:“盖茨比的形象有点模糊。读者的目光永远不能完全集中在他身上,他的轮廓模糊不清。现在关于盖茨比的一切或多或少都像是一个谜,或者说是有些模糊不清……难道不能把他的外貌特征描述得和其他人一样清晰吗?你难道不能多增加一两个有特征的词语,比如‘老兄’这样的称呼吗?也许你可以写具体一点,而不是那些空洞的话语。”[3-4]菲茨杰拉德似乎很固执,执意不听从帕金斯关于把盖茨比描写清晰的建议,于是在信中回答道:“奇怪的是,我觉得盖茨比形象模糊不清的想法是可以接受的。我自己也不知道盖茨比长得什么样,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这是一个复杂的想法,但我相信你会理解的。我了解盖茨比超过了解我自己的孩子。收到你的来信后,我的第一反应是让他放任自流,而让汤姆·布坎南(Tom Buchanan)成为小说的主要角色……然而,盖茨比在我内心深处却挥之不去。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很熟悉盖茨比,然后又对他生疏了,但现在我知道我又对他很熟悉了。”[4-5]
没有比这能更好地描述菲茨杰拉德与他创作的人物之间的关系了。菲茨杰拉德坚持他那“虚空”的盖茨比形象并相信读者会理解的。作者愿意冒着“模糊不清”的风险来完成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即刻意把一个朦胧的人物塑造成小说的中心角色。
3 讲述者尼克的模糊描述
正如许多评论家所说,从小说的处理角度来看,尼克的存在一直被认为是小说的一大成就。这本书是通过尼克的视角对一系列事件的叙述,尼克既是故事的叙述者,又是故事中的人物,这是故事产生模糊效果的来源。随着故事的展开,尼克的第一人称视角使读者产生一种冲动,就是期待了解他对周围人的欲望和梦想的探索。他与主要人物的实际距离很近,这使他能在很近的距离内观察到故事的发展。小说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尼克的倾听和观察的行为,它不仅描述了他所目睹的经历,而且还产生了使故事构建成一个整体的情绪、基调和维度。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焦点是叙述者的情感以及生活故事。诚然,所有带有小说基调的情感都是通过尼克的感知来传达的,这为读者深入了解故事提供了一个更高的视角。但“这部小说有一个看起来令人难以琢磨的深度……尼克没有完全看懂或理解他所感知到的东西”[6]109。一开始不久,尼克就表明他亲身经历了整个故事,并承认这个故事对他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是如此的沉浸在“狂欢”的故事中,以至于有时尼克不能满足于把自己局限在自己的感知和视角范围内,转而以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身份去获取全景。当他想象盖茨比第一次亲吻黛西时,他以一种无所不知的视角讲述了盖茨比的梦想,仿佛他看透了盖茨比的内心和精神状态。另一个例子是尼克讲述的他想象在盖茨比去世那天的感受,“我有个想法:就是盖茨比自己也不相信会有电话打来的,也许他已经不在乎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一定会感觉到他已经失去了那个往日的温暖世界,并且为抱着一个梦想时间太长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一定是透过骇人的树叶仰望着一片陌生的天空,当他发现一朵玫瑰是多么丑陋的东西,阳光照射在刚刚露出头的小草上又是多么残酷时,不禁感到毛骨悚然。”[2]157这段话从尼克的猜测开始:“我有一个想法”,“也许”。接下来的句子以条件句式呈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然后又转变为更明确和坚持的语气,“他一定会感觉到”。读者被慢慢地引导但最终坚定地接受了尼克无所不知的总结:“他已经失去了那个往日的温暖世界,并且为抱着一个梦想时间太长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下面的句子真的让读者了解到盖茨比的感知:一个陌生的天空,透过骇人的树叶,丑陋的玫瑰,阳光照射在刚刚露出头的小草上的残酷。但尼克有什么理由来说明自己明显感受到盖茨比所看到和感知到的一切呢?显然,讲述者用自己的观点在故事与其读者之间制造了一种“距离”,或者用美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韦恩·布斯(Wayne C.Booth)的话来说,是作者的感知,抑或是小说的规范与讲述者的感知之间的“距离”[7]21。我们可以假设他运用了源于他自己的情绪和情感的想象力,以及他对盖茨比情况的了解和经历的推断,并将二者融合为一体。他试图超越这种融合,就好像它是一个无所不知的讲述者的权威话语。这就提醒我们,盖茨比的故事包含在一本小说中,这本小说是尼克用更具感召力和诗意而不是描述性的手法所写的故事。
读者应该记住的是,尼克不仅是在讲述盖茨比的故事,也是在讲述自己的故事。尼克在小说中的角色并不是一个不起眼的参与者。他保持沉默,让威尔逊“沦为一个因悲伤而精神错乱的人,以便使整个故事可以保持最简单的形式。”而他的沉默对小说中的事件有重要的影响,因为它导致了盖茨比的被谋杀和威尔逊的自杀。可以说尼克同时也是一个不可靠的讲述者,他的不可靠性来自他对事实的妥协。尼克认为“所有这一切似乎是非本质和不重要的”[7]。
4 女主人公黛西的模糊意象
盖茨比对黛西的感觉也笼罩在典型的朦胧的浪漫主义诗歌的理想化之中,而不像是在现代小说之中。从盖茨比和黛西的重聚到盖茨比死亡,菲茨杰拉德似乎对他们之间的爱情进行了相当模糊的描述。盖茨比的整个梦想和愿望都建立在旧梦重圆的希望之上,期待重新点燃对黛西的爱。黛西也因此成为整个故事的核心。她很漂亮,一直是舞会上的美人。然而,就像对盖茨比的描述一样,作者对她的描述和呈现也几乎没有使用关于外貌特征的具体词语。因此,她的视觉形象也显得模糊不清。
詹姆斯·M·梅拉德(James M.Mellard)注意到,黛西只是出现在抽象的静态的描写中,而她的对手默特尔(Myrtle)则完全出现在具体的动态的描写中。“Daisy Buchanan虽然很迷人,但也从来没有像默特尔那样被具体的尖锐的词语来描述,而是代之以音乐方面的术语[8]。”菲茨杰拉德将黛西描绘成一个模糊不清的人物,但同时又通过强调她的声音让读者去洞察这种模糊。读者在小说中几乎不是看到她的身影,而只是听到她的声音。整本书中黛西的声音成为她魅力的缩影。正是她的声音,而不是她的身影特征,使她的轮廓主要存在于盖茨比、尼克和读者的想象当中。当尼克第一次到汤姆·布坎南家时,他将黛西的笑声描述为“一种滑稽而又迷人的低声笑语”,她的声音“低低的,听起来令人兴奋”,“这是那种叫人侧耳倾听的声音,仿佛每句话都是永远不会重新演奏的一组音符……她的声音中有一种激动人心的特质,那是为她倾倒过的男人都觉得难以忘怀的”[2]13。
人们可能很难摆脱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虽然简单但又非常重要:黛西有什么好看的?什么样的女孩才可能会令人如此倾心呢?然而,从尼克对她的声音的描述,他们很容易联想到一个迷人的女人的形象。她不可抗拒的声音提到了盖茨比渴望了解的一切。对于盖茨比来说,黛西的声音悦耳动听、夺人心魄、使人开心、令人振奋,代表了某个社会阶层的属性。她是一个被“浓缩” 成为声音的女人,一个理想的女人,一个成功的幻影,一个盖茨比信以为真的、被驱使着去获得的幻影。因此,黛西拒绝盖茨比而投入到汤姆的怀抱,并不是一种强烈的爱的表达,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对梦想的不安全感的表达。这是菲茨杰拉德的成功之处。“假如他把这种关系戏剧化了,他就等于是在证明这是一种骗局”[9]783。黛西的声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盖茨比的梦想,最终变成了一个幻想,一个无法实现的悲剧性的梦想。
5 盖茨比的梦想及其对美国梦的回应
盖茨比是美国小说中为数不多的人物之一,就像哈克·费恩(Huckleberry Finn)和海丝特·白兰(Hester Prynne)一样,他的名字很快成为人类生活某些方面的重要标志。盖茨比的梦想与美国梦和美国的史前历史有关,它可以追溯到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和早期的荷兰水手。然而,在菲茨杰拉德发出的独特声音中,美国梦缺乏他的前辈们故事中所表现出来的灵感和成就感。盖茨比则是菲茨杰拉德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称为“爵士乐时代”的梦想的回应。因此,盖茨比作为一个模糊的人物形象,不仅是为了引起读者兴趣的一种技术手段,而且是为了呼应他那难以名状的渴望,他那对生命契机的崇高信念。这个体现在盖茨比身上的梦想,读者就会越来越熟悉了。“虽然我们基本上看不到他,也几乎没有听到他说话,但他的存在始终与我们同在;他是作为一种生命的力量而存在,这与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不太一样”[9]787。
在盖茨比与黛西再次相逢的场景中,在肢体和情感方面通常都很保守的盖茨比,开始变得活泼起来,并且散发出极大的活力。菲茨杰拉德详细地描述了他的身心活动。读者可以看出,这就是盖茨比一直在等待和为之构建自己的生活的时刻。尼克将盖茨比对生活契机的反应比作记录遥远地震的地震仪,这种反应是永恒的。此外,在尼克和盖茨比等候在布坎南的屋子外准备驱车前往纽约的场景中,盖茨比把黛西的标志性本质暗示为“她的声音充满了金钱”。盖茨比不同寻常的确信并且以清晰而又直截了当的方式,补充了这句缺失的话。黛西的声音和金钱令人惊讶地被并置在一起,而尼克立即且简洁地表示同意这句话:“就是这样。”金钱一直被视为菲茨杰拉德计划的核心魔力。而美国梦,就像黛西的声音一样,可能会与金钱混淆,但它最终是以一种令人兴奋的自由,崇拜个人意志,消除所有社会差异。尼克说,他相信这个声音是最能打动盖茨比的:“它那起伏不定的、狂热的热情……这是无法超越的梦想——那个声音是一首不朽的歌。”[2]95黛西的声音就像那个没有任何障碍的梦想一样不可思议,让世界对我们的意志作出回应,重新塑造我们自己。
正如温斯坦(Weinstein)敏锐地指出的那样,“脱离证据或事实的约束,改变一个人的身份,保持多重身份而不是单一身份,克服时间、空间和背景的法则:这些正是小说的优势,是美国梦的优势,也是盖茨比的优势”[10]27。由于盖茨比的坚韧不拔和坚持不懈,他对那个女人的想法始终是忠实的、固执的。他“对生活前景的高度敏感”在于他否认生活的局限性。他对黛西的深情厚爱可以不受时间的限制,让过去的旧梦重温。从这个意义上说,盖茨比是了不起的,因为他相信一个凄美而珍贵的承诺:愿望和梦想可以实现。正如肯纳(Kenner)总结的那样,“简而言之,盖茨比应该是了不起的,这一点很重要。之所以很重要,因为这本书的中心神话与纯粹意志所塑造的貌似真实的表象有关:这是最古老的美国主题”[10]24。当听不到这种声音时,就表明盖茨比的梦想是悄无声息了,就像这本书的最后说的黛西没有电话留言一样。
6 结 语
不难看出,小说的难以捉摸的特点和模糊感。非但没有引起不可知论者的担忧,也没有给读者带来可怕的模棱两可的感觉。恰恰相反,它更倾向于激发读者,吸引读者,甚至说服读者去接受叙述者的价值观、是非观和热情。虽然菲茨杰拉德使盖茨比还保持着他的神秘感,但他实际上是在吸引读者映射出他自己对盖茨比的解读,对盖茨比的愚蠢和梦想的解读。“无论是对所隐含的内容还是对所讲述出来的内容,这个故事的效果都同样显著和强烈。它使读者产生一种经过抑制之后迸发的惊奇心情,在这种心情之下,读者需要考虑、深思和权衡一个又一个事实真相以及一个又一个隐晦的暗示……菲茨杰拉德先生的目的最终当然达到了”[6]98。更重要的是,它也对读者的推断能力提出了更强烈的要求,即:要求读者能对小说中那些假设需要回答的问题进行推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盖茨比的批评者们往往显得有必要揭示这些模糊的表象,去看穿和解构它们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