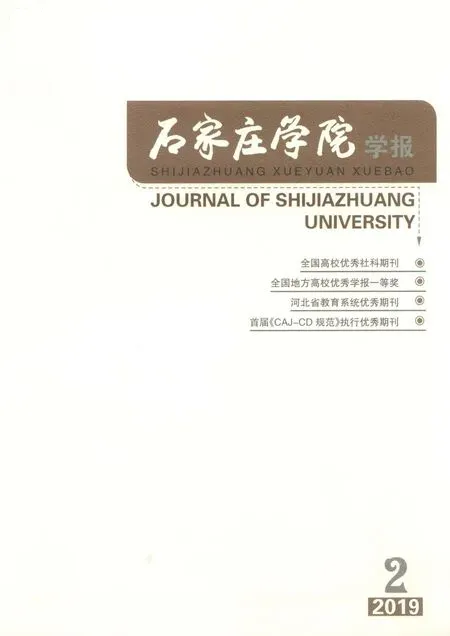从石家庄寺院碑记看明朝士大夫对佛教的认识
付金财
(石家庄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35)
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在中国生根发芽成长,逐渐中国化,中国文化呈现为以儒释道三者为主的格局。中国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不同于西方,西方是政教分离,中国是以政统教,以教辅政。士大夫即官员和士人接受儒家教育,秉承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官员士人对佛教的态度即代表儒家对佛教的态度,更代表政治对佛教的态度。
唐宋时期官员士人对佛教兴趣浓厚,众多士大夫或信仰佛教,工作之余从事相应的佛教修行;或热衷于和高僧交游,酬答往来,关系密切。即使是以《谏迎佛骨表》一文上书中央批评唐宪宗崇祀佛骨舍利的韩愈也未能免俗,在发配岭南后仍拜访岭南高僧大颠禅师。宋朝时期此风仍然盛行,苏轼与佛印禅师、王安石与蒋山元瓒交游之事广为人知。明朝时期,官员士人对佛教的态度与唐宋相比,更加理性、冷静,对佛教的直接或间接批评成为主流,这在石家庄地区佛教碑记中得到了明确的印证。
一、明朝时期石家庄地区佛教大发展
明朝时期石家庄地区的佛教文化同全国一样,在经历了东汉至魏晋南北朝的引进、隋唐至宋朝的中国化之后,进入到了一个向广大乡村迅速传播的时期。石家庄地区大规模兴建寺院,佛教成为百姓的主要信仰。嘉靖《真定府治·地理》风俗条说:“其小民习礼,送死多破家,供佛不少(稍)靳(控制)。”[1]144“邑俗素佞佛,凡丧葬皆延淄流做佛事,否则争鄙之。”①邑,指石家庄地区的灵寿县。[2]208
(一)大规模兴建寺院
辛集市(束鹿县)在石家庄地区的最东部,经济比较发达。康熙年间修成的《束鹿县志·建置志卷二》存录寺院明朝及以前的57所,具有明确初始建造时期的43所,不明初创时期的有14所。笼统标明隋唐、宋元、宋金、金元时期建造的有7所,明确为唐朝建造的4所,宋朝建的3所,金朝建的1所,而元一朝创建了21所,明朝创建7所。明朝新建寺院列于元朝之后居第二位。明朝新建寺院数量少于元朝,但对明朝之前建立的50所寺院全部进行了重修。这样明朝新建和重修的总数是57所,可见明朝时期辛集的佛教力量发展之快,佛教规模之大。
梁勇、杨俊科所著的《石家庄史志论稿》是石家庄较早的一部史志性著作。此书根据地方志材料和田野调查所得资料,对当时石家庄市辖区②当时石家庄市辖区包括石家庄市区、正定县、井陉县、获鹿县。的历代寺院加以统计,并制作了《石家庄市历代佛教寺院一览表》[3]214-227,基本将清朝以前历代所建寺院收录殆尽。根据此表,当时市区和市辖三县魏晋南北朝兴造寺院10所,隋朝兴造11所,唐朝兴造46所,五代2所,宋朝15所,金朝9所,元朝8所,明朝33所,清朝33所,明朝以前寺院经明朝重修的有14所,这样明朝新建和重修寺院共47所。新建、重建合计数量比唐朝多1所。新建的与清朝相等,是宋朝的2.2倍、金朝的3.7倍、元朝的4.1倍。
(二)聘请士大夫撰写碑记
寺院兴建的主持者是修行和声望较高的僧侣,支持者是石家庄地区的乡绅和乡民。寺院兴建完成后,都请当地官员、儒生或名士撰写碑记。兴建寺院何以要请士大夫撰写碑文,一是为寺院兴建者播名当时,传扬后世。赵州僧正本儒兴建柏林寺大慈殿,完工之后请文学家文冈子李时阳撰写碑记,“龚石丐记于余,用垂不朽”[4]524。李时阳应邀作了《增修柏林寺大慈殿记》。俗名杨大宝的僧侣修建的石佛寺位于赞皇县西部山区,他两度邀请进士出身曾任明朝礼部尚书、兵部尚书的山西乐平①山西乐平,今山西省昔阳县。人乔宇撰写碑记,叙述其修建石佛寺的基本情况,“用播永远”。[5]247二是提高寺院的合法性。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对寺院数量和僧侣人数都有规定,不允许寺院数量和僧侣人数无限制增加。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下诏对寺院进行整顿,要求“府州县只存大寺观一所,并其徒而处之”[6]26。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明朝礼部对僧侣人数进行限制,规定每府40人,州30人,县20人。同年,朱元璋下令,“各府州县寺观虽多,但存其宽大可容众者一所”[6]575。每个行政区可以有一所寺院,几十名僧侣,这是中央政府的理想数量。现实远远超过这个数量,故明朝在弘治、嘉靖时期开始整顿佛教,勒令非法僧人还俗,拆毁非法寺院。石家庄地区所建寺院若严格按照政府规定,绝大多数为非法寺院,所以便通过邀请士大夫撰写碑文的方式为非法身份洗白,一定程度上提高寺院的合法性。
二、士大夫对佛教的认识
士大夫撰写的寺院建设碑记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寺院的来历、修建的缘起和过程、主持修建的僧侣和协助修建居士、寺院的主要建筑结构等。士大夫在撰写的碑记中也表达了其对佛教的认识和评价。
中国古代文化,先秦时期为诸子百家,两汉经学独大,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道教兴起,唐宋时期形成三教并存的格局,明朝依然保留这个格局。东汉至唐宋,中国士大夫对佛教还有极大的热情,或研究其思想,或依其法修行,这个时期佛教文化在士大夫阶层中享有较高的地位。众多知识分子以高僧或禅僧为师友,向他们学习佛教。中唐以后以韩愈、李奥为代表的儒家士大夫开始批评佛教,并以吸收佛教思想丰富儒家思想中比较薄弱的本体论和修行论。南宋时期朱熹集当时儒学成果之大成,开创了中国儒家文化的新阶段,理学一方面吸收佛教理论的有益成分发展儒学,一方面批评佛教的避世和玄虚倾向。这样儒学一改唐宋以前的颓势,以全新的姿态重新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而为士大夫所秉持。朱熹的《四书集注》被明朝定为国家教育和科举考试的重要学习材料,这样朱熹的思想深深影响着明朝的士大夫阶层。
明朝建立者朱元璋对儒释道的认识是清醒的,他在《三教论》说:对于佛教道教,“若崇尚者从而有之,则世人皆虚无,非时王之治。若绝弃之而杳然,则世无鬼神,人无畏天,王纲用力焉”[7]卷十。佛教、道教对于社会教化而言不能没有,但也不能无限扩张。而儒家是社会教化的核心,其核心作用在于通过儒家教育培养治国理政的人才。佛教、道教是社会教化的补充,补充作用在于教化下层百姓。明朝时期石家庄地区的碑刻反映出来的士大夫对佛教的态度基本和朱元璋的认识一致。士大夫们接受儒家教育,是儒家文化的信仰者、传播者。同时他们又是政府官员。他们既承认佛教对下层百姓的教化作用,又对佛教的某些方面持批评态度。
(一)坚持儒家为主、佛教为辅
士大夫在为寺院撰写的碑记中往往强调儒家思想相对于佛教的主流地位。曾任职山西太谷县知县的无极人张子清在为无极县郝庄村的永宁寺所作的《重修永宁寺记》中认为:“圣人之教无佛氏之教则益行,佛氏之教无圣人之教则不行,何也?圣教重君臣之义,佛教则否。果去而君臣,行见世道日趋于乱。释安所获生。圣教重父子之亲,佛教则否。果去而父子,行见人类日沦于□。释安所获继。是圣人之教,其佛教所赖以行者与。”[8]516圣人之教即儒家文化,张子清所说大意是家国秩序靠儒家文化来维护,如果没有基本的社会秩序,佛教便没有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儒家文化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之旨归,反对拒绝承担家庭社会责任、离世修行以追求个人生命的解脱。如果社会成员都无视个人对家国的责任而出家修行,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会极为缓慢。进士出身的山西乐平县人赵思诚所作《净住寺创建藏经殿碑记》②净住寺位于赞皇县境南部。呼吁:“诸生游息梵院,日与释众为侣,尚可以正心诚意之实,因其教而利导之,使不惑于苦空之禅,则于仁义之旨不差。虽合孔孟佛老而一之,亦无不可。此又深望于凡我同志也。”[5]250赵思诚觉得诸生即儒生游览寺院时,要借助和僧侣接触交往的机会,用儒家思想纠正佛教文化对现实人生彻底失望和追求虚无飘渺的解脱的偏差,使其立足于仁义,以入世为出世,以烦恼为解脱。乔宇,明朝山西乐平人,进士,曾任礼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他应邀创作的《重修石佛禅寺记》中有“金天氏之教,雅与吾道有所戾”①金天氏之教指佛教。[5]247的话,就是说乔宇认为佛教和儒家本质上并不相同。也有士大夫在其撰写的碑记中对儒家与道教何为主辅未做明示,但他们往往表明自己不是佛教信众。进士出身曾任顺德府审理的正定人宋含弘在其《赵州柏林寺无声禅师重修藏经殿记》中称佛教为“异教”,说明自己“非溺于斯教者”。[4]526
明朝时期的石家庄地区,寺院的数量多于学宫,佛教信众多于儒生。而士大夫并未因此对儒学和佛教的地位产生模糊认识而崇佛溺佛,始终秉承以实现人间大同世界为旨归的儒家文化,反对出世修行,使得世俗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流,避免中国成为全民信仰宗教的国家。
(二)认可佛教对下层百姓的教化作用
佛教文化内容丰富,其中之一是业报因果理论。“业”,梵语音译为“羯摩”,意译为“造作”,相当于现代汉语的“行为”。佛教认为人的行为决定人的身心状态的作用,故可称为业力。因为业决定人的生存状态,故业也称为因,生存状态成为果。业又分为善业、恶业等。善业得善报,恶业得恶报,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最普及的有十善业、十恶业之说。十善业是不杀生而护生、不偷盗而布施、不邪淫而行清净行、不妄语而实语、不两舌而作和合语、不恶口而作柔软语、不绮语而作质直语、不贪欲而行梵行、不嗔恚而慈忍、不邪见而行正见。反之为十恶业。
不杀生而护生,今生得身无病、寿命长、鬼神佑、无噩梦、心常安的果报。命终之后,得往生六欲天的果报。杀生害命者,今生得多病、短命、冤家侵害、心不安、鬼神不佑的果报,命终之后,得堕于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不偷盗而常行布施,今生得资材丰饶、众人爱戴、善名远扬、自信坚定等果报。反之偷盗贪财,今生得身陷囹圄、臭名远扬、众人憎恨的果报,命终之后,得堕于三恶道的果报。不邪淫而行清净行,今生得举止安详、心理平衡、家庭和睦、邻里融洽的果报,命终之后,得往生人道或六欲天的果报。[9]55限于篇幅,只引述三条。这种理论对于缺乏文化常识的下层百姓而言很容易接受。百姓将今生的人生艰难归咎于自己前世的恶业,寄希望于通过今生的善行而获得来生的幸福。从能够引导百姓行善的角度说,佛教确实有教化百姓的作用。所以明朝文人李时阳在《增修柏林寺大慈殿记》中承认佛教能够将“种种诸恶潜归于善,不能无益于世教”[4]524。进士出身藁城人石珤在《重修兴善寺记》②兴善寺位于无极县境南部。中说:“欲为善者,利而趋之,欲为恶者畏祗而有所不敢。则细人之福,亦淄人之徒之所以报国家也。”[8]512曾任山西太谷县知县的无极人张子清在《重修永宁寺记》中将佛教教化百姓的作用论述得更加详细:“夫圣人之教主仁义,佛之教主慈悲不杀。圣人得位则治洽智愚。圣人不得位则教化及上智,逮下愚则不能化而入。今人诵念佛经,即愚顽亦时有感动,勃然存慕善悔恶意。是佛之道,固匪仁义中正之道,至其化诱愚俗,则圣人弃世之志或亦不没其功。譬如日月之明,不及蔀屋。时有假乎烛炬,似未可少之者。……而佛之教亦颇济圣人教化之未及。则皆自慈悲一念起,如烛炬之照屋,其何伤于日月。只见其时有济焉尔。或者曰彼其徒驾祸福以感俗,非名教所宜。独不曰今人慕为善之福,而为善。惧为恶之祸,而不为恶。不犹愈于无所慕而不为善,无所惧而恣为恶者也。余故断然取慈悲一语,化诱愚民一端,以为释家者奖。”[8]516
(三)批评天堂地狱业报轮回理论有荒诞成分
佛教理论认为众生分为六类,由高到低分别是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六类众生的生存空间是天堂、人间、地狱等。佛经所说的天梵语为“提婆”,原义为光明、自在、清净等,为六道之中的最佳最上者。天堂分为三界二十八层。欲界天为六层,色界天分为十七层,无色界由四层构成,共二十八层。地狱是一切宗教包括佛教给作恶之人安排的死后归宿。根据生前恶行的轻重和性质,堕入地狱,承受各种酷刑的折磨。根据佛教经典,有八大地狱、十大地狱、十八地狱等。唐朝时期翻译成汉语流行最广的《地藏菩萨本愿经·地狱名号品》对地狱的残酷痛楚介绍得十分详细。或有地狱,取罪人舌,使牛耕之。或有地狱,取罪人心,夜叉食之。或有地狱,镬汤盛沸,煮罪人身。或有地狱,赤烧铜柱,使罪人抱。或有地狱,使诸火烧,趁及罪人。或有地狱,一向寒冰。或有地狱,无限粪尿。或有地狱,纯飞蒺藜。众生根据生前行为善恶,或生天堂,或下地狱,或为恶鬼、或为畜生。
佛教信众将此作为真实,而一般士大夫则认为其荒诞。石珤在给位于无极县南端的兴善寺所作的《重修兴善寺记》中直接批评佛教的轮回之说:“彼方以天堂地狱轮回果证之说夸严闪倏,坐飨十方之馈。而奈有慕于吾声名礼乐之盛,岂为其不可教而然哉。其天堂地狱有无不足论,借有之为善者必登天堂,不善者必入地狱。亦非道祀忏谢而所可幸得苟免者。顾世俗之人不识善字,亦不知忠孝睦渊任恤是为善第一等,方且以施舍为善缘,何其不思之甚哉。”[8]512
无极县学生员靳□□在万历四年(1576年)所作《重修护国寺记》①护国寺位于无极县境西南郝庄村。中对佛教因果报应生死轮回说所持观点与石珤相同。[8]516
曾任山东章丘县令的晋县人吕秉彝也批评佛教广设神像、引人参拜的现象。他在《观音寺重修水陆殿碑记》②观音寺位于晋县东南杨家营村。中说:“寺有水陆殿,所以祀众神也。夫神各有主,祀各有分。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祭祖先。此理之正,不可毫变僭差。寺恶得而祭众神哉?此好事者殆欲张大其教,骇人视听,言由是可得福田利益,歆慕而尊崇其道。征诸神则非然也。”[10]548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乙丑科进士山西乐平县人赵思诚在为赞皇县境南净住寺修建藏经殿所作《净住寺创建藏经殿碑记》也委婉地表达了对佛教天堂地狱说法的不满,认为天堂地狱轮回的说法只是用于传教的寓言故事而已,“莲花宝树地狱天堂皆寓言以广教”[5]250。
佛教理论是释迦摩尼及其历代高僧以超凡的智慧和禅定为前提创建的,因而具有特殊性。佛教追求的不仅仅是人世间的幸福,而是超越生死、超越时空的彻底解脱和自由。它对于生命的存在形式和存在时空、对于生命形式的变化有自己特殊的认识。但是对于没有这种体验的人而言,认为其具有荒诞性是无可厚非的。更重要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是以追求了生脱死、往生天堂或极乐世界为目的的非世俗文化,主张通过仁义礼智信实现民生幸福和天下太平为目的的儒家始终是中国文化的主流。站在儒家文化的立场上,士大夫认为佛教理论具有荒诞性也是顺理成章的。
(四)指责广建寺院耗费民力,无益民生
正如前面所说,明朝时期石家庄地区兴造寺院过多。众多寺院得以兴建,除了僧侣和乡绅的组织号召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普通乡民百姓对寺院布施了人力、物力和财力。因为乡民认为这样做会为自己的现在和未来带来美好生活。原始佛教僧侣的生活资料来源主要依赖佛教信众的布施,僧侣不营产业,不蓄资材,以化缘的方式求得信众布施。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情况有所改变,出现了寺院经济,以支撑佛教的生存与发展。而乡民信众的布施仍然是佛教僧侣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佛教经典认为布施是信众修行的重要方法,大乘佛教主张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六种修行方法中,布施排在第一位。佛教经典大力宣扬布施者会因为自己的布施获得极大的美好的回报。布施有法布施和财布施,而普通乡民不了解佛教理论,他们所能布施的主要是财产。最高层次的布施是向佛陀、僧侣和有志修行者布施。北魏时期由瞿昙般若流支翻译为汉语的《毗耶娑问经》说:“有五种无上布施。何等为五?一施如来则为无上,二施众僧则为无上,三施法器则为无上,四施父母则为无上,五施王者失位贫穷则为无上。”这五种中有三种是佛教僧侣。布施作为付出能给布施者带来丰厚的回报,所以布施也称为做功德,种福田。北宋时期西天三藏法师翻译的《佛说布施经》中详细介绍了布施行为给布施者的回报。其中有:“以美食施,得离饥馑仓库盈溢。以浆饮施,得所往之处无诸饥渴。以衣服施,得上妙衣庄严身相。以住处施,得田宅宽广楼阁庄严。以卧具施,得生贵族资具光洁。以象马车辇施,得四神足无拥妙用。以汤药施,得安隐快乐无诸疾病。”又说:“若以上妙饮食供养三宝,得五种利益:身相端严、气力增盛、寿命延长、快乐安隐、成就辩才。如是南赡部洲,一切众生、父母妻子、男女眷属,如上布施,随愿所求,无不圆满。”③佛教以佛法僧为三宝。经过魏晋以来千年的深入宣传,日常生活本来艰辛的下层人民深信,以布施行为可以换取今生或来生的幸福,明朝下层乡民也是这样。1547年柏林寺大慈殿重修募捐开始时,“其愿施资财者累累皇皇,惟恐或后”[4]524。晋县杨家营观音寺的水陆殿重修时,“乡人出财众且频也”[10]548。无极县陈村的通圣寺1507年重修,“远近人心欢乐响应,万醜咸集。匪直戴白垂髫而已。凡木植砖石,鸠工匠作。每见车马纵横,不约自附。岂需量力用财而后成哉”[8]513。寺院修建有益于佛教文化的传播,但是毕竟消耗大量财富。生活本来贫穷的普通乡民将有限的收入布施给寺院,无益于他们生产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佛教经典中承诺布施的功德在现世中几乎无法兑现,这就引起一些士大夫们的批评。石珤认为这是“以天堂地狱轮回果证之说夸严闪倏,坐飨十方之馈”[8]512。吕秉彝认为修建寺院是“竭愚民之膏血,成无味之土木”[10]548。无极县知县曹崇信在《鼎建十方院并郊楼碑记》中说:“吁嗟楼兮,今天下龙宫梵宇不知几倍于国初,而闾阎窘迫日甚一日。故知修造寺观,全无福利也。”[8]519
佛教在中国古代社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下层乡民信仰佛教者众多,确实需要建造一定数量的寺院以满足乡民参与和进行佛教文化活动。不过以布施供养三宝建设寺院的功德激发乡民布施的宗教热情,不考虑下层乡民的经济条件,无节制地兴造寺院当然是不恰当的。辛集市在明朝有57所寺院,元氏县有50所寺院,其数量远远超出了乡民正常佛教文化活动所需的数量。盲目增加寺院数量,不但造成寺院使用效率降低,更是对广大下层乡民人力、物力、财力的毫无意义的浪费。这也就难怪士大夫们在碑记中一方面介绍寺院修建的基本情况,一方面抱怨修建寺院是与民争财,无益于乡民生产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三、结语
不同于西方的政教分离,中国历来是以政统教,教以辅政,二者相辅相成。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核心阶层,既是中央集权郡县制国家的统治基础,又是大一统国家的管理者。指引他们支持中央、管理地方的意识形态是以仁义礼智信为内圣修养、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外王事功的儒家文化。佛教则是中国下层广大农民的基本信仰。佛教与儒家文化最大的不同在于佛教主张个人现世的忧悲苦乐完全由自己负责。人所遭遇的现世之苦是其前世恶业的必然结果。若要改变现世的存在状态,只有依照佛法修行,守五戒,行十善,努力改善自己的心灵和行为。佛教反对通过改良或革命手段改变社会制度以促进人民的幸福。佛教的这种说法确实使现世的信众能够解释现状,看到未来,只不过这个美好的未来是在遥远的前世。即使这样,佛教也可以缓解苦难艰辛的下层人民的思想困惑。而佛教理论认为人的幸与不幸完全取决于自己而与社会制度无关,反对变革社会制度,这一定程度上消解泯灭了下层人民的革命精神。所以,士大夫们虽然认为佛教理论有些许荒诞,广建寺院是与民争财,但是他们仍愿意为寺院建设撰写碑记。他们对佛教的负面评价反倒提醒僧侣阶层认清僧侣的身份、明白僧侣的教化职能,让僧侣安心教化下层百姓,不要有任何非分的政治野心。佛教教化的作用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但是从维护当时社会制度角度考虑,佛教也发挥着协助儒家文化维护现有社会制度、消解下层人民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革命与实践精神的作用。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旧社会中国人民深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支配。中国人民深受神权的支配,石家庄地区下层乡民深受佛教影响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