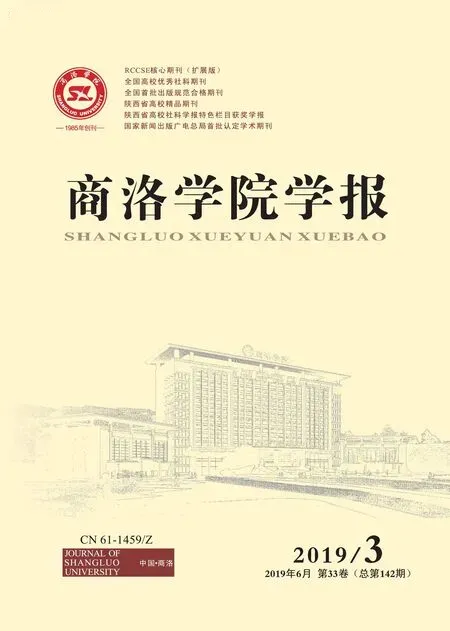论九连墩无字竹简的用途
——与《韩非子》“画荚”相互为证
赵小雷
(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069)
《韩非子》作为战国诸子的最晚出者,不但在思想史上具有法家集大成的意义,而且在文学史上也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这些固已为学界所公认。但是其语言文字作为史料真伪辨正之标准,这一价值,则还没有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在此,笔者拟就“画荚”一词,对考古资料的认识作用做一番辨正。
《韩非子》中的画荚,应是画策,实即背面绘以图案、正面为空白的髹漆竹简,其实物即九连墩无字竹简,并由此也反过来证明了九连墩无字竹简的实际功用,即待用之空白简策。
一、待用之空白简策——九连墩竹简用途
2002年湖北襄阳市枣阳境内吴店镇东赵湖村,抢救性发掘了一个大型的战国古墓群,称“九连墩战国古墓群”,被称为2002年考古大发现之一[1]。湖北省考古所所长王红星认为:“竹简的发现既是本次九连墩考古发掘最重大的发现,也是当年全国考古最重大的发现。它将为楚文化的研究工作提供重要依据。”[2]在其中出土了1359[3](一说为1364[4])枚竹简,“每支竹简宽约0.5 厘米,长约30 厘米”[2],据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胡雅丽介绍:“竹简篾黄一面空白,蔑青一面绘画,单元纹样为三角形变形凤鸟纹;若干单元纹样构成一组四边纹饰中间素面的回形云纹图案,一组图案需用竹简14 枚至19 枚,一般在16 枚左右;整画由若干组重复的图案构成,画纹凸起呈黑色,似由生漆掺和黑色颜料绘成。竹简的编线处均不见漆绘,所有画纹都在延续至编痕两侧时自动停断,说明绘画是在竹简编联成策后进行的。”[3]这批竹简与以往的发现最大的不同有两处:一是一面有规整的漆绘图案;二是一面为无字的空白。以前虽也有漆绘图案的竹简,但像这次“明显有编连的痕迹,上有漆书案,数量如此之大的竹简漆书图案是首次发现”[2]。而像这种大量的空白竹简以往更是从未发现过,胡雅丽称:“以前出土的竹简有时也杂有空白简,很明显是没有写完便让死者带到另外一个世界继续使用,但像九连墩竹简这样数量巨大却全部无字的现象还是首次发现。”王红星也持同样看法[5]。这就给后期的进一步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这批竹简到底是作什么用的,专家也感到困惑。自2002年发掘以来,十七年过去了,对此的研究几乎没有什么进展,甚至知网上根本搜索不到有关九连墩竹简的论文。在此,只能根据当时的新闻报导所引用专家的零星言论,作一归纳。总括起来有以下这样几种推测。
第一,舞谱、乐谱之类。“由于这批竹简出在女性墓中,研究人员曾推测这些画有可能是乐谱、舞谱之类。拼对编联后发现,‘简策’画由单一重复的图案构成,他们遂认为不具有寓意复杂的记录功能,而偏向实用。”[3]不具有记录功能是指重复的图案,那没有字的一面,会不会是文字脱落了?另有专家予以了否定,且理由充分:“无论漆或墨,化学成分都较为稳定,一般不会因为水浸泡或某种化学反应而完全脱落。而九连墩竹简上发现保存完好的漆绘花纹,就更不可能字迹完全脱落而另外一面的花纹仍在。况且……与竹简共存的漆木器都保存得较好,7 枚竹签牌上还发现了文字,可见竹简上如果有文字,也应当能保存下来。”那么是否因为墓主是女性,于是象征性地随藏了一些无字的空白竹简[5]?同样的也有专家对此予以否定:“竹简记录着有关随葬物品清单、墓主人疾病、占卜算命等方面的情况,从这点看来应与墓主人的性别无太大关系。当年在江陵望山2 号楚墓曾出土一批竹简,墓主就是一位女性,还有一些墓葬的主人性别现在并未确定,所以竹简不一定就出在男性墓中。”[5]在此,竹简肯定是有其某种实用功能的。一面绘有漆纹图案,一面为并非文字脱落之空白,那么剩下这样几种可能:一是准备记录用的空白简策;一是具有某种实用性功能的物品,这其中又有承载器物之衬垫和挂帘之分。
第二,背面绘有漆纹图案、正面为空白的待用简策。在这一点上,多位专家似乎具有相同的看法。胡雅丽认为:“另一种可能是,它是待用简策,有画的一面作为装饰,空白的一面有待书写。”[3]陈伟认为:“作为直接的目的,古代竹简应该都是用作书写的载体……就古书记载和迄今考古发现所见,还没有看到竹简有作为书写载体之外的功能。”[5]王先福认为:“第二种可能就是装帧精美的待用简策,就像我们现在用的稿纸,准备写字,可由于特殊的原因,稿纸随主人一起埋葬在地下。”[4]
第三,铺在器物底下的竹垫。胡雅丽认为:“以此纹样组成图案施于简策上,似乎意在装饰……‘简策’画的用途也许是在燕享酬宾时铺陈于筵席之上,承托饮食器皿。”[3]王先福认为“或许有置于俎上承托器皿的功能”[4]。
第四,挂帘。王先福推测的第三种可能就是:“在拼合成的竹简片边沿上下各有细小的穿孔,这不是可以穿进丝线,将竹简片穿起来,当帘子用吗?还可以挂在车上,挂在窗户上,挂在墙上作装饰用。”[4]
要之,对这批无字竹简的用途,由上述专家推测来看,一是乐谱、舞谱;二是待用简策;三是器物垫;四是挂帘。这其中,第一种在当时就有很大的猜测性,没有被大家所接受;第四种也只为一家之言;第三种器物衬垫之说,虽有不同的专家提出,但更多的只是一种推测,所论甚少,没有令人信服之处。而且既无以往的文物支持,也不符合葬礼规范。随葬礼多是“生者用以表达对死者的敬意,与墓主生前身份有关。而且这批竹简下葬时是装在竹笥(方形竹器)里的,更表明对待它们的态度非常慎重。”一般器物的衬垫,似乎还达不到这个程度。况且“这批竹简的长度和用于写书或官方记录的‘书简’大致相当”[5]。因此,只有第二种,即待用之空白简策的观点,认可的专家最多,也最有可信度。
如上所述,一是规制上与以往出土的竹简大致一样;二是竹简的用途,公认的也都是用于作为记录、书写的载体;三是以往出土的竹简也有漆绘的图案。这里唯一难以解释的是,大量正面空白的竹简,其用途到底是什么,至今没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但正是在此,空白,却显示出了它的真正用途,即作为书写和记录的载体。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是由“地下之材料”以证“纸上之材料”,但亦可相反,由文献资料以证明出土资料,从而达到互证的目的。
二、《韩非子》“画荚”实为“画策”
在此,如果引入《韩非子》中有关画荚的分析,所谓“无字天书”的九连墩竹简之谜或许有可能获得一个比较合理的解答。《韩非子》中所称的“素髹荚”“画荚”和“画策”者,即为髹之以漆,并用以书写的竹简。素者,即为只刷黑漆而无图案之竹简;画策者,即为背面绘有彩色图案之竹简。韩非是个实用主义者,他之所以主张使用素髹之竹简,而反对绘画之竹简,就是因为作为书写记录之竹简,只要刷之以漆便于使用即成,画不画图案都是一样的。
《韩非子》的原文为:“人主之听言也,不以功用为的……是以言有纤察微难而非务也,故李、惠、宋、墨皆画策也;论有迂深闳大非用也……客有为周君画荚者,三年而成,君观之,与髹荚者同状,周君大怒,画荚者曰:‘筑十版之墙,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时加之其上而观。’周君为之,望见其状尽成龙蛇禽兽车马,万物之状备具,周君大悦。此荚之功非不微难也,然其用与素髹荚同。”(《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其中的关键即在于对画荚之“荚”以及“髹”的解释。在此篇“客有为周君画荚者”条,《韩非子·新校注》引庐文绍曰:“‘荚’伪,下同。前作‘策’。策、筴同(按:筴,在《诸子集成》本作荚)”。接着有陈奇猷的按语:“此条所说即今幻灯之底片。荚盖豆荚、榆荚之荚。凡荚皆有薄膜。古者无玻璃,故取荚膜而制底片,取其易于透光也。若用简策,则无所用之。庐说殊谬。”[6]《韩非子·新校注》对“髹”的解释:“王先慎曰:‘髹’本作‘髤’。《玉篇》:‘髤,同髹。’《史记·货殖传》‘木器髤者千枚’,注:‘徐广云:髤,漆也。’《汉书·皇后传》‘殿上髤漆’,师古云:‘以漆漆物谓之髤。’”[6]据此,髹(髤)作为名词即为漆;作为动词,即为刷漆。而对于荚,则有两种解释:一为陈奇猷之新说,荚即为豆荚、榆荚之荚;一为庐文绍之旧说,即画策之策,策、筴、荚形近而误。笔者以为薄膜之说非,画策之说是。
庐文弨之所以认为:“‘荚’伪,下同。前作‘策’。策、荚同。”即,画荚当为画策。这是因为,前面之“画策”是“经”,后面的“画荚”是“说”,即对“经”之具体阐释。“经”即是今日之论点,“说”,即是今日之论证过程。故以前面的“画策”之真,证后面的“画荚”之伪。这是符合为文之规律的,相反则不能成文,因为论证是为论点服务的。而陈奇猷认为“策”当作“荚”,这是以后面的“画荚”之“真”,证前面的画策之“伪”,即以后面的“说”之画荚的正确,证明前面的“经”之画策的错误。这不是作者自己打自己的脸么?韩非会犯这样的错误?后面的“画荚”,陈奇猷先引庐文弨之说,“策、筴同”。但《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客有为周君画荚者”《诸子集成本》,该段的注二,庐说最后是“策荚同”,在陈本《韩非子新校注》(下册)该段的注五的奇猷按中则称:“‘筴’,当作‘荚’。”[6]是陈奇猷“荚”“筴”不分。筴与策可以通用,但荚与筴却不是一个字。“遍查《说文解字》《康熙字典》、新旧《辞海》等等辞书,均无荚与筴通用之解”[7],而策与筴本来即为同字而异形,如果不是印刷错误,则陈说难免前后矛盾。对于“此条所说即今幻灯之底片”[6],张觉亦采其说,但据张觉对该段的校记,“荚”,又训作“筴”和“策”[8]。因此,笔者以为,庐说不错,陈说“殊谬”,其原因盖以“荚”“筴”形近而混。
其一,不要说豆荚了,就以皂角而言,也大不过一拃,怎么在八尺之墙洞上观看?
其二,薄膜,就是如皂角之大,其膜,既软且薄,又怎么在上面用生漆绘画图案?又怎么编制成“策”,即以麻绳或皮条将其连缀成一体之形状?
其三,又怎么解释后面的,“其用与素髹荚同”,“先慎曰:素,未画也。此言画荚之用何异素髹。奇猷按:‘筴’,当作‘荚’。”[6]给豆荚一类的薄膜上刷漆,不论画与不画,也不论刷得上去刷不上去(实际上根本刷不上去),其所为何来,又有什么用?又怎么解释“素,未画也”?而给竹简上刷漆以记事,则是古制。中国对漆的使用早在文字发明以前,“至迟在7000 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代就已经发生”[9]。髹字(髤),即上引之画荚,其本意即为赤黑色的漆,作动词即为涂漆。《仪礼·乡射礼》:“楅,髤,横而拳之。”郑玄注:“髤,赤黑漆也。”《汉书·外戚传》:“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颜师古注:“以漆漆物谓之髹”。而“漆之为用也,始于书竹简”[10],不论是木牍还是竹简,髹之漆以防开裂、虫蛀、朽坏,既有利于书写,又便于保存。而释荚为薄膜者,不见于典籍,亦不见于《韩非子》其他篇章,而以画荚为幻灯之底片者,亦不见于他说,因此它连孤证都算不上,此处的漆和髹仍然是指涂抹、黑漆。
其四,韩非所论之荚,不过是为其功利观提供一个例证而已,因而刷过漆的那个东西,在日常生活中必然是有实际用处的,而这个用处,又是不需要花纹图案的。《周礼·春官·巾车》:“漆车……雀饰”,注云:“漆车,黑车也。”疏云:“凡漆不言色者,皆黑。”此即素髹漆者。所谓“画荚者……此荚之功非不微难也,然其用与素髹荚同”(《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者,指的就是背面刷了彩色之漆画的简策,与只是上了一层黑漆(素漆)而没有髹之以图案的简策,在记录的功用上,其效果是一样的。因此,这个东西只能是简策,即由有一定长度和宽度的木牍或竹简用绳、线连缀成策,由此则有一定的面积,故可以在其上髹漆作画。“髹荚”是指“漆荚”,用“素髹”工艺髹漆制作,画荚则用彩漆髹漆制作[11]。背面有图案的就是彩绘髹漆工艺;无图案的就是素髹漆工艺,即韩非所称的“素髹荚”。画荚所绘之图案,经过一定角度的光线投射,必然会有相应的投影放射出来。这其中有两种情况:其一,简策可以透过光去,日常生活中隔着竹帘向外看、皇宫之垂帘听政等现象,是其证。其二,就算不能透光,也能反光,中国生漆的光亮度完全可以反光成像,今日照相机的原理,在柏拉图时代就已经有所认识了,中国的《墨经》中已经有小孔成像的成分了。而利用光的反射而形成的神奇光影效果,在古代西方的建筑上都有不少例证。因此,所谓画荚,类似于幻灯之底片,这没有错,但它是简策,而非豆荚之薄膜。惟其是简策,有一定的面积,用来当投影的“底片”才是可以的,而一指大小的豆荚之薄膜则不可。
基于此,笔者以为所谓画“荚”者,当为画“策”无疑。因为只有它才可以既作为记录的工具,又可以用来作为投影的“底板”。以画荚为薄膜的错误在于,只看到韩非此论的前半段,而完全没有考虑到后半段的意思,因而也自然顾及不到全段话的本意了。依其说,就算是薄膜可以用来当幻灯的底片,但怎么用于书写呢?起码至今还没有发现上了漆的豆荚薄膜类的书写工具的实物。而简策,素髹“荚”者,则是有大量实物为证的,九连墩无字竹简的大量出土,则又提供了彩髹“荚”(策)的实物证据。
要之,筴与策实为同字而异形,与豆类之外壳全然无关,薄膜之说更是不知所云。画荚,正一字为画“策”,全篇皆通,陈说则是将正就错,不惜改变全文之意以圆豆荚之说。
三、九连墩无字竹简与《韩非子》之“画策”相互为证
笔者认为,以《韩非子》有关画荚的论述为据,则无字竹简的功用正是上述第二种,即背面有漆绘图案而正面为空白的待用简策,其形制证之以九连墩竹简为,简高30 厘米,幅宽13~15 厘米左右的长方形“竹帘”,“16 到19 支简能拼合成完整的一组……可拼合成60 余块竹简片。”[4]每根竹简上可以写字,这是其本来的用途。胡雅丽称“这批竹简的长度和用于写书或官方记录的‘书简’大致相当”[5],似乎也可用作他途,故有其他几种猜测。在此,不妨由形制方面分析一下两者的异同。
九连墩竹简:背面有纹样重复的彩色漆绘图案,正面为空白,有编制成策的痕迹;
《韩非子》之画荚,有只刷黑漆的“素髹”荚者,有“其状尽成龙蛇禽兽车马,万物之状备具”(《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的彩色漆绘图画。
这其中,两者有以下几个共同之处:其一,都为竹简;其二,都呈现为“策”,即编制成篇的形式;其三,都有髹之以漆的彩绘图案。所不同者,《韩非子》的画荚,没有提到正面是否为空白;又,髹之以漆者,是背面还是正反两面都有漆。但以《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客有为周君画荚者”这一段及其文意来看,髹漆者,肯定是在背面,且正面为空白以记录文字等。
第一,《韩非子》说得很清楚:“人主之听言也,不以功用为的……是以言有纤察微难而非务也,故李、惠、宋、墨皆画策也。论有迂深闳大非用也。”韩非对于“言谈”一贯强调要以功用为检验的标准,而坚决反对巧言令色之言说的技巧,以及诸如惠施之辩、墨翟之巧者。该篇后面更有对“白马非马”之否定,尽管在逻辑学上该命题是正确的,但在实际过关时,则不免要“顾白马之赋”。
第二,竹简正是言说之载体。与言说以实际功效为考察标准相对应,其载体自然也要以实用为标准。在此对应的正是“素髹荚”者,即背面髹之以黑漆、正面为空白以为书写、记录之用。否则为何要给竹简正反两面刷漆呢?作何用之?
第三,“素髹荚”者,如果不是背面髹之以黑漆、正面为空白以为书写、记录之用,为何要反对画荚呢?所谓画荚“之功非不微难也,然其用与素髹荚同”者,这个“用”正是指书写记录之所用,如今日之稿纸然。简者,单篇之稿纸,策者,一本之稿纸。否则单从漂亮来看,“此荚之功非不微难也”,然“不以功用为的……是以言有纤察微难而非务也。”在韩非看来,在竹简上绘以装饰性的图案,就纯粹是多余的了,因此要坚决地反对,此即“非务”,而原因正因为其“非用”。
综上所述,《韩非子》中的“画荚”一说,为九连墩的“无字天书”之用途提供了一种文献的证据,即它所具有的书写记录之实用功能;而反过来,九连墩的“无字天书”也为《韩非子》画荚之形制提供了实物证据,同时也足以证明其“画荚”当为画策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