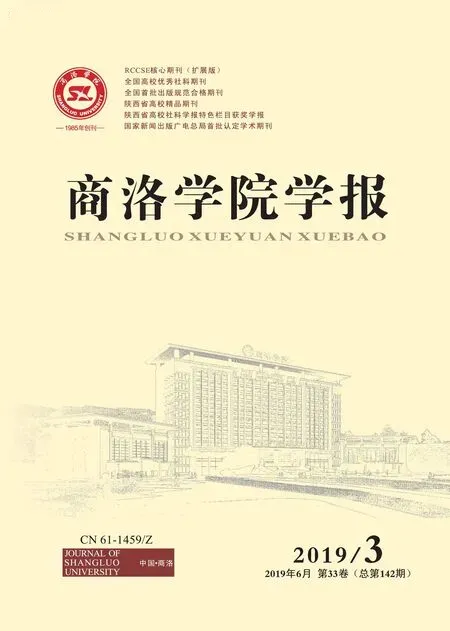族长的形象自觉及其文化意义
邰科祥,李继高
(1.西安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西安 716000;2.商洛学院 学报编辑部,陕西商洛 726000)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曾经有一类人物形象让读者记忆犹新,那就是地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作家笔下的韩老六、杜善人、钱文贵、江世荣、冯兰池、黄世仁、南霸天、周扒皮等凶恶的地主形象早就固化在一代人的头脑中。所以,当《白鹿原》中的白嘉轩出现的时候,很多人不由得惊呼:“好地主”或者“新地主”出现了。
早在《白鹿原》出版的1993年,评论家蔡葵说:“作品的新,表现在写了两个地主,作为主人公、正面人物,在新文学中很少见,这种全新的地主形象,我们能接受,有征服力。”[1]431曾镇南也说:“作品主要写了两户地主和他的儿女们的命运,表面上消解了阶级斗争,实际上有更深刻的阶级对抗”。[1]435直到2008年,还有评论者林觉民以《好一个“大写”的地主——试析〈白鹿原〉中白嘉轩形象的创新意义》为题来表述白嘉轩的形象。此文说:“白嘉轩的形象颠覆了长期以来我们在文艺作品中司空见惯的‘贪婪、吝啬、凶残、狠毒、淫恶’的地主形象,而给读者一种耳目一新的阅读感受;同时,白嘉轩还以其独特的地主身份和经历,引发当代读者对地主这一特殊阶层的重新审视和评价。”[2]
然而,笔者在2009年采访作者陈忠实时,他却这样回答:很多评论者都提到白嘉轩是一个好地主、新地主形象。如果放在文学史上地主类人物的形象画廊中去看,他的确与以往的形象大为不同。但是,实际上一开始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我没有想着去塑造一个新地主的形象,更没有想着把白嘉轩与南霸天、黄世仁等有意区别开来[3]。
也就是说,在作者自觉的创意中,“好地主”或“新地主”的概念就不存在,他根本不想从这个视角去塑造他笔下的主要人物。“所以,我没有自觉地反叛以往地主类形象的写作意识,而且在我的观念里,我并不否认现实中真有黄世仁之类的地主。我只是不想用以往的阶级斗争的观念去描写人物,如果非要说有反叛的话,这一点可能是明确的。我在80年代中期接受了一个文艺理论家的文化心理结构学说,我是用这个理论来塑造人物的。”[3]
一
陈忠实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他塑造白嘉轩这样的人物,是摒弃了以往的阶级斗争观念,而用他所认同的文化心理结构学说作为理论支撑。而且,他也着意选择了一个新的字眼或概念来对他笔下的人物给予命名,这个字眼就是“族长”。
“我没想着写一个地主,而是要写一个族长。”[3]当我从他口中听到这个名词时有点意外,但更多的是困惑。在我最初的期待中,希望他承认白嘉轩就是一个好地主或新地主的形象。然而,陈忠实不但明确否认其具有这个意识,而且还要换一个名词,我在内心中,当时觉得他有点故意标新立异,或者说玩文字游戏。直到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族长的称谓有其非同寻常的意义。
族长与地主根本不能划等号。它与经济实力有关也无关,不是谁地多业大就能成为族长,除了地多,还要有其他方面的资质。正如作品中的朱先生提醒白嘉轩说:“房是招牌地是累,攒下银钱是催命鬼。”拥有过多的土地,成为地主,早已不是实践朱先生思想之白嘉轩的目标。《白鹿原》中的鹿子霖从土地的拥有量上说不弱于白嘉轩,甚至几度都超过他,而且从本心里,鹿子霖也特别想做这个族长,但事实是他就是做不成。用陈忠实的话说:“也不是谁都可以做族长,一般来说族长不会是穷人,当然也不一定是大地主,常常是我们称作财东的人为多。”[3]
族长不是一级行政官吏,不是政治身份的标志,他没有行政权。他们没有国家赋予的行政权,他们主要依靠一个宗族自己制定、延续的乡约来规范和约束族中人的行为,这个乡约其实是儒家思想的通俗化[3]。所以,族长其实就是一个文化符号,是民间乡约、秩序的代表,是族众自发推举或拥戴的精神领袖。他们在乡村的地位凌驾于同层次政治与经济人物之上。在乡村最有权威的人是宗族势力,它的代表人物就是族长[3]。
族长是一个历史概念,它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在封建制度延续的时代,它是一直通用并具有实际功能的民间自治领袖。但在民国之后就逐渐被淡化,直到建国以后就再也不复存在。地主的形象虽与之有一定重合,但地主这个阶级概念的出现已到了20世纪20年代之后。所以,要描述新旧交替时代区间的这类人物就只能用族长的称谓。
另一方面,对《白鹿原》主旨的设计同样呼唤着族长的形象。陈忠实说:“我想得最多的是,处于封建制度解体、民国建立这种改朝换代的特殊区间的中国人到底做了什么?我们传统人格中一个完整的人是什么样的?”[3]
在这个改朝换代的特殊区间的中坚人物就是族长,正是他们承袭着老祖宗的文化基因,艰难地维持着家族的稳定。同样,传统人格中完整的、理想的代表仍然是族长。所以,《白鹿原》倾其心力塑造了白嘉轩的形象。
在陈忠实看来,只有族长的形象才能够完整地显现中国传统文化或者价值观对个体性格的塑造过程与结果。白嘉轩是传统文化的践行者,儒家思想的精华与糟粕在他身上完整地得到体现。他做到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行。他做事光明磊落,从不偷偷摸摸;他为人言出必行,说到做到;他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对儿子犯错从不护短,对长工鹿三敬重如兄;他嫉恶如仇,见善必行,连他的腰也总是挺得很直,让黑娃一辈子都感到敬畏。可以说,做一个君子似的好人和洞达世事之人是白嘉轩的理想与信念,当然也是小说作者陈忠实的希冀与追求。
白嘉轩的君子之风无需多言,但对他圆融通透的行事准则还要多提几句。众所周知,朱先生是《白鹿原》这部小说的灵魂,更是白嘉轩的人生导师。他以大儒的睿智,同时也以兄长的丰富阅历和人生体悟指点白嘉轩:“房是招牌地是累,攒下银钱是催命鬼,房要小,地要少,养头黄牛慢慢搞。”他传递的是儒家中庸思想的精髓,所谓:不过亦不能不及,不贪或知足常乐是幸福的真谛。
当时,处于盛年的白嘉轩还想发家致富,振兴家族,所以似乎不愿接受这种有度发展,见好就收的提醒。他更没有充分意识到这句话的文化分量,直到他进入暮年方逐渐领悟。他劝做了县长的儿子白孝文要有收敛,不要张扬。尤其是小说结尾的描写既展现了白嘉轩经历了气涌头顶、血蒙双眼的巨大刺激后对人生的顿悟过程,也曲折传达出作家陈忠实的某种价值象征——世事似应糊涂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白嘉轩重新出现在白鹿村村巷里,鼻梁上架起了一副眼镜。这是祖传的一副水晶石头眼镜,两条黄铜硬腿儿,用一根黑色丝带儿套在头顶,以防止掉下来碎了。白嘉轩不是鼓不起往昔里强盛凛然的气势,而是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尤其是作为白县长的父亲,应该表现出一种善居乡里的伟大谦虚来,这是他躺在炕上养息眼伤的一月里反反复复反思的最终结果。微显茶色的镜片保护着右边的好眼,也遮掩着左边被冷先生的刀子挖掉了眼球的瞎眼,左眼已经凹陷成一个丑陋的坑洼。他的气色滋润柔和,脸上的皮肤和所有器官不再绷紧,全都现出世事洞达者的平和与超脱,骤然增多的白发和那副眼镜更添加了哲人的气度。他自己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拉着黄牛到原坡上去放青,站在坡坎上久久凝视远处暮霭中南山的峰峦。
总之,儒家思想的精髓及其价值观念主导着白嘉轩一生的行止。由此可见,陈忠实有意区分“地主”和“族长”的人物称谓显然不是简单的用词之别,而是蕴含了他自觉的思考。
二
族长形象的塑造尽管是对中国当代文学人物画廊的一个崭新贡献,但它的意义却不限于此,我们还可从更广泛的背景上加以思考。
首先,族长的形象塑造有助于揭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源泉。《白鹿原》中的族长不能单单理解为白鹿两族的首领,实际上,在作者的思考中,其也是中华民族世代脊梁的代表。陈忠实显然不是讲述一个家族的故事,而是反思整个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而不衰落的原因。为什么作为世界上四大古文明之一的中华民族,其历史唯一没有间断,就是依靠着像族长这样的精英和脊梁才得以持续。所以,白鹿家族是中华民族的缩写,白鹿原的族长也是中华民族世代英雄的化身。
陈忠实还特别指出,延续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尽管有腐朽的基因,但主要是优良基因在发挥着作用。“我是有一个很清醒的理念:那就是如果传统人格、文化全是腐烂的、糟朽的,在乡村具有重大影响的人都是黄世仁、刘文彩,那封建社会还能延续两千年吗?虽然有些朝代的皇帝昏庸无能,但总体的传统文化精神没有改变,决不能简单的用腐朽一词来概括。王朝更替,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不变。准确地说,支撑我们民族延续几千年的文化因素是最优良的基因与最腐朽的基因的结合物。”[3]
建国以后,受阶级论观点的影响,封建社会被视为腐朽透顶的制度,没有任何正向的价值可言,这种简单的文化虚无主义导致了较长时间中国人对自己历史传统的严重误解甚至全盘否定,实际上也给自己造成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巨大困惑。按照一般的逻辑,一个制度中如果没有进步的、合理的因素,它怎么能存在几千年之久?然而,很长时间以来,没有人愿意或敢于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白鹿原》应该是在文学领域最早直面这个话题的作品。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陈忠实是为封建主义唱了一首赞歌。关于这一点,其实在《白鹿原》出版的当年,费秉勋就专门指出过,可惜没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费秉勋说:“对于中国封建制度生命活力和长命因缘的揭示, 也应成为中国文学用武的一个领域。白嘉轩这一人物的塑造,就不期而然地做了这种独特的工作。”[4]
这种“生命活力”或优良基因实际上已经内化为中国人心理的深层结构,成为左右中国人几千年行为的集体无意识。
文化心理结构在我看来是一个深层的人性特征。中国人和西方人在外形上好辨别,差异不大,无非一个是黑眼睛、黑头发;一个是蓝眼睛、黄头发。这些很表面,真正的差别在心理结构,尤其是做人。《白鹿原》中提到的乡约实际上就是普及到中国乡村的心理结构,它能判断人和事的好坏、高下、是非[4]。
这个集体无意识具体地说就是以儒学思想为主体的价值观,不论是改朝换代还是政党纷争,不管是作为个体的为人处世的准则还是作为协调人际关系的基本规范,几千年来,都是它在一直发挥着支配性的作用。
其次,族长的形象的成功塑造揭示了推动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在《白鹿原》之前的同类题材的作品,意识形态的立场成为作家审视世界的唯一工具,一方面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对人群进行简单的归类;一方面局限于历史教科书的材料,对众所周知的事件给予人云亦云的解释。尤其是涉及到建国前国共两党的敏感话题,就更没有作家敢于跳出这个阈限。
但《白鹿原》则试图站在民间的立场,为中华民族书写一部人类的秘史。这个秘史并非轶闻趣事,更非宫闱私密,而是中华民族的心灵史。此前的历史教科书还是历史小说,大多注目表层的社会事件和领袖人物而忽略或无视人心的轨迹以及普通民众的生活。这样的历史叙事无疑只能就事论事,浮于表面,难以挖掘出历史背后的动力。我们常说一句熟语:人民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这当然没有问题,但人民的“什么”在推动历史才是我们更加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数千年来没有人主动回答或去自觉地探索,《白鹿原》借助族长这个形象的塑造正好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个家族的兴盛有赖于他们数代祖先所总结、流传下来的经验,就像白家的“匣匣经”保证了他们家族的不败和强大。一个民族的昌隆同样有其被时间反复验证的优良传统。《白鹿原》中有这样一段话:
白嘉轩从父亲手里承继下来的,有原上原下的田地,有槽头的牛马,有庄基地上的房屋,有隐藏在土墙里和脚底下的用瓦罐装着的黄货和白货,还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财富,就是孝武复述给他的那个立家立身的纲纪。[5]
白鹿宗族繁衍不乱的传统就是这个内在的“纲纪”和我们在前文反复提到过的乡约: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
那么,中华民族几千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倒的精神支柱无疑就是“仁义礼智信”等等优秀的传统价值观。《白鹿原》通过白嘉轩作为族长的正面形象以及鹿子霖作为“乡约”的负面形象完整地演绎了人性的内在动力。
陈忠实以一部长篇小说为自己赢得生前身后名,《白鹿原》之所以长销不衰并逐渐地成为当代文学经典,其奥秘恐怕都在这里。
三
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尤其是儒家思想的价值观至今还在支配着华夏儿女的思维和言行,它已经内化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重新表述,更具时代色彩,但不管是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或者个人层面,其精神指向依然与传统价值观一脉相承。所以,我们凸显《白鹿原》借助“族长”形象的塑造所传达的深层意义也正是在反溯现代价值观的根系,从另一个侧面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核心语汇提供思想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