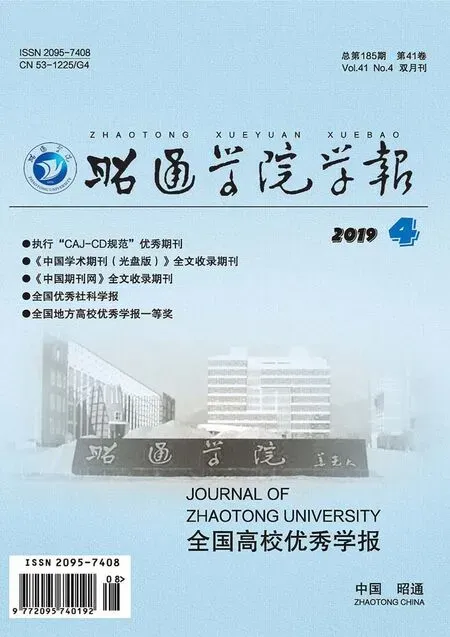博雅教育与工作的人文化
——论杜威与赫钦斯之争
金 凯
(浙江师范大学 杭州幼儿师范学院, 浙江 杭州 311231)
自从亚里士多德将博雅教育与机械训练区别开以来,博雅教育/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和职业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哪个才是学校教育的重点这一问题已被争论了数个世纪。美国的著名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和永恒主义教育流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梅纳德·赫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1899—1977)也为此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人们普遍认为杜威是职业教育的倡导者,而赫钦斯是博雅教育的支持者。然而对二者的作品《民主主义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 )和《伟大的对话》(The Great Conversation)原著进行详细的分析,就可以发现二者的相似点和不同点远比他们所呈现的要复杂。两位教育家都赞同每个人都应该接受博雅教育,反对只为谋生找工作而学习。他们也都认为有必要将博雅教育拉近人类生活。但是两人的教育理念在本质上的不同之处多于相同之处。二者的本质区别不在于杜威提倡工厂工人也需要接受博雅教育而赫钦斯主张每个人都应该阅读伟大的书籍,而在于他们对于博雅教育的本质以及博雅教育本身是工具还是目的这一问题存在分歧,在于二者对于生而为人的意义以及对于人类美好生活的截然不同的憧憬。杜威所渴望的理想社会是每个人都能够在自由意志下进行工作(以理性思考作为指导),享受作为回报的闲暇时光;赫钦斯则希望通过博雅教育,让社会上的所有人都能理解和批判性地审视各自的生活与工作,从而找到人生的意义。
一、杜威:博雅教育应与劳动相结合
(一)以个体能动性为其自由属性
杜威对博雅教育与工作的二元对立进行了批判。传统观点认为,“商品的生产效率和服务的提供效率天然就与自我指导的思想所分离;重要的知识和实用成就之间也是天生就分离的”[1]256。 这一观点的根源来自于古希腊时期社会阶层的高低之分,奴隶们承担了所有辛苦工作,只有自由人能享受闲暇(leisure)。这一区分也在之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体现在了政治上和心理上。杜威对此的批判是基于他的观察。他发现人文学科和所谓的实用学科之间能够相互转换。二者之间的界限现如今已模糊化。作为实用学科的自然科学,在教学方法上其“实用性”已被移除;而作为人文学科的音乐和文学在教学方法上则越来越注重技术技巧。同样地,几何和算术在古希腊被认为是属于博雅教育的人文学科,而在现代社会这两门学科正发挥着巨大的实用价值。
基于这一观察,杜威认为有必要也有可能将人文教育与劳动结合起来,因为他看到了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可以解决的问题。机器的发明解放了人类,让人类能享受更多闲暇时间,作更高层次的思考。然而问题在于“大部分工人对于他们工作的社会目标既没有深刻的认识也没有直接的个人兴趣……他们做着他们的工作,既不自由也没有智慧,只是为了挣工资。因此他们的工作是狭隘的,也会让今后的教育设计只倾向于为这些不自由和“不道德”(immoral)的工作提供技能培训。这样的工作是不自由的,因为工作的人并没有自由地参与进来”[1]260。从这个角度来说,仅以谋生为目标的职业教育是不自由的(illiberal)。一项活动或者工作是否自由,取决于个人是否自发自愿地参加,虽然同一活动的实体性质并没有发生改变。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教育若能联合社会成员的意向(disposition),那么这种教育也必能对社会统一做出贡献”[1]260。也就是说,一个理想的民主社会可以通过尊重个体的兴趣而得以实现。由此可见,个体的能动性和兴趣是杜威博雅教育/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人文属性/“自由”(liberty)属性中重要的因素与工具之一,从而帮助人们实现工作人文化和社会民主化。
(二)实现民主社会的工具
教育能推动的不仅仅是政治上的民主。杜威认为民主的实现需要依靠系统的教育,因为无论民主还是教育都会随着生活质量的改变而变化,且两者都关注共同兴趣点。 “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府形式,本质上更是一种相关的生活方式,一种联合交流体验(conjoint communicated experience) 。参与同一兴趣活动的个体数量得以扩增,如此每个成员都能对照其他成员的行为,思考其他成员的行为用以指导自身行为,这样做的效果等同于消除了阶级、种族和国境的障碍,让人们能更为全面地察觉到人类活动的意义 ”[1]87。 杜威将民主看成一种联结所有人的方式,方法就是让人们分享共同的兴趣,紧密联系,互相理解,相互学习,以实现人人平等,消减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隔阂。他考虑的既是个人福祉也是社会福祉。历史上所有的文化互动,无论是通过旅行还是通过经济和商业的交流,甚至是战争,都把人们拉得更近。他的民主理想来源于对美好社会的理解:美好社会的两条标准之一就是为各种不同群体提供更加多样化的共同兴趣点或共同目标,将这些共同的兴趣作为控制社会的要素;其二是允许不同群体之间进行更多更自由的互动,能适应由这些互动所引起的新状况 ,以确保社会不断的调整与进步,因为互动的多样性可产生刺激,有助于挑战思维、开发创意。
(三)满足社会需求的教育
在他的民主社会理想的指导下,杜威坚信教育的目的是要满足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孩子们无法像以前一样从家务劳动和邻里系统中学习集体精神,找到生活的意义。学校越来越像工厂,与真正的生活动机和意义毫无关联。学校通常被认为和个人有关,和社会无关。社会精神的缺乏也导致了学生之间的学习竞争和个人主义,因为“纯粹地吸收知识点完全是个人自己的事,很容易导致自私自利现象盛行”[2]。正如美国教育家与政治家霍瑞思·曼(Horace Mann)把社会比作“完善的成人阶段”,把学校比作社会的不成熟的婴儿状态[3], 杜威也认为学校里大多数的训练会影响到社会的未来,学校是社会的雏形,不应该只是一个传授抽象的不接地气的学科知识的地方。杜威秉承着“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一体” 的理念,主张学校应该用社会精神 ( 服务精神)来浸润学生,帮助学生找到工业时代所丢失的“自我指导”精神(self direction),找到生活的意义,从而使得社会更有价值、更加可爱与和谐。因此,杜威提出的博雅教育就是提供机会让学生在做中学,学习合作、承担责任、与他人交流、关心公共需求。人类本就有在实践中学习的冲动和倾向,而“做中学”的意义远比吸引孩子们上学更为深远。实践教学能给予孩子们真正的学习动力,有助于他们建立与现实世界和真理的联系。“我们现时代的这个问题比柏拉图时期更为迫切,那就是工作的人应当在其脑海中存有方法、目的和理念,一个人的活动应当对他自己有意义”[1]23。杜威在这里强调了认知过程中意识的重要性,成为真正的人就意味着找到自身的意义。
二、赫钦斯:博雅教育应与劳动相分离
面对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更多闲暇时间,赫钦斯也和杜威一样想到了人生的意义,但是思考方向截然不同。他认为要实现工作的人文化,就应该用博雅教育来使工作着的人先学习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的人,从而不被工作所束缚。赫钦斯提出疑问:“如果一个人在流水线工作以外的个人时间被浪费了怎么办?如今这种浪费就很普遍,人们在闲暇时间追求着只能被称为“低于人类”(subhuman)的活动。如果这个人在流水线上工作的时候脑袋里空空如也怎么办?”[4]22。 赫钦斯担心“低于人类”的工作会让人失去人性,这就意味着在赫钦斯眼中,人文活动比体力劳动要高级。然而他同时又看到了工业化可能会为民主带来的积极贡献,他承认“机械化容易把人降低成一个机器人,但也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和闲暇时间以供人们接受博雅教育,从而最终真正成为一个人”[4]23。对赫钦斯来说,工业化时代是一把双刃剑,为了利用好这把剑,必须用广泛的博雅教育来填平机械化与民主之间的鸿沟。和杜威一样,赫钦斯也主张每个人都应该接受博雅教育。“以前博雅教育是贵族教育,因为只要享有闲暇和政治权力的人能享受。如果在以前博雅教育对那些有闲暇时间和政治权力的人来说是最正确的教育,那么它对现今社会的每个人来说也是最正确的教育”[4]43。对于赫钦斯来说,博雅教育是最好的教育,在古希腊时期只有特权阶级才能享受,而现如今的民主社会中每个人都有接受博雅教育的权利。赫钦斯与杜威的一个显著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坚持博雅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分离,虽然批评家常常认为赫钦斯太过理想主义,给每个人都提供博雅教育这一想法很难实现。赫钦斯回应说:“历史已经证明:我们无法指望奴隶能展现自由人的美德,除非先解放了他们。当奴隶们获得了自由,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能有别于那些未获得自由的奴隶”[4]45。他认为全民博雅教育的理想只有试了之后才知道是成是败。因此,可以说赫钦斯是主张平等的,而不是精英主义者。他提倡的博雅教育看似要求很高,但这不代表他是精英论者,因为他对年轻人的智慧有信心。虽然目前看起来不太可能实现,但至少每个人都应当有机会接受博雅教育。问题是应当采用何种博雅教育,以何种方式进行教育。
三、人文的教学方式还是人文的教学内容?
杜威和赫钦斯均主张将博雅教育拉近生活。杜威的重点在于博雅教育的方式,主张通过人文的方式在实践中教学,而赫钦斯关注的是博雅教育的内容,推崇的是将伟大的书籍作为教学材料和老师。这个鲜明的分歧从根本上来说反映了杜威把理论看作是行动的工具而赫钦斯把理论看作是“绝对真理”[5]。杜威的博雅教育理想以他的学习心理学以及学习方法为基础。他强调“古代的理论发生了转变,因为人们意识到实践可以被引导,只要将思想所暗示的内容都纳入其理论内容中,只要结果能导致经严谨证实的知识。这样一来,“经验”就不再是基于过往经历的(empirical),而是实验性质的(experimental)。理性思维也不再是一种遥远到仅存于理想的能力,而是意味着所有能让活动富有意义的资源。杜威在这里表明了理论与实践应该相互促进,试图将理性与我们的经验结合起来,以使学习富有成效。在杜威看来,知识一词从广义上来说是客观的。但他的这种理解似乎缺乏任何意识形态或道德准则,这些元素一旦缺乏,就很难引导学生通过职业来思考人生的意义。
赫钦斯则主张通过博雅教育来激发共同的人性。赫钦斯认为,博雅教育的目的是使人类更优秀,达到个体优秀和公共优秀(因为人是一种政治动物)。其目标是人作为一个人也作为一个公民能更优秀。博雅教育把人看作是一种目的,而不是一种工具;它关注生命的意义,而非生命的途径。也就是说,生命的目的或意义不由其他事物所决定和控制,因为生命的意义是自由的。赫钦斯所理解的博雅教育的自由性也体现在教育的内容上,即:伟大的书籍。伟大的书籍包括讨论重要生命问题的伟大对话,通过阅读这些书籍,人们可以构建自己与书籍作者们的对话,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指导自己的行为。他相信,伟大的书籍是伟大的老师,它们每天都在告诉我们平凡的人们拥有着怎样的能力。这些书基于无知,探究人性,大多数都是写给普通人看的。赫钦斯将伟大的书籍作为进行博雅教育的唯一方式,对于职业教育是否可以作为博雅教育的方式抱有怀疑。他也认为这种博雅教育还有个额外的好处:实用性。因为接受过博雅教育的人有一种精神,能帮助他在所有领域都能表现出色。通过接受博雅教育,一个人的工作就实现了人文化,而经济独立只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手段。赫钦斯举了日本的例子,日本从一个小小的封建国家发展成了一个工业强国,但其经济发展并没有阻止它在世界大战中成为整个世界及其自身的威胁。他还强调,如果任何公共项目都不可能进行,如果每个人都应该接受的那种教育根本不存在,那么我们必须承认任何群体也不可能存在。每个人都是不同的,而每个人又都是相同的...... 西方需要一种教育,一种能够激发我们共同人性而不是强调个体的教育。这里赫钦斯提出了一个核心课程的概念,其基础理念是一个人应该首先学习如何做人,以及人类面对着诸如什么是美好人生、上帝是否存在等等这些共同问题。对赫钦斯来说,生活不仅仅关乎金钱,因为经济独立只是一种工具,生活关乎的是其意义。人类一直在追寻生命的意义,这也是我们需要博雅教育的原因。事实上,赫钦斯批判杜威太关注个体,前者认为年轻人的兴趣是不可靠的,在学校进行职业模拟永远不会像现实生活中的职业场景那样真实,因为人们只能参与到真实的社会和经济系统中才能真正了解这个系统。除了怀疑职业教育是否能切实帮助学生实现独立思考,赫钦斯还担心过分强调个体和兴趣会分散人们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部分大学及文理学院也认同赫钦斯关于博雅教育的理念,尝试着开设了博雅教育核心课程,例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Ursinus College为其所有一年级新生开设的名为《共同智慧体验》(Common Intellectual Experience)的必修研讨课已有18年之久,由人文系教育系以及其他各种不同专业的不同老师共同商议要求学生阅读的书籍,一起来上这门课,以阅读名著和研讨及论文形式为主,让学生思考各种人生与哲学问题,并鼓励学生在今后的生活和学习中也带着这种不断反思的习惯一路前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从根本上来说杜威与赫钦斯对于博雅教育的理解大不相同,这也体现了二者在把理论当做行动工具还是绝对真理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杜威认为博雅教育的人文属性在于强调教学过程和行为控制过程中的个体差异和兴趣,他试图通过劳动与博雅教育的结合来实现工作的人文化。赫钦斯则认为博雅教育的人文特质体现在教学内容上,即名著。他坚持他的人文理念,认为劳动只是通往美好生活的手段,人类需要博雅教育来持续构建与伟大书籍的对话,构建与他们自己的对话,以更好地理解生活和工作,过上苏格拉底所说的“反思的生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尽管两人的立论基础不同,但批判性思维和寻找人生意义是二者都关注和强调的要点。二者的教育理念对于中国的教育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杜威的“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教育理念在中国学校(尤其是中小学)已有渗透,而赫钦斯尊崇形而上学的理念也在中国生根发芽--中国有些幼儿园及中小学开设了儿童哲学课堂,孩子们通过哲学读本与绘本故事等各种方式共同寻找哲学问题的答案及人生的意义,大学也越来越重视学生批判思维的培养。在现代社会以及即将到来的科技大发展的人工智能时代,很多工作将被机器所取代,博雅教育对人的发展尤为重要,因此,笔者认为赫钦斯的观点更符合当前的时代背景,可以进行广泛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