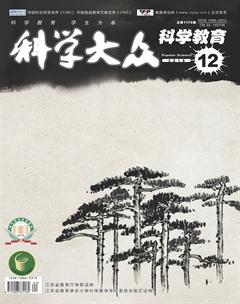符号互动论视域中的大学生网络暴力现象探析
陈希萌 吴彬

摘 要:基于2018年9月在浙江杭州下沙高教园区的问卷调查数据,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本文旨在分析大学生遭受网络暴力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个人特征、网络暴力认识程度、网络参与度是影响大学生网络暴力的重要因素(P<0.05)。个人特征中的年级与网络暴力呈现负相关,年级越高,遭受网络暴力的可能性越高;男性遭受网络暴力的可能性明显高于女性。网络参与度中的网络游戏与遭受网络暴力的可能性高度相关,参与网络游戏活动遭受网络暴力的可能性明显高于不参与的。
关键词:大学生; 网络暴力; 符号互动论; 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9)12-129-003
一、引言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统计,截至2018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8.02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8.3%,较2017年末提高了0.8个百分点,中国网民的人均周上网时长为27.7小时。网民以青少年、青年和中年群体为主,10-39岁群体占总体网民的70%,其中20-29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最高,达27.9%。①这些数据说明大学生是中国网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近些年来网络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其中涉及大学生的不在少数。随着互联网时代的不断发展,网络暴力情况日趋严峻,它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和发生。
那么什么是网络暴力?关于网络暴力的定义从知网的被引情况来看,学界比较认可的解释有姜方炳和陈秀丽。姜方炳从风险社会的视角认为,网络暴力是因交互行为致使当事人人格权益损失的网络失范行为[1],陈秀丽的关注点则在社会道德和自由意志方面,她认为网络暴力是出于维护社会道德的目的,通过心理压力进而导致生理压力,对被害人自由意志造成影响[2]。网络暴力在国外又被称为网络欺凌,传统的网络欺凌对象主要是中小学生,近些年来其范围开始扩展到高等教育中的学生。Tokunaga(2010)[3]将网络欺凌定义为几个或一群大学生通过数字或者网络媒体重复不停地进行语言攻击或发布恶意信息企图让他人感受到不舒服或伤害别人。Schenk和Fremouves将网络欺凌定义为通过E-mail、短信、社交软件、聊天室等进行的重复的、有目的的行為,伴随着伤害别人的企图[4]。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网络暴力的阐释都围绕以下几点进行展开:(1)行为人;(2)造成伤害;(3)伤害手段或途径。本文对大学生网络暴力的解释侧重点在造成的伤害,所以将大学生网络暴力定义为网络平台中的恶意行为对大学生的精神造成一定程度伤害,并且这种伤害短期内无法消除。并且根据恶意行为的影响程度来划分大学生网络暴力的等级,初级为对精神造成轻度伤害但没有波及大学生线下生活,中级为对精神造成中度伤害但影响学生的线下生活,高级为已造成行为大学生抑郁并且对大学生线下生活产生严重影响和干扰。
网络暴力归因方面有涉及到网民行为个性化和网络匿名性;网络社区不受限制性、网络参与者与家庭、社会互动关系;中国经济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网络技术固有的风险特性、网民群体年轻化的结构特点、泛道德化的文化心理[5-6]。
然而,现有的文献对网络暴力成因的研究大多从个人行为和网络平台等视角出发,对比国外相关研究,国内涉及到大学生这类群体的相对较少,研究大学生网络暴力与网络参与度之间的影响关系并且从符号互动论角度出发来分析成因的也是较少。因此,本文尝试通过符号互动论来解释大学生遭受网络暴力的影响因素。
二、数据来源说明
样本总体是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大学生,浙江杭州下沙高教园区,又称“下沙大学城”,是目前浙江省最大规模的高教园区。本次调查采用的是整群抽样,按照抽样方法,选取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中的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浙江传媒大学、浙江财经大学、浙江工商大学、中国计量学院等六所高校,每个学校抽取的样本数为30-40,抽样方式为简单随机抽样。本次调查主要为线下发送问卷的方式并且辅以问卷星作为线上补充。线下发放的问卷为220份,经过筛选最后得到的有效问卷185。线上收集到的问卷经过筛选后,得到的有效问卷量为22份。最终获得的有效问卷量为207份。
三、调查总体情况
(一)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参与本次调查的男生为84名,占比为40.6%,女生为123,占比为59.4%,一共207名。其中大一的30名、大二的44名、大三的97名、大四24名、研究生在读及以上的为12名。独生子女的为89名、非独生子女的118名。性格是偏安静型的为38名,偏活泼型的为23名,时安静时活泼的为146名。身边朋友或亲人经历过网络暴力的为42名,大约占了调查总体的五分之一(20.2%),身边朋友或亲人没有经历过网络暴力的为162名,占比为78.2%。最后所得的有效问卷有未填答部分,未填答部分在统计处理时设置为缺失值99,不影响整体的统计分析。
(二)影响大学生遭受网络暴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SPSS.20中的二元logistic模型对大学生遭受网络暴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采取的是向后条件分析,以是否有网络暴力经历为二分类应变量(没有过网络暴力经历为0,有过网络暴力经历为1),将年级、独生子女情况、性格、性别、有无网络暴力经历、是否注重网络个人隐私保护、是否喜欢关注网络热点话题、是否对网络暴力有了解、是否喜欢在网络空间发表看法观点、是否参与网络游戏等设为自变量,拟合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
由表1可知,性别、年级、独生子女、性格、关注网络热点话题、网络空间点评、朋友或亲人有网络暴力经历、参与网络游戏与网络暴力相关(P<0.05),网络个人隐私保护与网络暴力显示与网络暴力无关(P>0.05)。
(1)网络暴力认识程度:经常关注网络热点话题的为146名,没有经常关注微博热点话题的为61名。受过网络暴力影响的为42名,占比为20.3%,没有受过网络暴力影响的为152名,占比为73.4%。占比对网络暴力有所了解的为195名,对网络暴力不了解的为12名。
(2)网络参与度:喜欢在网络空间进行点评发表自我观点看法的为39名,不喜欢在网络空间进行点评发表自我观点看法的则是168名。经常参与网络游戏(包括手游)的为180名,不经常参与网络游戏(包括手游)的为27名。注重网络个人隐私保护的为182名,不注重网络隐私保护的为23名。有主动或被动施加过网络暴力的为28名,占比为13.5%,没有主动或被动施加过网络暴力的为177名,占比为85.5%。
四、符号互动论下的大学生网络暴力
(一)符号互动论简介
符号互动论创立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在60~70年代曾盛行一时,至今仍是具有很大影响力的社会学理论流派。米德是其理论的代表人物,为后续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符号互动论作为一种现代社会学理论,具有以下三个方面明显的理论特征:(1)重视人的主观(自我)因素,强调人既是客体又是主体(即自我的双重性);(2)重视对社会微观层次的研究,强调个人的特殊性,注重对个人之间的互动过程的研讨;(3)它重视对实际生活和互动的过程即所谓经验世界的考察,主张从生活经验中归纳出理论。[7]
(二)符号互动论视域中的大学生网络暴力原因分析
为什么个人特征、网络暴力认识状况以及网络参与度会与大学生网络暴力相关?下面本文从符号互动论的微观视角出发对这三个因素进行深入分析。
(1)个人特征——自我。自我概念是人们的主观意识的核心,但人们不是天生就具有自我概念,而是在于他人的互动过程中逐渐获得的[7]。个人特征来源于每个人的成长背景不同,从而与他人的互动不同,这就导致每个人对于自我的认识有区别。在不同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价值取向下,对事情的看法和处理态度不同。参与网络平台的人数众多,里面都是各个不相同的自我,这也就侧面体现出了网络平台的复杂性。不仅仅是人的复杂性,更是各种价值观点的复杂性,各种价值观点的相互碰撞,自然这就极易导致争论的发生,从而产生初级网络暴力。
(2)网络暴力认识——心智。米德认识到人类心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具有理解和运用象征符号的能力[7]。对于个体网络暴力认识的不同,也就从侧面体现出对于网络暴力符号的认识和理解不同。个体在网络平台中由于双发对彼此语言理解的误差,从而导致激烈语言攻击,形成网络暴力。米德将运用象征符号的过程称作想象性预演,通过想象性预演,个体得以调节和控制自己的行动,以谋求彼此间的最佳适应[7]。网络暴力的爆发正是彼此双方的错误想象性预演。
(3)网络参与度——“前台”和“后台”。前台和后台是戈夫曼拟剧论里面所涉及的要素,个体在特定时间内的表演,为观众展现一定的情境,须借助标准的,有规则的设置和道具,戈夫曼将表演的这一区域称为“前台”。“后台”是不让观众看到的,同时限制观众与局外人进入的舞台部分。后台通常与前台为邻,但彼此泾渭分明[7]。在后台中,因为一般不被人所见,所以后台中人们的表现是自我中的自我、最本质的部分,这里面可能有发泄情绪的过激言辞,不假思索地释放最原始的情绪。
网络参与度越高说明参与网络游戏、网络社交媒体的互动频次越高,而这个网络平台像是一个大的“舞台”,这个舞台和现实生活中舞台的区别在于网络的匿名性,这就导致了网络平台既可以是“前台”又可以“后台”,在网络暴力中,这个平台更多是承担了“后台”的功能。如果网络只是单纯地承担后台的作用那么还不会出现网络暴力事件,但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网络平台,它是新时代的传播媒介,能以极快的速度传播网络信息。网络参与者所认为的后台(如微博、朋友圈等网络展示平台)不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后台,因为个人在网络平台发表的任何内容都具有可见性和评论性。并且某个自我对于任意他人后台展示的内容的评价不仅带有个人主义,还掺杂情绪色彩。当个人在平台上发布的内容被他人所见并且他人持坚决的反对意见时,易出现双方彼此进行语言攻击的情况,这时初级网络暴力极易产生,当有更多第三方参与这场争论并且最后发展成全网知晓的情况时,这个过程中涉及的网络暴力程度其实也在不断上升。这种情况发生较多的是在兩个明星粉丝之间或路人与粉丝之间,而大学生群体中追星的群体不在少数,说明遭受此类网络暴力的大学生不在少数。并且在这种类型的网络暴力中,受害者不再是传统的单一个体,而是群体,只不过群体中每个人受到网络暴力的程度不同,因为每个受害者在这场争论过程中的参与度不同。网络平台对于明星而言是一个纯粹的前台。于他们而言,网络平台完全是营销自我和塑造粉丝理想形象的舞台,并且现在不少明星团队为了提高明星话题度和关注度刻意营造网络论战,这导致大量粉丝被动参与网络暴力而不自知。从某个方面来说,他们这种是故意营造和利用网络暴力为达自身目的的恶意行为。
五、结论与启示
由本次研究可见,大学生网络暴力是个人特征、网络暴力认识、网络参与度这三个因素相互融合的结果,三个因素间彼此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本文主要针对不同主体提出对应建议:大学生群体应减少花费在网络平台上面的社交、游戏、娱乐八卦的时间,多参加线下的活动,增强自己的社会联系;并且大学生应提高对于网络平台的认识,不随意将自己的隐私公布于此,提高个人的隐私保护意识;理性追星;不随意将个人情绪发泄于网络平台,避免成为网络暴力的施加者或受害者。高校可以尽量完善学生身心健康管理和处理方面的相关机制,关心遭受过网络暴力的学生,减轻网络暴力在他们身上产生的消极影响。网络平台应加强自身管理,政府可以完善相关网络法律法规,推行网络实名制,对于网络上的恶劣行为进行严厉监控和打击。
参考文献:
[1]姜方炳.“网络暴力”:概念、根源及其应对——基于风险社会的分析视角[J]浙江学刊,2011(6):181-187
[2]陈秀丽.网络暴力现象内涵及原因分析[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77-79
[3]Tokunaga R S. Following you home from school: A critical review and synthesis of research on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J].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2010,26(1):277-287
[4]Schenk A M,Fremouw W J. Prevalence, psychological impact, and coping of cyberbully victims among college students[J]Journal of School Violence, 2012,11(1):21-37
[5]刘艳.网络暴力问题的危害、成因及预防[D]浙江师范大学,2013
[6]陈海英,刘衍玲,崔文波.大学生网络暴力游戏与攻击行为的关系:暴力态度的中介作用[J]中国特殊教育,2012(8):79-84
[7]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
①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808/t20180820_70488.htm,2018-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