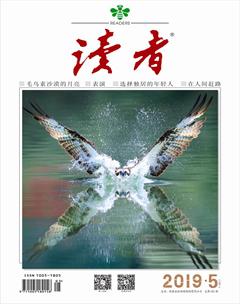塔楼里的 微光
2019-02-20 02:06祁文斌
读者 2019年5期
祁文斌

惯于“自省”的英国女作家伍尔夫在笔记中写道:“有一天,蒙田在巴勒杜克看到一幅勒内的自画像,便自问:‘既然他可以用蜡笔为自己画像,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鹅毛笔来写写自己呢?”当然,这只是伍尔夫想象的蒙田写随笔前的情景。
多年前,我的床头也放着一本《蒙田随笔》,节选本,不厚。后来才知道,全套的《蒙田随笔》有3卷,80来万字。印象中,16世纪的法国人文味很浓,所以,蒙田干了一件忒朴实的事儿:写自己的生活,所见、所历、所感,自自然然。也正因为如此,《蒙田随笔》很流行,至今长盛不衰。
蒙田从来不认为自己在“做学问”。不过,他还是在自己37岁那年继承了其父乡下的产业,一头扎进那座古堡圆塔三楼的藏书室。蒙田向往隱逸和宁静,他说:“我知道什么?”于是开始了对人生与世界的窥视和探询,蒙田的尝试尽管有过间断,但前前后后也持续了20多年。
在欧洲,蒙田无意中开创了“随笔”这一特殊的文体,随心所欲,娓娓而谈。后来,人们从培根、莎士比亚,还有卢梭的文字里都能看到蒙田的影子。读蒙田的随笔,人们面对的是一个朋友,而非“导师”。无疑,蒙田是谦和的,他的书中充满他对世事万物的体察以及对自然和生命的热爱。蒙田认知的核心不是怀疑或否定,而是对人与世界所怀有的最大的理解和宽容。孟德斯鸠说:“在大多数作品中,我看到了写书的人;而在这一本书中,我看到了一个思想者。”向来尖锐的尼采说:“这样一个人的存在使人倍感活在世上的欢欣。”
蒙田直到死去的时候,还一直说他不是真正的作家,只是个乡村绅士,冬天无事可做,才草草记下一些杂乱的思想。这思想的光,从那座古堡藏书室中微微散发,广博而悠长。
(大 浪摘自《今晚报》2018年12月18日)
猜你喜欢
阅读时代(2020年2期)2020-09-10
大众科学·上旬(2020年7期)2020-06-29
新民周刊(2019年21期)2019-06-05
作文周刊·小学二年级版(2018年36期)2018-01-02
中华家教(2017年12期)2017-12-15
校园英语·下旬(2017年7期)2017-07-14
爱你·健康读本(2016年7期)2016-02-11
读书(2015年3期)2015-09-10
小天使·二年级语数英综合(2015年2期)2015-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