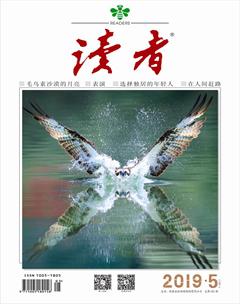毛乌素沙漠的月亮
陈忠实
朋友打电话来约我写一点有关月亮的记忆。话音未落,我的心底便有一轮又圆又大的满月缓缓浮现。这是我平生见过的最大的月亮,在毛乌素大沙漠的天空悬浮着,也沉浮在我的心底,整整25年了。
那是1985年的酷暑时节,由路遥挑头在陕北召开“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当时的情况是,新时期出现的一茬陕西青年作家,正热衷于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创作,尚无一部长篇小说出版,作协领导有点着急,便着手促进一下。会议的第二阶段聚会地由延安转移到毛乌素大沙漠中的塞北重镇——榆林,作家们的兴致更高涨了,纷纷表态要把长篇小说的创作列入最近的写作计划,“促进”促得会上会下的气氛十分热烈。挑头的路遥无疑很受鼓舞,顿时突发奇想,别出心裁地要搞一场篝火晚会,就在荒无人迹的毛乌素沙漠里。这在当时无疑是一场浪漫而又颇为新潮的晚会。
柴火是向当地乡民购买的,一捆一捆干燥的沙柳棒子,见到引火便蹿起火苗,得着沙漠夜风的鼓吹,火焰顿时腾起一丈多高,在刚刚降下的夜幕中映照出一片光亮的空间。与会的这一茬作家正值青壮年,又得着思想解放的时风的鼓舞,全都围着噼啪爆响的火堆几近疯狂地蹦跳起来,很难看到谁有规范的舞步,都是随心所欲地胡蹦乱跳,夹杂着平素很难发出的野性的狂呼和吼叫,把静谧的毛乌素沙漠吵翻天了。我也置身其中,蹦着跳着,有了难得的一次尽情放纵的生命狂欢。不料有人从背后抓住了我的胳膊,不容分说把我拉出狂欢的人窝儿,说,咱俩散散步去。依声音辨识,这是诗人子页。
我便随着子页走,几乎是漫无目的地无意识行走,却恰恰走在往北的沙地上。北边无疑是更为荒凉的沙漠腹地的方向。估摸不准走出多远了,篝火晚会的嘈杂的人声消失了,腾跃的火焰也看不见了,只有一片小小的略显红色的亮光标示着篝火晚会会场的方位。天上繁星点点,沙漠夜幕里仅有一丝微弱的亮色,我只能看见并排走着的子页的身形,完全看不清他的眉眼。凭着感觉判断,已经走得很远了,恰好脚下踩到了一道沙梁,两人不约而同停住脚步。他坐下来。我也坐下来。白天被晒得烫脚的沙子似乎还有余温。他说了些什么话,社会热点话题或文学写作什么的,认真的或不认真的,正经的或不正经的,现在竟通通忘记了,一句也没留下来。同样,我对他说了些什么话,也通通忘记了,一句都回忆不起来。我俩在沙梁上面对面坐着,此起彼落地聊着,仍然是谁也看不清谁的眉眼,依着说话的语调和口吻的缓急,感知对方的思想和情感。
无意间,我突然看清他脸的轮廓了,不由一惊,瞬间就意识到月亮出来了。他几乎同时轻轻地惊呼:“啊!多大的月亮!”我转过身,就看见沙漠尽头地天相接的地方,浮现一轮小碾盘那般大的月亮,惊得我一挺身站起来。子页也站起来了。
“多大的月亮。”我忍不住贊叹。
“没见过这么大的月亮。”他也随口赞叹。
“多大多圆哇。”我忍不住再说一句,便想到日子当在农历的六月十五或十六。
子页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诗人。我也算得一个作家。作为诗人的他和作为作家的我站在毛乌素沙漠里,面对初升的一轮满月,反复赞叹的词汇里,只有一个“大”字和一个“圆”字,竟然再反应不出一个更生动更美妙的字来。我们俩站在沙地上,看着那又圆又大的月亮缓缓浮升。沙漠里偶尔传来一声单调的野兽的叫声,我可以辨出是狐狸,在城市里长大的子页却以为是狼。月亮浮上天际大约有一竿子高,似乎渐渐缩小了一轮,却更明亮更清湛了。子页突然对我说:“我有一个提议——”却不说提议的内容。我也没有急着追问。只见他俯下身去,在月亮照亮的沙地上摸索,终于找到几根沙蒿秆儿,去枝叶,然后盯着我说:“面对毛乌素的满月,咱俩发誓——”说着便跪倒在沙地上,把三根蒿草秆儿双手举起,揖拜三下,插在沙地上,颇为郑重地发出誓言:“我对毛乌素沙漠的月亮起誓,和忠实老哥肝胆相照,永不背叛……”我看着他突如其来却甚为庄重的举动,虽然始料不及,却没有任何犹疑,随即便和他并排跪下,捡起三根替代香火的蒿草秆儿,照他的动作做起:双手握住蒿草秆儿,从胸前举起到眉心,反复者三,同样插在他插下的蒿草秆儿的一边,也信誓旦旦地对着毛乌素沙漠上空的月亮起誓,誓词自然和他的誓词保持一致。待我说完,俩人相应地转过脸来面对面瞅着对方,两双手便紧紧地握在一起,然后便四仰八叉躺倒在沙地上,纵声大笑起来……

有人吼叫我和子页的名字,我们俩当即应了声,料想篝火晚会要收场了,可我们似乎还留恋这一方静谧神奇的夏夜的沙漠,更有沙漠上空越升越高也愈加明亮的月亮。奔到我们面前的两位作家虚张声势:“还以为你俩被狼吃了呢!”我们都不在意地笑笑。有位作家颇认真地渲染说,沙漠里的狼可厉害了,常叼牧民的羊。子页随机应变,从沙地上捞起他和我插下的蒿草秆儿,说:“我们俩有金箍棒,什么样的恶狼都不怕……”
算不得结义,也算不得结拜,不过是面对沙漠上空一轮又圆又大的月亮,诗人子页诗性真情瞬间生发的举动。我之所以毫无犹疑地响应,有一个基本的感知,就是子页弃政从文的人生选择。他在新时期文艺复兴的热烈而又神圣的文学氛围里,辞去了给一位重要领导当秘书的工作,自愿调动到文艺圈子里来,在作家圈里曾引发长时间的议论。任谁都能想见,为一位重要的一把手当秘书多年,仕途上绝不会吃亏的;他却舍弃了,毅然投身到文学圈子里来,可见他对文学的痴迷和文学之于他的神圣。平心而论,我和他认识也有四五年了,但来往屈指可数,他热衷诗的创作,我学习写作的兴趣却在小说,文学大圈子里还有不同文学样式的几个小圈子。再说他住在西安城里,我住在白鹿原下的乡村,平素难得相遇。我对他最直接的印象,便是他舍弃官场投身文坛的举动。一个如此痴迷文学的同龄人,应该是可以信赖的……我便和他并排跪倒在毛乌素沙漠上,面对着那一轮又圆又大的月亮。
之后25年,淡淡如水,一年半载遇在一起,我看着他虽依旧浓密却大半花白的头发,他瞅着我光亮的秃顶,都先自笑了,竟然谁对谁都说不出一句客套的话,开口总是调侃。待喝了两盅之后,或他或我就会说起毛乌素沙漠里用蒿草秆儿做出对月起誓的事来,仿佛就在昨夜。可见毛乌素沙漠上空那一轮又圆又大的月亮,沉浮在我的心底,也在他的心底沉浮着。我便自然想到,如果谁有了或大或小的苟且之事,沉浮在心底的那一轮月亮,就再也不会浮现了。原本仅属于诗人子页兴之所至的一项提议,其实不无玩笑作趣的成分,现在倒感觉到一种人生中颇可珍重的情趣了。
(大浪淘沙摘自中国社会出版社《记忆》一书,李 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