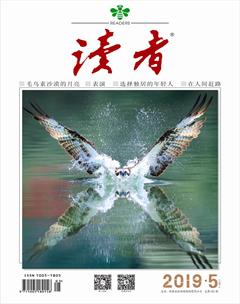表演
1
1986年,德国教授露特·梅尔辛来中国教我们表演课,课余我们带她吃烤鸭、涮羊肉、登长城,最后去看昆曲。看完昆曲以后她傻了,说中国原来有这么高级的表演。后来,她就找了当时北方昆曲剧院的蔡瑶铣老师学习昆曲。尽管学得很不好,但她一个60多岁的教授,还是很认真地去学,并且真的把学到的那些表演带到了课堂上。
她说,中国有这么好的表演,为什么在你们的话剧、戏剧舞台上看不见?

2
我演了这么多年戏,但说实话,我现在开始排斥在表演之前写人物小传。我们在家读剧本的时候,是一个人读所有的台词,是一个人读这个故事,你在用自己的理解去解读这段台词。但是跟你演对手戏的演员有他自己的生活经历,有他对社会的认知,他对台词的解读跟你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演员会在现场争论,原因就是对剧情的理解不一样。
在话剧《茶馆》里我演松二爷,每一场都必须说同样的台词。但如果你是一个热爱《茶馆》的观众,你从第一场开始看,等看到第100场,你会发现不是看了一出话剧,而是看了100出话剧。
《茶馆》的第599场,我印象特别深。第二幕开始,我在戏台的上场口,濮存昕在下场口,我们俩都准备上去。这时候一个报童跟王利发演完戏,往台下跑,只要他一跑下来,濮存昕就该上了。
结果他刚一跑下来,我们的布景墙“啪”就倒了。
所有人都急了,正好我这边有个舞台监督,我就赶紧和他说“关幕关幕”。当时饰演王利发的梁冠华一看墙倒了,马上接了句“打仗打仗,墙都倒了还打什么仗!”,当时他只能用这么一句话先自嘲一下。这时候幕关上,把墙扶起来后,再重新开始演这场戏。
这是什么?舞台事故。如果说有幸看了第599场《茶馆》的观众,看到这一幕,定格了。某年某月某一天,《茶馆》的第599场定格在二幕倒下的墙上,但是第598场和第600场墙都没倒。这就是戏剧,这就是戏剧的魅力。
如果你从《茶馆》上演第一年就看,到今年你再看,同样还是《茶馆》,这帮人走了20年,同样一个松二爷,同样一个王利发,同样一个常四爷,还是这些角色,但他们已经不是20年前的他们了。可如果你看我演的第一部电影《青春祭》,1984年拍的,到我死了,里面还是1984年的我。这就是电影、电视与戏剧的不同,各有各的魅力。就戏剧而论,你会发现20年前冯远征的表演是青涩的,20年后的冯远征对这个角色已经掌握得很纯熟。我不敢说最好,但是很纯熟。
3
有一个综艺节目叫《我就是演员》,其中有一段是演电影《1942》里的场景,两个演员在台上哭得一塌糊涂。看完以后我觉得演员都演得挺不错,评委也说得非常好,但是唯一的不足,我说他们在整个表演过程中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他们没饭吃。
什么是没饭吃?我们在拍《1942》的时候,有一天刘震云来探班,张国立见到他第一句话就是:“你给我写的词太多了,人在饥饿的状态下是不想说话的。”
刘震云一愣,想了一下,说:“我是在吃饱的时候写的。”
我再说两个实际的例子。拍戏的时候,为了进入角色,我们每个人都要减肥。我因为原本就瘦,减个五六斤后就看起来很瘦了。但是张国立和徐帆没我显瘦,他们俩其实已经减了十多斤了,但没办法,每天还必须饿着。
后来饿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开拍前,我旁边坐了一名工作人员,徐帆坐在我另一边。大家因为都在减肥,全部饿得没精打采。开始拍摄了,旁边的工作人员刚一起身,徐帆看了一眼,隔着我就爬了过去。我一愣,这怎么回事?结果发现,原来那人坐过的椅子上,有一个被压扁了的沙琪玛。徐帆当时饿得不行,都不管脏不脏了,捡起来就塞嘴里吃了。
也是在拍摄现场,有一次张国立站我旁边,我们俩都在等开拍,我回头抿了一下嘴。张国立马上问我:“你吃什么呢?”我说我什么都没吃啊,他说:“不对,我看你腮帮子在动呢!”其实我当时真的什么都没吃,只是抿了一下嘴,但人在饥饿的状态下就是会有这样的表现。
《1942》里有一场我卖孩子的戏,我带着人贩子把孩子从窝棚里拖出来,要带走的时候,徐帆发现了,就跑出来抢。拍这场戏的时候,徐帆特别用力,结果当时导演冯小刚就说,你不能这么演,你饿了多长时间了,你有那么大力氣吗?你最大的力气就是豁出命去把孩子拽过来扔窝棚里头,接着睡觉。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导演对角色的判断,对演员表演的判断。
所以,怎样才能让自己的表演有生命力?我觉得首先要调动起自己的本能。在《1942》里,生理上的直接反应,就是有生命力的表演。
表演,表在前,演在后。我们要用自己的身体,通过表象的东西,来演出内在的情感。
4
在拍摄《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时候,有一天张建栋导演突然和我商量说,他觉得安嘉和这个人物不能光是这一面,还得有好的一面。我说我也这么想,包括在医院对病人、在家对老人,这个人一定要好得不能再好。有了这个认知以后,这个人物的反差就有了。

说实话,在很多场戏里,我没有认为安嘉和是一个坏人,包括他救强奸过梅湘南的那个人。如果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这是个坏人,是强奸过我媳妇的人,我会恨不得杀了他。但我当时在手术台上,就是用一种很平静的眼神看他。因为安嘉和首先是一个医生,他有救人的天职,如果他当时想要杀了这个坏人,我认为缺少真实性。
我们绝大部分演员在演行业戏的时候,忽略了一样东西——职业特性。
如果你不信,咱们去医院观察医生和护士,刚上岗的和上了一年、十年、二十年班的都不一样,对病人的态度也不一样。但绝大部分演员在演这类戏的时候,永远演的是刚上岗的状态。
就像我有一次演警察,那是很多年前我刚回国时接的一个戏,在西城区丰盛胡同里面拍。当时我们几个去了以后觉得自己特别牛,双手插兜在胡同里走来走去。后来我们的顾问就说,冯远征你这不像警察,我们警察在工作的时候从来不会双手插兜,因为这样跟居民在一起是不礼貌的。所以从那以后我再演这一类戏,手永远不会插兜。
演员塑造人物,性格化、细节刻画,是基础。好的人物塑造能让你忘记那是在表演,让你相信他就是那个人物。
5
我在德国上学的时候27岁,班里都是20岁左右的小孩,在跟他们做表演训练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技术是最好的,但想象力是最差的。
所以我和表演系的一位老师说,我们做老师的永远不要给学生做示范,你要逼他,让他自己想,挖掘他的潜能。每一个演员都有自己的社会背景和阅历,做老师的绝对要一对一,而不是用一个方法对待所有人。
有一个著名的荒诞派戏剧叫《等待戈多》。这个戏刚诞生的时候,很多专家和观众都在批判。结果这个剧组带着戏到监狱里去演,犯人们看得鼓掌欢呼。为什么?不要忘记,这个戏的名字叫《等待戈多》,创作者就是想让你跟他一起等,而犯人们每天都在等。
这个戏很多人都觉得看不懂,不知道台词在说什么,可恰恰如果你把每个人物的台词单独拿出来,你会发现每个人的形象都是很完整的。这是因为大家即便处在同一个时空,每个人所思考的内容却是各自独立的。
6
一个岁数很大的人,在见到自己失散多年的亲人时,第一反应是什么?大多数演员几乎都是哭。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现实生活,绝大部分人并不是这样的。
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2005年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在北京人艺演《茶馆》,演完后我给家里打电话,是我爱人接的。电话一拨通,我心里咯噔一下。因为我爱人平时都在医院照顾我父亲,不在家里。所以电话接通的一瞬间,我就觉得出事了。我说你告诉我爸是不是走了?她说是,说要开车来接我。
我说你干吗要接我,我自己能开车。当时我心里没有丝毫的感觉,但是电话放下的一瞬间,我的眼泪就开始流。那会儿我们还在剧院后台,吴刚在我对面,一看到我哭,就回头说:“远征,你怎么了?”我说我爸走了,他说你赶紧回去,我说不行,还得谢幕,他说你谢什么幕,赶紧去。
那是我进人艺以来唯一一次没有谢幕。当时我就想,回家的路上会不会痛哭流涕,会不会开不了车,我先想了一下,感觉自己可以开车回去。到医院的时候,我父亲已经被送进了停尸房。进去以后,看到里面的工作人员在做面条吃,当时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后来回头想,这只是别人的工作,无可厚非。
进去之前,我爱人说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因为父亲生前插过管子,可能样子会不太好看。但我觉得我父亲特别善良,对我特别好。当我拉开抽屉看到他的时候,他就像睡着了一样,没有任何狰狞的表情。我看着父亲,就在心里说:“爸,我在演出,没来得及回来,剧场有一千个观众在等着,希望你能够原谅我。”心里想到这的时候,眼泪就开始往下流,我又怕掉到他臉上,只能不停地用手擦。我当时想了半天,唯一能做的就是伸出手摸了摸他的脸。他的脸还没有完全凉下来,还有温度。然后我低头亲了一下他的脸颊,把抽屉合上了。
对我自己来说,如果下次碰到这样的戏,我就知道应该怎样去演。但一个没有经历过的演员,他一定会先哭。当一个演员塑造角色的时候,真的应该从生活中去观察很多东西,再放到自己的表演当中。
在说上面这番话的时候,我没有哭,是因为我父亲去世已经十多年了。但如果在我父亲去世一两个月之内,我提起来,就会流眼泪甚至是哽咽,因为时间离得太近了。我记得在录《艺术人生》节目时,说到这里我已经泣不成声了。
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当很多年以后,你再想起一件事时就已经不会是当时的那种状态了。比如说你刚刚失恋,可能会哭,会痛苦,但是十几年以后再碰到这个恋人,尽管两个人还有情愫,你还会哭吗?所以不要脱离现实,去臆造表演,让观众误以为那就是生活。
(田宇轩摘自微信公众号“四味毒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