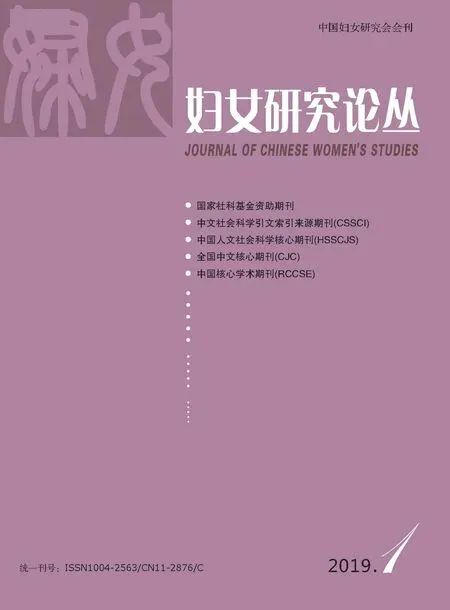城乡流动与农民工家庭变迁
——评《男性气质妥协:中国的农民工流动、家庭与性别》
王 欧 王天夫
(1.2.清华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084)
一、引言:城乡长期流动与农民工家庭变迁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打工劳动力的主体,其城乡流动模式已发生转变,改革早期(改革开放开始至21世纪初)的单身工人婚前短暂流动和婚后以男工为主的循环流动已转变为农民工家庭或夫妻的长期流动[注]新城乡流动模式具体表现为女性生育后很快外出打工,流动儿童的数量快速增长,留守儿童完成基本教育后迅速加入打工队伍,一些留守老人甚至在完成孙辈抚育后继续外出打工。,农村“空心化”和流动人口“常住化”已成为一种普遍趋势[1](PP 31-37)。新的城乡流动模式导致了一系列新的劳工问题(如新生代农民工的“增长型诉求”[2]和新抗争方式[3]、老一辈农民工追讨社保的行动[4]等),冲击了旧的农民工家庭结构。
已有研究敏锐地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和夫妻共同流动的趋势更强[5],更加难以忍受夫妻或亲子分居的“拆分型”家庭模式[6]。不过对城乡长期流动可能导致的农民工家庭的复杂变迁,既有研究多停留在家庭构成变化(如各类家庭比例[5])的描述层次,少数研究捕捉到某些家庭关系的变化(如“个体化”家庭理想的出现[7]),鲜有研究深入考察流动家庭内部关系的建构过程,更缺乏性别视角的分析;另一些研究虽从性别视角切入流动家庭内部,展现了早期城乡流动对某些家庭关系变迁的影响(如家庭再生产对女工的不利影响[8]和“流动的父权制”的建构过程[9]),却未系统考察新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家庭变迁的影响,尤其缺乏对男工经验的关注[10]。
香港学者蔡玉萍、彭铟旎的新著《男性气质妥协:中国的农民工迁移、家庭与性别》(以下简称《男性气质妥协》)一书基于珠三角三个城市的最新(2007-2015年)田野调查材料,以男工经验[注]该书共访谈了191位流动男工,平均年龄为36岁,71%为已婚,家庭和夫妻共同流动的比例为42.2%,从事的职业包括出租车司机(24.6%)、建筑工(23%)、保安(18.8%)、工厂工人(9.9%)、餐饮和宾馆服务员(9.9%)、白领(6.8%)及其他。和性别视角切入农民工家庭内部,通过男性气质妥协(masculine compromise)这一核心概念,呈现了农民工家庭变迁的复杂过程和不同家庭之间的差异,推进了新城乡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家庭变迁影响的研究[1]。
本文首先梳理出一个潜藏在该书论证逻辑之中的分析框架,并据此呈现其主要研究发现,接着将该研究发现放入国内农民工家庭研究的文献脉络之中,阐明该书的主要研究贡献,最后指出由该书引出的一个有待深入的研究问题。
二、男性气质妥协:城乡长期流动引起农民工家庭变迁的关键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男工与女工之间的性别关系一直是塑造农民工家庭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早期,单身工人流动很快被婚后以男工为主的循环流动替代[1](P 31),男女之间的性别关系由“流动的父权制”形塑[9],“拆分型”家庭是农民工家庭的主导模式[11]。进入21世纪之后,新的城乡流动模式(尤其是新生代女工婚后继续流动)打开了新的性别关系建构空间,为重构农民工家庭关系提供了动力。
《男性气质妥协》一书正是在新的城乡流动背景下,以既有研究很少关注的男工经验为对象,通过新的男性气质性别视角切入农民工家庭内部,考察农民工家庭关系的建构过程。该书发现,由于新城乡流动模式既让男工受到城市社会(如城市工作与消费)的强烈影响,又将其置于城市的边缘位置,迫使他们保持与流出地社会的关联[1](PP 36-37),因此一种新的性别关系建构形式,即不同方式和程度的男性气质妥协,就成为农民工家庭关系变迁的关键机制[1](PP 151-154)。该书据此组织全书各章内容并展开分析和论述,其中潜藏在书中的分析框架见图1。[注]由于该书并未明晰城乡流动模式与特定男性气质妥协之间的关联机制,图1用虚线表明二者之间的松散关系。本文第四部分将讨论二者之间可能的关联机制。

图1 《男性气质妥协》的潜在分析框架③
作为两位作者提出的最重要的分析性概念,男性气质妥协是指流动男工一方面携带并坚持农村社会的父权制家庭传统(如父系、从夫居、男性对女性的权力和男性的养家者责任等),另一方面又必须在新的城乡流动处境下做出不同方式和程度的协商、调适或让步,由此建构出一系列新旧杂糅、形式各异的流动家庭关系[1](PP 151-153)。具体而言,在恋爱阶段,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出以城市消费为基础的浪漫爱情和婚前性关系,但男工的边缘经济地位却不断侵蚀其物质根基,使该平等化的浪漫关系无法稳定,一部分男工不得不在城市浪漫爱情与农村父母压力之间妥协,甚至接受缺乏浪漫爱情基础的“现代式安排婚姻”(即由父母牵线、子女认可的介绍型婚姻)[1](PP 61-65)。在该书访谈的59个35岁以下的已婚男工中,只有6个找了跨省妻子;许多未婚男工表示,在尝试了城市浪漫关系(urban romance)之后,他们最终也会找本地妻子(local wife)[1](P 62)。由此可见城市的边缘处境和农村的父母压力对新生代男工的强烈影响,他们中的大部分不得不在浪漫爱情和结婚成家之间作出艰难妥协。
结婚成家之后,流动男工在父系和从夫居这两根父权制家庭的支柱上绝少妥协,一部分男工仍然很少参与或策略性地躲避家务劳动,一些深受城市消费主义影响的男工在家庭经济权力方面也很少让步[注]书中论及的男工的消费欲望包括参与吃饭喝酒、K歌和出入洗浴中心等。,甚至不惜为此对妻子施暴[1](PP 84-85,P 103)。与此同时,另一种情况是男工大多赞成妻子继续打工,其中一部分还主动承担越来越多的家务劳动,并向妻子让渡管理家庭经济的权力,促使夫妻关系向平等化方向发展[1](PP 79-81,PP 96-100)。在书中呈现的案例中,几乎所有男工都反对妻子婚后继续对原生家庭进行经济支持,也反对在靠近女方家的地区购房或居住,他们十分看不起上门女婿,甚至不惜以离婚来捍卫父系和从父居原则[1](PP 76-78)。尽管绝大多数(约80%)男工认为他们才是主要养家者,但是迫于经济压力,他们中的多数也同意女性以放弃照顾子女为代价到城市打工挣钱[1](PP 79-80)。与这种一致性相对的是,男工在让渡家庭经济权力[注]该书并未提供以不同方式让渡家庭经济权力的男工比例。和参与家务劳动方面出现了巨大分化,其中有44%与妻子或家庭共同流动的男工承担了一半或以上的家务劳动[1](PP 96-97)。
在家庭代际关系方面,打工增强了男工履行传统养家父职(breadwinning fatherhood)的能力,却剥夺了他们通过日常相处管教留守子女的可能性,并造成严重的情感创伤(emotional turmoil),男工们只能转而通过物质补偿、电话沟通等不得已的妥协方式履行父职[1](PP 122-123)。与此同时,男工对留守老人的照料依然秉持强烈的传统孝道观念,但低经济收入和沉重的下一代抚养义务,迫使他们向其他替代性照料实践(如远距离的电话照料)妥协,甚至不得不一再压缩老年父母的照料需求,直到其生命最后阶段才提供危机照料(crisis care)[1](P 144)。不过,该书并未详细论及携子女流动与让子女留守的父职妥协差异[注]该书仅在论述让子女留守的父职妥协部分的最后简要提及携子女流动的父职情况。,也未涉及不同子女照料模式下可能存在的与老一辈父母的代际关系差异。
因此,正是通过上述不同方式和程度的男性气质妥协,新城乡流动模式促成了农民工家庭关系的一系列变迁,也形成了不同农民工家庭之间的差异。
三、研究的推进:揭示家庭的性别化过程和家庭关系差异
上述研究发现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推进了新城乡流动模式下的农民工家庭研究。
首先,该书切入农民工家庭的角度非常新颖,通过丰富的男工经验材料和独特的男性气质性别视角,揭示了农民工家庭关系的性别化建构过程。之前的研究多基于人口统计资料,呈现新城乡流动模式导致的农民工家庭构成的变化,如新生代农民工婚姻模式(婚龄、通婚圈、婚前同居等方面)的“现代”转型[12]、家庭和夫妻共同流动比例的增长[5]。一些研究者还通过量化统计模型,发现一系列影响农民工家庭流动比例变化的因素(如城市户籍与公共服务、人力资本、家庭资源)[5]。这些研究勾勒出农民工家庭构成的新状况,但特定家庭构成的出现、维持和转变是要以特定的家庭关系建构为中介的。《男性气质妥协》一书正是以新的经验材料和性别视角深入既有家庭构成研究未能触及的领域,呈现了农民工家庭关系复杂的性别化建构过程,推进了既有研究。
其次,该书呈现了男性气质妥协方式和程度的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农民工家庭关系的差异,纠正了当前对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研究的“片段式”观点。
在既有家庭构成研究之外,目前仅有少量研究考察了新城乡流动模式对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影响,其研究结论往往指向旧农民工家庭的彻底转型。与改革开放早期强调“流动的父权制”[9]和“拆分型”家庭[11]盛行、单身女工的婚恋受父权制压迫[13]和家庭再生产(如生育、抚育和赡养老人)将女工置于父权制的控制之下[8]不同,最近的一些研究认为,在新城乡流动模式下,新生代农民工的浪漫爱情经历已十分普遍[14],“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倾向非常明显,对“个体化”新家庭理想的追求甚至已清除了父权制的影响,他们不再愿意为了集体的利益和扩展家庭的延绵不绝而牺牲自己,转而通过家庭的运作来寻求自己的利益与快乐[7](PP 9-10)。与此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啃老”的现象十分普遍,他们(尤其是女工)在婚姻、购房、子女抚育和其他日常开支方面“代际剥削”父母一辈[15],而小家庭一旦实现城市化流动便很少与留守父母联系,后者的养老需求被一再压缩,导致代际交换的工具理性化、孝道式微和较为严重的伦理危机[16]。
《男性气质妥协》一书的研究结论表明,以往对新流动模式下农民工家庭变迁的观察是“片段式”的,即只捕捉到家庭生活的某些片段或家庭关系的某一层面,而实际的家庭变迁过程更加复杂,不同农民工家庭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在婚恋关系方面,新城乡流动模式的确为新生代农民工普遍经历浪漫爱情提供了社会空间,却在经济条件上不断侵蚀其存在的消费基础,使得浪漫关系极不稳定;在向婚姻转型时,该浪漫关系还面临农村父母的压力,甚至导致缺乏浪漫爱情基础的“现代式安排婚姻”[1](PP 64-65)。在夫妻经济权力方面,一些男工的确表现出强烈的个体化社交和消费倾向,甚至不惜为此对妻子施暴,但多数男工出于家庭再生产的重负主动向妻子让渡或与妻子协商家庭经济管理权,且鲜有男工在父权制的支柱(即父系和从父居)上妥协[1](PP 79-84)。在家庭性别劳动分工方面,一部分流动家庭的确已向平等化的性别关系转型,其中的男工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家务和子女看护劳动,有一些甚至为了兼顾家庭照料而接受较妻子更低薪的工作,但另一部分男工却坚持“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模式,可以完全免除或设法逃避家务劳动[1](P 144)。在与老一辈父母的代际关系方面,新流动模式的确强化了“子代优先”伦理并加剧了代际间的严重不平等,老一辈父母在各项家庭再生产事业上一再付出,从打工子代得到的回报却越来越少,但流动男工仍持有强烈的传统孝道伦理,并为无法对父母尽孝深感愧疚,还发展出一套替代性的照料实践(如电话、合作或危机照料)[1](PP 132-137)。
因此,新城乡流动模式导致的农民工家庭变迁,不仅包括既有研究已观察到的浪漫爱情、“个体化”家庭理想和不平等的代际关系,还有其他被“片段式”家庭研究忽略的丰富面向。《男性气质妥协》一书正是通过由书名“点睛”出来的关键机制,呈现新城乡流动模式下农民工家庭的复杂变迁过程和新旧杂糅、形态各异的变迁结果,推进了对农民工家庭变迁的理解。
四、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解释农民工家庭的性别化机制和家庭关系差异
男性气质妥协是一个分析农民工家庭变迁过程的重要概念,那么解释不同的妥协方式和程度以及由此造成的家庭差异就成为一个迫切问题。
实际上,《男性气质妥协》一书最有洞见和分析最精彩的地方之一,就是发现了男性气质妥协的方式和程度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该书已详细论述的夫妻经济权力[1](PP 80-84)和家庭性别劳动分工[1](PP 92-100)方面,还存在于该书没有充分展开的浪漫关系向婚姻家庭转型[1](PP 61-64)、携子女流动和让子女留守的父职(fatherhood)[1](PP 122-123)以及对老一辈父母的照料[1](PP 132-137)方面。
对于男性气质妥协方式和程度的差异,该书已给出了一些尝试性回答。一方面,该书指出了流动男工在城乡之间的矛盾处境,另一方面试图对某些男性气质妥协方式作出微观说明。例如,在解释男工参与家务劳动的不同模式时,作者列出了“丈夫对妻子的收入比例、夫妻的相对可支配时间、子女的年龄和男工的男性气质观念”四个因素,并特别强调男工建构的“家庭取向的男性气质话语”对他们主动承担家务劳动的影响[1](PP 103-104)。同样,在解释夫妻管理家庭经济权力的差异时,作者认为年纪大的男工更倾向于向妻子让渡家庭经济权力,挣钱比妻子更少的男工则绝不妥协[1](P 85)。
在笔者看来,书中给出的解释尚不足以充分说明在既定的城乡流动模式下,不同的男工为何会出现男性气质妥协方式和程度的差异。结合其他流动家庭研究视角,尤其是注重农民工家庭的工作与生活组织方式,可以丰富对男性气质妥协差异和家庭关系差异的解释。
实际上,跨国移民家庭研究的一个主要范式是将流入地社会的宏观结构条件(如移民政策、劳动力市场结构)与移民家庭的微观处境紧密结合,通过梳理男工和女工在流入地的工作机会和生活方式,解释特定的性别化机制和家庭关系的出现[17](P 141)。例如,北美的后工业劳动力市场通常为流动女工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如护工、家政工等工作),却将流动男工置于待遇低的“不稳定工作”位置,由此导致家庭性别关系向平等化方向发展。但这些流动工人常常生活在传统浓厚的移民社区之中,流动男工妥协的程度极为有限,女工在家庭关系中仍处于弱势地位[17](PP 141-144)。同样,散落在《男性气质妥协》中的经验材料也说明男工和女工的工作与生活组织方式在解释特定的男性气质妥协方式和家庭关系的重要性:书中那些“主动参与”(active participation)家务劳动的男工,几乎无一不以妻子的更长时间或更高收入的工作(如工厂工作)为前提,而他们自身的工作往往收入更低(如工厂保安)或时间更有弹性(如出租车司机)[1](PP 96-100)。与此同时,那些在个人经济花费方面很少或绝不向妻子妥协的男工,多数在打工地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消费与生活方式,包括与其他男工一起吃饭喝酒或出入KTV等社交场所等[1](PP 82-84)。
因此,在既定的城乡流动模式下,注重农民工家庭的工作与生活组织方式,有助于进一步深入解释不同的男性气质妥协方式和家庭关系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男性气质妥协》一书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亟待未来专门的研究作出回答。
五、结论
本文将《男性气质妥协》一书置于农民工家庭研究的文献脉络之下,通过一个潜藏在该书论证逻辑中的分析框架呈现其主要研究发现,并指出该研究发现对推进既有研究的两个主要贡献和一个亟待深入的研究问题。本文认为,该书最有洞见和论证最为精彩的发现,是揭示出新城乡流动模式通过不同方式和程度的男性气质妥协机制,导致了农民工家庭的一系列复杂变迁和不同家庭之间的差异。这一研究发现促使既有研究从家庭构成描述向家庭关系建构过程分析深入,以及从“片段式”的家庭生活观察向呈现家庭变迁的复杂过程和结果差异转型。该书还引出了如何解释持续存在的农民工家庭性别化机制差异和家庭关系差异问题,结合其他流动家庭研究视角(尤其是注重家庭的工作与生活组织方式),有助于丰富对该问题的解释。
在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打工劳动力的主体、家庭化流动趋势日益明显和“流动人口不流动”[18]的新城乡流动模式下,农民工家庭变迁是一个与其他新劳工问题同样重要却远未得到应有重视的新议题,亟需引起更多关注和更充分的研究。《男性气质妥协》一书正是在此背景下,用最新的田野材料和独特的性别分析视角,推进了既有研究对农民工家庭变迁的理解,并指向了一个更具潜力的研究议题。该书在呈现新流动模式下的家庭关系变迁时,各章不仅在分析论证上层层深入、逻辑严密,而且在引用质性材料佐证研究论点方面丰富饱满、甚见功力,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田野工作的深入、对农民工家庭处境的同情和对性别平等的期待。但是学术著作中这些难能可贵的人文关怀并未影响作者的审慎分析,在该书的最后,两位作者写道:“特定的男性气质妥协是实用主义的产物,而非文化价值上的彻底转型……当促使男工妥协的条件消失时,性别关系将可能重新变得传统和保守。”[1](P 154)因此,进一步的研究不仅要敏锐地洞察农民工家庭内性别关系的平等化趋势,而且要明确促使其出现的结构条件和机制过程,同时对其他性别化机制和家庭关系保持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