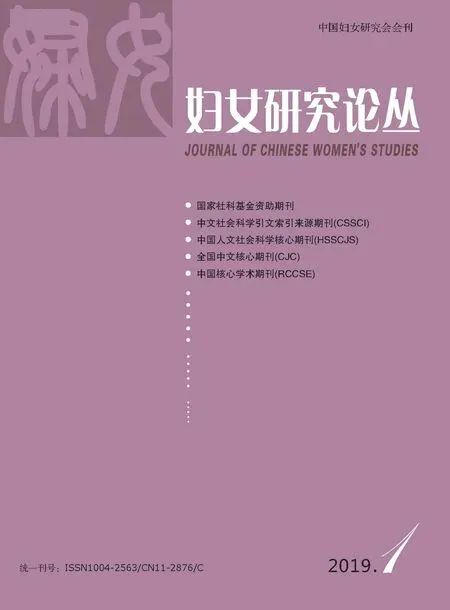对贫困决定因素的性别比较研究*
——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城乡非农业人口的实证分析
肖 萌 丁 华 李飞跃
(1.天津师范大学 应用社会学系,天津 300387;2.北京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北京 100871;3.南开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系,天津 300071)
女性贫困问题在中国由来已久。全国妇联连续三期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2000年中国城镇低收入的女性比例已高出男性19.3个百分点,2010年该比例进一步增至19.6%。女性与男性在从业率上的差距亦从1990年的13.9%增至2000年的17.8%,并在2010年扩大到19.7%[1]=[2]。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虽然对女性绝对收入的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女性相对于男性所面临的贫困、失业等风险则在持续增大。而就中国现有的女性贫困研究来看,其大多停留在定性与理论论述层面,在少量的定量研究中则存在着性别比较视角缺失、贫困概念体系单一等问题。这些研究局限造成国内学界对中国女性贫困程度与成因认知的模糊,进而影响了具有性别意识的反贫困战略的发展。为此,本研究旨在以定量方法为基础,在更多元的贫困概念体系下构筑性别比较分析框架,探究女性贫困的独特因素及更为精准的女性贫困治理机制。
一、文献回顾
西方学界对女性贫困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个体、家庭、劳动力市场、性别观念几种基本视角。个体视域下的女性贫困研究主要关注个人的人力资本禀赋对女性贫困风险的影响。无论女性相比于男性较低的受教育水平,是源于父代对子代男孩教育投资的偏好,还是夫妻对家庭产出最大化理性计算后的投资决策结果[注]该理论认为家庭中两性不同的劳动分工,是两性对各自投资的成本收益进行权衡比较后,而进行的理性家庭投资组合决策。出于收益最大化的理性原则,男性选择对个人职业发展有益的人力资本进行更多投资,而女性则优先考虑在家庭/家务活动中进行投入(Blau,F.,et al.,The Economics of Women,Men and Work,New Jersey:Pearson Prentice Hall,2006;Ehrenberg,R.and Smith,R.,Modern Labor Economics:Theory and Public Policy,Person Addison Wesley,2006)。[3]=[4],女性在人力资本投入(包括教育、职业培训和专业经验)方面相对不足的现实都造成其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的弱势地位,使其面临更高的贫困风险[5]。库马尔(Abhishek Kumar)认为,受教育水平除了通过就业直接影响贫困,还会通过子女数量和卫生保健而间接作用于贫困[6]。
婚姻家庭视角强调不同婚姻家庭类型中的女性角色地位以及女性在家庭生命周期中的生存状态对女性贫困的影响。关于婚姻对女性贫困的影响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离婚率不断上升、婚外生育增多、女户主家庭大量涌现的社会背景下,皮尔斯(Pearce D.)最早提出了“贫困女性化”概念[7]。此后大量研究都表明,女户主家庭中的女性由于需要同时扮演养家者和家务劳动提供者的双重角色,常常难以获取家庭正常生活所需的经济资源,从而面临较高的贫困风险[8]。子女出生及抚育这一重要的家庭生命周期过程,也是家庭视域下的女性贫困研究要点。塞恩斯伯里(Sainsbury,D.)的研究显示,未成年人的人口数量会对女性的贫困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9]。斯蒂文(Steven Pressman)发现,对于单亲母亲而言,其子女数量越多、子女年龄越小,其从事短期、兼职性质的工作的可能性就越大[10]。
劳动力市场视角关注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水平和参与形式对其贫困程度的影响。伴随经济的发展,女性的劳动参与意愿与劳动参与率与先前相比已有了很大的提高,但相对于男性来讲,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依然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11]。芬诺夫(Finnoff,K.)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就业者集中于非正规部门就业,这是女性容易陷入贫困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原因[12]。霍瑞斯等(Horrace,W.C.& Oaxaca,R.L.)基于对东南亚地区劳动力市场的观察发现,即便女性可以进入正规就业领域,女性的工资收入也要显著低于男性[13]。
性别观念视角强调文化、行为规范等因素对女性贫困的独立影响作用。巴斯图斯等(Bastos A.,Casaca S.F.,Nunes F.,et al.)研究者认为,不应将女性承担更多家庭无偿劳动等家庭内部不平等的性别分工单纯归因于前述个体视角中提及的“家庭理性投资策略”,也不能将工作场域中所存在的职业隔离与性别工资差距简单归咎于女性受教育水平不足[14]。诸多研究显示,在控制教育水平变量的情况下,女性的失业风险和非正规就业可能还是显著高于男性[15],正说明了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观念及性别歧视仍渗透于工作场域,限制着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平等参与[16]。此外,还有不少研究者提出,一个社会经济平等性的总体增进,并不能确保性别平等的同步提升[17]=[18]。正如贝司麦克等(Bussemaker,J.,Kersbergen,K.V.)的研究所示,很多西方福利国家虽已有效降低了总贫困率,取得了国家内部的经济平等,但依然维持着传统的男性养家者的性别角色和低妇女劳动力市场参与率[19],表明女性贫困及贫困女性化问题的产生,有着不同于男性贫困的复杂独特的文化影响机制[20]。
对于中国女性贫困问题的发生机制,国内学界大多是基于定性研究方法展开讨论,既有结论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人力资本不足是女性贫困的主因[21];妇科病及性传播疾病的增多加大了女性健康贫困的风险[22]=[23]=[24];单亲家庭救助制度缺位是离婚妇女贫困的重要原因[25]=[26];性别歧视及劳动力市场权益缺失增加了妇女的失业贫困风险[27]=[28],性别平等意识与发展意识不足增大了女性脱贫的难度[29]=[30]=[31]=[32]。此外,还有少部分研究者运用定量方法对女性贫困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如王增文[33]、张晓颖[34]对老年女性和流动妇女贫困成因的分析,及陈银娥[35]对女性总体的贫困影响因素的讨论。
总体来看,关于中国女性贫困的研究还主要局限于定性研究层面,而既有的定量研究则仍存在两方面的研究不足:首先,现有研究对贫困的测量单一沿用主流贫困测量方法,即以贫困线或最低生活保障线为标准,以“家庭”或“户”为收入测量单位,将所有家庭人均收入低于贫困线或低保线的人口,不论其性别、年龄、个人可支配收入数量,都统一确定为贫困人口。这种以家户为单位的贫困测量方法具有一定局限性,其假定家庭收入是在家庭成员间平均分配的,从而忽视了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差异。事实上,大量西方研究发现,一个根据家庭人均收入测量方法被定义为非贫困的家庭,其中的某些家庭成员特别是妇女和儿童,仍有可能面临严重的贫困问题[36]=[37]=[38]。中国亦有类似的实证研究发现,即家庭内部基本生活资源的消费存在性别等级之分,且表现为女性弱势[39]。其次,既有研究虽然在理论层面上都认同女性贫困问题的特殊性,但是在实证研究设计中,均只对女性的贫困成因进行独立分析,未能将男性同时纳入分析框架。这种研究设计虽然可以展现女性贫困的决定因素,但是无法清晰地揭示男女两性贫困发生机制的差异性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由此给出的反贫困政策建议亦难以准确映射“社会性别意识”。
基于上述研究不足,本文尝试从两方面推进中国的女性贫困研究。首先,在贫困的测度上,除了遵循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贫困测量手段——以家庭人均收入低于贫困线为内涵的贫困测量法之外,本研究还将以个人可支配收入低于贫困线为标准,对个体的收入状况进行测量,从而更清晰地揭示个人从劳动力市场中获得基本生存资源的独立能力。我们认为,对于拥有劳动力市场参与意愿(本研究不纳入自愿失业样本)但缺乏就业机会,或就业参与水平较低乃至难以从市场中获得高于贫困标准的物质资料的个人而言,即便其有可能获得家庭成员的收入支持,使其家庭的人均收入高于贫困线,其个人仍面临着发展机会的匮乏和市场参与权利的贫困。其次,无论是在以家庭为单位还是以个体为单位的贫困回归模型中,我们都将把男性和女性同时纳入分析样本,从而对男女两性陷入贫困的影响机制的差异、原因和对策进行深入的对比研究分析。
二、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的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为提高抽样的代表性,CFPS 采用了多阶段、内隐分层和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系统概率抽样设计。其调查对象是中国(除香港、澳门、台湾以及西藏自治区、青海省)29个省、市、自治区的家庭户以及样本家庭户的所有家庭成员。该调查旨在通过对来自全国代表性的样本村居、家庭、家庭成员的跟踪调查,以反映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状况。其调查方法严谨,覆盖面广,代表性强,数据质量较有保障[40]。CFPS2014原始数据库由村居、家庭成员、家庭、成人和少儿5个数据集组成,我们在家庭数据集中提取了家庭收入信息,在家庭成员数据集中提取生成了“未成年子女数量”的信息,在成人数据集中提取了户主的人口特征、就业、婚姻、性别观念等个人信息。在此基础上,根据个人编码将三部分数据匹配为一个总的数据集。
考虑到CFPS2014关于个人劳动收入的调查只涉及非农业人口及本文将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作为核心变量的研究需要,我们删除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中的丧失劳动能力者样本,共获取到5917个有劳动能力的非农人口样本(男,16-60岁;女,16-55岁)。以上样本中,就业者和失业者样本量分别为4584和1258。在失业者样本中,对于“没有工作的原因”问题,51个样本的选择是“不需要工作/不想工作”,即属于所谓的“自愿失业”。虽然“自愿失业者”的样本量并不是很大,但考虑到影响其市场参与和劳动收入不足的机制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譬如能够获得劳动力市场以外的收入支持,抑或是受特定价值观念的影响而主动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这有别于我们所想要研究的有意愿参与市场就业,但缺乏参与机会或能力而陷入个体收入不足的情况。我们据此删除了“自愿失业者”样本,将剩余的由在业者和非自愿失业者构成的5866个样本纳入贫困成因回归分析(见表1)。

表1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二)变量
1.因变量
根据本文的研究需要,我们设置了以下两个因变量:其一是被调查者的家庭人均收入是否低于当地低保线的“家庭贫困”变量,其二是被调查者个人的可支配收入是否低于当地低保线的“个体收入匮乏”变量[注]低保标准数据来自于2014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前者是在考虑家庭成员互济功能的基础上,对家庭中的个人是否贫困的判断;后者则是将个人作为劳动力市场中的独立个体,是对个人是否具有从市场中获得基本生存资源的独立能力的考量。
2.自变量
(1)人口学因素:户主年龄为连续型数值变量;户主性别为二元虚拟变量,男性为1,女性为0;户主教育水平处理为五分类变量,分别为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户主健康状况分为较差、一般、较好三类。
(2)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户主就业处理为三分类变量,分别为失业/无业、非正规就业及正规就业。
(3)婚姻家庭情况:户主婚姻状况处理为四分类变量,分别为在婚、未婚/同居、离婚、丧偶;子女情况处理为二分类变量,分别是有未成年子女和无未成年子女。非在业人口比重为家庭中无就业活动人口与家庭总人口之比。
(4)性别观念:将“男人应以事业为主,女人应以家庭为主”“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及“男女应平等分担家务”三种观念,分别定义为“性别角色”变量、“婚嫁观念”变量和“家务分担”变量。变量取值1-5分别代表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一般同意、比较同意、非常同意。
三、研究结果
(一)“家庭贫困”影响因素的全样本分析
表2所显示的是,基于全部样本得出的家庭贫困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在具体模型设置中,我们设计了4个嵌套模型。模型1显示的是基本人口特征对家庭贫困的影响;模型2在控制了人口特征因素后,考察性别观念对家庭贫困风险的影响作用;模型3探讨了在控制人口特征和性别观念后,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对家庭贫困可能性的影响;模型4综合考察了人口特征、就业、婚姻家庭及性别观念对家庭贫困的影响作用。
研究发现:(1)就人口学特征因素来看,健康状况和教育水平对家庭贫困发生着显著且稳健的影响。在各模型中,健康较差都显著增加着家庭贫困的可能性;教育水平对家庭贫困发挥了显著的负向影响,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家庭贫困的概率越来越小。年龄的提高会显著增加家庭贫困的风险(模型4)。(2)就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的影响而言,相较于正规就业者,非正规就业者和失业者家庭贫困的风险在各模型中都显著增加。(3)婚姻状况对家庭贫困发挥着显著作用。与在婚的户主相比,未婚/同居、离婚、丧偶的户主家庭贫困的可能性都显著提高。(4)性别观念变量无显著性影响。
(二)“家庭贫困”影响因素的性别比较分析
考虑到男户主和女户主陷入家庭贫困的影响因素有可能不同,我们根据性别对调查对象进行了分组(见表3)。回归结果显示,基本人口特征因素对男户主家庭贫困的影响总体强于对女户主家庭贫困的影响。具体来看,如模型6和模型8所示,健康较差女户主家庭贫困的可能性是健康较好女户主的1.742倍,而健康较差男户主家庭贫困的可能性则是健康较好男户主的2.999倍。学历为高中、初中、小学、文盲的男户主家庭贫困的可能性分别是大专及以上学历的男户主的3.302倍、3.709倍、4.319倍和7.119倍。学历为高中、初中、小学、文盲的女户主家庭贫困的可能性则分别是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女户主的1.918倍、2.220倍、2.757倍和3.855倍。可以发现,在各教育层次上,教育对男户主的影响都明显强于女户主,且统计上的显著性影响主要发生于男性组。
在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影响因素中,就业状况对男户主家庭贫困的影响作用亦要强于女户主。对于男户主而言,失业者家庭贫困的可能性是正规就业者的3.250倍(模型6)。而对于女户主来讲,失业者家庭贫困的可能性是正规就业者的2.580倍(模型8) 。
就婚姻家庭影响因素来看,婚姻对女户主家庭贫困产生了更强和更显著的影响作用。对于女户主来说,未婚/同居、离婚、丧偶者家庭贫困的可能性分别是已婚者的3.044倍、2.123倍和2.828倍。而就男户主来看,离婚家庭贫困的可能性是已婚者的1.507倍,未婚和丧偶对男户主家庭贫困无显著影响。

表2 “家庭贫困”影响因素的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Exp(B)值]
注:*P<0.05,** P<0.01,*** P<0.001。

表3 “家庭贫困”影响因素的性别比较分析[Exp(B)值]
注:*P<0.05,** P<0.01,*** P<0.001。
(三)“个体收入匮乏”的影响因素及其性别比较分析
表4反映的是“个体收入匮乏”,即个人可支配收入低于低保线的影响因素。模型9和模型10是基于样本总体的分析,模型11和模型12是对男性样本的分析、模型13和模型14是对女性样本的分析。考虑到性别观念有可能通过就业这一特殊的中介变量影响收入,在对各组人群的分析中我们都分别建模,在控制性别观念的基础上再纳入就业变量,以更清晰地揭示性别观念是否会通过就业影响个体收入。结果显示,对于样本总体来说,性别为女性、年龄增高、学历较低、健康较差及就业层次降低都会对个体收入不足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就性别观念的影响来看,性别角色变量在模型9中对个体收入匮乏产生了显著影响,但在模型10中则不再显著,说明该变量确实会通过就业的中介效应间接影响收入。婚姻家庭因素对个体收入匮乏无显著性影响[注]研究采用联立方程的方法,检测了个体收入和婚姻间有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即个体收入和婚姻之间是否发生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具体构建的方程为“lowincome=α0+α1marriage+α2χi+μi(1)”,“marriage=β0+β1lowincome+β2χk+μk(2)”。收入方程为公式(1),其中marriage表示是否已婚,χi是影个体收入不足的其它控制变量,μi是随机误差项;婚姻方程为公式(2),其中lowincome表示收入不足,χk表示其它影响婚姻的控制变量,μk为随机误差项。具体检验步骤如下:首先,作marriage对lowincome的logit回归,得到marriage的估计值marriage_hat和残差值u′。其次,作lowincome对marriage_hat和u′的logit回归,并对u′的系数作t检验。检验结果显示u′不显著,表明个体收入和婚姻间不存在内生性问题。。

表4 “个体收入匮乏”影响因素的性别比较分析[Exp(B)值]
注:*P<0.05,** P<0.01,*** P<0.001。
就男性组别而言:(1)在人口特征因素中,年龄因素和健康因素具有显著影响。健康较差男性面临个体收入匮乏的可能性是健康较好男性的2.023倍(模型12)。(2)婚姻家庭状况和性别观念无显著影响。(3)就业状况对男性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失业/无业的男性个人收入不足的可能性是拥有正式工作的男性的63.88倍。
就女性组别而言:(1)在人口特征因素中,年龄、健康和教育水平因素具有显著性影响。高中、初中、小学、文盲学历的女性面临个体收入匮乏的可能性分别是大专及以上学历女性的2.606倍、2.813倍、2.617倍和3.402倍。健康较差女性面临个体收入匮乏的可能性是健康较好女性的2.282倍(模型14)。(2)就性别观念的影响来看,性别角色变量在模型13中对个体收入匮乏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即女性对“男人应以事业为主,女人应以家庭为主”的观念越为支持,其面临个体收入匮乏的风险越高。家务分担变量对个体收入匮乏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即女性越支持“男人应该平等分担家务”的观点,其陷入个体收入匮乏的概率越小。在模型14中,性别角色和家务分担变量都不再显著,说明上述性别观念对个体收入匮乏的显著影响是由就业的中介效应造成的,即女性对传统性别角色和家务分担模式的认同度的增高,会导致其劳动力市场参与水平的下降,进而增加个体收入匮乏的概率。婚姻家庭状况对女性无显著影响作用。(3)就业对于女性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非正规就业女性和失业女性个体收入不足的可能性,分别是正规就业女性的3.272倍和176.7倍。
四、结论与启示
第一,在不同的贫困测量体系下,我们所观察到的贫困决定因素有所差别。对比模型4和模型10可以发现,“家庭贫困”和“个体收入匮乏”既受相同因素也受不同因素的影响。相同因素包括一系列的基本人口特征和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变量,表现为户主越年轻、健康状况越好、受教育水平和就业层次越高,无论其所在家庭还是其个人都会面临更低的贫困风险。
对“家庭贫困”和“个体收入匮乏”产生显著不同影响的则是婚姻变量。与在婚户主相比,未婚、离婚、丧偶户主个人收入低于贫困线的风险未显著增加,但是其家庭贫困的可能性会显著升高。这意味着,对于中国有劳动能力的城乡非农业人口而言,非婚模式虽不会对个人基本的劳动力市场资源获取能力产生消极影响,但如果将观察单位从个人拓展至家庭,非婚模式在家庭成员互济功能方面的缺陷及其对家庭经济的负面影响便展现出来。譬如,单亲家庭的父/母亲与完整家庭的父/母亲虽然在个人收入上并无显著差异,但由于单亲家庭父/母亲缺乏配偶收入支持而需要独自负担育儿支出,家庭人均收入不足的风险性便会显著提高。
第二,在不同的贫困测量体系下,男女两性的贫困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对比表3和表4可以看出,在“家庭贫困”分析模型中,人口基本特征和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对男性的影响要强于对女性的影响,婚姻状况对女性家庭贫困的作用则大于男性。而在“个体收入匮乏”影响因素中,人口基本特征中的教育变量及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都对女性产生了更强的影响作用。
男女两性贫困的影响因素之所以会出现上述差异是因为,在“家庭贫困”模型中,我们对贫困影响因素的考察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由于在中国,男性对家庭收入的贡献作用通常要强于女性[41],相对于女性家庭成员而言,男性家庭成员的就业情况及与其就业密切相关的教育、健康特征,便会对整个家庭的贫困程度及“家庭贫困”风险产生更强的解释力。此外,国内学界已有大量实证数据显示中国的婚配模式存在着“婚姻梯度”。特别是在教育和收入维度上,女性表现为明显的向上梯度婚,即女性通常会选择教育和就业水平高于自己的男性作为配偶[42]=[43]。上述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相比于女户主,男户主的教育和就业水平不足会对家庭的“家庭贫困”风险产生更强的影响。至于我们在回归分析结果中所看到的,女性在经历离婚、丧偶等非婚模式时,会面临更大的人均家庭收入下降以至贫困的风险,其实也与“婚姻梯度”有密切关系。受“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影响,女户主离婚所损失的来自于原男配偶的经济支持,通常要大于男户主离婚所丧失的女配偶经济支持,其陷入家庭贫困的可能性自然要较高。
在“个体收入匮乏”模型中,贫困影响因素的分析是基于个人进行的。可以看出,当我们超越家庭范畴,将男性和女性作为独立个体来观察个人的低收入风险时,女性在市场活动中多纬度的脆弱性便凸显出来。与“家庭贫困”模型中基本人口特征和就业情况全部对男性发挥出更大作用不同,在“个体收入匮乏”模型中,教育及就业情况变量对女性的影响都超过了男性。这说明与男性相比,受教育水平不足和就业层次降低会对女性个人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及个人收入水平产生更为不利的影响。
第三,性别观念仍是诱发女性贫困的深层次原因。研究发现,性别观念会通过就业中介变量影响个体收入匮乏,且该影响特别显著地作用于女性。具体表现为,女性对传统性别分工和家务分担模式认同度的增高,会导致其劳动力市场参与水平的下降,进而增加其个体收入匮乏的可能性。除家庭内部性别分工观念的影响,家庭以外的职业场域及社会环境中所存在着不平等的性别分工观念亦可能是导致女性贫困的潜在影响因素。原因在于,当我们对个体、家庭、就业变量进行充分控制的条件下,发现女性陷入个体贫困的风险仍然是男性的3.205倍[1/EXP(B)=1/0.312=3.205](模型10)。这与克莱森(Klasen,S.)与塞圭诺(Seguino,S.)等研究者在控制各类人口及家庭特征变量下,所观察到的女性更高的失业和低收入风险相类似[44]=[45]。同时也再次印证了巴斯图斯关于教育水平、工作经验等外显变量无法解释两性收入差异的原因,在于工作领域的性别分工并不完全取决于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还与职场性别偏好密切相关。女性所面临的职场区隔及其所导致的低收入风险,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建构”的结果。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缓解女性贫困:首先,应向离婚及丧偶贫困女性提供多元化的社会支持。研究发现,与在婚模式相比,离婚、丧偶会显著提高家庭贫困的风险,且该风险对女户主家庭的负面影响要强于对男户主家庭的影响。为此,应积极发展各类社会福利及社会服务项目,增强女性对婚姻解体及其所引发的贫困风险的应对能力。其次,应促进女性人力资本及劳动力市场参与水平的提升。研究显示,尽管在家庭单元下,女性的贫困风险受婚姻梯度的影响得以一定程度的分散,但从个体角度来看,女性仍然面临着比男性更高的个人收入不足可能,且其个人收入更易受到教育水平和就业层次低下的负面影响。为此,应关注女性的教育与培训,并通过改善用工环境、生育保障服务等多种方式促进女性就业。只有通过教育和就业参与水平的提升,女性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个人的抗贫困能力,也才能在离婚风险不断上升的社会背景下,更有效地应对婚姻问题所引发的家庭贫困问题。最后,还应在国家的反贫困战略中,进一步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为妇女摆脱贫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奠定更加牢固的社会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