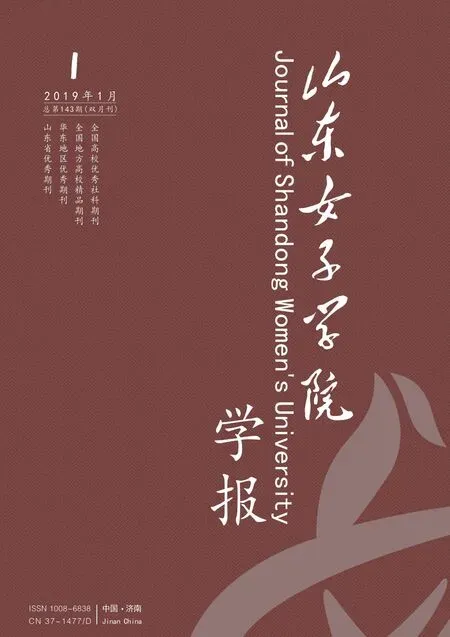明清方志文献书写的母教模式研究
杜云南
(肇庆学院, 广东 肇庆 526061)
根据中国儒家“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原则,女性的生活场域囿于家庭之内,其扮演的家庭伦理角色主要有女、妻、媳、母、姑等,而其中的母亲角色对古代女性别具意义,母亲与儿子的互动关系及情感又是影响古代女性处境与命运的关键因素。如今性别史学方法被运用于妇女史研究,女性作为母亲在家庭中的伦理角色日渐受到关注,其中台湾学者郑雅如[1]、熊秉真[2]78-93注意到不同时期的母亲角色与亲子关系,衣若兰则以《清史稿·列女传》为例,分析了有清以来正史书写、旌表制度以及方志列女传皆较凸显母亲角色[3]。这些研究虽然都注重爬梳不同史料,强调父系文化制度对母子关系的构筑,但忽略了不同地域、不同性质文献书写女性生活的差异。作为正史史料来源的地方志,如何书写地方女性,至今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应有关注。明清时期,官方组织的地方志编纂逐渐规范化和制度化。这些代表王朝价值观的地方志记录下了地方历史的发展进程,也在一定范围内留下了当地女性的言行举止。其记载的女性多为贞孝节烈的列女,形象大同小异,具有明显的模式化倾向。但仔细阅读这些女性贞孝节烈事宜,我们从中亦可以发现,实际上方志文献也为读者呈现了诸多理想的母亲形象,及其编者积极认同的贤母之教。本文拟通过梳理明清广东方志书写的有关母子互动关系的列女传记,试图探讨方志文献如何书写母亲课子,以及编者期待的理想的母亲形象。
一、训子忠义
我们现能见到的最早的岭南母亲教子的历史人物应是冼夫人,冼夫人是梁陈隋三代高凉地区的土酋首领,其生活的梁陈之际也是中国历史的大变革时期。最早书写冼夫人传记的是唐魏征的《隋书·谯国夫人传》,该书叙述:
谯国夫人者,高凉冼氏之女也。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夫人幼贤明,多筹略,在父母家,抚循部众,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每劝亲族为善,由是信义结于本乡。越人之俗,好相攻击,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强,侵掠傍郡,岭表苦之。夫人多所规谏,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洞。梁大同初,罗州刺史冯融闻夫人有志行,为其子高凉太守宝娉以为妻……
魏征将冼夫人描述为自幼贤明聪慧,能率部众的首领形象,更重要的是冼夫人自小就有向善、劝善的美德。冼夫人嫁与冯宝之后,不仅能够辅助丈夫统领岭南地方豪酋,而且能够带领土酋归附中原王朝。丈夫冯宝死后:
……及宝卒,岭表大乱,夫人怀集百越,数州晏然。至陈永定二年,其子仆年九岁,遗帅诸首领朝于丹阳,起家拜阳春郡守。后广州刺史欧阳纥谋反,召仆至高安,诱与为乱。遣使归告夫人,夫人曰:“我为忠贞,经今两代,不能惜汝,辄负国家。”遂发兵拒境,帅百越酋长迎章昭达。内外逼之,纥徒溃散。仆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将,转石龙太守。诏使持节册夫人为中郎将、石龙太夫人,赉绣幰油络驷马安车一乘,给鼓吹一部,并麾幢旌节,其卤簿一如刺史之仪。至德中,仆卒。后遇陈国亡,岭南未有所附,数郡共奉夫人,号为圣母,保境安民……
冼夫人在欧阳纥企图诱惑儿子冯仆一起反叛之际,告诫儿子,我家两代忠贞,我不允许你做出有负于国家的事。并亲自发兵坚守,欧阳纥的军队顿时溃散。所以,魏征笔下的冼夫人,不仅辅助丈夫,还会教导儿子,书写的是一个积极归附中央政权的形象。隋立国初,番禺人王仲宣叛,冼夫人初派遣孙冯暄出兵平叛,然而冯暄与叛军陈佛智“素相友善,故迟留不进”,冼夫人知之后大怒,将冯暄系于州狱,又遣孙盎出兵平乱,斩首叛军陈佛智。隋皇帝因此降敕书曰:
朕抚育苍生,情均父母,欲使率土清净,兆庶安乐。而王仲宣等辄相聚结,扰乱彼民,所以遣往诛翦,为百姓除害。夫人情在奉国,深识正理,遂令孙盎斩获佛智,竟破群贼,甚有大功。今赐夫人物五千段。暄不进愆,诚合罪责,以夫人立此诚效,故特原免。夫人宜训导子孙,敦崇礼教,遵奉朝化,以副朕心。
可见,冼夫人的归附与忠诚之心,也得到中央王朝的褒封与认可。在每年大会的仪式上,冼夫人都将王朝封赐物品陈于堂,“以示子孙,曰‘汝等宜尽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赐物具存,此忠孝至报也,愿汝皆思念之。’”冼夫人在表达自己对朝廷的归附之情的同时,还不忘谆谆告诫子孙应赤心向天子,行忠孝之道。
然魏征于武德五年(622年)开始着手编撰《隋书》,距冼夫人逝世的602年已有20多年时间,他并没有亲历亲见冼夫人的事迹,更遑论冼夫人所发出的各种言辞,如果编者是根据前人的记录而成文的,那成文的过程中也一定暗含了书写者需要表达什么样的人物形象而选取什么样的素材的意图。贺喜通过分析《隋书·谯国夫人传》中冼夫人的形象及其文本诞生的时代背景,认为魏征塑造冼夫人归顺陈隋二朝、尽心事主的事迹与家风显然可以作为冯氏家族忠诚唐王朝的最好宣传,和当时皇帝与土酋间的政治与外交亦相配合[4]。那么在这种书写意图下,作为一个母亲角色的冼夫人,在教导子孙的言行上,必然也是显示其致力于维护岭南与中央政权一致的面。可见母教对于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及政治的清明起到了一定作用。
至少在宋代以后,冼夫人就成了表达地方与中央王朝关系的符号,她既是地方的领袖,又是归附的象征,也是方志收录最早的一位训子忠义的母亲形象。现能见到最早的方志中的冼夫人形象是正德十六年(1521年)刻本《琼台志》[注]本文引用的地方志均为2007年岭南美术出版社影印的《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卷33《名宦·冯冼氏》中记载的冼夫人,此文仅用202字书写冼夫人在海南地方上的军事行政事迹,其在海南之外的事迹全被省略,贤妻与贤母的形象也不见踪影。而在嘉靖十四年(1535年)刻本《广东通志初稿》卷14《将略》中的《隋冼氏夫人传》中,该书的编纂者戴璟认为,冼夫人因明春秋大义、保境安民而载入史册,在《将略》中排在南北朝的覃元先之后,因而文字亦注重叙述冼夫人的军事谋略,其作为母亲形象的文字全无,也没有刻意突显冼夫人的忠诚之心,通篇记载冼夫人重大战事,全文也只350字,不及《隋书》本传1421字的四分之一。到嘉靖四十年(1561年)广东名儒黄佐编纂的《广东通志》,其在挖掘地方历史人物上不遗余力。黄佐于正德年间编纂《广州人物列传》,力图显示岭南在人才将略、忠孝义烈的历史人物在在有之,并不亚于中原王朝。在通志中他根据《隋书》《北史》参修了冼夫人传,用了1500多字书写了《谯国夫人传》。与此前方志不同,他将冼夫人传记置于卷36《列传二十》中的《列女》一栏,其内容基本沿袭《隋书》,冼夫人训子忠义的母亲形象在方志中得以凸显。以后万历、康熙期间编纂的《广东通志》,多从黄佐版本。
此后方志中训子忠义的母亲亦不乏其人。黄佐的《广州人物列传》收录了一位宋代陈烈妇:陈烈妇,东莞士人李颐妻子,其侍奉公婆孝顺严谨。生子李佳后,夫亡故,“守志教子,俾知向学”。时值宋元易代之际,宋帝昺自闽入粤,驻留于崖山冈川。陈母让儿子“应勤王之诏”,临别时,与子诀别说:“汝宜竭忠,勿以老身为念也”。其意是嘱咐儿子应一心事宋主,不要对她有所牵挂。待李佳出行后,陈母为了断绝儿子的后顾之念,亦趋广州的黄木湾,毅然赴水而死,而李佳不知情。后李佳至崖山,得到宋皇帝封赐潮郡教授,归家拜母不见,“哀陨莫及”,筑“望母堂”,“以寓终天无涯之悲,闻者两伤之”。黄氏在传文之后附录了时人陈琏为陈氏所作的《精卫词》,并标注传文根据《广州志》和《琴轩集》参修。大德八年《南海志》和天顺八年(1464年)刻本《东莞县志》因是残本无迹可考,成化九年《广州志》并无此传,崇祯十二年(1639年)刻本《东莞县志》卷5《人物志·节烈传》中的陈烈母传是现能见到的最早方志记录,编者因感叹陈母“勉子勤王而死,以绝其内顾”之烈而将其列于本县节烈女性记载之首,内容与黄佐所记基本一致,只是编者将人物言论中的“老身”改为“我”。此后的方志基本沿袭此文。
类似上述陈烈妇教子尽忠,并以身殉国的母亲形象,在明清换代之际亦有出现。同治十一年(1872年)刻本《南海县志》卷22《列传十·列女》记载明末抗清将领陈子壮[注]陈子壮(1596~1647),明末抗清将领,与陈邦彦、张家玉合称“岭南三忠”;字集生,号秋涛,谥文忠;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其著有《云淙集》《练要堂稿》《南宫集》。母亲朱氏训子事迹:朱氏,陈熙昌[注]陈熙昌,生卒年不详,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进士。妻,“生而姽婳,明诗习礼,而性情贞正”,幼读春秋,读到宋伯姬死时曾感叹:“为女子当如此矣”,后归家陈熙昌生子子壮,“严督养”,子壮以文章显。时值清军攻陷江南之际,明庄烈帝朱由检殉国,弘光帝朱由崧(1607~1646年)在南京继位,后南京陷落,子壮得太后指令:“星驰还粤集旅勤王”,得间隙抵家拜母,朱氏对儿子说:“南京破,吾以汝为死矣,今福王何在,汝何缘独归?”朱氏言下之意责问儿子为何不以死烈护主,而独存归家。子壮泣诉“君臣散失”缘故,朱氏却劝勉说:“尽忠即以尽孝,汝毋以我故藉口养亲,若徒知事我以生,反速我以死也。”朱氏诫子以忠义为先,舍私情取大义,不仅在言语上训勉督促,更在行动上积极支持。1646年,闽粤两地陷落,1647年6月子壮受命与舅子朱实莲起兵抵抗清军,朱氏亦“尽斥金钗犒士”。在攻打广州的过程中失败,子壮被执殉节,朱氏闻讯后说:“儿获死所矣,吾家世受国恩,非是无以报国。”说完则从容入室,投缳而死。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崇祀于节孝祠。方志编者以一千多文字形象地传达了朱氏幼时知书习礼,为母则深明大义,教子尽忠护主的情操。此前康熙三十年(1691年)的《南海县志》和乾隆六年(1741年)的《南海县志》均无朱氏传,但列传“节义”栏目中则有其夫其子传文。后光绪五年(1879年)广州粤秀书院刻本《广州府志》卷142《列女一》则据《南海县志》收录朱氏传文,但文字有所删减,全文仅200多字,朱氏读书言论被删去,勉子言论亦被简略为“尽忠即以尽孝,汝无以我故藉口也”,可见,编者篡改了朱氏的教子言论,而此后的方志基本沿袭此文。
经以上案例分析我们发现,岭南由于地处边陲海隅,在宋以前属于未开化之地,由中原士人所记载的冼夫人是一个积极拥护中央政权,又训导子孙行忠义的母亲形象符号,她所行忠义的对象是中央王权,而这种王权并无朝代之分。宋以后,王室南迁,岭南经济崛起,逐渐形成了一批士大夫集团,他们开始记述母亲形象;又由于广东地处边陲,在更朝换代之际,是前朝皇帝流离避难或者蓄力以待东山再起之地,因而他们书写的母亲训子忠义均是易代之际如何教导儿子忠贞前主,并以死殉国的烈母形象。但是不同方志编者在书写同一人物时,或多或少地篡改了母亲教子言论。
二、课子成立
明清方志多属当时人记当时事,对历史久远的女性事迹的挖掘毕竟是少数,编者书写的多为宋以后的女性事宜,又集中于夫亡守节的女性生活。女性遭遇夫亡厄运,其活下来的理由是抚孤育子,延续夫家血脉,她们把自己的希望和命运寄托在儿子身上。岭南方志编者亦聚焦于守节女性,书写她们抚育孤子,重点是书写她们如何负起教育孩子的责任,尤其是对男孩的教育,这种教育包括亲授儒学,或者激劝亲子学儒,培养儿子走上仕途。
嘉靖以后,广东方志记载的由母亲教授儒家经典,并培养出岭南学士名儒的案例不胜枚举。万历间刻本《琼州府志》卷10《人物志·列女》记载了琼山县海瑞(1514~1587年)母亲谢氏:海大恭人谢氏,庠生海翰妻子,年28岁守寡,子海瑞4岁,“家计萧条”,谢氏矢志鞠育儿子成立,“日夜勤女红”,并“口授瑞以《孝经》《学庸》诸书”。海瑞少时“有戏谑必严词正色诲之”。谢氏在夫亡子幼家境贫寒的情况下,母代父职,亲自传授海瑞以儒家经典学问。后海瑞官至右都御使,其母功不可没。谢氏因此于天顺年间获得官方旌表。
由母亲来传授学问,这反映了明清女性本身具备良好的学识教养,给子嗣的知识教育带来极大的帮助。美国学者高彦颐注意到明清妇女在教育、读书、出版和交流等方面机会的不断增加,为其行使母亲责任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条件;而且寡母督管儿子教育,被突出地描绘在传记中,以至于它几乎成了一种文学惯例[5]。又如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英德县志》卷3《贞烈志》记载刘氏,“通大义,过目吟”,年21寡,守志抚孤,育子有成,后又以《孝经》《四书》口授幼孙。像前述谢氏一样,刘氏在夫亡后,也亲自传授、督管子孙学习儒家经典。
同样,嫡母教授庶子也是编者书写的内容。光绪五年(1871年),广州粤秀书院刻本《广州府志》卷142《列女一》记载香山县何氏,生员杨兆公妻,侍奉公婆“动止有仪,吐辞以则”,姊妹都以她为师,何氏婚后无子,悉出嫁妆为兆公买妾生子,后兆公病卒,妾生子晋,何氏亲自鞠育,口授以《小学》经传,后晋学有所成,“捧檄色喜”,何氏说:“汝欲效毛义[注]毛义,字少节,东汉末庐江人。自幼丧父,母子相依为命。家境贫寒,年少便以为他人放牧为生,箪食瓢饮,奉养其母。母病伺候汤药,曾割股疗疾。逐以孝行称著乡里,举为贤良。朝廷得知,送檄文赏封他为安阳县令,为了安慰母亲,毛义迎至“临仙桥”喜接檄文。然时隔不久母亲病逝,朝廷派人前来看望,岂知毛义却跪拜于“临仙桥”上,将原赏封安阳县令的檄文双手捧还,“躬履逊让”,不愿为官。葬母后隐居山野。见《后汉书·刘平传序》。耶?与子偕隐足矣。”毛义有孝行且不贪禄,为世人称道,何氏引经据典鞭策庶子淡然处世。从这则案例,也可见编者意欲凸显的嫡母与庶子之间应有的亲密关系。后来何氏守节三十九年,县令上其事请旌。像谢氏、刘氏和何氏这样亲授诗书的案例,方志中屡见不鲜。英国学者白馥兰曾将明清书写妇女教育孩子现象的增多,归于宋以后劳动经济的专业化和商业化,妇女在纺织劳动上的价值降低,使其职责迁移到生育和教养孩子上来[6]。但是在方志书写的千篇一律的寡妇家庭中,明清女性不仅仍要像远古家庭女性一样,从事纺织、侍奉公婆的职责,还承担了训子读书的任务,编者总是乐意记载这些毫无怨言地担负起没有男性家长的家庭事务又能教子有成的女性事迹。这似乎说明了明清女性在家庭、社会中所承担的职责范围越来越广泛,其主体地位也在逐渐提升。
如果说上述有教育背景的女性亲授儒学是母教职责的话,对于大众家庭来说,即使母亲所受教育没有达到可以亲自教子的程度,她也能够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鼓励儿子向学。嘉靖四十年,《广东通志》卷63《列传二十·列女》记载肇庆府四会县欧阳氏:
欧阳孺人,四会林相妻,年十五归相,惠柔孝敬,相省父于故城,返于途卒,欧阳闻之即欲以死从,每哀恸欲绝而复苏。一子世远。所亲讽以他适,欧阳曰:“吾忍舍儿女,不忍负吾夫。”言者愧沮。成化甲午,舅补官上高,召世远往就学,人有以孤幼勿远游言者,欧阳曰:“吾妇人不知书,亟往,万一有成,庶不泯渠父也。”世远既登第,令莆田芜湖,迎母就养,每戒毋用严刑。以子贵赠孺人。弘治二年,知县立详具奏旌表其门,缙绅作《贞则録》以美之,少傅姑苏王鏊为之传。
此传文后标示“据肇庆志修”,嘉靖以前的肇庆志现不存,无法查对。不过,该传形象地描述了欧阳氏励苦守节教子的言行,欧阳氏虽“不知书”,但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积极督促儿子学习,后儿子学有所成,又诫子为好官。她也因此荣获官方旌表,美名远播,姑苏大学士王鏊(1450~1524年)为之作传。后万历十六年(1588年)刻本《肇庆府志》卷20《列女传》亦收录欧阳氏传文,与前述传文有所区别:
欧阳氏,四会人林相妻,相省父于故城,归至湖口卒,欧阳闻之哀恸几绝,誓无他志。一子世远,教有义。方舅补官上高,召世远往就学,有以孤幼言者,欧阳曰:“是宜亟往,他日有成,庶不泯其父也。”世远登进士,令莆田芜湖,迎母就养,每以严刑为戒。后赠孺人,诏旌其门,少傅王鏊为之传。
与前面的传文比较,该传文仅一百多字,删略了亲人劝其改嫁的情节和言论,是据王鏊所作的《林节妇传》以及旧志通志所修。王鏊,江苏吴县人,成化十一年进士,官至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其所作《林节妇传》长达500多字,叙述了林相远的母亲欧阳孺人,幼时就有贤明孝敬的本性,夫死后又矢志守节,勤俭操劳,帮助家庭度过经济危机,并精心调护多病的幼子,对其学习更是“少懈则苛责不贷”,督子往公公处求学的言论为:“吾舅命也,吾意正在此耳”。很显然,编者虽与王鏊所写传文表达意思一致,但对文字进行了修改。此后的县志、府志和通志基本沿袭万历府志。从这则案例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方志编者根据自己编修的需要对欧阳氏的传文以及言论进行了修改。
母亲感化儿子向善亦是方志编者书写母教的重要内容。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刻本《新会县志》卷15《列女志·节孝》记载甘氏,16岁嫁给刘承业,25岁夫卒,甘氏欲以死相殉,亲族劝以抚孤儿以安舅姑心,乃不死,后子鸣世“少任侠弗羁”,甘氏训诫说:“儿若此,先人其弗嗣矣。”放声哭,鸣世惧,“跪白请改求师于叔杰”,杰说:“无如黄先生孚者”。后鸣世跟随黄孚折节读书,“尽捐夙习揆义于矩”,甘氏则能宽心纺绩事舅姑。……甘氏用谆谆之言语,加上眼泪的攻势,终于感化世鸣奋发求学。光绪二年重刊本《肇庆府志》卷19《人物二·列女一》记载生员温召妻李氏,温愿的母亲,年25岁而寡,“家贫勤纺绩,训子严正”,其子“偶佻挞,必不恕”,常常流涕对子说:“我寡家贫,只生汝,苟堕家声,不若与汝俱死”。其子受其感化,“慎守其训”而成立。该方志还记载一例阳春县黄守玑妻教子济贫行善的言行:吴氏年19夫故,儿子仅生两月,上有孀居的婆婆,时逢乡寇劫掠,吴奉姑与子播迁经营,孝养勤俭致裕,尝教子说:“贫而能约,富而能济,古之道也”。后子纯武游庠,“善体母志”,捐金赈饥,代穷乏者偿夫役之费,邑令朱以惠及桑梓表其闾。纯武之善举可谓得益于母教。
总之,寡母不仅要承担家庭的物质生活责任,还要担负起教育年幼儿子的责任。其教育涵盖启蒙授书、立身处世、改过迁善、救世济物等,通过道德价值观念的灌输,使孩子成为一个符合儒家标准的有用之人。在教子过程中,母亲性格往往是“严正”,行为举止动则以礼,其作为教导者,具备不可违抗的权威性,儿子作为受教育者,对母亲恭谦顺从。熊秉真认为,母亲与儿子一起忍受人生种种苦难并教育儿子成人立世的经历,加深了母子之间的情感,这种经历不仅加深了儿子对母亲的依恋,母亲的痛苦和对儿子的无私奉献也在儿子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儿子怀着一辈子的内疚感[2]255-280。所以我们看到的贤母传记,一般是儿子在晚年时回忆而书写的,带着这样的情感因素的书写者,必然会将母亲的苦难和自己的成就联系在一起,并将其归功于母亲的无私奉献。因此,从方志描述母亲如何教子有成,如何塑造母子之间的慈爱和敬重的关系,似乎可以看出母子之间的关系已悄然逾越了男尊女卑的藩篱。
三、助子为官
在母亲严苛的教育下,儿子往往奋发求学,年长后学有所成,并晋升于官场。对于做官的儿子,方志一方面会书写儿子如何责无旁贷地禄养母亲,一方面又会叙述作为官员的母亲,如何训诫儿子尽忠国家,扬名立业。嘉靖十七年(1538年)刻本《增城县志》卷7《人物志五·列女传·贤母类》以专栏记载岭南大儒湛若水母亲陈氏:“生而孝敬”,至及笄年龄,嫁与湛公瑛,在湛家,陈氏恭逊诚恳侍奉公婆,和妯娌之间也能和睦相处,众妯娌或言笑喧嚣,陈则“步履有节,出入必以扇自蔽,虽卑幼未尝见其面。每晨兴以五皷为节,昏必二皷乃寝,有事则三皷乃就寝,丝麻针缕必谨……”后夫早亡,陈孀居寄寓母家教子向学,她虽“菲衣粝食”,却命其子若水求学于外,后若水领乡荐,因无人侍养寡母,“不赴礼闱十三年”,陈氏又遣子从岭南大儒陈白沙先生游学,并告诫若水说:“汝受国家教养,可以我故不仕乎?可不及我未老见汝行志乎?”训示儿子应尽忠服务国家,避免因私累公。后若水赴礼部,举乙丑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若水受官后,迎陈母至京供养,陈氏也因子秩满推恩封孺人。陈氏可谓教子有成而荣显之明例。
传文又记载若水奉命封安南国子,便道奉陈归乡时,陈氏说:“我居京师甚适,我儿还朝当与之俱”。其意应是陪伴儿子在京为官,免除儿子挂念之虑。传文还描述陈氏待客甚厚、行善义举:其子若水喜与名士游,前来拜访者无虚日,陈则“率家人治具以燕乐之东”。……后陈氏以风疾卒于京邸,卒时遗命“糴□□百石为建义仓千坟所以賙”……又命子“出其家粟市田若干亩,岁入榖二百斛,立小宗义田,其法,凡小宗之亲昏嫁丧葬则给助之,有差。又置宗子田若干亩,岁入粟二十斛为祭服,具俾世守之不替。”陈氏的义举获得了乡人的敬重,她可谓集儒家提倡的美德于一身的典范。
传文以六百多字记载了贤惠母亲与孝顺儿子之间的互动。母亲勤俭节约助子求学,儿子学有所成后,又劝以报效国家为先,孝义为后。湛若水的成功可谓得益于母亲的自我牺牲和鞭策,子以母教而立功扬名。传统士大夫所期望的女性在家内扮演的角色大抵如此:牺牲自己,成就男性,因为男性才有光耀门楣的希望和机会,而女性也以教养杰出的儿子来获得肯定与尊敬。后康熙十二年《增城县志》卷9《人物后志·列女》将陈氏并列于本地节妇列女之中,陈氏传文被简略为二百多字,母子之间的互动关系被模糊,陈氏言论均被取消,编者仅只是客观地叙述了陈氏行谊,重点似乎在凸显陈氏的捐赠义举。此后的方志也基本沿袭此文。
前文提及嘉靖四十年《广东通志》卷63《列传二十·列女》记载了肇庆府四会县欧阳氏教子成立走上仕途之后,其子迎母就养,仍教子“每以严刑为戒”,而王鏊的《林节妇传》则描述了欧阳氏诫子为官:“每举‘淸、慎、勤’三事为训,犹戒毋用严刑,意独恳恳,侯迄今遵之不敢违”。在其他府县也有类似于欧阳氏训子为官的母亲。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韶州府志》卷九《人物志二·列女》记载韶州府英德县刘氏:诸生谢造妻,善事舅姑,茂年夫逝,厉节育孤,长子因科举补官,刘氏令次子寄书信告知:“而须为好官,以承先志,否则虽禄养,吾将吐之”。刘氏言论体现了她期望儿子做一个好官。
从上述案例可见,方志编者期望的母亲形象也表现在维护社会公义这一方面。年长的儿子对母亲怀抱深厚的感激之情,孝顺母亲,而母亲又能以社会公义为先,以言语训诫儿子将这种私情转化为公义,以母亲的权力与母子之间的情感促使儿子为国家社会服务。有的母亲甚至通过帮助儿子,或者直接参与到儿子的社会活动中,将女性的影响力从家庭延伸到了社会和国家。道光十五年(1835年)刻本、同治八年(1869年)重刻本《南海县志》卷41《列传十》记载谭氏:佛山义士洗灏通妻,黄萧养寇乱,灏通父子积极捍御,当时有吴萧者,“怀金二千,自大良来,众疑为贼,将执杀之”,谭对儿子靖说:“彼若贼安携多金,可白而免之。”吴获免后,要求寄金,谭令其自埋,贼平,吴掘地取出“封识宛然”,吴喜欲以半相赠,谭氏谢却不受,当时贼寇泛滥之时,有当地妇女来奔避者,谭将之“磬资给之”,存活下来的人为数不少。该传文后标注“据陈佛山志修”,但此志现不存无法查对,后光绪五年(1871年)广州粤秀书院刻本《广州府志》卷142《列女一》系复制此文。谭氏在战乱之际,凭着自己的智能,洞察时事,使吴萧免一死,并善用吴萧钱财帮助乡村妇女渡过了困难时期。女性通过向公共领域行善施德,使自己的行为超越了内外之别的界限。而惠州府的何氏在危难紧急的情况下,甚至直接参与了儿子的官职政事:
何氏,颜容穆妻,希琛母也,性慈惠明大义,初,希琛任山东粮道,何就养德州官署,忽大雨七昼夜,山水骤涨,居民争登城避水,哭声殷天,时希琛因事留省,何命速发仓榖赈饥,署内外皆坚持不可,曰:“此须详明奏准,否则擅动仓榖,处分綦严为祸甚钜,愿垂三思。”何曰:“此何时,犹拘文法乎?德州距省远,俟其详奏,数十万灾黎尽成饿殍,君等无恐,速发以救倒县,吾子功名不必计较,即查封备抵罄吾家所有尚足以偿。”于是尽出簪珥易钱,运米城上,发给其有缘树登屋不能为炊者,聊筏载礳饼施之州民,赖以全活,山东巡抚某果以擅发劾参,□□高宗曰:“有如此贤母,好官实心实力不加保荐乃转列之弹章,何以示激劝?”立赏何三品封衔,……封至一品太夫人[7]。
何氏“性慈惠明大义”,在山洪骤涨、城民危在旦夕的紧要关头,能不拘文法,亦不顾自身得失,慷慨解囊,救民于危难之际。她的言行,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深明大义、行事果断,置大义于私情之上的聪明有识的妇人。而从官署内外之人与何氏的互动对话中,可以看出母亲对儿子似乎具有相当大的权威。而高宗能明辨良莠,特别予以旌封,以示激劝,亦可见何氏在特殊情形之下不拘明律、救民救灾,委实难能可贵。
方志书写的母亲训子为官,不一定只存在于寡母对儿子的训示,亦有父亲在时母亲也参与训导儿子的案例。光绪五年(1871年)广州粤秀书院刻本《广州府志》卷155《列女十四》记载广州府番禺陈氏:东井先生政女,“幼端重寡言笑”,七岁丧父,受《孝经》《论语》于诸姊,17岁嫁给编修黄畿配,奉事舅姑非常严谨,舅姑“性严或有谴责受之而不怨”;后夫游学邻邑,陈氏为夫罄财以资其求学,夫友屡有需索者,至陈氏必慷慨解囊,“脱簪珥以应之”;其子由翰林贬为广西按察佥事,陈氏则训诫道:“此汝外祖之旧职也,其无以外补为歉,惟求无愧于师道足矣。”及至儿子因病弃官归养,后又被复召任用,陈氏又告诫儿子:“此殊恩也,不可辞,吾当就汝养耳,乃趣之行”,鼓励儿子出仕服务国家。
这些案例均表明,儿子走上仕途之后,其在工作、政治或者军事领域里,仍可能受到母亲的影响。虽然传统女性的性别角色在礼法上是“正位于内”,但方志对母亲助子为政,甚至参与儿子政事的记载,却显示了女性的影响力通过儿子由家内延伸到了家外,跨越了性别权力的界限。
四、结语
综上所述,明清广东方志所书写的母亲多为明清时期的守寡女性,这与嘉靖以后岭南士大夫的崛起是同步的,有知识的男性书写母亲事宜日渐增多,而士人专注于守寡母亲事宜,与明代以后贞节观念强化的趋势不无关系[8]。爬梳这些母亲传文,不见母亲关爱儿子衣食住行的慈育描写,几乎均为寡母辛勤操劳和训子之言行,其训导的方式不一而足:或亲授儒学,或劝子早日成立、改过迁善,或助子为官、行善亲民,或训以忠义,等等。母亲以教导者的形象受方志编者称扬,反映了编者对母子关系的描述以及对贤母之职的期望。而从性别角色的角度分析,母亲教导的对象聚焦于男性子嗣,一方面说明了传统社会里,人们往往期望男性能有优秀的表现,承担起兴旺家庭的责任,达到母以子贵的荣显;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古代女性虽不能借由社会活动建立个人成就,但她可以通过生育教养杰出的儿子,获得社会的肯定与尊敬。
同时,我们在分析具体传文时也发现,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母亲课子的许多言行举止常常有高度的相似性;同时,不同版本的方志,对同一母亲的书写或不断的复制,或又进行不同程度的改写。但是对于这种贤母教子的书写,多受明清方志文献青睐,不仅具有模式化特征,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们与其将之视为当时生活中的真实案例,不如将之当作是文献编者对母亲职能的期望的传达,他们以此树立儒家正统的母亲形象,鼓励女性培养优秀的男性,为家族、国家和社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