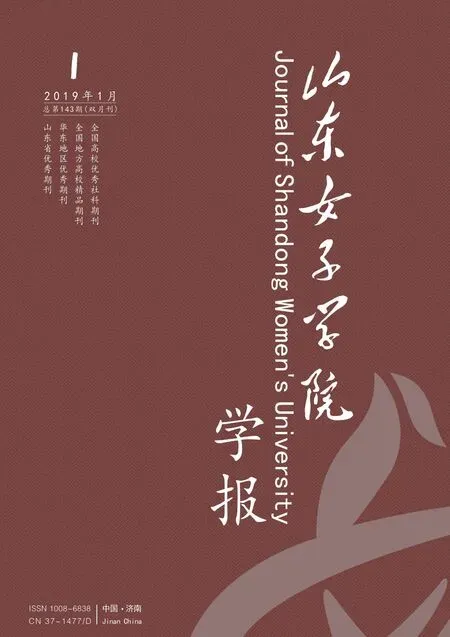冼星海与钱韵玲爱情和婚姻的历史考察
胡艺华, 潘 婷
(1. 武汉音乐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0; 2. 武汉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2)
伟大的时代孕育伟大的爱情,高尚的人格支撑高尚的婚姻,冼星海和钱韵玲之间既有伟大的爱情,也有高尚的婚姻,耐人寻味、令人敬慕、给人启示。冼星海,1905年出生于广东番禺,1945年病逝于莫斯科,是中国现代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音乐理论家和音乐教育家。这位贫苦渔民的遗腹子,在时代浪潮的激荡之下终其一生用音乐为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而奋斗,被毛泽东称为“人民的音乐家”。钱韵玲,1914年出生于湖北咸宁,1994年于杭州去世,是中国近代知名的音乐教育家,在儿童音乐和群众歌曲的创作方面成就斐然。红色教授钱亦石的这位女公子,在抗战歌咏运动过程中与冼星海并肩同行,成为生死伴侣,与冼星海紧紧联系在一起,倾注毕生的心血支持冼星海的音乐创作,继承冼星海的遗志,传承冼星海的精神,可以称之为“冼星海背后的女人”。作为一个以革命为己任、具有英雄气概而又性格内向的音乐家,冼星海对钱韵玲这位战火中的生死伴侣、音乐上的忠实助手、生活上的得力帮手,倾注了崇高、真挚、朴实的大爱深情。他们的结合是革命与音乐的碰撞、青春与理想的交融、爱情与命运的共振,开创了中国音乐界革命伉俪、生死伴侣的新风尚,谱写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感天动地的爱情婚姻之歌。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爱情和婚姻发轫于音乐演出的舞台上,成熟于红色延安的土壤,淬炼于抗日救国的战火中,定格于黄河怒吼的歌声里。每一个历史阶段都蕴含着可歌可泣、可敬可叹的精彩故事,既浸润着传统文化的血脉,又闪耀着革命理论的光芒,也映照着红色初心的赤诚,更洋溢着音乐情怀的浪漫,堪称是马克思主义爱情婚姻观的生动范例,为文艺工作者爱情和婚姻的培育和升华提供了示范引领。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艺界的培育和践行,红色家风和家庭文明在文艺工作者队伍中的传承与发展,都迫切需要我们深入到历史的场景中去全面考察、科学解读冼星海和钱韵玲这一对革命夫妻、音乐伉俪在爱情和婚姻方面的精彩故事。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冼星海和钱韵玲从初在上海时的模糊印象,到武汉时的相逢相恋,再到延安时的不离不弃,最后“两地遥隔,能不依依”[1]。他们的爱情与婚姻经过了从萌芽到发展再到成熟最后到升华的过程,对此我们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进行考察。
一、奠基阶段:冼星海和钱韵玲的相识相交
1935年冼星海从法国学成归来,即在上海投身于抗战歌咏运动,先后创作了《救亡进行曲》《青年进行曲》《保卫卢沟桥》等一系列救亡歌曲,抗战爆发后随“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第二队”赴各地进行巡回演出,先后途径苏州、南京、徐州、开封、洛阳、郑州,一路上既教唱抗战歌咏,又创作救亡歌曲,于1937年10月3日到达当时的全国抗战中心武汉,随后进入到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三厅文艺处音乐科工作。在郭沫若、田汉的直接领导下,冼星海与张曙等人一起组织大规模的抗日群众歌咏运动,同时创作了《游击军》《在太行山上》等一大批抗日歌曲。此时的冼星海已经33岁,漂泊的生活、动荡的时局使得他一直孤身一人,他把主要心思都花在谱写抗战歌曲上,但是作为一个具有艺术情怀的大龄青年,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同样怀有对幸福家庭的期待和对甜蜜爱情的向往。钱韵玲是中国共产党湖北党部早期创始人、我党早期著名教育家、理论家、社会活动家钱亦石的女儿,作为家中唯一的女儿、最小的孩子,深得父亲的疼爱,从小就随着钱亦石在上海读书,曾在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学习音乐,经常和母亲一起为中共地下党传送信函。“七七”事变之后,23岁的钱韵玲奉命回到武汉,在武汉第六小学担任音乐教师,同时经常参与抗战歌咏运动。来自于不同地方、看似毫不相干的两个人,因为抗战歌咏活动联系在了一起。
其实早在上海时,两个人就有过交集,一方,面,钱韵玲的父亲钱亦石是冼星海十分敬重的师长,而钱亦石是当时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公开身份是上海暨南大学教授。他家是上海左翼文学艺术家们的一个重要聚会场所,冼星海也时常去参加聚会,但由于钱韵玲当时正在上海新华艺专上学,在钱韵玲家中二人未碰过面。另一方面,冼星海在上海为电影配曲时,时常找上海新华艺专的学生合唱,而钱韵玲就是合唱团中的一员,与冼星海有过数面之缘。但由于学生太多,二人没有机会进行单独的交往,彼此的印象都非常模糊。而抗战爆发后,在武汉,冼星海再次与钱韵玲相见。当时钱韵玲是武汉六小的音乐教师、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的积极分子,工作之余钱韵玲参加了由冼星海创建的“海星歌咏会”,每周两次向他学唱救亡歌曲,然后又各自分散去创建另外的歌咏队,到街头去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多年以后对他们在武汉相见的场景,钱韵玲记忆犹新。钱韵玲在《忆星海》一文中写到:“一九三七年的秋天,在武汉,我在一次会议上第一次见到了星海,他朴素、诚恳、热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钱韵玲在此文中提到的“第一次见到星海”,实际上是指钱韵玲与冼星海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面对面的交流。因此钱韵玲称之为与冼星海真正意义上的初次相识,但是冼星海对钱韵玲的印象并不深刻。
直至1938年1月29日钱亦石先生去世,在他的追悼会上冼星海才知道钱韵玲原来就是他所敬仰的前辈钱亦石的女儿。作为中共湖北党部的早期创始人,党内早期著名的理论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社会文化名流,钱亦石先生在上海因病去世的消息在全国尤其是湖北引起了强烈反响,武汉市文化界人士于2月27日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朱德发来唁电,周恩来、董必武亲自主持追悼会并致悼词,郭沫若敬送挽联,邹韬奋、沈钧儒在会上发表激情演说。在追悼会之前,著名词作家施宜专门撰写了“钱亦石先生挽歌”,心怀敬意而又悲痛万分的冼星海受命谱曲并亲自指挥钱韵玲所在的“海星歌咏会”进行演唱。当时“海星歌咏会”派来取歌谱的恰恰是满面凄容、双眼红肿的钱韵玲,通过追问和交谈,冼星海才得知他敬仰的前辈钱亦石先生原来就是钱韵玲的父亲。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到:“他的女儿韵玲在我歌咏班里学习,直至今天我才知道她是亦石的女公子。今早她把我作的挽歌送上来,我偶然问亦石先生是她何人,她便含着泪来答我‘是我父亲’。她悲伤到不能成声!这个印象给我非常深刻!”[3]211至此,冼星海才知道钱韵玲的真实身份。这也许是钱亦石先生在冥冥之中为他们牵起的缘分的红线,使他们有了单独交往和深入交流的可能。
从此以后,钱韵玲才开始真正走进了冼星海的关注视线和精神世界里,冼星海的书信和日记里面也逐渐出现了钱韵玲的身影。他多次提到与钱韵玲的交往过程,他用“海星歌咏会”的训练来激励宽慰钱韵玲失去父亲的悲伤,不时约钱韵玲喝咖啡、看电影、参加音乐会,并且鼓励和激励她学习音乐、合作歌曲。而在此期间钱韵玲也开始慢慢了解冼星海、走近冼星海,成为他歌咏会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也成为他失意时的忠诚陪伴者和耐心倾听者。这些都使身在异地他乡的冼星海十分感动,他在5月10号的日记中提道:“我在很烦闷的时刻就用电话约韵玲出外……我觉她是很纯洁的,我很尊敬她!”[3]214进而在5月12日给钱韵玲的信中写到:“你很慷慨、很爽直地去帮助别人的困难!我非常感动,你这种善良的心,使我永远记着。”[3]324这些从相识相见到相交的过程使他们逐渐由远而近,并为进一步的交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发展阶段:冼星海和钱韵玲的相知相恋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了全面抗战的大本营,轰轰烈烈的全国抗战歌咏运动在武汉兴起,冼星海和钱韵玲都参加了这一运动,并开始有了密切的交往与合作。最初两人的交往,自音乐而起,也仅限于音乐,可以说是非常单纯的同事和朋友关系。冼星海是大名鼎鼎的音乐家,是钱韵玲眼里的导师、兄长。钱韵玲是音乐爱好者,又是冼星海室友钱远铎的亲妹妹,所以在冼星海眼里,钱韵玲只是个可爱的邻家小妹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冼星海在当时的演剧二队里也有一个心仪的姑娘。由于种种原因,冼星海对她的暗恋刚刚萌芽就夭折了,为此冼星海“非常失望”“非常痛苦”。正是在冼星海心情处于低谷的特殊时期,钱韵玲的天真可爱、温柔娴静、活泼聪慧、知书达礼,深深地嵌入了他的脑海,打动了他的心灵。而对于刚刚失去父亲的钱韵玲来说,善良正直、成熟稳重、才华横溢、质朴热情的冼星海就如同一棵大树,让她的内心产生了依恋感和安全感。虽然两人年龄上有较大差距,生活的境遇以及成长的环境也大不相同,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交往,反而因为他们在个性上的互补,使他们相互吸引。
1938年3月至4月,冼星海和钱韵玲共同参与电影《最后一滴血》的拍摄,在此期间有了更直接、更频繁、更深入的交往,他们多次相约游览东湖,在湖畔畅谈革命理想,交流音乐之道,在朝夕相处、合作共事的过程中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和理解。钱韵玲非常仰慕冼星海的音乐才华和奋斗精神,而冼星海也极为喜爱钱韵玲的天真活泼和善解人意。后来因导演金山与国民政府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发生冲突,这部电影中途流产,冼星海为电影配乐所谱写的曲子《江南三月》最后没能播出,但是他并没有为此感到愤懑和遗憾,而是满怀激动和欣喜,将这首充满着优美亲切、纯朴清新的民间乐调,与旨在抒发抗战妇女爱国深情的合唱曲,当作两人东湖之游的纪念赠送给了钱韵玲。以曲表意,以乐传情,正所谓“一切尽在不言中,一切尽在此曲中”,这也许是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表达爱意的一种特殊方式,也是最贴切、最有效的一种方式,对此,同为音乐人的钱韵玲对其中蕴含的深意了然于心并欣然接受。
钱韵玲与冼星海相爱的种子从此萌发,二者的感情急剧升温并发生了质的飞跃,进入到美好恋情的实际性阶段。1938年5月14日冼星海在日记中提到:“韵玲拿热水给我洗脚,拿靴子给我换!我觉得她心地太好。她又天真可爱,外表美又能处处表现出来,内心美更切实。我不禁很感动,甚至我要爱恋她起来!”[3]216如果说这还只是冼星海对钱韵玲单方面的爱慕和思念,那么5月30日冼星海和钱韵玲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情投意合、牵手连心,怀着浓浓的爱意度过了愉快的一天,在“维多利”看《袖里乾坤》,一起吃冰,一块谈笑,相依相伴。他在5月31日给钱韵玲的信中写到:“昨天晚上你给我很大的快慰,无形中使我忘却一天的劳苦,不知怎样我总觉得同你一块儿是有乐趣的”;“总之我觉得你的忧愁就是我的忧愁,你的快乐也即是我的快乐。我们虽然没有很久的交谊,我却明了你,除了尊敬你以外,我还想爱护你”;“韵玲,我很尊敬你,很爱你,我不想你有一点难过或痛苦存在心里”[3]326。这表明二人的关系实现了从友情到爱情的升华。
两人的相恋给冼星海带来极大的心理慰藉和精神快乐。他多次在日记中写道:“不知怎样,我这一月来都有韵玲的印象,而且是很深刻地印在我脑袋里!我喜欢她的沉静,又喜欢她的嬉笑,她的幽默,她圆圆的大眼睛和修长的黑发——但可怜我始终是一个炭头,还是一个不大理解爱的傻瓜”[4]134;“我委实很爱伴着她!……她可以令我向上,可以减少我许多痛苦”[3]218。由此人民音乐家的简单直率而又真挚的情感跃然纸上,为此他写了《野睡》《温静的绿情》《妹妹你是水》这三首歌预备赠与钱韵玲,而且与钱韵玲畅谈恋爱问题,讨论二人的将来和事业的发展。在钱韵玲的陪同下,冼星海上门拜访了她的母亲王德训及其他亲属,以自己的诚恳、率真、正直、上进,赢得了钱韵玲家人的一致认同,同时,冼星海通过写信向远在上海的母亲黄苏英介绍了钱韵玲的基本情况,得到了母亲的首肯和祝福。就像许多水到渠成的中国式爱情一样,相知相恋的两个人从爱情的原野走向了婚姻的殿堂。
1938年7月20日,33岁的冼星海和24岁的钱韵玲选择在当时武汉文化人聚会较多的普海春酒楼,举行了简单而又隆重的订婚仪式,出席订婚仪式的有冼星海的好友和同事,以及钱韵玲的亲属和好友,如国民党元老陈铭枢将军,《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时任“军政部第三厅”文艺处处长的田汉及其夫人——著名剧作家、作词家、女诗人安娥,从事抗战宣传的知名画家吴恒勤,钱韵玲的兄长钱远铎及其女友黄冰,还有钱韵玲的老师张慈云、王有佳等。在这个订婚仪式上,安娥担任司仪,陈铭枢和田汉分别发表演讲,对冼星海和钱韵玲的婚姻爱情给予了高度评价和美好祝福。在两人的婚庆典礼上,郭沫若还欣喜地说:“这对歌坛伴侣,他们的歌声,是抗战的歌声,是中华民族解放的歌声”。对这个甜蜜而浪漫的历史片段,2005年,正值冼星海诞辰100周年之际,冼星海和钱韵玲的共同挚友、92岁高龄的“历史见证人”黄冰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详细、清晰地描绘了其中的细节,向人们再现了冼星海和钱韵玲从相知到相恋的欢乐与浪漫。
三、成熟阶段:冼星海和钱韵玲的相随相伴
早在1937年10月,冼星海到武汉后就经常见到“抗大”“陕公”招生的广告,又见到一些延安来的青年,他们的刻苦、朝气和热情引起了冼星海的注意。在1938年3月他就读过《抗战中的陕北》,并在日记中写到:“中国现在是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向着堕落处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扬地”,“假如我还觉悟的话,我应该想到自己的现时责任和将来的前途”[3]211。1938年6月18日,日本下达了实施对汉作战的命令,战事紧迫,每个人都必须决定自己的去留。加之国民党政府内部出于党派之争,消极抗战,人为地限制“第三厅”的活动,尤其是对冼星海主持的抗战歌咏运动进行了排挤、压制和阻挠,这引起了冼星海的强烈不满,他期待可以有一个安心写歌曲的地方。
1938年9月,冼星海收到了一封来自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全体师生的邀请电报和院长沙可夫的亲笔聘书。“鲁艺”由毛泽东同志发起创办,其教育方针是:团结与培养文学艺术的专门人才,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这给正处于纠结苦恼和忧郁徘徊中的冼星海打开了一扇窗,让他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冼星海毅然决然地决定奔赴这个“追求真理的青年所热烈向往的地方”[2]。随后冼星海邀约钱韵玲外出讨论去陕北的问题,他满怀深情地对钱韵玲说:“你也该在这时代里去开辟你自己的路……我们到陕北去吧!那里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勇气,那里可以使我们更了解真正的爱,再去创立我们的事业和将来。”“我想到不久要到陕北的时候,那边给我们多么伟大的前途和希望!我也希望你一样地不和我分离,同在艰苦中奋斗,同在炮火中生长,使我们能够增强抗战力量,能够充实自己的生活和学识”[3]328,对此,钱韵玲表示强烈地支持,欣然同意与他一起奔赴延安。钱韵玲对冼星海的支持与信赖是对他爱的最好回应,她在《忆星海》中写道:“党在召唤,延安在召唤,这给星海多么巨大的支持和鼓舞啊!”[2]。钱韵玲的体贴给了冼星海奋勇前行的力量,于是1938年10月1日,他们奔向了去延安的红色之路。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他们以旅行结婚的名义离开武汉,辗转千里,在途中结成了伴侣,于11月3日顺利到达延安。冼星海在“鲁艺”音乐系担任教授,不久后出任系主任,同时在中国女子大学兼任音乐教员,钱韵玲则进入鲁艺音乐系高级研究班学习。由此,他们的婚姻和爱情翻开了新的篇章。
延安生活对他们来说既是革命理想的践行和崇高事业的拓新,同时也是巨大的挑战和严峻的考验。在武汉,他们生活吃穿不愁,还可以看电影、吃冰淇淋、游东湖。而延安地处大西北,自然条件恶劣,物质极为匮乏,尽管党中央为冼星海提供了当时全延安地区最高的薪水待遇,其月薪高达15元,相当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月薪的三倍之多,但很显然延安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平与繁华的大都市武汉不可同日而语。加之饮食习惯的差异、语言交流的不畅和亲情的隔离、战事的紧迫等,给他们的新生活带来了诸多的困难。冼星海在1938年11月20日的日记中写到:“他们在那轰炸之下,好像失了秩序一样,我们气也气不耐烦,就在山上的旧窑洞睡了!玲有点难过,但我还是沉默。因为在战时的生活是不免有点难过的,但我也以沉默对付环境,使我们练成有经验、有魄力的青年!”[3]23811月22日:“‘鲁艺’给我们住的是一个旧窑洞,每天我们都要跑上跑下,尤其早晚相当的麻烦”[3]238。但是这些困难并没有使他们抱怨或离开,在各级组织的关怀和甜蜜爱情的滋养下,他们在简单贫乏甚至清贫的家庭生活中体会到了浓浓的家庭温情和极大的生活乐趣。冼星海用日记记录了他们生活的点滴,1938年11月28日:“今天玲有点不舒服,因左边大牙发肿了!她在太阳底下晒着打绒衣”[3]240;1938年12月18日:“与玲往城内买了一点猪肉和咸菜、酒来烧东西食”[3]245;12月24日:“玲在早上替我洗了好几件衣服,她有点疲倦。我在写歌剧,她替我做许多事,的确帮助我很多”[3]247;1939年2月12日:“她的确是个家(庭)主妇,在事务方面特别帮忙,这样我才安心写我的新作”[3]256;1939年2月16日:“玲还是洗被单、洗衣裳,手已弄破了!我做面包给她食,弄鸡蛋给她慰劳”[3]257;1939年3月9日:“玲又替我抄写《中国锣鼓击法》”[3]261。从这些日记中我们不难想象到他们简单而甜美、幸福而惬意的生活状态。钱韵玲不仅在生活上与冼星海相随相伴,而且在音乐上与冼星海夫唱妇随,更是在思想上与冼星海同心同行。1939年8月他们唯一的女儿冼妮娜出生,从此人民音乐家舔犊情深、爱家顾家的一面更加体现了出来,他们相濡以沫、相互支持、相随相伴,一时在延安传为佳话。
四、升华阶段:冼星海和钱韵玲的相念相思
194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取得了抗战以来的极大胜利,恰逢此时,为了向全国乃至于全世界人们展现延安与抗日根据地生机勃勃的面貌和八路军的战斗生活,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居民坚持抗战的英勇事迹,鼓舞全国抗日居民的士气,著名导演袁牧之、八路军电影团团长、著名摄影家吴印咸等人历经两年合作拍摄了一部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这是延安的第一部纪录片,毛泽东对其十分重视,在电影配乐方面,袁牧之指名让当时在延安谱出《黄河大合唱》这一经典歌曲的冼星海为其配乐。鉴于当时苏联的设备先进,为了取得更好的影片效果,中央委派袁牧之与冼星海共同前往苏联完成配乐。冼星海怀着一腔为人民而音乐,为抗战而传唱的热情欣然接受任务。当时冼星海与钱韵玲唯一的女儿冼妮娜刚出生不到一年,正是牙牙学语之时,初为人母的钱韵玲正处在需要呵护与关怀的阶段。他们没有父母亲人在身边,也没有请保姆,完全靠自己打理衣食住行等家庭日常生活。为了支持冼星海的革命工作和音乐事业,钱韵玲毅然选择留在延安,一边参加学习一边照顾女儿,独自承担起“齐家”的责任。但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是与挚爱之人的生死别离。由于冼星海是被秘密派往苏联,于是便与妻子钱韵玲约好用黄训这个化名,黄是冼星海母亲的姓氏,训是钱韵玲母亲的名讳,这种独特的结合,蕴含着他们之间的深情厚意。冼星海去苏联并不顺利,他们辗转西安、兰州以防反动派的破坏,并寻机赴苏联。在漫长忐忑的路途中,对钱韵玲与女儿妮娜的思念使他的心灵得以慰藉,这在给钱韵玲的多封来往信件中明确表达过,1940年5月16日:“我常想念着你和妮娜,为着爱我们更应该加倍努力,我们要贡献一切所有,为民族解放、为实现我们的最高的理想。望你珍重,小心爱护妮娜。让我吻着你和她。”[3]3295月28日:“你近来读了多少书?身体好吗?我常想念你和妮娜!”[4]1679月5日:“妮娜周岁的时候西安下雨,我闷闷地想念她,又想及你和我过去的恋爱过程,使我勇气加增。”[3]350
虽然古人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但实际上天各一方的相思之苦是一种巨大的精神折磨,当然也是对于爱情婚姻的重大考验。冼星海到达苏联后不久,苏德战争爆发,冼星海在苏联的预期工作学习计划被迫中断。由于新疆军阀盛世才反共,以及国民党对边境的封锁,冼星海的回国之路由此阻断。从此在苏联、哈萨克斯坦、蒙古等多地开始了长达五年的漂泊。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加之身份的特殊性,冼星海常常处于失业、无援、贫病交加的状态。在异国他乡,他常常思念远在延安的妻子和女儿。直到1941年9月,他才有机会托人给钱韵玲带回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匆匆别后不觉已届两度寒暑,两地遥隔,能不依依?时为秋凉,尤望加紧珍重。”“妮娜在你殷勤爱护之下,必定很幸福地过她的生活,亦必比以前更天真活泼了。她这一副小面孔,我时常都怀念着她”,“我想再不久,我们可以见面团聚彼此交换一些过去的经验和意见,又是何等愉快的事呢。现在你更要安心工作,我回来时必定带给你许多安慰和愉快。”[1]这是冼星海在苏联期间写给钱韵玲的唯一的一封信,寒冷的气候、生活的困顿击垮了他的身体,但丝毫没有改变他对妻子和女儿的思念,他常常在工作之余,抱着小提琴,紧闭双眼,面对旁人的不解和疑问,他说:“我想中国,想妻子和女儿……”[5]29他甚至“把小提琴称之为女儿”,把房东家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有加。1945年10月积劳成疾的冼星海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医院溘然长逝,而钱韵玲对冼星海的思念在冼妮娜的身上得到体现,冼妮娜在《我的父亲冼星海》这篇文章中写到:“我在妈妈对爸爸的思念中渐渐长大。我从延安鲁艺师生的谈话中,知道父亲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是一个意志坚强、工作勤奋的人,是一个爱国爱家的人,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是一个真正把音乐作为终身追求,以至献身的人。我多么希望见到爸爸。”“我和妈妈天天都在盼望中度过那些望眼欲穿的日子。可是爸爸没有回来。当我看到鲁艺的师生们召开隆重的追悼会,很多人失声痛哭,我知道爸爸不会回来了,我再也听不到他唱歌了。”[6]25一个对亲生父亲没有记忆的孩子对父亲的崇拜与思念,定然来自母亲的潜移默化,来自于母亲对父亲的点滴思念。1975年,在冼星海逝世30年后,钱韵玲还专门致信毛泽东主席,并促成首都音乐界举办了一次盛况空前、激动人心的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的音乐会,在乐坛传为美谈。
五、结语
哲学家黑格尔曾说:“爱情是男女青年共同培育的一朵鲜花,倘若把它囿于‘个人私生活’的狭小天地,就要枯萎凋零,只有使它植根于‘为人类幸福而努力奋斗’的无限沃壤中才会盛开不衰。”冼星海与钱韵玲的爱情与婚姻是革命与音乐的结合,既有红色的印记,又有时代的特点。革命是贯穿其爱情与婚姻的主题,他们都崇尚革命、认同革命、投身革命,在革命的洪流中,树立了共同的革命信仰,培育了共同的革命情怀,最终成为了志同道合、情投意合的革命伴侣。而音乐又是贯通其爱情与婚姻的红线,他们拥有各自的音乐情节、秉持共同的音乐立场、追逐共同的音乐理想,在抗战音乐活动的浪潮中,彼此欣赏、互生情愫,从而结成琴瑟相谐、相濡以沫的艺术伉俪。从他们结合的过程来看,他们的爱情与婚姻经历了逐步演进、不断升华的过程,从相识相交的懵懂、相知相恋的憧憬、相随相伴的成熟,到相念相思的升华。他们的爱情与婚姻洗尽铅华、不畏艰难、休戚与共,走出了一条通往幸福的康庄大道。真正的爱情是共同成长、相互成就的,钱韵玲为冼星海洗衣、烧饭、画谱、抄曲,使冼星海没有生活的后顾之忧、潜心创作,成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在注重自我成长的同时,也不断为钱韵玲探寻成长之路,让她学习政治理论,教她谱曲创作,不断为她注入精神动力,使得钱韵玲成为了“音乐教育家”。冼星海与钱韵玲在生活上、音乐中、革命里,切实做到了志同道合、情投意合、互相关怀,为当代文艺工作者的爱情与婚姻提供了典型案例和示范引领。他们的爱情与婚姻启示着当代文艺工作者在爱情与婚姻的道路上应该秉承和恪守初心,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和各种各样的诱惑中牢牢把握爱情的本质和婚姻的真谛,自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爱情观、婚姻观引领和规约自己的情感世界,始终保持坦诚相待、信守承诺、担当责任、相互包容,为当代文艺发展、艺术精进、社会和谐不断助力,谱写当代文艺工作者爱情与婚姻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