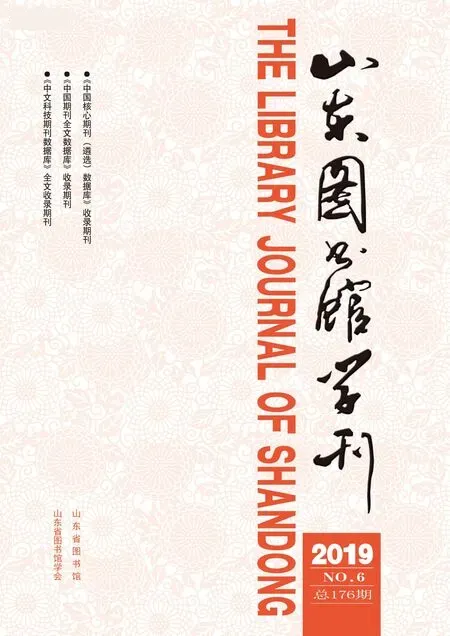“觇文化之变迁,知世运之迁嬗”
——《方志学大家吴宗慈》的叙述脉络及特点
石 莹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图书馆,江苏南京 210013)
“方志”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周礼·地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周礼·春官》又载:“外史掌四方之志。”顾名思义,“方志”即地方志书。原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方志学专家仓修良认为方志是“介于史地之间的一种边缘学科”,[1]总体属于历史学范畴,具有地理性,是记录方域情况的综合性著作。中国新方志首倡者之一、原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刘纬毅则认为方志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即方域志,广义包括“全国性的总志和各门类的专志”。[2]由于涵盖甚广、门类众多,自然产生了以方志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即方志学。学界对于方志的发展分期大同小异,但公认清代为鼎盛期,民国则为嬗变期。清末民初,方志修撰理论多有变革,方志学理论体系也初见规模。
此时期,全国各地先后修成不少志书,其中江西省以吴宗慈(1879-1951)《庐山志》《庐山续志》及其主持修撰的《江西通志稿》为著。除了三部志书,吴宗慈还撰写了最早的方志理论专题文章,著有《江西全省方志考略》等,成就斐然。然而,对于这位民国的历史学家、方志学大家,学界的相关研究并不算多。并无专著,相关论文也篇数寥寥,主要内容集中在吴宗慈方志理论或者某部志书的编纂故事。其中《吴宗慈与〈江西通志稿〉》较为别致,其作者——已故江西省博物馆研究员陈柏泉为当时“江西通志稿整理组”负责人,因此本文对《江西通志稿》的整理出版工作叙述详细,并论及当代学者对稿本的修订内容和评价,十分具有参考价值。[3]另有学位论文《社会变迁与知识分子的探索——以吴宗慈为例》,是少有的以吴宗慈个人生平和思想转变为研究内容的成果。[4]
因此,《方志学大家吴宗慈》的出版,意义非凡。本书著者江西省图书馆副馆长黄俊女士,长期从事江西传统文化和地方文献的发掘、保护工作,深谙江西风土掌故。《方志学大家吴宗慈》一书,对吴宗慈的生平及学术成就做了详细考证与论述,既丰富了吴宗慈的相关研究,也为江西方志研究添了一笔重彩。
1 时代变迁与个人际遇
本书分为三章,包括“生平”“庐山两志”和“《江西通志稿》编纂与特点”。全书结构简洁明了,但内容充实丰富。“生平”一章中,作者对吴宗慈的生平做了详尽考察,以时间为线索,分阶段论述,为读者完整展现了吴宗慈的人生经历、思想转变——如何从一个出身官宦世家、接受传统儒家教育的文人,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方志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一生所历,大致包括求学、革命、参政、实业、教育、修史(方志),所涉领域极为丰富,但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救国图强。本书关于其生平的论述,虽然是以事迹为主,但核心还是吴宗慈的人格塑造与思想形成。
时维清末,国家飘摇,局势动荡,同时在经世致用思想重新兴起、西学东渐思潮的影响下,一大批文人学士为救亡图存,纷纷走上了探索救国、强国之法的道路。本书在论述吴宗慈生平时,十分注重时局大环境的叙写,并且关注社会、思想环境与吴宗慈个人思想的联系。对吴宗慈一生活动与思想轨迹的介绍以时间为线索,可说是一种纵向视角,那么将每一阶段的吴氏个人生活与时事结合的论述,则是横向视角,这是本书的一大特点。这种横向展开的材料取用分析,能够将主题人物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牢牢结合在一起,不仅使传记人物形象更加生动、血肉丰满,不再是孤立的人物研究,更重要的是形成一种时局与个人的互相参照,既能参考历史背景来加深对吴宗慈思想、行为的理解,又能以小见大,从吴氏个人身上窥见当时的社会之变、历史潮流。例如在有关“南通求学”的部分,作者对吴宗慈就学的南通师范学堂做了背景陈述,简要介绍近代著名政治活动家、实业家、教育家张謇(1853-1926)创办南通师范学堂的经过,以及张謇和该校的办学理念。[5]而在关于吴宗慈置身报界的“报界搏击”章节部分中,对于吴投稿的《警钟日报》、创办的《晓钟日报》、执笔的《民呼报》、接管的《江西民报》等,本书对报刊情况做了简要说明,将重点放在了报纸影响上。[6]作者非常善于抓住重点,并通过详略得当、点面结合的写法,使关于吴氏生平的叙写,阶段性非常明显,但同时不失连续性,不同时期的活动与思想特征之间过渡自然,水到渠成。
本书书后附有吴宗慈年谱,写法亦是别具一格。一般人物年谱以人物为中心,所有的叙述紧密围绕年谱主人,通行格式为某某年此人做了某某事。对于研究该人生平十分方便,但未免失之意趣,并且一定程度上缺乏与大背景的关联性。本书所附吴宗慈年谱,除了吴宗慈本人行迹这部分传统内容,还有同时期重大历史事件或者历史人物活动,即上文所说的横向视角。例如年谱中出现了晚清维新四公子之一陈三立(1853-1937)的部分生平事迹,乍看未免令人奇怪,但若看完全书便知道,陈三立乃是重修《庐山志》的创议者并为之作序,并且对修撰体例提出了意见。又如年谱中提及孙中山(1866-1925),乃是因为孙中山是吴宗慈极为尊敬的革命领袖,并且吴氏创办《新民国报》、撰写《中华民国宪法史》等革命活动与孙中山有很大关系。因此细细品之年谱,吴宗慈的生平脉络与其所以然,跃然纸上。
2 旧学与今用
正如书中所评价,吴宗慈的方志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清末民初,是新旧思想碰撞、交织的时期。实学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思想潮流,开教化、启民智以救国是各界爱国志士的共同期冀。文士治学,也多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取其精华,改造向新。
方志学随方志诞生而起,是“研究方志的修纂宗旨、体例与内容及其特有的运动形态、特征和规律性的学科”。[7]清代是方志修纂的鼎盛时期,也是方志理论研究正式成为一门学问,迅速发展并走向系统化的重要时期。清初顾炎武(1613-1682)、卫周祚(1611-1675)、方苞(1668-1749)等人作文阐述了一些修志主张,多见于各种志书序作。[8]清中期,乾嘉学派是学界的绝对主流,其长于考据的学风也影响了方志学理论。地理学派的戴震(1724-1777)、洪亮吉(1746-1809)、孙星衍(1753-1818)等人便认为地方志主要内容是考证地理沿革。而同时期的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章学诚(1738-1801),素来秉持“六经皆史”的思想,因此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文献派,亦称史志学派,更重视方志的史学性质。本质上这是典型的浙东学派治学风格,偏重史学研究、“经世致用”。章学诚是方志学的奠基人。他建立了初具规模的方志编纂学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一,志属史体;二,“三书四体”的撰写体例;三,方志辩体,即界定各类方志撰写范围与界限;四,设立志科;五,遵循史法;六,重视文献。[9]
到了民国嬗变阶段,方志学修撰有几点新变化。主要是民本思想的确立、经济类目比重提升、突出反帝爱国思想和思想解放的需求、新增近代西方科学体系下的材料记录等方面。[10]民国十八年(1929)时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的蒋梦麟提出《方志新体例及进行办法案》,主张废旧体,以现代立场修撰新方志,核心要求有“三重”,即重现状、重实用和重物质。[11]同年南京政府内务部颁布《修志事例概要》22条,不少规定也反映了方志修撰的新趋势。
自清代章学诚始,至民国,方志学理论有了长足进步,但仍有学者认为绝大多数学者的论述还是以方志学修撰为阐发基点,从学科角度评价,直到傅振伦(1906-1999)的《中国方志学通论》,方志学体系方初见规模。[12]但吴宗慈在方志学发展中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吴宗慈的方志思想,有着非常清晰的思想脉络传承,又鲜明地体现了民国方志与方志理论的新与变。他对方志学性质的定义是“记录地理、历史、民族、社会、经济类实学内容的综合体”。[13]他继承了章学诚“志属史体”的认知,又提出自己的“实学”定义。吴氏“实学”与章氏“史学”可以说大有不同,也可说本质上并无分歧,乃是经世致用思想呼应时代需求,进步发展的体现。章氏时代以史为裁,史学的视角与观点,对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等方面影响匪浅,而到了民国,民智民生成为社会的重要议题,方志修撰的出发点与侧重点自然又有所变化。但“实用”,一直是贯穿方志学理论的指向标,均不出“适今日之用”。[14]
章氏方志学思想,可谓是吴宗慈方志理论的底本。他吸收了章氏对方志修撰体例的构建,在此基础上进行删改和发展。在篇目设计上,“实用”是他增删改定的标准,科学性则是其最为进步、最顺应时代潮流的思想亮点。本书对于吴氏方志体例理论的研究十分充分,不过分散在第一章“方志编纂理论”部分和第二、三章对庐山两志和《江西通志稿》的分别论述中。本书在提炼吴氏理论之余,辅以丰富的例证和对比,解释详略得当,恰到好处,既满足了专业学人,又照顾了普通读者。例如编修《江西通志稿》时,吴宗慈主张加入大地内层构造的描写,就是一个相当具有西方现代科学性的做法。又如吴宗慈对“星野”“祥异”条目的处理,[15]其背后实际上反映出学界政治文化思想从中国传统到近现代的一个转变,而在作者的介绍下,非专业读者也能窥知一二。
3 对江西省方志研究的补充
民国六年(1917)北洋政府内务部和教育部就通令各地修志,但响应者寥寥。《修志事例概要》22条颁布至1937年七七事变这一时期被认为是民国修志黄金时期,共编纂了600多种志书。[16]通常所见的方志学研究著作中,黄炎培(1878-1965)所修《川沙县志》作为民国时期佳志代表,常受赞誉。虽然吴宗慈的《庐山志》完成于1933年,但江西省的新方志编纂工作起步较晚,江西省志筹备委员会1940年才成立,41年更名江西通志馆。根据统计,民国时期江西修撰的方志数量只有25部,对于一个地域广博、文化悠久的大省而言,实在不多。[17]
本书第二、三章讲述了吴宗慈编修庐山两志与《江西通志稿》的始末,并对三部志书进行了详细评述。第二章论述了《庐山志》和《庐山续志稿》,涉及两志的编纂初衷、思想、体例与特点,是全书最为详细、连续性最强、体量最大的部分。作者做了大量文献调研与对比,全面细致地梳理了庐山两志的修撰特点,在此不赘述。其中吴宗慈对于庐山“地质”部分内容的编选,和首创“山政”纲目,最能体现他“以实用为归”的思想主旨。[18]同时可以看出,《庐山志》与《庐山续志稿》虽然是山水志,但因庐山的特殊地位及年代原因,庐山两志的政治意味较其他山水志更为浓厚,尤其是续志的内容,有着非常深刻的时代烙印。第三章对于《江西通志稿》的编纂与特点,作者也进行了详细论述,但由于通志稿本身并未编成,直到1985年才由江西省博物馆整理出版,因此关于此志的研究篇幅比较有限。
本书虽以《方志学大家吴宗慈》为名,详述了吴宗慈一生际遇、思想转变和学术成果,但关于他所修三部志书的评述占了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因此本书实际上应视为吴宗慈及其学术成果的研究专著,同时也是一项江西省方志研究、江西地方文献保护工作的优秀成果。学界对于江西省志的关注研究并不多,本书填补了这一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