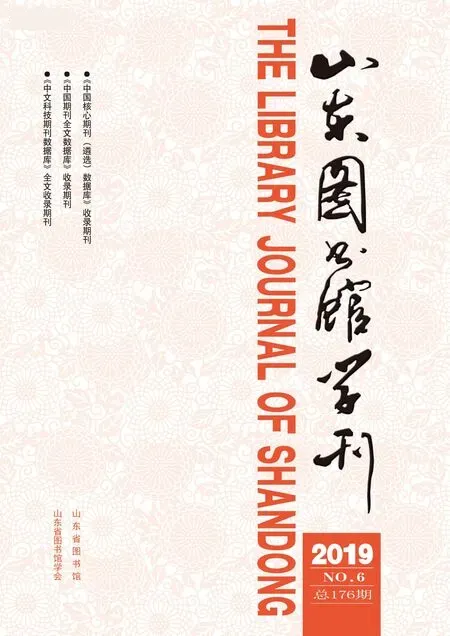矢志不移创辉煌
文榕生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北京 100080)
以历史悠久、馆藏宏富著称的山东省图书馆是中国十大图书馆之一,今适逢建馆110周年,笔者谨以老图书馆员与作者之双重身份特致以热烈庆贺。尤其是笔者少小离家走向社会半个世纪,近40年来与齐鲁大地结下不解之缘,更是受惠于孔孟故里人颇多,愿借此机会将部分雪泥鸿爪公之于众,由衷地表达感激之情,并与大家分享。
1 登临泰山的感悟
泰山乃华夏五岳之首,孔子曾感慨“登泰山而小天下”,司马迁也将人的生死大义以鸿毛、泰山相喻;毛泽东更是在风华正茂的青春时代(1920年)登临泰山,感受它的雄浑……
久怀对泰山的向往,在“旅游热”尚未兴起的1980年暑假初,我们意气相投的同窗好友便结伴连夜登泰山。当时,泰山还是无围墙的旅游胜地,没有缆车,台阶错落不齐,伴随北方罕见的萤火虫闪烁,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疾行到南天门下的“十八盘”,东方已显现鱼肚白。大家又饥又渴,轻装前行的同学手持水壶引逗,最终手脚并用,勉强在日出前赶到了日观峰的拱北石附近。幸运的是我们目睹一轮红日从云海中喷薄跃出,万道霞光映红东方,也在瞬间染红了我们周边与近处的地貌景观,如此壮观的场景与我之前看过的一部纪录片相仿。面对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所有的辛苦一扫而光。
太阳冉冉升起,这时我们才发现由于急着赶路,好几个人不知何时拉胯了,下山时,只好一瘸一拐地移动。待回到“十八盘”,只见那些负重百八十斤的挑夫们步履不疾不徐,稳稳地向上攀登着。捶着隐隐作痛的双腿,看着挑夫们似曾相识的步态,我不禁想起12年前在农村插队的事儿来。
那是1968年12月6日,我们北京知青(当时我尚未成年)来到太行山西坡的小山村——山西省榆次县黄彩公社(1)经过数次分、合、改,现为榆次市晋中区庄子乡。杨壁村插队。我们第一次挣工分的劳动是冒雪到离村七八里外的山沟扛茭棍(高粱杆),结果知青们皆不敌与我们同龄的带工村民,尽管带工村民要在我们全都妥帖上路后才能起身,尽管我们负重皆不及带工村民,尽管知青中不乏身强力壮者。事后,我们才体会到带工村民虽然起步晚,却后来者居上,主要是他一直迈着沉稳的脚步,不慌不忙地匀速行进;确如俗话说:远路无轻载,路远不胜金;不怕慢,就怕站。
之后,我们同登泰山的伙伴们对胡耀邦讲话:“好比登泰山,已经到了‘中天门’,前面还有一段要费很大气力的路——三个‘十八盘’。要爬过这一段路,才能达到‘南天门’。由‘南天门’再往前,就可以比较顺利地向高峰‘玉皇顶’挺进了,到了那里就好比我们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任务”[1]倍感亲切,可见胡耀邦确有亲身经历。后知胡耀邦1981年初上泰山登十八盘时,谢绝人们的搀扶,全凭自身力量登上。当他站在南天门前,转过身来,俯视着险峻的十八盘说:“如果有人爬到这儿,别人问他累不累,他要说不累,那就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大家到达山顶时,太阳西沉,胡耀邦站在极顶眺望,久久未能离去(2)胡耀邦的三次山东之行.http://www.qingdaonews.com/gb/content/2005-12/19/content_5753184.htm。
随着中天门到南天门修建缆车,不少人不一定亲身体验登十八盘,而挑夫负重行走的风景也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是他们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永驻我心中,并一直激励着自己科研探索。
2 90载,搭建学术研究平台的急先锋
笔者撰写此文查找资料,却意外发现《山东图书馆学刊》的历史应延伸到90年前。
1931年刊出的《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下文简称《省立》)由“酷爱读书”的国民党元老戴传贤(季陶)题写刊名,当是数度主政山东省立图书馆的著名图书馆学家、版本目录学家、考古学家王献唐先生等大手笔之一。
《省立》共500余页,与现全年各期合订本相当,由多种纸张印制,有的已泛黄发脆一碰就碎。现《省立》已叫卖到1000-2500元/本,显然被视为文物。笔者虽无暇仔细考究《省立》,但仅浏览其封面、《引言》《总目》等,便感到其确实珍贵,内含颇多重要信息,值得深挖。
《省立》的书影显示:不仅刊名中含“季刊”,而且标明“第一集第一期”,可见其刊期原计划是按“季”出版,达到4期/年。
冠于刊首的《引言》称:
现代中国图书馆学,尚在一初期运动时期。旧日之成规,既不尽适用,欧美之方式,又未便从同。如何而能斟酌尽善,中外适宜,此应共同研求者一。
中华民族四千年来自筑之宝库——图书——如开矿然;日日掘之,愈掘而宝藏愈富,迄至现在,尚不能测其究极。吾人对此民族精神寄托之图书,不能以保藏二字,了卸责任。更当荟萃全力,继续发掘,以发掘之所得,公诸世界,此应共同努力者二。
基于以上情形,本馆同人,决意于此两重使命之下,发行本刊;期以自身工作之收获,在此刊物上一一表襮之。
同人工作,除图书学及图书馆学外,尤注意搜集发扬全省之图书文献。本馆既为山东公共藏书总汇,应以所处地位,负其地位上搜集发扬之责任。其地处相近,其声闻想通,调查蒐讨,亦易于为力,且可免除他省人士展转钩致之困难,而得所稽考。
本刊付印,初在民国十九年六月。中更政变,稿件散落,自忖无分与图书馆界同人及阅者相见;今见矣,如不以其谫陋,进而教之,于流离琐尾之余,所获固已多矣!
此中披露的一些图书馆学信息有:
●“中国现代图书馆学”其时尚在初建阶段。中国的现代公立图书馆肇始于19世纪末,山东省图书馆建馆于1909年。故在学术创建之初,旧式图书馆之成规不尽适用,西方的图书馆之新规又不便照搬之际,确实应共研“斟酌尽善,中外适宜”之良策,实有必要设立研讨图书馆学的平台。
●图书馆“不能以保藏二字,了卸责任”。如何妥善处理“藏”与“用”的关系,一直是困扰图书馆员与读者的难题。笔者因长期从事学术研究,故具有图书馆员与读者双重身份,对于所提出的“不能以保藏二字,了卸责任”深有体会。因为时至今日,在复制、转录技术日新月异之际,仍有不少大馆、老馆实际上皆有相当数量半个多世纪前的文献秘不示人。很有必要统筹规划,共商良策,改善“藏”与“用”的矛盾。
●“更当荟萃全力,继续发掘,以发掘之所得,公诸世界”。窃以为对此还有更深层含义。尽管现还缺乏实证表明中华民族的古文明最为久远,但却是全球唯一没有中断文献记载的文明古国,使得3600年来文字记载、博大精深的古籍中的瑰宝应通过我们的发掘(3)尽管这些主要是古人记载,但其完全可以与自然界的遗存相互印证。,将世人可共享的成果公诸于世。
●“尤注意搜集发扬全省之图书文献”。作为省图书馆,当处于本省文献保障体系的至高层面,方显出其特色并发挥作用。山东省图书馆数十年来将此作为办馆方针之一并践行之,被评为国家一级图书馆也就水到渠成。
●《省立》初印在1930年。《引言》虽仅“本刊付印,初在民国十九年六月。中更政变,稿件散落”寥寥数语,却传达出:《省立》的正式发刊本应提前1年;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时局变化使图书馆业务与学术研究更为艰辛。王献唐先生又一次在危难时期“再四筹思,乃决意留馆,力之所及,决为山东全省保护此一线书脉。”
《省立》虽仅出版了2期(第2期是1936年出版),实在是迫不得已(5)停办原因既有资金方面的问题,也有王献唐因个人事务太忙而无暇顾及等原因,还有政局的动荡。,但在图书馆史、出版史与学术史等方面皆有极高价值与地位。尤其是1981年创刊的《山东图书馆季刊》(下文简称《季刊》),2016年改称《山东图书馆学刊》(扩展为双月刊;下文简称《学刊》),皆保持了刊登理论联系实践的图书馆学与介绍馆藏珍本、善本、抄本书影等特色。笔者建议将《学刊》创刊时间延伸到在动荡年代首创刊物的1931年,甚至可提前为1930年,此举亦是纪念先辈的开创之功。
《季刊》的创刊号是在1979年《山东省图书馆学会会刊(成立专号)》之后,于1981年问世的。但是直到1988年第4期(总第30期)才公布编辑部成员名单。我们注意到《季刊》编辑部人员变动较大,但从《季刊》直至《学刊》的栏目、风格、选稿等保持稳定,可称与《省立》一脉相承。
3 25载,助力探究图书馆学真谛
笔者虽是1978年考取晋中师范专科学校(现为晋中学院),却塞翁失马,毕业早77届本科生半年(6)当时北京高校一再扩招,没有专科;而我们这些年龄偏大的知青在外地,不少人不得已只能上大专。77届实际上是冬季入学,而78届又改为秋季入学,前者推后,后者提前,故实际上只差半年。,在“文革”后普遍出现人才缺乏/断层之际,高校图书馆近水楼台留住了一些毕业生加强图书馆业务工作。笔者先是在图书馆从事多年业务工作,又到兰州大学图书馆学系进修一年后才开始撰写论文,1986年即在2家省级图书馆学刊物上各发表处女作一篇。当山西省首次高校图书馆职称评定时,则因发表论文较多,破格获得第一批馆员职称。迄今,笔者已在国内图书情报界绝大部分刊物上发表200余篇论文;而从1996年到2012年,在《季刊》约发表13篇作品,乃笔者发文较多的刊物之一。很重要的一点,是编辑老师不仅甘为他人做嫁衣,而且业务精湛,更对作者满腔热情。2007年,笔者还收到赵炳武主编的致谢与再邀稿专函。
在多年的“市场经济”熏陶下,赵公明挂帅,人们常感叹“士风日下、人心不古”。诚然,把握良好职业操守的编辑仍有,包括《季刊》编辑部各位老师。笔者多年因发表作品常与编辑打交道,更有深刻感受。不少作者面对学位、职称、职务等升迁,不得不依赖编辑的青睐;而后者中一些人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们或者明确通知作者录用,却又忘却此事,作者数次追问,却避而不答;即使作者3个月后询问文稿时,则以打不开文稿为由搪塞;前任主编虔诚发聘书征稿使刊物刚有起色,换届后突然“变脸”,刊物质量再度下降;或者事前约稿,后又毁约;或者先收取各种名目费用再说;或者要求在文稿中夹带其私货,否则就推翻之前的数次用稿通知……各种怪现象不一而足。好在现发表作品并非“自古华山一条路”,只要文稿质量过硬,面世并非绝对无门。
最近笔者接触到“参考文献”著录问题,看到“GB/T 7714”的数次修订似缺乏理性根据,进而造成使用者实际标注失当(有些经我说明后,得到补救),就是一些与之商榷文章本身也存在领悟偏差……因笔者曾对此有过研究并发表系列文章[2-4],以为有必要对此发声。又鉴于目前发文收费是多数刊物的“惯例”,有的还是天文数字,而我们没有任何经费资助,费力写出文章,难道还要倒交不菲的版面费、审稿费等?
《学刊》编辑部明确回复不收费用后,我才正式着手再度认真研究,起草。
经查,认真商榷“GB/T 7714”的文章寥寥,而笔者《新版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求疵》文稿已超2万言(当没有隔靴搔痒之言)。笔者惴惴不安地将文稿发送《学刊》,即第一时间获悉录用。
总之,课堂提问包含着许多玄机,它既要讲究科学性,又要讲究艺术性,教师要潜心研究,不断探索,注意提问的多样性、艺术性,把握提问的时机,给学生留有积极思维的空间和时间,实现师生互动,生生互动,让课堂变得生动活泼,就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4 大师扶持,攀登科学高峰
先父文焕然研究员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创建者之一、开创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的著名学者。谭其骧院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这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既缺乏现成的经验,又没有捷径可走,取得的成果也不一定在短期内得到学术界的承认和肯定,所以具备了这两方面条件的学者而又愿意选择这一研究方向的,更是屈指可数了。[5]”父亲于1986年在科研岗位上倒下,未竟的艰巨工作只能由我承担(7)研究者屈指可数,亦见有浅尝辄止者;尤其是我只能属于体制外的个人行为。这也是笔者对王献唐提及“发掘”文献深意的领悟;也是退休后放下图书馆学研究,全身心投入此方面研究之故。,并得到百余位各相关学科的专家支持与帮助,其中就有5位山东籍院士。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1911-2013)院士,恩县(现德州平原县恩城镇)人。侯老领衔鼎力推荐,促成先父的首部遗作《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首获出版基金在1995年面世,得到国内外学界与出版、图书馆等各界好评,今年将第3次出版;他还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植物地理》中提到的:“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也进行了不少研究,如文焕然的《试论七、八千年来中国森林的分布及其变迁》。”更为难得的是,30年前在侯宅前由夫人张玮瑛先生亲摄侯老与我的合影。
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1915-1991)院士,1989年4月8日亲笔给笔者复信,明确表示他乐于为先父的遗作出版推荐。
著名哲学家、佛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原馆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任继愈(1916-2009),平原县人。2008年4月24日,任老以《中华大典》主编身份召见我们《中华大典·生物典·动物分典》主编与编委,经申述,任老完全同意我们力主采用最早记载野生动物的“甲骨文”与古籍中记载野生动物分布的“方志”要求。
著名生态学和森林学家李文华(1932-)院士,广饶县人。李老不仅在1998年与贾兰坡院士共同就我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鼎力推荐(8)此申报未获成功,乃体制外研究者之困难实例。,后又欣然为拙作《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续)》[6]作序并出席“文榕生《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续)》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做了感人的发言(9)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新作:“文榕生《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续)》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实录.https://mp.weixin.qq.com/s/B7ed8tLy_07V_kIzhthQgw。
著名古脊椎动物学家邱占祥(1936-)院士,青岛市北区人。10年前,笔者撰写专著《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7]见到邱老《虎年谈虎的起源》中有古中华虎头骨的图片[8],为解来源而贸然与邱老联系。谁知仅凭一个陌生的电话,邱老便委托其学生刘金毅(现为研究员、标本馆馆长)将高清古中华虎头骨图片发来。笔者再撰《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续)》遇到难题向邱老请教,他皆拨冗耐心作答,并亲自为该书推荐,其中提到:
拟出版的续集是一部对我国最重要的常见大型珍稀动物的史前、历史时期及现代分布资料的全面而深入的整理,其中对于历史时期部分的工作是该书的核心。由于我国得天独厚地具有近五千年的文字记录的历史,这一部分的资料的整理和正确诠释在全世界来说都是绝无仅有的。
待第一批《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续)》到京,因450万字的3卷精装书太重,我专程给几位老先生送上门。邱老抱歉地说,他正忙碌所负责的多单位合作大型著作出版前工作,分身无术。早就听说年逾八旬的邱老仍然坚持每天到办公室工作,还不时出野外,值得我辈学习,我们就在邱老工作室合影留念。
5 各方鼎力,成就“中华绝学”
2代人经历70余年前仆后继的传承与锲而不舍,今天我们可以说唯中国独有的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成果已初现端倪:千余万字的大部头精品著作——《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中国古代野生动物地理分布》[9]《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续)》《历史时期中国气候变化》[10]《历史时期中国森林地理分布与变迁》[11]与《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地图集》[12]等皆由首席编辑张波编审操刀,4度获得国家出版基金眷顾,由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独家出版。我们坚信,历史已然用浓墨重彩记录下他们的功绩,学术界不会忘记山东科技社矢志不渝,扶持科技传播之举。
在《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续)》“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上,专家们认为:“这是一部前无古人的巨作”,“可以代表当代该领域的水平,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具有利用和再创新的价值”,“还一致对文榕生先生长期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披襟斩棘、刻苦钻研、锲而不舍的治学态度表示高度赞扬和钦佩”,“各位院士、专家也提出了自己对我国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尤其是历史植物地理学与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忧思: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我国这两门分支学科的研究后继乏人,濒于绝境,希望有关方面能够重视这个问题,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培养新人,使这两门可以说目前唯中国独有的分支学科得以延续和发展”(10)文榕生《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续)》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在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举行.http://www.las.cas.cn/xwzx/zhxw/201811/t20181128_5193904.html;勿使其成为“中华绝学”[13,14]。
世间万物相互依存,科技成果也不例外。世人对作者与编辑,往往皆以作品的成败而论,但二者的关系用唇齿相依更为恰当。离开作者的原创作品,对编辑而言,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没有编辑在幕后对原稿的精雕细琢,修饰设计,再好的作品往往只是璞玉。
6 结语
人们获得成功的秘诀固然不尽一致,窃以为其中之一多有矢志不移、锲而不舍。我们回眸,无论是山东省图书馆110年今终成辉煌,还是《学刊》90载的桃李不言,或笔者在图书馆学与历史自然地理学方面的探讨体会(11)二者皆离不开图书馆:图书馆学研究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无论是其理论的产生,还是最后检验相关理论,皆需要通过图书馆的工作实践。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更需要存在于图书馆的浩如烟海、博大精深的古文献支撑。,概莫能外。
上文所记述的雪泥鸿爪,也仅是笔者从齐鲁大地上获得的雪中送炭,刻骨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