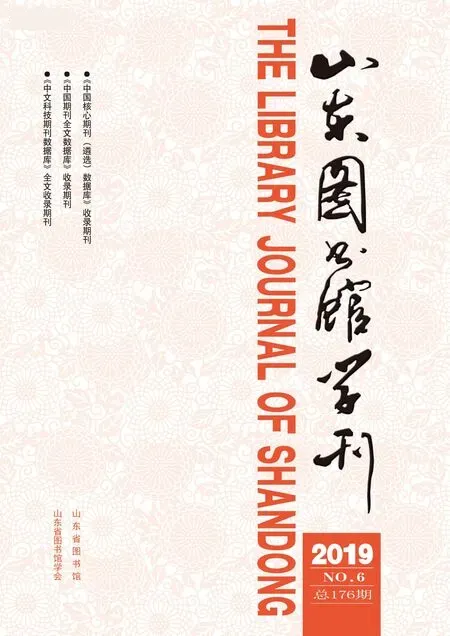“识力横绝”的临清学者*
——吴秋辉生平与学术
刘迎秋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济南 250013)
1 前言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风雨飘摇,为“数千年来一大变局”[1],学术的发展脱离不了社会,学者的思想亦脱离不了现实,故梁启超云:“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2]在这变局中,对传统学术的反思,对西学借鉴,以及新的出土材料的发现,使得清末民初的学术有了很多独特的特点,对传统经学治学思想和治学方法的全面质疑成为了一个学术主流。作为清末民初山东重要文字学家与经学家之一的吴秋辉,深深地被这些新思潮所影响,对于过去的一切学者、权威、论断皆持有怀疑态度,从而写出了大量的批判性研究经学的著作,有一定的时代代表性。但同时,他质疑和批评传统经学研究的目的正是为了挖掘传统经学的真正内涵,使经学研究摆脱旧的窠臼,并重新为学界所重视。
吴秋辉在济南一代是一位较有名的学者,康有为[3]、梁启超、胡适[4]、傅斯年[5]等学者均略晓其名,梁启超更是曾称赞他道:“先生识力横绝一世,而所凭藉之工具极笃实,二千年学术大革命事业,决能成就,启超深信不疑。”[6]但由于偏居济南一隅且晚年穷困交加,其多数著作直到最近几年才得以陆续出版,致使今人知之者甚少。随着其著作的出版,学界已经开始有人关注吴秋辉先生的学术成就,如沈阳师范大学许晓娜硕士论文《〈齐鲁方言存古〉和〈渔古碎金〉民俗语汇研究》(2013)对其方言学著作进行考释,东北师范大学曹伟芳硕士论文《吴秋辉及其〈诗经〉研究》(2015)对其最重要的著作《说经》进行研究。另有部分学者撰有介绍性的文章,如80年代《文吏哲》曾刊有吴秋辉《桃之夭夭》考,文中认为“桃之夭夭”应为“桃之天夭”,立论新奇,朱广祁先生很快撰文予以探讨质疑[7];又吴鸿春[8]和唐莉[9]都曾在自己的论文中引用吴秋辉关于“雎鸠即鸿雁”的考证;何九盈教授[10]曾引用过一段吴秋辉关于“契即仓颉”的考证,并予以肯定;王明波、梁兆斌、马景瑞等学者则从其“怪狂”性格和奇异言行入手进行介绍,已不属于学术研究范畴。由此可见,目前整体上对吴秋辉深入研究者和研究成果较少。孟子曰:“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11]因此,对吴秋辉生平际遇与学术之路的深入研究,可为我们提供一个观察清末民初传统经学复杂性变迁的新例证。
2 生平:人生坎坷、性格怪傲
吴秋辉,名桂华,字秋辉,号“侘傺生”,室名侘傺轩,取自《离骚》“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12]以表一生失志穷困之义。吴秋辉于1877年9月15日生在山东临清考棚街一小客栈家庭中,少时家中薄有家产,因此得以受到良好的私塾教育。自幼天资聪慧,专好诗词歌赋等,十余岁即闻名临清,但身体一直欠佳,至18岁废学卧病,习八股并参加乡试,不中;时逢中国甲午之战中惨败于日本,康有为、梁启超等有识之士宣传变法、建立新学,吴秋辉遂毅然于1901年入新学,于山东大学堂(1903年附设师范学校,后独立)学习数理,以求实业兴国。在校学习凡八年,除习数理课程外,于经史子集等书无所不读,并著有《算法正宗》《算法易解》等通俗读物。1909年,学满毕业后,赴北京考取了官费留日资格,但因左目有疾被以“有碍国际观瞻”为由取消了资格,不得已而返回故居临清执教,自此以“侘傺生”自称。1912年,民国成立,吴秋辉复返济南,任《山东齐民报》主笔,针砭时事、沉毅敢言。后见时事日非,便逐渐消极,日以饮酒作诗聊以自慰,作《傺轩诗词》两卷。自1917年开始,吴秋辉致力于经史文化研究,先治《楚辞》,著《楚辞古文考正》。1919年,再赴北京历任《民意报》《民主报》等主编,始著《学文溯源》及《说诗解颐录》,1921年,吴秋辉复离京返济,于大明湖南岸赁一小楼,专任《说经》一书写作。1924年春,山东国学研究社成立,吴秋辉应邀主讲经学,后又任山东第一师范学校教员主讲诗词,学识高深,见解独到,于前贤所言从不轻易苟同,在师生间引起不小轰动,在当时的济南学界亦颇有名气,同栾调甫、张默生、解子义等学者交往密切。1927年5月28日,吴秋辉病逝于济南,年51岁。
吴秋辉一生命运坎坷,生前贫困潦倒,郁不得志,不止属于他一个人的悲哀,也是乱世中多数人的悲哀,如其《述愤》一诗所言:“穷年倦行役,况复逼中年。世事竟如此,吾心胡惄然。荒城蛇自斗,败壁鼠尤穿。大错何人铸,空思西狩前。”[13]家庭上,生有六女,而唯一的儿子一岁时因故夭折,此其一生最痛之事,并曾赋诗哀思亡子“生小忍相离,别来又几时。人皆怜幼子,我自爱仟儿。计日未周岁,何年解颂诗。家贫有慈母,亦足慰余思。”[14]仕途上,由于相貌之故,丧失了赴日留学的机会,也丧失了改变人生的最大机会,作为一个读了近十年新学的中年人,失落感可想而知,如其《满江红》一词所言:“十载学堂只赢得空文一纸,更说甚马科知县,牙科进士。化电声光成弃物,积微元代徒为耳。到头来,还干旧营生,毛锥子。……”[15]虽然吴秋辉生不逢时、命途多舛、家庭不幸、仕途艰难,但他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学术研究中,如《醉书侘傺轩说经后》一诗所言:“潇潇风雨夜生寒,面壁挑灯向夜阑。老作经生岂得已,要留巨眼与人看。”[16]
关于吴秋辉生平记载的现存文献资料不多,较早的1935年的《临清县志》评价他:“为人貌寝又不修边幅,而天才卓越,目空千古,视时辈蔑如也。”[17]此外,张默生著有《现代学界怪杰吴秋辉先生》[18]长文,初载于1940年林语堂主编的《宇宙风》期刊,该文有一万八千多字,是对于吴秋辉最为全面的介绍。文中用“怪”来形容吴秋辉的性格与行为,如白天睡觉晚上治学,屋里肮脏却泰然处之,寒风凛冽也不肯添衣,衣着污秽且随地吐痰,喜好诗词却报考数理。前人走的路子,他虽是走过,确实是倒着走。人家发愤著书,是为古圣先贤作注脚,他则是赏给古圣先贤的耳光,等等。虽然由于写作文体和写作目的,某些言辞或略有夸张,但由于张默生同吴秋辉在世时交往密切,因此此文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吴秋辉先生的真实面貌,是研究吴秋辉不可或缺的宝贵材料。
吴秋辉著作颇丰,但其在世时除《学文溯源》和部分讲稿、杂论出版外,多数著作皆为手稿,未能整理出版。此外,吴秋辉去世时较为突然,众多欲著之作仅列有提纲,尚为腹稿,其遗著后来由最小的女儿吴少辉保管,在抗战、文革等重重磨难中以身家性命竭力保护,大部分得以有幸保存下来,今经其外孙辈张树材、张东蕙等人数十年的不懈努力,遗著终得以陆续影印出版,有《侘傺轩文存》《侘傺轩说经》《吴秋辉遗稿》《吴秋辉遗稿补编》等,成为山东文化史以至民初学术史的一个历史见证。
3 追求:竭力以明经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19]清末民初时期多数学者介于政治、学术之间,吴秋辉并非仅仅是一个只顾埋头做学问的学者,同样有着深厚的家国情怀,关心时政与民生疾苦。如其1909年在省优等师范读书的时候就曾联合同学上书巡抚,请求严惩盗卖中国文物的日本商人:“尝谓古物者,天地之菁华、国家之特色、祖宗之留遗,而进化之迹象也。其权利俱非个人之所得私有。个人无其所有之权利,则买着卖着皆当认为不法之行为。”并请求抚帅大人“持法彻究并妥筹善后办法,以杜觑觎而振国权”。[20]而巧合的是,正是这一年年民政部发布了有关文物保护的《保存古迹推广办法》,要求“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各直省将军、督抚、都统”,对现存古迹和文物进行调查和保护。同时,作为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读书人,忠君爱国思想已深入骨髓,清亡即国亡,国家民族何去何从,其痛心与迷茫可从《春望》诗中一览无余“天地自春色,江山非故园。艰难双鬓改,丧乱一身存。薄俗文章贱,当官虎豹尊。残年无限意,愁绝杜鹃魂。”[21]民国元年,吴秋辉从故乡临清回到济南,应邀从事《山东齐民报》等纸编辑工作“时国体初更,政潮纷乱,先生为某报主笔,沉毅敢言,对于时局痛加批评,人咸以为快。”[22]又如1914年日本侵占胶东半岛事件时,吴秋辉曾愤慨地写下《哀潍东》:“城阙鱼龙入,郊原战伐新。村空唯有树,兵过更无人。异族宁相恤,天心太不仁。残年杜陵泪,东望一沾巾。”[23]再如1926年,军阀张宗昌聘请前清状元王寿彭主持恢复山东大学,吴秋辉听闻王寿彭欲以旧学授课,于是发报批评并代拟新学提纲,王寿彭急忙趁夜色拜访吴秋辉,请求他不要再发并许诺给其好处。吴先生勃然大怒道:“我凭借一知半解,愿为山东学子请命,……我并不是骂街的学棍,有意来敲诈,我要你的干薪干什么?”[24]后王寿彭果因食古不化遭到校内师生的强烈责难而辞职,亦可见吴秋辉的远见卓识。
纵观吴秋辉先生五十一年短暂的生命历程,三十余岁毕业后除担任过数年的报社主编外,其生命的最后时光都在从事学术研究,并以弘扬中国经学为终身事业,体现了其深厚的家国情怀。但吴秋辉原本并不甚喜好经学,如《侘傺轩说经》自序中所言:“余少不喜训故之书,以其纠缠附会,说经而经反晦。人生可为之事正多,何苦矻矻孜孜为是慢圣以诬民也”[25]又如王泽同在为《学文溯源》一书所写的序中说:“余于秋辉吴子交最久。……顾绝口不谈经术,间有道及者,亦唯唯敬谢而已。”吴秋辉走上全心全力的治经之路有些偶然,见于1926年写给梁启超先生的信中[26]:1917年夏天,他居济南于百无聊赖之时,有人持《楚词集注》去看望他,他便留阅之“披览之下,偶然发见中间伪字多处,一为推寻其致误之由,又多非今文之所能解释,绎再三,乃始恍然于楚词原系古文”,而用古文一探究,“有若干不可通处,皆得砉然而解”。于是乎作《楚词正误》,“属稿未半,适因考察古韻,特从冷摊头以铜子三十枚购得《诗经集注》一部。披览之下,始知《诗经》之类此者正复不少……。于是又抛弃《楚词》而专致力于《诗》,是为愚从事治经之始”。此外,1921年他在天津购买的《印度遗事》有《夫爱达》一书,此书的形成时间和内容与《诗经》相仿,但由于后人乱解经义,以致如今的印度人对其内容连同所用文字,都已不识,竟需要向欧人学习,因此“言念及此,无任悚栗,用是不敢自诿,闭户殚精,谢绝百事,虽箪瓢屡空,亦所不恤。”
此时,正是“疑古思潮”的最高峰,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的“新文化运动”,顾颉刚、钱玄同等人的“古史辨运动”都是对传统文化的质疑和否定。而吴秋辉却不为名、不为利、不为时代风气所动,一心致力于恢复中国古代经学,坚持自己的梦想和追求,并不停奔走呼吁,希望更多的人重视经学,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如他在《上同乡诸大老请振兴经学书》中言:“能筹集巨款,政局兴修,使六经之真论一一表现于世,此则千秋之盛业,国家文化之所攸关。桂华虽不才,定当竭其驽骀,以为涓埃之报。”[27]在1921年《上大总统清修明经学书》亦言“伏见我大总统自蒞宇以来,即以斤斤文化为治,近复有提倡《四存》月刊之举。对于一家一人之学说,尚不惜极力推崇,况六经为我中国立国之根本,东洋文明之所自出,其论诸家学说,殆不止麟凤之于鸟兽,……当必不惜乐为提倡,拨款兴修。”[28]皆希望政府、乡绅能够重视中国传统经学文化的发扬与研究,莫丧失了中华文化的根基。他曾不无自负地说:“历来言经学者,其目的无一不在于经学之外。十之九为利,而其一则为名也。其超出于两者之外,而一以经为事者,三千年来,其惟予一人乎!”[29]
面对动荡的社会环境和贫困的生活现实,吴秋辉先生依然在学术方面取得较大的成就,其在文字学、甲骨金文、经学、史学等诸多领域皆有建树,尤其是结合甲骨金文的文字学尤其精湛,为其治学之根柢,梁启超也对吴秋辉的文字学成就赞誉有加:“记甲子春夏间,在都中师范大学讲学,有一学生购赠我以《学文溯源》一册,归而读之,字字莫逆于心,欢喜踊跃,得未曾有。”[30]吴秋辉先生虽然天不假年,但治学前后近三十年,按照其求学治学的过程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即“早年专事词章,中年耽于小学,晚年则致力于经学及古史的探讨。”[31]词章之学主要在私塾与山东省优级师范学校阶段(33岁以前),著有《侘傺轩诗词》等,收诗词二百余首,多为这一时期所作;小学则主要在毕业至离京返济的阶段(42岁以前),著有《学文溯源》《中国文字正变源流考》等;经学及古史的探讨则在他返济的最后几年,是其成果最为丰富的阶段(42岁到去世),著有《楚辞正误》《侘傺轩说经》《周易正误》以及各类古史杂考数十篇。当然这几个阶段不是截然可分的,此仅就其主要着力点而言,可以说吴秋辉先生的一生是当时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转型的一个时代缩影,通过研究各阶段的著作和遗稿,可以充分体现他的传统文史功底和新时代的新方法、新材料、新观点结合的过程,正如张之洞所言:“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32]吴秋辉先生也是沿着这条治学之路一步步夯实了自己的学问,在小学及经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独特的成果。
4 治学根基:词章与小学
吴秋辉早年受到较好的传统私塾教育,对经史子集皆有涉猎,尤其爱好词章,并一直坚持写作,留下不少诗词集,如《侘傺轩诗剩》《侘傺轩诗全》《侘傺轩词余》《侘傺诗词》《寄傲轩吟稿》《秋日同张怡白游大明湖放歌集》等。这些诗歌贯穿于吴秋辉一生,诗中写情写景、写人写事、写心中情怀、写日常生活,内容丰富,体现了其细致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情感,为研究吴秋辉生活、治学与交游的重要资料。
除词章之学外,吴秋辉早期接受的是传统小学的训练,因而对文字、音韵、训诂之学颇为精通,吴文祺曾言“考订学、文字学、校勘学、训诂学,……不但研究中国的文字要靠着它,就是研究中国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也要借重它。”[33]此外,清末以来由于甲骨文的发现而掀起的古文字学热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若今日则地不爱宝,古器之发见者日多,其考订训释,亦渐精确。虽尚苦字少,然即此千数百字而善运用之,则精骑三千,未必不胜于羸卒十万也。……逆料数十年之后,古文学一派,必将郁为大国,起而夺汉学家之席而代之。”[34]当时考据学家们最为重视的一部著作便是《说文解字》,而与其他学者奉《说文》为圭臬不同,吴秋辉结合甲骨文和金鼎铭文等新出土材料对《说文》错谬大加批驳,并在1922年命为《学文溯源》出版,其在自序中指出“东汉人所作《说文解字》,虽其间亦附有古文,然非原本于传伪,即多出于后世妄人之所臆造,……今幸而金文龟文相继出世,商周二代之文字,其大体已略可窥知。”[35]最后总结《说文》所失道[36]:一为文字方面,不知字形转抄之误。“古书之流传,胥赖手抄,得风原本甚难,故讹变特易。”东汉许慎著《说文》时所能见到的古文与真正古文已出入甚多,许慎据之以解字本义,且多以小篆字形解之,所缪必然甚多。二为音韵方面,不知语音因时而变。“语音乃代有转变者,不惟此古与彼古不同,即同一时代,而因地域上之关系故,彼此亦不能无稍异。”而《说文》没有考虑此类变化。三为训诂方面,不知字义因时而变。“时代几经转变,往往古文之甲,适同于今文之乙,使必固执乙之义意,以上合于甲,终将无望其能通矣。”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对一系列文字的全新解释,颇有新意,且言之有据。
钱穆曾言:“一时代之学术,则必有其一时代之共同潮流与其共同精神,此皆出于时代之需要……,时代变,需要衰,乃有新学术继之代兴”[37]。吴秋辉先生对于小学的爱好与研究,正与此时甲骨金石之学大盛声息相通。可以说,吴秋辉真正涉足学界,并崭露头角,跟其深厚的小学基础有着很深的关系,故梁启超先生亦对其《说文溯源》一书大为赞赏。然而,对小学的精通,并没有让吴秋辉先生止步于小学领域,而是将文字、音韵、训诂的小学工夫作为基本工具来研究先秦经史的。
5 治学之大成:经学及古史研究
在传统治学过程中,小学的训练多是为了更深入地研究经学,因而在打下深厚的小学功底后,吴秋辉先生自然将研究对象转向了经学。钱玄同曾言“中国学问皆出于经,经义不明,则神州哲学无从讲求,而汉、唐、宋世之前注,则发明经义者少,胡说乱道者多。不究白文,无从治经也。”[38]据《致梁启超书》,吴秋辉在完成《学文溯源》一书之后,将主要精力用于《诗经》等经学研究,在1919年-1924年完成了《三百篇通义》这部60余万字的巨著,体现了其独特的治学理论、方法和思想。吴秋辉在1923年《再致康南海书》中曾详细地作了总结,形成了自己一套成熟的治经体系,康有为也因此称赞他道:“足下真好学深思之士也,于今世不可多得也。”[39]吴秋辉总结其治经之法为以下几方面:“一曰经之本文。文以载道,中外古今之通义,故欲明其所言之意,必当先于其文字求之。华则遇有疑义,必首先荟萃本经中义意与之相关者,用归纳法以求其会通,然后再用演绎法反之各处,自无不适合;一曰古书互证。经之自身,不必其尽有可证,则不得不稍加推广,以扩大其范围;一曰古文望文生义,本事理之当然,而后人乃反举之以为戒者,则以今日经书所用之文字,初非当日之本来文字;一曰方言。经书所纪之文字,即今鲁、豫、山、陕、直南一带之方言。盖文以纪言,自来言文未有不归一致者也;一曰实物之考察。今之社会实自古之社会所蜕变而成,谓今之社会即古之社会固不可,然视为絶对歧异,了不相关,亦殊非通论也。”[40]究其治学之法,以出土的甲骨金文结合现有史料考释文字、词语本意,不仅已完全具备了“二重证据法”的要素,且能够结合方言及实物,颇有20世纪80年代才提出的“三重证据法”的味道。
这段时期吴秋辉还著有《周易考略》《檀弓纠缪》《说易》《左传正杜》《论语发微》《仪礼今古文考异》《礼记正误》《诸经名物拾义》《古史钩沉》《贝币源流考》《秦建国考》《五霸考》《酒醴考》《夹谷考》等经学及古史研究著作。《临清县志》评价道:“读书得间多前人所未发,其谈名物训诂皆取证当前,绝不空疏……尤能凿险缒幽,时获创见,惜才高数奇,落落寡合。”[41]刘又辛先生读过吴秋辉的遗著后亦曾言:“涉及上古历史、文物制度、古文字、方言学、训诂学、哲学等方面。其考据方法远胜清人,许多论点,今天读了仍有新颖感;有些考订,发前人所未发。六十余年前写成此等著作,实属不易。”[42]除了经史类研究,吴秋辉还有部分杂考、杂钞著作,如《学海绀珠》《读庄漫录》《杂考》《艺苑杂抄》《东梅琐录》,另有日记类著作若干,如《说鬼》《破屋宾谈》等,主要内容为吴秋辉日常琐记、读书心得、闲谈高论、讲稿讲义、小说创作等。
在吴秋辉先生的学术成果中,经学类研究成果最为丰硕,并曾有一系类研究规划:“余于《诗》《论语》《左传》《尚书》后,当从事于此(指《礼经》)也。”[43]可惜天不假年,在刚刚完成《诗经》的研究工作后,便遗憾离世、魂归道山,很多著作尚为腹稿,未及著述。曾经张默生曾设想“把吴老接到青岛,在我们的工作余暇,帮助他整理旧籍。预计的办法是他尽可躺在烟榻上口述,我们充作记录,由一书整理起,一书完毕,再及其他,但我不幸被张宗昌通缉,亡命海外。”[44]此事只好作罢,而吴秋辉也由于贫困交加,不久后便病逝,遗著也未能剞劂出版。因此王献唐先生曾称“近世山东治古文字者,黄县有丁佛言,临清有吴秋辉,皆早去世,遗著多未刊行。”[45]吴秋辉去世前,曾于病榻之上捶床而叹曰:“吾以数十年之精力研讨古籍,今方彻底了悟,著述未及一半而病入膏肓,岂非命也!天之生我,果为何者!”[46]其坎坷不平的命运岂是他一人所有,而是那一个时代多数中国人所有。
6 结语
朱谦之将“考证学派”划分为三支:王国维、罗振玉等倾向甲骨文字学研究;梁启超、胡适、顾颉刚等注重“写的历史”的真伪问题;李济、傅斯年等注重“科学发掘的方法。”[47]从吴秋辉先生的治学历程和治学风格看,可谓三者兼而有之。与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等留学海外的学者不同,他们直接受西方近代文化的洗礼,归国后皆能以西方角度观察中国,以西方立场“整理”中国,易于打破传统,甚至反传统,而吴秋辉先生更多地是以传统的方法去反驳传统学术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其治学思想的开放性。但吴秋辉先生立足于传统小学,从甲骨金文等文字起源入手,对传统经学研究进行反思,立志要在“古文学上开一新纪元,而在学术上起一大革命”[48],以丰硕的学术成果为我们描绘了清晰可见的现代学术发展的轨迹。吴秋辉穷困潦倒而心系家国,箪食瓢饮而笔耕不辍,以弘扬经学为己任,以传承文化为志向,这些都值得我们尊敬,正如其《自题秋窗著书图》所言:“抱影空山老著书,蓬门久已断来车。不知门外秋深浅,落叶堆阶一尺余。”[49]一个人的价值所在,或许不能立刻于其在世时显现,甚或离世多年仍不得彰显,但时间和历史是最好的评判者,虽然吴秋辉先生的生命和著述已经成为过去,但是随着当前学者对其人其学的深入发掘和研究,他的学识、追求和梦想定将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重现光芒。
——评高明峰《北宋经学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