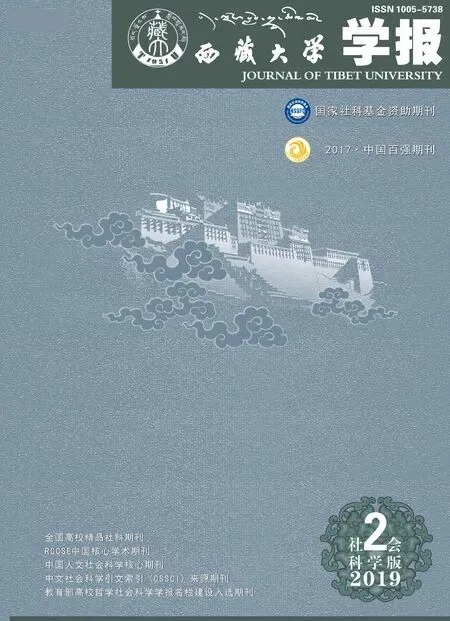拉加里人的“噶拉”(Skal):嫁妆、聘礼还是其他?
白赛藏草
(西南民族大学藏学学院 四川成都 610041)
伴随着婚姻缔结而发生在男女双方家庭的经济交换类型,有彩礼(聘礼)和嫁妆两种。关于彩礼和嫁妆的研究人类学界已经有了很丰硕的成果,归纳起来有六大观点。[1]第一种观点是继承说①竞争说的相关研究,可参见斯蒂文·葛兰(Steven J.Gaulin)、詹姆斯·博斯特((James S.Boster,1990、1993)、米尔德丽德·迪克曼(Mildred Dickemann,1991)、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1991)的文章。,是指嫁妆是女性在其父母死亡之前的一种财产继承形式,譬如古德(Jack Goody)在其欧洲社会的考察研究中指出:嫁妆在它的一般表现形式上,是在父母死亡之前的一种财产继承形式。[2]第二种是福利说②福利说的相关研究,参见爱丽斯·斯郝莱格尔(Alice Schlegel)与罗恩·埃劳尔(RohnEloul,1988)、张俊森与陈威廉(1999)、巴利·休利特((Barry S.Hewlett,2001)等人的文章。,其主要观点是嫁妆与女儿在接受妻子集团中的生活是否幸福有关。[3]爱丽斯·斯郝莱格尔(Alice Schlegel)与罗恩·埃劳尔(RohnEloul)认为,家庭能够用女儿的嫁妆来增加她们的幸福,在印度社会里嫁妆可以用来“交换具有高地位的女婿”,或者“吸引较穷的但是像样的女婿,可以通过女儿的财富来确保他的忠诚。”[4]第三种是劳动价值说③劳动价值说的相关研究,可参见伊斯特·博赛若普(Ester Boserup,1970)、杰克·古德(Goody Jack,1976)、华若璧(Rubie S.W atson,1981)、植野弘子和阿齐兹(1978)的文章。,其主要观点是婚姻偿付与男女双方在生产性劳动中所创造的价值有关,而由于男女两性在同一社会中所创造的劳动价值的差异产生了社会类型与婚姻偿付制度的对应,古德便是这种观点的提出者。第四种是竞争说④竞争说的相关研究,可参见斯蒂文·葛兰(Steven J.Gaulin)、詹姆斯·博斯特((James S.Boster,1990、1993)、米尔德丽德·迪克曼(Mildred Dickemann,1991)、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1991)的文章。,认为嫁妆是女人之间的竞争,而聘礼是男人为了女人而展开的竞争。第五种是家庭意图说①家庭意图说的相关研究,可参见爱丽斯·斯郝莱格尔与罗恩埃劳尔(1988)、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1961)、弗里德曼(1992)、陈其南(1990)的文章。,其观点是婚姻贸易经常被解释为新娘的父母与新郎之间所作的安排,嫁妆可以保持和提升家庭的社会地位,反映的是父亲的意图。第六种观点是财产转移说②财产转移说的相关研究,可参见古德、闫云翔(2000)的文章。,认为嫁妆和聘礼是一种财产再分配的方式,从一个家庭转移到另一个家庭。
具体到中国社会中的彩礼和嫁妆研究,学者们提出了“婚姻偿付理论”③婚姻偿付理论,是以婆家为女方的加入向娘家提供补偿作为前提,认为女性是一种礼物,是一种具有生育价值和劳动价值,可以带来人口和财富增长的礼物。这种理论强调群体之间的关系,而忽略代际关系。和“婚姻资助理论”④不同于婚姻偿付理论的婚姻资助理论,则突出新建立家庭在群体当中的位置,强调代际关系在婚姻交换中的重要作用。根据这一说法,彩礼与嫁妆就是一种代际间的资助。以及偿付资助相结合的理论。相对而言,关于藏区婚姻中发生的双方家庭之间的经济交换,学界研究比较少。目前,已经发表的有阿齐兹的《藏边人家》[5]、格勒等人的《甘孜色达牧区的嫁妆和聘礼》以及龚摘的《华锐藏族婚礼中的礼物交换》。阿齐兹认为,尼泊尔定日人之婚姻偿付与社会经济相联系,因此与劳动价值说的观点基本一致。格勒利用甘孜州色达牧区的田野资料,否定了彩礼嫁妆是男女两性在社会生产和家庭经济中所做贡献的反映形式之说⑤即古德等人所持之生计经济决定理论。,认为藏区婚姻偿付的形式和内容受“家庭经济条件、男女婚后的居住模式以及各个地区大同小异的财产继承方式和文化传统”[6]等因素的影响,并将流行于色达牧区的吾噶(Bag-skal)和玛噶(Magskal)解释为聘礼和嫁妆。龚摘则指出:流行于今天青海省大通河流域华锐松多地方的彩礼和嫁妆,既有古德所说的生计经济地位的体现,又同时兼有婚姻偿付和婚姻资助的特征。[7]位于西藏山南地区曲松县的拉加里⑥关于田野点拉加里的基本情况,笔者已有专门的文章描写,故不在此赘述。具体参见《拉加里的过去和现在》和《苯加与米仓——西藏山南拉加里的亲属制度研究》。人,[8]在其婚姻生活中经常有被称为“噶拉”的物品以及财产流动。那么,流行于拉加里一带的“噶拉”是否等同于上述之彩礼嫁妆之婚姻偿付?如果不是,那它又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和特点?这便是本文将要描述和讨论的问题。
一、“噶拉”的日常表述
“噶拉”是拉加里的方言,人们在谈到卡图⑦卡图,是藏文Kha-thug之音译,是指一对男女自愿结合。此处笔者没有使用“结婚”一词,是因为拉加里方言中的卡图与汉语之结婚所指意义不尽相同。、泰代顿巴⑧泰代顿巴,是藏文Tha-dad-vdon-pa之音译,是指一个人的居住形态与之前的状态有所区别,不管是从妻居、从夫居,还是单独居住,都发生了变化。在拉加里,泰代顿巴是指一对夫妇和他们的孩子搬到一起居住。的时候经常会提到它。在访谈中,只要说起家里的家具,抑或房子的修建情况,人们都会使用“噶拉”这个词汇,并能明确地说出哪些是“我的噶拉”,哪些是配偶的“噶拉”,或是家里其他因为婚姻关系而加入人员的“噶拉”及其数目。笔者之所以会将“噶拉”与上述之彩礼、嫁妆放到一起讨论,是因为“噶拉”与之有些许相似的特征,这主要体现在“噶拉”的流动方向上。在拉加里“噶拉”的流动方向有三种,需要说明的是每一次的流动都与婚姻的发生、终止是有关联的,或者可以说“噶拉”的流动与婚姻关系相生相伴。
案例1:
WM,女,属鸡,今年44岁,拉加里村三组成员。她的阿酷⑨阿酷,是当地方言,系藏文A-khu之音译,意思是指男性配偶。名叫BD,属鼠,今年41岁,是下江朗珍人⑩下江朗珍,是藏文Shag-byang-bla-vdren之音译。这是地名,位于今曲松县下江乡,该地有曲松县境内九大格鲁派寺院之朗珍寺而得名。。夫妇俩有两个女儿,都在上学。WM和她的阿酷年轻时一起参加劳动而相识她25岁的时候,两个人走到了一起。“32岁的时候我们泰代顿巴,阿酷搬过来的时候,从他父母家带来了一对桌子、两个箤楚①箤楚,为拉加里方言,是藏文Rtsub-phrug之音译,指一种编织物,常常用来披盖在身上。、两个铺盖(买来的被子)、四个莱布玛②莱布玛,系藏文Leb-ma之音译,是指一种纺织品,又分两种,一种是可以用来作铺床的,一种则是用作被子盖的。、两对箤楚卡垫③卡垫,系藏语Kha-gdan之音译,是指垫子。,粮食总共载来了一拖拉机,有青稞、小麦,还有菜籽”,WM回忆说。
案例2:
ZG,女,属猴,今年33岁,她的阿酷SN今年43岁。他们家属于拉加里村2组。家里有四口人,夫妻俩和两个女儿。ZG和阿酷自小就认识,大概19岁左右的时候,两人卡图。她28岁的时候从母家搬出来住到了阿酷家,和SN的父母以及兄弟姐妹一起生活。她带来的“噶拉”有一对藏式柜子、一对藏式桌子、一对箤楚卡垫、两副铺盖、一对莱布玛,还有差不多30博尔④博尔,是藏文Vbo的音译,是藏族的一种度量衡,五个藏升(Bre)为一个博尔。的粮食。
案例3:
BJ,女,属猴,今年57岁,出生在拉加里村。他们家有七口人,夫妻俩和两个孩子以及他们的配偶和孩子。他们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已经和阿姐⑤阿姐,是藏文A-ce之音译,在拉加里方言里是指女性配偶。搬出去单独居住。小儿子和他的阿姐以及一个八个多月大的儿子都住在父母家里,准备过年的时候搬出去单独居住。老二是个女儿,有阿酷,也有个女儿,以后会和父母一起生活。
大儿子泰代顿巴的时候,从家里带走的“噶拉”有:一对藏式桌子、两对藏式柜子、一对藏式床、三个箤楚、三个莱布玛、一对箤楚卡垫,另外还有差不多95博尔的粮食,其中有青稞、油菜籽、小麦和豌豆。
在这三个案例中,每个更换了居住地的人在搬迁时都带了自己的“噶拉”,反映的便是“噶拉”的三种流动方向。案例1中WM的阿酷从他下江的原生家庭搬到了拉加里,选择的是从妻居,搬出来时他从母家带来的“噶拉”装满了一拖拉机。案例2中,ZG和她的阿酷是同村人,当她选择从夫居住从母家搬出来时也同样带了自己的“噶拉”,与阿酷的父母住到一起后,这些“噶拉”就变成了这个家庭的共享财产。在这两种居住形态中,新搬进来的人带了自己的“噶拉”,而当他或她进入新家庭之后,原本属于那个家庭的所有动产和不动产也都同样归属于他或她,他或她与住在这个家里的所有成员享有同样的使用权。案例3是一个单独居住的个案,BJ的大儿子在搬出去时也从母家带走了他的“噶拉”,在这样的家庭,儿子的阿姐在从她母家搬出来的时候也同样会带一份自己的“噶拉”。单独居住的两个人在未来生活中对双方带来的“噶拉”与上述两种家庭一样拥有同样的使用权。
二、“噶拉”的内容和分类
在拉加里,“噶拉”的内容很丰富,但最常见的有以下几种:卧具、家具、炊具、田地牲畜和房子。
(一)卧具
但凡有人分得了“噶拉”,卧具都会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卧具具体表现为莱布玛、卡垫和铺盖。莱布玛又有两种:一种是用来盖的,相当于被子;另一种则是用来铺的,相当于褥子。卡垫也分很多种类,在拉加里常见的有绒垫、箤楚垫和一般的卡垫。绒垫和一般的卡垫在材质上有所不同,绒垫似乎更多地是用一种专门的毛线纺织而成。箤楚在取材和加工程序上都不同于上述两种,更像是用麻制成的,通常也有用来盖的和铺的两种。这里所谓用来盖的和铺的,只是尺寸上有所不同而已,没有其他差别。人们常说的铺盖,是指从商店里买来的成品被子。
(二)家具
家具在“噶拉”中出现的频率仅次于卧具,也是分配“噶拉”之必备。家具主要有床、柜子和桌子,柜子和桌子都是藏式的。较之普通的柜子和桌子,藏式的会大一点,能容纳很多碎小物品。这些家具有买来的,也有定做的,上面都有精美的漆画。村里有许多画匠,被称为琮当堪(Tshon-btangmkhan,意为画匠),手艺都很不错。
(三)炊具
家用中除了上述之家具,还有锅碗瓢盆,详见案例4中女主人的“噶拉”。
案例4:
QZH,女,属龙,今年49岁,出生在拉加里。她的阿酷是CR,属鼠,今年53岁,也是拉加里人。QZH在19岁的时候生了大儿子,第二年便和阿酷泰代顿巴。
QZH和他的阿酷属于单独居住,当年从家里搬出来的时候,也都带来了自己的”噶拉”,她还给我们一样一样地看了以前从父母那里分来的旧器具。她的”噶拉”有一个小柜子、一个桌子、一个桑廓①为藏语Zangs-khog之音译,是指一种铜制成的锅。、一个酥油桶、一个鼎俦②为藏语Ding-phrug之音译,是一种炊具。、一个噶朵热③为藏语Ka-to-ra之音译,是一种炊具。、一个廓迪④为藏语Khog-ldir之音译,是一种炊具。、一个金木巴⑤为藏语Skyum-pa之音译,是一种炊具。、一个卡垫、两个莱布玛、一个道廓⑥为藏语Lto-khog之音译,是一种炊具。、一个曲尔廓⑦为藏语Phyur-khog之音译,是一种炊具。、一个巴东⑧为藏语Gdong之音译,是一种炊具。、一个巴兰姆⑨为藏语Pa-lam之音译,是一种炊具。、一个麦廓⑩为藏语Me-khog之音译,是一种炊具。、一个约廓⑪为藏语Yos-khog之音译,是一种炊具。,还有50博尔左右的粮食和4亩农田。阿酷的”噶拉”有两个铪央⑫为藏语Ha-yang之音译,是一种炊具。、一个莱布玛、4个噶仁木⑬为藏语Ka-rum之音译,是一种炊具。、50博尔的粮食和3亩农田。
(四)粮食
在拉加里,泰代顿巴的时间大多是在藏历正月,因而分配口粮也成为了必须进行的一项内容。受地理和气候所限,当地的种植物以青稞和豌豆居多,还有少许谷地种植小麦。此外,每家每户或多或少都会种植油菜籽和土豆,油菜籽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所有的粮食都是自给自足,不会向外出售,口粮不够部分还得另外购置。分配“噶拉”之粮食时,在过去都是以博尔即藏斗计量,如今大多数都以麻袋计数。
(五)房子
对于那些单独居住的夫妇而言,“噶拉”中还有包括一种特别的项目——新建房子。不同于其他居住形态的家庭,这些家庭在初建之时还需要修建属于自己的居所。修建房子所需要的所有资金由两个家庭共同承担,通常都是平摊费用,即人们经常说的“一半一半”。所需之人力,理论上也是由两家人共同承担,但实际上还取决于居住地的选择和对双方家庭劳力的考量。如果夫妇俩决定将新房子修在离女方家不远的地方,女方家出的劳工可能在数量上会多一点,反之亦然。特别是对男女出自不同村落的家庭而言,劳力上的差别更明显。
(六)田地
夫妻俩的出生地还决定了“噶拉”是否带有土地。如果这对夫妻是来自同一个地方,包括同一个行政村或一个乡镇的,从妻居和从夫居中的对方家庭、单独居住的双方家庭都会给搬出来的人按照家庭拥有的土地额数而分配相应的农田。譬如说扎西和卓玛夫妇都是拉加里村的人,或者一方为附近村落的人,他们的“噶拉”中就会带有农田。但是,如若夫妻俩来自不同的地方,“噶拉”中就不会出现农田。案例4中的QZH和她的阿酷CR都是拉加里村的人,因此,他们俩各自从母家搬出来时都分得了农田。而村民拉卓和白玛的阿酷都是从曲松县外搬进来的,前者是从山南琼结县搬过来的,后者是由加查县搬过来的,他们俩的“噶拉”中就没有农田这一项内容。另外,从案例4中我们还发现,尽管QZH夫妇是单独居住,都分得了农田,但其数目是不同的。因此,能够分得多少“噶拉”,具体是什么内容,这都依赖于原生家庭的实际情况,包括家庭的经济条件和兄弟姐妹的数目。
(七)牲畜
“噶拉”中还有一部分是家畜,例如羊、巴炯①巴炯,系藏文Ba-phyugs之音译,是指黄母牛。在拉加里每个家户都会饲养几头母黄牛,成为牛奶和奶制品的来源。等。但是,总的来看,在拉加里每个家户中饲养的家畜并不多,因而“噶拉”中巴炯和羊的数目也并不显著。有些人家在分配“噶拉”时会分拨其中的几只或几头给儿女,也有的人家只分配上述之卧具、家具和一些日常家用,而不会在少得可怜的牲畜中进行再分配。
随着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夫妻俩泰代顿巴时带过来的“噶拉”也有了新的变化,新式的组合柜、电器等纷纷走入了人们的选择,“噶拉”的形式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家具。
三、“噶拉”的分配方法
通过长时间的田野调查,笔者发现在拉加里“噶拉”分配的基本原则是每个儿女都有份,份子的大小与多少大体上是一致的。关于这一点,报道人提供的下面几个案例是最好的说明。
案例5:支书的甘雄②甘雄,是拉加里方言中关于亲属称谓的术语,为藏文Rgan-gzhon之音译,可简单地理解为兄弟姐妹,包括同父异母和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
GM,属猴,今年57岁,是拉加里村支书。他有兄弟六人,他是老大。支书单身,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母亲早年已经去世,父亲去年过世了。支书最大的弟弟,叫QP,属狗,今年55岁。他从家里搬出去时,还是人民公社的时候,大概是在1977、78年的样子。他的阿姐也是住在拉加里的,生了孩子以后,他们俩就在外面借了别人家一间小房子,住在了一起。因为当时家里条件不好,所以也没带走什么东西,只带走了一个用来盖的莱布玛、一个用来铺的卡垫和一个用来盖的箤楚,并且这些也都是他以前用过的。至于粮食,“因为当时是公社统一发放的,因此他们俩搬到外面以后就自己直接去公社里面领取”。现在他们也盖了新房子,也在拉加里村,与支书家离得不远。
支书兄弟中的老三兄弟叫DB,在县某部门任职。他的阿姐是下江乡人,也是公务员。他从家里分出去的时间,是找到工作的那年,后来才与阿姐结婚。弟弟大约是在17、8年前县里聘用干部的时候,“成了拿铁饭碗的工作人”,当时他被分到了一个乡上。他找到工作以后父母给了他一套卧具、一套柜子和一个桌子。
老四兄弟叫ZHX,属马,今年47岁,是名医生。他虽为DB的弟弟,但比哥哥早两年找到工作。ZHX也是在工作的那一年从家里搬出去的,搬出去的时候分到的东西也是小桌子一个、卧具和柜子各一套,和他哥哥一样。
支书家的老五叫SZH,属狗,今年43岁,现为一家茶馆老板。在弟弟搬出去之前,支书曾主持修建过一套三个噶的房子。“SZH分出去的时候,除了我盖的那栋房子,父母还给了他一个桌子、一套卧具和一套灶具”。
支书家最小的甘雄,叫DZ,属牛,今年40岁,现在乃东县工作。他中专毕业以后,被分到了昌都地区的某个公安局。因为分配的地方离家太远,父母并没有给他任何家具。因而在2004年DZ被调回乃东时,他的父母让人送去了一套柜子、一些钱和糌粑作为他的“噶拉”。
这个案例中支书的几个甘雄都是男孩,每一个男孩离开父母时都得到了“噶拉”。在每个儿子分得的“噶拉”在数量上稍有不同,对于这一点,报道人支书解释跟当时的家境有密切关系。就像他的第一个弟弟搬出去时,不仅支书家经济条件不好,据老人们讲整个拉加里的生活水平都不如现在,因此,分得的“噶拉”数目显然是不能和后来的ZHX相比。尽管卧具和灶具的数目不一样,但是根据支书的回忆,几个弟弟搬出去时带走的卧具和灶具都是一套的,也就是说这些“噶拉”都是他们后来的生活必需品,或者足以应付日常的生活了。
在拉加里,不光是儿子们分得的“噶拉”是一样的,父母分给女儿们的“噶拉”也会尽量保持一致,就像下面奥觉LM的这个案例。
案例6:奥觉LM的几个女儿
LM,女,今年61岁,与丈夫有7个孩子,四个女儿已结婚并搬出去居住。大女儿LMZM,今年38岁,现居于邻村。大概十年前,LMZM搬过去。除了家里帮忙修建的房子,彼时LM夫妇还给女儿置办了一套床上用品,包括藏垫、被子和莱布玛等,还给她送了一对藏式柜子、一个藏式桌子,分了四、五十博尔的粮食。
二女儿QZ,今年37岁,现居于邻村。QZ于12年前搬到炯嘎塘(kyong-go-thang),与阿酷住在他们新建的居所。当时分得的”噶拉”与其姐姐LMZM一样。
三女儿是QJ,属羊,今年34岁,现居住于曲松镇的另一个行政村。她的阿酷是家中幼子,与其母亲一起生活。QJ搬过去的时候并没有带很多”噶拉”,而只是分了些粮食。因为他们和母亲住在以前的房子里,家什齐全,没有必要让女方出。
四女儿CDZG,属狗,今年31岁。她和阿酷都是在昌都某县的小学老师,两人为西藏大学专科时期的同学。因为她是莱切巴,所以除了上学时用过的行李,她跟阿酷单独居住的时候,并没有另外从家里分得”噶拉”。
其余三个孩子中有两个儿子还在上学,小女儿则在拉萨打工,还没有结婚。按照奥觉LM的计划,未来不管是谁跟他们老两口一起生活,搬出去居住的孩子们的”噶拉”会是一样的,也尽量会和前面几个女儿保持平衡。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得知“噶拉”的分配还有一个互动的过程。就像奥觉LM的第三个女儿QJ,因为她是从夫居住,泰代顿巴的时候阿酷和母亲一起生活,他们俩不仅不需要重新盖房子,也不需要重新置办日常家用。因此,QJ在母家分得的“噶拉”中并没有卧具、灶具等,而主要是粮食。即便是粮食的数目,就像报道人奥觉LM说的那样,有一个协商的余地,“对方家里情况和我们家相当,他们不让带其他的噶拉”。
尽管拉加里的“噶拉”分配原则是儿女都有份,但是家庭中那些参加了工作、有稳定收入的孩子,以及掌握有一门手艺,例如会开车、能画画的孩子,在分配“噶拉”时也和其他孩子是有区别的。
案例7:房东家的孩子们
在拉加里的时候,我和妹妹就住在伉巴奥觉①伉巴,为房东的房名,奥觉为拉加里的亲属称谓,是对父亲或母亲之母亲的直接称呼。家。她有九个孩子,丈夫三年前去世了,现在和三个孩子一起生活。奥觉的大女儿是ZHG,也是ZX的母亲,现在住在拉加里村的三塘之一——炯噶塘②炯噶塘为地名,是藏文Gyong-dkar-thang之音译,就在拉加里对面比较平坦的地方。。老二是BM,是个卡车司机,住在下洛③下洛为地名,系藏文Shag-lho之音译,属于今曲松县曲松镇。的阿姐家。老三是QZH,和她的阿酷住在拉加里。老四DJ,和她的阿酷住在曲松县县城通往拉加里王宫的路上。老五是个儿子,现在在山南琼结县工作。老六是QJZM,在阿里地区工作。老七叫JZ,与奥觉住一起,现在还没有结婚,是家里的主要劳力。JZ平时会干农活,农闲时去加查县打工。老八叫WM,现在在拉萨的一个印刷厂做临时工。奥觉最小的女儿在上大学。
老大女儿ZHG泰代顿巴已经有13个年头了,搬出去的时候”噶拉”有2.5亩的农田、一头巴炯、20博尔的粮食、一对藏式桌子、一对藏式柜子、一对藏式床、一对箤楚卡垫、一副铺盖和一个箤楚。另外他们单独居住的时候,房子也是两家人一起修的,费用由两家人平摊。老二BM会开车,是个汽车司机,他要搬出去跟阿姐住的时候,没有从家里带”噶拉”。因为家里孩子比较多,所以老三QZH从小是由她阿奶④阿奶系藏语A-ne之音译,为拉加里的亲属称谓,是对父亲姐妹的直接称呼。抚养的,后来她找了阿酷以后,也是从阿奶家直接搬出去的,”噶拉”自然也是由她的阿奶家分的。老四DJ搬出去单过的时候,”噶拉”和老大ZHG是一模一样的。老五和老六因为都是莱切巴①为藏语Las-byed-ba之音译,意为有工作的人。,所以找到工作的时候就从家里搬出去了,除了上学时的铺盖,其他什么也没有带走。
奥觉伉巴的几个孩子中,有两个是莱切巴,即有工作的人。一个儿子在琼结县政府工作,一个女儿是阿里地区的公务员。有工作的人,也就是那些在当地被称为是莱切巴的人,在拉加里通常情况下都不会再从家里分得“噶拉”,有时候人们也会将他或她在上学或者刚参加工作时从家里带走的行李、桌子等当作是给他们的“噶拉”。在这个案例中,比较特别的是奥觉的老二BM。他并不是莱切巴,但当他找到阿姐,并从家里搬出去居住的时候,并没有从母家分取“噶拉”,据奥觉解释,这是因为BM“是个拉辛巴②拉辛巴,是藏语Lag-shes-ba之音译,意思是指身怀技艺之人,或者懂工艺之人。在拉加里,司机、画匠、木匠、工匠等都居于拉辛巴之列。,有手艺”。虽然BM在家里分获“噶拉”是与其他甘雄不一样,但在拉加里像他这样的并不是特例。这些匠人、司机和有工作的其他兄弟姐妹,在找到卡图并开始泰代顿巴的时候,不会再从家里带走“噶拉”。此外,奥觉的孩子中还有一位在“噶拉”分配当中也扮演了特殊的角色,这就是她的老三女儿QZH。QZH自幼由她父亲的妹妹阿奶抚育,在她搬出去单独居住的时候,其“噶拉”也是从阿奶家获得的。至于女儿QZH“噶拉”的获得形式是另一个议题,还需做单独的文章讨论。
四、“噶拉”是嫁妆、聘礼,还是其他?
在许多访谈中,我的那些报道人都说不明白“噶拉”究竟是什么,尽管他们对自己带来的“噶拉”记得一清二楚。直到田野中期,在一次与老人美朗的闲聊中,老人的一句话使我茅塞顿开、恍然大悟。老人说,之所以儿女搬出去“泰代顿巴”的时候要给他们准备“噶拉”,是因为他们在此前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努力,遭受了辛苦。因此,“噶拉”也可以说是对即将从这个家搬出去的儿女的一份回报,或者他们理论上应该获得的酬劳、份子。
因而,拉加里方言中之“噶拉”其藏文书面写法应该是Skal。至于为什么将藏文的一个字Skal变成了两个单独的音节Ska和La则是语言学要解决的问题,在藏语很多方言里都有这种拆分的现象。
Skal(噶拉),在辞典中有三种解释。第一种,是指份子,即分摊得来的部分;第二是指缘法和福分,命中注定的机会;另外一种则是数学术语,是指代替、替换的部分。根据上述的几个案例,以及老人的启示,可以确定“噶拉”就是份子,儿女从家里分得的属于自己的份子。因此,“噶拉”揭示的不是以嫁妆、聘礼为中心的婚姻偿付,而是拉加里的财产继嗣制度。
首先,在形式上“噶拉”不同于彩礼和嫁妆。从前三个案例,我们也可以看得出,不管是从妻居、从夫居,还是单独居住的家庭,总有“噶拉”的流动。仅从“噶拉”的流动方向来看,案例1中WM阿酷的“噶拉”,与我们谈论的彩礼有些相似,因为这些财物是由男方家庭提供的;案例2中ZHG的案例与嫁妆又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是由女方提供并流入男方家庭。在案例3中,如果单看BJ大儿子的“噶拉”,似乎像是男方家提供的彩礼,但是它的流向并不是妻子家,而是第三个家庭,即他和妻子新建的属于他们自己的小家庭。同时,对于他们的小家庭而言,“噶拉”从BJ及其儿子妻子的父母家流入。无论是男方带来的还是女方带来的财物,在拉加里都使用“噶拉”这一词汇,而不加区别。
其次,“噶拉”在内容上的表现也与彩礼和嫁妆有别。在中国农村盛行的彩礼,通常都是由钱和物一起构成,龚摘在青海松多藏族村落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其中,“物”这一块包括衣服、首饰等比较珍贵的物品。嫁妆亦是如此,并且逐渐趋向于金银项链、镯子等一些非基本生活需求的物质。但是拉加里人的“噶拉”在内容上则多表现为房屋居所、粮食、家具、卧具和灶具等一些生活必需品。
第三,“噶拉”流动的时间并不是婚姻的开始。“噶拉”之所以被误解为彩礼和嫁妆,是因为这些财产的转移与一对夫妇住在一起是同时发生的,也就是人们通常理解的结婚。但实际上,拉加里人的婚姻并非开始于“住在一起”,而是在此之前的“卡图”,关于这个议题笔者已有相关的讨论[9]。“住在一起”只是夫妇俩改变了居住模式,即由原来的分开居住转变成了从夫居住、从妻居住或者单独居住。
第四,在拉加里流动在婚姻当事人家庭之间的“噶拉”,与藏族法典中记载的财产分配相一致。关于藏文中的Skal这个词汇在藏族古代的法典《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中都有相关的条文记载。例如《十六法典》的第十三条“亲属离异法”中规定在夫妻离异的案例,“对于没有孩子的(女性)要分得她朵噶①朵噶,即藏文Lto-skal之音译,意为糊口的份子。”,其内容包括“土地、房屋以及衣物”等。
第五,“噶拉”的获得者并不仅限于婚姻发生的当事人。在拉加里,“噶拉”的获得并不只是以婚姻的发生作为分配时间和数目的依据,那些被村民们称为“拉辛巴”或“莱切巴”的手艺人和国家公职人员,并不是在结婚甚至改变居住形态之时才会从父母那里获得自己的“噶拉”。特别是后者,当一个人在政府机关或学校等谋得一份工作,成为“莱切巴”时,他的家人和父母就会在就职上岗之前给他或她置办卧具、炊具等作为他们的“噶拉”。如果其工作的地方与家距离比较远,家人就会选择支付一定数额的钱,让其购置这些日常用具。就像案例5中支书的弟弟、案例6中奥觉LM的女儿,以及案例7中房东的两个女儿,都是在参加工作的时候,从家里获取了以卧具为内容的“噶拉”,而并非在自己结婚之时领取的。根据法典中的记载,“噶拉”的分配不仅出现在离婚的案件中,还适用于父子、兄弟之间的分异案例,譬如“依据人口之多少,分配土地、房屋、牲畜和物品等”。[10]此外,出家人在离家举行剃度仪式之时亦会从原生家庭获得一定数量的“噶拉”②对于出家之人,也要依据家庭条件分配噶,以厨具、土地等作为衣食保障。参见:藏族法典选编(藏文)[M],藏族历代法典(藏文)[M].。[11]上述法典中关于“噶拉”的分配,则更体现了其非彩礼和嫁妆的这一特征。
第六,在藏族社会有专门表示彩礼和嫁妆的词汇、术语,即居(Rgyu)和宗哇(Rdsongs-ba),有别于噶(Skal)或“噶拉”(Ska-la)。“居”指的是在结婚前男方需要向女方家庭提供的,其内容有金银首饰、衣服,还有一定数额的货币;而“宗哇”则是指由女方流向男方家庭的物质提供,其内容有牛羊等牲畜,同时也包括女方父母为新娘子置办的贵重衣服及其配饰,譬如珊瑚、绿松石、珍珠等做成的价值不菲的项链。一经婚礼,男方赠与女方父母的“居”其所有权便属于新娘的原生家庭,若非因为女方的重大过失而导致婚姻关系的破裂,否则女方父母是不会退还的。同样,藏族法典《十三法》《十五法》和《十六法》中也出现了一个与噶组合的词汇即噶宗(Skal-rdzongs),例如“如果女子找到合适的人家,还要审时度势付之于相应数量的噶宗”。其中的“噶”是分得的份子,而另一半词“宗”则是指女孩子结婚时原生家庭让她带入新家庭的牛羊等财物,即汉语之嫁妆,这一词汇在今天的安多等地仍旧被广泛使用。由此,也可以推断拉加里的“噶拉”即是法典中出现的表示份子之意的“噶”,也即藏文Skal的转音,同时有别于表示彩礼嫁妆的“居”(Rgyu)和“宗哇”(Rzdongs-ba)。
总而言之,“噶拉”作为发生在婚姻主体之间的财物转移,其流动方向有三种,并与男女婚后的居住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从夫居住的家庭,流动的方向表现为由女方到男方;在从妻居住的家庭方向则是由男方到女方;而在单独居住的家庭,“噶拉”流动的方向则是由男女两个原生家庭转入新建立的核心小家庭中。
不难发现,在多元的“噶拉”流动方向中,其实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因为其方向始终与居住形态保持了一致性。这个规律联结的,正是拉加里人的家庭观念。拉加里人的家庭观念是以居住形态为中心的,因而在家庭财产的继承和分配制度上依据的还是这个原则。凡是居住在一起的人,对家庭财产的继承都拥有同等权利。从原生家庭搬出去的人离开时带着自己分得的“噶拉”,加入另一个家庭组织。如此,他或她获得了新家庭中一切财产的使用和继承权,但同时也不再拥有先前在原生家庭中的权利。
“噶拉”的内容繁多,但归纳起来有房屋、田地、卧灶家具等生活用具以及少量的牲畜。从这些类型来看,“噶拉”并不是高级需求,很少有奢侈品,而满足的是基本生活需求。“噶拉”并非彩礼,也非嫁妆,其分配机制反映的是拉加里人的继嗣制度。因此,以往学者们关于婚姻偿付的各种理论都无法解释拉加里的“噶拉”流动。在拉加里,每个人都有从原生家庭分得“噶拉”的机会,它不仅承载着家人对其付出艰辛和劳苦的感谢,也反映了子女在父母那里享有共同分配财产的平等机会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