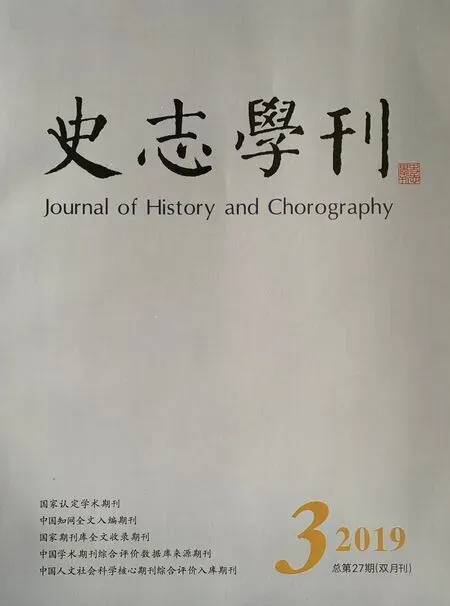宋代儒学复兴中的女子礼佛
徐 爽
(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随着士大夫阶层自我主体意识崛起,从唐代的韩愈、李翱到北宋范仲淹、欧阳修再到南宋朱熹,皆强烈呼吁并倡导儒学全面指导民众的社会生活和秩序,儒学复兴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在这一复兴过程中,士大夫笔下却出现了大量对礼佛女子的赞颂言辞。宋代文集、墓志铭等资料中有众多关于女子礼佛的记载,尤其在墓志铭中士大夫极尽嘉言赞美这些女子的品德修养。
一、士大夫建构的理想型:墓志铭中的礼佛女子
在众多的墓志铭资料中,士大夫用赞誉的形式逐步建构了礼佛女子的理想形态:有良好的自我修养,趋向于清静无为,维持着正常的家庭生活秩序,妻妾和睦,给子女良好的影响和教育。我们可以看到,墓志铭中士大夫对礼佛女子的赞誉也主要集中在女子自身修养及美德、保持家庭和睦、子女教育等方面,而随时间的推移礼佛女子的形象在赞誉声中逐渐清晰。
为人处事态度的淡定、对环境际遇变化的宽容不执著,由内而外表现出的脱俗气象为士大夫们所推崇,浦城陈氏“姑嗜佛书不预家事,夫人性澹然,所好雅合”[1](宋)徐元杰.楳埜集·浦城陈氏墓志铭[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一).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长平游夫人“资静淑”“不疾呼,不怒视”之气象,朱熹为其铭曰“长平之游,世有徳人”[2](宋)朱熹.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第九十一卷)[M].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P4212)。而陈氏在得到太孺人的赐封时所表现的气象“自处者不少异于平日”[3](宋)朱熹.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第九十二卷)[M].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P4251),国子监丞葛寔丞之妻尹氏同样不在乎外在的名利,葛君“以文进而久不第”而“夫人未尝戚戚”[4](宋)蔡襄.端明集·尹夫人墓志铭[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三十六).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而且,礼佛女子这般与世无争的品德修养还进一步影响了家人尤其是丈夫,在其仕途不顺、情感受挫时给予开导宽慰。长寿县君高氏在丈夫“方且栖栖筦库间,或以为恨”之时,劝勉他:“仕,谁不愿达?其不得达者,命也。君如命何?我闻为善必有报,姑教诸子以俟之,可乎?”[1](宋)邹浩.道乡集·长寿县君高氏墓志铭[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三十七).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而在对待生死之人生问题时,我们可以在墓志中发现大量的诸如“绝生死之怖”“不惑于死生之际”之类对礼佛女子去世前从容状态的描绘。如太孺人陈氏:“绍熙元年三月某日,以疾卒于家。卒时精爽不乱,享年六十有八。”[2](宋)朱熹.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第九十二卷)[M].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P4304)建安郡游夫人“颇信尚浮图法”“端居静室,焚香读儒佛书”,对佛教思想有较深的认识,游夫人对死亡便有颇深的见解,“病革,大夫公泣视之。夫人曰:‘生死聚散,如夜昼然,何以凄凄为哉?’”[3](宋)朱熹.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第九十一卷)[M].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P4211)游夫人认为她们“生死聚散”都只是如“夜昼”般的自然现象,不需要如此悲凄。
礼佛女子自身止恶修善、与世无争和清心寡欲的品德修养也使她们能够较好地处理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尤其是妻妾之间,从而保持家庭和睦。如汀州宁化县主簿俞备之妻陈氏“自少奉佛,中年益笃,多不茹荤,持诵终日,无妒忌之心,饰妾妇以奉君子”[4](宋)黄裳.演山集·夫人陈氏墓志铭[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三十三).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又如永安县君金氏就是“对梁君如宾客,处姬妾如娣姒,抚诸子如己出,喜读书善笔”[5](宋)黄庭坚.山谷集·永安县君金氏墓志铭[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外集卷八).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女子礼佛对调节家庭成员尤其是妻妾关系还是起了相当的作用。宋代士大夫纳妾成风,妻子们会自然而然产生嫉妒,妾的出现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和尊严,对丈夫纳妾不满就自然表现在语言、态度和行动上。虽然认识到嫉妒的情绪所具有的破坏性,但是认识不可能时时战胜情绪,嫉妒所产生之情绪会满溢成言语、态度和行动不恭与刻薄,而违背柔顺、贤惠之道。而佛教教义提供了一视角去摆脱烦恼还自己安详沉静,也提供了空间让女子实现自我价值,以“与世无争”的教义置换了没有自我的“柔顺、贤惠之道”,促使她们与妾之间和睦共处。当然也有因长期斋居生活而无法履行做妻子的义务而对夫妻关系造成影响的。如上引陈氏“盛年而独寝处,姑妇焚诵,蚤暮合席”[4],金氏“信释氏,读其书,奉其戒律。年四十则扫除一室,谢梁君而斋居”[5]。她们便会主动为丈夫纳妾以代自己履行做妻子的一些义务,所以妻妾的关系也就自然和谐。
女子的自身品德修养同样影响到后代子女的教育,女子对子女的教育主要是言传和身教两个方面。宋代教育是以培育圣贤为目的,强调“学者学所以为人”,在家庭教育中,更强调的是礼规的学习和道德的培养。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朱熹在《小学》中转《列女传》言:“古者,夫人壬子,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跸,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邪色,耳不听淫声,夜则令瞽诵诗,道正事,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过人矣。”[6](宋)朱熹.朱子全书(第 13 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P379)说明女子在“壬子”之时便已开始“道正事”的身教之法。如前引游夫人便是“颇信尚浮图法,娠子则必端居静室,焚香读儒佛书,不疾呼,不怒视”,谓之“古人胎教之法”[3](4212)。孩子出生之后,便是一些基本礼仪知识即“洒扫应对”的传授,其所重视的亦是“正”。而如游夫人般“不疾呼,不怒视”“端居静室”的身教和孩子稍大就置其于腿上“诵儒佛书”的言传,相信孩子对儒家要求的“正”定有深刻的理会。
母亲对孩子的教育和影响不仅是一些基本礼仪知识即“洒扫应对”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品德即“孝悌之道”的熏陶。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7](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中华书局,2008.(P49)孝悌之道是教育的第一位。而宋代的佛教理论中孝道已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目连孝亲”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女子给孩子讲述这些孝亲的小故事,这样的言传可以在孩子心里留下关于“孝”初步映像。而女子在侍奉公婆时“婉娩听从”、谦恭有礼,孩子们可以在母亲的身体力行中受到教育,而对“孝悌之道”有更具体的认知。此外,礼佛女子那种淡然安于命、不以外物动其心的道德修养,对孩子思想素质和优良品格的培养不无帮助。
总而言之,无论是在自身修养及美德、保持家庭和睦方面还是在子女教育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佛教对女子家庭生活影响相似于儒家礼教,而礼佛女子的理想形态宛然是儒家伦理中的贤妻良母,这并非只是简单的巧合,可以说是士大夫们精心选择的结果。士大夫的评价背后所隐藏的是儒家伦理道德这一筛子,筛选出的是儒家理想形态的礼佛女子——贤妻良母,所期望达到的状态是承担儒家的社会责任义务、维持家庭内部正常生活秩序,简言之,履行妇职。
二、“反佛”与“礼佛”
墓志铭主要是墓主的后代为纪念先祖的高行贤德而请有盛誉的士大夫写就的文章,志其生平事略,铭其“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因此,墓志铭中鲜有直接的批评指摘之语,细细解析才得见深藏于背景中的批评,作者往往通过对他人不当言行的批判来凸显墓主德行。“反佛”及其思想观念也就隐藏在其中。有这样的记载:
岁时宗戚,趋寺庙以嬉,(蒋氏)曰:“彼岂我属游止处耶?”[1](宋)许景衡.横塘集·丁昌期妻蒋氏墓志铭[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十).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元丰、元祐间,释氏禅家盛,东南士女纷造席下,往往空闺门,……(严氏)戒家人曰:“苟尽妇道,即契佛心,安用从彼扰扰耶?”[2](宋)邹浩.道乡集·寿昌县太君严氏墓志铭[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三十七).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两则史料都是礼佛女子对家人的警示之言,作者通过对墓主观点的赞同提倡来表达对于那些女子的反对。蒋氏认为寺庙里聚人众多,岂是女子的“游止处”,严氏也批评“空闺门”,认为不用“从彼扰扰”。可从上下文窥得,作者认同这两位礼佛女子的观点,对“空闺门”的礼佛女子持反对态度,更确切地说,在家庭生活中士大夫们“反佛”是批评反对“空闺门”这样不当的礼佛方式。
依儒家观点,女子就该在“闺门”之内,她们的责任与义务或者说最好的状态是献身于丈夫的家庭成为贤内助。但是一些女子忙于礼佛,对“承先祖、主中馈”之家事甚是疏忽。如陆游曾道,“近世闺门之教略,妄以学佛自名,则于祭祀、宾客之事皆置不顾,惟私财贿以徇其好,曰:‘吾徼福于佛也。’呜呼!娶妇所以承先祖、主中馈,顾乃使之徼佛福而止耶?”[3](宋)陆游.渭南文集·陆孺人墓志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三十三).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女子因礼佛而疏忽妇职,置“祭祀、宾客之事”于不顾之地,是不为士大夫们所接受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女子的任何礼佛行为,对寺庙的捐赠布施都成了贿赂,只为“徇其好”。当然陆游如此贬斥只是为了强调“承先祖、主中馈”等家事的重要性,体现的是儒家伦理。如果女子在完成既定的妇职并任劳任怨,得到的便是赞誉,如陆游在《陆孺人墓志铭》中赞誉陆氏:
奉家庙尽孝尽敬,朝夕定省如事,凡祭祀烹饪涤濯皆亲之,至累夕不寐。承议平生所与游,多知名士,每客至,辄信宿留。孺人执刀匕,白首无倦色,曰:“此妇职也。”[3]
只有在很好地履行了儒家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的前提下,士大夫们才会接受女子礼佛,并对礼佛行为如陆氏“自幼奉佛法,戒击鲜,终身不犯”等给予肯定,由这些行为体现的仁慈善良才会成为士大夫们赞誉的美德。如尹夫人:
“事姑勤谨不懈,而于夫人之族亲抚接,皆有礼意……念母之老,迎归以养,年八十余终于夫人之家,即葬近墅,其于孝爱深矣!丞以文进而久不第,夫人未尝戚戚。岁时奉祀、与娣姒族亲宴饮,列女僮鸣管弦以相和乐[1](宋)蔡襄.端明集·尹夫人墓志铭[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三十六).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在做好家事尽于妇职的前提下,尹夫人“喜浮屠书,颇知其指”才被认可,其“均一之徳、法度是循”等行为表现的坚韧才会得到赞誉,蔡襄为其铭曰“夫人兹其尚焉”[1]。
进而言之,“反佛”的原因在于佛教的一些生活方式和行为与儒家传统观念有所冲突,如佛教礼拜佛菩萨与儒家孝亲崇祖的观念相冲突,再如佛教大量在外的佛事法会与儒家“内外”的观念相冲突。
孝亲崇祖是儒家伦理的核心,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维护着国家的宗法制度。“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是具有共同性,所以不论国或家,他们的组织系统和权力结构都是严格的父权家长制。所以儒家伦理不仅是治国之指导,也是齐家的观念基础,而“孝亲崇祖”作为儒家伦理的核心观念重要性也就可见一斑。“男主外,女主内”是父权家长制的体现,也是儒家伦理的基本观念格局。可以说这两个观念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基础,不可动摇,任何的否定就是对儒家思想的全盘扬弃。对于自我意识强烈的士大夫来说,佛教思想是不得不排斥的,否则便是在否定国家的宗法体制。因此,在“外”的世界,士大夫们以排佛为首任从而复兴儒学,依儒家纲要治理社会,在“内”同样依此治家,要求女子“三从四德”。女子教育的文本无论是《女论语》《女诫》还是《烈女传》《孝女经》,都是以此作为理论支持。
但是礼佛女子参加各种佛事法会,必定会走出闺门,将自己暴露于众目之下。如墓志中有记载“岁时宗戚,趋寺庙以嬉”[2](宋)许景衡.横塘集·丁昌期妻蒋氏墓志铭[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十).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东南士女纷造席下,往往空闺门”[3](宋)邹浩.道乡集·寿昌县太君严氏墓志铭[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三十七).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这两则史料中蒋氏和严氏所批评的女子,她们迈出家门且“趋寺庙以嬉”,将自己置于睽睽众目之中。女子如此“抛头露面”之行径,必定引起士大夫们的不满与批评,原因主要有:第一,这一不合传统且有违妇德的做法给士大夫家族本身带来耻辱,将“莫窥外壁,莫出外庭”“出必掩面,窥必藏形”视为美德的观念中,“抛头露面”便成为不可为之的耻辱之行。而且儒家观念严格的“内外”之分,男子不介入女子做的事,当然女子亦不能闯入男子的领域[4](美)伊佩霞著.胡志宏译.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P25)。女子在外“抛头露面”,参加各种佛事活动已有“牝鸡司晨”之嫌疑了;第二,有些女子因忙于礼佛而置祭祀、孝亲之事于不顾,如陆游所言:“近世闺门之教略,妄以学佛自名,则于祭祀、宾客之事皆置不顾,惟私财贿以徇其好。”[5](宋)陆游.渭南文集·陆孺人墓志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三十三).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这违背了儒家最基本的“孝亲崇祖”观念,“娶妇所以承先祖、主中馈”[5],不能如此,则娶妇何用。
相对于男子的“治世之道”,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更强调女子的“治家之道”。男子若想在外有所作为,家庭的安宁有序是基础条件,特别是对上层阶级而言,家庭事务繁多。所以男子尤其是士大夫们对于能管理家中大小事务使生活秩序井然的女子总是赞誉有加。虞夫人因“江公从官事,先畴之入,恣兄弟衣食无所问”[6](宋)朱熹.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第九十二卷)[M].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P4251),朱熹特而志之,又赞美太孺人陈氏在丈夫周君“不以家人生产为事”的情况下“佐以勤敏,持家简而有法”[6](P4304)。在宜人丁氏的墓志铭中也特书其“居家严”“内外井井”[6](P4306)。李友直在赞美亡妻史氏时也突出了她管理方面的才能:“吾游太学久乃得仕。未尝屑意家事。凡出入有无,丰约之调度,皆吾嫔处之,不以累我。”在士大夫对女子“持家”“治家”能力的赞美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士大夫对于女子不理家事、将自己暴露于外的反感。基于上述“外”及“内”的原因,士大夫们才如此“反佛”。
士大夫对女子礼佛的态度上虽然存在着矛盾,但思想观念中却不存在冲突。原因在于士大夫对女子礼佛行为有一评价标准,即礼佛行为本身及其影响是否符合妇职所规定的内容。妇职正是儒家伦理的体现,那也就是说士大夫“反佛”或者“礼佛”的准绳是女子的礼佛行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维护还是违反了儒家伦理。
三、作为生活方式的礼佛:士大夫的选择?女子的选择?
礼佛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普遍地存在于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女子中,这是士大夫们的设定,还是女子们自主的选择,抑或是错综复杂的兼而有之?这答案也许需要在儒学发展的自身脉络中寻觅。
儒学虽然始终在中国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但功用已经大大减弱,尤其是魏晋后到隋唐,除了实际政治和贵族的门第礼法,儒家的领域已经大大丧失,至于最后的精神归宿,中国人不是归于道,就是归于佛。在此情况下,尤其是佛教的刺激和影响下,宋代士大夫们竭力排佛斥佛及重建儒家的基础和权威,夺回失去的领域以复兴儒家。
韩愈是中唐排佛兴儒的先驱,主要是从政治经济利益的角度揭露佛教对社会经济和国家造成的严重危害,要求“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来战胜佛教。北宋儒学的积极倡导者如范仲淹、欧阳修、石介、孙复、曾巩、张载、二程等从“夷夏之辨”、坏乱儒家圣贤之道、破坏传统伦理纲常等方面斥责佛教不尽孝道、无君臣父子,认为“儒齐驱并驾,峙而为三”[1](宋)孙复.孙明复小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三).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是为大辱。后来张载、二程等新儒学家则入室操戈,吸收改造释道哲理,对佛教进行了“内在批判”,斥责“佛氏逃父出家,便是绝人伦、背离君臣父子夫妇之道”[2](宋)程颢,程颐.二程集(上)[M].中华书局校点本,1981.(P148)。南宋朱熹更进一步,除政治经济、伦理道德方面的批判而外,从学术发展、构建儒学体系的需要出发“援佛入儒”,立足于儒家的伦理本位来阐明儒家自身的微言大义,在吸收的基础上建立新儒学理论体系,填补了心性理论的空白。
如果依旧用“内、外”的区分模式,在“外”的世界,儒家士大夫们对作为一种社会生活方式、一种思想哲学体系的佛教进行彻底的批判打击,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了儒家自身的理论体系,成为“内向超越”型的儒家,有了自己的彼岸——“天理世界”。而后作为一种更为包容的思想:在儒家政治主导的社会中容纳了佛教禅寺清幽生活这一别样的社会生活方式,也因自身完善具足的自信容纳了异端的思想体系[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P424-432)。
而在“内”的世界中,佛教已经深入了人们的家庭生活中,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普遍存在于士大夫阶层的女子中。士大夫亦是精心设计,以话语权利之笔,消融了家庭生活中的儒佛边界,儒家和佛教经典兼而修之,并在经典熏陶之下修炼高尚德行,这是很多礼佛女子的写照。如上引游夫人“焚香读儒佛书”[4](宋)朱熹.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第九十一卷)[M].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P4212),又如仁寿郡夫人李氏“尤好修身养性之术,每阅儒释书,欣然有所得”[5](宋)范祖禹.范太史集·保宁军节度观察留后东阳郡公妻仁寿郡夫人李氏墓志铭[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四十七).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是儒家经典还是佛教经典已不再重要,经典本身也不再是权威的象征,而只是一种手段,用来维护儒家家庭生活秩序的工具。所以,在儒家家庭生活框架下,手段可以是多样的,只需共同维护基本儒家伦理。
当然,在另一方面,女子作为礼佛主体依然有着选择的自主性,为什么选择佛教,为什么选择在家礼佛这一生活方式?也许可从佛教自身的发展中求解。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因魏晋的连年战乱,佛教乘虚而入,以其极乐的“彼岸”征服了中国上层思想界。魏晋以后佛教发生了重大影响,从唐代到宋代,佛教成为了中国思想和信仰的主流之一,并在一般人的生活中占据着中重要的位置。
唐代佛教的入世转向更为女子的选择提供了可能性。惠能创立的禅宗以“不立文字”“直至本心”使佛教信众大大扩展,教育程度不高的妇女和大众都可归于门下。而惠能的“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之说,使得修行更深得扎根于人们的生活中,成为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百丈怀海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更是让日常的劳作有了佛教“入世苦行”的精神依托。《华严经》云“佛法即世间法,世间法即佛法”[1](唐)实叉难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五十四)[M].大正藏(第10卷).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P285),说明佛教的世界不仅仅只在彼岸,不仅仅是来世的精神依托,可以说,佛教在此世也具有了精神指导意义,成为最高的法则。佛教教义不再消极地否定此世的无明,深居寺院精进修持,待得涅槃解脱,而是入世尽人的本分,经过此世的磨砺,度人世间一切苦厄,才得登彼岸极乐世界。佛教不仅是人们最后的精神归宿,而且进一步开始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P402-408)。
佛教对于世俗生活的亲近以及“援儒入佛”的积极契合,剔除有悖于儒家思想的众多观念和仪式,同时佛教思想本身众多解释世界社会的维度也符合了女子的心理诉求,还发展了更普遍更易于接受的修行仪式,如在家修行、带发修行等,给女子提供了礼佛之平台。相比之下,佛教思想便是女子最优的选择,礼佛成了最易实施的修行。
士大夫对女子礼佛虽然有两种心态,但应该注意的是,无论是“反佛”或者“礼佛”,士大夫所针对的目标并非是“佛”,而是女子礼佛行为及其社会作用。或者更确切地说,“反佛”与“礼佛”虽然各执一端,态度迥异,但其所持的价值标准却是同一的,即女子的行为是否符合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在宋代儒学复兴与重建的过程中,在士大夫排佛斥佛的声音中,与士大夫联系最紧密、接触最频繁的人——母亲、妻子和女儿却是佛教的信仰者,在家礼佛成为她们的生活方式。士大夫的排佛与其家人的礼佛并存的事实虽然极为怪异,但事实上两者是以一事之两面展开,排佛是为了重建儒家的社会秩序,容忍家人礼佛亦是建立儒家社会秩序。如此,宋代社会中女子礼佛的普遍现象自有其社会依据与根源。
——士大夫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