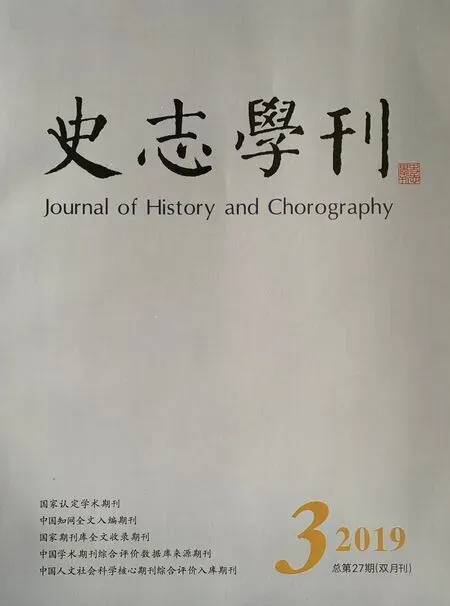西夏“水军”新考
田晓霈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宁夏银川750021)
历史上关于西夏水军的记载十分匮乏,传统史籍中仅见三条材料有所涉及。陈炳应先生在《西夏军队的兵种兵源初探》一文中引据此三条材料提到西夏在大河沿岸设有数量不多的水军[1]陈炳应.西夏军队的兵种兵源初探[J].固原师专学报,1989,(1).(P12)。但本文经过考证,认为以上三处记载作为判断西夏水军存在的证据尚存疑点,西夏“水军”问题的真实情况如何,有无正规编制?迄今尚未得到关注和研究。本文拟通过对传统史料的辩证分析,结合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相关条文,对西夏的“水军”问题做重新考证,以求教方家。
一
《宋会要》载熙宁三年(1070)三月十八日诏“河东所报探西贼水军恐于石州渡河,令吕公弼过为之备”[2]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点校.宋会要辑稿(方域二○)[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P9687);《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元祐六年(1091),熙河路经略司言:“有西界水贼数十人俘渡过河,射伤伏路人,寻斗敌,生擒九人”[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四).元祐六年八月癸丑条[M].中华书局,2004.(P11092);《宋史·地理志》载:“政和六年,筑清水河新城,赐名(德威城),属秦凤路……河北倚卓啰监军地分,水贼作过去处。”[4](元)脱脱.宋史(卷八十七)[M].中华书局,1977.(P2160)陈炳应先生在《西夏军队的兵种兵源初探》中据此认为西夏存在数量不多的水军。但本文认为以上三条材料是否足以论证西夏存在水军建制有待考辨。第一条史料来源于熙宁三年三月十八日,此时正是宋夏绥州之战前夕,一个月后西夏即发兵2万来争绥州,当时的西夏军队也极有可能是向绥州逼近。石州位于绥州以东,其地三面临水,北、西、南分别有北川河、离石水和宁乡水。离石水向西汇入黄河,后来宋于元丰五年(1082)在此汇口置吴堡寨[5](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百十六)[M].中华书局,2011.(P8585)。史称此处黄河“河东西俱在万山中”[6]杨守敬,熊会贞疏,杨甦宏,杨世灿,杨未冬补.水经注疏补(卷三)[M].中华书局,2013.(P240),两侧皆是山地,因此夏军很有可能是沿离石水河谷向西横渡黄河。所以这条材料所描述的“西贼水军”,只是渡过黄河而已。如此不禁设问,仅仅渡河算不算“水军”?所谓水军,应该是能够完成水上作战任务的兵种。宋初为平定江南,宋太祖“出内府钱,募诸军子弟数千人,凿池于朱明门外,引蔡水注之。造楼船百艘,选卒,号水虎捷,习战池中。命右神武统军陈承昭董其役”[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乾德元年夏四月庚寅条[M].中华书局,2004.(P89),后改称虎翼水军,这是正式的水军建制。而这里的夏军目的是争夺绥州城,仍须骑兵和步兵发挥作用,渡河只是行军必要,没有水上作战的任务。事实上,史籍中描述西夏的骑兵也完成过多次渡河任务,元丰五年的永乐城之战中重甲骑兵“铁鹞子”曾渡无定河,“是日,悖麻先纵铁鹞军渡河,曲珍望见,白禧曰:‘此锐卒也,当半渡击之,乃可以逞,得地则不可当也。’禧不从。铁骑既渡,震荡驰突,大众继之,禧众大败。”[2](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二十六)[M].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P297)所以,仅仅渡河并不能称为水军,《宋会要》所言称的“水军”事实上只是渡河的步兵和骑兵,不可偏执为据。
第二条材料出自元祐六年(1091)。元祐二年至元祐七年,西夏国相梁乙逋正频繁进攻兰会一带,经过先前的灵州和永乐城会战,宋夏双方损失惨重,政治保守的元祐党人重拾消极防守战略,无心组织新的争夺战。西夏也已军力疲惫,梁乙逋的政治意图一定程度上并非夺城争地,而是包含着转移国内不满情绪,加强个人对军队管控的因素,有些进攻具有骚扰性以争取战略上的主动,并非全力出击,宋人称当时“夏兵慓悍,倏忽往来,未尝久顿”[3](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二十八)[M].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P319)。所以这些进攻兵力很少,宋人以“水贼”蔑之,体现出人数小众,并且同样没有体现出明显的水上作战特点,仍然是渡河后在陆上击敌。第三条材料中同样以“水贼”称之,理由同上。
二
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有几则材料值得注意。《渡船门》中有:“一河水上置船舶处左右十里以内,不许诸人免税渡船……船舶左右十里以外有渡船者,不许船主诸人等骚扰索贿。”[4]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M].法律出版社,2000.(P392)《缴买卖税门》中还有“船上畜税”[4](P562)字样。西夏的确在河流渡口有专门负责行船渡水的人员,而且人畜渡船皆要收税,说明是官方设置经营的渡口,行船者称“船主”。此外,《军持兵器供给门》显示,“船主”还允许配给兵器战具,具备一定的军事防御功能。《敕禁门》记:
“诸人由水上运钱,到敌界买卖时,渡船主、掌检警口者等罪,按卖敕禁畜物状法判断以外,其余人知闻。”[4](P287)
《敌军寇门》中还有:
一边地敌军盗贼入寇者来,守更口者先监察,报告局分处,已派遣监视军情者,及说敌军动向,来处,水、陆、道口、地名等使明时,所派遣监视军情者不好好监视军情,大意失察。先水、陆、道口、地名等使明时,敌军来,失察而使穿入地面者,按穿入多少,与大检主管失察罪相同判断[4](P213)。
可见,西夏在重要的水陆津要设置有职管人员,归属局分处管理。“守更口者”“检警口者”既负有军事布防任务,也兼负查禁本国贩卖钱币的走私贸易行为。在这里“渡船主”与“检警口者”共同构成军事布防体系,后者主要负责监查军情,前者在平时收税渡民,发挥民用功能,但同时又配有军事装备,一旦遭遇敌情可当即进行军事守卫和还击,具有兵民合一的职能。舍此之外,西夏史料中再未见到任何有关涉水军事内容的记载,因此,宋人史籍中所云的“西界水贼”极有可能就是西夏的“渡船主”。
“渡船主”在西夏属于较为重要的职属。《矫误门》中有“一等任重职部、溜,依下所示避重职而为轻职,及由边军至中地,由种种转院部而为敕院不同等处,一律当绞杀:牧主、门楼主、侍奉帐者、船舶主……”[1]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M].法律出版社,2000.(P385)。“渡船主”犯罪还可以以官抵罪,《罪则不同门》载:“牧、农、车、舟主,相军、乐人、种种工匠等犯十恶,罪本获死而获长期、因盗犯大罪当获死而获长期中,依有官及减免等法判断,当遣送为苦役处。”[1](P615)此外,“渡船主”有属于个人的“使军”“奴仆”。《戴铁枷门》中有“牧、农、舟、车主等四类人及诸人所属使军、奴仆等犯种种罪时,长期徒刑”。“使军”“奴仆”是西夏较为特殊的阶层,史金波先生认为西夏的使军大约相当于唐宋时期的部曲[2]史金波.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卖人口契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104,(4).(P126)。杜建录先生认为使军为依附于贵族地主的农奴[3]杜建录.西夏阶级结构研究[J].固原师专学报,1998,(4).(P51-56)。总之,他们在西夏社会属于具有人身依附关系的贱民阶层,“渡船主”有私属奴仆,相当于奴隶主阶层,具有一定社会地位。
那么这个“渡船主”是否属于“水军”呢?前揭,水军之所以能够称之为“军”,是其独立于步兵和骑兵之外的一个有独立编制的兵种。以宋代为例,宋代水军由沿江都制置使司统辖,“掌經畫邊鄙軍旅之事”[4](元)脱脱.宋史(卷一百六十七)[M].中华书局,1977.(P3955),绍兴八年(1138),在平定杨幺起义军时,宋军布防“以水军万人分五军,每军二千人,用车船二只,每只容正兵二百五十人,将佐梢工百人鳅船三十只,每只容正兵五十人,并棹夫、押队共八十二人,各令附带钱粮,多集矢石,其行常与鳅船一进一郤,进必有所取,却必有所诱,亦计之上者也。”[5](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十六)[M].中华书局,1988.(P1116-1117)可见宋水军有专门的管理体制,士卒和战船有机组合成了军事编制,并且梢工、棹夫、押队等各司其职,有针对水面作战的战术准备。相比之下,西夏的“渡船主”主要职能限定在对河流渡口的管理,不立军籍,不设统帅,没有针对性的军事训练,与真正意义上的“水军”有一定差距。
事实上,在河流渡口布置监察警卫机制宋、金皆有。宋代在重要的河流渡口处设置有监渡官和巡检,主管各处津渡事务[6]王坤.宋代津渡管理研究[D].安徽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主要职能有三:第一,经营官渡。宋代对河流渡口严格管控,由官府“缮治舟舰,选募篙梢”[7](元)脱脱.宋史(卷九十七)[M].中华书局,1977.(P2413),监渡官对在渡口用船渡河的人按例收费,“南北津渡,务在利涉,不容简忽而但求征课。”[7](P2413)第二,纠察敌奸。为防止北方辽、金军事间谍渗入宋境,在与国边界的渡口担负起军事预防的职能。隆兴元年(1163),宋臣奏言:“归正人略无来历因依,虑影匿奸细。措置下诸渡密切伺察,如有透漏,监渡并巡铺各黜官一等罢任。任内无透漏,进官如之。”[8]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三)[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P9537)第三,查禁走私。绍兴和议之后,宋金两国先后于边界设置了十余处榷场,但依然不能禁绝民间私贩贸易的出现,渡淮河私贩者屡屡不绝,宋人令监渡官“渡口检察,方令上舡”[9]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P6847)。金朝在河流渡口设有排岸官。《金史》有载一则事例,金臣肩龙与宰相侯挚相处不睦,“留数月罢归,将渡河,与排岸官纷竞,搜箧中,得军马粮料名数及利害数事,疑其为奸人侦伺者,系归德狱根勘。适从坦至,立救出之。”[10](元)脱脱.金史(卷一百二十三)[M].中华书局,1975.(P2692)“从坦”是金朝宗室将领,肩龙曾帮其剔除冤案,肩龙在渡河时因与排岸官口舌纠纷,意外泄露军事信息被误认为是敌国奸细,被捕入狱,从坦出面舒解将其救出。由此事可以看出金朝的排岸官同样担负着排查军事奸细的职责。
不难看出,宋代的“监渡官”、金朝的“排岸官”,与西夏的“渡船主”“检警口者”职责十分相似,是政府设在重要河流渡口的安全检查人员。一方面将河流作为国有资产,通过收取渡船税费来补充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也是国家国防事务的监察者,对内禁绝违法外出,对外预警敌国情报。相比之下,西夏的“渡船主”配给军事装备,具备一定的军事抗击能力,故而宋人蔑称为“水贼”。但即便如此,它仍然是国家专门设于河口关卡的管理职员,并不归属军事编制,更没有任何信息显示西夏将其作为独立的兵种组编为水军。因此,与其将“渡船主”言称“水军”,不如将其定位为主管河渡事务的津渡官更为恰当!前文所述三条出现西夏“水军”字样的文献,皆出自宋人记载,前文已对内容进行辩误考证。如果西夏真的有正规的水军建制,那么在西夏人自己编修的官方文献中必然留有痕迹,然而无论是官方法典《天盛律令》还是专门的军事法典《贞观玉镜将》中,均未出现任何符合前述水军编制特征的条文。所以可以判定,西夏并未形成正式的水军建制,只是宋人将具备一定军事防御功能的“津渡官”或渡河步骑兵误称为“水军”而已。
三
西夏自身虽然没有发展成正规水军,但在和邻国的交战史上,却遭遇过敌国水军的攻击。西夏第一代国君李元昊在位末期辽夏关系恶化,辽重熙十五年(1046),辽兴宗就曾动用水军攻夏。《辽史·萧蒲奴传》载:“十五年,为西南面招讨使,西征夏国。蒲奴以兵二千据河桥,聚巨舰数十艘,仍作大钩,人莫测。战之日,布舟于河,绵亘三十余里。”李谅祚即位后,辽夏仍有争战,辽重熙十七年,兴宗再造战舰,“命铎轸相地及造战舰,因成楼船百三十艘。上置兵,下立马,规制坚壮,称旨。及西征,诏铎轸率兵由别道进,会于河滨。敌兵阻河而阵,帝御战舰绝河击之,大捷而归,亲赐卮酒。”[1](元)脱脱.辽史(卷九十三)[M].中华书局,1974.(P1379)十八年复征西夏,“(萧)惠自河南进,战舰粮船绵亘数百里。”[1](P1375)可见辽国已经可以在水战中熟练使用大型战船,水军也已经具备一定规模。
西夏境内有黄河、渭水及其众多支流,渡水行船以及沿河布防有必要的现实需求,故仿照宋、金沿河设置了津渡管理机制。但和宋、金的津渡官相比,西夏在军事布防方面除了排查敌国间谍之外,更突出了监测敌情的军事警卫职能。“守更口者”发现后及时报告局分处,须明确指认敌军出现的地点和行军路线,并且对“渡船主”配给兵器。此外,西夏虽然没有形成一支正规的水上军队,但却有一定规模的造船业。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内宫待命等头项门》记载:“御舟不固者,营造者工匠人员等当绞杀,头监、检校者等徒十二年、若行用时为诸人所盗损,水贯出而底上折毁不固,不堪行用,则盗者造意当绞杀,从犯徒十二年。若船舷及其他无碍处少有盗损者,造意徒十年,从犯徒六年。”[2]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M].法律出版社,2000.(P431)证明西夏有专门为皇家打造舰船的工匠,官方对其修造质量严格要求,如果出现瑕疵,工匠本人及其监察者皆依法治罪。《天盛律令》中还有《舟船门》,由于文献残损,只保留下少部分条文残句:“制造船及行日”“大意制做舟船坏”“盗减应用日未满船坏”“船沉失畜人物”“制船未牢水中坏”“铁钉未及式样”“应用未减制船未牢日未满坏”“造船及行牢等赏”[2](P563-564)。水军的建设离不开造船业的支撑。可以看出西夏造船业是官营,官方对舰船的样式、修造细则均有明确规范,已初具规模。虽然没有信息证明所造之官船有充归军用,但船舶制造业的积累,为军事的发展做了技术上的准备。因此,我们是否可以据此推测,西夏正是迫于战争和现实需要,原本有意组建一支正式的水军,故而使“渡船主”配备战具,不仅纠察间谍、查禁走私,更特别强调监察敌军来犯,军事意义相对突出,才有了宋人口中的“西界水贼数十人俘渡过河,射伤伏路人”这种小规模军事攻击。然而最终并未形成正式规模,仅仅作为一种雏形和萌芽存在于西夏历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