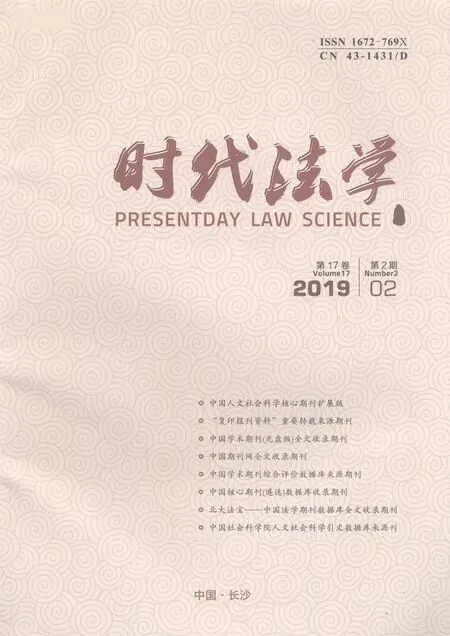诉讼中的第三方资助协议研究:域外经验与中国选择*
吴维锭
(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871)
一、 问题的提出
第三方资助(Third-Party Funding)这种由非争议当事人出于盈利目的向当事人一方提供无追索权的资助同时从被资助人胜诉裁判中获取一定比例的收益作为回报[注]第三方资助尚未有统一的定义,本文研究的模型限定在民商事纠纷中,资助人为具有盈利目的的商业机构,被资助人为民事诉讼中的原告,资助形式为无追索权资助的第三方资助。这种第三方资助也是最为典型的定义。具体的讨论限于民事诉讼这一争议解决程序。See Maya Steinitz, “The Litigation Finance Contract”, William & Mary Law Review, Vol. 54, Issue 2(November 2012), p. 459.的法律实践发展十分迅速,在国外已经十分普遍,在国内也在逐渐兴起[注]截止至2018年2月,国内从事第三方资助业务的机构和平台至少包括多盟诉讼融资基金、前海鼎颂投资、为安法律金融、赢火虫诉讼投资、盛诉无忧和律诉网等。参见多层次资本市场联盟.多盟诉讼融资白皮书[EB/OL].(2018-07-17)[2018-9-29]. http://www.lawsuitfund.net/index.php/companynews/351.html.,以至于著名的国际研究机构兰德公司高度评价第三方资助为“民事司法领域最大最具有影响力的趋势之一”[注]See RAND CORPORATION. Third Party Litigation Funding and Claim Transfer[EB/OL]. (2009-06-02) [2018-10-01].http://www.rand.org/events/2009/06/02.html.。与实践的燎原之势对应的是学界的风起云涌,国外法学界和经济学界对第三方资助的关注度急剧上升[注]See Julia Shamir, “Saving Third—Party Litigation Financing”, Northwestern Interdisciplinary Law Review, Vol. 9, 2016, pp. 189.,相关论文产量猛增[注]在法律全文数据库HeinOnline上的Law Journal Library子库中以“third party funding”为关键词检索到135,094篇文献,在该检索基础上再以“control over the litigation”为关键词进行结果检索,搜索到69290篇文献,占比为51.3%。。而反观国内对于第三方资助的研究,不仅仅发表的文献数量少[注]在知网(CNKI)上以“SU=‘仲裁’*(‘第三方融资’+‘第三方资助’+‘第三方出资’)”为检索式进行检索得到的文献共有41篇。(除去重合),而且在研究偏向上存在一定的缺失。国内学界对第三方资助的研究几乎都聚焦于第三方资助这种法律现象对民事诉讼和商事仲裁程序本身的负面影响和相应对策上,诸如滥诉问题[注]郭华春. 第三方资助国际投资仲裁之滥诉风险与防治[J]. 国际经济法学刊,2014,(2):85-97;肖芳.国际投资仲裁第三方资助的规制困境与出路——以国际投资仲裁“正当性危机”及其改革为背景[J].政法论坛,2017,35,(6):69-83.、利益冲突问题[注]徐树.国际投资仲裁的第三方出资及其规制.北京仲裁,2013,(2):39-50;丁汉韬. 论第三方出资下商事仲裁披露义务规则之完善[J]. 武大国际法评论,2016,(2):220-235;周艳云,周忠学. 第三方资助国际商事仲裁中受资方披露义务的规制——基于“一带一路”视阈[J]. 广西社会科学,2018,(2):101-106.和费用问题[注]史晴霞. 国际仲裁中第三方资助问题研究[J]. 法大研究生,2017,(2):445-460.等,而对于第三方资助协议本身的法律性质和效力问题特别是程序控制条款的效力[注]现有文献中仅有一篇对此问题进行了略微分析,参见覃华平. 国际仲裁中的第三方资助:问题与规制[J].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8,(1):54-66,207.研究极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国外同主题的文献中涉及到第三方资助协议本身特别是程序控制条款效力讨论的文章却占据其整个文献体量的半壁江山[注]在法律全文数据库HeinOnline上的Law Journal Library子库中以“third party funding”为关键词检索到135,094篇文献,在该检索基础上再以“control over the litigation”为关键词进行结果检索,搜索到69290篇文献,占比为51.3%。。国内文献对第三方资助协议本身研究的缺失值得我们反思,因为除去国外文献的事实证据,仅仅从发生学和逻辑上来看,也是先有第三方资助及其协议本身,然后才会有第三方资助对民事诉讼和商事仲裁程序的影响。越过第三方资助及其协议本身的研究,直接分析其影响无异于“未爬先走”。鉴于此,本文的中心即是分析第三方资助协议本身的内容、性质和效力,特别是其中富有争议的程序控制条款的法律效力问题,以便站在国内立场上回答中国要不要认可第三方资助协议,如果认可,要认可何种程度或类型的第三方资助协议。
本文的主体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界定第三方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并且分析资助协议的法律性质;第二部分聚焦于国外对于第三方资助协议本身特别是其中的程序控制条款的法律效力的争论;第三部分则站在中国国内法的立场分析适合我国国情的第三方资助协议规则和司法态度。
二、第三方资助协议的法律性质:独立合同之辩
从外围研究第三方资助,而忽视第三方资助本身特别是作为核心的资助协议似乎是学界的一个特点[注]See supra note 4, at 152.,这种研究方向的“默契”固然与第三方资助协议本身的保密性有关[注]See Maya Steinitz, “Whose Claim is This Anyway—Third-Party Litigation Funding”, Minnesota Law Review, Vol. 95, Issue 4 (2011), p. 1270.,但是考虑到资助协议是整个第三方资助法律关系的基础[注]See Maya Steinitz, supra note 1, at 463.,所以非常有必要厘清资助协议的内容。
(一)第三方资助协议的内容
1.要素一:费用资助条款和回报补偿条款
第三方资助协议中第一类必备条款是费用资助条款(indemnification clause)。该条款规定的是资助人向被资助人提供争议解决程序中的费用的合同义务,比如律师费、调查费等。实践中该条款往往有多种表述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全额承担不封顶型”。在这种费用资助条款中,资助人的资助义务在金额上是不设限的且承担的是被资助人在程序中的全部费用,资助人有义务支付被资助的原告依据法庭裁判应当支付的任何不利费用(any adverse costs),比如“Metzler Investment GmbH v. Gildan Activewear Inc.”[注]See Metzler Investment GmbH v. Gildan Activewear Inc. (2009), 81 C.P.C. (6th) 384, [2009] O. J. No. 3315 (Ont. S.C.J.).案中,原告和第三方资助机构达成的资助协议中即约定资助人同意支付原告依据法庭判决应当承担的任何不利费用,资助人的义务没有封顶。第二种形式的费用资助条款是上一类型的变种,为“份额承担不封顶型”。虽然资助人在可能承担的最终费用上也没有限度,但是相比“全额承担不封顶型”,资助方不需要全额承担法庭裁判的不利费用,而是根据一定的份额比例承担该不利费用。这种类型的费用资助条款在著名的全球第三方资助机构百福德资本(Burford Capital)提供的第三方资助协议条款中十分常见,协议中百福德资本的义务是向被资助人提供一定比例的诉讼中费用,而且比例越高,其获取的收益比例也会越高[注]这种条款被冠以一个形象的名称——“瀑布交易”(a Waterfall Deal)。See Michele DeStefano, “Claim Funders and Commercial Claim Holders: A Common Interest or a Common Problem”, DePaul Law Review, Vol. 63, Issue 2 (Winter 2014), p. 319.。第三种类型的费用资助条款是“封顶型”。该类型下资助第三方的资助义务在数额上存在一个绝对限度,超越该限度后资助人没有义务再向被资助人提供资金,例如在“Dugal v. Manulife Financial Corp.”[注]See Dugal v. Manulife Financial Corp. (2011), 105 0.R. (3d) 364, [2011] O.J. No. 1239 (Ont. S.C.J.), supp. reasons 218 A.C.W.S. (3d) 760, [2011] O.J. No. 3493 (Ont. S.C.J.).案中原告与资助人签订的资助协议中约定资助人资助金额限制在5万美元。这意味着当资助人的资助金额超过5万美元时,被资助人即无权请求资助人进行更多的支出。同样类型的费用资助条款也出现在了Chevron案[注]See Chevron Corp. v. Donziger, 768 F. Supp. 2d 581, 621 (S.D.N.Y. 2011).中,在该案的第三方资助协议中,资助人百福德资本的义务是分第三轮投入资金,第一轮投入400万美元,第二轮和第三轮分别投入550万美元。超过1500万美元,百福德资本即无义务再行投资。
回报补偿条款(commission clause)是第三方资助协议中的第二类必备条款。它规定资助人有权从被资助人胜诉裁判中分享的金额比例。从现有的实践来看,回报补偿条款可以区分为“封顶型”和“不封顶型”两种类型。“封顶型”回报补偿条款下,资助人能够从被资助人胜诉裁判中获取的经济利益存在上限,比如在“Dugal v. Manulife Financial Corp.”案的第三方资助协议中,资助人有权利从最终的裁判或者调解协议中获得7%的佣金,但是根据纠纷最终得到解决的情况,资助人获得的佣金不得超过5百万或者1千万美元[注]See supra note 17. Also see Charles M. Wright & Anthony O’Brien, “Third-Party Funding for Class Actions, and Control over the Litigation”, Canadian Business Law Journal, Vol. 55, Issue 1 (March 2014), p. 169.。与此相反的是“不封顶型”回报补偿条款下,资助人对于被资助人从胜诉裁判中分享的利益虽然有比例限制,但是却没有绝对的数额限制,这意味着资助人能够获得的经济利益将随着最终裁判或者调解结果的增加而增加。“Metzler Investment GmbH v. Gildan Activewear Inc.”案中即是如此,资助方能够获得的佣金比例同样是最终裁判或调解协议的7%,但是没有一个绝对的最高数额限制[注]SeeCharles M. Wright & Anthony O’Brien, “Third-Party Funding for Class Actions, and Control over the Litigation”, Canadian Business Law Journal, Vol. 55, Issue 1 (March 2014), p. 168.。
2.要素二:程序控制条款
第三方资助协议中第三类比较常见而有意思的条款是程序控制条款(control clause)。该类条款的主旨是赋予非当事方的资助人以对案件程序一定的控制权以保护资助人对被资助人的投资的安全性和盈利性。实践中资助第三方根据资助协议能够享有的程序控制权各色各样,根据其享有的程序控制权大小,程序控制条款可以被划分为两种类型:“轻度控制型”(Minor Control)和“深度控制型”(Heavy Control)[注]有其他文献采取的是其他的分类方法,比如“relatively minor control”和“almost complete control”,参见Anthony J. Sebok, “The Inauthentic Claim”, Vanderbilt Law Review, Vol. 64, Issue 1 (January 2011), p.109. 还有文献采取的分法是“passive model”和“active model”,see Michele DeStefano, supra note 16, at 320.这些分类方法与笔者提出的方法类似,重在区分资助人对争议解决程序的控制程度。。“轻度控制型”程序控制条款下资助人对争议解决程序的介入十分有限,其地位就像“赌马比赛中的下注者”:一旦下注,就只能站在赛道外静待比赛结果[注]See Michele DeStefano, supra note 16, at 320.。资助人享有的程序控制权内容因而十分狭窄,一般仅仅为对案件的知情权,包括诉讼策略和胜率等。在这种条款下,资助人不能控制或者参与到任何有关诉讼程序的决定中来,包括律师的选择、和解、诉讼策略决定和协商等[注]Ibid, at 321.。典型的案例是Dugal案[注]See supra note 17, at para. 6.,该案的资助协议约定,资助人有权了解争议解决程序中包括胜诉率和诉讼策略在内的任何重要事件,并且为了获得有关程序的任何信息可以向原告和律师提出任何合理请求。但是同时,资助人承认案件的律师代表的是原告而不是资助人,只有原告有权利指示律师。“深度控制型”程序控制条款下资助人对争议解决程序介入的程度更加深入,享有广泛的控制权利。资助人不仅仅享有对案件程序进展信息的知情权,而且在被资助人诉讼策略的选取、律师的选择、协商与和解协议的签订等方面享有决定权[注]See Vicki Waye, “Conflicts of Interests between Claimholders, Lawyers and Litigation Entrepreneurs”, Bond Law Review, Vol. 19, Issue 1 (2007), pp. 253-254.。在Chevron/Ecuador案涉及到的资助协议中,资助人有权决定被资助人的诉讼策略、律师的选取及任何和解协议的签订[注]SeeMaya Steinitz, supra note 14, at 471.。而在澳大利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Fostif案[注]See Campbells Cash & Carry Pty Ltd. v Fostif Pty Ltd. (2006) 229 C.L.R. 386, 413 (Austl.).中,涉案的第三方资助协议下资助人甚至被视为原告代理律师的客户。
(二)第三方资助协议的法律性质:独立合同之辩
厘清第三方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后,一个新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第三方资助协议是何种性质的合同[注]本文不区分“协议”和“合同”用语之间的区别。?它是已有的合同类型中的一种还是一种独立于典型合同的新型合同?如果说探寻第三方资助协议的内容是一个事实问题,那么分析资助协议的法律性质无疑是一个法律问题。对资助协议的法律性质的认定,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用何种法律规则框架去规制这种协议,进而决定了这种协议的法律效力。
1.非独立合同
现有文献在考量第三方资助协议时往往是站在“学术效率”的立场,试图将资助协议直接纳入某一有名合同的规则范围,因而认为资助协议并不是一种独立合同,其实质是某一类典型合同,比如贷款合同、合伙合同、投资合同、买卖合同和保险合同等。例如有文献认为资助协议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可能是借贷合同或者投资合同[注]张光磊. 第三方诉讼融资:通往司法救济的商业化路径[J].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6,(3):24-35,159.。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一方面第三方资助协议很难被认定为一种借贷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96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借款人的还款义务是确定的,还款数额也是十分明确的,但是资助协议下被资助人与资助人分享胜诉利益的义务(还款义务)的有无和最终分享的利益数额(还款数额)都是不确定的,取决于最终的诉讼或仲裁结果。即使资助协议下资助人能够获取的经济利益十分确定,与借贷合同还款义务本身的确定性还是存在差异,不可同日而语。另外一方面也不能将资助协议简单认定为一种投资合同,因为投资合同是否属于典型合同,其内容和法律性质是否确定也是一个问题;也有观点将资助协议视为一种权利转让合同(claim transfer),即通过资助协议被资助人让渡了其实体权利的部分给资助人,发生争议的实体权利实际由被资助人和资助人共同享有[注]See Maya Steinitz, supra note 13, at 1323. Also see at Michele DeStefano, “Nonlawyers Influence Lawyers: Too Many Cooks in the Kitchen or Stone Soup”, Fordham Law Review, Vol. 80, Issue 6 (May 2012), p. 2823.。这种观点很有理论解释力度,但是与实践中资助协议的内容和当事人的意志不符,现行的资助协议主要条款中只有费用资助、回报补偿和程序控制三类条款,并没有权利转让条款;还有观点认为资助协议实际上是一种隐名合伙合同(a Silent Partnership),合伙的目的是通过共同“经营”争议解决程序获取盈利。其中资助人作为隐名合伙人不参与合伙事业的管理(参与案件程序),其财产也独立于合伙。原告是显名合伙人,代表并且经营整个合伙,对合伙事业承担无限责任。随着案件的最终裁判,整个合伙根据合伙合同(资助协议)的约定进行清算[注]See Marco de Morpurgo, “A Comparative Legal and Economic Approach to Third-Party Litigation Funding”, Cardoz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Vol. 19, Issue 2 (Spring 2011), p. 402.。这种观点虽然很有说服力和想象力但是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在第三方资助协议中存在着程序控制条款,籍借该条款资助人获得了对诉讼程序一定的控制权,进而参与到案件的管理中来(合伙事业的管理),这与隐名合伙人的消极不作为状态是存在矛盾和抵触的。
2.独立合同:程序实体混合合同
无论是把资助协议当作是借贷合同、投资合同、权利转让合同或者是隐名合伙合同,都无法完满刻画资助协议的法律性质。分析资助协议的法律性质必须通盘考虑协议的全部主要条款,包括费用资助条款、回报补偿条款和程序控制条款。但是这些观点往往只考量了费用资助条款和回报补偿条款这些涉及到实体权利的约定,而忽视了处分被资助人的程序权利的程序控制条款。实际上,这些观点在分析资助协议的法律性质时已经先验性地将这种协议视为关于实体权利约定的实体合同,所以才会有意识地忽视资助协议中关于程序权利的约定。而借贷合同、投资合同、权利转让合同或者是隐名合伙合同都是有关实体权利义务约定的实体合同,必然无法涵盖兼具程序权利处分的资助协议。
笔者发现第三方资助协议并非纯粹的有关实体权利义务约定的实体合同,而是兼具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处分的实体程序混合合同。资助协议中存在两种性质不同的约款,第一种是费用资助条款和回报补偿条款,这两类条款的内容涉及到的是实体权利设置,比如费用资助条款赋予被资助人从资助人处获取资助的权利,而回报补偿条款则使得资助人有权分享被资助人胜诉裁判中的经济利益;另一种属于程序权利约款即程序控制条款,触及到程序权利的处分,依据程序控制条款被资助人将其在诉讼程序中享有的程序权利(诉讼策略的选取、律师的选择、协商与和解协议的签订等方面享有的决定权)让渡给了被资助人[注]这种让渡或处分是否有效或者说程序控制条款的法律效力如何正是下文讨论的中心。,如此一来原本属于原告决定的程序事项必须听从资助人的调遣,选择何种诉讼策略、委托哪位律师,是否和解或接受调解等必须由资助人决定而非原告。
事实上,学界早已注意到了处分实体权利的合同和处分程序权利的合同之间的区别。例如“民事诉权合同”[注]巢志雄. 民事诉权合同研究——兼论我国司法裁判经验对法学理论发展的影响[J]. 法学家,2017,(1):32-47,176.这一处分民事诉权的合同,在性质上与本文探讨的第三方资助协议中的程序控制条款相同,属于程序权利处分合同而非实体权利处分合同。
三、第三方资助协议的法律效力:撕裂的实践
探析第三方资助协议的法律性质,固然是为了增进对这种协议的主观认识,但是最终目的还是判断其法律效力。从全球范围来看,立法和司法对第三方资助协议本身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普遍绝对禁止到逐渐“适度”允许的转变。之所以说这种允许是“适度”的是因为一方面仍然有部分国家和地区不承认第三方资助协议的效力,另一方面,即便在那些认可第三方资助行为的国家和地区,资助协议得到立法和司法支持的程度也存在区分。这些对第三方资助协议持宽容态度的国家地区往往一致认可资助协议中的费用资助条款和回报补偿条款[注]虽然回报补偿条款的法律效力在学界的争论不大,但是不代表在司法实践中该条款不会纳入法庭的考量范围,实际上法庭经常会审查该类条款,以防止不合理的条款出现,See Michele DeStefano, supra note 30, at 2821.,但是对程序控制条款的态度分歧很大:有些判例认可程序控制条款的效力和资助人藉由该条款获得的对争议解决程序的控制权,而有些案例倾向于资助人在资助的争议程序中扮演消极角色因而否定程序控制条款的法律效力。程序控制条款的效力问题也在学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形成了有效和无效两派对峙观点。
根据对第三方资助协议的官方态度,我们可以把现有国家和地区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态度最开放的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其不仅仅认可资助协议中的费用资助条款和回报补偿条款,而且也认可协议中的程序控制条款;第二类国家态度较为折中,比如英国、加拿大和新加坡等,虽然承认资助协议中的费用资助条款和回报补偿条款,但是否认资助人在争议解决程序中的程序控制权;第三类国家和地区的态度最为闭塞,根本排斥任何资助诉讼的行为[注]See Kraft v. Mason, 668 So. 2d 679, 682 (Fla. Dist. Ct. App. 1996).。值得思考的是为何不同国家地区对于第三方资助协议的态度存在如此大的区别?为何有些国家对第三方资助协议的态度从不支持逐渐走向支持而有些国家依然排斥第三方资助?又为何部分国家认可资助人对争议解决程序的控制而部分国家则否定?下文将基于判例和立法分析这些问题。
(一)第三方资助协议的法律效力:绝对禁止到适度允许
第三方资助原告提起争议解决程序的实践刚开始受到司法体系的绝对禁止,因为这种行为违反了“禁止助讼与帮讼分利规则”(the rule against maintenance and champerty)[注]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Maintenance and Champerty please take a look at Percy H. Winfield, “History of Maintenance and Champerty”, Law Quarterly Review, Vol. 35, Issue 1(1919), pp. 50-72, also see Ari Dobner, “Litigation for Sal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Vol. 144, Issue 4 (April 1996), pp. 1543-1545.。严格来说助讼(Maintenance)与帮讼分利(Champerty)并非同一层级的概念。根据《布维尔法律词典》(Bouvier Law Dictionary)[注]此词典可见于西文法律数据库Lexis Advance。,助讼是指在民事诉讼中给一方当事人提供不公正的帮助,不管是以资金支持,咨询建议还是提供律师的方式。而帮讼分利下非当事人不仅仅通过给一方当事人提供资金支持进行助讼,而且还分享被资助当事人的胜诉利益[注]可以认为仅仅包括费用资助条款的第三方资助行为属于助讼行为,同时包括费用资助条款和回报补偿条款的第三方资助属于帮讼分利行为(当然也属于助讼行为)。。所以,前者是后者的上位概念,助讼行为包含了帮讼分利行为,而帮讼分利行为则是助讼行为的特殊形式[注]See In re Primus, 436 U.S. 412, 98 S. Ct. 1893, 56 L. Ed. 2d 417, 1978 U.S. LEXIS 28: maintenance is helping another prosecute a suit; champerty is maintaining a suit in return for a financial interest in the outcome; and barratry is a continuing practice of maintenance or champerty.。
禁止助讼与帮讼分利规则有着漫长的历史,该规则最晚被成文法吸收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3世纪的爱德华一世[注]See Percy H. Winfield, supra note 36, at 59.。更有评注者认为禁止助讼与帮讼分利规则起源于希腊和罗马的法律[注]See Elliott Associates, L.P. v. Banco de la Nacion, 194 F.3d 363, 372 (2d Cir.1999).。助讼和帮讼分利行为之所以被官方否定有着多重原因:首先是这些行为会导致滥诉,而在当时诉讼本身被视为不受欢迎和令人厌恶的事物;其次,助讼特别是帮讼分利中存在的类似高利贷行为(usury)或者食利行为与当时的宗教信仰相违背;最后,禁止助讼和帮讼分利规则也被当时的国王借以打压针对自己和自己拥护者的诉讼来保护自己和拥护者[注]Max Radin, “Maintenance by Champerty”,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 24, Issue 1 (November 1935), pp.60-67.。因此在早期的司法实践中助讼和帮讼分利行为一律被禁止,同一性质的第三方资助协议也会被判定为无效,而法庭引注的理由往往是资助协议违反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注]See Noland v. Law, 170 S.C. 345, 353, 170 S.E. 439, 442 (1933). Also see at Fausone v. U.S. Claims, Inc., 915 So. 2d 626, 630 (Fla. Dist. Ct. App. 2005).。禁止助讼和帮讼分利规则的影响十分深远,如今,仍然有部分法院会根据该规则的精神否定第三方资助协议的效力[注]See Anthony J. Sebok, supra note 21, at 126.。
近代以来,官方对第三方资助协议的态度逐渐缓和。这种转变首先体现在立法上,1967年英格兰通过成文法形式废除了帮讼分利罪[注]Criminal Law Act, 1967, c. 58, §§ 13(1), 14(1) (U.K.).,其后1993年澳大利亚许多州也逐渐把助讼与帮讼分利行为从刑法和侵权法中剔除[注]Maintenance, Champerty and Barratry Abolition Act 1993 (NSW). Also see Oliver Gayner & Susanna Khouri: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Meets Third Party Funding”, Fordham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40, Issue 3 (April 2017), p. 1035.,近年来香港和新加坡立法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注]See Ibid, at 1033-1034.。这种变化在司法审判中也逐渐见其端倪,极具代表性的案件包括澳大利亚的Fostif案[注]See Campbells Cash & Carry Pty Ltd. v Fostif Pty Ltd. (2006) 229 C.L.R. 386, 413 (Austl.).、英国的Giles案[注]Giles v. Thompson, [1994] 1 A.C. 142 (Eng.).和Arkin案[注]Arkin v. Borchard Lines Ltd., [2005] EWCA (Civ) 655, [16], [45], [2005] 3 All. E.R. 613.及新加坡的Re Vanguard Energy案[注][2015] SGHC 156.。
为何立法和司法逐渐接纳第三方资助这种帮讼分利行为?官方态度为何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或许从上述裁判的判决词中我们能够找到答案。Fostif案中,原告与资助人达成的资助协议被指控为违反公共政策,但是法庭指出,公共政策的内涵已经发生改变,在程序滥用的倾向得到有效控制的前提下能够提供接近司法的资助协议受到法律的认可,也符合公共政策的要求[注]See(2005) 63 NSWLR 203 at 227 [105].;Giles案中,被告诉称原告签订的资助协议具有帮诉分利性且违反了公共政策。法官Steyn LJ首先分析了公共政策的多种含义,并且指出资助协议涉及到的需要保护的公共政策是公共民事司法的纯洁性。针对资助协议可能招致公共司法腐败,资助人为了获得资助协议项下的利益可能隐匿证据、收买证人或者夸大损失这一问题,Steyn LJ指出隐匿证据、收买证人和夸大损失等不端行为在诉讼中是一个永恒存在的风险,第三方资助协议并没有在这些不端行为方面造成特别的风险。相反,资助第三人在选择资助对象时会通过质询和交叉询问等方式进行调查,选择胜率高的案件进行资助,这样就会大大减少司法腐败行为的出现。而且被资助人的律师出于职业道德的要求也会监督资助人的不端行为[注]See Giles, supra note 49.。随后,法官认为如果判定资助协议无效,将会剥夺拥有合理诉求的个人接近民事司法(access to civil justice)的权利,最终限制个人的诉讼自由,公共政策并不寻求这样的结果。资助协议最终被判定为有效[注]See Ibid.;Arkin案中,法官在论及原告签订的第三方资助协议的效力时指出,对于拥有合理诉求但是资金匮乏的原告通过第三方资助来获得司法审判资源是十分必要的。只要不干扰合理的司法程序,资助人通过资金援助的方式为原告提供接近司法的行为就应该受到鼓励[注]Arkin v. Borchard Lines Ltd., [2005] EWCA (Civ) 655, [16], [2005] 3 All. E.R. 613.。
仔细研究这些肯定第三方资助协议效力的判例[注]类似案例还可以参考香港地区的裁判:Unruh v. Seeberger [2007] 10 HKCFAR 31; Re Cyberworks [2010] HKCU 974; Re Po Yuen Machine Factory [2012] HKCU 816。加拿大的裁判:Dugal v. Manulife Financial Corp. See Dugal v. Manulife Financial Corp. (2011), 105 0.R. (3d) 364, [2011] O.J. No. 1239 (Ont. S.C.J.), supp. reasons 218 A.C.W.S. (3d) 760, [2011] O.J. No. 3493 (Ont. S.C.J.).,我们可以发现法官在陈述这些资助协议有效性的理由时有一个词组几乎必然会出现——接近司法(access to justice)。虽然资助协议加剧司法不端行为的忧虑依然存在,但是给予拥有合理诉求却困于资金的原告以接近司法获取正义的价值取向占据了主导地位。由此我们观察到了司法理念的一个显著变化——判断第三方资助协议的效力时,司法公正不再是唯一的教条,接近司法同样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目标。民众获取司法资源的需求被提升到与司法程序的公正和圣洁同样的高度[注]这种司法理念变迁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比如对个人权利的更加重视、司法程序费用高昂等,篇幅所限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到这里,官方对第三方资助协议态度从绝对禁止到允许的转变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近代以来,整个社会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更加重视,而保护个人权利的最佳方式——诉讼——却由于费用居高将一些拥有合理法律诉求却匮于资金的个人拒绝在正义的大门之外。出于为这些个人提供接近司法的机会,第三方资助行为应当被允许。第三方资助对司法程序本身带来的负面影响应该重视但是不足以否定第三方资助本身。
(二)程序控制条款的法律效力:冲突的现实
出于对接近司法目标的追求,部分国家对于第三方资助协议的态度逐渐缓和,但是这些国家对第三方资助协议接纳的程度存在着区别。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对于资助协议中一类特殊条款——程序控制条款——效力的不同态度上。实践中,资助人为了确保资助的案件能够胜诉,往往会在资助协议中设置程序控制条款,要求被资助人转让部分或全部诉讼权利(比如律师选取、诉讼策略选择及是否和解调解的决定权等)给自己,从而获取对所资助案件的控制权。对这一条款的法律效力[注]前文中区分了两类程序控制条款,即轻度控制型和深度控制型,司法实践中关于前者的效力分歧不大,分歧主要集中在后一类型,所以本处讨论的程序控制条款的效力特指深度控制型程序控制条款。司法实践争议较大,有些判例认可资助协议中程序控制条款的法律效力和资助人对争议程序的控制权,而有些判例虽然对于资助协议中的费用资助条款和回报补偿条款不持异议但是坚决否定程序控制条款的效力。
1.无效论及其理据
从现有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否定程序控制条款的观点(即无效论)占据主流。在加拿大,法官明确否定程序控制条款的法律效力。Dugal案中法官G.R. Strathy J.在论述为何批准诉讼中的第三方资助协议时提到因为该案涉资助协议约定诉讼程序的控制权利依然掌握在原告手中,资助人无权干涉诉讼的具体走向[注]See Dugal v. Manulife Financial Corp., supra note 17, at [33].。Sino-Forest案[注]See Labourers’ Pension Fund of Central and Eastern Canada (Trustees of) v. Sino-Forest Corp., [2012] O.J. No. 2219.中法官P.M. Perell J. 也认可了内容类似的资助协议。在Kinross案中[注]See Musicians’ Pension Fund of Canada (Trustee of) v. Kinross Gold Corp. (2013), 117O.R. (3d) 150, [2013] O.J. No. 3669 (Ont. S.C.J.).P.M. Perell J.更是根据判例法提炼出了第三方资助协议受到认可的十二个条件,其中第六点指出“第三方资助协议想要被认可则必须不可减损原告指导和控制诉讼程序的权利”[注]See Ibid, at [41].。美国的司法实践和立法态度与加拿大相似,在美国第三方资助协议的资助人也被禁止以任何形式干扰诉讼程序,也无权控制诉讼程序[注]See John C. Jr. Coffee, “Litigation Governance: Taking Accountability Seriously”, Columbia Law Review, Vol. 110, Issue 2 (March 2010), pp. 340-341.。美国俄亥俄州的立法在涉及第三方资助协议时指出:“资助人必须同意其无权并且也将不会进行有关被资助的民事诉讼或者诉求或者任何和解协议的决策,这些决策权排他性地由被资助人和被资助人的诉讼律师享有”[注]Ohio Rev. Code Ann. Sec 1349.55(B)(3).。Haskell案[注]Anglo-Dutch Petroleum Int’l, Inc. v. Haskell, 193 S.W.3d 87, 104 (Tex. App. Houston 1st Dist. Mar. 9, 2006).中法庭从反面指出赋予资助人选择代理律师、制定庭审策略或者参与和解协商权利的第三方资助协议违反公共政策因而归于无效。类似的还有英国。英国法庭十分抵制将诉讼程序控制权从被资助人转移给资助人的条款。一个含有程序控制条款的资助协议将会被认定为无效。相反,只有费用资助协议和回报补偿协议而没有转移程序控制权利条款的资助协议在英国法律体系下是有法律效力的[注]See Marco de Morpurgo, supra note 31, at 398.。比如Arkin案中上诉法院批准案涉的第三方资助协议时特别强调原告(而非资助人)才是对诉讼结果有主要利益关联并且控制诉讼程序的主体[注][2005] EWCA (Civ) 655,at [40], [2005] 1 W.L.R. 3055 (Eng.).。
无效论在程序控制条款的司法意见中占据主流。这种司法观点的背后是对资助人通过程序控制条款干扰司法程序正常进行(du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的担忧[注]See Clairs Keeley (2004) 29 WAR 479 at 502 [125].。学界的有力观点对无效论进行进一步的解释,认为程序控制条款无效论背后的理据是资助人和被资助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注]Vicki Waye, “Conflicts of Interests between Claimholders, Lawyers and Litigation Entrepreneurs”, Bond Law Review, Vol. 19, Issue 1 (2007), pp. 225-274.。从表面来看,资助人和被资助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并不会产生冲突。比如根据资助协议中的回报补偿条款,资助人能够获得的经济利益与被资助人最后通过判决或者和解协议取得金额成正比,所以资助人和被资助人追求的目标相同,即使得被资助人的诉讼请求尽可能大地得到法庭的支持。但是如果深层次分析,就会发现资助人和被资助的请求权人之间在多种情形下存在着利益冲突。第一,诉讼策略冲突。被资助人想要采取的诉讼策略与资助人的想法不同。第二,赔偿额冲突。在调解谈判过程中,被资助人愿意接受的赔偿会使得资助人对案件的投资亏损,因而得不到资助人的认可。第三,赔偿形式冲突。调解谈判后,被资助人愿意接受非金钱形式的赔偿比如产品等,但是资助人只想要货币形式的赔偿。第四,撤诉冲突。被资助人由于身体状况不佳或者出于恢复与被告之间关系的目的想要撤回诉讼,但是因此会导致资助人的资助目的落空而遭到资助人的反对[注]See Vicki Waye, Ibid, at 237-238.。资助人作为投资者关注的是投资的最终效益,这决定了其仅能用冰冷抽象的金钱逻辑思考被资助的诉讼。而被资助人作为具体的社会人,诉讼的经济价值并非其唯一追求,其看待诉讼的视角也更加多元化。资助人和被资助人的这种角色差异使得上述冲突不可避免。而当双方就诉讼的程序问题产生矛盾后,法院需要回答的问题也就一个:被资助的诉讼是谁的诉讼?是被资助人的还是资助人的?持无效论观点的法院的裁判逻辑十分简单:资助人并不因为资助协议而成为诉讼的原告,被资助人才是诉讼的原告,而诉讼策略的决定、和解调解协议的签订和撤诉等诉讼权利都归属于作为当事人的原告,所以当上述程序事项产生冲突时应以被资助人的意志为先。程序控制条款使得资助人有权干扰司法程序的合理进行,自然归于无效。
2.有效论及其理据
虽然多数观点对程序控制条款持否定态度,但是澳大利亚最高法院对该条款和资助人对所资助案件的控制权态度十分温和。一个主要的案例是Fostif案[注]See supra note 27.,案件中原告签订的资助协议约定了程序控制条款,根据该条款诉讼律师须由资助人选取,资助人实际控制了整个诉讼过程[注]Lexis citation number: BC200606677, Australia, at [278], [279].。对方当事人指控资助协议中程序控制条款使得被资助的原告的利益附属于作为案外人的资助方,可能导致程序滥用,因而无法律效力。但是澳大利亚最高院最终以5:2的多数认定资助人可以对被资助的案件施加重大(significant)控制,程序控制条款并不违反公共政策,也不会造成程序滥用[注]See Fostif, supra note 27, at 388-389.。在解释判决的理据时,法庭提出了两点理由:第一,程序控制条款是由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persons of full age and capacity) 与资助人签订的,从意思自治和合同自由的角度出发,该条款应当有效[注]Ibid, at 413.;第二,一般的原告可能不愿意冒着败诉和白白支出诉讼费用的风险向法院提起诉讼,而资助人愿意承担这些风险,所以资助人想要拥有诉讼程序控制权毫不奇怪[注]Ibid, at paras 87-88.。事实上资助人对诉讼程序的控制权和程序控制条款已经构成资助人承担诉讼风险的对价(quid quo pro)[注]See Charles M. Wright, supra note 20, at 172-173.。
如果单独看,无效论和有效论的理据似乎都有法理支撑,但是两者对待程序控制条款的态度却如此悬殊,不禁引人深思。两种司法观点理据背后的分歧到底在哪里?笔者认为无效论和有效论的分歧在于对“诉讼权利是否可以在私主体之间进行交易”这一问题理解不同。无效论认为诉讼权利依附于诉讼当事人的法律地位而存在,专属于诉讼原被告,所以不存在能够由诉讼当事人转移给作为案外人的资助人一说,因而把诉讼权利从被资助的原告转让给资助人的程序控制条款没有法律效力。而且资助人资助案件的行为并没有使得其取代原告的当事人地位,受资助的诉讼依然是被资助人的诉讼而不是资助人的诉讼。有效论也承认受资助的诉讼仍然是被资助人的诉讼,被资助人依然是案件的当事人。但是其同时也认为诉讼权利虽然生发于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但是绝不意味着诉讼权利永远只能依附在诉讼当事人周围,不能转让。依据民事诉讼处分原则[注]张卫平.民事诉讼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48.,诉讼权利的行使最终是为了确保实体权利的实现,诉讼权利只不过是民事实体权利在诉讼领域的延伸[注]巢志雄. 民事诉权合同研究——兼论我国司法裁判经验对法学理论发展的影响[J]. 法学家,2017,(1):41.,前者附属于后者,与后者具有同一属性,而民事实体权利具有私法可交易属性,诉讼权利在性质上也应当具有私法面向,可以由当事人自由处分转让。所以在被资助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意思表示真实的情况下,诉讼权利可以作价转让给资助人,程序控制条款因而有效。
四、第三方资助协议的中国回应
前文根据域外经验分析了第三方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法律性质和法律效力问题,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探讨我们国家的立场,中国的司法和立法对于诉讼中的第三方资助协议应当持何种态度?对此问题的回答具有一定程度的紧迫性,因为第三方资助协议的实践在中国诉讼程序中已经逐渐兴起[注]截止至2018年2月,国内从事第三方资助业务的机构和平台至少包括多盟诉讼融资基金、前海鼎颂投资、为安法律金融、赢火虫诉讼投资、盛诉无忧和律诉网等。参见多层次资本市场联盟.多盟诉讼融资白皮书[EB/OL].(2018-07-17)[2018-9-29]. http://www.lawsuitfund.net/index.php/companynews/351.html.。伴随着这一趋势,我们有必要参考域外经验并结合中国国情,分析清楚第三方资助协议对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可能造成的冲击。根据对于第三方资助协议的态度,现有国家和地区可以划分为三类:开放型(不仅仅承认资助协议中的费用资助条款和回报补偿条款,也认可程序控制条款)、折中型(仅仅承认资助协议中的费用资助条款和回报补偿条款,但是不认可程序控制条款)、闭塞型(根本否定第三方资助协议,不承认费用资助条款和回报补偿条款,更不用说程序控制条款)。中国应该进入哪一国家类别?这需要我们思考和回答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中国是否应该承认第三方资助协议的效力?即是否应该认可费用资助条款和回报补偿条款;第二,假设中国应该承认第三方资助协议的效力,那么中国是否应该认可资助协议中的程序控制条款?
(一)第三方资助协议效力的中国回应:个人权利与司法秩序的考量
从历史来看,第三方资助刚开始并不受立法和司法体系的待见,大部分国家对第三方资助协议持“闭塞型”观点。这种观点的背后是对司法秩序的维护,他们担心如果认可第三方资助协议,一方面会导致“滥诉”,一些毫无法律根据的诉求也会进入司法程序挤占有限的司法资源,另一方面会破坏司法程序的公正性,不受诉讼程序规制的案外资助人在利益的驱使下可能隐匿证据、收买证人,诱使司法腐败。司法判决也往往以维护公共政策为由否决第三方资助协议。近代以来,随着公民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社会对人的关怀由抽象走向具体,国家看待第三方资助协议的视角也发生了改变——从原先的司法秩序“大”视角转向个人权利“小”视角。立法和司法体系开始注意到第三方资助协议对于个人权利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那些拥有合理诉求但是困于资金的诉求人,第三方资助能够为他们提供接近司法从而最终实现权利的机会。于是第三方资助协议的效力逐渐得到法律体系的认可,部分国家和地区纷纷立法将第三方资助协议合法化,司法实践对第三方资助协议的态度也变得温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在面对将第三方资助协议合法化还是非法化的问题时,同样需要结合本国国情从司法秩序的维护和个人权利的保护两个角度进行考量,一方面不可忽视第三方资助协议给司法秩序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要关注第三方资助协议对于促进个人权利保护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所以只关注司法秩序维护而不考虑个人权利保护的“闭塞型”态度不足取,其已经逐渐被历史淘汰,进入故纸堆。事实上,第三方资助协议合法化已是世界潮流[注]如前文所述,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英国、新加坡、香港地区都逐渐承认第三方资助协议的法律效力。。笔者认为中国对待第三方资助协议的合适态度应该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从个人权利保护的视角出发,承认第三方资助协议的合法性;第二个层次是基于对司法秩序的维护,对第三方资助协议进行规制。
对于第三方资助协议的规制,域外第三方资助协议的实践已经比较成熟,司法判决和立法已经有比较成型的经验可供我们参考。从这些经验出发,笔者认为中国在规制第三方资助协议时,应该主要关注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回报补偿条款的规制,第二个问题是程序控制条款的规制。第二个问题笔者在下文分析,此处暂先分析第一个问题。美国俄亥俄州在规定资助人能够获得的回报补偿方面并没有实质性的约束,仅仅是要求资助协议必须列明一次性收费项目(an itemization of one-time fees)、被资助人应当支付的总金额以及资助人的年收益率(annual percentage rate of return)[注]OHIO REV. CODE ANN. SEC 1349.55(B)(1).,而Dugal案中法官总结到资助人的回报必须合理(reasonable)且是其在资助案件中承担的风险的公平反映(a fair reflection)[注]Dugal案中,法官梳理判例法后总结出有效的第三方资助协议必须满足的要件,参考Dugal案,See Dugal v. Manulife Financial Corp. (2011), 105 0.R. (3d) 364, [2011] O.J. No. 1239 (Ont. S.C.J.), supp. reasons 218 A.C.W.S. (3d) 760, [2011] O.J. No. 3493 (Ont. S.C.J.).。中国在设计第三方资助协议的回报补偿条款时,不仅仅应当要求资助协议列明一次性收费项目、被资助人的总支付义务和资助人的回报年收益率,而且应当介入资助协议,从实质上限制资助人能够获得回报,要求资助人从资助协议中获得的收益必须合理,即与其承担的风险一致。这是因为,在第三方资助协议中,寻求资助的被资助人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其议价能力弱于资助人。
(二)程序控制条款效力的中国回应:民事诉讼处分原则与诉讼权利的私法面向
承认第三方资助协议的效力之后,我们需要考虑的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是如何看待程序控制条款的法律效力。虽然第三方资助协议合法化已是主流,但是在这些认可第三方资助协议的国家中,对于资助人对资助案件的控制权和程序控制条款的效力仍然有不同的看法。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认为资助人的权利和义务止于费用资助条款和回报补偿条款,并不认可程序控制条款的法律效力和资助人对资助案件的控制权。其背后的理据在于,诉讼权利附属于诉讼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只能由诉讼当事人享有,不能转让给案外人,而程序控制条款目的在于将诉讼权利由被资助的原告转让给案外的资助人,因而无效;但是,澳大利亚最高法院认为程序控制条款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被资助人根据自己的意思与资助人签订,资助人从被资助人处受让对资助案件的控制权或诉讼权利时,也付出了一定的对价,根据合同自由原则,程序控制条款应属有效[注]See Fostif, supra note 27.。
程序控制条款实质是资助人从被资助的原告处受让诉讼权利以获取对资助案件控制权的约款,上述无效论和有效论的对立根源正在于对“诉讼权利是否可以交易”这一问题的理解不同,无效论认为诉讼权利专属于被资助的原告不能转让给资助人,而有效论认为诉讼权利虽然产生于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但是可以转让。我们国家在考虑如何对待程序控制条款的效力时,也必须回答“诉讼权利是否可以交易”这个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涉及到对民事诉讼处分原则和诉讼权利的私法面向等问题的思考。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这一条款即民事诉讼法上的处分原则。如果对该条款中的“处分”作广义性的文义解释,似乎也包括“被资助的原告有权将诉讼权利和案件控制权转让给资助人”之意,但是这种理解能否得到主流观点的认同存有疑问。现行主流观点对民事诉讼法处分原则的定义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原则上由当事人自由决定,国家不能干预。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应当处于被动消极的地位”[注]〔85〕张卫平.民事诉讼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47.48.,也就是说主流观点认为处分原则处理的是当事人和代表国家的法院之间的“私对公”法律关系,解决的是诉讼权利在当事人和法院之间的分配问题,并未涉及“原告的诉讼权利能否通过合同转让给资助人”这一被资助的原告和资助人之间的“私对私”法律关系问题。处分原则的主流观点似乎并不能回答“诉讼权利是否可交易”的问题。但是,如果对处分原则的法理依据作一番考察,诉讼权利的可交易性或私法面向问题或可得到较为完满的解答。处分原则的法理基础与私法诉权说同源,认为诉讼权利是民事实体权利的延伸〔85〕,所以诉讼权利本质上与民事实体权利一样都是私法权利,具有私法权利的普遍性质,比如进行交易。综合来看,程序控制条款无效论是现行主流观点,我国遵循此主流观点显得更为稳妥,但是从民事诉讼处分原则的法理依据出发,我国选择有效论作为对待程序控制条款的态度亦无不可。
五、结论
国内民事诉讼领域的第三方资助已经逐渐兴起,这种实践会对国内民事司法秩序产生的影响亟需立法者和司法者的考量。而考量的出发点,应当是研究第三方资助协议本身,包括其内容、性质和效力。第三方资助协议主要包括费用资助条款、回报补偿条款和程序控制条款,在性质上属于一类独立合同,即既包括实体权利处分(费用资助条款和回报补偿条款)也包括程序权利处分(程序控制条款)的混合合同。现有国家和地区对第三方资助协议的态度由紧到松可以区分为三类:闭塞型、折中型和开放型。闭塞型态度与折中型态度的界分在于看待第三方资助协议的视角不同,前者更关注第三方资助可能给司法秩序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后者却把焦点放在了第三方资助对个人权利保护的增进。折中型态度和开放型态度虽然对第三方资助协议持宽容态度,但是对于其中的程序控制条款的法律效力存有分歧,分歧的关键在于对“诉讼权利是否可交易”这一问题的理解不同。随着社会对个人权利保护的重视,闭塞型观点逐渐被淘汰,第三方资助协议合法化已是大势所趋,中国应当顺应这种潮流,一方面认可资助协议的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对第三方资助协议进行规制。而规制的重点应当落在第三方资助协议的回报补偿条款和程序控制条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