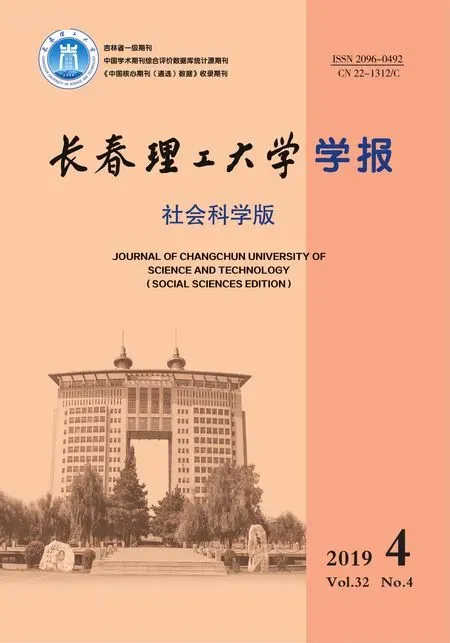福柯话语理论对跨文化偏见研究的意义
郭金英,黄乐平
(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300134)
在近年来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深的大背景下,西方世界却萌现出了一种逆全球化的潮流,集中表现为英国脱欧带来的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倒退、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等。该潮流的出现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不同文化之间的误解和偏见更是愈演愈烈。偏见作为一种错误的认知,是在未获得全面、准确的信息的基础上对他文化作出的不理性判断,并形成对他文化的否定性态度,此种态度往往通过话语得以表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偏见是一个话语问题。随着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转向的发生,以福柯为代表的话语理论由于其注重社会文化性,成为人们认识世界、认识现实的重要媒介。鉴于此,本研究以福柯话语理论为基础,对其理论的渊源、生成和内容做梳理,并从该理论的角度解读跨文化偏见的产生机制和特征,以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偏见,更客观地看待不同文化的差异,公正地对待异文化。
一、福柯的话语理论
作为20世纪法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福柯反对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的结构主义二元对立的语言观,提出了第三个维度“话语”,认为作为主体的人与世界是一种话语关系,任何东西都不能离开话语而存在。福柯的这种根植于结构主义的话语渊源带来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转向,也带来了后现代主义思潮。他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将话语视为中心,围绕话语、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对话语从考古学和谱系学两个方面展开研究。福柯话语考古学注重话语建构性和实践性[1],具体表现为话语建构社会,换言之,任何话语实践都是由它与其他话语的关系界定的;而谱系学研究注重权力和社会的话语性和话语的政治性,具体包括权力在多大程度上是话语性的、权力斗争是在话语中发生的、社会实践与社会变化的关系等。
根据上述内容,笔者认为福柯话语思想可以被总结为以下三点:一是注重建构性和互动性;二是注重实践中的知识和权力;三是对社会文化等外因的关注。
(一)互动性和建构性
话语的互动性和建构性集中体现在话语的形成过程中,其形成的过程亦是与不同话语互动建立关系的过程。福柯认为话语的形成过程有四个方面,包括对象的形成、陈述方式的形成、概念的形成和策略的形成[1]。在这一过程中,“陈述”作为一个重要概念界定了话语形成的中心。其中,话语对象的形成是话语与处在一个复杂的、与整体相关联的发散的关系中的其他对象在互动中完成的,这一互动过程也建构了话语对象;陈述方式是在回答谁、在哪里、以什么身份去说话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来确定的,即陈述方式不是随意选择的,而是受约束于其在更大范围内的位置;概念的形成是在与其他话语相互关联、彼此联系的程序中发生的;策略的形成是指话语可能的相切点和根据,相切点构成话语意指链,而根据形成话语内部和外部的环境。笔者认为策略的形成就是确定语义及语境的过程。
由上述内容可知,话语是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互动过程建构了话语。换言之,话语是被建构的。因此,福柯的话语理论是一种“建构性的话语观”,“它涉及到将话语看作是从各个方面积极地建造或积极地构筑社会的过程:话语构建知识客体、社会主体和自我‘形式’,构建社会关系和概念框架”[2]。笔者认为,福柯的话语观在此种意义上指的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下,为了一定的目的,通过特定的手段所创造出来的、为特定目的服务的社会实践过程。因此,话语的形成过程就是在互动中被建构的过程。
(二)实践中的知识和权力
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提出了“知识”的概念。而这一概念也是围绕与话语实践的关系界定的,认为“没有特定的话语实践就没有知识;而任何一个话语实践都可以由它所构成的知识来界定”[1]。换言之,知识是在话语实践中产生的,而话语实践又是由它所构成的知识来界定的。权力、知识与话语之间是一种同构关系,权力、知识由话语来实现,话语既是权力、知识的产物,又构成权力和知识[3]。因此,话语的实践性与知识性交织在一起。一方面,话语是由话语主体在知识空间中根据知识范围谈及的;另一方面,话语主体所谈及的知识又是由某种话语实践按照其规则构成的。因此,在话语实践——知识——科学这条轴线上知识作为中心,连接话语实践与科学。话语实践按其规律构成知识,科学则处于话语实践所形成的知识中并以它为基础发挥作用。
在话语内部,福柯引入权力的概念,将考古学的研究从认识型的知识观念转向一种对权力与知识关系的谱系学研究[4]。认为权力是话语运作的控制力量,哪里有话语哪里就有权力,生产出了对知识的分类,权力产生于知识的生产过程中。没有相关的知识领域的建构,就不存在权力关系,任何知识都以权力关系为前提,并建构着关系[1]。但是,尽管权力生产出知识和话语,但话语也是“权力的工具,话语在权力的范围之内,作为权力运作的手段发挥作用”。此外,话语对权力的反作用在于它也“承载着和生产着权力”。权力生产话语,话语又作为工具反过来生产权力。知识是一种权力的体现,且“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1]。
因此,知识和权力都是在话语实践的过程中体现的。权力存在于生产知识的过程中,而知识的生产过程又是由占据统治地位的主体控制的,是一种权力的体现。由此,话语、知识和权力相互交织在一起,知识和权力通过话语的实践性凸显其实践性。
(三)对社会文化等外因的关注
除了上述权力和知识的互生外,福柯还意识到作为话语主体,他所能思考的、所能说出的必然会受到其所处历史时代的话语框架的诸多限定和制约,即话语是在某种特定的社会文化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被制造出来的。所以,话语从来就不是孤立的语言力量,而是与社会文化网络中的一系列力量纠缠在一起的,是活生生的力量竞争和紧张关系,是靠特定的策略和权术来实现的。话语的形成、传播、转换、合并等过程都势必搅动一系列的社会文化因素,搅动整个权力网络的运作[2]。
笔者在此强调的是,社会文化作为外因在话语生成过程中起到某种辅助或催化作用,与上文提到的权力有一定的差别。权力是内生与话语实践过程中的,而此处的社会文化外因是外在条件,是福柯在论述其话语观时对于话语的社会性关注的一个集中体现。
二、偏见、文化与话语
偏见最初属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在研究初期被理解为一种错误的态度,一种“精神变态”反应[5]。20世纪60年代,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偏见是在动机驱动下的一种隐性心理认知偏向,是人们社会化过程的一种体现,主要表现为对不同群体的态度的迥异。人们往往对内群体成员持积极态度,认为内群体成员聪明勤奋,而对外群体成员持消极负面态度,比如认为外群体成员愚蠢懒惰等。“文化”一词的内涵从古至今发生着演变。《说文解字》中“文”和“化”是分开使用的,“文,错画也,象交叉”,意即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化,“变也”,引申“教行也”,即本意为改变,同时引申为教行迁善之义[6]。因此,偏见与文化紧密相关。
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跨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群体间的一种交互活动,在此过程中人们分别透过不同的文化框架去认知和解释对方的行为,从而产生不同的态度,即跨文化偏见。因而,文化差异是导致偏见产生的直接因素。Scollon&Scollon(2000)认为文化涵盖了价值、规则、习惯系统,存在于地区、国家、性别、年龄等几乎所有层面,且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是人们解释社会现象的一种手段学界[7]。而后现代主义的视角认为,文化的差异都是符号的社会建构的结果,与社会现实一样,都是被呈现的[8]。按照萨义德的观点,一个文化体系的文化话语通常并不存在真理,只是对它的一种表述;不存在直接的在场,只存在间接的在场或表述[9]。换言之,文化只是话语对文化现象的一系列表述。在跨文化传播中,由于不同文化群体倾向于按照既存的自身的认知框架去看待异群体,因而极易在没有获得全面、准确的信息的基础上对他文化作出不理性判断,由此形成对他文化的否定性态度,形成文化偏见。且一旦文化偏见形成,它就很容易随着话语的传播而为人们所接受,并可能转变为一种权力,影响和限制人们对其他文化问题的正确感知[10]。因此,一方面,偏见作为一个认知过程,是在人与人或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是关系的一种体现,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映,偏见一旦形成又会对人们的实践产生一定的反作用;另一方面,偏见是在人们社会化互动的过程中,通过语言与非语言,借助于权力建构出来的对他群体在包括习俗、观念、信仰、服饰、食物、语言等一系列隐性和显性层面上的认识,是一种文化的话语表征和建构,体现了话语的特征。因此,偏见作为一种话语形式,也具有互动性和建构性。换言之,跨文化中的偏见恰恰是社会行为、社会实践活动、支配关系、不平等关系和权力争夺的一种话语体现形式,亦具有权力性。
三、话语理论对跨文化偏见的解读
(一)偏见的社会建构性
按照福柯的观点,某个领域的知识是通过话语建构起来的,没有相关的知识领域的建构就没有话语。而在跨文化传播中,话语对现实的重构或对偏见的建构往往是一个复杂和宏大的社会文化现象。因此,对偏见的研究不能与主体、客体以及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剥离开来。例如,形成于19世纪的“黄祸论”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理论,该理论声称黄种人是极大的祸患,白人应联合起来对抗黄种人。该种言论导致了美国社会中极端的排华潮,中国的形象变得愈发丑陋。很明显,中国人的丑陋形象是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极大偏见,这种偏见是参照西方自身的文化在西方语境下通过华人与西方人互动建构起来的知识,这种知识亦可被称为一种话语,是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脱离不开的。
从该意义上说,理解话语的生产和接受的过程是理解偏见社会建构性的基础,而霍尔所提出的编码、解码理论范式对理解偏见的社会建构有一定的指导性。该范式提出人们对于信息的三种解读模式:优先解读、协商解读和对抗性解读,但无论哪种方式都是解码者对于编码者所提出的话语在参照自身文化符码和文化语境的情况下的认知、处理和阐释,这一过程都涉及到双方的社会互动性,而在这一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建构了对另一群体的认知。而毋庸置疑的是跨文化传播活动中的偏见也是具有明显差异的文化观念和表征体系的人们在交流中产生的,是社会互动的结果,是被建构的。因此,我们须将扭曲和误解的偏见放在话语的生产和接受的动态过程中进行考察。在考察的过程中,话语不再仅仅是表征现实和用来强化主体的工具理性的中性工具,而是变成了或者重构了现实。
按照福柯的话语理论,偏见从本质上来说,是意识形态的话语,无论是作为理论结构还是作为知识体系,偏见是派生于群体的话语实践,并规范、引导着群体对知识与真理的理解和探求[11]。因此,跨文化的偏见是在一定的语境下,在互动过程中建构的一套话语,它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权力结构,并通过一系列话语实践服务和巩固于这种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从该意义上来说,完全客观真实的跨文化传播是不可能的,正如彼得斯所言,交流失败是丑事,可它首先是推动交流观念的力量[12]。因为传受双方的交流一方面要服务于其所在的群体,体现该群体的权力,另一方面受到多种文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二)偏见的权力性
福柯话语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其权力性。福柯认为话语与权力紧密地勾连在一起,哪里有话语,哪里就有权力,而权力又是话语运作无所不在的支配力量。在福柯的权力体系中,话语和话语实践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每一个话语实践中,权力都渗透并蔓延其中。权力概念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其生产性,权力生产出了对知识的分类,知识的分类又影响和制约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而思考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关系又不能脱离话语。换言之,哪里有话语哪里就有权力。并且,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都受到一定程序的控制,以决定由谁对谁说,在什么场合下说。在权力斗争和话语实践方面,他认为话语不仅改变斗争,而且斗争借助于话语而存在,话语就是被争夺的权力,且这种权力关系往往以隐形的方式存在于社会各层面。
而作为话语形式的偏见也是跨文化这一社会实践过程中权力斗争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参与者往往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参与者从内容、主体和关系上进行控制。内容决定了跨文化传播过程的信息,即说什么;关系决定了传受双方的身份,即是否被作为平等的主题;主体决定了传受双方的地位,即主从地位。因此,正是由于处于优势地位的参与者凭借其权力确定认知对象,界定社会关系和参与主体,才导致在这种关系下产生的知识正是占优势地位的参与者所要借此形成的对弱势群体的偏见认知。换言之,偏见的形成过程也是权力作用的结果。
跨文化偏见的权力性除了其话语形成过程本身的原因外,还体现在传播力量、信息流量、流向以及传播内容的不平衡上。这种种不平衡导致的人们对异群体,尤其是优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扭曲的认知,影响了不同文化间正常的平等交往和社会和谐。正如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指出的:东方主义是在东西方不平等力量模式下运用话语所生产出来的一套知识体系,这套知识体系以权力关系为前提,反过来又建构和维系着权力关系。因此,这套知识体系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西方对东方在权力关系作用下形成的一系列偏见。在这一偏见的认知下,东方的历史、地理、社会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传统等便在不平等权力关系下通过话语过程而被建构成各种文本及符号。再比如西方提出的妖魔化中国的“中国威胁论”亦是站在西方立场上对中国新时代崛起的偏见,集中体现了偏见的权力性。
偏见是跨文化传播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从福柯的话语理论出发,跨文化偏见作为一种话语形式,是传播过程中的双方在互动过程中建构的,是双方互相认识的一种知识,同时不可避免地充斥着权力性。掌握权力或者掌握话语权、占有优势的一方必然有足够的理由大量生产出针对他国或他文化的偏见话语,进而在更大的范围内产生偏见认知。因此,在理解了上述偏见的特征和生产过程的基础上,在跨文化传播中批判性地解读偏见,对正确认识跨文化主体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然而,当今社会的跨文化传播权力依然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性,西方社会掌控着媒体话语权,往往站在自身立场上生产出褒扬自身、贬斥东方尤其是中国的偏见言论和作品,这在BBC生产的大量纪录片中可以看出,比如《中国人要来了》《中国的秘密》等无一例外的是对中国偏见的描述,严重歪曲了中国文化,扭曲了中国形象。可见,文化的相异性和竞争性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偏见的产生。然而,每一个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3],这种竞争性与权力运作密切相关。由于权力的介入,处于优势地位的文化群体就拥有较大的建构偏见的话语权力,使得偏见表述自然化。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处于弱势的一方在对偏见进行解构的过程中重建了话语,生成了新的对优势一方的知识或偏见。这样传播双方就在这种建构-解构-建构偏见的过程中不断建构着自身的形象,进行着跨文化的交流。因此,可以说,一方面偏见妨碍了公正的跨文化沟通,另一方面又客观地促进了跨文化传播双方的形象建构。
综上所述,福柯的话语观对我们深入理解跨文化偏见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和积极的借鉴作用。以福柯话语观为指导,从偏见的生成和特征入手,能更清晰地理解偏见的成因,能从根本上更客观地解读偏见,了解偏见的意义和存在价值,更好地利用偏见进行有效的跨文化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