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与姚雪垠的《李自成》
阎开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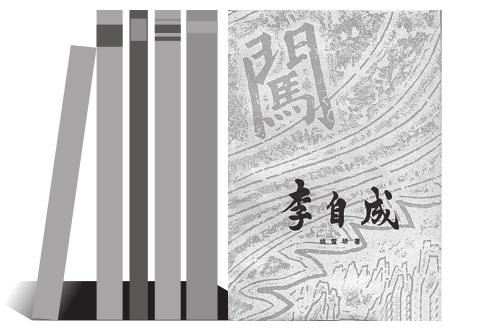
《李自成》是姚雪垠于抗战时期“动念”、1957年开始秘密写作、1963年出版第一卷、1999年全部完成出版的五卷本长篇历史小说。由于这部小说的创作时间长,并且还是贯穿了政治动荡的“十七年”以及整个的“文革”时期,其历史小说的创作主张、思想主题上的“儒法斗争”、结构形式上的“章节回目”以及围绕小说写作、出版而“上書主席”等,一直到今天都有不少的传言、争议与误会。其实,要弄清楚这些事情也并不困难,它们已如实地写在了茅盾与姚雪垠的书信集——《谈艺书简》之中。
说到姚雪垠的历史小说创作主张,姚雪垠的儿子姚海天在《谈艺书简·编后记》中曾经指出,自1974年至1980年的7年时间里,姚雪垠与茅盾共通信88封,其中,收入《谈艺书简》的73封大“都是围绕《李自成》谈长篇历史小说创作或其他重要文艺理论问题”。很显然,姚海天所说的“谈长篇历史小说创作或其他重要文艺理论问题”无疑就包括“历史小说的创作主张”。读《谈艺书简》可知,关于历史小说的创作主张,是姚雪垠与茅盾谈得最早,也是最多的一个问题。归纳起来,他的主张大致有如下四点:一,“历史小说是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统一”;二,历史研究是历史小说创作的基础,作家“首先要对历史深入研究和理解,然后才有艺术的构思”,也即“先研究历史,做到处处心中有数,然后去组织小说细节,烘托人物,表现主题思想”;三,“写历史小说毕竟不等于历史”,它“既要深入历史,也要跳出历史”,并且允许“虚构”和“翻案”。四,长篇历史小说还有一个创作上的“美学问题”,它“包括如何追求语言的丰富多彩,写人物和场景如何将现实主义手法与浪漫主义手法并用,细节描写应如何穿插变化,铺垫和埋伏,有虚有实,各种人物应如何搭配,各单元应如何大开大阖,大起大落,有张有弛,忽断忽续,波诡云谲……等等”。对于姚雪垠的这些创作主张,茅盾在回信中虽然没有像姚雪垠那样作大段的理论阐述,但他都结合具体作品分析一一作了回应。如他说《李自成》“毕竟是小说,不是历史”,“全书翻旧案者必多”,“第一卷中写战争不落《三国演义》等书的旧套,是合乎客观现实的艺术加工”等,都表达了与姚雪垠几乎相同的观点。其中,特别是1975年6月18日至21日的回信,他详细写下了对于《李自成》第二卷各章节的读后看法和修改意见,更可说是与姚雪垠的“艺术追求”和创作“美学”“恰相吻合”。
当然,两人观点“恰相吻合”的还有《李自成》思想主题上的“儒法斗争”。所谓“儒法斗争”,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儒法斗争”也即“儒法之争”,它是中国先秦时期儒家与法家之间的学术思想论争。狭义的“儒法斗争”又称“评法批儒运动”,它是指在“文革”后期的70年代,由毛泽东发起、被“四人帮”所利用的一场全国性、群众性的儒法斗争史研究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权威报刊相继转载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石仑”为笔名发表在《学习与批判》创刊号上的《论尊儒反法》一文,大力宣扬“儒法斗争”的观念。文章认为,“儒家是维护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反动学派,法家是代表新兴的地主阶级利益的进步学派”,儒家提倡“礼治”,法家提倡“法治”,儒家主张守旧,法家主张革新,儒家与法家的斗争不是学术主张之争,而是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在思想政治战线上一场剧烈的阶级斗争”。儒法斗争不仅在春秋战国时期存在,而且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进行着”,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一时间,这种观点广泛传播,并很快占据主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茅盾以商量的口气在1974年12月23日的信中向姚雪垠“贡献鄙见”:
现在展开历史上儒法斗争的研究,凡分析农民起义全都着重突出其反儒反孔;您此书写李自成之所以能号召广大农民,实质上有其反儒反孔的一面,似乎还可以正面点出,重笔写几个插曲(似乎可以虚构),则更妥善。第一卷您本来还要修改,似乎在第一章中就可以突出李自成反儒反孔之措施,以后逐章加浓。李自成内部矛盾之尖锐化与深化,似乎也可拉扯上儒法斗争。尊见以为何如?
接到茅盾的书信不到一周,姚雪垠便写了回信。他在12月29日的信中主要从儒法斗争的角度谈了《李自成》中几个人物的塑造:
李自成是我国历史上农民革命的杰出英雄,但他有历史的局限性,其局限性也表现在他受了儒家思想的腐蚀。……我在第一卷中即埋伏了李自成失败的一个原因:“问道于孔孟,求救于牛金星。”
……?……
牛金星这一个有“经世致用”之学的孔孟之徒,只想做一个“佐命元勋”,开国功臣。他对李自成的事业有过帮助,但也起了较大的腐蚀作用。
……?……
在我原来的设计中,李岩这个人在思想上受了管仲、贾谊、诸葛亮等人的影响,所以在第二卷中强调写他向李自成建议据宛洛为根本,抚辑流亡,恢复生产,……经过一年来的评法批儒学习,我想应该将他所受的法家思想加重一点,但是,也要有个分寸。据我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有纯粹的法家,也没人自觉地要做法家,无宁说常常是外儒内法。
针对此信,茅盾在1975年1月6日的信中首先肯定了姚雪垠“李自成是我国历史上农民革命的杰出英雄,但他有历史的局限性”的观点“至为精审”,接着又说:
你将修改第一卷,鄙意以为李尔重同志从前评第一卷已将李自成改的一个原因:“问道于孔孟,求救于牛金星”,此语一针见血。
这根伏线仍当保存,因为李自成不可能像刘邦那样自觉地轻儒重法也。……历史人物的性格是复杂的。其发展过程也是复杂而曲折的,因而我以为第一卷中虽写了“问道于孔孟,求教于牛金星”,仍然可以写李自成有其反孔、儒的法家思想及其措施。历史上农民起义领袖之所以能号召广大农民,就在于反孔、反儒,……您想把李岩主要写成外儒内法,这是对的。而同时他也有历史的局限性,不可能是一个彻底、坚决的法家。
1975年3月7日,姚雪垠又给茅盾写信,“略微详细地”谈了他对于“李自成与‘批孔问题”的四点意见:
(一)在《李自成》全书中要努力写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至于“批孔”,需要重视这个问题,但不能强拉硬凑。……(二)?李自成和朱元璋都是领导农民战争的杰出领袖,都生活在封建社会后期,……他们都受了儒家思想很深的毒,都按照儒家的政治思想去建立封建王朝……(三)根据现存的、经得住推敲和复查的文献资料,李自成没有过反孔政策和措施,倒是相反的资料不少。这正是他的弱点,他的局限性。……李自成的积极的一面远远超过两汉以来的任何法家,也远远超过他自己的消极的一面,所以他是历史上的杰出的农民英雄。……(四)历史运动的现象(包括一个时代的具体人物)是很复杂的,不出于总的阶级斗争轨道,但不一定都在“儒法斗争”的范畴之内,李自成领导的大规模农民战争是对明末北方封建统治阶级的致命打击,其历史意义和作用的深度与广度大大超过了地主阶级内部的“儒法斗争”。能够努力写好这一点,《李自成》这部小说就基本上完成了任务。
此后,茅盾又在6月8日和7月1日的信中相继谈到李自成与批孔的问题,并以“我基本上赞同”“我赞同”“这很对”来表达对他姚雪垠观点的肯定。这样,我们就看到,两位作家依然保持了他们密切关注社会政治的一贯风格,他们一方面想紧跟上当时的社会时代潮流,一方面又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思考精神。这就正像茅盾在粉碎“四人帮”后给姚雪垠的信中所说:“二年前儒法斗争史研究,给‘四人帮别有用心地搅乱了,一些问题,不容有不同意见,实行棍子政策。您就李自成之例辨明农民起义领袖之非必反孔,也打到了一个公式。”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与两人在上述两个问题上的“恰相吻合”不同,茅盾与姚雪垠在《李自成》的章节回目问题上则出现了一些分歧。关于《李自成》的章节回目问题,最早是由姚雪垠提出并请茅盾帮忙“考虑裁定”的。在1975年3月7日的信中,姚雪垠这样说道:
每个单元有一个暂时标的题目,只是为着自己查阅和朋友们看稿子方便。但是从第一卷出版之后,读者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也常在思考。读者对这部书常常不是只读一边,许多人是读两遍或者两遍以上。即隔些时间,又想重读。也有些人特别喜欢某些章节,只找那些章节重读。因为每章没有题目,翻阅感到不便,就有人建议我每章加个题目。我的尚不成熟的想法是不必每章有题目,但不妨每单元有题目,便于抽阅,每卷前边加一“目次”,列出单元题目,下注自某章至某章,以及页码起止。关于这个问题,希望您得暇时帮我考虑裁定。
茅盾接到姚雪垠的帮忙信后,他先是在6月7日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關于本单元题名:《商洛壮歌》不是概括内容,且犯下边的《商洛风云》。我以为不如用章回体小说每回目是一对联的办法,索性写为:
弄巧成拙,郑制台棋输全局;
制敌机先,李创王险渡难关。
再者:兄曾说第一卷要修改后再重印,那么,我建议:把原来的章改为卷,每卷包含数章,(其在旧章回体则改为每卷数回),每章各起一副对联作名。
后又在6月12日提出了“新的意见”:
一、原来全书五卷的格局可以抛弃,将你新拟的单元格局也拆散,全书只有“章”,分册出版。
二、每章拟一个对联作为每章内容的提要,此即章目,仿旧章回体之回目……
三、如果采取这个办法,则《商洛壮歌》可分为四章或六章,章各有目,那就更加便于读者翻检。
四、用对联作章目,在别人或许为难,而在你正可大展其长。……
对于茅盾提出的这些“采用传统回目格式”的“建议”和“意见”,姚雪垠认为“这是一个较大的问题”。于是,他在7月13日的信中专门而又详细地谈了自己的“想法”:
在开始写第一卷的时候,如何写历史长篇小说在我的面前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各种问题都在探索。曾经试拟了一批回目,对仗也相当工稳,但没有使用,随即烧掉了。第一卷出版之后,也接到过读者来信,建议使用回目。我不用回目那种格式,是考虑到章回体小说的两句回目,讲究对仗,是从律诗、律赋的造句法演化出来的,是一个完全旧的传统。《李自成》虽然融化了一部分章回体小说的手法,但目的是在创新,倘若使用回目,就会首先给读者一个陈旧的印象,好像作者是在走回头路,而且它和此书所追求的艺术目标很难谐和,反而受了章回体那种回目形式的局限和破坏。……所以我考虑只能为单元立题目,或者于每卷后附一“本卷大事索引”,便于读者查阅。
茅盾在了解了姚雪垠曾经的做法和现在的想法之后,尽管他表示理解,但也仍然不忘表达自己的“鄙见”。在8月14日的信中,他这样说道:
十四日大涵谈到回目问题,我这才知道您写第一卷时就打算用回目并拟写了一批回目,后又烧掉,则是想摆脱旧传统。但鄙见以为,旧传统不妨以“古为今用”的方法而化为神奇,回目的造句格式是旧传统,属于形式方面的;但回目的内容,可出奇制胜,不落窠臼。
之后,尽管姚雪垠还多次表示他对“使用回目问题”“十分重视”,但他最终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而没有采用茅盾所建议的章回体形式。
同样,在是“上书主席”的问题上,两位作家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据1975年10月7日姚雪垠给茅盾的信交代,最早提出给毛主席写信的建议者是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负责人江晓天,直接的原因则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复业”与《李自成》的出版都遇到了问题。在这封信中,姚雪垠先是摘抄了江晓天10月6日的来信:
作为一个编辑,从党的文学事业着想,也应竭力支持把《李自成》尽快尽好出版,而况主席又说过话呢?……最近有个想法供你参考:可以给主席写封信,报告《李》稿的写作情况和你的愿望。所传主席对一卷说的话,虽尚待了解确切,但看来是有这回事,说明伟大领袖对《李自成》一书是关心的。
接着他又谈到了毛主席看过《李自成》第一卷后所作的“指示”以及这个“指示”给他带来的好处:
关于主席看过第一卷,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上旬王任重给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同志(现为湖北省委书记)打电话说。当时王任重为中南局代第一书记兼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从北京打长途电话给宋侃夫,告他说毛主席看过了《李自成》第一卷,传达主席的指示大意:虽然有些问题,但应该让作者继续写下去,将全书写完。详细的话,我不清楚。另外只知道市委领导接到王任重的长途电话后就秘密通知工作队设法对我采取保护,所以经过六六年八九月间的“扫四旧”,到处烧书,以及六七、六八年的“大乱”,我的藏书、文稿、多年积累的读书卡片和笔记未受丝毫损失。我也不像文艺界多数知名人士所受的冲击猛烈,从七二年夏天开始我能够坐在家里重理旧业,也就是市委有关领导同意我专心致志地写《李自成》,与王任重所传达的话颇有关系。这都使我不能不终生感激毛主席,感激党。
最后,姚雪垠还表达了他对江晓天“建议”的“慎重”态度以及期盼得到茅盾“关心”、关怀的强烈愿望:
关于江晓天同志的建议,我正在慎重考虑。有无必要,何时写信,如何能到达主席手中,如何措辞,都要仔细斟酌,务求妥当。……以上所考虑的问题,都不打算使别人知道,因为我将您作老师看待,又深知您对这部书特别关心,所以我愿意让您随时多知道一些关于此书的情况。
知道了姚雪垠报告的这一“重大问题”及其“慎重”的态度之后,茅盾当然也不敢怠慢,他在10月23日的信中就直接表達了自己的“意见”:
来信说江晓天同志建议你写个报告给主席,我以为此事不宜贸然为之,将来你全稿写成(即使是初稿)而没有出版社接受的时候,那时再诉诸主席,情况就不同了。鄙见如此,是否有当,请你斟酌。
姚雪垠“反复诵读”茅盾的这封来信,他既感到“感动”,也感到矛盾。一方面,他很想尽快出书以“满足读者的愿望”,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担心自己的创作受到“干扰”。所以,为了《李自成》第二卷早日出版,也为了给自己今后的写作“提供比较顺利的条件”,他经过“慎重考虑”与反复“斟酌”,最终还是决定给毛主席写信。这样,到11月7日,他就及时地向茅盾“奉告”了一个“极好的消息”,也即“今日上午接北京电话,我不久前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信经主席看后批了两句话:‘将全书写完,提供方便条件”。12月13日,姚雪垠又十分兴奋地告诉茅盾,不但“中青提前复业和由谁家出版《李自成》的问题一并解决”,而且他还即将进京,并“准备较长时间住在北京”来“更快更好地完成”《李自成》写作的这一“重大的政治任务”。
上述可知,无论是意见一致的创作主张和“儒法斗争”,还是存在分歧的“章节回目”与“上书主席”,两位作家都能够互相尊重,坦诚相见。作为晚辈,姚雪垠既虚心向茅盾请教和求助,同时又能够坚持自己的想法和做法;而作为前辈,茅盾不但及时地回答了姚雪垠的各种问题,而且还总是以商量的口气提出观点、表达意见。因此可以说,作为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茅盾与姚雪垠的《谈艺书简》不仅谈出了有关《李自成》创作的许多问题,而且还显示出了一种文学大家的坦然风度。正是从种意义上,它被江晓天称之为《歌德谈话录》《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式的“弥足珍贵的遗产”。
(作者系岭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