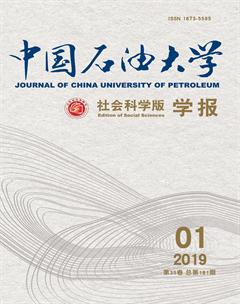论黄震的《春秋》学思想
马丽丽
摘要:黄震是南宋末年一位博学通儒,其为学反对空言心性,主张躬行实践。其主张体现在治《春秋》上,即将《春秋》视作史书,反对《春秋》学上的褒贬凡例之说,力图以史事为根据来注解《春秋》,反对没有根据的臆度和猜测;在《春秋》经传关系上,绝对信经疑传,但又反对时人将“三传”束之高阁,而是有所取舍,并且尤重《左传》;重视训诂之学,反对空言《春秋》大义,尤其注重结合社会现实阐发《春秋》经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关键词:黄震;《春秋》;“三传”
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9)01-0056-06
黄震,字东发,学者称为于越先生,门人私谥曰文洁先生,南宋庆元府(今浙江宁波)慈溪县人,生于宋宁宗嘉定六年(1213),于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因宋亡饿于宝幢山而卒。①黄震是南宋末年一位学问渊博、反对空言心性、主张躬行实践的学者,其为学一宗朱熹,全祖望称“四明之专宗朱氏者,东发为最”[1]2884。但于朱熹,黄氏并不墨守。姚世昌曰:“五经,朱子于《春秋》、《礼记》无成书,慈溪黄东发取二经为之集解,其义甚精,盖有志补朱子之未备者,且不欲显,故附与《日抄》中,其后程端学有《春秋本义》、陈澔有《礼记集说》皆不能过之。”[2]可见后人对黄氏的《春秋》學评价甚高。《黄氏日抄》中,《读春秋》共七卷,黄震就整篇经文进行注解,既引用“三传”,也引用他人注说,其中尤以宋人之说居多,可谓博采众说。另外,《黄氏日抄》中还有读“三传”一卷。一共八卷的内容为我们今天研究黄氏的《春秋》学思想提供了文献资料。
一、以史解《春秋》,反对臆测
黄震认为《春秋》乃据实记事之书,《春秋》大义寓于史事之中。在《读春秋》卷首,黄氏就表明了自己的这一观点:
盖方是时,王纲解纽,篡夺相寻,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权,于是约史记而修《春秋》,随事直书,乱臣贼子无所逃其罪,而一王之法以明,所谓拨乱世而反之正。[3]106
因此,治《春秋》者,“惟平心易气,随其事而读之”,则“善恶自见,而劝戒存矣”。至若其余微辞奥义、当时书法,非后世所能推测,亦非后世所能尽知。[4]14由此,他对历来《春秋》学者以褒贬凡例来解说《春秋》极为不满。他说:
自褒贬凡例之说兴,读《春秋》者往往穿凿圣经以求合其所谓凡例,又变移凡例以迁就其所谓褒贬。如国各有称号,书之所以别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国以罪之,及有不合,则又遁其辞;人必有姓氏,书之所以别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名以诛之,及有不合,则又遁其辞;事必有日月,至必有地所,此记事之常,否则阙文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致以危之,故不月以外之,故不日以略之,及有不合,则又为之遁其辞。是则非以义理求圣经,反以圣经释凡例也,圣人岂先有凡例而后作经乎,何乃一一以经而求合凡例耶?《春秋》正次王,王次春,以天子上承天而下统诸侯。弑君弑父者书,杀世子杀大夫者书,以其邑叛、以其邑来奔者书,明白洞达,一一皆天子之事,而天之为也,今必谓其阴寓褒贬,使人测度而自知,如优戏之所谓隐者,已大不可,况又于褒贬生凡例耶?理无定形,随万变而不齐,后世法吏深刻,始于勅律之外立所谓例,士君子尚羞用之,果谁为《春秋》先立例,而圣人必以是书之,而后世以是求之耶?以例求《春秋》,动皆逆诈亿不信之心。愚故私摭先儒凡外褒贬凡例而说《春秋》者集录之。[3]106-107
当然,指出《春秋》的一字褒贬、凡例、变例为穿凿附会之说的,在黄震之前就有,宋儒石介就曾对《春秋》凡例产生了怀疑,认为所谓的凡例并不能适用于《春秋》全文:
称人者贬也,而人不必皆贬,微者亦称人;称爵者褒也,而爵未必纯褒,讥者亦称爵;继故不书即位,而桓宣则书即位;妾母不称夫人,而成风则称夫人;失地之君名,而卫侯奔楚则不名;未踰年之君称子,而郑伯伐许则不称子;会盟先主会者,而瓦屋之盟则先宋;征伐首主兵者,甗之师则后齐;母弟一也,而或称之以见其恶、或没之以著其罪;天王一也,或称天以著其失、或去天以示其非。[3]107
而关于《春秋》褒贬说,郑樵曾痛加指责,他认为:“以《春秋》为褒贬者,乱《春秋》者也。”朱熹也认为:“《春秋》大旨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霸而已,圣人光明正大,不应以一二字加褒贬于人,不过直书其事,善者恶者了然自见。”[3]107尽管石介、郑樵、朱熹等学者已经对褒贬凡例说提出了怀疑和指责,但是其并不彻底,而黄震的这种“私摭先儒凡外褒贬凡例而说《春秋》者集录之”的做法实际上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春秋》学上的褒贬凡例说进行的一次较为全面的清算。
既然黄震反对《春秋》学上的褒贬凡例说,那么他是如何来解说《春秋》的呢?通读《黄氏日抄》中七卷《读春秋》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黄氏对《春秋》的理解完全是通过分析《春秋》中所载史事来完成的。如《春秋》鲁十二公中,僖公向被称为贤君,黄震对此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世之称其(僖公)贤者,以《诗》有僖公之《颂》,而《谷梁》释《春秋》书不雨为公之闵雨,书雨为公之喜雨也。然《颂》乃臣子颂祷之辞,皆无其实;《春秋》书雨、不雨者,特以其闵民事而书。后之读《春秋》者,因《诗》有《颂》以贤待公,而意其为闵雨喜雨尔,亦岂有其实也哉?若其灭项、伐邾、取须句、取訾娄、取济西田、以楚伐齐、及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阳谷,皆其不贤之实,而始僭礼卜郊,则《春秋》所书,尤不贤之大者也。诗人反以郊为夸,尚可(何)以《诗·颂》为据,而臆度《春秋》之书雨书不雨为褒也耶?[5]197
这里,黄震通过归纳《春秋》经文中所记鲁僖公的事迹,认为鲁僖公并不是一位贤君,指出《诗经·鲁颂》不过是诗人颂祷之辞,并无事实根据;而《谷梁》之“闵雨喜雨”说也只是以《诗经·鲁颂》为据的一种臆度。因此,他反对对《春秋》经文的臆度和猜测。又如,僖公二十五年经文有“宋杀其大夫”,于此,杜预注曰:“其事则未闻。”可是宋儒多有所发挥。胡安国曰:“以泓之战,不死难也。”崔子方曰:“岂嗣君三年丧毕,既临事而治泓战之罪,诸大夫有以众死者乎?”赵鹏飞曰:“宋为楚所败,宋襄自取之也,安可以责其臣,今襄公死,成公立,晋文即位二年方图伯,宋将托于晋,乃归罪于其臣,以灭先君之耻,而杀其大夫。”宋楚泓之战发生在僖公二十二年,而宋杀其大夫却在僖公二十五年。时隔三年,二者之间似乎很难有因果关系,故黄震认为胡、崔、赵等人“皆以宋之事而意度之”,对此应该采取的做法是“阙所不知,当从杜注”[5]185,其态度非常客观。由此可见,用客观的态度、以史事为基础来解说《春秋》确实较臆测为长。
另外,在考察史事的过程中,黄震注意到了历史是发展的,这就是《读春秋》中的“势”说。如僖公十四年秋,狄侵郑,先儒多以此怪罪当时的霸主齐桓公不能相救,黄震却持不同的观点,认为相互侵并乃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不应以此来责备齐桓公。他说:
地丑德齐而相侵并,势则然也。商周初兴,尝一正之,随复侵并,故禹之万国至周兴才千八百国,至春秋才七十余,其间侵并谁以罪商周之君哉?方春秋之初,夷狄交侵,诸侯亦纷纷如斗兽,齐桓公积二十余年,尽心力经营辑睦诸侯,盟楚伐戎,以少杀其侵并之势,年至气衰,鼓舞既倦,戎狄荆楚之间作,亦势然矣。岂皆齐侯之身事而责之备也哉。[5]175
因此黄震在解说《春秋》的时候常将事情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来进行考察。如襄公十五年夏齐侯伐鲁国北部边境,并包围成这个地方,鲁襄公救成之师至遇,齐师退,公即不再前进,而由季孙宿、叔孙豹帅师筑成郛,诸儒于此多责襄公不能救成,致成郛坏而鲁非时以城之。当时鲁国已尽为孟孙、季孙、叔孙三家所有,成乃孟氏私邑,救成、城成并非襄公所能左右,因此,黄震认为以前诸儒所论“殆腐儒之谈,不能尚论其世者也”[6]274。因此,在考察春秋之事的时候,应“惟以春秋之世而求圣人之心,则思过半矣”[3]108。这样,黄氏解说《春秋》经文所得出的结论一般比较公正。如襄公年间,郑国屡遭晋楚侵伐,郑因此时附晋,时附楚,对此,前辈学者多责郑之无夷夏之辨,而黄震却比较平和地说道:“郑处晋楚之间,亦难矣。”[6]268
黄震以史事为根据来解说《春秋》,使《春秋》的意思一下子变得简单明了起来。如《春秋》十二公中,有七公书“即位”,五公没有书“即位”,一直以来《春秋》学者对此都务作深求,认为此乃含有圣人笔削之深意。如隐公元年,未书“公即位”,“《左氏》谓隐摄,《公羊》谓隐为桓立,《谷梁》为隐让”,后世学者“或谓其禀命为正,而正者不必书,或谓不禀命而即位,圣人故绌夺之而不书”,黄氏认为他们的说法“皆无所考”[3]109,之所以不书“公即位”,是因为“不行即位之礼”[7],相反,书“公即位”,乃是因为行了即位之礼,《春秋》不过是“即其实而书之”[3]121。于是这个繁琐的问题一下子就变得简单明了起来。再如关于《春秋》的历法问题,我们知道,夏商周三代分别以建寅(一月)、建丑(十二月)、建子(十一月)为岁首,可是商周在称他们始建国的第一年第一月的时候,是称“元年十二月”或“元年十一月”呢,还是称“元年正月”?这就是改月不改月的问题。与此相关,还有一个“时”的问题。“时”即季节,在夏历里,一、二、三月属春季,四、五、六月属夏季,七、八、九月属秋季,十、十一、十二月属冬季。如果以年、时、月连书的话,殷人或周人新君即位的第一年第一月,是该称“元年冬正月(假设已经改月)”呢,还是该称“元年春正月”?这是改时不改时的问题。《春秋》历法,有无改时改月,诸家聚讼纷纭。在有无改月上,自杜预注《左传》云“周正月今十一月”之后,各家多主张《春秋》“改月说”,只是在这“改月说”中,又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改月乃周人所改,孔子只是纪实而已,朱熹就持这种观点;另一种认为周人虽用周正,但记事书时是不改月的,今日所见《春秋》中的“春王正月”乃孔子所改,这是胡安国的观点。在改时的问题上,学者们也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时随月移,周人既以建子之月为岁首,则十一、十二、一月为春,依次类推,因此《春秋》中的“時”是与周正有关的;一种认为《春秋》的时与周正无涉,采用的乃是夏时,如胡安国的“以夏时冠周月”之说,为的是体现孔子的“行夏之时”的微言大义。朱熹虽反对胡安国的孔子“改月说”,但是对于《春秋》中采用夏时是表示赞成的。由此可见,《春秋》历法这一问题实在是纷繁复杂。黄震认为《春秋》乃圣人据实记事之书,因此在这一问题上对前人这些观点表示了怀疑,他说:“以春为夏正之春,建寅而非建子,可也;以月为周之月,则时与月异,又存疑而未决也。”[3]109因为“三代虽有改正朔之事,而天时恐无可改迁之理”。于是他在这一问题上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天时无可改易之理,圣人无谓冬为春之事,商之建丑以异于夏,周之建子以异于商,皆以革命欲整一人之心,故以此月为岁首,受朝飨耳。其建丑之为十二月,建子之为十一月,固自若也。建丑、建子之为冬,建寅而后谓之春,固自若也。圣人作《春秋》,书“春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正以顺天时正人事,所谓行夏之时,见之行事者也。周实未尝改天时,孔子亦初非改周制也。自汉儒有“三正”之说,杜氏有“周正月今十一月”之语,诸儒遂以《春秋》之春为今日之冬,每于系时系月之事随事生说,以为非时而讥之。今以夏时参之,未见其有非时者。[3]127
可见,黄震认为不但周人未尝改时改月,孔子在修《春秋》的时候也只是据实直书,并没有改周制。他还为此寻找证据到:
商之建丑,十二月也,《书》称“惟元祀十有二月”,未尝改十二月为正月;汉初建亥,十月也,汉史亦书“冬十月”,未尝改十月为正月。以此而推《春秋》之“春正月”,恐即自古及今之春正月,安得以十一月为正月,而又就以十一月为春耶?且《诗》作于周,如“四月惟夏”、“六月徂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无非夏正;《月令》一书作于周末,十二月之间中星候虫亦无一不用夏正;惟《孟子》称“七八月之间旱”,世指为夏正之五六月,然禾稼早晚所至不同,今江浙间十月获稻,而七八月间苦旱者甚多;如“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殆亦冬寒而济涉耳。惟《小戴礼》之《杂记》有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若可疑者,然此书出于汉儒,恐因周以建子为岁首,遂追称正月,未可知。汉改正朔,儿宽等议曰:“帝王必改正朔,至不相复,推传序文,则今夏时也。”此其证矣。姑舍是而《春秋》言之,《春秋》书“秋八月,大阅”,时也,今因以八月为六月,遂曰“盛夏大阅,妨农害人”;书“冬十月,雨雪”,亦时也,今因以十月为八月,遂曰“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此类安知非经文本用夏正,不过据实而书耶。[4]13
黄震从《书》《诗》《月令》和汉史等文献记载中寻找《春秋》并无改时改月的证据,力主《春秋》经文所用的本是夏正,这样就使以《春秋》改时改月为前提而产生的讥贬之说失去了依据,使纷繁复杂的《春秋》历法问题也一下子简单明了。
二、以经为正,取舍“三传”
与宋代的大多数学者一样,黄震对于《春秋》经传的态度是绝对信经疑传的,当经传记载产生差异的时候,黄氏总是“以经为正”[8]。但是与其他宋代学者不同的是,黄氏并未将《春秋》“三传”束之高阁,而是采用了批判地采纳的态度。
在黄震看来,《左传》并不是传经的,他说:
《左氏》虽依经作传,实则自为一书,甚至全年不及经文一字者有之,焉在其为释经哉?经与传等夷相错,经所不书者,传亦窃效书法,以附见其间,其僭而不知自量亦甚矣。若夫浮夸而杂、品藻不公又在所不论也。[9]868
关于《左传》究竟是不是传经的,自汉代以来就已成为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左传》所记载的内容并不总是与《春秋》经文一一对应的,除了有大量的无传之经外,似乎还有数量相当可观的无经之传。黄震也正是因此而否定《左传》的传经性质。另外,《左传》好诬,叙述了许多虚妄怪诞之事,且好以成败论是非,因此黄震认为其“浮夸而杂、品藻不公”也确有所据。正是因为这样,黄震对《左传》中的“君子曰”之类的议论进行了驳斥,如,晋国的赵穿杀了晋灵公,但是因为赵盾为当时晋国的执政大臣,赵穿是其家人,因此太史记载这件事就书为“赵盾弑其君”。于此,孔子发议论云:“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对此,黄震评价道:“弑君之罪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而曰越境乃免,左氏每借君子妄为之辞,今又诬吾孔子,不其甚乎?”[9]852但是黄震并没有否定《左传》的价值,他说:“因其舍经而别载行事,可以验其曾见当时国史,故读《春秋》者不可以废《左氏》。”[9]868可见黄震是重视《左传》的记事性质的,事实上,在《读春秋》中对《春秋》经文的解释,多是以《左传》所记史事为出发点的。在“三传”中,黄震也最相信《左传》的记事,当《公羊传》《谷梁传》所记事迹、人名、地理与《左传》不同的时候,黄震一般都以《左传》为准,他说:“左氏及见国史,故依之以释经,公羊不知何所主而然,意亦别有记载之书而集之欤。世远不知孰是,若以次而言,且当据《左氏》尔。”[10]872
对于《公羊传》,黄震是肯定它的传经性质的,他说:“迹其所释皆经,未尝舍经而为之文,此视左氏之僭为贤。文虽不及《左氏》之核,而明白则过之。”[10]872可见,黄震是肯定《公羊传》对《春秋》经义的阐释的。但是,对于《公羊传》所释经义,黄震也是采取了批判地采纳态度,他说:“《公羊》‘大居正之语固可谓能执其义之要者,至谓‘权为反经,谓‘百世可以复仇,则非义已甚而乱之萌也。”[10]872
对于《谷梁传》,黄震认为其“言经略与《公羊》同”。而在对有些经义的阐释上,黄震认为《谷梁传》优于《公羊传》,他说:“《公羊》以妾母夫人为礼,而《谷梁》黜之;《公羊》以宋襄之师,文王不是过,而《谷梁》非之,所见似又过于《公羊》。”但是在《春秋》“三传”中,《谷梁传》一直不受学者重视,故黄震对此同情到:“然举大体言,则视《公羊》又寂寥矣。”[11]873
对于“三传”的注家,黄震对范宁评价最高,他说:
杜预注《左氏》独主《左氏》;何休注《公羊》独主《公羊》;惟范宁不私于《谷梁》而公言三家焉。如曰:“《左氏》以鬻拳兵諫为爱君,文公纳币为用礼,是人上可得而胁,居丧可得而婚也;《谷梁》以卫辄拒父为尊祖,不纳子纠为内恶,是为子可得而叛,仇雠可得而容也;《公羊》以祭仲废君为行权,妾母称夫人为合正,是神器可得而窥,嫡庶可得而齐也。”又曰:“《左氏》艳而富,其失也诬,《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凡皆确论云。[11]873
从黄震对《春秋》“三传”的批评可以看出:黄震重视《左传》的记事和《公羊传》《谷梁传》二家的传义,但当经传记事产生差异的时候,黄氏总是以经为准;在《春秋》经义上,对《左传》的议论有所怀疑,并且对《公羊传》《谷梁传》的经义也有所取舍。这样,黄氏主要以《左传》所记的春秋时期的史事为基础,参以《公羊传》《谷梁传》及先儒所发挥的经义,对《春秋》经文进行了注解,这较以前宋儒脱离“三传”、一味臆测经义的做法客观了许多。
三、出入现实,体现时代特色
历代《春秋》学者对《春秋》的讲解和发挥都会带有时代的特色,黄震也不例外。通读《读春秋》,我们可以发现黄氏的《春秋》学有两个时代特色。
黄震是一位理学名家,但是在南宋末年,由于理学正统地位的确立,朝廷崇奖理学,周、程、张、朱之书布满天下,形成人人争诵的局面,士大夫耻言政事,拱手高谈性命义理以相尚;士子为苟合时好,则埋头记诵语录、章句,以猎取声利。陆九渊的“心学”在这时有了取代朱学的趋势。理学的空疏化倾向已非常严重。因此南宋末年的一些学者开始对此种倾向进行纠正,黄震就是其中一位。对当时学术界的情况,他说:
文公既没,其学虽盛行,学者乃不于其切实,而独于其高远。[1]2899
汉、唐老师宿儒泥于训诂,多不精义理,近世三尺童子承袭绪余,皆能言义理,然能言而不能行,反出汉、唐诸儒下,是不痛省而速反之,流弊当何如也![1]2896
谨于此,黄震主张躬行实践之学即实学,他说:“圣门之学,惟欲约之,使归于实行哉!”[1]2889这一实学的主张使黄震在治学上的表现就是要多学,要通过训诂来讲求义理,他说:“夫万事莫不有理,学者当贯通之以理,故夫子谓之一以贯。然必先以学问之功,而后能至于贯通之地。”[1]2889“自本朝讲明理学,脱去诂训,说虽远过汉、唐,而不善学者,求之过高,从而增衍新说,不特意味反浅,而失之远者或有矣。”[1]2888而这样的治学主张在他的《春秋》学上也有所反映。首先,前文述及的他以史事为基础来讲解《春秋》,反对臆度和猜测,正是对当时学界空疏学风的一种纠正。其次,他善于运用考证、训诂等方法对《春秋》经文进行注解,如《春秋》经文有隐公“六年春郑人来渝平”,黄震对此注解是:
《左氏》作“渝平”,渝,变也,渝前日之平,犹绝交也。《公》、《谷》皆作“输平”,《公羊》曰:“输平犹堕成也”、“败其成也”,《谷梁》曰:“输者,堕也”、“不果成也”。然诸儒多从《公》、《谷》作“输”,而不从其训,曰:“输,纳也,输成于我,以求平也。”[3]115
这里黄震就是从字意的训诂着手,对包括“三传”在内的各家注解作了一个比较。而在比较之后,黄震作了考证:
以经考之,前年公子翚伐郑,是尝有憾而未尝有平,初无平之可渝,言渝平者非也。郑与齐党,鲁与宋党,今宋伐郑围长葛,惧鲁从宋,而郑亦殆偶。郑尝伐宋,宋求救于鲁,使者失词,鲁怒不出兵,郑乘此隙致平于鲁,以离宋之党,故今年春,郑来输平。今年夏,公即与齐盟,已而公与齐、郑又会于中丘以谋伐宋,是前乎此,鲁与宋,后乎此,鲁背宋而与齐、郑,皆郑输平所致,言输平者是也。[3]115
通过对当时的形势进行分析,黄震对各家的说解作了判定。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黄震一般都会阙疑存异,态度非常客观,如文公十四年经文有“宋子哀来奔”,关于“子哀”是名是字,黄震说:
子哀,一以为字,一以为名,不可考。孙氏曰:“宋公族,子,姓,哀,名也。”黎氏曰:“子哀必宋公之子,经有子同、子纠。”未知孰是。[12]
再者,黄震在《春秋》经文的文字上也下了一定的功夫,他善于比较《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家经文文字上的差异,如桓公十三年,经文有“郑伯使其弟语来盟”。这是《左传》的经文。黄震于此条经文下注曰:“语,《谷梁》作御。”[3]132桓公十一年经文有“公会宋公于夫锺”,黄震注曰:“夫锺,郕城,《公羊》作夫童。”[3]130对于一些难读的字,黄震也是一一标明字音,如僖公九年经文有“甲子,晋侯佹诸卒”,对“佹”字的读音,黄震注曰:“佹,九委反。”[5]171由以上可以看出,黄震以史事为基础并运用考证、训诂、小学等方法来注解《春秋》,态度客观,努力纠正南宋末年理学的空疏化倾向,这可以说是黄震《春秋》学的第一个时代特色。
另外,黄震生活于南宋末年,当时民族矛盾非常尖锐,金、元少数民族政权先后对南宋王朝形成巨大的威胁,于是,在黄震的《春秋》学中,“内中国、外夷狄”“严夷夏之辨”这一《春秋》大义就被突出得更为强烈,这主要表现在他对春秋时期霸业的评判标准上。他认为“霸之为言,王室既衰,方伯出而攘夷狄以安中国”,也就是说,称霸者,以攘夷狄、安中国为前提,非此则称不上霸。在这一标准下,他不赞同流行于世的“五霸”说,以为终春秋之世,真正能称上霸的只有齐桓公和晋文公,“霸业惟齐为盛,惟晋为久,惟齐威(桓)、晋文为可以言霸”。 宋襄公“戕中国而结夷狄,霸之反也”,秦穆公、楚庄王“以夷狄而胁中国,霸之变也”,他们“皆不可言霸也”。[5]194
也是在这一标准下,黄震对“贵王贱霸”这一传统的《春秋》大义进行了修正,在尊王的前提下,他对齐桓、晋文的霸业也给予了充分的褒奖,他说:“后之读《春秋》者弗察也,凡威、文之功皆指以为威、文之罪,呜呼!独不观威公未霸,天下之乱为如何,威公霸而天下定矣;威公甫没,天下之乱又如何,文公霸而天下又定矣。此春秋之世,生民倚之为司命,周之宗社所恃以不泯不灭,而顾以为罪,可乎?”[5]195既然齐桓、晋文的霸业是为了攘夷狄、安中国,那么,对他们在建立霸业的过程中所进行的征伐、会盟等活动,黄震开始重新定性。兹举两例:
僖公四年齐桓公率领诸侯伐蔡国,传统学者认为因为齐桓公“娶蔡姬,公怒归之,未绝也而蔡嫁之”,齐桓公此举是“以私憾加蔡”,是以归罪于齐桓公。黄氏不同意这一说法,他认为:
蔡、郑当楚之冲,华夷之门户也,故齐侯不得蔡,无以及楚,侵蔡伐楚,势当然矣,诸侯之师安能飞越蔡城而伐楚哉?……蔡以中国陷于楚,得蔡而后楚之门户启矣,呜呼,一问而楚词屈,兵不血刃,堂堂之楚,摄如鸟鼠,而中国不为左衽者,威公之力也。[5]164
又僖公二十八年有“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盟于践土”和“天王狩于河阳”两件大事,对此,传统观点多认为是晋文公以践土之盟定霸业,后召周王以见诸侯,属以臣召君,当为不敬。黄震并不这样认为,他说:
僖二十四年书天王出居于郑,自后未尝书归于成周,践土即郑地也,则天王盖居于是久矣……天王之归,盖因践土之盟也,前此郑陷于楚,天下无勤王者,今晋侯克楚于城濮,以敌王忾,奏凯于王,会诸侯以盟于郑,以诸侯朝焉,天王因是复归于成周。冬,书河阳之狩,则天王既归而出狩也。非文公缓于纳王也,盖先胜楚而后纳王也,伐楚者纳王之资也,然则践土之盟,厥勋茂哉。小人不乐成人之美,取“三传”掇蜂之说,以疵吾晋文,君子所不甘焉,故愚稽于经以正之,非私晋文。[5]189
这样,黄震不但洗脱了齐桓和晋文的罪名,反而赋予其尊王攘夷的荣誉。由此可见,尖锐的民族矛盾使黄震的夷夏观念非常强烈,从而影响了他对春秋大义的理解以及春秋时期诸侯行为是非的判断,这可以说是他的《春秋》学的第二个时代特色。
综上所述,黄震是将《春秋》视作史的,反对《春秋》学上的褒贬凡例之说,他力图以史事为根据来注解《春秋》,反对没有根据的臆度和猜测,并注意到了历史是发展的,善于以当时的背景来考察当时的历史,因此得出的结论常比较客观和公正,并且使《春秋》的意思也变得简单明了起来。在《春秋》的经传关系上,黄震是绝对信经疑传的,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抛弃“三传”,而是采取了一种批判地采纳的态度,并且在“三传”中,因为《左传》的记事性质,黄震最重《左传》。因为黄震生活于南宋末年,為了纠正理学的空疏化,黄震在注解《春秋》的时候开始注重考证、训诂等方法的运用。另外,尖锐的民族矛盾使黄震具备了更为强烈的夷夏观念,从而影响了他对春秋大义的理解和对诸侯行为是非的判断,这就构成了黄震在《春秋》学上的两个时代特色。
参考文献:
[1]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86)·东发学案[M].全祖望,补修.北京:中华书局,2013.
[2] 朱彝尊.經义考(卷142)[M].北京:中华书局,1998:1642.
[3] 黄震.黄氏日抄(卷7)·读春秋一[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 黄震.黄氏日抄(卷33)·读本朝诸儒理学书·程氏经说·春秋[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 黄震.黄氏日抄(卷9)·读春秋三[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 黄震.黄氏日抄(卷11)·读春秋五[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 黄震.黄氏日抄(卷8)·读春秋二[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37.
[8] 黄震.黄氏日抄(卷12)·读春秋六[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293.
[9] 黄震.黄氏日抄(卷31)·读春秋左氏传[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 黄震.黄氏日抄(卷31)·读春秋公羊传[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 黄震.黄氏日抄(卷31)·读春秋谷梁传[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 黄震.黄氏日抄(卷10)·读春秋四[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211.
责任编辑:赵 玲
Abstract: Huang Zhen was a scholar of profound learning living in the end of the Song Dynasty. In the empty academic atmosphere, Huang Zhen insisted on studying for applying in practice. He took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s a historical book, instead of a book of complimentary and critical commentaries. He tried to annotate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on historical facts and opposed the unfounded assumptions and speculations. In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book of the Annals and the commentaries on it, Huang Zhen absolutely believed the book and doubted the Commentaries. But he was against putting the three commentary books on the shelf and advocated having some choices. He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Zuo Zhuan(Zuos Commentary). Huang Zhen emphasized on exegesis and opposed pedant talks of the principles of the Annals. In particular, he paid attention to reinterpreting the Annals with the social reality. His studies had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Key words: Huang Zhe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he Three Commenta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