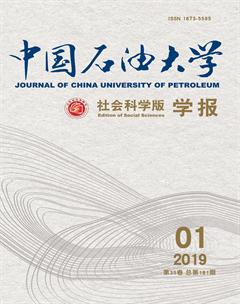文化政治批判:伊格尔顿与后现代主义论争
周思钊
摘要:后现代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背道而驰,特里·伊格尔顿是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他以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迎接挑战,旗帜鲜明地从文化政治批判视角切入后现代主义论争,将后现代主义的起因归结为20世纪60年代激进运动的失败,并从后现代主义激进姿态中看到其保守本性:后现代主义不过是犬儒主义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表现。于是伊格尔顿对其展开针对性的批判,主张回归社会主义宏大叙事。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清算后现代主义思潮,也是中国学术界在移植后现代主义时必须做的工作,因此特里·伊格尔顿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值得深思。
关键词:特里·伊格尔顿;文化政治批判;后现代主义;社会主义宏大叙事
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9)01-0068-06
后现代主义思潮于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国家兴起,八九十年代转移到亚洲,在中国也是热门话题,正如特里·伊格尔顿(以下简称伊格尔顿)所言,中国在“进口减肥可乐的同时一起进口德里达”[1]139。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激进锋芒直指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值得认真对待;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大力宣扬反本质主义、反总体性、反宏大叙事等观点,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背道而驰,与后现代主义紧密相连的“后马克思主义”也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背离①。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清算后现代主义思潮,是中国学术界移植后现代主义时必须做的工作。伊格尔顿是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具有极其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意识,在2011年出版的专著《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Why Marx Was Right)中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可以说,他对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政治批判,是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清算的典型,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一、伊格尔顿介入后现代主义论争
“后现代”一词出现很早,美国学者凯尔纳(D. Kellner)与贝斯特(S. Best)在《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中认为,最早使用“后现代”概念的是英国画家约翰·瓦特金斯·查普曼(John Watkins Chapman),大约是1870年前后,他专门用“后现代”一词来指那些比法国印象主义绘画还要现代和前卫的绘画作品[2]118,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一词才在西方逐渐成为流行话语。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在西方引起了一场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的争论,这场争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法国尤为激烈,许多大思想家都参与其中:哈贝马斯站在捍卫现代性的立场上,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我们仍生活在现代——而不是后现代”[3],因此现代社会中产生的很多问题应该依靠现代性来解决,而不是后现代性;与哈贝马斯相反,其他思想家纷纷站在后现代主义立场上,颠覆现代性,主张告别现代性,走向后现代,例如,福柯“人的死亡”命题的提出,利奥塔对大叙事或元叙事的否定,布尔迪厄通过“场”的概念来消解理性与普遍性,德里达则通过“延异”等概念解构一切形而上事物,等等。这场论争很快越出法国学术界,成为欧美学术圈的重要话题,国际上很多学者纷纷参与进来。[4]
伊格尔顿介入后现代主义论争具有一定机缘性。伊格尔顿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研究后现代主义思想,其专著《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出版已经是90年代中后期,此时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学术界已经开始退潮。正因后现代主义的“退潮”,伊格尔顿才能够“把后现代主义放在历史视角中进行观察,努力保持了与它的一段批评距离”[1]“致中国读者”2,只有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距离,才有条件将整个对象纳入研究视野当中,进行更为全面的反思和批判。
其实伊格尔顿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关注后结构主义,他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承续他对后结构主义批判而来,因为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关系密切,许多后结构主义大师,如福柯、拉康、罗兰·巴特等,也是后现代主义大师。除此之外,后现代主义思潮也时常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摩擦。一些后现代主义者直接攻击马克思主义,利奥塔说,“就它(指利奥塔所著的《异教主义指示》)是一个表明在多大程度上马克思主义的大叙事已不再能推动法国知识分子的问题而言,它稍稍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对政治力量,也即是对现存的、确定的政治力量的分析”[5]47,“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们在努力消除异化,但人的异化似乎以毫无变化的形式被重复了”[5]158。在利奥塔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大叙事已经不能够解决当下问题、已经过时,因为历史中并不存在什么宏大叙事,存在的只是各種微观政治,马克思对劳动异化的批判并没有取得什么实际效果,后工业社会中的人依然身处异化世界当中。还有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声称是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伊格尔顿在《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雅克·德里达和〈马克思的幽灵们〉》中指出:“《马克思的幽灵们》不仅想赶上马克思主义,而且想比它更左,声称解构主义始终就是激进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6]德里达将激进的解构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实际上混淆了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这种混淆极具欺骗性,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引入歧途,比利奥塔的做法危害更大。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使得差异、相对、多元观念盛行,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人文主义大行其道,而这些思想又与战后复苏的资本主义经济一起企图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西方世界消亡。作为一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认清这种局面,有必要站出来给以回击。他说:“它(指马克思主义批评)自其如日中天的1970年代中期以后就憔悴下来,并陷入了某种沮丧。”[7]在各种激进左派政治落潮之时,伊格尔顿并不放弃马克思主义信念,也不盲目乐观,而是坚持与各种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思想作斗争。他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说:“马克思并非无懈可击,而我只是想展示马克思观点的合理之处。”[8]
二、伊格尔顿视角下的后现代主义概念
后现代(postmodern)、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是一组复杂的概念。虽然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现代主义” 是热门话题,但是关于“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这三个词的定义众说纷纭。据考证,“后现代”一词在1870年左右被查普曼使用过;“后现代主义”一词在1934年被奥尼斯(F.Onis)使用过,用来指一股诗歌潮流;“后现代性”一词最早出处无从考证。实际上,从20世纪60—80年代,这三个词经常被混用,并且没有被明显区分,到了90年代,这三个词才逐渐被一些学者区分开来。伊格尔顿介入后现代主义论争时,已认识到这种复杂情况,知道后现代主义涉及建筑风格、哲学观念、文化观念、历史问题等各个方面。伊格尔顿首先承认“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两词的区别。他指出:
“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怀疑关于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的经典概念,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解放的观念,怀疑单一体系、大叙事或者解释的最终根据。与这些启蒙主义规范相对立,它把世界看作是偶然的、没有根据的、多样的、易变的和不确定的,是一系列分离的文化或者释义,这些文化或者释义孕育了对真理、历史和规范的客观性,天性的规定性和身份的一致性的一定程度的怀疑。”
[1]1然而,后现代主义则是“一种文化风格,它以一种无深度的、无中心的、无根据的、自我反思的、游戏的、模拟的、折衷主义的、多元主义的艺术反映这个时代性变化的某些方面,这些艺术模糊了‘高雅和‘大众文化之间、艺术和日常经验之间的界限”[1]1。其次,伊格尔顿“倾向于坚持使用较常用的术语‘后现代主义来概括这两种事物”[1]2。
伊格尔顿如何能够将两种事物概括进同一个术语当中?原因是关于后现代性,伊格尔顿并不关注后现代哲学的具体理论公式,不关注个别理论家的著作,而是抽象出后现代主义者信奉的信条,这些信条正是一种抽象的思想风格;关于后现代主义,他并不关注其具体的文化艺术流派,不对个别艺术品进行讨论,而是排除掉这些特殊性事物,关注作为整体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观念,这其实也做了抽象化处理。通过将这两个词都从具体事物提升到抽象的思想领域,在这抽象层面上两者成为均质性之物,因此两者能够融汇在同一个术语中。
伊格尔顿说他试图从政治和理论层面批判后现代主义,而不是考察后现代主义的颠覆力量,因此,伊格尔顿的后现代主义批判其实就是其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一次交锋,具有极其明显的政治倾向。这次交锋的形式是抽象的思想批判,交锋的另一方则是伊格尔顿所预设的对手:一些激进的左派人士和一些看似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一些左派人士在激进政治运动失败之后,转而分享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想,而后现代主义者以更激进姿态出场,和激进的左派人士有很多共同点,两者关系极其密切。伊格尔顿不仅批判后现代主义者虚假的激进观,同时也批判那些放弃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转身投向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左派人士。
① 伊格尔顿说:“无论后现代主义出自其他什么地方——‘后工业社会、对现代性的最终怀疑、先锋派的重新发现、文化的商品化、生气勃勃的新政治力量的出现、关于社会的某些经典思想体系和主体的崩溃——它也是,并且主要是一场政治失败的后果。”见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8页)。
三、伊格尔顿视角下的后现代主义起因
关于后现代主义起因,说法众多,学术界并未达成共识。
佩里·安德森比较综合地指出,后现代主义起因来自三个方面:首先,统治秩序自身命运发生了变化;其次,科技价值发生了变化;最后,时代政治发生了变化。[9] 根据陈嘉明的归纳,后现代思潮的起因及其性质可以简要地归为五类。其一,社会动因说。即将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归结为社会政治背景下的产物,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美国的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示威活动等社会运动的兴起,使得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相信,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已经破晓,同现代社会与文化的决裂已经出现。其二,后工业化或信息社会说。即现在以服务业为基础的新社会亦即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正在形成,它将逐渐取代工业社会。于是,“信息社会”概念为“后现代社会”概念提供一个认识基础,引导人们从“知识状态”的角度考察后现代问题。其三,消费社会说。即认为后现代社会表现为一种“消费社会”的生活方式,其中消费文化盛行,它支配着社会所有成员,成为全新的、公认的社会状况。消费主义把所有东西都当成相同的消费类别,它以生产影像和时尚为己任,以此来取代现代叙事赋予事物以意义的任务,它通过消费者对其预言性话语的认同,而成为日常生活的真实事件。其四,文化反叛说。即西方现代文化的价值体系已经被摧毁,西方社会正处于一个时代转换的风水岭,后现代文化就是对现代主义的激烈攻击,它反叛过去的价值与文化、反对资产阶级、用毫无道德标准的享乐主义来取代资本主义文化的正当性。其五,叙事危机说。即作为现代性标志的元叙事发生了危机。随着当今知识的本质、状况和地位的改变,知识成为一种商品化的四处流动的信息,成为生产力的要素,于是现代性的元叙事必然发生危机。而后现代的标志就是反对这种元叙事,反对现代知识观念与方法,从而寻求对知识性质与思想的方法论导向上的重新解释。[2]118-121前三点偏重从社会层面寻找后现代主义起源,而后两点偏重从文化层面寻找后现代主义起因,不过总而言之,后现代主义基本上是一种合力作用的结果。
然而,伊格尔顿却给出一个十分独特的见解,即后现代主义是西方激进政治运动失败的产物。①
这里的“失败”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从激进政治运动方面看,“失败”主要指二战以后西方世界爆发的一系列激进政治运动的失败。西方世界20世纪60—70年代爆发了一系列社会运动,尤其以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最为突出,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参与者达一千多万人(法国当时总人口五千万左右),但是这场激进的政治运动最终以戴高乐为首的资产阶级政府胜利而告终。这些激进政治运动的目的旨在反对当下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并没有取得理想结果。其次,从激进思想运动方面看,“失败”主要指英国新左派运动的落潮。英国新左派运动是一种非体制化的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终结,其第一代以汤普森、威廉斯等为代表,第二代以霍尔、安德森等为代表。
但是70年代末,保守主义者撒切尔夫人当选为英国首相,她提倡經济自由化和私有化,大幅度削减国家福利、调整财富再分配制度,采取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措施,推动英国社会经济发展,使英国社会、经济重新焕发勃勃生机,这些也动摇了英国新左派思想的经济基础,使得社会主义在英国变得遥遥无期。同时各种亚政治的运动(如女权运动、生态运动、和平运动等)很快取代了英国新左派政治运动,由此英国新左派政治运动被时代遗弃了。[10]伊格尔顿讽刺说,新左派的政治学说和常用的社会语言相比“是不同星球的话语,而不是相邻国度的话语”,左派们“说着一种如此古怪、与当今时代格格不入的话语,好像是在说诺斯替教或者雅典爱情式的语言,没有谁会劳神探求它的真实价值”。[1]5最终英国新左派所关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新左派既没有得到对手赞成,也没有得到否定,而是直接被社会淘汰,成了过时之物。
面对这场失败,政治左派做出了各种不同反应。伊格尔顿分析了其四种反应:第一种是转向右派;第二种是出于习惯或者怀旧之情,继续坚持左派政治信仰,但面对现实焦虑不安;第三种则是坚定的左派信徒,持着左派必胜的信念,盲目相信革命即将来临;第四种是将左派激进冲动坚持下去,只不过转移了冲动对象。伊格尔顿批判的对象主要是持第四种反应的左派人士,因为其对马克思主义者极具迷惑性,危害最大,相比之下右转派和幼稚的左派必胜派错误明显,其极容易被左派人士察觉,危害不是很大。激进的政治左派们面对现实制度无法突破,面对有关阶级、生产方式、经济正义等问题难以解决,只好将激进冲动转移到制度的边缘领域,这些边缘领域受制度的控制较松,充满着含糊不清、不确定等特性,因此政治左派认为在这些边缘领域抗争还是可以的,伊格尔顿反讽道:“这个制度无法突破,但是至少可以对它的权限含糊不清的那些神经痛点进行短暂的侵入刺探。”[1]6这些边缘领域是指资本主义总体制度控制较松散的语言、性、身体、无意识等,因此政治左派们对话语、欲望、身体等方面的兴趣急剧膨胀。
随着这种激进冲动的转移,政治左派激进的敏感性也发生了分化,一方面是脆弱的悲观主义,一方面是对差异、变动和瓦解的憧憬。悲观主义是指政治左派们相信资本主义制度无法突破,坚持强调权力的桀骜不驯、自我的脆弱、资本的吞噬力量、欲望的贪得无厌、形而上的不可避免等;憧憬是指政治左派们继续梦想着一种乌托邦世界。伊格尔顿指出,政治左派这种对未来充满憧憬的乌托邦思想,对制度总体的批判主要是从制度外部和制度內部两个方向展开的。首先,一部分极左的思想家(ultra-leftist)试图从制度外部寻找具有颠覆性的他者,而他者必须超出人们理解框架之外,因为人们所能够理解的事物都与人们堕落的逻辑有共谋关系,最终他者也就像康德所说的神秘的物自体一样无效,这种试图从制度外部寻找他者的思想也就走向了伪神秘主义(pseudo-mysticism)。其次,一部分不那么浪漫极左的思想家(less romantically ultra-leftist)努力发明一种新版的关于“内在批评”的标准,试图从制度内部来寻找具有颠覆性的他者,“任何制度都是在自己的内部注册它的他性”[1]12,但是这种来自内部他者的颠覆只能是短暂的、阵发性的,“因为对它来说,变成制度性的就是堕落成为被它所质疑的那一逻辑的牺牲品”[1]12。伊格尔顿指出这种“内在批评”注定失败,因为这种思想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假定:创造性制度(a creative system)的观念是一种矛盾修饰法(oxymoron),即现实制度同时将其对立面的事物也包含进制度内,那些具有颠覆力量的他者完全是制度本身的产物,而且他者也知道自身就是如此。所以伊格尔顿说:“那些到处搜寻某种便利的力量用以反对‘现存制度的人们,通常是身穿多元主义外衣的纯粹一元论者,他们忘记了‘制度本身是与它的核心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的。”[1]13
从伊格尔顿对激进冲动转移的批判中,可以看到伊格尔顿政治对手的演化过程。激进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激进冲动并没有就此扑灭,而是转移到语言、性、身体等离资本主义制度更远的领域。面对失败,持第四种反应的左派人士就很容易演化成伊格尔顿所批判的后现代主义者。后现代主义兴盛于20世纪70—80年代,正好是激进运动遇挫的一段时期,伊格尔顿正是看到两者在历史中的关联性,并且后现代主义一出场便强调对现代主义的断裂、反叛,与左派思想一样,具有浓烈的激进色彩。美国后现代主义研究者戴维·哈维指出:“(后现代主义)一种反权威主义的和反偶像崇拜的思想方式,一种坚持他者声音之本真性的思想方式,一种赞赏差异、非中心化和趣味民主化的思想方式,一种赞赏想象战胜物质性之力量的思想方式,都必须具有一种激进的锋芒。”[11]因此后现代主义思想本身也容易与左派思想发生联系,一些重要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如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德勒兹等都受到法国“五月风暴”等激进运动的影响,不过伊格尔顿知道其对手并不是均质化的,所以他常对各种各样的后现代主义者加以区分,比如他在《后现代主义的幻象》中提到过“比较脆弱的后现代主义者”“不那么妥协的后现代主义者”“更为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1]76-77,不同的后现代主义者有不同的主张。伊格尔顿同时也看到,各种后现代主义者有着共同特点,即激进冲动。在激进政治运动时期,激进冲动促使人们采取积极的政治行动,从而改变现实;但是在后现代主义时期,激进冲动只不过满足部分激进者的心理需要,并没能够促使人们采取有效的政治行动,也不能有效地改变现实,所以这种“激进冲动”从具有积极的改革作用转向了一种消极作用。
四、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批判的政治取向
伊格尔顿将后现代主义的兴起直接归因为左派政治运动的失败,同时他也认识到,“后现代主义文化在它短暂的存在中已经产出了涵盖艺术的全部广度的一大批丰富、大胆和令人振奋的作品,这决不能归因于一场政治失败”[1]35。毫无疑问,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是由经济、政治、艺术文化、哲学思想等多种原因合力作用的结果,左派政治运动的失利只是后现代主义兴起的一个诱因,并非全部因素。然而伊格尔顿将其他因素悬置不谈,只把政治因素凸显出来,他甘愿冒着“简化论”嫌疑而坚持这样做,是试图为他从文化政治批判视角切入后现代主义论争提供策略性服务。
伊格尔顿巧妙地将文化政治批判视角带入后现代主义论争后,接着便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观念展开严厉的批判,指出后现代主义虽然表面上具有强烈的激进色彩,但是其政治本质仍然是保守的。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政治激进姿态十分明显,后现代主义者在语言、身体、性等领域保持着反抗、不合作的姿态,他们调动多元性、差异性、非同一性、相对论、微观叙事等话语资源反对本质主义、总体性、目的论、普遍性、宏大叙事等,解构一切形而上事物和一切绝对价值。而资本主义制度在象征符号领域需要一些形而上事物、绝对价值、自我同一的主体作基础,比如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启蒙运动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社会契约论,鲁滨逊式的主体等。因此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在主观目的上与西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是对抗关系。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是共谋关系,没有光明的政治前途。因为后现代主义思想本身虽然是激进的,但是其思路有问题,它们只是从认识论上反抗资本主义制度,将资本主义制度与其思想基础看成等同之物,从而以为从思想层面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基础,便等于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这种做法其实是将政治实践领域的问题转移成思想领域的问题,以为在抽象的思想层面解决了问题,也就解决了具体生活中的政治问题,这其实是颠倒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命题。因此,伊格尔顿认为后现代主义只不过是犬儒主义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表现,是晚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无法为人们提供一种有希望的政治前途。
① 参考:柴焰《伊格尔顿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之路》,载于《理论学刊》2012年第11期;肖琼、龙昕《超越后现代:走向社会主义实践伦理学》,载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年第6期;阴志科《特里·伊格尔顿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思想的借鉴——兼论其“神学转向”是否发生》,载于《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2期。
伊格尔顿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后现代主义话语资源进行了清理,这使得他能穿过后现代主义幻象,堅持一种更具远大政治前途的立场:社会主义。后现代主义并没有解决那些经典性政治问题,如贫穷、阶级、劳动异化、人的自由解放、公正等,他们将那些问题放到日常议程之外,而去专心讨论性、语言、身体等领域;社会主义则从未间断对经典政治问题的探索。从某种意义上看,社会主义把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二者的精华结合到了一起。首先,社会主义努力消除匮乏,大大增加每个人追求幸福所必需的基本利益。更多的公共社会结构与个人利益的多元性并不对立。其次,社会主义使社群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得到解决:自由主义者反对社群主义,害怕每个人都信奉相同的事物,共享相同的好生活概念,使个人行动的自由和利益的多元性丧失殆尽;社群主义者反对自由主义,认为在自由主义社会中,男人和女人没有任何普遍规模上共享共同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们是没有根基的、分化的、被剥夺的。然而社会主义则一方面汲取了社群主义“关于意义和价值的集体决定,以及自我的文化和历史塑造的信念”[1]97,不过,这种“集体决定”并没有抹杀个人的特殊性,走向独裁政治,而是走向“自由主义者所赞许的异质性社会秩序”[1]97。而后现代主义不过是结合了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中最坏的方面: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把社群主义者的观点推向一种畸形的文化主义、道德相对主义;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又结合了自由主义最不受人欢迎的一些方面,把自由看作不受外在限制的自行其是的现代的消极自由,认为妨碍主体自由的东西是主体本身,于是努力使主体变得虚无缥缈,使主体服从于消费主义主体,使主体成为欲望存储器,结果也就没有什么主体来体验自由。
通过多个角度对比,伊格尔顿从理论上论证了社会主义优越于后现代主义,指出社会主义才是值得颂扬的事业,于是伊格尔顿主张回归社会主义宏大叙事。①
首先,需要恢复主体力量,坚持宏大叙事。后现代主义因为遭遇了一场重大激进政治运动的失败便自欺欺人地主张分裂的、去中心的主体,这种做法最大的危害就是消解了作为同一性的主体。分裂的、去中心的主体是无法采取重大政治行动的,只有同一性的主体才能采取重大政治行动。因此必须恢复主体的力量,回归宏大叙事,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无法否认的元叙事,如社会生产和再生产、阶级压迫与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斗争等,为革命的主体提供奋斗的目标和方向。其次,需要恢复社会主义实践维度。后现代主义错误之处就是丧失实践维度,将具体的政治对抗转入语言、性等领域的对抗,将革命政治问题转变成了语言、性别、话语问题,后现代主义也就无法在政治行动上真正推翻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回归社会主义宏大叙事就应该恢复实践的维度。
五、结语
伊格尔顿认为,纯理论只是一种神话,所有理论都具有政治性、意识形态性,如果不弄清后现代主义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性,无论是认同还是反对后现代主义,都是其思想的奴仆。这告诫我们,当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涌入中国时,我们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后现代主义的合法性和有用性进行审慎评价,不能盲目赞成或反对。可以说,伊格尔顿对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政治批判,为我们展示了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如何看透西方流行思潮背后的意识形态特性。然而,伊格尔顿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也存在一些值得反思的地方,比如:伊格尔顿批判时主观色彩极其强烈,有夸张之嫌;此外,伊格尔顿虽然与后现代主义针锋相对,提倡社会主义宏大叙事,但是囿于其学院知识分子的身份,难以在西方社会中将其理论付诸革命实践,最终难逃话语实践的命运。
参考文献:
[1] 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M].华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2] 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M].李安东,段怀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03.
[4] 姚介厚.“后现代”问题和后现代主义的哲学与文化[J].国外社会科学,2001(5): 10-17.
[5] 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M].谈瀛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6] 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M].马海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21.
[7]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26.
[8] 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M].杨文,任文科,郑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4:1.
[9] 杨生平.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主导[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9):153-154.
[10] 张亮.英国思想界新左派运动的兴起与终结[N].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07-21(8).
[11] 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438.
责任编辑:曹春华
Abstract: Postmodernism is opposite to classical Marxism. Terry Eagleton, a famous Marxist literary theorist and cultural critic,meets the challenge as a self-conscious Marxist and participates in postmodernism debate with a clear political stand. He attributes the beginning of postmodernism to the failure of radical political movements in the 1960s and reveals the conservative nature of postmodernism from its superficial and radical posture. That is, postmodernism is a kind of cynicism during the period of late Capitalism.Therefore, he argues for the socialism grand narrative. Terry Eagletons critique of postmodernism is worth of our deep consideration, as we must evaluate postmodernism comprehensively in the position of Marxism when we introduce in postmodernism.
Key words: Terry Eagleton; cultural political critical; postmodernism; socialism
grand narrative
——《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