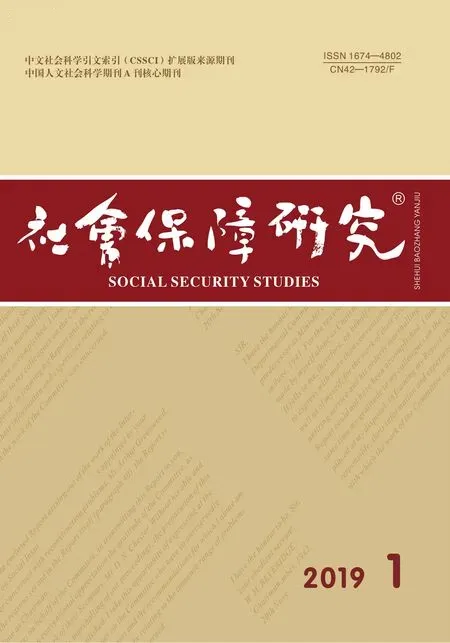多维贫困与精准脱贫
——以中部地区少数民族自治县Y县为例
朱丽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3)
一、研究背景
消除贫困是人类的共同目标。扶贫攻坚、精准扶贫,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是我国的重要战略布局。关于“精准扶贫”如何“精准”是一大难题。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使用收入贫困线来识别贫困,直到阿马蒂亚·森提出能力贫困,拓展了人们对贫困的认识,他认为贫困是对人们平等的获得教育、医疗等机会的剥夺,使人们无法改善生存状况。[1]此后,学者们的研究也从单维走向多维,开始关注研究多维贫困,并提出了不同的构造多维贫困指数的方法,例如信息理论的方法、[2]公理化方法、[3]克服贫困线界定中随意性的模糊集方法、[4]投入产出效率方法、[5]“双界线”方法即A-F法及主成分分析、多元对应分析等统计方法。[6][7]其中,“双界线法”使用得最为广泛,本文也将使用该方法测算多维贫困。另外,目前国内学者大部分使用公共数据库数据研究多维贫困,本文将采用实地调研数据来研究这一问题。
2015年7月—8月,笔者以“贫困户精准识别与多维贫困”为主题,实地调研了湖北国家级连片贫困地区的“一区四县”(神农架林区、竹山县、房县、长阳县和秭归县),并对其中的Y县的L镇和G镇部分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多维贫困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752份,测算了样本户的多维贫困指数。
2018年的7月,笔者以“建档立卡贫困户未脱贫原因”为主题,对Y县L镇和G镇未脱贫的137户样本户进行了实地回访。此次回访,旨在探究阻碍脱贫的原因、影响机理及其改进路径。
Y县集老、少、山、库、穷于一体。其境内有土家族、汉族、苗族、满族、蒙古族、侗族、壮族等23个民族,其中,土家族占全县总人口的65%。Y县所处地区是长江流域重要的生态屏障和全国水资源战略储备库,其山水气候资源的层次结构丰富,坐拥大山、大江、大湖(库)和大湿地,自然村落与原山、原水、原生态相互镶嵌。Y县生态守护压力巨大,但将自然资源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潜力巨大。多年来,由于天险闭塞,该县以城带乡能力弱,区域性贫困与群体性贫困并存。2014年,Y县建档立卡的数据显示该县的贫困发生率为28.03%,高于全省平均14.7%的贫困发生率。
针对Y县的实地调研及测算分析,旨在解剖一个多维贫困的微观样本。
二、贫困精准识别中的多维贫困
(一)贫困精准识别的流程
对贫困户的精准识别涉及目标群体界定、识别方法、识别准确性等问题。找准“穷人”知易行难。国际上通用的救助对象瞄准方法有家计调查、社区瞄准、地理位置瞄准等。
贫困的影响因素有两类。一类是宏观层面的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区域特征、政策制度等;另一类是微观层面的因素,包括家庭规模结构、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状况、市场参与程度等。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库兹涅茨的“倒U形”曲线等均是从宏观层面分析贫困问题。一般认为,经济增长有助于减少贫困人口,而减少赤贫人口则更多依靠收入分配。阿马蒂亚·森批判了仅仅从“经济收入”或“基本需要”角度定义贫困的局限性,他将个人禀赋、权利关系和能力方法纳入贫困测量范畴。[8]
在中国,贫困精准识别一般有“三步工作法”:
第一步,进村入户“算账”,一看房屋算家当,二看产业算后劲,三看劳力算收入,四看医教算支出,并据此打分,根据分数从最穷的人开始倒排,一个靠一个,敲定名单。
第二步,组织专班逐户逐人调查,下列家庭将被“剔除”出贫困户名单:家有公职人员的家庭、在外打工且收入可观的家庭、户籍不在本村或常年居住时间不足6个月的家庭,有轿车的家庭,企业主家庭,有“洋楼”或购买商品房的家庭,有子女赡养而单独生活的老人家庭等。
第三步,调查结果与建档立卡数据进行比对后进行公示,让群众“挑刺”,并且实行“户建卡、村造册、乡立簿、区归档”的“留痕”管理。
把账算准是“贫情大起底”的关键。在完成“三步工作法”后,全村农户被划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富裕户,人均可支配性收入是村平均水平的3倍及以上;第二类是一般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国家规定的贫困线标准以上、富裕户以下;第三类是扶贫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国家规定的贫困线以下,扶持后能够脱贫的家庭;第四类是特困户,因九种原因(因病、因学、因残、因灾、因智、因老、因弱、因环境、因劳力)需要政策兜底的家庭;第五类是“五保”“孤儿”等“特困户”。
(二)识别贫困的“精准性”遭遇挑战
一是家庭收入核算弹性大。补贴类的政策性收入易于核实,而务工的收入支出和其他隐性收入的信息难以获取;家庭收入与家庭财产有区别,财产占有状况对家庭福利水平的影响重大。
二是“分户拆户”钻政策“空子”。原本同桌吃饭的一家人,为了把其中两位老人搞成贫困户就分成两家。
三是贫困户与贫困边缘户之间的“悬崖效应”。评上贫困户的家庭因得到扶助而脱贫,贫困边缘户因细微的差距未评上贫困户而无法获得政策支持,并且很有可能因此滑入了贫困之列,从而产生“悬崖效应”。村民不会攀比绝对贫困户,但针对相对贫困户多有意见,甚至通过上访要挟干部。
四是奖勤罚懒机制未能体现。例如,同户分家的两兄弟,哥哥勤劳苦干,常年在外务工也盖不起一套房子,而生性懒惰的弟弟却因为当上了贫困户,近乎无偿地获得一套住房。[9]
五是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由于不符合评选贫困户的条件,其家中的留守老人和妇女不乐意参与识别活动。缺了农户的充分参与,村干部可能会很方便地优亲厚友,宗族和门派也容易裹挟投票与评议程序。
三、Y县的多维贫困情况
(一)数据来源
2015年,笔者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在Y县L镇和G镇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中,抽取了784个样本户进行了有关多维贫困原因的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752份,样本农户分布情况见表1。

表1样本农户的分布情况
(二)多维贫困测算
本文借鉴多维贫困指数(MPI)来构建多维贫困指标体系,采用A-F法进行多维贫困测算。
1.多维贫困指标体系的构建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2010年与英国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OPHI)合作开发的多维贫困指数(MPI)由3个维度的指标构成,包括:生活水平(做饭燃料、卫生设施、饮用水、通电、地板材质、资产)、教育(受教育年限、适龄儿童入学情况)、健康(营养、儿童死亡率)等。[10]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发展能力的维度,采用房屋结构、饮用水、通电情况、受教育年限、受教育机会、疾病与残疾、医疗保障、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参与合作组织等10个指标来衡量贫困户的多维贫困情况,同时采用等权重法(各维度等权重、维度内部指标等权重)对各个维度的重要性进行赋权,见表2。

表2多维贫困维度、指标、赋值及权重
说明:受教育机会指标选择18~20岁子女是因为考虑到读书晚与复读等实际情况;人均耕地面积指标中1.35亩为中国人均耕地面积。
2.测算方法
先测算每个维度的多维贫困再进行加总。其中有两条标准线,一是判断每个指标是否贫困的标准线,二是发生多维贫困的剥夺线,即k的取值。
(1)各维度取值
假设Mn,d是一个n×d维的矩阵,xij(xij∈Mn,d)表示第i个贫困户在维度j上的取值(i=1,2,3,…,n;j=1,2,3,…,d)。
(2)单一维度的贫困识别

(3)多维度贫困识别

(4)贫困加总
识别了多维贫困户之后,对各个维度进行加总,测算多维贫困指数M0。计算方法为:M0=H0×A0,其中H0为多维贫困发生率,A0表示平均剥夺份额。计算公式如下:
(1)
(2)
M0(k)=H0(k)×A0(k)
(3)

(5)贫困分解
多维贫困指数具备按照维度和指标进行分解的属性。本文中,各维度的分解等于加总后的贫困程度除以维度数。

(4)

维度j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为:
(5)

3.测算结果
根据剥夺维度k的不同取值,得到多维贫困发生率、剥夺份额、贫困指数等测算结果。(1)当k=0.1与k=0.2时,分别有97%和87%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陷入多维贫困,贫困剥夺份额相差不大,分别为0.35和0.37,仅扩大了0.02,多维贫困指数也十分接近,分别为0.34和0.32;(2)当k=0.3时,多维贫困情况发生了较大改变,多维贫困户急剧下降到378户,贫困发生率也下降到50%,剥夺份额上升到0.45,多维贫困指数下降到0.23;(3)当k=0.4时,多维贫困继续保持大幅度下降,贫困发生率下降到28%,剥夺份额上升至0.51,多维贫困指数下降到0.14;(4)当k=0.5时,多维贫困发生率已经下降到9%,多维贫困指数仅为0.06;(5)当k=0.8、0.9、1时,多维贫困已经不存在。具体结果见表3。
表3中的结果说明:k=0.1与k=0.2时的贫困指数均在0.3以上,这代表绝大多数家庭都存在个别指标上的贫困;k取值在0.5~0.7时,多维贫困户数量极少;k取值在0.8以后(包含0.8),已没有多维贫困户,这代表多维贫困程度特别深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因此,k=0.3和k=0.4时测算的多维贫困更具有观测价值,这也符合本文选择k=0.3和k=0.4这两个标准作为衡量收入贫困户多维贫困情况的初衷。

表3不同剥夺水平下的多维贫困发生情况
表4显示了各个维度及各项指标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具体如下:
(1)各维度的多维贫困贡献率。对多维贫困贡献率最高的是发展能力,其次是生活水平和健康情况,两者几乎持平,教育的贡献率最少,为12.77%。
(2)各指标的多维贫困贡献率。a.家庭成员患病或残疾的高居榜首,贡献率达到了21.53%,这意味着调查中超过1/5的家庭有患病和残疾的家庭成员,伴随而来的是劳动力的减少、医疗费用的增加及家庭负担加重。b.人均耕地面积排位第二,贡献率为17.75%。这是因为耕地是农村家庭维持生存和取得收入的基本硬件。c.是否参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排位第三,贡献率为17%。未能参加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可能是因为农户错过了参加的机会和未能正确估计参加合作组织的前景,而参加经济合作组织能够显著降低发生多维贫困的概率。d.房屋结构排位第四,贡献率为15.79%。房屋结构中的土坯房和土窑洞意味着生活条件恶劣。e.饮用水的贡献率达到了9.59%,其原因或与Y县多山的地理环境有关,也或与小区域的面源污染有关。f.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的贡献率为8.32%,教育机会的贡献率为4.45%,可见大部分贫困户希望子女获得更高学历。其余指标的贡献率均在3%以下,影响有限。

表4各个维度及各项指标的多维贫困贡献率单位:%
表5显示了各维度多维贫困发生率的情况。(1)生活水平维度。住房安全的家庭在k=0.3时,多维贫困发生率为8%,k=0.4时为4%,而家庭住房未达标的贫困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在k=0.3和k=0.4时分别为43%和24%。符合安全饮用水标准与饮用水未达标的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相差不大,在k=0.3和k=0.4时符合安全饮用水标准的家庭其多维贫困发生率为24%和12%,饮用水未达标的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为27%和16%。由此可见,房屋结构不安全和饮用水未达标的贫困户更容易发生多维贫困,这些贫困户大部分住在山上无力改建住房,只能收集雨水饮用。(2)教育维度。总体户主的文化程度越高,多维贫困发生率越低。户主文盲户可能因为样本量较小(仅为53户),而呈现出不符合这一规律的结果。户主为小学、初中、高中文化水平的家庭在k=0.3标准下多维贫困发生发生率分别为27%、16%、2%,k=0.4的标准下为16%、7%、1%。这说明,较高学历的户主家庭更不容易发生多维贫困,这可能与户主通常是一个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决策者有关,较高学历的户主更容易找到更好的工作,为家庭发展做出更好的决定。(3)健康维度。家庭成员均健康的家庭在k=0.3和k=0.4的标准下多维贫困发生率分别为14%、6%,明显低于家中有人患有慢性病、大病或残疾的家庭的36%和22%。这可能是因为家中有人患有慢性病、大病或残疾,其家庭除了需要支付医疗费用,还要面临丧失主要劳动力和长期照护的情况,因此更容易发生多维贫困。(4)发展能力维度。多维贫困发生率对比明显:在k=0.3和k=0.4时,参加农村合作组织的家庭的多维贫困发生率为12%和6%,未参加的家庭为39%和22%;家中人口均有劳动能力的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为5%和1%,家中有人丧失或无劳动能力为45%和27%;家中人有人外出打工的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为12%和4%,无人打工的为39%和24%。可知,发展能力强的贫困户发生多维贫困的概率更低,这可能意味着除了劳动力的数量,家庭自身对发展的判断也很重要。
表5各维度多维贫困发生率

维度指标k=0.3k=0.4维度指 标k=0.3k=0.4生活水平家中通电0.500.28安全饮用水0.240.12饮用水未达标0.270.16安全住房0.080.04住房未达标0.430.24教育户主文盲0.050.04户主小学0.270.16户主初中0.160.07户主高中0.020.01健康家中有人患慢性病、大病或残疾0.360.22家庭成员均健康0.140.06参加合作医疗0.500.28发展能力参加农村合作组织0.120.06未参加农村合作组织0.390.22家中有人丧失或无劳动能力0.450.27家中人口均有劳动能力0.050.01家中有人外出务工0.120.04家中无人外出打工0.390.24
说明:家中未通电、户主大学文化水平和未参加医疗保险指标所涉及的样本量极少,不具有观测性。
但在2018年回访时,Y县L镇和G镇大部分贫困户的饮用水都达到三级水质标准;住房安全问题也得到改善,建档立卡贫困危房户可以得到7500元~12000元的补助,居住环境恶劣的贫困户可自愿异地搬迁,按每人不高于25平方米的标准建房。因此,本文重点研究教育、健康、发展能力三个维度的多维贫困情况。

表6未脱贫原因 单位:%
四、针对“未脱贫原因”的回访
2015年抽取的752个样本户中,414户已经脱贫,137户尚未脱贫。农户排查过程中发现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在识别前存在硬伤,包括城镇购房、买车、参办企业、家中有财政供养人员等问题,在确认其“两不愁三保障”稳定解决后,根据要求予以适量清退处理。有201户在后来Y县实施的精准识别“回头看”中,因未通过相关数据“比对”,作为“硬伤户”被剔除贫困户之列。2018年7月,笔者对137户尚未脱贫的样本户进行了回访(见表6)。
在“未脱贫原因”的深度访谈中,笔者感受到精准扶贫3年来,领导重视程度、政策投入力度、责任落实硬度、合力攻坚强度均前所未有。已经脱贫的样本户,其脱贫原因各有差异;尚未脱贫的样本户,未脱贫原因的差异更大。
多维贫困就像病毒一样,生成机理颇为复杂,欲斩断穷根、抽出穷筋,需要进一步细化多维贫困的判别指征。对“一看房、二看粮、三看劳动力、四看读书郎、五看有无重病躺在床”中的每一项,都要递进分解,且审视其有无出现转机的可能。例如,因病致贫与教育致贫的不同之处是后者有盼头,孩子毕业了就有转机。以下是对回访所得一手资料的归纳梳理,从中可以发现扶贫过程存在的问题。
(一)普惠型脱贫政策的边际效果下降
脱贫效果指标越过某一个临界点之后有停滞不前的倾向。脱贫工作是越到中后期,边际难度越大:易于脱贫的人群,政策略有帮扶,早已脱贫;脱贫有一定难度的,历经3年的帮扶也基本脱贫了;剩下未脱贫的,往往是绝对贫困户,其家底薄,能力弱,往往缺乏劳力、技术、资金、“两信”(信心和信息),而观念改变和技能培训都需要很长一段过程。绝对贫困户在高强度帮扶之下脱贫有望,但是,只要稍微遇上点事,返贫概率就很大。
(二)产业扶贫“怎么扶”遭遇多种不确定性
“扶持谁”和“谁来扶”是村庄内部的程序性决策,再难也有抓手,而“怎么扶”则是市场风险决策。虽然贫困户享有政策特惠的“滴灌”,但是政府不可能为贫困户划定“非贫莫入”的垄断产业。因而,产业扶贫应更好地运用市场思维,尊重市场规律,并鼓励致富能人的参与其中。目前产业扶贫面临以下几方面的困境。
一是贫困地区的产业链短或不完整。对产业扶贫而言,能够盈利且看得到“现金流”是硬道理,自然资源禀赋再有优势,倘若商业模式、项目甄别、物流配送、基础设施、适用人才等要素组合跟不上,优势就无法发挥出来,且钱和时间都是耗不起的。以农村的电商物流为例,“互联网+”运用的前提是突破需求规模的临界点。线上没有节点,可以从零到无穷大,但一到线下就变回实体,倘若没有足够的规模,贫困地区的物流配送成本会高得不可承受。
二是农产品遭遇价格“天花板”和成本“地板”的双向挤压。游资炒作的“猪周期”和“蛋周期”等,使得商业种养殖业不像做实业而像炒股票。“种不种”“何时种”“卖不卖”“何时卖”都变成了与周期对抗的过程。契合了周期就赚一把,反之,一旦倒下难以爬起来。
三是重大自然灾害面前的脆弱性。例如,2016年7月初,Y县大面积洪灾使一些贫困户颗粒无收、猪场淹没、网箱冲垮、鱼儿跑光,其资产“归零”。
四是“外源发展”与“内源发展”的矛盾。农民拥有土地和劳动力,但是缺资金、缺技术、缺市场销售渠道、缺社会资源导致其决策能力涣散。而外来资本注入的不仅有资金、技术、市场销路、社会资源,更重要的还有商业眼光、资源集成能力和决策能力。外来资本下乡存在的问题是资本逐利可能造成“非农化”经营、农地流转风险与收益不均衡、外来资本与内源发展起冲突等。
(三)空心村扶贫项目“筹劳”难
贫困村往往就是空心村。一些到村的扶贫项目,“筹劳”比“筹资”更难。看起来万事俱备的事,有可能就因欠一点“人气”的“东风”而难以做成。例如,在产业到户的扶持项目中,政府补贴了购买种苗的钱,也实行了保底的收购措施,并将这些写进了“明白卡”使人人知晓。但是,有些贫困户的劳动力外出打工,土地撂荒多年,机械复垦不仅需要高昂的费用,并且因为缺了劳动力照应,即使“肉吃到嘴里也咽不下去”。
(四)易地搬迁脱贫的利益保障缺乏长远的眼光
易地搬迁贫困村一般处于“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的生态脆弱地区或地质灾害区。贫困户搬迁后的就医、就学和就业前景一般优于原住地,但也存在阻碍脱贫的因素:一是“易地”难以界定。农耕活动半径一般在步行30分钟之内,搬近了无意义,搬远了照应不了原有的耕地、水面和山林。二是“资本下乡代替了老乡,却没有带动老乡”。有些地方把搬迁户的耕地集中流转给一些大户、专业合作社或龙头企业,搬迁户除了得到一笔土地流转费之外还能打一份零工。老宅子则由开发方从贫困户手中收购或是通过本村村民互相买卖调剂等。三是原来的“生计”手段可能因搬迁而断裂,新的还得从头来。不同个体的“可培训性”和“可就业性”的差别很大。倘若搬迁后不能增收就稳不住,有可能加深贫困或造成“返流”。
(五)家有重特大疾病的贫困户脱贫难度高
目前,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商业保险公司承办的大病保险都基本实现了“全覆盖”。针对住院费用,前者先报销一定比例,后者再实施二次报销,合计报销比例达90%。因此,许多原本应该住院治疗但是因无钱而放弃治疗的病人得以住院诊治,这种情况以老年患病者为甚。[注]笔者此前调研中,询问过多位贫困户,得知家庭成员患病的诊治顺序:儿童优先,劳动力其次,老人排在最后。然而,有些特别贫困的家庭无力承担自付医疗费用。“恶质性”疾病、癌症、瘫痪、重度残疾和精神病等,现代医学无能为力根治,旷日持久的“消耗”拖垮全家人。除了医疗费用上的消耗,重特大疾病的患者通常都丧失了劳动能力,需要有专人照护,这意味着一个贫困家庭丧失了至少两个劳动力。数位受访者提及,直到重病在床的家人“灯油耗尽”去世了,家庭才逐步脱贫。
(六)非义务教育支出影响脱贫进程
在Y县,“砸锅卖铁”供孩子读书的传统深植民间,还有“英子姐姐”等助学启智的知名公益品牌。“不让一个学生因贫困而失学”的“靶向”扶贫政策,指向小学和初中的义务教育。并且农村居民也逐渐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投资,这有利于斩断贫困遗传链。然而,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支出和各种陪读支出阻碍了脱贫。
一是早教费用增加。村民越来越重视“早教”,农民工外出长了见识,更倾向于将子女送入镇上或县城的幼儿园就读。幼儿园不属于义务教育,学费开支不菲,母亲陪读的租房和交通费用是一大笔投入,并间接导致家庭减少一个劳动力。
二是义务教育阶段陪读的机会成本较高,学校距家过远。小学教育属于义务教育,虽然不缴纳学杂费,但是,陪读开支类同于幼儿园。不得不陪读的原因是“一少”“一多”和“一高”(学龄儿童减少、打工者随迁子女增多、家长对教学质量的要求提高),原本的“村村办小学”演变为“麻雀学校” 的大量出现,“撤点并校”在所难免。有条件“陪读”的家庭吃力地跟上了“队伍”,有些“走不出去”的留守儿童则“掉队”了,而贫困代际传递的重点对象正是后者。
三是高中及高等教育投入的增加。高中和高等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名校的录取是按分数“说话”。倘若“读书郎”考得上“一本”“二本”,学费相对较低且就业前景较好,毕业后会显著缓解家庭贫困;如果就读于“三本”高校,学费高出一大截,毕业后的收入可能还赶不上农民工。对此,农村家庭对高中及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提升,教育投入明显增加。
(七)新增贫困人口削减脱贫效果
一是能够在打工地领取退休金的高龄农民工(60岁及以上)数量微乎其微,绝大部分在年老体衰时返乡养老。其中很多是积劳成疾,其养老医疗由户籍所在地政府兜底买单。这是劳动力流入地对流出地的社保负担转嫁。
二是职业病患者和因工致残者增加。因病(残)致贫人口的占比高并非完全是“疾病谱”演化所致。其中,职业病患者增加,缘于外出打工时用工双方的“无知无畏”和风险敞口。一些用工单位对有毒有害岗位不提供或不使用防护设施用具;还有一些用工企业利用职业病缓发特征,通过“试用期”或“短期合同”方式,将农民工辞退在职业病发病之前。另外,因工致残者以建筑工地的打工者居多。2015年国家强制建筑施工方为农民工缴纳工伤保险费,否则不发施工许可证。但是在此之前的因工致残者,事发时仅拿了一点赔偿金,倘若项目施工方是“草台班子”,项目完工后当时的包工头难以被找到,户籍所在地政府就成为其养老与医疗保障的最终买单者。
三是打工地削减产能、机器换人、企业外迁、老板跑路等,使农民工失业返贫的概率增加。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人打工,全家脱贫”遭遇不确定性。
(八)盖房和结婚导致脱贫与返贫之间的悖论
在农村,盖房和结婚本是“大喜”之事,却对脱贫产生了“逆向”冲击,甚至成为一种悖论。
住房条件差是贫困的特征,但是,盖房又会致贫或返贫。第一代农民工打工赚钱的目标是回家乡盖一栋房子。盖房耗尽家底,甚至两代人为此出去打工。一家人不是在打工挣钱准备建房子,就是在挣钱还建房债务,等到债务还清,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后代退不回农村了,必须挣钱在城里买更贵的房子。
新中国成立后提倡“结婚不讲财”。然而,农村实施30余年的“一孩半”政策使得“男多女少”,贫困山区的男性成了“婚姻挤压”的最后一级,其彩礼费用连续上涨。谈婚论嫁的“标配”是男方有住房和8万元左右的“彩礼”,有时女方还会要求男方在县城购房,以备将来“陪读”或就业之需。贫困户有一个儿子结婚往往就导致父母“一夜白头”“家庭一夜返贫”。
(九)懒人难脱贫与奖勤罚懒机制有矛盾
“懒人”是指身体健康、四肢健全,自身没有脱贫动力,抱有侥幸心理,指望政府兜底的贫困户。“懒人”的占比不高,但却难以脱贫。对这些人给予帮扶救助,是对扶贫正义性的挑战,也绝非精准扶贫政策的本意。对于这些“扶不起”的“懒人”,有些乡村干部指望将其搞成“低保兜底户”,省力省事。但脱贫攻坚“收工算账”时,倘若养了一些四肢健全、没病没灾,却“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还到处炫耀“干部怕狠人”“不拿白不拿”的人,会颠覆了扶贫政策初衷,搅乱社会再分配机理,破坏勤劳致富的淳朴民风。因此除了宣传教育引导,还必须出台相应的奖惩措施,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
五、政策建议
脱贫攻坚是一场历史大考。贫困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空心化、基本公共服务短缺、基层政权“微循环”不畅、民风粗俗、信息闭塞、技术停滞等问题。拔掉穷根需仰仗长效机制,眼下应秉持“应急谋远、标本兼治”的原则循序推进扶贫工作。
(一)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
针对小农户发展权利不充分的问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从雪中送炭的实事做起,以服务半径、服务人口为基本依据,按照覆盖城乡、区域均衡、全民共享的要求,进行制度设计、系统规划和整体推进。有关财政资金运用要突出贫困片区、突出基本标准、突出对困难群体的兜底。例如,因病(残)致贫减损了国民健康资本,带来自身贫困、家庭贫困和代际贫困。健康投资是一个“慢变量”,需要从国家“医改”方向和职业安全体制上加以审视,不仅要有治疗,更要有预防和保健,而后者,与工作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饮食构成的关系极大。
(二)以“小农户振兴”为重要抓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精准脱贫的“下一站”应该就是乡村振兴了。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管长远、管全面的大战略。“小农户振兴”是其题中应有之意。目前,我国仍有2.6亿农户,6亿多人生活在农村,其中2.3亿户是承包农户,也就是所谓的小农户。[12]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小农户之间的集结与合作,家庭农场是小农户进阶到专业化阶段之后的经营形态。“小农户占主导”是“三农”问题的基本面。乡村振兴战略平台承载着产业、就业、教育、健康、搬迁等功能,可将各种政策资源归拢到这个平台上,针对当地资源结构、商业环境特征等深度挖掘,找准“小农户振兴”目标定位。解决方案应是“一揽子”而非“碎片化”。贫困地区的产业扶贫尤其要注重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的配套。宏观层面的政策指向要稳固脱贫,使脱贫户不再返贫,防止贫困边缘户滑入贫困,还要扭转“涉农劳动不能脱贫、涉农投资难有回报、涉农财政不能增收”的格局。
(三)大力支持农民的组织化
乡村振兴战略涵盖的“五个振兴”中包括了“组织振兴”。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贫困户,发展动力和抗风险能力显著高于散兵游勇的贫困户。政府要大力支持农民的组织化,统筹协调农民与外来资本的矛盾。目前,应重点发展“社区化”“联社化”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区化”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立足本乡本土,组织成本、交易成本和监督成本均较低。多个合作社聚合成为合作联社,其发展前景更好。其应通过适度规模化种植和集约经营做大“蛋糕”,优化治理结构,在“抱团”闯市场过程中使议价能力变更更强,进而逐步成长为影响农产品价格的本土力量,以更强的实力与外来资本、农业技术推广组织、行业协会“联姻”。
(四)提升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斩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恶性遗传链
贫困本质上是“人”的问题。贫困父母会将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传递给后代,就像“割韭菜”一样,老一茬的贫困被解决掉了,新一茬的贫困又被复制出来。“解锁”贫困代际传递恶性遗传链的封闭之“环”,需要对 “贫”和“困”分类施治。“贫”指物质层面的“一穷二白”;“困”则是指处境的“逼仄”。一个人被“困住了”,意味着没有走出困境的机会和能力了,如缺少劳动技能、缺少信息获取能力和渠道、观念意识落后、不愿意或者不懂参与和沟通,以及由此带来的恐惧感和自卑感等。这些都不是用钱就能够解决的事。
走出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是提升人力资本,而教育培训、健康维护和非农就业是三条最重要的路径。其中,前两条耗资大、见效慢、投资主体与受益主体分离,需要被持久地关注,第三条受制于外部环境与自身努力的相互作用程度。阻止贫困代际传递是个宏大的话题。应在制度层面给予贫困户以均等的公民权利和发展机会,从长效机制角度来看,本文有两个建议。
一是教育扶贫向学前教育扩展。十九大报告将民生聚焦的光圈进一步加大,提出了“幼有所育”。儿童3~6岁时的大脑处于最可塑造的状态,投资回报率最高。政府不能够也不应该阻止中产阶层或富人投资自己的子女,政府要做的是采取措施来帮助穷人的孩子。乡村幼儿园建设有成功案例可循。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的团队合作,探索在贫困山区普及学前教育。主要做法是“送教到村、就近入园”“注重培训、保证质量”“营养和教育并重”等。通过帮助乡村幼儿园改善教师培养、儿童健康、早期教育和硬件设施,实现乡村幼儿园的高质量、低成本和广覆盖。
二是建立企业、高校、社会各界协作的职业教育体系。企业可通过建立“学徒”岗位,同步实行学生早期分流机制,与学生双向选择,为全社会培养精益“工匠”。另外,职业教育培训应去行政化,管办分离,还应通过“首岗适应”与“多岗迁移”,使接受教育的学生形成终身职业技能。
(五)“扶贫”与“扶志”的契合
“小康路上一个不能少”。脱贫攻坚“收工”之际,对于收入达不到脱贫标准的深度贫困户,国家将对贫困线和低保线实施“两线合一”兜底政策,前提是内外动力聚合,贫困户先要“立志”脱贫,方能够提升脱贫能力。[13]“两线合一”兜底政策的实施,依然要建立在家庭经济状况核查基础上,有标准,有程序。另外,对“懒人”实施社会教化、亲情感化、组织劝化和法治引导的“三化一治”综合治理。
(六)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
政府的有形之手要在制定规划和标准、实施培训和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平台搭建、市场秩序维护等方面提供赋能支持。在市场有效的领域,政府要减少不必要的干预,放手让市场主体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