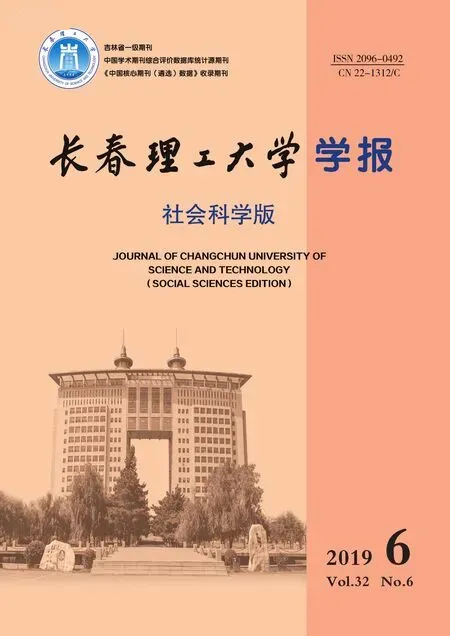道格拉斯·罗宾逊翻译思想中国化带来的启示
程福干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200444;安徽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安徽凤阳,233100)
一、引言
道格拉斯·罗宾逊是一位享誉世界的美国翻译理论家,著有《译者登场》《翻译与禁忌》《翻译与帝国》《译员培训》《谁翻译?:超越理性的翻译主体性》《施事性语言学》《疏远与文学身体学》等,对翻译身体学、翻译对话性、译者主体性、翻译与摇摆等问题有深刻见解。他于2010年移居香港,先后执教于香港岭南大学、香港浸会大学。伫立于香港这片中西文化荟萃之地,罗宾逊对中华儒道哲学进行了深入思考,于2015年出版的《翻译之道》将老子、孟子、子思等华夏先哲与皮尔斯、索绪尔、布迪厄的思想融会贯通。可以明显看出,罗宾逊翻译思想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我们从罗宾逊翻译思想中国化中得到很多启示,对中国翻译理论话语体系建设有着促进作用。
二、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的翻译之道
罗宾逊早期的翻译理论主要植根于西方文化土壤,依托西方理论话语,而近作《翻译之道》中阐述的几种“道”吸收了中国儒道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试析之。
(一)不可言说之道
道可道,非常道。
—《道德经》第一章
罗宾逊引述Martha P.Y.Cheung(张佩瑶)的观点认为,无处不在的“道”是万事万物的本原和规律,若隐若现,不可言说。任何对其阐释或命名的做法都是企图对一个不能确定的意义加以确定,意义和意义的表达之间永远存在断层[1]5。翻译同样以“道”的方式存在,所有翻译行为、翻译产品、翻译决策都归结于“道”。基于此,罗宾逊推断道,“能够形成文本的文本不是真正的文本;能够被翻译的源文本不是真正的源文本;能够被付诸实施的翻译行为不是真正的翻译行为;能够被决定的翻译决策不是真正的翻译决策。”[1]7那么何谓真正的文本、源文本、翻译行为、翻译决策?如此一来不免陷入神秘玄学主义,于是罗不再将“道”看作“事物”—Way,而倾向于赞同Roger T.Ames(安乐哲)和David L.Hall(郝大维)的理解,把“道”视为一种活动或过程—way-making,是集体化习惯在社会中的运作。翻译只有在活动过程中才体现各种形式的“道”[1,2]。
(二)直觉推理之道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道德经》第三十七章
芬兰翻译研究学者Heinonen(黑诺伦)在博士论文中指责罗宾逊《译员培训》一书中赋予了译者太多能动的角色,如语言学习者、编辑、作者、研究者等,并声言只需“让语言符号翻译自己”,译者任其发生,无需介入[1,3]。罗宾逊认为黑诺伦明显体现出“无为”的道家思想,不过却曲解了罗的本意。罗构建了“经验之轮”,将“直觉推理—归纳推理—演绎推理”三角构型内嵌对应于“本能—经验—习惯”三角构型之中,认为习惯是本能通过经验形成的,继而推动译者快速而完美地处理文本,并在有意识的文本分析和近乎无意识的文本完美处理之间“穿梭”[1]17-18。虽然黑诺伦和罗宾逊均将“直觉推理/本能”看作第一性,但黑诺伦遵照的却是“直觉推理/本能—演绎推理/习惯—归纳推理/经验”路线,将属于第二性的经验置于末尾。然而,一个娴熟的职业译者正是通过从新手阶段开始的大量操练才渐入佳境,经验不容忽视,“无为”不是不作为,而是“习惯性作为”[1]26。直觉推理之道是建立在“经验/有为”基础上的无为之道。
(三)移情之道
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
—《孟子·尽心上》
孟子倡导的“四端”(仁、义、礼、智)在移情上分别表现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恭敬之心、是非之心[1]40。“仁”作为一种社会情感生态要求译者成为“仁人”,在对别人的情感进行接收和再发送时,尽量在自己的体内模仿出同样的情感,实现“跨情感”(transfeeling)沟通。这种跨情感沟通能力可称作“识别”(identification),它是一种移情投射,或称“情感变认知”(affective-becoming-cognitive)投射。这种投射不是单向的,而是在一个群体内部循环或呈网状分布[1]68-69。罗宾逊举了亲身经历的一个翻译事件来解说“仁”。他多年前受邀将X教授的会议讲稿从芬兰语译成英语,却发现源文本语法不连贯、文体无重心、主次不分明,于是设身处地从听众的角度对源文本进行大幅改动,结果博得X教授的赞赏和听众的欢迎[1]66-67。“义”要求译者顺应他者的群体规范,入乡随俗,便宜行事。“仁义”不是私人拥有的道德,而是集体存在的社会生态现象,罗宾逊称其为“群体向善”(ecosis)。“礼”是孔孟儒学链条的重要一环,所谓“发乎情止乎礼”。然而“礼”不只是对规则的机械服从,在特定情形下要权衡利弊而灵活变通。这就需要“聪明”之“智”,但“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译者需要融入不同的情境中。罗宾逊探讨移情之道时主要借鉴的是儒家思想,然而儒道不分家,儒和道本属于“同体”,互补共生[4]。也可以说,道家思想对应于天道,儒家思想对应于人道[1]52。人道包蕴于天道之内。
(四)习惯/惯习之道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论语·阳货》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礼记·中庸》
罗宾逊论述了个人习惯和集体惯习在翻译中的运作。不同译者的个人习性千差万别,但一致遵循着稳定的集体惯习,而惯习并不强行监管。个人在集体中会受到某种“压力”的潜移默化,这种赋予译者“身体自动主义”的“压力”通过“动觉→情感→意动→认知”的过程转化为习惯[1]144。罗宾逊创造了“群体认同”(icosis)和“群体向善”(ecosis)这两个词来描述惯习。集体意志渗透进团体规范之后,每一个经验事件遵循团体规范而“降临”到团体中的单个成员身上。没有加以组织的经验,或者说“偶然性”经验被罗宾逊冠名为“个体身体的”(idiosomatic)经验,具有特质性和非规范性。而团体动力学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将个体躯体的经验降到最低,尽量使经验“意识形态身体化”(ideosomatization),在团体成员之间达成意识形态共识。这种使得看法成为真理、观点成为现实的经验“身体化”过程被称为“群体认同”[1]96。“群体向善”是一个团体趋于善的过程,也是抽象的善念趋于团体化的过程。代表“善”的规范在群组中进行社会情感辐射,使得每个成员都能逐渐感受到善恶好坏之分,最终达成一种圆满状态[1]137。在所谓的自动翻译模式下,翻译处于自动驾驶状态(autopilot)。这种“无为”翻译背后蕴涵的“道”即为:在社会生态中群体认同和群体向善烛照之下的集体翻译惯习和受辖于集体惯习的个人翻译习惯[2]。
三、儒道哲学的本质特征
罗宾逊以倡导翻译身体学(或身体翻译学、身心翻译学)著称,而近来转而崇尚中华儒道哲学。其实翻译身体学和儒道哲学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儒道哲学的本质特征之一即为“体知”属性,另一个本质特征是“境界”旨归。分述如下:
(一)儒道哲学的“体知”属性
罗宾逊的翻译身体学并非是对“心智”的排斥,而是想引发人们对翻译学人文性的关注,聚焦译者翻译时的身心感受,包括直觉和身体反应等[5]。这种观点恰在中国人身上得到更有力的说明。汉学家吴光明指出,与西方的抽象性思维不同,中国人持有一种具体性的“身体思维”[6]。陈立胜认为,身体已经成为一种思维范式[7]。对于翻译来说,“情感沟通或直觉交流”位于“意义阐发”之前[8]。
这种对“身体”的强调深合中国传统哲学意蕴。当今以张再林为代表的一大批哲学研究者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可以称为身体哲学。诚然如此,《尚书》的“慎厥身”、《周易》的“近取诸身”、《诗经》的“明哲保身”、《论语》的“吾日三省吾身”、《孟子》的“反身而诚”、《礼记》的“敬身为大”、《大学》的“修身”等俯拾皆是的表述,均是在为中国古代“身体哲学”正名[9]4-5。从孟子“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情怀可以看出,身与道已休戚与共;从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昭告中看出,壮志难酬的世人可以反求己身,身体始终是不可撼动的立命之所。儒道哲学以“体知”而非“认知”为鲜明属性,这与西方的具身认知哲学思潮有某种相似性。
“体知”分为三个基本特征:直觉性、关系性、践履性[9]170-171。首先,直觉性是“体知”的首要特征。“直觉”是对事物本质的直接把握,与作为一种“本质直觉”的“洞悟”或“洞观”有关[9]170-171。其次,关系性突显的是身体哲学中具身化的普遍联系,即“感通”,类似西方哲学中的“共通感”和“同情”[9]181-182。中国文化对“体悟”、“移情”、“类比联想”以及“诗性思维”的强调随处可见。再次,践履性即为“致良知”之“致”的功夫,体现“知行合一”和“身体力行”。身体行为既是语用学行为,也是族类学行为[9]187-194。“万物一体”必须要通过“致良知”上升到境界层面[10]。罗宾逊所说的译者通过群体认同和群体向善形成翻译惯习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种身体力行的“致良知”过程。反观当下翻译市场,不少译者唯利是图,不以译文的质量为虑,粗制滥造拙劣译文,分明在与“致良知”背道而驰。
(二)儒道哲学的“境界”旨归
与长于思辨和分析的西方哲学相比,中华传统哲学没有西方哲学中关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的严格划分,在本质上属于境界说[11]。近代王国维推动境界说从客观性的审美转向主体性的“内审美”,之后不少学者如宗白华、朱光潜、冯友兰、牟宗三等宏论迭出。那么何谓境界?境界是“一种存在状态或存在方式。这种状态既是心灵的自我超越,也是心灵的自我实现”[12]413。汤一介指出,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中国传统哲学以“内在超越”为特征,迥异于以“外在超越”为特征的西方哲学。如果说孔孟通过升华理想而超越自我,那么老庄则通过净化精神来实现内在超越[13]。
“境界”论运用在翻译研究上有独到之处。国内学者陈大亮发现,如果将金岳霖知识论的逻辑分析法运用于文学翻译,势必捉襟见肘。金岳霖注重语言的工具性,侧重概念、意念和命题等思议的内容[14]42。译意与语言的工具性相联系,而译味与语言的社会性相联系[14]87。从功能语言学来看,译意只局限于传达概念意义,而译味能够传达出人际意义[15]。概念、意念和命题只能是译意的依据,属于知识论的辖域,通向形而下的“理”,是知识经验能够到达的名言世界,因而通过命题和概念表述使得译意成为可能。然而译味依据的是想象、情感与意象,通向形而上的“道”,是知识经验不能到达的非名言世界,因此很难用命题来表述[14]48。译味尚且不能,遑论译境?故而知识论行不通。那么必须打破译意和译味之间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的关系,从知识论转向境界论,就能够通过层级超越机制来达成译意、译味乃至译境的和谐共存。如陈大亮所言,“境界论追求翻译的审美境界。心灵的境界越高,译出的作品就越好,有境界的翻译才有品味,才有名句。”[14]57
可以发现,儒道哲学的“体知”属性和“境界”旨归分别从“身”和“心”两方面来导引翻译研究。翻译中意味和意境的境界属于审美的直觉体验领域[14]48,而直觉感悟法是提高翻译境界的根本途径[14]59。返观《翻译之道》一书,罗宾逊虽然反对黑诺伦脱离经验的激进式直观推理之道,但无疑对直观感悟很是推崇。在译味和译境方面,陈大亮认为“审美共通感”证明意味和意境具有普遍的可传达性,并总结出意象思维的形象性、直觉性、移情性特征以及原象思维的想象性、整体性、妙悟性特征。两位中西学者对儒道哲学的应用不谋而合,均反映出一种以“儒道境界”为取向的翻译观。
冯友兰[16]将境界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结合这一分类法,可以运用身体哲学话语,对儒道境界翻译观进行初步概括:第一,重视直觉感悟和移情作用,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能近取譬推己及人,“体”悟翻译之道;第二,译者应竭诚奉献,淡泊身外之物,不能因追逐金钱利益而抛却翻译行业的服务意识和精品意识;第三,“仁义礼智”应成为普遍奉行的道德观,在译界收到“群体认同”和“群体向善”之效;第四,译者应秉承“知行合一”和“身体力行”原则,“神”游翻译之境,最终抵达“天人合一”境界。
四、中国翻译理论话语体系建设反思
(一)儒道境界翻译观能对碎片化的翻译研究进行一次集结
翻译学具有跨学科性,能融合语言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生态学等各学科视角。各种学说如多元系统论、操纵学派、规范原则、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轮番登场,虽然开阔了研究视野,然而造成“碎片化”倾向[17,18],以至于术语混乱、学派林立、研究者各自为战、研究问题无限泛化、学科游离不定。[17,19,20]针对这一困境,切斯特曼提出“因果观念”这一纽带理念,以求将翻译学近几十年来的发展成果进行有机融合[17]37-38。斯奈尔·霍恩比[21]以语篇体裁为主体视角提出翻译研究综合模式,尽管该模式包含社会、文化、交际和语言层面,但只是指出了各个流派的研究之间的联系,很难真正使各个研究途径综合在一起[22]。曼迪同样呼吁道,为了避免翻译学被其他学科吞没,研究者特别要加强在具体话题方面的合作研究,力戒单兵出击[19]。翻译理论研究的碎片化现象在国外如此,在国内尤甚。有论者基于对中国译学界顶级期刊《中国翻译》的实证考察指出,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研究存在着研究领域不够细化、缺乏团队合作精神、争鸣商榷不足、欠缺国际传播机制等问题[23]。其中团队合作意识的缺失尤为明显。在翻译理论的浩瀚江洋里,众多研究者“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然独木舟终究难以经受大风大浪的考验,应该共同乘坐一艘或几艘“诺亚方舟”联合行动,才有望驶出漩涡,开辟新航路。团队合作需要共同的指导思想,作为“主心骨”。而中华儒道哲学直指人生终极关怀问题,为人类提供最有价值的智慧。作为“天人合一”的境界,“道”的境界也是真理境界、道德境界和审美境界[12]204。儒道境界翻译观将引领翻译研究达成共识,增进翻译圈的凝聚力。
(二)儒道境界翻译观能助力中国翻译理论学术话语体系建设
世界主要国家向外部传播自己的文化和观念的基本经验表现为:语言是基础,文化是外围,学术是核心。中国要掌握学术和思想的话语权,就必须使中国人文社科研究在世界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24]。从横向看,世界范围内的翻译理论在过去很长时间内秉承文艺复兴以降西方意识形态的“欧洲中心主义”传统,“以输入欧洲文化为主,成为消费和吸收欧洲思想观念的关键工具”[25]。后来,美洲大陆主义渐趋翻译话语圈的中心,而这些都不是平衡发展的翻译话语生态,翻译研究应实现“国际转向”[26]。中国本土译论建设长期以来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套用国外理论或挪用术语概念等现象屡见不鲜[27]。国人对中国译论自己的特色资源挖掘不够,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关注度欠缺。事实上,中西译论在语言类型、思维类型和文化类型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28]。习近平主席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29]中国翻译理论建设在过去三四十年中取得长足进展,然而真正扎根本土文化土壤的学说却也不多,以中华传统儒道文化作为立论根基的创见乏善可陈。大易翻译学论出于雄踞六经之首的《周易》,对纷繁复杂的翻译现象作出太极建构,在传播学术话语的同时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如果放眼光辉灿烂的中华儒道文化,就会发现除了易学思想之外,足资借鉴的理论资源无比丰厚。穷究“天道”的道家思想和彻察“人道”的儒家思想相映生辉,正是历经几千年盛行不衰的中华文明生存发展之“道”。博大精深的儒道典籍,正可以给翻译研究者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
儒道境界翻译观的树立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普及相辅相成。我们欣喜地看到,2017年修订的高考考试大纲“增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考核内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表示“十三五”期间会适度增加“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领域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数量”。传统文化在政策推动下势必更加深入人心,儒道境界翻译观一定能深入人心。
作为一位国外翻译理论家,罗宾逊能从儒道文化中获取灵感来创立学说,这给国内学者带来若干启示。国内学者要增强文化自信,相信中国的儒道哲学是一座文化宝库。中华儒道哲学具有“体知”属性和“境界”旨归,可以分别从“身”和“心”两方面导引翻译研究。译者应树立儒道境界翻译观,“体”悟翻译之道,“神”游翻译之境。当然,对本土话语资源的倚重并不意味着对国外理论的排斥,而是在坚守自我这一个背景下的中西交融,是一种“本位观照,外位参照”。只有“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才能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笔者真诚希望中华儒道文化在世界各地能够蔚然成风,“人类命运共同体”赫然在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