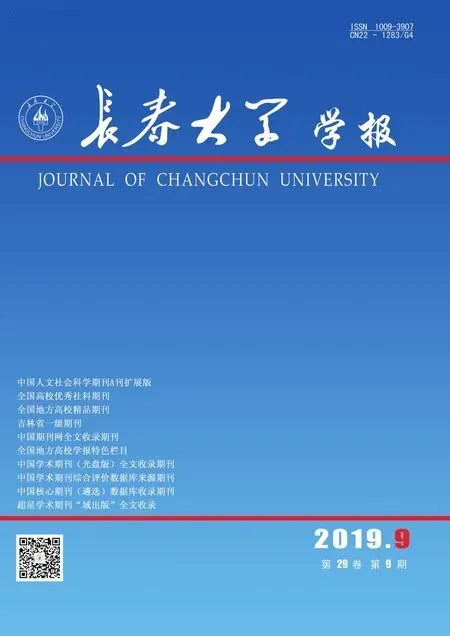中国文化情结的消解与重构
——《金锁记》与《北地胭脂》的对比研究
於 涵,李新国
(安徽工程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张爱玲在1955年后于美国进行了大量中英文双语间的自译改写活动,试图打入英语写作世界。张爱玲对自己早年中文成名作《金锁记》寄予厚望,亲自执笔将其翻译成英文,期待借此叩开英文写作世界的大门。该小说被傅雷誉为“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2]。张爱玲将自己的中文代表作品《金锁记》两改两译,形成包括原著在内的写译本PinkTears(以下称《粉泪》)、英文直译本(TheGoldenCangue)、英文改译本TheRougeoftheNorth(以下称《北地胭脂》)和中文回译本《怨女》五个文本,构成了独特的自译现象。本文选取《金锁记》原著及英文改译本《北地胭脂》为研究对象,分析原著在译本中转化重构的过程,揭示张爱玲在游走于中西文化之间积极打入英语世界所做出的努力。
1 《金锁记》与《北地胭脂》
《金锁记》中“以实写虚”的逆向意象技巧被广泛运用,丰富的比喻发展成为大量琐碎奇绝杂色质感的物化意象,创造出奇特的苍凉感[3]。大量蕴含中国文化的意象结合老道熟练的张氏叙事手法,成就了张爱玲在中国文坛上的早期辉煌。
作者在美国期间几次对其改写改译,在文学创作史上也是少见的现象,由此可窥见张爱玲对自己的成名作寄予厚望,期待借此进军美国文学市场。
张爱玲以《金锁记》为蓝本,进行了三次英文创作。第一次英文稿《粉泪》投稿被拒,对张爱玲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据此改写的英文小说《北地胭脂》兜兜转转,于1967年由英国Cassell书局正式出版,打入英文文学市场,却反应平平;后应夏志清的邀请,张爱玲再次忠实于原著,创作了英文直译本TheGoldenCangue并于1971年收录于夏志清编写的Twentieth-centuryChineseStories一书。该书被列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材,然而学生普遍反映该小说“人物性格病态,令人作呕”,让人无法接受[4]。由于直译本受众过小,无法反映美国文学市场的接受程度,本文选取受众较为广泛的改译本《北地胭脂》和原著《金锁记》进行对比,研究张爱玲在改译过程中对原著的重构与再现,揭示她为迎合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期待的同时试图保留原著中的中国文化所做出的尝试,并探究这一尝试背后的原因。
2 《北地胭脂》对原著《金锁记》的改写
2.1 中国文化意象的消解与重构
《金锁记》一书譬喻巧妙,意象丰富,充满了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元素。书名以“金锁”这一意象形象地隐喻了束缚主人公曹七巧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枷锁,预示了她在受害的同时寻求宣泄与报复,最终葬送了自己和子女的悲剧命运。“金锁”这一充满中国文化色彩的意象,凸显了小说主题,暗示了冲突鲜明的小说情节,渲染了小说极具苍凉感的悲剧气氛。
除此以外,《金锁记》中贯穿始终的“月亮”意象,在小说主题的渲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小说以“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开始,又以“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结束,采用了中国白话小说首尾呼应的写法,荡气回肠。月亮意象无处不在,在书写中伴随着浓墨重彩的风景描写,深刻且形象地衬托了人物的精神和心理状态。
隔着玻璃窗望出去,影影绰绰乌云里有个月亮,一搭黑,一搭白,像个戏剧化的狰狞脸谱。一点,一点,月亮缓缓地从云里出来了,黑云底下透出一线炯炯的光,是面具底下的眼睛。[5]111
此处的月亮化身为狰狞恐怖的七巧,用她“面具下的眼睛”窥探与掌控儿子的生活。黑白强烈对比下的戏剧化脸谱,营造了月亮阴森恐怖的形象,正如七巧正用她扭曲变异的心理窥探隐私,破坏儿子的生活,最终逼死儿媳,狂躁而阴郁。
教学方法的多样性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启发学生的学习思维.可以组织学生学习国内外的一些数学大家做专题演讲,介绍自己在搜集学习的过程中受到了哪些启发,从大师身上学到了什么,自己将来要如何做等内容.
书中极具中国色彩的主题与意象书写过于本土化,大量绮丽的中文表达在翻译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失去了特色,甚至造成英语读者的疏离感。张爱玲在译《金锁记》一书时曾写信给夏志清说,“译得极不满意,一开始就苦于没有十九世纪英文小说的笔调,表达不出时代气氛”[6]72。
改译本的书名采用了全新的中国文化意象“北地胭脂”。书中扉页部分这样解题:“The face powder of southern dynasties, The rouge of the northern lands.Chinese expression for the beauties of the country, probably seventh century.”[7]“南朝金粉,北地胭脂。大约七世纪时,中文指国之美人”。书名中采用“北地胭脂”的意象至少有两重含义:一指主人公银娣貌美;二指主人公银娣这个出身贫寒的上海人嫁入来自北京的姚家后,按北方氏族大家的规矩浓抹胭脂,遵循夫家规矩,为挤进上层社会牺牲感情、迷失自我的人性蜕变[8]209。新的书名完全摆脱了之前书名抑郁阴沉的气氛,“枷锁”这一喻意被消解,以“胭脂”这一更易为英语世界接受的中国文化意象代之,另立新意,试图唤起读者对娇媚女性形象的期待,同时也暗喻了书中叙述的一个下层女子进入上层社会的辛酸奋斗史。这样的改变试图顺应上世纪60年代美国女权运动的潮流来迎合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更能迎合大众的审美意向。自此,小说的立意与主旨已发生了巨大改变与重构。
同时,小说当中运用了大量的中国式的意象和夸张的色彩对照,再加上大量的具有张氏特色的无主句式与词汇表达,若直译成英文,不可避免地会怪异而笨拙。兼顾到英语文化的规范,《北地胭脂》删减了大量的用以凸显主人公极端心理的乖张的月亮意象,缓和了原本抑郁紧张的气氛;语言表达上则舍弃了原著常用的跳跃的无主句结构,代以流畅的符合英文文法的句式表达,力图符合英语读者的思维习惯,更易于英语读者理解与接受。
2.2 叙事手法的转变
《金锁记》以姜家分家事件为分水岭,将小说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写主人公曹七巧在姜家被歧视被压迫的故事;后半部则着重描述曹七巧在丈夫和婆婆去世后分家,在长期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压力下人性扭曲,在子女身上实施疯狂报复的行为,最终导致了一家人的悲剧命运。在叙事手法上,张爱玲对故事情节发生的时间操控灵活,时间在张爱玲的笔下具有极大的可塑性。
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5]99
镜中景象变换,时间一下过了十年,不着痕迹地跳过了丈夫和老太太过世的情节,直接过渡到分家时哭闹争夺家产的高潮描写。故事叙事节奏变得紧凑而具有张力,衔接自然,叙事技巧精熟,被诸多评论家赞誉。此外,全书多次以“缩影”的电影手法集中描述矛盾冲突,从帮儿子娶亲到逼死儿媳,从帮女儿裹脚到处心积虑拆散女儿婚事,叙事界限分明,节略法的巧妙运用加大了故事张力,加快了叙事节奏,对比鲜明、跳跃性强,塑造了乖张的人物形象,气氛渲染得毛骨悚然,令人窒息。小说中对于情节跳跃和节略的处理,往往借助具有古典中国文化特色的意象,以大段复杂的无主句式来实现。在翻译成英文时,过于中式的文化意象和语言表达,脱离了读者的认知域,为原著的再现制造障碍,给英语读者造成了疏离感,“令人反感,觉得肮脏卑鄙”[6]10。
正因为这样的教训,张爱玲在将《金锁记》改写为《北地胭脂》时,为了迎合英语读者的文化期待,一改跳跃的叙事格调,以线性的叙事手法,将主人公银娣出嫁前在娘家的生活、到嫁入姚家后被歧视、再到分家后折磨家人直至暮年将尽的人生经历,按时间的发展顺序娓娓道来。这种按照事件发生顺序展开的线性叙事方式,普遍适合西方读者的思维逻辑,同时也大大缓和了跳跃性叙事所营造的紧张气氛,为英语读者接受主人公的乖张性格与行为方式进行了铺垫,预留了空间。
2.3 人物形象的重构
《北地胭脂》一书中,张爱玲在塑造主人公银娣形象的过程中显然经过深思熟虑,谨慎地避免重复原著主人公曹七巧癫狂的疯妇形象,用容貌和行为的改变为银娣这一形象争取读者认同,拉近读者距离。“胭脂”一词多为中国古典美人的代名词,用于题名暗示了银娣的貌美,提高了读者的期待。书中增加了对银娣的外貌衣饰的描写,塑造了比七巧貌美的女性形象。“文学里美人自怜自艾,只要行为检点,并不惹人嫌厌。”[8]213银娣是南方人,嫁入姚家后不得不摒弃南方的生活习俗,浓妆艳抹,遵循北方夫家的规矩,逐渐稳固自己在夫家的地位,由“南朝金粉”转化为“北方胭脂”。小说原著叙述的中国女性形象被改写成为竭力跨越地域和阶级差异、奋力跻身于上层社会的下层阶级女子,这一形象的转变迎合了当时美国社会的女权运动思潮,旨在争取读者对主人公的认同。在情节设计上,张爱玲着意删减了女儿长安这一角色,抹去原著中七巧逼迫长安缠足、诱骗长安吸食鸦片并破坏女儿婚事的情节,将七巧窥探儿子隐私逼死儿媳芝寿改成银娣为难儿媳致使儿媳患肺痨而死,缓和了原来剑拔弩张的叙事风格,淡化了凸显主人公扭曲的性格的情节设计。书中在情节上的改动为主人公性格上的蜕变提供了合理的解释,竭力避免英语读者对人物的反感。主人公形象也从原著中难以忍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变为软弱的、压抑的普通人,人物设定不再变得那么让人难以忍受。
值得一提的是,原著《金锁记》中几乎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名字,七巧的妯娌玳珍和兰芝,三爷姜季泽,儿子长白,女儿长安,儿媳芝寿等等。大量中文人名和纷繁复杂的人物关系势必会造成英语读者的阅读困难,望而生畏。《北地胭脂》对这个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除了几个关键人物银娣(Yindi)、儿子玉熹(Yensheng)等,其他出场人物均以家庭关系称谓代替,如大爷、二爷、三爷(Big Master,Second Master,Third Master),妯娌简化为大奶奶和三奶奶(Big Mistress,Third Mistress)。人物姓名的改动保留了中国大家庭称谓的特色,同时大大减少了阅读障碍,更符合英文读者的阅读习惯。
尽管张爱玲在英文改译本《北地胭脂》创作中作出诸多调整以迎合主流市场,美国文学界似乎并不买账。张爱玲至少投过三家出版社,却未能出版成功,最终几经波折在英国出版,也未能达到她的期望,市场反应平平。
3 游走在边缘的中国文化情结
为在英语文学市场立足,符合西方读者视野,张爱玲的后期文学创作需要顺应美国社会主流文化规范,然而为满足西方读者对中国世界的好奇心,她的创作又必须倚仗自身的中国文化底蕴,以中国文化作为创作根基,防止个性缺失,可谓游走于东西方文化边缘,举步维艰。
3.1 文化差异
《金锁记》创作成功的首要原因在于故事来源的真实性。其故事、人物脱胎于“李鸿章次子李经述的家中”[9]。李府多彩的大家庭生活为张提供了极佳的写作素材和熟悉的写作场景,书中讲述的是出身贫寒的单纯女孩如何被父权和礼教步步蚕食、人性蜕变的故事。尽管《北地胭脂》经过大幅度改写,然而赖以生存的故事本质源于陈旧的中国封建氏族家庭,无法动摇。故事中巨大的东西方文化差异使得西方读者无法理解中国封建家庭的礼法制度和繁复的人际关系,无法理解封建礼教对于女性的迫害。缺乏这一文化背景,自然无法接受主人公这样饱受压迫导致心理变态的人物形象。这种灰暗的故事情节既缺乏浪漫的爱情元素,又无法体现文化交流汇融大背景下的东西方文化碰撞,也不迎合当时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阅读兴趣。由于省略了诸多人名,人物以家庭关系称谓登场,对人物关系进行详细的解释不可避免;加上书中特意添加了关于中国传统情调与习俗的描写,尽可能为英语读者扫清文化意识上的障碍,尽管可以一时迎合西方读者的猎奇心理,然而冗长的细节描写会打乱故事主线的叙事节奏。这样的文本,即使具有中国背景的西方读者也难以理解,更何况面临的是大众读者。由于当时的美国文学市场致力于宣扬表达细腻伤感的新文艺腔,张爱玲小说中塑造的这样的人物形象,性格乖张,小说的宗旨又致力于人性及社会道德的探索,显然无法迎合出版机构的口味,因为“我们曾经出过几本日本小说,都是微妙的,不像这样squalid”[6]10,市场反应冷淡也就不足为奇。
3.2 创作心态的妥协与不甘
《北地胭脂》里,张爱玲在对情节、人物大幅度改写之余,试图弥补中英文差异造成的语言鸿沟,甚至采用流畅的英文句法来替换先前碎片化的语言表达,在降低自身文化心态的同时迎合读者市场,却也同时失去了原著中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以及极具特色的古典中国文化情结。在经历屡屡碰壁之后,作者思想与艺术风格也随着改变,经由早期的华丽绚烂过渡到后期的平实自然,最终不得不妥协于读者期待。
迎合西方读者的口味几乎是所有华裔作家的共同特征,然而“流散海外的境遇并未改变他们作为中国人的自我认同,异己的环境反而更能强化他们的文化回归意识”[10]。作为第一代华裔作家,张爱玲以《北地胭脂》小说中银娣出身的地域差异和她进退两难的结局,影射的是自身身处异域打入美国主流社会遭受挫败的两难境地。在原著中国文化情结消解的同时,作者并未全盘摒弃赖以生存的中国文化,在改写过程中试图对中国文化进行重构,继续以英文书写中国旧事,却同时无法避免地将自己排除在当时英语文学主流之外。
4 结语
张爱玲在美国的创作生涯一直身处文学创作的困窘之中。她寄望于成名作《金锁记》,不断对文本中的主旨、情节乃至独具一格的语言描写删减润色,试图迎合当时英文读者对于中国情节的期待;却踌躇于对自我中国情结认知的执着,试图最大限度地复现文本的主题信息和写作意图,保留原著中独特的中国意象。几番再创作的历程中,她的作品始终徘徊于西方主流文化与中国文化边缘之间,再未重现早年的事业高峰,她的文学创作放低姿态,由纷繁的花团锦簇回归于微冷的平淡苍凉。